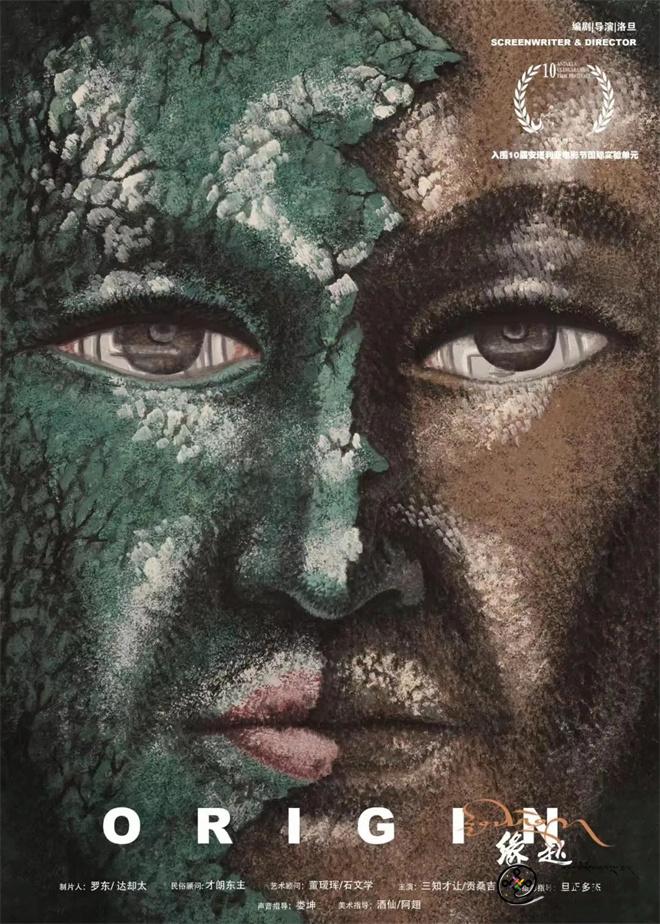еңЁдәәзұ»еӯҰз ”з©¶зҡ„з”°йҮҺи°ғжҹҘдёӯпјҢйғӯеҮҖжңҖеҲқеҸ‘зҺ°дәҶдёҖдёӘзңӢдёҚи§Ғзҡ„д№Ўжқ‘пјҢиҝҷжҝҖеҸ‘дәҶд»–еҜ№еҪұеғҸжқғеҲ©зҡ„ж·ұе…ҘжҖқиҖғпјҢ并дҝғдҪҝд»–еҚҒеҮ е№ҙиҮҙеҠӣдәҺжқ‘ж°‘еҪұеғҸзҡ„еҸӮдёҺејҸиЎҢеҠЁгҖӮиҝҷз§ҚиЎҢеҠЁе’Ңз ”з©¶пјҢжңҖз»Ҳд№ҹи®©д»–еҸ—зӣҠеҢӘжө…пјҢдҪҝд»–еҫ—д»Ҙд»Һ“и§Јж”ҫиҖ…”зҡ„зңје…үдёӯи§Ји„ұеҮәжқҘпјҢиҺ·еҫ—дәҶ“и§ӮеҜҹиҖ…”зҡ„иҮӘз”ұгҖӮ
дә‘еҚ—д№Ўжқ‘еҪұеғҸеӣўйҳҹзҡ„йғЁеҲҶжҲҗе‘ҳпјҲд»Һе·ҰиҮіеҸідёәпјүпјҡжқЁжҳҶгҖҒзҺӢеҝ иҚЈпјҲиӢ—ж—ҸпјүгҖҒеӯҷиҜәдёғжһ—пјҲи—Ҹж—ҸпјүгҖҒйҳҝжҙӣпјҲи—Ҹж—ҸпјүгҖҒж—әжүҺпјҲи—Ҹж—ҸпјүгҖҒйғӯеҮҖгҖҒйҳҝзүӣпјҲи—Ҹж—ҸпјүгҖӮпјҲж‘„еҪұ/е’ҢжёҠпјү
гҖҖгҖҖеңЁд»ҺдәӢдәәзұ»еӯҰз”°йҮҺи°ғжҹҘ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ә‘еҚ—зңҒ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з ”究е‘ҳйғӯеҮҖз»Ҹеёёзў°еҲ°еҪ“ең°жқ‘ж°‘жҸҗеҮәиҝҷж ·зҡ„иҰҒжұӮпјҡ“и®©жҲ‘д№ҹжӢҚдёҖжӢҚпјҒ”еҗҺжқҘд»–еҸ‘зҺ°пјҢжңҖ让他们е…ҙеҘӢзҡ„пјҢжӯЈжҳҜйӮЈдәӣеҸҚжҳ 他们з”ҹжҙ»зҡ„зәӘеҪ•зүҮгҖӮ
гҖҖгҖҖйғӯеҮҖ1996е№ҙејҖе§ӢжҺҘи§ҰеҲ°зәӘеҪ•зүҮпјҢжӯӨеүҚдёҖзӣҙеңЁдә‘еҚ—гҖҒиҘҝи—Ҹд»ҺдәӢдәәзұ»еӯҰз ”з©¶гҖӮеҗҢе№ҙпјҢеӣ дёәеҸӮеҠ дә‘еҚ—з”өи§ҶеҸ°зҡ„ж°‘й—ҙиүәжңҜжӢҚж‘„и®ЎеҲ’пјҢйғӯеҮҖе’ҢйЎ№зӣ®з»„жҲҗе‘ҳејҖе§ӢжҺҘи§ҰзәӘеҪ•зүҮеҲ¶дҪңпјҢ并жҲҗз«ӢдәҶ“azaraеҪұеғҸе·ҘдҪңз«ҷ”гҖӮ
гҖҖгҖҖ2000е№ҙеҲқпјҢ他们еңЁдә‘еҚ—зңҒ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жҲҗз«ӢдәҶзҷҪзҺӣеұұең°ж–ҮеҢ–з ”з©¶дёӯеҝғпјҢдёҖдёӘдё»иҰҒзҡ„йЎ№зӣ®е°ұжҳҜејҖеұ•“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зҡ„е°қиҜ•пјҢйј“еҠұеҪ“ең°дәәжӢҝиө·ж‘„еғҸжңәи®°еҪ•е®¶д№Ўзҡ„ж–ҮеҢ–гҖӮйғӯеҮҖжҳҜиҜҘйЎ№зӣ®зҡ„дё»жҢҒдәәпјҢд№ҹжҳҜеҸӮдёҺиҖ…е’Ңи§ҒиҜҒиҖ…гҖӮ
гҖҖгҖҖ“еҪұеғҸеә”еҪ“з»ҷдәҲж°‘дј—дёҖз§ҚеЈ°йҹіпјҢиҖҢдёҚеҸӘжҳҜдёҖз§ҚдҝЎжҒҜгҖӮ”еҹәдәҺиҝҷж ·зҡ„и®ӨиҜҶпјҢдёҖзҫӨе…іеҝғзӨҫеҢәе»әи®ҫзҡ„дә‘еҚ—еӯҰиҖ…еңЁиҘҝйғЁеҒҸеғ»зҡ„д№Ўжқ‘ејҖеұ•“зӨҫеҢәеҪұи§Ҷж•ҷиӮІ”зҡ„еҸӮдёҺжҖ§з ”究пјҢеё®еҠ©еҪ“ең°жқ‘ж°‘еҲ©з”ЁеҪұеғҸе·Ҙе…·иЎЁиҫҫиҮӘе·ұзҡ„и§ӮзӮ№е’Ңж„Ҹи§ҒпјҢ并еҲ©з”ЁиҝҷдәӣдҪңе“ҒпјҢиҝӣиЎҢжң¬еңҹж–ҮеҢ–зҡ„ж•ҷиӮІдёҺдј жүҝжҙ»еҠЁ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еҒҡиҝҷдәӣйЎ№зӣ®зҡ„ж—¶еҖҷпјҢз»Ҹеёёжңүдәә问他们пјҡ“дҪ 们дёәд»Җд№ҲиҰҒжҠҠеҪұеғҸиҝҷз§ҚеӨ–жқҘзҡ„дёңиҘҝеј•е…Ҙжқ‘йҮҢпјҢж”№еҸҳеҪ“ең°дәәзҡ„з”ҹжҙ»пјҹ”
гҖҖгҖҖйғӯеҮҖз»ҷеҮәзҡ„жҳҜдёҖдёӘжҖҺж ·зҡ„зӯ”жЎҲе‘ўпјҹ гҖҖгҖҖ
зңӢдёҚи§Ғзҡ„иҘҝйғЁд№Ўжқ‘
гҖҖгҖҖе…¶е®һж—©еңЁиҜҫйўҳз»„еҲ°жқҘд№ӢеүҚпјҢзҺ°д»ЈеҪұеғҸж—©е°ұжё—е…ҘдәҶеҪ“ең°зӨҫеҢәз”ҹжҙ»гҖӮ
гҖҖгҖҖеӯҰиҖ…们еңЁеҫҲеӨҡд№Ўжқ‘зӣ®зқ№дәҶиҝҷиҲ¬жҷҜиұЎпјҡжҜҸеӨ©жҷҡдёҠйғҪжңүдәәиҒҡйӣҶеңЁдёҖжҲ·дәә家е ӮеұӢйҮҢзңӢз”өи§ҶгҖӮеңЁдёҖдёӘзҘһеұұи„ҡдёӢзҡ„и—Ҹж—Ҹжқ‘еә„пјҢжӢҘжңүз”өи§Ҷе’ҢVCDж”ҫжҳ жңәзҡ„жҙ»дҪӣ家жҲҗдёәе…Ёжқ‘дәәжҷҡдёҠиҒҡдјҡзҡ„еңәжүҖгҖӮеӨ§е®¶д»Һеҗғе®ҢжҷҡйҘӯпјҢдёҖзӣҙзңӢеҲ°еӨңйҮҢеҚҒдёҖдәҢзӮ№пјҢжңүзҡ„дәәиҫ№зңӢиҫ№е–қй…’гҖҒиҒҠеӨ©пјҢжңүзҡ„з”ҡиҮіеҪ“еңәзқЎзқҖ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иҜҫйўҳз»„жҲҗе‘ҳгҖҒдә‘еҚ—зңҒ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еӯҰиҖ…з« еҝ дә‘пјҲзҶҷз»•жЎ‘жіўпјүж·ұе…Ҙи°ғжҹҘиҢЁдёӯжқ‘еҪұеғҸеҺҶеҸІеҸ‘зҺ°пјҡиҢЁдёӯдәәжҺҘи§ҰеҪұеғҸжңҖж—©еҸҜд»ҘиҝҪжәҜеҲ°1953е№ҙеҲқпјҢжқ‘йҮҢеҮ дҪҚиҖҒдәәиҝҳи®°еҫ—пјҢ他们еҚҒжқҘеІҒж—¶пјҢеҺҝйҮҢжңүдёӘж”ҫжҳ йҳҹпјҢ第дёҖж¬ЎжқҘжқ‘йҮҢж—¶пјҢжқ‘йҮҢдәәйғҪеҺ»зңӢзЁҖеҘҮпјҢи®°еҫ—ж”ҫзҡ„第дёҖйғЁеҪұзүҮжҳҜгҖҠиҚүеҺҹдёҠзҡ„дәә们гҖӢпјҢеҪ“ж—¶жқ‘йҮҢжҮӮжұүиҜӯзҡ„дәәжһҒе°‘пјҢж”ҫжҳ зҡ„ж—¶еҖҷпјҢдёӨдҪҚеёҲеӮ…иҪ®жөҒжҠҠеҪұзүҮйҮҢзҡ„еҜ№иҜқеңЁиҜқзӯ’йҮҢи§ЈйҮҠз»ҷеӨ§е®¶еҗ¬гҖӮ
гҖҖгҖҖдёҠдё–зәӘ90е№ҙд»Јд»ҘеҗҺпјҢйҡҸзқҖз”өи§ҶжңәгҖҒеҪ•еғҸжңәгҖҒVCDзҡ„жҷ®еҸҠпјҢжқҘиҮӘдё»жөҒжё йҒ“пјҲз”өи§ҶеҸ°гҖҒзӣ—зүҲе…үзўҹпјүзҡ„дә§е“Ғжё—е…ҘеҲ°иҝҷдёӘжқ‘еә„гҖӮ“иҝҷдәӣдә§е“Ғж—ўеұ•зӨәдәҶеӨ–йғЁдё–з•Ңзҡ„еҘҮеҰҷпјҢи®©еӨ§еӨҡж•°жІЎеҮәиҝҮиҝңй—Ёзҡ„жқ‘ж°‘й•ҝдәҶи§ҒиҜҶпјҢд№ҹжҸҗдҫӣдәҶдёҖз§ҚзҺ°д»Јзү©иҙЁз”ҹжҙ»зҡ„е№»иұЎгҖӮдҪҶе…¶дёӯжүҖеҢ…еҗ«зҡ„д»·еҖји§ӮдёҺз”ҹжҙ»еҪўжҖҒпјҢйғҪиҝңиҝңи„ұзҰ»еҪ“ең°ж°‘дј—зҡ„дј з»ҹгҖӮ”йғӯеҮҖиҜҙгҖӮ
еңЁйғӯеҮҖзңӢжқҘпјҢиҝҷдёӘең°еҢәзҡ„ж°‘дј—дёҖзӣҙеңЁеҸ—еҲ°еҪұеғҸзҡ„зҶҸйҷ¶пјҢе……еҪ“дҝЎжҒҜзҡ„иў«еҠЁжҺҘеҸ—иҖ…пјҢеҚҙд»ҺжқҘжІЎжңүйҖҡиҝҮеҪұеғҸеҸ‘иЎЁзңӢжі•зҡ„жқғеҲ©гҖӮеҪұеғҸеҜ№дәҺ他们пјҢд»…д»…жҳҜдёҖз§ҚдҝЎжҒҜ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дёҖз§ҚеЈ°йҹігҖӮе°ұиҝһиҜҫйўҳз»„иҮӘе·ұжүҖжӢҚж‘„зҡ„еҪұеғҸпјҢд№ҹеҗҢж ·еёҰжңүеӨ–жқҘиҖ…зҡ„и§Ҷи§’пјҢеҫҲйҡҫж·ұе…Ҙең°жҸӯзӨәзӨҫеҢәе·ҘиүәгҖҒдҝЎд»°гҖҒз”ҹдә§жҙ»еҠЁзҡ„з»ҶиҠӮпјҢжӣҙйҡҫеҮҶзЎ®ең°жҚ•жҚүжқ‘ж°‘зҡ„жҖқжғіе’ҢиЎҢдёәеҸҳеҢ–гҖӮд№Ўжқ‘зҡ„ж°‘дј—пјҢ他们зҡ„з”ҹжҙ»жҲҗдёәеҲ«дәәзҡ„еҪұеғҸиө„жәҗпјҢиҖҢ他们йҷӨдәҶиў«еҠЁең°и§ӮзңӢпјҢеҫҲе°‘иғҪеҲ©з”ЁеҪұеғҸеҸ‘еЈ°пјҢеҲ©з”ЁеҪұеғҸдёәиҮӘе·ұжңҚеҠЎгҖӮ
гҖҖгҖҖ“еҪұеғҸеә”иҜҘдј иҫҫи°Ғзҡ„еЈ°йҹіпјҢдёәи°ҒжңҚеҠЎпјҹ”иҝҷжҳҜйғӯеҮҖдёҠдё–зәӘ90е№ҙд»Је°ұжҸҗеҮәзҡ„дёҖдёӘй—®йўҳгҖӮ гҖҖ
е°Ҷж‘„еғҸжңәдәӨз»ҷеҶңж°‘
гҖҖгҖҖ1999е№ҙпјҢйғӯеҮҖжңүжңәдјҡеҸӮеҠ дёҖдәӣзӨҫеҢәеҸ‘еұ•зҡ„еӣҪйҷ…йЎ№зӣ®пјҢ并д»ҺTNCгҖҒCBIKзӯүйқһж”ҝеәңз»„з»ҮйӮЈйҮҢжҺҘеҸ—дәҶеҸӮдёҺејҸз ”з©¶зҡ„еҹ№и®ӯпјҢд»ҺдәӢдәҶеҫҲеӨҡе®һйҷ…и°ғжҹҘгҖӮиҝҷжңҹй—ҙпјҢд»–жүҚд»ҺзҗҶи®әдёҠжҖқиҖғ“дёәи°ҒжӢҚж‘„пјҢжӢҚз»ҷи°ҒзңӢ”зҡ„й—®йўҳгҖӮ
2005е№ҙпјҢйҰҷж јйҮҢжӢүеҺҝжұӨе Ҷжқ‘зҡ„еҲ¶йҷ¶иүәдәәеӯҷиҜәдёғжһ—еңЁжӢҚж‘„жқ‘ж°‘иҒҡдјҡ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дёҺж°‘й—ҙNGOжҺҘи§Ұ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дәҶи§ЈеҲ°1991е№ҙз”ұдә‘еҚ—зңҒз”ҹиӮІеҒҘеә·з ”究дјҡдё»жҢҒгҖҒзҰҸзү№еҹәйҮ‘дјҡиөһеҠ©зҡ„“еҰҮеҘіз”ҹиӮІеҚ«з”ҹдёҺеҸ‘еұ•”йЎ№зӣ®пјҢеё®еҠ©дә‘еҚ—53дҪҚеҶңжқ‘еҰҮеҘіиҮӘе·ұжӢҚж‘„еҘ№д»¬зҡ„з”ҹжҙ»еңәжҷҜпјҢз”Ёз…§зүҮж•…дәӢиЎЁиҫҫеҘ№д»¬зҡ„иҰҒжұӮпјҢеҪұе“Қз”ҹиӮІеҒҘеә·зҡ„еҶізӯ–гҖӮ“иҝҷеҗҜеҸ‘дәҶжҲ‘们ејҖе§Ӣи®ӨзңҹжҖқиҖғеҪұеғҸдёҺеҸӮдёҺејҸж•ҷиӮІзҡ„зӣёдә’е…ізі»гҖӮ”
гҖҖгҖҖйғӯеҮҖжӣҫи·ҹзқҖжҳҶжҳҺйҷ„иҝ‘зҡ„еӨ§иҠұиӢ—еӯҰдәҶдёҖж®өж—¶й—ҙиӢ—иҜӯиӢ—ж–ҮпјҢиҷҪ然没жңүеӯҰеҘҪпјҢеҚҙиһҚе…Ҙ他们зҡ„иҜӯиЁҖжғ…еўғдёӯпјҢдҪ“йӘҢеҲ°дәҶйҷҢз”ҹзҡ„жҖқжғіиЎЁиҫҫж–№ејҸгҖӮ“еңЁеӯҰжңҜзҡ„е’ҢNGOеңҲеӯҗйҮҢпјҢ专家жңүж—¶дјҡжү®жј”и§Јж”ҫиҖ…зҡ„и§’иүІгҖӮеҸҜеңЁжң¬еңҹзҡ„иҜӯеўғдёӯпјҢжҲ‘们иҝҷдәӣеӨ–жқҘзҡ„‘专家’еҸҳеҫ—жңүзӮ№‘ејұеҠҝ’пјҢиҜҙиҜқдёҚеҶҚдҝЎеҝғж»Ўж»ЎпјҢз”ҡиҮіж—¶иҖҢдё§еӨұдәҶжј”иҜҙзҡ„жңәдјҡпјҢжҲҗдәҶж—Ғеҗ¬иҖ…гҖӮ”
гҖҖгҖҖ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дёҖдёӘиў«з§°дёә“DVиҝҗеҠЁ”зҡ„зәӘеҪ•еҪұеғҸйЈҺжҪ®еңЁдёӯеӣҪзҡ„еҹҺеёӮйқ’е№ҙдёӯжөҒиЎҢиө·жқҘгҖӮи®ёеӨҡдәәжӢҝиө·е®¶еәӯз”Ёж•°з Ғж‘„еғҸжңәпјҢеҺ»жӢҚж‘„д»ҘеүҚдёҚдёәдәәе…іжіЁзҡ„иҫ№зјҳдәәзҫӨгҖӮдҪңе“ҒиҷҪ然жңүзҡ„зІ—зіҷпјҢжңүзҡ„ж ҮжҰңж—¶е°ҡпјҢдҪҶе…¶дёӯжңҖеҘҪзҡ„йғЁеҲҶпјҢеҚҙеҜ№еҪұеғҸзҡ„жқғеҲ©жҸҗеҮәдәҶз–‘й—®пјҢиҖҢдё”жҳҺзЎ®ең°дё»еј еҪұеғҸзҡ„ж°‘й—ҙеҢ–пјҢиҮҙеҠӣдәҺдёӘдәәзҡ„еҪұеғҸиЎЁиҫҫгҖӮиҝҷеҜ№дәҺйғӯеҮҖж— з–‘е…·жңүеҗҜиҝӘзҡ„ж„Ҹд№үпјҡ“жҲ‘们зҗҶи§Јзҡ„ж°‘й—ҙпјҢеҢ…жӢ¬дәҶд№Ўжқ‘зҡ„дёӘдәәе’ҢзӨҫеҢәпјҢе°ҶеҪұеғҸеҲ¶дҪңзҡ„жқғеҲ©пјҢд»ҘеҸҠеҲ©з”ЁеҪұеғҸејҖеұ•е…¬дј—ж•ҷиӮІзҡ„жқғеҲ©дәӨеҲ°д»–们зҡ„жүӢйҮҢпјҢеӨҡж ·еҢ–зҡ„еЈ°йҹідҫҝеңЁеұҸ幕дёҠеҮәзҺ°дәҶгҖӮ”
2000е№ҙеҲ°2003е№ҙпјҢжқҘиҮӘдә‘еҚ—зңҒзӨҫдјҡ科еӯҰйҷўгҖҒдә‘еҚ—еёҲиҢғеӨ§еӯҰгҖҒдә‘еҚ—ж°‘ж—ҸеӨ§еӯҰгҖҒиҝӘеәҶи—Ҹж—ҸиҮӘжІ»е·һзҡ„дёҖзҫӨеҝ—еҗҢйҒ“еҗҲиҖ…пјҢеңЁзҰҸзү№еҹәйҮ‘дјҡиө„еҠ©дёӢпјҢеңЁдә‘еҚ—и—ҸеҢәејҖе§Ӣе®һж–Ҫ“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ж•ҷиӮІ”йЎ№зӣ®гҖӮжӯӨеҗҺеҚҒеӨҡе№ҙпјҢ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еңЁеҗ„ең°еҸ‘иҠҪз”ҹй•ҝпјҢеңЁд№Ўжқ‘д№ӢзңјгҖҒеҚЎз“Ұж јеҚҡж–ҮеҢ–зӨҫгҖҒйҰҷжёҜзӨҫеҢәдјҷдјҙгҖҒиҚүеңәең°е·ҘдҪңз«ҷгҖҒе№ҙдҝқзҺүеҲҷз”ҹжҖҒзҺҜеўғдҝқжҠӨеҚҸдјҡгҖҒйӣ…е®үеёӮд№Ўжқ‘ж‘„еҪұеҚҸдјҡгҖҒдёҠжө·зҲұжӢҚе·ҘиүәеҪұеғҸеҸ‘еұ•дёӯеҝғзӯүжңәжһ„жҺЁеҠЁдёӢпјҢ蔓延еҲ°дә‘еҚ—гҖҒеӣӣе·қгҖҒйқ’жө·гҖҒеұұиҘҝгҖҒиҙөе·һгҖҒжІіеҢ—гҖҒе№ҝиҘҝе’ҢдёҠжө·пјҢдёҚд»…еҮәдәҶдёҖжү№дҪңе“ҒпјҢеҹ№е…»дәҶдёҖжү№дҪңиҖ…пјҢиҖҢдё”иҝҳеҮәзҺ°дәҶж‘©жўӯдәәе’Ңи—Ҹж°‘иҮӘе·ұдёҫеҠһзҡ„жң¬еңҹеҪұеғҸеұ•гҖӮ
гҖҖгҖҖ2009е№ҙпјҢеҢ—дә¬еӯҰиҖ…еҙ”еҚ«е№іеңЁжҳҶжҳҺеҸӮеҠ дәҶеҗҚеҸ«“дә‘д№ӢеҚ—”зҡ„ж°‘й—ҙзәӘеҪ•зүҮеҪұеғҸеұ•пјҢеңЁ“зәӘеҪ•еҪұеғҸдёҺд№Ўжқ‘зӨҫдјҡ”е…ідәҺ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зҡ„и®Ёи®әпјҢи®©еҘ№еҚ°иұЎйўҮж·ұгҖӮ
гҖҖгҖҖеҙ”еҚ«е№іеңЁдёҖзҜҮж–Үз« дёӯд»Ӣз»ҚдәҶйғӯеҮҖиҝҷдҪҚзҳҰеүҠиҖҢ笑зңҜзңҜзҡ„дә‘еҚ—еӯҰиҖ…пјҡ“йғӯе…Ҳз”ҹеёёе№ҙжқҘд»ҺдәӢдәәзұ»еӯҰз”°йҮҺи°ғжҹҘпјҢиҮӘе·ұжӢҚж‘„зәӘеҪ•зүҮ并主жҢҒиҝҮзӨҫеҢәж•ҷиӮІйЎ№зӣ®зҡ„зәӘеҪ•зүҮе·ҘдҪңеқҠпјҢжҳҜиҝҷдёӘйўҶеҹҹдёӯзҡ„зҺҮйЈҺж°”д№Ӣе…ҲиҖ…пјҢ并еҶҷеҫ—дёҖжүӢеҘҪж–Үз« гҖӮ他并дёҚжҖҘдәҺжҳҫзӨәиҮӘе·ұзҡ„и§ӮзӮ№дёҺеҠӣйҮҸпјҢе°Ҷ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зҡ„и®Ёи®әдё»жҢҒеҫ—ж—ўиҪ»жқҫеҸҲжңүиҠӮеҘҸгҖӮ” гҖҖгҖҖ
йҰҷж јйҮҢжӢүзҡ„е…ҲиЎҢиҖ…
гҖҖгҖҖ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пјҲеҗҺжқҘд№ҹеҸ«д№Ўжқ‘еҪұеғҸпјүд№ӢжүҖд»ҘеҸ‘жәҗдәҺдә‘еҚ—пјҢжҳҜеҜ№зҺ°е®һйҖјиҝ«зҡ„дёҖз§Қеӣһеә”гҖӮ
гҖҖгҖҖдә‘еҚ—и—ҸеҢәеҗ„ж°‘ж—Ҹеӣ еӨ–жқҘж–ҮеҢ–еҶІеҮ»иҖҢжҝҖеҸ‘зҡ„ж–ҮеҢ–и§үйҶ’пјҢдёәиҜҫйўҳз»„зҡ„йЎ№зӣ®еҘ е®ҡдәҶеҹәзЎҖгҖӮйғӯеҮҖ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дёӘйЎ№зӣ®е®һж–ҪиҝҮзЁӢдёӯе®Ңе–„дәҶеҜ№еҪұеғҸжқғеҲ©зҡ„жҖқиҖғе’Ңз ”з©¶гҖӮ
гҖҖгҖҖд№Ўжқ‘еҪұеғҸ第дёҖжү№еҸӮдёҺиҖ…жҳҜеҮ дҪҚдёҠдәҶе№ҙзәӘзҡ„дәәгҖӮ第дёҖдҪҚжҳҜиҝӘеәҶе·һйҰҷж јйҮҢжӢүеҺҝпјҲеҺҹеҗҚдёӯз”ёеҺҝпјүе°јиҘҝд№ЎжұӨе Ҷжқ‘зҡ„еӯҷиҜәдёғжһ—еёҲеӮ…гҖӮжұӨе Ҷжқ‘еҺҶеҸІдёҠе°ұд»ҘеҲ¶дҪңйҷ¶еҷЁй—»еҗҚпјҢиҖҢжқ‘йҮҢеӨ§еӨҡж•°йҷ¶еҢ йғҪжӣҫжӢңеӯҷеёҲеӮ…дёәеёҲгҖӮ1997е№ҙпјҢйғӯеҮҖи®ӨиҜҶдәҶеӯҷеёҲеӮ…пјҢж—¶дёҚж—¶еёҰзқҖж–°д№°зҡ„зҙўе°јж•°з Ғж‘„еғҸжңәеҲ°д»–家зҺ©пјҢжӢҚиҝҮ他们家з ҚжҹҙгҖҒиҝҮж–°е№ҙгҖҒиҪ¬зҘһеұұгҖҒеҗғзҒ«й”…зҡ„еңәжҷҜгҖӮ
гҖҖгҖҖйӮЈж—¶пјҢдё»жөҒзҡ„и§Ҷи§үж–ҮеҢ–е·Із»Ҹжё—йҖҸеҲ°иҝҷдёӘж·ұеұұйҮҢзҡ„и—Ҹж—Ҹжқ‘еә„пјҢжқ‘йҮҢжңү100еӨҡеҸ°з”өи§Ҷжңәе’Ң10еӨҡеҸ°VCDгҖӮжҜҸж¬Ўд»–жӢҚдәҶеҪ•еғҸпјҢеӯҷеёҲеӮ…йғҪиҰҒжұӮзңӢдёҖзңӢгҖӮ第дёҖд»Јж•°з Ғж‘„еғҸжңәжІЎжңүжҳҫзӨәеұҸпјҢеӯҷеёҲеӮ…е’Ңд»–зҡ„иҖҒдјҙгҖҒе„ҝеӯҗе’ҢеӯҷеӯҗеӯҷеҘіе°ұеӣҙеңЁзҒ«еЎҳиҫ№пјҢеҮ‘зқҖеҜ»еғҸеҷЁиҪ®жөҒи§ӮзңӢжӢҚзҡ„зҙ жқҗгҖӮ
гҖҖгҖҖйғӯеҮҖеңЁеӯҷеёҲеӮ…家е®ҢжҲҗдәҶиҮӘе·ұзҡ„第дёҖдёӘзҹӯзүҮ——гҖҠй»‘йҷ¶гҖӢгҖӮ
гҖҖгҖҖ2000е№ҙпјҢ“зҷҪзҺӣеұұең°ж–ҮеҢ–з ”з©¶дёӯеҝғ”жҲҗз«ӢеҗҺпјҢеңЁзҰҸзү№еҹәйҮ‘дјҡзҡ„иө„еҠ©дёӢпјҢйғӯеҮҖе’ҢдёҖдәӣеҪ“ең°еӯҰиҖ…ејҖе§Ӣе®һж–Ҫ“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ж•ҷиӮІ”и®ЎеҲ’гҖӮжӯӨеүҚйҖҡиҝҮеҸӮдёҺ“ж»ҮиҘҝеҢ—еӨ§жІіжөҒеҹҹдҝқжҠӨдёҺиЎҢеҠЁи®ЎеҲ’”пјҢиҝҷдәӣдәәзұ»еӯҰеӯҰиҖ…е’ҢеҪ“ең°и—Ҹж°‘е»әз«ӢдәҶиүҜеҘҪзҡ„е…ізі»гҖӮ
гҖҖгҖҖзҷҪзҺӣеұұең°йҖүе®ҡзҡ„第дёҖдёӘеҗҲдҪңиҖ…пјҢе°ұжҳҜ54еІҒзҡ„еӯҷеёҲеӮ…гҖӮйӮЈе№ҙ10жңҲзҡ„дёҖеӨ©пјҢйғӯеҮҖеёҰзқҖдёҖеҸ°зҙўе°је®¶з”Ёж‘„еғҸжңәеҺ»жұӨе ҶпјҢеҹ№и®ӯеӯҷеёҲеӮ…жҖҺд№Ҳж”Ҝи„ҡжһ¶пјҢжҖҺд№ҲејҖжңәпјҢ然еҗҺеӯҷеёҲеӮ…еқҗеҲ°зҶҹжӮүзҡ„дҪҚзҪ®дёҠпјҢжӢҚдәҶдёҖж®өиҮӘе·ұеҒҡйҷ¶зҪҗзҡ„еҪ•еғҸгҖӮжӯӨеҗҺпјҢж‘„еғҸжңәе°ұз•ҷеңЁеӯҷеёҲеӮ…家гҖӮд№ӢеҗҺдёӨдёӘжңҲпјҢеӯҷеёҲеӮ…е’Ңе„ҝеӯҗжҒ©дё»жӢҚдәҶдә”зӣҳеҪ•еғҸеёҰпјҢи®°еҪ•дәҶ他家еҒҡйҷ¶гҖҒзғ§йҷ¶зҡ„е…ЁиҝҮзЁӢгҖӮеҗҺжқҘпјҢиҝҷйғЁзәӘеҪ•зүҮгҖҠй»‘йҷ¶дәә家гҖӢеҒҡжҲҗдәҶе…үзўҹпјҢдҪңдёәзӨҫеҢәж•ҷиӮІзҡ„ж•ҷжқҗз»ҷжұӨе Ҷе°ҸеӯҰеӯҰз”ҹзңӢпјҢе°ҸеӯҰиҝҳеңЁеӯҷеёҲеӮ…е’ҢиҖҒеёҲ们зҡ„жҢҮеҜјдёӢејҖдәҶеҲ¶йҷ¶иҜҫгҖӮ
гҖҖгҖҖеҸӮеҠ “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ж•ҷиӮІ”жҙ»еҠЁзҡ„еҸҰеӨ–дёӨдҪҚжқ‘ж°‘жҳҜеҫ·й’ҰеҺҝиҢЁдёӯжқ‘66еІҒзҡ„еҲҳж–Үеўһе’Ң54еІҒзҡ„еҗҙе…¬йЎ¶гҖӮ
гҖҖгҖҖеҲҳж–Үеўһи—ҸеҗҚеҸ«жүҺиҘҝз»•зҷ»пјҢдјҡжұүгҖҒи—ҸгҖҒзҷҪгҖҒзәіиҘҝгҖҒеғіеғіж—ҸиҜӯпјҢи§Јж”ҫеүҚи·ҹжҙӢзү§еёҲеӯҰиҝҮжі•иҜӯгҖӮд»–еңЁжҳҶжҳҺиҜ»иҝҮеёҲиҢғпјҢж•ҷиҝҮдёүе№ҙдёӯеӯҰпјҢдёғе№ҙе°ҸеӯҰгҖӮеӣ з”ҹжҙ»зҗҗдәӢеңЁ“ж–Үйқ©”дёӯеҸ—еҲ°иҝ«е®іпјҢиў«ејҖйҷӨе…¬иҒҢпјҢд№ӢеҗҺеңЁиҢЁдёӯе°ҸеӯҰд»ЈиҜҫгҖӮд»–йҖҖдј‘еҗҺжІЎжңүе·Ҙиө„пјҢеҸӘжңүжҜҸжңҲ180е…ғзҡ„дҪҺдҝқпјҢдҪҶдҫқ然еҝ«д№җең°з”ҹжҙ»зқҖпјҢиҮӘе·ұз§Қең°пјҢзӣ–жҲҝеӯҗпјҢеҒҡи‘Ўиҗ„й…’пјҢдёәжӯ»еҺ»зҡ„дәәеҒҡжЈәжқҗпјҢеҸӮдёҺж•ҷе Ӯзҡ„з®ЎзҗҶпјҢиҝҳдјҡжӢүејҰеӯҗгҖҒжүӢйЈҺзҗҙпјҢеҗ№з¬ӣеӯҗпјҢжҳҜеӨҡжүҚеӨҡиүәзҡ„еҶңжқ‘ж–ҮеҢ–дәәгҖӮ
гҖҖгҖҖеҗҙе…¬йЎ¶д№ҹжҳҜеӨ©дё»ж•ҷеҫ’пјҢжҗһ科жҠҖиҮҙеҜҢпјҢж•ўжғіж•ўе№ІпјҢиў«иҜ„дёәеҺҝйҮҢзҡ„иғҪжүӢгҖӮ
гҖҖгҖҖдёӨдҪҚиҖҒдәәж—ўз»ҙжҠӨзқҖдёҖзҷҫеӨҡе№ҙеүҚдј е…Ҙзҡ„еӨ©дё»ж•ҷдҝЎд»°пјҢеҸҲдј жүҝдәҶжі•еӣҪдәәз•ҷдёӢзҡ„й…ҝй…’е·ҘиүәгҖӮ他们еҸҲеңЁз« еҝ дә‘зҡ„жҢҮеҜјдёӢеӯҰдјҡдәҶжӢҚеҪ•еғҸгҖӮдёӨдәәжӢҚж‘„зҡ„еҪұзүҮйғҪе’ҢиҮӘе·ұзҡ„з”ҹжҙ»еҜҶеҲҮзӣёе…іпјҢеҲҳж–ҮеўһжӢҚдәҶгҖҠиҢЁдёӯеңЈиҜһеӨңгҖӢпјҢеҗҙе…¬йЎ¶е’Ңе„ҝеӯҗзәўжҳҹжӢҚдәҶгҖҠиҢЁдёӯзәўй…’гҖӢгҖӮиҝҷдёӨйғЁзүҮеӯҗеҗҺжқҘдҪңдёәзӨҫеҢәж•ҷиӮІзҡ„ж•ҷжқҗпјҢж”ҫз»ҷиҢЁдёӯе°ҸеӯҰзҡ„еӯҰз”ҹзңӢгҖӮдёӨдҪҚиҖҒдәәиҝҳеёҰзқҖеӯҰз”ҹе’ҢиҖҒеёҲеҸӮи§ӮиҢЁдёӯж•ҷе ӮпјҢи®ІеҪ“е№ҙзҡ„ж•…дәӢпјҢиҝҳж•ҷеӯҰз”ҹз§ҚжӨҚи‘Ўиҗ„зҡ„з§ҳиҜҖгҖӮ
йғӯеҮҖиҮід»Ҡи®°еҫ—2007е№ҙеҲ°дёҠжө·еҸӮеҠ “дә‘д№ӢеҚ—е·Ўеұ•”зҡ„жғ…жҷҜгҖӮжҷҡдёҠпјҢ他们еҺ»йҖӣеҚ—дә¬и·ҜпјҢеҲҳж–ҮеўһеңЁзҶҷзҶҷж”ҳж”ҳзҡ„дәәзҫӨдёӯе…ҙеҘӢең°жӢүиө·ејҰеӯҗи·іиө·иҲһпјҢиў«еҗҢиЎҢзҡ„иӢ—ж—ҸзәӘеҪ•зүҮдҪңиҖ…зҺӢдёӯиҚЈжӢҚдәҶдёӢжқҘгҖӮиҝҷе№ҙ12жңҲеңЈиҜһеӨңпјҢ他们еҺ»иҢЁдёӯжқ‘пјҢиҝҷж®өеҪ•еғҸеңЁиҢЁдёӯж•ҷе ӮйҮҢж’ӯж”ҫпјҢжҠҠжқ‘ж°‘йғҪйҖ—д№җдәҶпјҢеҲҳж–ҮеўһиҮӘе·ұд№ҹеҝҚдҝҠдёҚзҰҒгҖӮ
2007е№ҙеҶ¬еӨ©пјҢж—әжүҺеңЁеұӢйЎ¶дёҠжӢҚж‘„йӣӘеұұж—ҘеҮәгҖӮ
гҖҖгҖҖйҰҷж јйҮҢжӢүеҺҝеҗүжІҷжқ‘зҡ„жқ‘ж°‘ж—әжүҺ2002е№ҙиҜ·жңӢеҸӢд»ҺйҰҷжёҜд№°дәҶеҸ°е°ҸDVеӣһжқҘпјҢејҖе§ӢжӢҚжқ‘йҮҢзҡ„е”ұжӯҢгҖҒи·іиҲһе’ҢејҖдјҡгҖӮжңү家公еҸёеҲ°еҗүжІҷејҖеҸ‘еҚғж№–еұұжҗһж—…жёёпјҢйқһж”ҝеәңз»„з»ҮеҸҲжқҘеҒҡз”ҹжҖҒж—…жёёйЎ№зӣ®пјҢеңЁжқ‘йҮҢеј•иө·еҫҲеӨ§дәүи®®гҖӮдј—дәәиҫ©и®әзҡ„ж—¶еҖҷпјҢж—әжүҺе°ұжӢҝзқҖж‘„еғҸжңәжӢҚж‘„гҖӮд№ӢеҗҺд»–жӢҚдәҶиҝҮе№ҙзғ§йҰҷпјҢжӢҚдәҶжқ‘ж°‘жү“зҜ®зҗғпјҢиҝҳеңЁеҗ•е®ҫзӯүNGOжңӢеҸӢзҡ„её®еҠ©дёӢз”ЁеҪ•еғҸи®°еҪ•жқ‘еә„зҡ„еҸҳиҝҒгҖӮд»–жҠҠеҪұзүҮеҲ»жҲҗе…үзӣҳз»ҷеӨ§е®¶зңӢгҖӮеӨ§е®¶йғҪеҸ«д»–“ж—әжүҺеӨ§еҸ””гҖӮйғӯеҮҖд№ҹи·ҹзқҖеҸ«пјҢе…¶е®һ他们е№ҙйҫ„е·®дёҚеӨҡгҖӮ
гҖҖгҖҖеҪ“еӯҰжңҜз•ҢејҖе§Ӣе…іжіЁ“д№Ўжқ‘еӘ’дҪ“”зҡ„з ”з©¶ж—¶пјҢйҰҷж јйҮҢжӢүзҡ„иҖҒдәә们已з»ҸжӢҚдәҶдёҚе°‘и®°еҪ•дҪңе“ҒдәҶгҖӮ“ж—әжүҺеӨ§еҸ”еҸҜд»ҘиҜҙжҳҜжңҖж—©еңЁиҝҷж–№йқўиҜүиҜёиЎҢеҠЁзҡ„жқ‘ж°‘д№ӢдёҖгҖӮ”йғӯеҮҖиҜҙпјҢ“ж—әжүҺеӨ§еҸ”еғҸдёӘи®°иҖ…дёҖж ·пјҢйҡҸж—¶е…іжіЁзқҖжқ‘йҮҢзҡ„еҸҳеҢ–пјҢд»–еҲ¶дҪңзҡ„еҪұзүҮгҖҠеҗүжІҷзәӘдәӢгҖӢй•ҝеәҰеҸӘжңүдәҢеҚҒеҲҶй’ҹпјҢеҚҙй”ІиҖҢдёҚиҲҚең°иҝҪиёӘеҲ°еұұзҒ«гҖҒжҡҙйӣЁе’Ңж°ҙзҒҫзӯүдёҖиҝһдёІиҮӘ然зҒҫе®ізҡ„жәҗеӨҙпјҢжҸӯйңІдәҶзӣІзӣ®ејҖеҸ‘жүҖеёҰжқҘзҡ„еҸҜжҖ•еҗҺжһңгҖӮ”
2012е№ҙпјҢзҷҪзҺүзҡ„зү§ж°‘еӢ’ж—әеңЁжӢҚж‘„йј е…”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гҖҠж°ҙгҖӢиҝҷйғЁзүҮеӯҗйҮҢпјҢж—әжүҺеҸҲ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ж•Ҹж„ҹзҡ„иҜ—дәәпјҢеңЁи®°еҪ•и—ҸдәәзҘӯзҘҖж°ҙзҘһзҡ„д»ӘејҸе’Ңдәә们讨и®әй—®йўҳзҡ„еҗҢж—¶пјҢд»–еҖҫеҝғең°и§ӮеҜҹзқҖж°ҙзҡ„жөҒеҠЁпјҢз”ЁдјҳзҫҺзҡ„й•ңеӨҙиҜӯиЁҖдј иҫҫеҮәж°ҙе’ҢеҶ°зҡ„е‘ўе–ғз»ҶиҜӯгҖӮ
гҖҖгҖҖ2012е№ҙеҶ¬еӨ©пјҢз« еҝ дә‘еҗ¬иҜҙж—әжүҺеӨ§еҸ”еҫ—дәҶйҮҚз—…пјҢзү№ең°еҲ°еҗүжІҷеҺ»жҺўжңӣгҖӮеұӢеӨ–дёӢзқҖеӨ§йӣӘпјҢеұӢеҶ…пјҢж—әжүҺеӨ§еҸ”ж–ӯж–ӯз»ӯз»ӯи·ҹеҘ№и®ІзқҖиҮӘе·ұзҡ„ж•…дәӢпјҢиҜҙж‘„еғҸжңәе°ұеғҸ笔дёҖж ·еҸҜд»ҘжҠҠеӨҙи„‘йҮҢзҡ„жғіжі•иЎЁиҫҫеҮәжқҘпјҢеҸҜд»Ҙи®°еҪ•дёӢжқ‘йҮҢзҡ„дәәе’ҢдәӢпјҢеӨҡе№ҙд»ҘеҗҺпјҢиҝҷдәӣдёңиҘҝе°ұеғҸдёҖжң¬жң¬жңүе…іиҮӘе·ұжқ‘еӯҗзҡ„д№ҰдёҖж ·жөҒдј дёӢеҺ»пјҢи®©еӯҗеӯҷеҗҺд»ЈеҸҜд»ҘзҹҘйҒ“家乡зҡ„ж•…дәӢгҖӮ
гҖҖгҖҖ2011е№ҙд»ҘеҗҺпјҢж—©е№ҙеҸӮдёҺд№Ўжқ‘ж‘„еҪұзҡ„иҖҒдәә们еҢ…жӢ¬еҲҳж–ҮеўһгҖҒж—әжүҺеӨ§еҸ”гҖҒеӯҷиҜәдёғжһ—йғҪзӣёз»§зҰ»дё–гҖӮ“иҝҷдәӣиҖҒдәә们ж”Ҝж’‘зқҖйҰҷж јйҮҢжӢүж°‘й—ҙж–ҮеҢ–зҡ„ж №еҹәпјҢ他们д№ҹжҳҜ‘д№Ўжқ‘еҪұеғҸ’зҡ„е…ҲиЎҢиҖ…гҖӮ”йғӯеҮҖ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
зү§дәәзңјзқӣзңӢеҲ°зҡ„дё–з•Ң
гҖҖгҖҖ2007е№ҙ10жңҲпјҢеңЁеұұж°ҙиҮӘ然дҝқжҠӨдёӯеҝғе·ҘдҪңзҡ„дә‘еҚ—дәәеҗ•е®ҫеҸ‘иө·дәҶ“д№Ўжқ‘д№Ӣзңј”еҹ№и®ӯпјҢең°зӮ№еңЁдә‘еҚ—еӨ§еӯҰеҶ…гҖӮдјҡи®®жңҹй—ҙпјҢйғӯеҮҖ第дёҖж¬ЎзңӢеҲ°жқҘиҮӘиҚүеҺҹзҡ„дәәжӢҝзқҖж‘„еғҸжңәжӢҚж‘„зҡ„зүҮеӯҗгҖӮдёүе№ҙеҗҺпјҢд»–и·ҹеҗ•е®ҫжңүжңәдјҡж·ұе…ҘеҲ°йқ’жө·зңҒжһңжҙӣе·һд№…жІ»еҺҝзҷҪзҺүд№ЎеҸӮеҠ еҪ“ең°ж°‘й—ҙз»„з»Ү“е№ҙдҝқзҺүеҲҷз”ҹжҖҒзҺҜеўғдҝқжҠӨеҚҸдјҡ”з»„з»Үзҡ„“д№Ўжқ‘д№Ӣзңј”еҹ№и®ӯпјҢд»–зңӢеҲ°зү§ж°‘еңЁжЁӘе№…дёҠеҶҷзқҖпјҡ“и®°еҪ•жҲ‘们зҡ„зҺҜеўғе’Ңж–ҮеҢ–”гҖӮ 
2010е№ҙпјҢйқ’жө·“е№ҙдҝқзҺүеҲҷз”ҹжҖҒзҺҜеўғдҝқжҠӨеҚҸдјҡ”дёҺеұұж°ҙеҗҲдҪңпјҢеҸ‘иө·еҪ“ең°зҡ„第дёҖж¬Ў“д№Ўжқ‘д№Ӣзңј”еҹ№и®ӯ
гҖҖгҖҖе’Ңзү§ж°‘еҗҢеҗғеҗҢдҪҸпјҢдёҖиө·и®Ёи®әеҲ°ж·ұеӨңзҡ„иҝҷж¬Ўеҹ№и®ӯпјҢи®©йғӯеҮҖ收иҺ·йўҮдё°гҖӮд»–ж„ҸиҜҶеҲ°пјҢеңЁйқһеҶңдёҡең°еҢәеҒҡ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пјҢжңүжӣҙдёәзӢ¬зү№зҡ„д»·еҖјгҖӮ“йҰ–е…ҲжҳҜд№Ўжқ‘еҪұеғҸзҡ„жҰӮеҝөеә”иҜҘиҝӣдёҖжӯҘжң¬еңҹеҢ–пјҢдј з»ҹзҡ„зү§еҢәеҺҹжқҘжІЎжңүжқ‘иҗҪзҡ„жҰӮеҝөпјҢзү§ж°‘д»ҺиҮӘе·ұзҡ„з«ӢеңәеҮәеҸ‘пјҢжҠҠжұүиҜӯзҡ„‘д№Ўжқ‘’жү©еӨ§дёә‘家乡’гҖӮ”
гҖҖгҖҖзү§ж°‘з”ҹеӯҳзҡ„иҘҝйғЁеұұең°жүҖйқўдёҙзҡ„зҺҜеўғеҸҳиҝҒй—®йўҳпјҢжң¬иҙЁдёҠжҳҜи®ӨиҜҶиҚ’йҮҺзҡ„иҝҮзЁӢгҖӮиҰҒзңҹжӯЈдәҶи§ЈиҚ’йҮҺпјҢе°ұеҝ…йЎ»и®ӨиҜҶдёҺиҚ’йҮҺжү“дәӨйҒ“зҡ„ж°‘ж—ҸпјҢдәҶ解他们дёҺиҚ’йҮҺдәӨеҫҖзҡ„ж–№ејҸ——他们зҡ„ж–ҮеҢ–гҖӮиҝҷжҳҜеҜ№еӨ–дәәзҡ„ж„Ҹд№үгҖӮеҜ№еҪ“ең°дәәиҖҢиЁҖпјҢиҚ’йҮҺе°ұеҰӮеҗҢдёҖеҢ№иөӣ马пјҢе®ғжңүйҮҺжҖ§пјҢеҚҙиҰҒиў«зәіе…Ҙдәәзҡ„规еҲҷдёӯгҖӮ“зү§ж°‘еңЁе…¶дёӯж„ҹеҲ°зә и‘ӣпјҢиҝҷжӯЈжҳҜ他们и®ӨиҜҶиҚ’йҮҺеҸҠе…¶иҮӘиә«зҡ„иүҜжңәгҖӮ”йғӯеҮҖ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д№Ўжқ‘еҪұеғҸеңЁзү§еҢәжҺҘиҝ‘дёҖз§Қй•ҝжңҹзҡ„и°ғжҹҘжҙ»еҠЁгҖӮ“иҝҷдәӣи°ғжҹҘзҡ„йңҖиҰҒ并дёҚжҳҜеӨ–дәәе…ҲжҸҗеҮәзҡ„гҖӮ”еҹ№и®ӯдёӯпјҢжүҖжңүеӯҰе‘ҳйғҪеңЁи°ҲдёҖдёӘй—®йўҳпјҡжғіжӢҚж‘„пјҢжҳҜеӣ дёәиҮӘе·ұзҶҹжӮүзҡ„з”ҹжҙ»еҝ«иҰҒж¶ҲеӨұдәҶгҖӮжҜ”еҰӮеӯҰе‘ҳжӣҙзҷ»иҜҙпјҢд»–ж•…д№Ўзҡ„й»‘еёҗзҜ·йғҪеҸҳжҲҗзҷҪеёҗзҜ·дәҶпјҢе№ҙиҪ»дәәйғҪдёҚзҹҘйҒ“еҗ„йғЁеҲҶзҡ„еҗҚеӯ—пјҢд»–иҮӘе·ұд№ҹеҚҒдә”е№ҙжІЎдҪҸиҝҮй»‘еёҗзҜ·дәҶпјҢжүҖд»Ҙжғіиҫ№жӢҚиҫ№еӯҰ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е№ҙдҝқзҺүеҲҷпјҲе·ҙеҪҰе–ҖжӢүеұұжңҖй«ҳзҡ„дё»еі°пјүеұұдёӢж”ҫзү§зҡ„иҖҒзҺӢжғіз”Ёж‘„еғҸжңәи®°еҪ•жӨҚзү©е’ҢеҠЁзү©зҡ„еҸҳеҢ–гҖӮ“д»Ҡе№ҙйӣӘеұұиһҚеҢ–жӣҙдёҘйҮҚпјҢд»–жғіжӢҚеҮәжқҘз»ҷеӨ§е®¶зңӢзңӢгҖӮд»ҘеҗҺжІЎжңүйӣӘеұұе’ҢеҶ°е·қпјҢе°ұжІЎжңүжІіжөҒпјҢжІЎжңүдәәдәҶгҖӮеҫҲе°‘жңүдәәдёәжӯӨжӢ…еҝғпјҢдҪҶзҲ¬иҝҮйӣӘеұұзҡ„дәәпјҢзңӢеҲ°еҫҲеӨҡж№–жіҠйғҪе№ІдәҶпјҢз”ЁиҮӘжқҘж°ҙзҡ„дәәеҪ“然дёҚжҖ•гҖӮиҖҒзҷҫ姓жӢ…еҝғзҡ„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зҺҜеўғпјҢиҖҢжҳҜдёәдәҶзҘһеұұгҖӮ”
гҖҖгҖҖ然иҖҢпјҢи®Ёи®әдёӯпјҢеӨ§е®¶иҜҙжғіи®°еҪ•еҸҳеҢ–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з®ҖеҚ•ең°з”ЁжӢҚж‘„еҺ»ж”№еҸҳзҺ°зҠ¶пјҢиҝҷеӨҡе°‘еҸҚжҳ дәҶи—Ҹж—ҸдәәзңӢй—®йўҳзҡ„дёҖз§Қи§’еәҰгҖӮеҸ—дҪӣж•ҷзҡ„зҶҸжҹ“пјҢи—Ҹж—ҸдәәеҜ№еӨ–з•Ңе’ҢиҮӘиә«зҡ„еҸҳеҢ–еқҰ然жҺҘеҸ—гҖӮеңЁдҪӣж•ҷзҡ„и§ӮеҝөйҮҢпјҢд»»дҪ•дәӢзү©йғҪжңү“жҲҗгҖҒдҪҸгҖҒеқҸгҖҒз©ә”еӣӣдёӘеҸҳеҢ–зҡ„йҳ¶ж®өпјҢеҚід»Һж¬Јж¬Јеҗ‘иҚЈиө°еҗ‘и…җиҙҘе’Ңжӯ»дәЎгҖӮиҝҷиҝҮзЁӢжҲ–еҝ«жҲ–ж…ўпјҢдҪҶз»Ҳ究дјҡеҸ‘з”ҹпјҢдёҚд»Ҙд»»дҪ•дәәзҡ„ж„Ҹеҝ—дёәиҪ¬з§»гҖӮ
2012е№ҙпјҢеңЁзҷҪзҺүдёҫеҠһ第дёҖеұҠиҚүеҺҹз”өеҪұиҠӮгҖӮ
йӮЈдёәдҪ•иҝҳиҰҒи®°еҪ•е‘ўпјҹ“дәӢе®һдёҠпјҢдҪӣж•ҷжң¬иә«е°ұжҳҜдёәдәҶжҺўи®Ёиҝҷж— жүҖдёҚеңЁзҡ„‘еҸҳеҢ–’иҖҢдә§з”ҹзҡ„гҖӮжҖқиҫЁйңҖиҰҒеҗ„з§ҚиЎЁиҫҫзҡ„ж–№ејҸпјҢеҰӮз”»е”җеҚЎгҖҒеҰӮ穷究з»Ҹд№Ұдёӯзҡ„йҒ“зҗҶпјҢж‘„еҪұд№ҹжҳҜдёҖж ·гҖӮйҷӨдәҶи®°еҪ•е’Ңи°ғжҹҘпјҢжҲ‘们иҝҳжңүд»Җд№Ҳж–№жі•еҸҜд»Ҙж·ұе…Ҙең°дәҶи§ЈеҸҳеҢ–зқҖзҡ„дё–з•Ңзҡ„йқўиІҢпјҹ”
гҖҖгҖҖйғӯеҮҖеҸ‘зҺ°пјҢеӯҰе‘ҳ们еұ•ејҖзҡ„жӢҚж‘„дё»йўҳзҡ„и®Ёи®әе°ұеғҸеңЁеҒҡи°ғжҹҘзҡ„и®ЎеҲ’пјҢзңӢдјје°Ҹе°Ҹзҡ„йўҳзӣ®пјҢеҰӮе»әз»Ҹе ӮгҖҒйј е…”гҖҒзү§еңәжҗ¬е®¶гҖҒй»‘еёҗзҜ·гҖҒи—ҸзӢ—гҖҒзүӣйһҚеӯҗпјҢйғҪзүөжүҜеҲ°еҗ„з§ҚеӨҚжқӮзҡ„е…ізі»пјҢиҖҢжј”еҸҳжҲҗйңҖиҰҒй•ҝжңҹи§ӮеҜҹжүҚиғҪе®ҢжҲҗзҡ„зі»еҲ—гҖӮ“з»ҸиҝҮз»ҶиҮҙзҡ„и®Ёи®әпјҢжӢҚж‘„иҖ…дјҡеӯҰзқҖз”Ёж‘„еғҸй•ңеӨҙйҮҚж–°еҮқи§ҶзҶҹжӮүзҡ„з”ҹжҙ»пјҢеӯҰзқҖи·ҹиў«жӢҚж‘„еҜ№иұЎе»әз«Ӣж–°зҡ„иҒ”зі»пјҢд№ҹеӯҰзқҖд»Һж–°зҡ„и§’еәҰеҺ»и®ӨиҜҶеҸҳеҢ–зҡ„жң¬иҙЁгҖӮ” гҖҖ
еҜ№д№Ўжқ‘еҸҳиҝҒеҒҡеҮәзҡ„еӣһеә”
гҖҖгҖҖеңЁиҝӘеәҶи—Ҹж—ҸиҮӘжІ»е·һйҰҷж јйҮҢжӢүеҺҝеҒҡ“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ж•ҷиӮІ”зҡ„ж—¶еҖҷпјҢйғӯеҮҖжӣҫиҜҙиҝҮпјҢзӨҫеҢәеҪұеғҸжҳҜдёҖдёӘиҮӘжҲ‘ж•ҷиӮІзҡ„иҝҮзЁӢ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з”ЁдәҶеҪұеғҸзҡ„жүӢж®өиҖҢе·ІгҖӮд»–з”ЁдёҖеҸҘиҜқжқҘиЎЁиҝ°иҝҷз§ҚеҸҰзұ»зҡ„ж•ҷиӮІпјҡеӯҰд№ жҲ‘们иҮӘе·ұзҡ„дј з»ҹгҖӮ
гҖҖгҖҖд»–и®ӨдёәпјҢи—Ҹж—Ҹе’Ңжұүж—ҸпјҢйғҪйқўдёҙзқҖж—·еҸӨжңӘжңүзҡ„еҸҳиҝҒпјҢйңҖиҰҒжңүдәәеҜ№иҝҷз§ҚеҸҳиҝҒеёҰжқҘзҡ„й—®йўҳеҸҠеӣ°жғ‘еҒҡеҮәеӣһеә”гҖӮиҖҢзҷҪзҺүзҡ„и—Ҹж—ҸдәәиҮӘе·ұеҒҡеҪұеғҸеҹ№и®ӯпјҢжӯЈжҳҜзӨҫеҢәж•ҷиӮІз”ұеӨ–жқҘиҖ…жҺЁеҠЁеҲ°жң¬еңҹиҮӘи§үиЎҢеҠЁзҡ„иҪ¬жҠҳзӮ№гҖӮ
гҖҖгҖҖйғӯеҮҖзңӢеҲ°пјҢзү§ж°‘们еҲ¶дҪңзҡ„зәӘеҪ•зүҮеңЁеҪ“ең°дј ж’ӯзҡ„еҗҢж—¶пјҢд№ҹеј•иө·дәҶи®ёеӨҡеҹҺеёӮи§Ӯдј—зҡ„е…ҙи¶ЈгҖӮ“еңЁиҝҷдёӘд»ҘйҮҚеҶңжЁЎејҸжҺЁеҠЁиҘҝйғЁеӨ§ејҖеҸ‘зҡ„еӣҪеәҰпјҢйқ’жө·зҡ„зү§ж°‘第дёҖж¬Ўи®©жҲ‘们иҒҶеҗ¬еҲ°жқҘиҮӘйӘ‘马民ж—Ҹзҡ„еЈ°йҹігҖӮиҝҷеЈ°йҹіиҷҪ然еҫ®ејұпјҢеҚҙжҳҜдёҚеҸҜзјәе°‘зҡ„гҖӮ他们зҡ„еҪұеғҸпјҢеҗҜеҸ‘жҲ‘们йҮҚж–°е®Ўи§ҶдёҖдәӣж–Үдәәе’Ңе®ҳе‘ҳеҜ№жёёзү§ж–ҮжҳҺзҡ„иҜҜиҜ»пјҢеҸҚжҖқ‘иҘҝйғЁејҖеҸ‘’еҜ№еҪ“ең°зҺҜеўғе’Ңж–ҮеҢ–еёҰжқҘзҡ„еҪұе“ҚгҖӮиҖҢиҝҷз§ҚеҪұе“ҚпјҢжҳҜдёңйғЁе’ҢиҘҝйғЁеҫ—дёҖиө·жүҝжӢ…зҡ„гҖӮ” 
2007е№ҙпјҢеұұж°ҙиҮӘ然дҝқжҠӨдёӯеҝғеңЁдә‘еҚ—еӨ§еӯҰдёҫеҠһдәҶ第дёҖж¬Ў“д№Ўжқ‘д№Ӣзңј”еҹ№и®ӯгҖӮ
гҖҖгҖҖиҝ‘еҚҠдёӘеӨҡдё–зәӘд»ҘжқҘпјҢдёӯеӣҪзҡ„д№Ўжқ‘е’ҢеҹҺеёӮиў«дҪ“еҲ¶еҲҶйҡ”пјҢдҝғиҝӣиҝҷдёӨеҚҠзҡ„жІҹйҖҡпјҢж— и®әеҜ№дәҺејҘеҗҲзӨҫдјҡзҡ„еҲҶеҢ–е’Ңдҝ®иЎҘзҺҜеўғзҡ„еҲӣдјӨпјҢйғҪжңүзқҖеҚҒеҲҶйҮҚиҰҒзҡ„ж„Ҹд№үгҖӮй•ңеӨҙжң¬иә«е°ұе…·жңүеҲәжҝҖзҡ„дҪңз”ЁпјҢе®ғеҸҜд»Ҙж”»еҮ»пјҢд№ҹеҸҜд»ҘжҝҖеҸ‘пјҢ并еӣ иҖҢдҝғиҝӣдәҶдёӘдәәе’ҢдәәзҫӨд№Ӣй—ҙзҡ„дә’еҠЁе’ҢдәҶи§ЈгҖӮ“д»ҺиҝҷдёӘж„Ҹд№үдёҠзңӢпјҢд№Ўжқ‘еҪұеғҸзҹӯзҹӯеҚҒеҮ е№ҙзҡ„еҺҶеҸІпјҢе°ұжҳҜдёҖдёӘдәәдёҺдәәзӣёйҒҮгҖҒдәӨеҫҖгҖҒеҶІзӘҒе’ҢзҗҶи§Јзҡ„ж•…дәӢгҖӮ”еӣһйЎҫд№Ўжқ‘еҪұеғҸеҺҶеҸІпјҢйғӯеҮҖж·ұжңүж„ҹи§Ұең°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д»–и®°еҫ—2008е№ҙжӣҫеңЁи…ҫеҶІеҺҝжЁӘжІіеҜЁзҡ„дёҖй—ҙе°ҸеӯҰж•ҷе®ӨйҮҢпјҢзңӢеҲ°еӮҲеғідәәй«ҳеҗҜзҺӢдёәжң¬ж—ҸеӯҰз”ҹзј–зҡ„дёҖжң¬жҜҚиҜӯж•ҷжқҗпјҢе…¶дёӯеј•з”ЁдәҶдёҖж®өеӮҲеғіж–ҮеңЈз»Ҹзҡ„ж јиЁҖпјҡ“жҲ‘жүҖжөӢдёҚйҖҸзҡ„еҘҮеҰҷжңүдёүж ·пјҢиҝһжҲ‘жүҖдёҚзҹҘйҒ“зҡ„е…ұжңүеӣӣж ·пјҡй№°еңЁз©әдёӯйЈһиЎҢзҡ„йҒ“пјҢиӣҮеңЁзЈҗзҹідёҠзҲ¬иЎҢзҡ„йҒ“пјҢиҲ№еңЁжө·дёӯиҲӘиЎҢзҡ„йҒ“пјҢз”·еҘідәӨеҗҲзҡ„йҒ“гҖӮ”иҝҷж®өж јиЁҖиҷҪ然жҳҜж–Үеӯ—еҶҷзҡ„пјҢеҚҙиғҪжҸҸз»ҳеҮәж ©ж ©еҰӮз”ҹзҡ„з”»йқўпјҢи®©дәәеӣһе‘іж— з©·гҖӮ
гҖҖгҖҖ“иҜӯиЁҖиЎЁиҫҫе’Ңи§Ҷи§үжүӢж®өд№Ӣй—ҙжҖ»жңүжҹҗз§ҚеҘҮеҰҷзҡ„иҒ”зі»гҖӮеҰӮжһңжҠҠиҜӯиЁҖжҜ”е–»дёәй№°гҖҒиӣҮгҖҒиҲ№е’Ңз”·еҘіпјҢйӮЈд№ҲпјҢд№Ұжі•гҖҒеҚ°еҲ·жңҜгҖҒз»ҳз”»гҖҒйқҷжҖҒе’Ңжҙ»еҠЁеҪұеғҸдҫҝжҳҜйЈһиЎҢгҖҒиҲӘиЎҢе’Ңз”ҹе‘Ҫз№ҒиЎҚеҖҹд»ҘйҖҡиҫҫзҡ„йҒ“гҖӮдәә们жІҝзқҖйҒ“и·Ҝж—…иЎҢпјҢйҒ“еҲҷйЎәд№ҺиҮӘ然гҖӮ”
гҖҖгҖҖеӯҰиҖ…йғӯеҮҖжӯЈжҳҜд»ҘйЎәд№ҺиҮӘ然д№ӢйҒ“пјҢиө°еңЁжҺЁеҠЁд№Ўжқ‘еҪұеғҸзҡ„йҒ“и·ҜдёҠгҖӮ
гҖҖгҖҖпјҲжң¬ж–ҮеҶ…е®№еҸӮиҖғйғӯеҮҖгҖҠеәҸиЁҖпјҡеҪұеғҸпјҢжҜҚиҜӯе’ҢеҜ№иҜқгҖӢгҖҠеҪұеғҸзҡ„еЈ°йҹігҖӢзӯүж–Үз« гҖӮзү№жӯӨиҮҙи°ўпјҒпј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