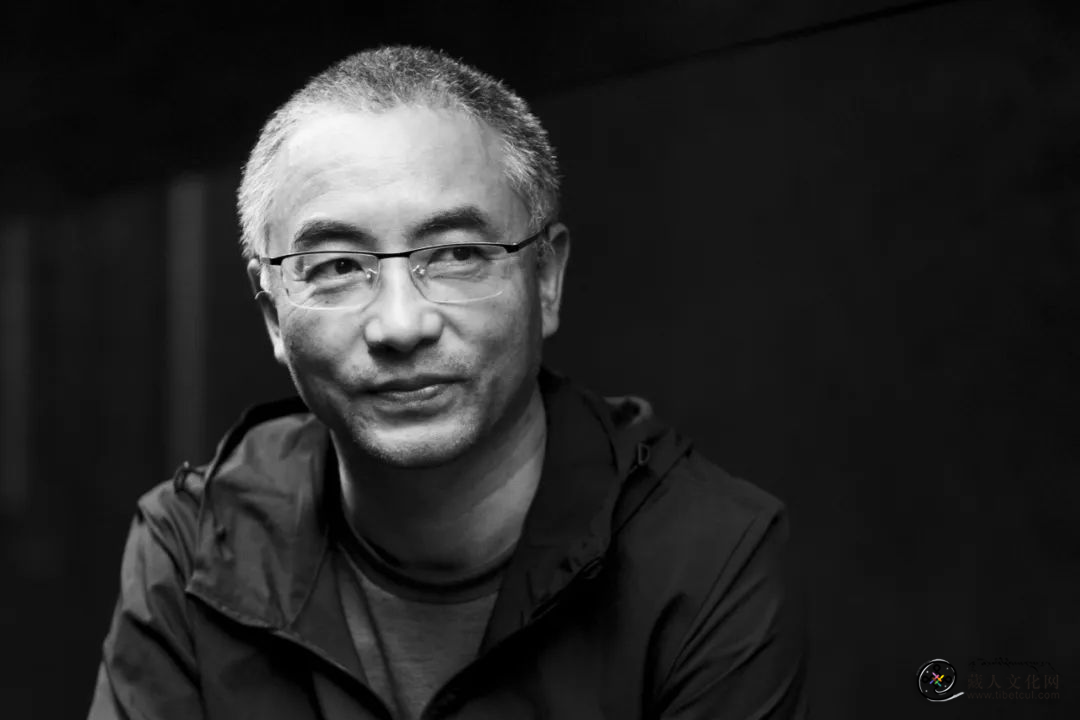去年,也就是1999年的夏天,我在被称为“康巴”的四川藏区转游了三个月后回到拉萨,很偶然地,看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杂志—— 《光与影》1999年第一期,里面的一篇生动有趣的文章和数张色彩强烈的精美照片,激起我内心的触动。尤其是照片中,那土堡似的寺院前飞舞的火红经幡,那霞光里青翠的草地上盛开的簇簇野花,那依傍着火红经幡在青翠的草地上低头吃草的白马,还有,那绛红色的喇嘛,那虹光中神态安详或碧湖边背影肃穆的绛红色的喇嘛--巴伽活佛,还有,那穿厚皮长袍、挂锋利长刀、骑高头大马的康巴汉子一脸的虔诚,无一不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却丝毫也不陌生,而且亲切无比,使我仿佛再度回到了我的康巴老家。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梦回阿须》,作者与摄影者是自称"盲流"的艺术家温普林。在文章中,温普林记录了他和弟弟温普庆在康巴大地上的一段丰富的游历,特别是和巴伽活佛的深厚友谊,最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在阿须,我懂得了什么叫'家乡有一条小河'。以前觉得这是乡土作家们酸溜溜的小调,家乡有一条小河也值得写?到那儿之后,明白了。出生的地方要是在一片有山有水之处,那是多么深厚的滋养啊!生命在这儿多么自然而然地存在,又多么自然而然地消失。对于我这种没有故乡感的孤魂野鬼,依恋一方水土意味着什么?我从此会有一缕乡愁,一丝牵挂。……从来没有停止过走,从来没有依恋过什么地方,可为什么独独的,我到了那个地方就觉得跟我有关系,这关系太大了,大到我要倾我一生。一个人总得依恋点什么,按佛的说法,这就是缘分。阿须张开双臂接纳了我们兄弟俩,我们找到了故乡。对于我们来说,阿须,是不可选择的。"
今年年初,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名为"风马旗书系"的丛书,一共三本:《巴伽活佛》、《苦修者的圣地》和《茫茫转经路》。作者皆为温普林。我在《光与影》上看到的《梦回阿须》一文即选自《巴伽活佛》一书。而此书也正是丛书中最能够引起我共鸣和感慨的一本。《巴伽活佛》使我对位于藏东的那一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更血缘的亲密,和更难以消却的归宿感。这一切都缘于作者温普林以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异族人的自然和平常的心态,逐渐地融入一个散发着宗教生活的芬芳和游牧生活的纯朴气息的世界之中,而这样一个世界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显然是另外一个陌生和神秘的世界。其实陌生和神秘无非是一种渲染,一种不知。其实作者的经验虽然是特别的,少有的,但因为发自于内心,是自觉的,真诚的,袒露的,所以他在书中所展示的这段心路历程无疑让读者认同,并也随之一起走上了归乡之路。
2
说起来,"康巴"一词十分特别。从意义上来讲,因为"巴"指的是"人",而"康"代表的是位于藏东的某个区域,所以直译过来应该是"康地的人"的意思,是一个偏正词组;然而很早就有了变化,也就是说,从很早起,在时间和习俗的作用下,在外来语言的影响下,"康巴"更多的替代了"康",成为一个有所指的地域性名词,并且隐含着一个庞大而混合的部族。不仅如此,有时候它甚至还是形容词。当然若变成形容词,那就会引发出太多、太多的话题了。
在康巴,过去竟有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为出家众,还有许多瑜伽士和在家修行的人,称得上是一个"喇嘛之邦",现如今也是遍及各处,且愈发有增长之势。"康巴"因此而更多地意味者云游僧、隐修士和"仁波切"(像珍宝一样的活佛)。这实际上和藏地各处的情形相同。不过,若要细细究竟,各处又有其鲜明的特点,比如在藏地早就盛传着"安多的马,康巴的人,卫藏的教"这句老话。
暂且不论康巴人在外表上容易造成的某种审美眩晕,也不说康巴人似乎个个擅长生意和骑术的本事,就其整体性格而言实在是有两极之分的。从地理上来讲,在康巴的周围,除了某一边是逐渐平缓下去的地貌,其它方向几乎全是趋向于愈发高拔、险峻的群山,之间夹隔着汹涌而奔腾的江河,故长久以来,内陆或外域的空气及人气得以源源不绝地涌入似乎是一个不必待说的现象,康巴人也因此而不能算作是一种纯粹的土著了,这里面聚集着这块土地上各成一统的许多部落,他们使原本就在马背上成长的骑士们的性格更加极端化。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胸膛里燃着野性的火焰",在一大群具有侠骨义胆的勇士们演绎的充满英雄主义基调的历史戏剧里,多少年来,甚至至今,关于家族或乡里之间仇杀和械斗的故事从未停息过,他们里面还有肆意妄为的"夹巴"(强盗),胆大包天的"古玛"(小偷),佛教慈悲、怜悯和行善的教义似乎很难制约他们的心灵。也有人会在特别的时候被突然显现的因果和业报所惊骇,犹如大梦初醒一般看见自己的面目,于是就像俗话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样,匆忙将武器折断,悉数归"仓"(这个"仓"指的是寺院),而后遁入深山洞穴之中,祈望在余生以绝对的苦修来抵消自己的恶业。这样极端化的故事我从小就听过,康巴人性格中的烈性由此可见。
不过,这倒不是说在康巴人中占相当一部分的僧侣队伍是由于这种原因形成的。这种情况其实极少。应该说如佛教这一中庸之道,倡导以戒律来减弱人的欲念,从而减少人的诸多烦恼和痛苦,而康巴人天生易于出格的品性似乎很难使他们归附其上,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又如何解释呢?
在这里,我要转述一个关于喇嘛和土匪的故事。他们都是康巴人。他们是否正好代表了康巴人群体中最具典型的两个部分?这个故事来自又一部非常有趣而饶富深意的书:《雪狮的蓝绿色鬃毛》。这部书的作者,确切地说是记录者,是一位美国的犹太人,六十年代颓废而叛逆的嬉皮士,七十年代以后其心智突然转向而且至今的宁玛教徒--舒雅·达。另外他还是个诗人(他的经历是不是与温普林相似?)。在这部书里,他从他的诸位上师,那些远在国外的西藏喇嘛之处收集了许多故事,"这些奇异精彩的故事都带有精神的意义,唤出宁静、轻松自在和古怪离奇的气氛,显出峻峭喜马拉雅山的自由和超越。"
《智慧也可以传染》就是这样一个极具意蕴的故事,其中说到:
巴楚仁波切有一次独自在玛康附近崎岖山里流浪,夜里便露宿野外。他禅修寂天菩萨的菩提心教法,那是关于发愿利他以求证悟的教法。巴楚的愿力是希望毫不偏私地对待他人如己一般。
一条崎岖的泥土小径横切过山脉,连接着山谷中两个争执不休的家族。这位离群独修的上师敏锐地感觉到四周的暴力气氛,激起他慈悲、虔诚的祈祷。
有一天,交战的双方注意到一个流浪汉在路旁,大家都想知道他是谁,有何意图。他们发现巴楚横躺在山径一段狭窄转弯处,每一个过路人都不得不跨过他。以如此不寻常的姿态,巴楚便可以为每个过路的人个别祈祷,希望能平息他们暴力的情绪。
一段时间后,三个武装的年轻骑士遇到这个饱受风霜的老行脚僧,他旁边的营火早已熄灭。他们被迫突然勒马而且跨了下来,他们诘问:"你是病了,精神错乱,或者是个麻疯病人?你有什么毛病,这样横躺在路上?"
这位漫不经心的大师回答:"别担心,年轻人,你们不会感染上我的病,这叫做'菩提心',很难传给像你们这样年轻健壮的战士!"三个人有些迷惑,跨上马急驰而去。
后来巴楚说:"或许这无私的菩提心也是会传染的,因为你可以从伟大的精神修行者处感受到它。但是现在,虽然很多人宣称拥有它,却很少人真正发展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征兆。"
然后他祈祷着:"愿一切众生无有例外,都能感染到这宝贵的菩提心。"
很神奇地,玛康地区原本不断地流血争斗很快就平息了。当地的人们声称,年轻的战士一定是从那挡在山路中,隐名证悟的流浪汉处感染到和平的疾病,而他们从此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正如故事中所强调的,"菩萨"即是精神英雄,"菩提心"代表的是"菩萨"的公正、利他的证悟之心,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康巴人天生所有的英雄气质,并未因佛教教义的约束而消失,相反得到了净化、上升和完善。不知是否有人注意过,在地道的康巴人的容颜中往往含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在里头,它使几乎每个康巴人的脸都有令人难忘的效果。不是说它可以使之漂亮无比,一张近乎完美的脸或许会因之而扭曲,而另一张丑陋的脸或许会因之而生辉,总之它像是一种隐而不显的印记,惟有康巴人或与康巴人心有灵犀的人方可辨认得出。这一点在温普林所拍摄的照片中,可以说是显露无遗。所以像巴楚仁波切这样的"精神英雄"而不是世俗意义的英雄,无疑是最理想化的康巴人,是漫步在喜马拉雅山上的闪烁着宁静的蓝绿色光芒的美丽雪狮。
3
实际上,在温普林的书中,巴伽活佛也正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精神英雄"。比如说在文革时期,"当时为了改造僧人,都逼他们娶老婆,杀生。活佛为了不杀生,装瘫痪在床上躺了十几年。他只有在后半夜偷偷地爬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地运动。造反派曾多次把他揪区,逼他站起来,说他是假装的,但他死活都不起来。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80年代,看到改革开放宗教可以恢复,才把拐棍一扔,开始了恢复佛法的努力。不到十年的时间,他到处化缘,恢复了阿须几乎所有的宗教设施。"
又比如说书中所讲的,"实际上是从1990年开始,我们已经发现了活佛越来越多地操劳。他是一方百姓的精神寄托,生老病死全部都归他管,只要你活着,你一生也就免不了跟宗教打交道。比如刚生下来的孩子活佛要去祝福,孩子到了取名的时候,需要请活佛取名;病了,老了,需要活佛的临终关怀,连药都要拿到活佛那儿请他吹口气才吃。死了就更不用说了,所有要死的人都渴望活佛亲自超度。……我曾问一个老妇,活佛摸顶幸福吗?她说,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吗?他就是天上的太阳,太阳出来人身自然暖和。"
在全民信仰佛教的藏地,作为精神生活的导师的活佛们素来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义务和责任,比较而言,正如温普林引用巴伽活佛的话来说,"有三种活佛受人敬重,一种是深居旷野,终生苦修,道法高深,弘扬天下,比如米拉日巴尊者那样的。还有一种法相庄严,金碧辉煌,俯视众生,令百姓顿生虔敬之心,比如噶玛巴活佛这样。再有一种是多做实事,恢复寺院,关心老百姓生活,对他们尽量有求必应。这样的活佛和百姓的关系密切,也受到他们的尊敬。"而巴伽活佛恰恰就是第三种平民化的活佛。
温普林也正是在与巴伽活佛多年来心与心的交往中,直接深入到藏人生活的核心部分,那就是西藏佛教。且不说他本人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对那片土地充满人性的关怀和依从,而是他对于这种信仰的认识,应该说已经很接近一个普通藏人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状态。对于一个藏人来说,宗教不是一件色彩强烈的外衣,宗教纯粹与他们的血缘有关,因而也就成了他们生活的根本意义。既然已经是生活本身,那就和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换句话说,"宗教对于他们来讲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呼也自然,吸也自然,环境也自然。佛法就是好,自然而然地让你彻底解脱"(见温普林的《苦修者的圣地》一书)。如此自然的行为,在外与生理相关,其实属于心理的范畴。所以,温普林深有感触地说,"跟随巴伽活佛十年,如果要我谈感悟最深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一颗平常心而已。平平常常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4
因为温普林幽默、朴实的口语化文字,起初,我是把《巴伽活佛》这本书当作一部生动有趣的记实读物来读的。但读着读着,你会发现在那些频繁出现的"康巴"、"阿须"、"岔岔寺"一类字眼之间,游移着、行走着一个个十分亲切的形象,是活生生的形象,有着仿佛亲人一般的气息和容颜。尤其是巴伽活佛的形象,正如温普林所说,"……作为活佛--举足轻重的社会角色,我看到了秩序、和谐以及藏族社会未来的希望。作为一个人,在巴伽活佛的身上我看到了仁慈、宽厚、自律、达观、智慧和风度。"
而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正是在书中对这些形象的描写里,我"发现了某种温情--或者说某种激情,"这使我在阅读中不由得常常联系起有篇小说来。这篇小说是博尔赫斯的《接近阿尔莫塔辛》,其中描写了一个"失去宗教信仰并在逃的大学生",认定偶然通过其他的人和事物反映出某种温情或激情的人即阿尔莫塔辛"定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他本人就是这种情感的化身。于是,大学生决定花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寻找他。"
"开始时,借助于另一些人的面孔只'露出一个微笑',或只说出只言片语,后来才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他的理智之光,显露出大学生想象的那种光芒。"--这是否与温普林走在康巴大地上的经验很相象呢?实际上,他或者你或者我只要走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上,所见到的人,所得到的信息,不都是如"阿尔莫塔辛"这个"他"的化身吗?用佛家的话来说,这是诸佛菩萨的示现。
在西藏游历是容易被感召的。因为你会渐渐地发现被人们称做"世界屋脊"、"雪域"、"香巴拉"的西藏大地恰如一幅辽阔的绛红色地图,其上星罗密布着数不清的寺院和隐修洞,容纳或掩蔽着太多、太多的僧尼和瑜伽行者,在那中心则端坐着千年前即已承诺庇护此地的观世音菩萨或隐或现。换句话说,仅仅是西藏的自然地理便饱含一种教化的作用。当然是深藏不露的教化之作用,惟有"渐渐地"过程才有可能意会并为之震撼。有些人会因此而变成一个寻找什么的朝圣者。我尤其对我的康巴老家更有一份认可和归依。我说过,"康巴"是一个"喇嘛之邦"。
但不仅仅是朝圣或者寻找谁。
这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否则就落入了博尔赫斯所批评的那种俗套。在小说里,他对有可能出现的这种结局不无讥讽:"……科钦有一个黑皮肤的犹太人在谈到阿尔莫塔辛时说他皮肤黝黑;一个基督教徒说他张开双臂站在塔楼上;一个红皮肤的喇嘛回忆起他时,说他是'坐在牦牛油上的神像,它是我塑造的,并将它供奉在塔西乌波寺里的'。"博尔赫斯认为,这些说法"向我们暗示,这是一个对各种不同信仰的人都不相同的神。"因此,为了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即原意为"寻找庇护的人"的阿尔莫塔辛,"朝圣者去朝圣的这个圣人自己就是个东奔西跑的朝圣人",他特意在小说的注解里概述了一首关于三十只鸟儿寻找它们的国王西姆格的古代波斯长诗,诗中的三十只鸟儿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国王所在的山上,却发现"它们自己就是西姆格,而西姆格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只,或者是它们全体。"
5
所以当你走在康巴大地上,你终究会渐渐地发现,并不是你去看望或者游历"康巴",而是"康巴"在问候着一个终于回家的游子。同时,你会听见它在无声地呼唤着你的名字犹如你内心深处的阵阵回响。在呼唤或回响的时候,你的名字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一个原来的名字退隐了,它是长久以来与你的世俗生涯相关的象征或联系。而另一个名字诞生了,带着浓重的卷舌音和弹音,质朴而原初,充满精神的慰藉。
"康巴"似乎让你从未如此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的名字,你于是被一个温暖的怀抱热烈地接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