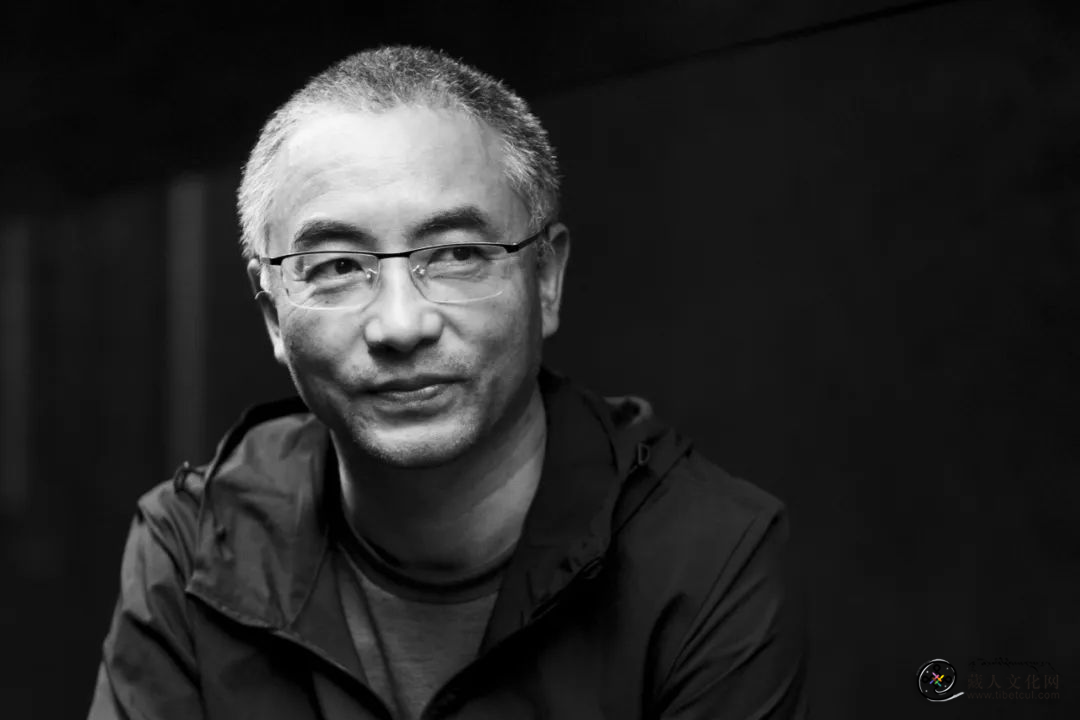真正意义上西藏本土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则起步于八十年代初。1977《西藏文艺》(汉)创刊,1980年《西藏文艺》(藏)创刊,文学刊物的创立极大地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也为长篇小说创作培养了作家。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和精神动力。西藏长篇小说也应时而生,迅猛发展,十年间集中产生了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迷惘大地》《菩萨的圣地》,叶玉林的《雪山强人》,秦文玉的《女活佛》,朗顿·班觉的《绿松石》,单超的《活鬼谷》《布达拉的枪声》等十多部作品。这些作品运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生动书写了西藏近代的历史变革和普通人的命运变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幸存的人》《格桑梅朵》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而《绿松石》被评论界称为“藏族当代文坛第一部直接用藏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①
九十年代以来,西藏作家队伍发生了较大变动,不少汉族作家离开了西藏回到内地生活,这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值得肯定的是,尽管这个时期长篇小说的数量上远不如八十年代,但还是出现了一些精品力作。1993年扎西达娃的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这个阶段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者采用魔幻的表现手法,以59年西藏民主改革和文革十年为写作背景,通过激烈动荡的社会局势,描写了各类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构成一幅既现实又虚幻的历史画卷。时隔几年,1997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藏族女作家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这部22万字的作品,通过主人公央吉卓玛的心路历程,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旧西藏大家族的衰败史,深刻揭示了旧西藏严峻的社会问题,强调唯有接受变革才是西藏发展的必然旨归。《无性别的神》的出现,让人耳目一新,使得西藏的文学叙事有了新的面貌,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力量。也因此,这部长篇收获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殊荣。一年后,1998年由旺多先生创作的长篇母语小说《斋苏府秘闻》出版。小说通过旧西藏贵族阶层内部激烈的矛盾纠葛,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权利之争,有力地批判了旧制度的腐败。在这部长篇中,旺多先生以他丰富的历史学、民俗学的知识书写了西藏传统的风俗人情,是为作品的另一个亮点。
新世纪以来,西藏长篇小说创作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产出了《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紫青稞》《风雪布达拉》《祭语风中》《光芒大地》《藏婚》《藏漂十年》《天堂上面是西藏》《雪葬》《直线三公里》等汉文长篇小说和《昨日的部落》《花与梦》《天眼石之泪》等母语长篇小说,以及《绿松石》《斋苏府秘闻》《远去的年楚河》等汉译本长篇小说,共计三十多部。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力,比如,尼玛潘多的《紫青稞》(汉文),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荣获第六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汉文)入选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获得“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三强、2015年度“中版好书”、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芳草》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等殊荣;旦巴亚尔杰的《昨日的部落》(藏文)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艾·尼玛次仁的《天眼石之泪》荣获第三届全国岗尖杯藏文文学奖,充分显示出西藏作家持续不懈的创作热情和不断奉献精品佳作的创作能力。
新世纪以来的西藏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创作的大环境、作家的文学观念、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都有许多拓展与革新,这既是西藏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也预示西藏长篇小说创作新的方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解读。
新世纪以来,置身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西藏图书市场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长篇小说的出版获得前所未有的生长气候。(删除了一句)另外,新世纪以来活跃在西藏文坛的作家,大多经历过8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的熏陶、滋养,90年代的沉潜、学习、酝酿,进入新世纪后,他们在思想与技术上也逐步进入创作的成熟期。而时代也在纵横两条线索上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可书写的素材;从纵向看,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西藏社会的发展历史、充盈的现实生活、不断成长中的人,给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从横向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与世界开展的全方位交流更加频繁与深入,这些从根本上带动了社会环境、经济生活、价值取向、审美精神等一系列的改变,也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构成了时代的复杂语境。西藏虽地处边境,但在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也不是旁观者,同样置身于时代的潮流中,加上西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激荡也为作家创作营造出特别的复杂语境,使得作家的创作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展开维度。
国家政策的倡导和文学奖项的激励,也极大地推进了西藏长篇小说的创作。目前,西藏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可参加评奖的奖项除了国家级的 “五个一工程奖”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外,还有自治区级的“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西藏作协设立的“新世纪文学奖”以及市一级的“拉萨市政府奖”“雅砻文学艺术基金奖”“珠峰文学艺术基金奖”等,这些政策和奖项的设立在发现作家、激励创作、扩大长篇小说的影响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家被称作“时代的代言人”,长篇小说在把握时代,反映历史方面又是最理想的体裁,因此,很多作家都会自觉地把写作长篇视为证明自我写作能力的一种方式。新世纪以来,西藏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也许和作家的这一主观动因有一定的联系。
与八九十年代的西藏作家不同,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与交通便利,使西藏与世界的距离不断缩小,全球化、现代化的影响走向纵深。与老作家相比,年轻的作家们接受到更多元的文化滋养,创作思想与视野更加开阔,知识结构不断完善,这些都为他们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2018年第3期《芳草》杂志刊登了一篇《次仁罗布:温暖与悲悯的协奏》的访谈,文中,作者周新民提问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在我看来,您不仅仅接受了藏族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深受国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熏陶。您可否举例说明最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哪些?它们给了您什么样的启迪?”次仁罗布在回答中,例举了海明威、福克纳、鲁尔福、川端康成、奈保尔等人的作品对他创作与思想的启发。②无独有偶,中国作家网2014年1月3日发表的《白玛娜珍:悲悯情怀是文学境界写作追求心灵的自由》一文中,作家白玛娜珍在回答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胡沛平提出的“您时常阅读国内和国外其他作家的作品吗?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的问题时说:“我从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汉文翻译作品。文本显示出的那些不拘一格的叙述方式,具有异国文化特色的故事、人物及思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我喜欢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亨利·米勒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拉日巴传》《莲花生大师传》《西藏度亡经》《德兰修女传》《甘地传》、西蒙波娃传记、《西藏生死书》、香奈儿传记、《慧灯之光》《佛本生故事》以及《我的名字叫红》和大江健、张爱玲等等还有很多我的朋友们写的书,一一例举不完。”“除了文学作品,我的阅读兴趣较广泛,也喜欢时尚杂志、医学刊物、生命科学、宇宙之谜以及自然科学类、哲学、心理学、佛学类书籍等等都很爱看。”也表现了作家开阔的阅读视野和多元文学思想的接受经历。
八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学长篇小说创作,几乎都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九十年代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在艺术上采用意识流、时空倒错等叙事手法,呈现出奇特风貌和神秘氛围,是西藏长篇小说中少数现代先锋文学的代表。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西藏的交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旅游业日渐成为西藏的支柱产业,“天堑变通途”,“坐上火车去拉萨”成为一种时尚,曾经神秘的西藏更多地向世界洞开,对现实的西藏社会、西藏人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成为很多人的愿望。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讲,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有浓郁的藏地特色,有深厚的生活底蕴,有浓厚的烟火气息的西藏文学作品成为读者新的阅读期待。
新世纪以来,西藏本土作家逐渐成长,他们积极寻找适合表现现实生活和时代需要的文学叙事模式,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理念与方法被更多的西藏作家认同并选择。2015年9月21日,《中华儿女报刊社》发表了一篇题为《用笔还原真实的西藏》的访谈,其中,被访者次仁罗布表达了“写作要坚持展示内心本质的文学道路,用笔还原真实的西藏”的写作态度。他说:“‘还原真实的西藏’就是要超越上世纪8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的藏族文学的辉煌,找到属于当下的一个叙事世界,在作品里呈现藏族人的内心世界和传统的价值观。”之后作家尼玛潘多也在《紫青稞》的创作谈中说:“我看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书,但是神秘和猎奇大行其道。很多人对西藏真正的生活不了解,对普通老百姓的情感不了解。”“我在创作之初,并没有预想要表达社会转型过程这么个宏大题材,或者肩负起历史、社会责任感,我只是很喜欢这样一群人,希望能够展现他们的生活。我希望能还原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这也许就是不自觉的社会担当吧。”。③
也许正是阅读者和写作者共同的心理合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向现实主义的回归很快成为西藏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趋势。
四、作品:主题多元,文体新颖
1、主题多元,内涵丰富
(1)历史书写与政治叙事
吴秉杰在《“骏马”奔腾向前方——评近年少数民族长篇创作 》一文中说:“历史创作无疑是长篇小说的优势领域,它的线性长度与历史纵深的要求相一致,作为时间的艺术,综合性与宏观把握又与长篇的丰富及复杂性要求相一致。” ④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新世纪以来,西藏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大多把西藏几十年历史变革,世事沧桑作为背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描写西藏社会的变革与人的发展。
《风雪布达拉》是克珠群佩、王泉共同写作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以20世纪初拉萨城真实的历史风云为背景,通过农奴主与贫苦农奴之间的矛盾斗争,歌颂了爱国宗教人士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感人事迹。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继承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叙事方法,语言质朴,情节生动,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紫青稞》是尼玛潘多的代表作。于2011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过阿妈曲宗和她的三个女儿的曲折人生经历,表现了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历史变革,生动表现了西藏农村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精神成长的历程。
《光芒万丈》是70后西藏作家张祖文的作品,张祖文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入藏工作。小说从异乡人的视角考察藏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呈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50多年的历史变迁,表现了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对爱情的忠贞,歌颂了汉藏民族间的血肉联系。
(2)民族志与心灵史
《绿松石》是朗顿·班觉的代表作,它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一部藏文长篇小说,新世纪初由次多、朗顿·罗布次仁合作翻译成汉文,2009年在《芳草》第2期全文刊出。
这部长篇围绕着一颗珍贵的绿松石头饰勾连起各个阶层的人,讲述了平民班旦一家三口因为这颗宝石而遭遇的曲折命运。作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的老作家,朗顿·班觉的这部长篇的立意为揭露旧制度的罪恶,表达对善良者的同情。值得肯定的是,朗顿·班觉没有让这部作品成为简单的表现阶级斗争主题的叙事作品,而是凭借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广博的知识,“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藏社会上自噶伦下至乞丐的生活以及藏族传统的风俗礼仪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和描绘, 鲜活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旧西藏世俗生活的风景画以及藏族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历史记忆”。⑤
《复活的度母》是作家白玛娜珍的作品,作品以西藏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为背景,将普通人的情感经历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相互交织,揭示了西藏的沧桑巨变,展示了普通人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发展轨迹。白玛娜珍在这部长篇中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让琼芨白姆以及茜玛母女三人轮流充当叙事主角,第一人称的叙事策略突出了主人公微妙的内心世界,被著名作家吉米平阶称为“藏族女性的心灵秘史”。⑥
评论家石华鹏在《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写作品质》一文中写到:“一个小说家只有迈入成熟之阶段,写作才能散发出真正的自由和意义来”,⑦近年来,次仁罗布的写作也开始显示出这样的成熟气象。《祭语风中》是次仁罗布201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主副两条线索推进,主线以西藏近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变迁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晋美旺扎从僧人到俗人的经历,讲述了西藏历史上的59年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民主改革以及中印自卫反击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副线讲述了藏族历史上的藏密大师米拉日巴超越苦难、参悟生死的一生。小说中两条线的交织延伸,生动表达了藏族人的生死观念与生命态度。《祭语风中》的出版,标志着次仁罗布创作的一个新高度,也是新世纪以来西藏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3)现实关照与社会批判:
次仁央吉是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藏文写作的重要作家,近两年,她的写作越发成熟,
在小说集《山峰的云朵》收获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2017年她又推出了长篇小说《花与梦》,这是西藏第一部女性作家创作的母语长篇小说,小说一面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飞速发展,交通与通讯的便利拉近了城乡的距离,更多的来自乡村的人走进了城市,近距离感受城市的现代与繁华。但城市的光鲜亮丽的景观与丰裕的物质背后也有更多的竞争与压力,有更加异化的心灵与冷漠的人际。在这里商业主义的利益追逐,让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更多面临考验,甚至溃败。没有根基和实力的农民工要想在城市梦想成真就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经历更多的挫折。
《花与梦》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讲述了四个进城务工的藏族农村女孩的人生故事,描写了她们从心怀梦想到痛苦挣扎,从人生溃败到幡然醒悟的命运沉浮。小说如同一面镜子生动反映了几个女性经历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磨砺,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底层女性群体命运的深刻思考与人文关怀。
次仁央吉是一位认真写作的作家,她的写作不回避现实的矛盾,没有做作和夸饰。女性如何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如何才能在精神上成人,次仁央吉在《花与梦》中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在表达了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的同时,作者也批判了物欲贪婪对女性心理精神的腐蚀,肯定了正直、勤劳的品格,提醒现代女性唯有自立、自强、自尊才是幸福的正途。
2、文体的创新与探索
与九十年代西藏长篇创作中现实主义文学与先锋文学并存,多元文体相互融合的状况相比,新世纪的西藏长篇小说创作显示出鲜明的发展倾向:回归现实主义。但面对鲜活的作品,这样的判断不免归于笼统。如果我们对新世纪西藏长篇小说的文体进行细致的分析的话,又能在这些作品之间看到不同,次仁罗布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具有代表性。他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在“怎么讲”上别开生面,安排了两条线索推进故事:一条线索是主人公晋美旺扎从僧人到俗人的经历,一条线索是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藏密大师米拉日巴排除困难解脱成道的一生。小说中,这两条线索的自由交替,打破了时空的阻碍,让作者能够自由穿行于人物的前世今生,使叙事具有了更开阔的界面,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成功融合,也是对西藏长篇小说文体内涵的丰富。
西藏长篇小说应时而生,且顺势而为,创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从整体上来看还存在不少缺憾。长篇小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体,它更是一个写作者思想力、历史观、价值观的展开过程,对作家的知识储备、经验阅历、视野格局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从已出版的西藏长篇小说作品来看,不少作家在这一方面还有所欠缺,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不足,驾驭长篇的能力较弱,使得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的把握不够,不能充分深入地表现人的命运和人性的丰富性,有一些作品甚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存在概念化、脸谱化的现象,另外,不少作家还是乐于在写实主义的框架内创作,缺少对文学形式的创新和实验。
我们知道,长篇小说“这个文体曾经或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承担的丰富人类精神世界、提升民族素质的使命,也是无可回避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篇小说不单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主餐,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它的发展也就格外引人关注。⑧新世纪新时代赋予长篇小说的责任与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大,作为西藏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唯有在创作中牢记使命与担当,正视不足,不断突破局限,方能写出有厚度、有高度的作品。
注释:
①《评析长篇小说<绿松石>》,西藏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摘要,次仁顿珠。
②《次仁罗布:温暖与悲悯的协奏》,周新民,《芳草》,2018年第3期。
③《尼玛潘多<紫青稞>》,《中国西藏网》,王舒,2010年9月2日。
④《“骏马”奔腾向前方——评近年少数民族长篇创作 》,《文艺报》,吴秉杰,2011年12月31日。
⑤《诗化的藏地民族志———评朗顿·班觉的长篇小说<绿松石>》,《当代文坛》,俞世芬,2009年第3期。
⑥《藏族女性的心灵秘史》,《民族文学》,吉米平阶,2008年第7期。
⑦《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写作品质》,《文学教育》,石华鹏,2016年6月 上旬刊。
⑧ 《长篇小说创作:需要讨论的三个问题》,《黄河文学》,梁鸿鹰,2010年第1期
注:本文为“藏财教指(2018)54号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民族文学》201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