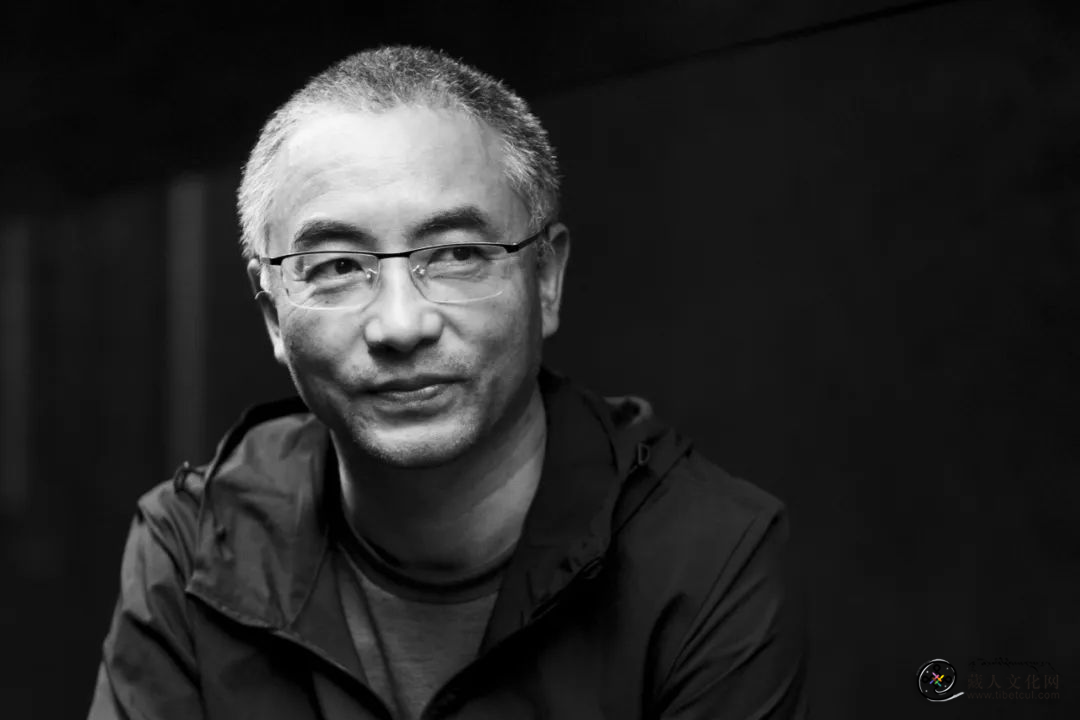曾以《尘埃落定》轰动中国文坛的藏族作家阿来也倾心于散文的创作。他的散文篇章主要被收录在《就这样日益丰盈》《大地的阶梯》和《看见》三本文集中,此外还有一些未入文集的零散篇目。作为一个对自己要求甚高的作家,阿来的散文往往是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准。笔者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阿来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学?确切地说,阿来如何借助其散文作品来传达他的(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佼佼者之一,阿来对(少数)民族文学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这在他的散文中有着较为集中的表现。本文旨在对他的这些思考作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论述。笔者以为这种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比如可以深化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了解,可以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提供某种启示等。概而言之,阿来的民族文学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非母语写作的独特价值;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化表现。
一
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收获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更成为整个中国文学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的,用以专门指称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对于命名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而言,“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有其积极意义。但对于某些对文学认识不清之人,它也具有一种潜在的理论误导性,即往往会用一种关于文学对象的认识来取代关于文学功能的认识。“民族文学”当然会以某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民族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的功能也仅限于有限的民族范围。遗憾的是,很多人恰恰陷入了这样一种理论的误区。这些误入歧途之人往往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以鲁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作为之所以如此的依据。
对于上述做法,阿来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在这一点上,我决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他并且呼吁读者注意这种“普遍性”的表达:“在我们国家,在这个象形表意的方块文字统治的国度里,人们在阅读这种异族题材的作品时,会更多地对里面一些奇特的风习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作为这本书(指《尘埃落定》——笔者注)的作者,我并不反对大家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到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普遍性。因为这种普遍性才是我在作品中着力追寻的东西。”笔者以为,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不能作一种简单和机械地理解。首先,这句话是否源自鲁迅一直以来就颇受争议。鲁迅的原话出自他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的一封信中的一段:“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这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意思显然有很大出入。即便撇开出处问题不谈,对这句话本身也不能作一种简单和机械的理解。民族性的题材中往往潜藏着世界性的因素,具有一种普泛化的可能性,但并非一切关于特定民族的描写都具备这种可能。反之也是,很多时候文学所表现的特定的民族对象仅仅属于某一民族所特有,完全不能对其意义加以泛化。或许正是看到某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误解了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一味地注重文学的民族性而忽视了文学的世界性,阿来特别强调了对文学普遍性的追求,这种关于民族文学的认识无疑是清醒和明智的。
那么,阿来所追求的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民族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这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的文学。阿来说道:“有很多的学科在研究此地与彼地,此种文化与彼种文化的不同,但是,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却应该致力于寻找人类最大限度的共同点。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决定了不同国度的不同命运与不同的发展水平,文化基因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民族的不同面貌,但人类和人,最根本的目的,难道不是一样吗?”他以《尘埃落定》为例指出“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它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为这部小说呼唤没有偏见的,或者说愿意克服自己偏见的读者。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共同的名字:人。”关于文学,有个老生常谈的说法:文学是人学。原意是指文学以人为表现的对象和中心。而阿来关于“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的重申却旨在强调文学对人之为人的共通性的表现,这种共通性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民族文学的普遍性。基于这种认识,阿来对“民族文学”的理解与很多民族文学作家不同,不去刻意强调那些民族差异性的内容,而注重对不同民族一致性部分的表现。巧合的是,这种观点正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构成了某种暗合。阿来也因此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比如民族文学批评家姚新勇就曾批评阿来似乎要有意淡化自己的民族身份而过于追求一种政治的正确性。殊不知,阿来的这种民族文学观念其实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并不是有意迎合意识形态的诉求。首先,这源于阿来高远的文学追求。阿来是一个对自己有着很高的文学期许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要当作家就要当第一流的,否则不如不去写作。对于这样的作家来说,是不会满足于创作那种只关注本民族的生活,更关键的是只具有本民族意识的民族文学作品。因为这样的创作往往是对民族文学作了一种保守而狭隘的理解,不利于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壮大。其次,这与阿来对文学本身的理解有关。民族文学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学,也必须具有文学的特性,不能因为带上了“民族”二字就要人为地限制它作为文学的特点。阿来曾在《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一文中写道:“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家世、阶层、文化、种族、国家这些种种分别,只是方便人与人互相辨识,而不应当是竖立在人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这些界限不只标注于地图,更是横亘在人心之中时,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性,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来认为民族文学的精义恰恰是要超越单一民族的界限,去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的文学”。再次,它也与阿来受到的异域思想的影响有关。阿来曾坦言“我比较信服萨义德的观点,他说,知识分子的表达应该摆脱民族或种族观念束缚,并不针对某一部族、国家、个体,而应该针对全体人类,将人类作为表述对象。即便表述本民族或者国家、个体的灾难,也必须和人类的苦难联系起来,和每个人的苦难联系起来表述。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贯彻的原则。”如果说萨义德对阿来民族观的形成主要是一种文化思想的影响,那么在文学思想上阿来受到的影响则有辛格、莫瑞森、菲利普·罗斯、艾里森、奈保尔等人。比如阿来认为“流散写作”的代表人物奈保尔的小说《自由国度》表现的就“是一种新的超越种族的世界性眼光,而不是基于一种流民的心态”。这种文化和文学思想上的双重影响都赋予了阿来一种开阔的民族胸怀,而不再拘泥于一种单一的民族视野。
应该说,正是因为阿来秉持着这样的民族文学观念,他的小说才能摆脱一般的民族文学作品容易陷入的窠臼,具有一种广阔的视域,达到了一种相当的高度,甚至在国外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在这个意义上,某些质疑阿来不做藏族文化代言人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为代言者,往往倾向于一味地认同本族文化而排斥他族的文化。“弱势族群的作家,常常会被人强加上一个代言人的角色。这个角色,有时会与个人表达之间,形成非常大的冲突。所以,我想说的是,在这里保持冷静与低调是容易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保持一种明确的个人立场。”在这里,阿来关于民族文学的“个人立场”是他的独特之处,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学追求。
二
如果从语言的角度,可以把民族文学分为两类:母语写作和非母语写作。前者指的是民族文学作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写作,后者指的是民族文学作家使用非本民族(主要是汉族)的语言进行写作。其中,非母语写作达到了民族文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并且这种优势还在继续扩大。阿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了整个大陆中国,打破了境内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与文化上的封闭与禁锢,当汉语普通话成为官方语言,借国家机器的强力在所有族群中推行时,一种统一的语言对不同文化的整合就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与力度展开了,结果自然是越来越多的非汉族人来使用这种语言,同时建设这种语言。”阿来自己的写作就属于非母语写作——他的全部作品都是用汉语进行创作的。
既然如此,民族文学作家使用汉语进行非母语写作与汉族作家的写作完全一样吗?显然二者会有诸多不同之处。那么,非母语写作的独特性何在?它给整体的汉语写作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学贡献?对此,一般认为非母语写作的文本在题材的表现上与汉族作家的创作有区别,往往表现了迥异于后者的景物、习俗、礼仪、观念等等。总之,是一些容易感受得到的、属于作品内容层面的东西。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些人往往低估了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其独特的艺术价值,认为民族文学不过是汉族作家创作的一种“翻版”,是相对于后者来说“慢一拍”的创作。对此,阿来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直到今天,恐怕还没有人真正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看这些所谓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除了为汉语言文学提供了一些新的题材样本之外,还增加了什么新鲜的东西。比如,这样一些异族人写成的汉语言文学作品,是怎样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开辟了汉语言文学新的语感,新的想象空间,并找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表达这些想象的更自如、更诗意,当然也是更为文学化的方法。”“非汉语的人们加入汉语的写作中来,并非仅仅是同化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也给这种语言表达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丰富了这种语言,扩展了这种语言。”
这种对汉语言的丰富和扩展是非母语写作本身自然带来的结果吗?当然不是。它实际上源于民族文学作家对非母语写作的深刻洞察和苦心经营。阿来看到,异族(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通过接受以汉语为主的教育,接受汉语,使用汉语,会与汉民族本族人作为汉语使用者与表达者有微妙的区别。汉族人使用汉语时,与其文化感受是完全同步的。而一个异族人,无论在语言技术层面上有多么成熟,但在文化感受上却是有一些差异的。”他举例说:“汉族人写下月亮两个字,就受到很多的文化暗示,嫦娥啊,李白啊,苏东坡啊,而我写下月亮两个字,就没有这种暗示,只有来自于自然界的这个事物本身的映像,而且只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天文景观相联系,我在天安门上看到月亮升起来时,心里却还是本民族神话中男神或女神命名的皎洁雪峰旁升起的那轮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看上去,都大,都亮,都安详而空虚的月亮。”在这种比较的基础上,阿来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追求:“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和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则是圆满与安详。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然后,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这种描绘,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已经把一种非汉语的感受成功地融入了汉语。这种异质文化的东西,日积月累,也就成为汉语的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被传播。这样,悄无声息之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
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要实现这种追求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语言的转换或翻译的问题,对此阿来提供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尤其是我在写人物对话的时候,我会多想一想。好象是脑子里有个自动翻译的过程,我会想一想它用藏语会怎么说,或者它用乡土的汉语怎么说,用方言的汉语怎么说,那么这个时候,这些对话就会有一些很独特的表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提供的汉语文本与汉族作家有差异。有人说,像翻译,我说,其中有些部分的确就是翻译,不过是在脑子里就已经完成的翻译。”也就是说,他在书写前脑子里首先有个文字翻译的构思过程,根据文化翻译的理论,文字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翻译。经过这样的翻译,就创造出了一种输入了新的文化元素的文本,也就与汉族作家创造的汉语文本“有差异”,从而彰显出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这实际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睿智的批评家认为阿来的小说尽管是用汉语创作的,但给人的感受又是很藏族的,从而具备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民族文化价值。比如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句子:“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这种对地理方位的表述就带有浓厚的藏族色彩。又比如:“亲爱的父亲问我:‘告诉我爱是什么’?‘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这种对爱的理解虽是出自傻子少爷之口,也体现了藏族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例子在阿来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阿来的语言运用策略有利于把少数民族(藏族)的文化感受注入汉语言,从而丰富汉语言的表现功能,增强其活力和保持其不断发展的趋势。这无疑是对非母语写作独特价值的一种重要彰显。而从整个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情况看,非母语写作的困境很多,诗人于坚就曾指出,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写作既丧失了母语的根基,也未能在通用的汉语写作中获得独立的地位。因为他把语言的转换仅仅视为一种既定阅读习惯的认可,而创造的目的成了次要的,在这种转换中,对汉语的具有利己目的的媚俗掩盖了写作的根本目的。写作似乎仅仅是为了得到汉语文学的一般性承认,并获得相关的所谓作家待遇。”从这个意义上看,阿来关于非母语写作的思想确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笔者发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小说作品的文化色彩非常浓厚,许多作品里都充满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元素,这几乎构成了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往往是源于民族文学作家一种自觉的赋予。比如阿来就把其文学创作当成了一种表现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作为一个作家,我不会空谈文化多样性,我也不知道如何在宏观的层面上保持弱势民族的文化特性,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基因特别丰富的世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文化在我首先是一份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我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
要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首要的问题是表现一种真实的文化。这看起来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并非易事。之所以对民族文化的真实表现会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有来自于民族内外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外界会形成对某个民族真实文化的误读。比如阿来在《西藏是形容词》一文中就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说。很多人心中都有“关于西藏的定性:遥远、蛮荒和神秘。更多的定义当然是神秘。也就是说,西藏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应该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一个形容词可以附会了许多主观的东西,但名词却不能。名词就是它自己本身。”何以如此呢?“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许许多多的人并不打算扮演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他刻意要进入的就是一个形容词,因为日常状态下,他太多的时候就生活在太多的名词中间,缺失了诗意,所以,必须要进入西藏这样一个巨大的形容词,接上诗意的氧气袋贪婪地呼吸。”可见,这种误读的形成往往出于文化他者某种特殊的文化心理(比如文化弥补的心理),这样一种误读虽然荒谬地存在着,但实际上很难彻底地消除。另一方面,来自外界特别是强势文化的误读又会对某些所谓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产生影响,进而加深这种误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那个被叫做西藏的地方,总是少数人天然地成为所有人的代言。而这些代言往往出于一己之私,或者身处其中的利益集团的需要,任意篡改与歪曲族群与文化这些概念的内涵。”阿来对此无疑是不满的。在他看来,民族的本原文化不容被歪曲和污名,而只应被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来。阿来特别注重对民族文化的真实表现,并为此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比如“《大地的阶梯》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因为,小说的方式,终究是太过文学,太过虚拟,那么,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么,我要记述的也该是一个明白的西藏,而非一个形容词化的神秘的西藏。”可见,阿来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化解着所谓西藏的“神秘”,致力于描绘普通人在西藏文化中真实的生存境况,从而恢复这种文化的全貌。
为什么阿来特别看重对民族文化的真实表现呢?这与他对文学和文化的理解有关——“在我的理解中,小说家是这样一种人,他要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种族间传递信息,这些信息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沟通与了解,而真实,是沟通与了解最必需的基石。”原来,文学对真实文化的表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了解。这又可以见出阿来关于民族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远见卓识。这在《遥望玉树》一文中有着具体而生动的体现。面对电视上出现的共和国军人和藏族人民一起救灾的画面,阿来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个画面告诉我们很多,人类共同的基本情感,不同的族群同心协力的可能。尤其是在今天,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总是被放大,被高度地意识形态化,而不同的人群之间,可以交流与相通的那些部分总是被忽略,不被言说与呈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这样的画面尤其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在当前的后现代语境下,“民族(文化)认同”正在不同的领域被大家津津乐道为热门话题。所谓民族认同,简而言之即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认同。当下对民族认同的宣扬其实有着复杂的背景,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民族认同概念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本民族文化相对于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实际上内在地隐含着一种对他民族及其文化的排斥性,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无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抑或全球的文化发展,过分强调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而忽视对他者文化的认同,都不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甚至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基于这样一种理解,阿来关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沟通与了解的认识虽然是逆民族(文化)认同的潮流而动,但其实真正击中了当前文化发展问题的一个要害,因而具有一种可贵的纠偏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
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樊义红,男,1978年生,汉族,湖北荆州人,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文学的民族认同特性及其文学性生成: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