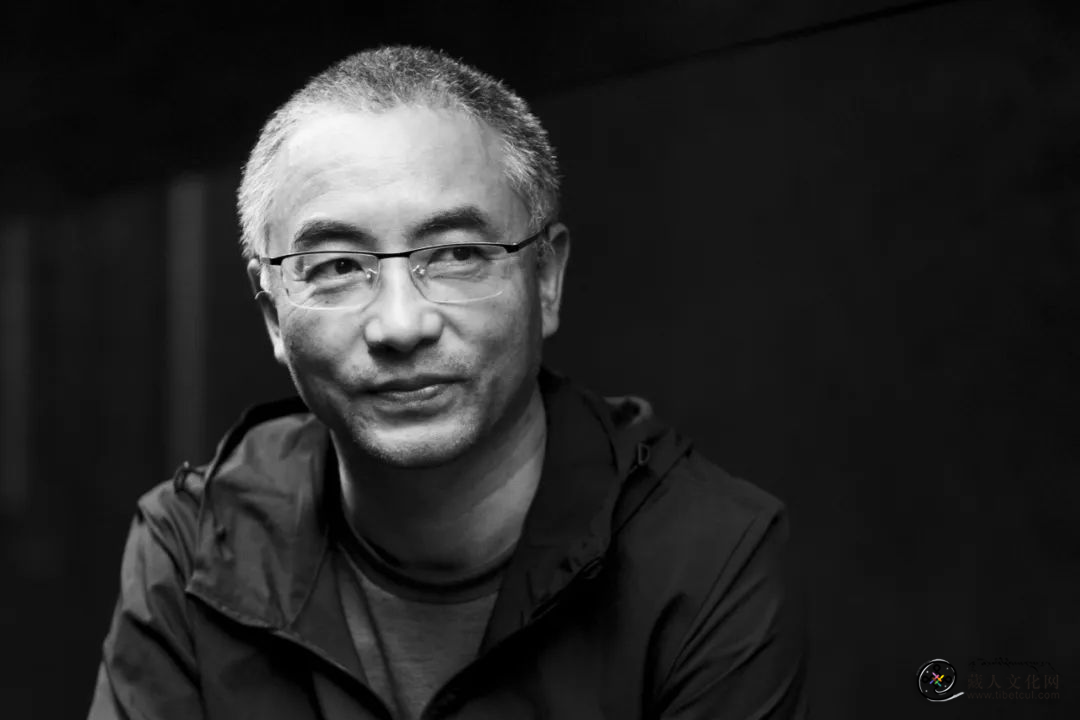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摘 要】甘肃是西部文学生成的重镇,甘肃的诗歌不仅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带一路”上的文学风景线。扎西才让、刚杰·索木东、离离、唐亚琼这四位诗人是甘肃典型的“70 后”诗人。在新时代里,他们的诗歌呈现出了西部诗歌的独特意蕴与抒情方式:扎西才让的神性表达,刚杰·索木东的“根”文化情结,离离的西部女性性情,唐亚琼的西部都市写真等都无疑凸显了西部诗歌在“丝绸文化”地带的发展与方向。对此的阐释论述,必将见证历史、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导向。
【关键词】西部;甘肃;诗歌;“70 后”;神性
在中国诗坛上,甘肃诗人总是背靠雪域高原这块大地,坚守着自己的诗歌创作之梦,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扎西才让、刚杰·索木东、离离、唐亚琼四人是甘肃“70 后”较活跃的诗人,他们(她们)致力于诗歌创作20 多年,现已成就丰硕。他们(她们)生活在甘肃境域,并以民族多元文化语境为坐标书写“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甘肃。这四位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内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个性化,这归因于他们同生于“70 年”这一代际和对西部的独特感知。四人中,扎西才让与刚杰·索木东为“前 70 后”,唐亚琼与离离为“后 70 后”(如果以 1975 年为中间段)。在诗歌创作中,他们又难免呈现出各自的共识性与独特性,而且也表现了西部诗歌的多元性。从这四人的诗中,我们能看出独特的民族精神在当代诗歌中的多元化表达,这种表达将丰富着中国当代乡土诗歌的抒情方式与经验化表现。
一、扎西才让:西部民族文化与神性表达的“70 后”

扎西才让,藏族,1972 年生,甘肃籍人。扎西才让最有特征的诗都收集在《大夏河畔》中(作家出版社 2016 年版)。这部诗集成就了扎西才让,加深了他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影响,同时也激活了诸多“70后”诗人的创作热情。
扎西才让是少数民族诗人,因此他的诗歌中把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不断加以强化,使其呈现出民族诗歌的“亮丽”,铸成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元性与丰富性。扎西才让擅长从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某种灵性,打磨其诗歌的内在美与整体观。这些诗的“灵性”就呈现在《大夏河畔》的部分诗中。扎西才让诗中更表现出“70 年代”人的使命感,这一使命感使诗人在借用文化元素、地域意象加以呈现的同时也把自然属性与诗人的代际焦虑合二为一,一一表现。
“大夏河”,是诗人扎西才让要给世人展示的一个文化世界,这一空间里的原始神灵、野性、木匠、冷漠的天葬师、婚嫁的女儿,阳光和雨露等意象均能承载诗人的个人情感与生活体验,传递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对于情绪,诗人曾这样写:
秋天,大夏河摧枯拉朽,暴怒地卷走一切,/我们在愤怒中捶打自己的老婆和儿女,/像极了历代的暴君。
不难发现大夏河在代际中遭遇现代性创伤,遭遇被破坏、改变的命运,这才使其暴怒。大夏河是我们,我们也是大夏河,我们无可奈何地跟着大夏河的嬗变,而走进不同的代际中,不过我们把释放焦虑情绪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亲人,大夏河却无情地展示出自己个性与疯狂,表现出其面对自然天象的无奈与妥协。因为在这一方水土之上,作为空间符号的“大夏河”是“70 年代”人走过的影子见证,我们从中能找到他们的生活印记。在《达娃央宗》一诗中他说:
那年她八岁,我九岁。/当我压住她,她伤心地哭,/仿佛过家家是件无耻的事。/我压倒她的时候,太阳就在院子里。/别人也在院子里,站在一旁哄笑。/后来她嫁给了别人,那人叫我叔叔。/我答应着她,走向了更为遥远的过去。
诗人连用了那年、后来、现在三个表示时间变化的词,就写完了人生的大半个时光。我想“达娃央宗”与“大夏河”都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总之,大夏河在扎西才让的诗中并不是指严格地理意义上的大夏河,也不是特指的河流彼岸,而是文化艺术,是精神的彼岸世界。大夏河也是“70 年代”人生存的历史见证,是个体时间路过的浅层表达,其承载着紧张的时光维度。从“大夏河”到“桑多山”,这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路过,更是诗人心理上的一种转变,由此也牵动了叙述上的转型。从文学地理学的意义而言,地理往往成为诗人建构诗歌特色的影响源。古有屈原的楚地、李白的秦地,今有阿来的“马尔康”等。杨义认为:“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是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使文学连通‘地气’”。 [1]
“70 后”人对地域文化是怀有热情的。扎西才让将诗集的卷二命名为“桑多山”,这又是原始宗教文化的开启。如果说大夏河的文化基因是“江河文明”的话,那么“桑多山”无疑要从“高山文明”说起。这种文明的特点是崇拜神山、圣湖,颂扬弓马勇武,具有世界屋脊的崇高感、神秘感和雪域精神。在这部诗集中,“桑多山”是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见证,这种精神代表着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
顺着诗人的文化观念与创作激情,诗性又从高山文明回归到农耕文明。在《途中》诗人写道:“歌行者吟过的田野上,那些深秋沉重的/紫色草穗,笨笨地深深地一躬到底。”这是从高山文明到农耕文明的转型,是文明进步的见证。诗人就是在这样的文明变迁中静下心来思考生活,叩问生命。在《桑多山》辑中,我们可以看到“桑多山”经历了从高山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现代文明的转变,这种时间上的推进之快,诗人化用为“一袋烟的功夫、青稞黄的速度、什么也来不及想、什么也来不及说、什么也来不及做”等一系列时间的代名词,暗示了个体生命与民族历史文化的相融和对峙。在对峙中表现了“70 后”人的代际焦虑。
走向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中国美学中常把死亡与罹难看成悲剧之美。《大夏河畔》中诗人写下了《那遥远的花香》《圆寂》等一些诗作,足以引证出诗人对生命的叩问。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在没有感受到死亡之时,一个人实际上也就遗忘了存在,而存在则是提前到来的死亡,这正是许多作家通过对死亡现象的描写而触及到对生命易逝的感伤,这种感伤更多来自于孤独,《大夏河畔》中有不少表现人生孤独的诗篇,但这部诗集的神性意味远远超越了其抒情性。
藏传佛教文化对扎西才让的写作有较为深刻的影响,诗集《大夏河畔》就凸显了藏传佛教思想中崇拜万物的特征。集子以“大夏河”命名,实际上就已经隐含了诗人对“水”的崇拜。集中又以“桑多山”命名,更体现了诗人对“山”的崇拜,藏文化中有“羊年转湖、马年转山”的习俗。诗集《大夏河畔》也反映了诗人对“水神”和“山神”的崇拜。当然正是因为崇拜“神”,才有了对其祭祀的一切行为。扎西才让在其诗中也体现了神性崇拜。诗中他首先从对“人”的崇拜上升到了对“山神”的崇拜。比如《桑多山》辑中的《桑多山上的柏树》《桑多山上的雪豹》《狩猎者》《头戴玛瑙皮帽的扎西吉》等诗中首先隐喻了对“人”的崇拜,从而突显了桑多人的精神价值,接着又开启了对“山”的崇拜,诗人写了《晚风里的桑多山》《酒后雪山》《山祭》等。
在诗集中,他把这些崇拜又落实到了对“山神”的崇拜中。他在《山祭》中这样写道:“我们手执火把,/上了高山。/祭祀山神的夜晚,/那些山顶的积雪,又一次被火光照亮……/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咳嗽,/还是惊醒了那些熟睡的山神、水神和树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山是男性的象征,先秦时期有向山求子之说,水则是一种女性的象征。山的崇拜其实体现了对男性的崇拜,水的崇拜体现了对女性的崇拜,不同的文化崇拜共同渗透着扎西才让诗歌的生命体验与神性特征。
二、刚杰.·索木东:西部根文化书写的“70 后”

刚杰·索木东主要致力于乡土诗歌创作,其诗歌入选《2017 年中国诗歌年选》《2016 年中国诗歌年选》《2000 年中国诗歌精选》等。部分诗歌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藏文、蒙古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多种文字发表。 2017 年出版的诗集《故乡是甘南》列入中国作协资助项目“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
燎原说过:“天才在他乡是寂寞的。”用一种深度和厚度来抒写西部乡土,是刚杰·索木东与西部其他诗人卓尔不群的方面。他是以都市的眼光来审视乡土世界,以城市的现代进程回望发展缓慢的“前乡村”。他笔下的乡土往往在历史的过去中呈现出它的沧桑和独白,譬如:静坐的寺院、反复劳作的土地、逐年退化的草原等。刚杰·索木东有着广阔的诗学眼光与写作经验,他是典型的“70后”乡土诗人。 20岁以后其写作语境发生了改变(诗人从乡村移居到省城),因而他的诗作中具有强烈的怀乡意识。故乡在诗人心中是一个整体,并不是碎片化的组成。在“故乡”的整体意象中,诗人任意撕下一片,都可以是一首诗歌佳作。比如像《青稞点头的地方》中诗人这样写:“青稞点头的路口/风把四季的门次第打开/一段路在脚下不能到达的地方/把零落的肋骨仔细收藏。”青稞地是一个整体的地域空间,他的范围可以无限延展、放大,在这个无限放大的空间里,诗人自由想象和书写那些乡土中劳作的场景,抒发乡情。
从文化层面而言,青稞地又是农耕文明的象征,其渗透着游牧文明的印记,处在两种文明的交汇地带中的索木东,更痴迷于农耕文明。他曾这样写过:“庄稼是大地的根脉,而人情,却是村庄的心。”文明是历史,是不断演进与变化着的意识形态。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乡村文明,实质是一种文明的扩大,一种历史推进的见证,索木东的诗体现了对文明意识的追寻。同时,索木东的诗也自觉表现了“70后”人的文化寻根意识。翟文熙在《遗物》中写道:
“我们拥有的天赋,骨头。/我说过的方言,看过的河流和岛屿,鸟群和星宿。”[2]
在“70 后“的批量诗人中,索木东是很少写爱情的一位诗人。他并不是不愿写爱情诗,而是农耕文明对其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他要去阐释,要去赞誉,这就要从故乡的黄土地说起,从故乡的绿水青山说起。因为他对故乡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执迷,故乡的每一粒元素,飘进诗人视野后立即成诗。这正如吉狄马加所说:一切诗歌都从“当地”产生。索木东是从“当地”努力寻找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元素来见证文明历史的诗人。
读索木东的诗,就会有一种被挤压的紧迫感,这种挤压是现代文化对乡土文化的挤压,说白了就是“中生代”诗人与“80 后”诗人对“70 后”诗人的挤压。这正好锻造出“70 后”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用心与突破。黑格尔说:“诗是心灵的普遍艺术,是心灵最自由的艺术。在这种艺术里,心灵不受外在材料的束缚,它自由地翱翔在思想和情感的天空里,在空间与内在时间里逍遥游荡。”[3]回到当代诗坛,不难发现“70 后”诗人开始创作诗歌的时候,中国诗坛摆脱了政治话语、集体话语和宏大话语对作品的规约,开始走向自由的个人化写作。
向往自由并努力追求自由是索木东诗歌的特质,但过度的自由常常会让主体脱离群体,陷进孤独的境地。“60 后”诗人阿信在诗歌《草原》(之四)写道:“我独自一人穿行/只能是盲目的、孤独的穿行/更多的人、空旷的草原、有更空旷的回声。”而索木东所书写的孤独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群体分离,而是呈现出一种“超群”意识,甚至以一个佼佼者的姿态站立着。比如他诗歌中不断塑造的牦牛、秃鹫、雄鹰、神山等。用这些既超群又有群体的意象代名词,来建构诗歌的“别一性”,无疑成为他的亮点。
索木东在诗中常把代际与自己的某种错过或悲伤之事关联起来,从小事中力透大事,从大事中思索代际,表现一种无奈和妥协。譬如:《能带我回家的那把钥匙丢了》《袖起双手一言不发》等。“70 后”与“50 后”“60 后”的生存处境不一样。当“50 后”“60后”诗人进入到 80 年代时,时逢思想解放的历史机遇,诗人可以放开手脚,尽情书写自我。诚如何光顺所言:“‘70后’诗人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既失去了‘50 后’‘60 后’诗人的机遇,又没有‘80 后’‘90后’诗人对网络的熟稔。”[4]当把“甘南”作为诗歌主要书写场域时,不表达悲剧的历史,就难以彰显其内在的力量。
“70 后”诗人没有目睹过动荡的历史,也与自然灾害、大跃进、人民公社、上山下乡、劳动改造等这些让青年人难以忘却的时代变革擦肩而过。因此,他们的诗歌中难以呈现出像《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谈到“70 后”诗歌时洪治刚说:“‘70 后’作家自觉游离了‘50 后’‘60后’作家们所推崇的精英意识,有意回避了启蒙角色的担当,努力将自身还原为社会现实的普通一员,以平常之心建构自己的诗学空间。对于他们来说,直面现实生活,尤其是面向非主流的边缘化日常生活,不仅是作家对巨变时代的一种认识需求,也是创作主体的一种自由选择。”[5]回到诗歌的艺术本位上来探讨诗歌本身,无疑也会发现“70后”诗作的艺术价值。
索木东诗歌最明显地突出了诗歌的当下性与寻根意识、还乡意识,同时我们在索木东的诗中发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如何阐释民族文化的“精粹”;二是我们如何抛开内心的焦虑消解“70 后”诗歌的沉重与苍凉。
三、离离:西部都市生活书写的“70 后”

离离与唐亚琼同生于1978年,是典型的“70后”都市女性诗人。这两位诗人成长并逐步走向诗坛大概在 1995 以后。她俩对 80 年代兴起的朦胧诗、新生代诗歌、以及 89 年诗人海子的自杀等事略知一二。她俩对诗的热爱与 90 年代兴起的“女性诗歌”热是分不开的。洪子诚说过“90 年代,‘女性诗歌’及其写作者的规模与成绩是 80 年代所不能相比的。”[6]
90 年代,中国社会进入迅速全球化之后,诗歌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遭遇了被边缘化的窘境。朦胧诗的地位一度下沉,诗歌的抒情方式趋向于“固化”。但因诗歌表达情感集中,语言精练含蓄,阅读写作周期短等自身的特点还是吸引着不少阅读者与书写者。
同时《诗刊》《诗林》《诗选刊》《诗潮》《诗歌月刊》等刊物力求于诗歌自身的精湛。《人民文学》《花城》等一些综合性的文学、文化刊物也辟出一些空间支持诗歌写作者。《倾向》《九十年代》《现代汉语诗》《南方诗志》等各地“民刊”的创办,诗歌朗诵会兴起,诗歌节活动的开展等,改变了诗歌的传播渠道与文学价值,推动了20 世纪 90 年代诗歌的多元化取向,为汉语诗歌创作和诗人的复出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文学发生的地理学而言,地域文化决定文学风格已经成为事实。北方诗有北方诗的苍凉与遒劲,南方诗有南方诗的柔情与绵密。如果说刚杰·索木东发出了“70 后”北方男性的苍凉话语,那么离离的诗见证了“70后”北方女性的绵密浓情。正如陆机所言“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诚然不同的代际中诗会呈现出不同的抒情特色,诚如张执浩所说,离离的诗中少了一些我们熟悉的粗砺和苍茫。细看起来,离离的诗也没有完全摆脱“70 年代”西部女性诗人的代际特征,她的诗在书写亲情中,表现出了个体内心焦虑与疑惑,呈现出属于“70 后”人的寂寞和凄凉。离离也是最善于记忆生活的“70 后”女诗人,她所有的抒情都是在记忆中展开书写,在记忆的伤痛中,离离留下了《蝴蝶》《拥抱》《致》《渔网》《觅见》等细腻的爱情诗与《灯》《母亲》《妈妈》《哥哥》等深沉的亲情诗。
选取生活中最平凡的意象群来表达孤独是其诗歌的一个亮点。在她的诗中,“鱼”是书写最多的一个审美意象。远古的先民认为鱼是通天的神灵,是引导死者灵魂进入永生世界的使者。远古时代传输下来的对鱼的崇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鱼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视“鱼”为两种“祥瑞物”的隐喻:一是隐喻人间的吉祥富贵;二是隐喻家族的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殖崇拜和生命意识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人因为鱼繁殖力强、成活率高、生长迅速的特点而用其象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因此,鱼自然成为新生命到来的预告。离离这样写鱼:“喂鱼的时候/我想象过大海/———太陌生了/我为鱼和自己同时难过/没有人给我解释过/大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难发现“鱼”在离离的诗中是生命的象征,对“鱼”意象的建构,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对个体宿命的静思。
我们再看另一个意象“坟”,坟是死者遗体的归宿之地,鲁迅曾以此命名为杂文集。“坟”是一个满含情感能量的意象,诚然,这一意象中蕴含了作者对已故亲人的思念。在《坟》中她这样写道:“有些坟很温暖/比如父亲的,外婆的/有些坟看见了不愿再看一眼。”坟带给离离的是一种沉痛的思念与对死亡的想象。
以意象寄托情感是离离诗的亮丽之光,这样的构思也许是诗人对朦胧诗的效仿。离离诗中的每一个意象都承载着生活的能量,浸透着诗人的情感热度。比如“绳”表达了对母亲的依恋,“杯子”表达了对父亲的念,“刀”表达了爱情,“蘑菇”表达了生活的美满,“苹果”表达了生活中的悲伤,“灯”表达了生活的寂寞和孤独等。
总之离离能在细碎的生活中找到情感共鸣的意象,成为最善于睹物思怀的“70 后”西部女性诗人。
四、唐亚琼:西部都市爱情书写的“70 后”

唐亚琼是甘南新生代女诗人,她从中学起,就一直坚持写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7]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不同景物有不同的形貌;人的情态随景物的变化而变化,文辞则因情盛而抒发。唐亚琼的诗通过对树叶、露珠、海棠等这些眼前之景的描绘,营造出一种诗意的“轻构”,在“轻构”感伤情思时,发出了属于“70 后”都市女性的声音。
把唐亚琼的诗歌堆垒起来看,主要有爱情、健康、泛爱、感恩四大类主题。对爱情的不断回味与留恋是她在诗中发出的声音。在爱情的沉思中,唐亚琼常把男女两性关系的裂变、夫妻情感的隔膜等用平淡的语言表现出来,其背后暗含着覆水难收的无奈与感伤。比如她的《路过》这首诗:“我们经过为数不多的时间∕经过来不及说完的心里话∕我们还经过雨后的河面∕经过暗暗涌动的忧伤。”
诗人描绘的日常事物是眼前最容易被忽略的,在这些众多物象背后,潜伏着“70 后”都市女性无法言说的焦虑。读唐亚琼诗歌经常会有三种明显的感受:先是欢快的节奏,接着是活泼的意象跳入眼帘,而后是巨大的伤痛。尼采说过,一切文学,吾独爱以血书者。可以说唐亚琼诗歌是轻构之后的“血书”。
唐亚琼之所以写出缠绵悱恻的都市爱情,这源于她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冷静沉思。从抒写爱情,表达自己纯真痴热的爱情观到真实再现与病魔作斗争的生命体验是唐亚琼诗歌的创作变向。纵观她所有的诗歌,描写病魔的诗大都出炉于 2010 年。之后她的诗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亲情的赞美、家乡的念、童年生活的追忆等,诗中更多地出现了细雨、落花、夕阳、积雪、泥泞、黄昏等意象,不难看出,这些诗写作时诗人情绪低落,思想极其消沉,情感十分偏激。远离病魔、渴望健康是“70 年代”人、乃至全人类的根本诉求,只有健康,人才能勇敢地融入生活。
唐亚琼的诗也折射出了对健康的强烈诉求。她的部分诗写的都是与病魔斗争的过程,背景选择在医院、病床,时机选在病着的时候。这些诗如同一面镜子,既表现了她对健康生命的尊重与认可,又表现了对健康生命的渴望。如 2012 年发表在《民族文学》上的《病》中这样写:“糜烂的阑尾和爱你的勇气/一起被掏走/冰凉的药水/从血管走遍全身/我愿意,发烧到 48.8 摄氏度/在昏迷中/趁机说出:我爱你。”
诗中的她,是把爱情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因此爱情成为她唯一与疾病抗衡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正是诗歌给予的。她的诗中,常常描绘出两种人:健康的人与病魔中行走的人,病魔中的人大多是自己。她的诗从多重角度表现出与病魔斗争的复杂过程。现实中的唐亚琼性格温柔,身材瘦小,待人和善,但有谁能想象到这么瘦小的身体,竟然承受了那么多病魔的侵袭,她历经了“同代人”离去的悲痛,目睹过朋友永别的凄凉场景,由此时刻提醒着健康的重要与伟大。
从宏观的层面解读,不难发现在西部背景下,唐亚琼所有诗歌承载着泛爱的价值主题,从爱自然景物、爱天体、爱动物,到爱时光、爱青春、爱旅途、爱花木,爱父母、爱丈夫、爱孩子、爱弱者等,表现出对一切生命个体的尊重,这一切都缘于她的家庭教育。她从小受到父亲过多的偏爱,长大后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她将这些爱推广到自己的生活领地,用诗歌表达出泛爱的秉性。尽管她的心情沉重、情绪低落,但泛爱的品德在她的思想中占了主流。西部人对生命的尊重,待人的朴实、热情和豪爽的秉性,我们从她的诗中都能略知一二。在西部的土地上,她把爱写得既含蓄又虔诚,时常催生出一位性格温柔、感情炽热、知恩图报的“70 后”西部女性形象。她不但用泛爱注视着身边的人事,而且也用“爱”见证着自己的人格,把“爱”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之,“一代一路”孕育下的西部,不但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之路,同时也是西部诗歌的亮丽之路。对这四位诗人而言,西部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生活场域,而且更代表着奇特的文化现实。丝绸之路的历史文明点燃了甘肃“70 年代”人的独特诗性,而特殊的代际特征又铸成了他们的情感言说方式。对以上这四位诗人而言,他们同受西部多元文化的影响,他们(她们)同处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西部境域中,他们(她们)共同书写了对西部的热爱、感恩、痴迷,也共同表现了“70 年代”人的甘肃情怀和审美追求。诚然,西部本身的苍凉、深沉、厚度构成了西部诗人的诗歌内质。同时对西部文化的不同理解以及西部生活方式的差异又注定了他们(她们)不同的情感书写方式。从他们(她们)四人的诗中,我们既领略了西部诗的大气和苍劲,更感受了西部的柔情和审美。
参考文献:
[1]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5.
[2]翟文熙.时间软壳[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5:14.
[3][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71.
[4]何光顺.等待的焦虑与 70 后诗人的时间之思[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5]洪治刚.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J].文学评论,2011(4).
[6]洪子诚,刘登瀚.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3.
[7](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M].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2.
原刊于《甘肃高师学报》2019年第6期

朱永明,藏族,甘肃甘南人。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近几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作家汉语文学创作,曾在《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兰州学刊》《中国民族报》《名作欣赏》《聊城大学学报》《西江文艺》《甘肃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20余万字,参与完成高校青年项目一项。现供职于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