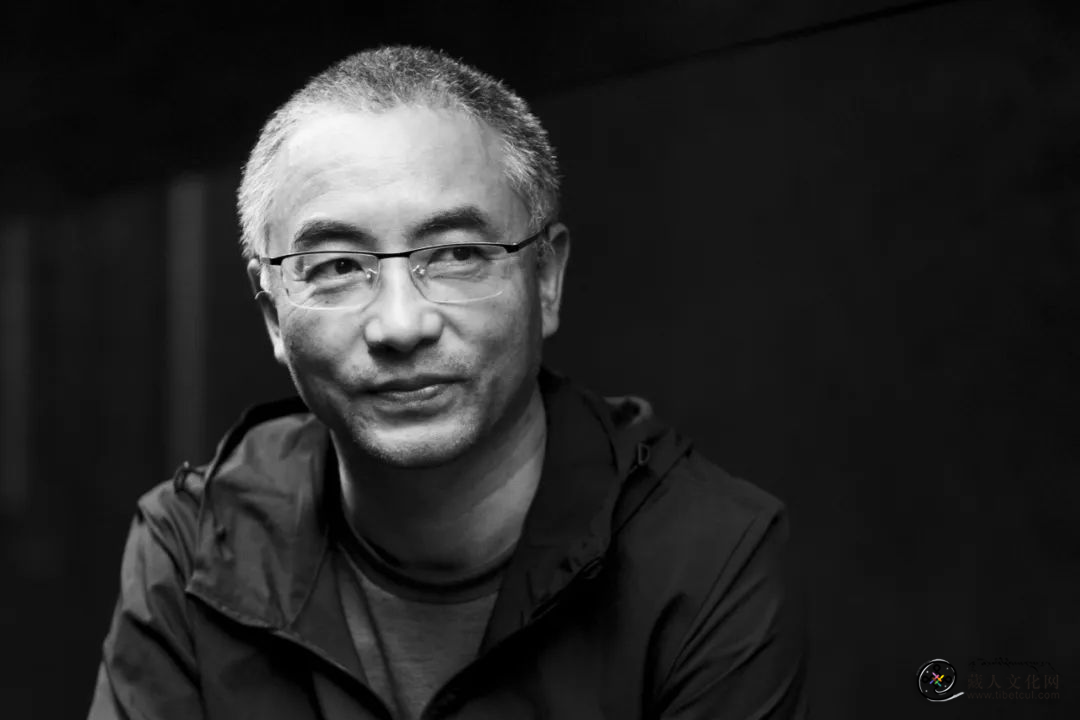要是不去香格里拉,或许我会错过此称的小说。香格里拉的风景如此美好,民风有一种汉地少见的朴拙。在行程的间隙,我读此称的小说集《没有时间谈论太阳》。诗人于坚在序言中这么说此称——他不刻意经营莫测高深的现代主义,没有控诉什么。世界美如斯,也有漫漫黑夜,他见过的故事而已,不仅是听来的故事。他就是一搁置在这个时代中的材料,他的语言,他的世界观。他只要开口。他仅服从他自己即可。
在于坚眼中,此称似乎就像展现在我眼前的这片土地,湖泊平静,雪山高耸,带着神性,植物丰茂得飘着奇异的香味,此称和这片土地之间有一个隐秘的通道,他从土地里捡出故事,就像在土地上捡起随风飘落的果子。“我看见几只苹果被风吹落在地,砸落在地的声音使人心疼。”此称如此描述。
读此称的短篇《糖果盒子》是一个惊艳的过程。是的,我蛮吃惊的,写得如此出色。我读藏胞的小说很少,我看到一种未被污染的小说,一种带着自然神性、秩序庄严的小说,一部自洽的并且极具创造力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此称加深了我此次香格里拉之行的印象。旅行者多么肤浅,看风景,拍照片,到此一游,从不深究。此称让我看到这片土地上的真正生活。
我猜此称应该是先会藏语,然后才学的汉语吧。他用汉语写作。他的汉语相当棒,带有某种异质性,但又是我们心里面美好的汉语。他写下的每一个句子,就像一件擦亮的器皿,放在阳光下,散发着特有的光芒。他写下的每个汉字都像是从他心里长出来一样,有一种未被侵袭过的新鲜感和古老感。这很像汉语最早的表达,我一直认为《诗经》是最好的汉语,每次读都感受到一种上古的新鲜。这种语言在汉地的语境中已是稀有之物。我们的耳根不清净,众声喧哗。此称的语言是安静的。他竖着耳朵,捕捉汉语的音节。也许是某种陌生感让他更容易辩识汉语的音节。
《糖果盒子》是一部结构精巧的小说。就像小说的题目,带有一种叙事游戏的感觉。好像马戏团要变戏法,一只空盒子里总能源源不断地取出糖果。这篇小说确实深藏着戏法,但读着一点也没有轻浮感,相反,小说结实、诚恳,有一种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质朴感。
一开始,读者会认为这是一个成人故事,一群人在村长曲品的带领下建造一座理想意义上的村庄的故事。“新的村庄不会像我们现在住的村庄,所有人家都不会住得那么散。我们会聚居到这棵树下,每户之间走10步就到了……村中央必须留出一条大路,大路两侧种上柳树……每天干完活之后,全村人都可以聚集到柳树下,请老人给我们讲故事,直到很晚才散开。”曲品这么描述。这群人在高原的阳光下劳作,像在构筑一个乌托邦家园。
慢慢我们知道,这只是几个孩子的游戏。这是这篇小说第一个转折。曲品这个头人,转变成了爸爸,卓玛是母亲,我和拉姆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只是在玩过家家。但他们认真的劲儿比成人还严肃。此称把这个游戏写得天真、有趣、纯洁,让我想起卡尔维诺那些充满童话气质的小说。但与卡尔维诺不同的是此称小说里的土地气质。大地上生长着人类生活,也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果实。“有时候,我们会走到苹果树下,果汁溅开一地,黏糊糊地粘着脚底,早间太阳出来后,那些果汁被晒化了,腻人的果香弥漫开来。成群的蜜蜂和蝴蝶闻香而至,在果树下欢享被人遗落的甜蜜。”
此称在小说中部虽然写的是童年游戏,但在这个游戏中看到了人类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对孩子王曲品来说,他的权力来自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总能无中生有地创造游戏。“我”当然可以不同曲品玩,不听曲品的话,但曲品的点子太多了,如果不和曲品玩,生活是多么沉闷。“我”因此愿意服从曲品的指令。“糖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我”家有一只糖果盒子,爸爸每天会给“我”糖果,因此,“我”身上总是藏着糖果。曲品通过“权力”从“我”那里攫取糖果。而“我”也总是愿意给曲品留着糖果以示效忠。甜蜜的糖果在此成为一个象征之物。它来自爸爸,是父爱的产物,而在曲品那里成了献祭。
“我”父亲死亡的消息并没有中断这个造村游戏。他们继续。也许因为孩子们太小,他们并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他们没意识到死亡是一件重大的事。此时小说的视野拉得很远,几乎是上帝的视角,几个孩子的行为像原初时期先祖的劳作,如此专注。死亡的消息像刮过的一阵风,没有泛起一点涟漪。读到这里,我猜想着小说的结局,“我”最终要面对死亡,“我”又如何面对父亲之死。
然而小说出现令人惊异的第二次转折。孩子们把“我”唤醒。此时的“我”已是老人,原来“我”在做梦。以上的故事只是一个老人的梦境。老人醒来后最关心的问题是“家里人都回来了吗”?这是强有力的一笔。时光好像并没有流逝,大地永恒,生命轮回,一切好像近在眼前。时间还是流逝了,一个孩子变成了老人。小说并没有描述父亲之死带给孩子的悲伤,对一个孩子来说,一只糖果盒子足以抵抗父亲死亡带来的不安。但无论如何这是生命中的重大时刻,对生命无常的恐惧,以噩梦的形式进入“我”年迈的身心。“我”最惦记的是自己的孩子们平安回家。
读到这里我想起美国作家魏德曼的短篇《父亲坐在黑暗中》,一位父亲在黑暗中枯坐回忆往昔亲人间的温情时光,而此称的《糖果盒子》一样充满亲情,却在此时此刻。
此称创作谈:说些什么好呢
聊死亡,总是不合时宜的,特别是频繁提到死亡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压迫感。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人们并不避讳死亡,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大人们就会毫无顾忌地在我面前谈论死亡,甚至有些时候,小孩子被允许参与或见证一个人在生命中最后走出的几步路。
我不明白这些经历对我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做到看淡死亡,但也理解不了他人对死亡的极端抵触。
我越来越倾向于简化理解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无非就是生下来,活一阵,然后死去,中间过于繁杂的阐释和意义,似乎仅仅是一种消遣。我们总得走些弯路、找点意义来对抗时间,生活的本质就是对抗。时间与生命,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动力关系。
在西藏,死亡是一门学问,人们及早练习死亡,用去太多时间和精力为死亡做准备。生命是一种比一生更要漫长的过程,没有人能够借助逻辑看到尽头,所以对现实没有那么多的紧迫感。
但除去那些修为高深的大德,对像我一样的平凡人而言,死亡在我们的一生中,一直是个无法确定的命题,即便我们被教导死亡仅是一种新的开始。并且,我们有着比较完善的临终关怀传统,但当死亡像一只横冲直撞的猛兽,倏然闯到自家门口时,人们依然会慌乱,坚持一生的信念,总会在这只猛兽面前失效,轻而易举地沦入悲绝的天性中。
在俗世中,一个人对死亡的淡漠会被视为怪诞,但懵懂的孩子、痴呆的老人,以及毕生修行的大德,在这方面有点相似,就像见证一片秋叶落到地面、一片雪花融于湖面。
成人世界对一些事物的执著,以及小孩子在游戏中的执著,有些时候,可能没有高下之分,都是基于自己的真实天性和立场,都是真实的,都是重要的。不仅在面对死亡时,基于不同的经验和立场、关系、价值等,我们的悲喜并不共通,分歧或隔膜、孤独等,也可能是基于相似的歧异。小孩子把所有情感和精力献给游戏中的细节,大人把所有情感投入倏然而至的灾难中,都是真实的,没有隐瞒,没有捉弄。基于这些不成熟的思考,我试图在小说中,让糖果盒子与死亡变成一种等式。或者,还有过别的什么思考。
这篇小说是我三年前写的,初衷不是为了看轻死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死亡与生活总会相伴而行,总会有人先于我们离开,我希望能够发现死亡的幽默感,也当是一种练习,像那些成天摇着经筒的老年人,或者,像小说中的孩子们一样,活在死亡的阴影之外。
聊死亡,总是不合时宜的,但在这篇小文中,我提到了20次死亡,加上最后一次,一共是21次,望海涵。
原刊于《文艺报》2020年1月6日

艾伟,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盛夏》《南方》,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战俘》《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多种,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

此称,藏族, 1987年生于云南迪庆德钦。曾从事藏汉翻译、编辑、记者等职,2008年开始涉足文学,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长江文艺》《散文选刊》《大家》《西藏文学》《边疆文学》《青海湖》《滇池》《贡嘎山》等刊物。鲁迅文学院第23期少数民族创作培训班学员。出版有诗文集《没时间谈论太阳》。现供职于云南迪庆州广播电视台康巴藏语影视译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