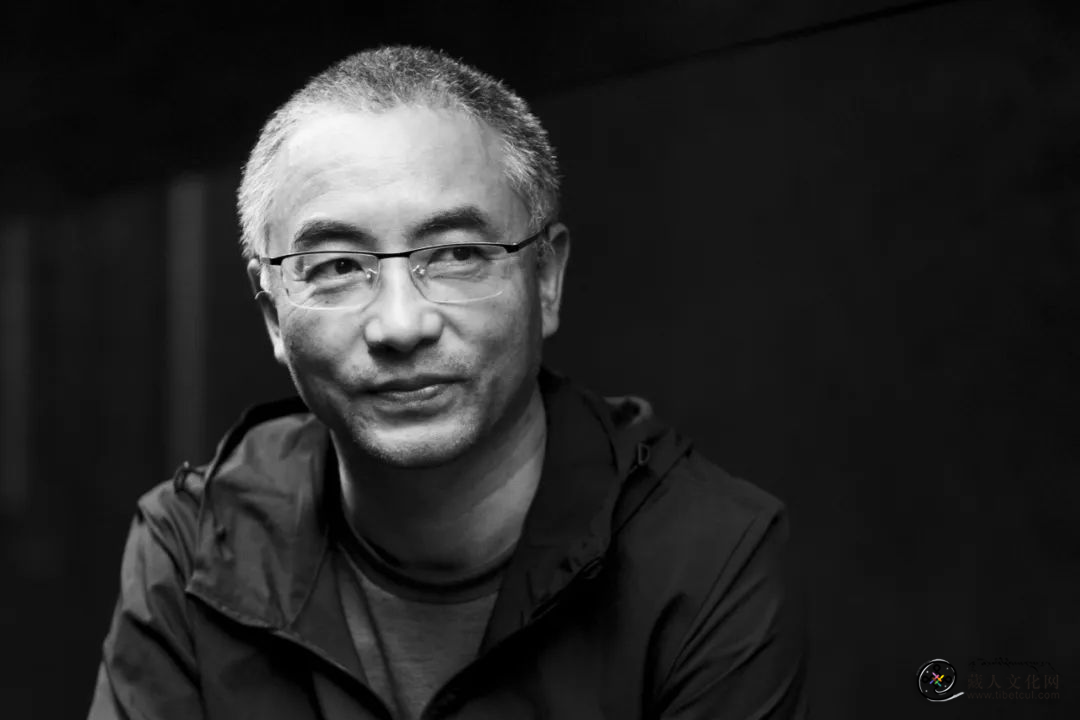在甘南,扎西才让是一位勤奋而虔诚的耕耘者。2020年8月,他以《桑多镇》诗集荣幸获得国家级四大文学奖之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10月,又以《桑多镇的男人们(组章)》为主获取2019“茅台酱香杯”《星星·散文诗》年度奖大奖,为他向峰巅冲击盘好了积蓄力量的营地。笔者以为,其诗歌、小说创作的文学品质,值得深入学习和探究。
《菩萨保寻妻记》《喇嘛代报案》:影视叙事
扎西才让的小说,有多种叙事方式,有像《雪豹》一样的魔幻叙事,《宿命》一样的诗性叙事,《回归文学的老人》一样的戏剧叙事,《菩萨保寻妻记》一样的影视叙事,题材有关注心灵情思的,也有关注地域民风的,有关注时代变迁的,看起来作者在随着阅读的扩展,在尝试着多种叙述表达方式。其中《寻妻记》之作,表现了藏地桑多镇人的“家事”,婚姻中女人对男人的期望和男人对女人的期望,两性间的“征服”是其主题,依赖、自尊、抗拒、征服、惩罚等多种情感交织,再现了桑多镇的久远的民风况味和精神世界。《报案》一文,表现了桑多镇的“民事”,再现了邻里之间比较典型的一类冲突,其中有深陷迷信导致的人性丧失,也有拔刀威慑造成的流血悲剧。像《寻妻记》中,“那人说:‘女人,光哄不成,还要吓唬,要吓唬,女人是最怕刀子的!’”;“老女人:‘你心软了,他的心就硬了,你在他家里,就再也没有地位了。’”等等,都是一种典型传统的农牧民的思维。“威慑”应是贯穿其中的主题词。还有一些语言,如“红丢丢的票子”“脏腑客”“很不感冒”等等,很有地方特色。
两篇小说,都是一种全能视角,读其有一种俯瞰的感觉,开端都有一个突发事件,引起读者的悬念,接着再有新的悬念推进,中间用插叙手法交待一些前因,叙述语言有很强的造型感,使情节如一幅幅电影画面一样在向前推进。这样的叙事,有明显的节奏感,让人阅读有一种快感。语言整体干净、洗练。其《寻妻记》中,将事件情节发展与台上《铡美案》的演出情节交相穿插,以《铡美案》的相关情节烘托小说氛围,节与节之间的过渡有象征物,也是一种不错的手法。《报案》中有不少乡间俚语,也强化了地域色彩和异域风情。
在《桑多镇故事集》中,作者主要关注了藏地现代人的现在事,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心态和价值观来审视他目睹的现实社会的,他对主人公的做法和心态多是持惋惜和悲悯的,更进一步说是抱有否定态度的。他通过揭露现实中残酷的现象,隐晦、曲折地予以批判,以期渴望人们来理性地、现实地看待社会进化,文明地来对待和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自觉地从乡俗人、传统人向现代人、文明人进行转变。
《宿命》:诗性叙事
这本小说集中,《雪豹》和《宿命》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写法截然不同,以营造意境、感觉为主,而非以故事和情节为骨架,是去戏剧化的写法,有着诗性的品格。《雪豹》的风格是轻盈的,《宿命》的风格是凝重的。其中的雪豹,兽焉,仙焉,有魔幻格调,如梦如幻,飘逸朦胧,可能是意在让自然来洗涤烦世之尘埃。《宿命》以撷取几个笔记断片联掇而成,以多重复调并置成篇,只有碎片和特写,注重场面和氛围的有光调地刻画,朦胧,有格调,有似绘画中“以实当白,以白当实”的构图之法,只露冰山少许,大部分让读者去联想、去补叙。《宿命》中大量用欧式化的语言,如介词语句、复式语言,像用油画笔触勾勒出了一副幽暗、沉郁、凝重的藏族女性在过去年代之悲怆命运的典型瞬间,用语言和画面激活了我们对过去年代藏族女性悲剧生活情态的想象,让人睹境震撼。这两篇小说,不是讲述故事、呈现故事,而展现的是一种模糊、幽深和神秘的情景,是让我们来体验和分享场面和氛围,引起我们内心的颤动,产生凝思及共情。显然,这时,作者是以诗性的人格来观照“神性”自然和历史女性的。
诗集《桑多镇》:叙事性、民歌性和韵律感
当下诗歌界,有的诗人的思维是向内收缩的,关注和表达的是内心隐秘的世界,像显微镜一样在搜寻着自己微妙的情感思绪;有的作家是站到极高天宇的高度在俯瞰民族,像航天员一样在书写一个雪域民族共有的金戈铁马、沧海桑田的雄阔人生。而扎西才让的诗歌比前者的视野大一些,是外向的;比后者的视野小一些,是内收的,他像是飞翔在桑多镇一域高空的雄鹰,他关注和再现的是一个不太大的地方。前两种诗人更多地趋向于抒情——小抒情和大抒情,而他更多地张扬了诗歌的叙事功能,富有情感地刻录了一方地域族群的生存状态和微观脸谱,富有史诗样的品质。正如他获得2019“茅台酱香杯”星星散文诗年度奖大奖时评委会的授奖词:“扎西才让对桑多镇的持续书写,建构出一个庞大的文化地理王国,富含张力的语言和多维度的审美视角,还原了甘南藏地繁复深厚的文化图谱。他的《桑多镇的男人们》用非虚构技法呈现桑多镇历史人文中神性而温暖的一面,考古学式的书写思维及散文诗开阔的抒情表达,让他成为了另一个马尔克斯式的民族文化勘察者和书写者。”这样的评价对他是甚为到位与精准的。
关于“多维度的审美视角”“还原了甘南藏地繁复深厚的文化图谱”的内蕴,确实,他的诗歌写了许许多多的桑多镇的人物:牧民、女仆、二小姐、老爷、小厮、少女、诗人,以及庄园、香浪节等等,涉及过去与现在的各种人、事、物。这里,笔者重点就“富含张力的语言”和“散文诗开阔的抒情表达”论说一二。作者在表达时尽量沉淀了强烈的情感,把深切的情感隐藏在细节和叙述之下,一直在用“冲淡的语言”和“徐迂的语调”(刘大先语)努力再现情节和画面,不是大量叠加形容词而抒情,不是代读者来抒情,而是让读者去通过有情调的画面去“感受”,冰山露一角,下面有九分;不是爱恨情仇的一泻千里,而是内蓄着势能,微澜之下汹涌着感情的波涛。他的诗篇大多有情节,有场景、有叙事;他绝大多数的篇章是二二、三三、四四式的章句结构,加上大量复沓句式的运用,形式上有较为规整的节奏,让人有读民歌和律诗的感觉,韵律感比较强,富有音乐性,读起来比较好期待和把握。这种韵味,也有益于使他的诗歌有更强的可诵读性、可记忆性,很有中华民族和古典文化的气质,有的篇什有成为经典诗歌的可能。
当代有的诗歌似乎喜用非常复杂的句式,用非常复杂的词语搭配,像语言的迷宫,故意让人猜解,有执意远离俗常世人之嫌。而扎西才让的句子从“痴人呓语”回归到了“常人话语”,用散文式的语言营造出了诗的节奏,透溢出了诗的情感。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白话入诗,是对“之乎者也”的解放,是将诗从象牙塔中的解放和落地,那么他的散文式的话语,似是将深奥离众的诗圈小众之语向俗常民众的接近和回归。以其他的艺术种类做比喻,读扎西才让的诗,如读书法展中的行书,徐舒而明朗,易明白、很亲民;而那种复杂、深奥的诗,如观看草书一样,需要艰难地猜测,受众可能只是专家和诗人一族。他的诗如线描、工笔之画,以富有意味的形象传神,而以繁复、难解的语言为主的诗族,似西方印象主义、抽象主义类的绘画,不具备同圈子的专业知识者,是难以解读和感受的,他们似在拒绝一般的吃瓜族。扎西才让的诗,有如民歌,节奏简洁、明快,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方式。
正如骏马奖给他的授奖辞所说:“在扎西才让的《桑多镇》中,生命中每一个细节都熠熠生辉……”是的,扎西才让用他的审美洞察力,捡拾了桑多镇上过去与现在的许多珍珠和钻石,用人性之光透射了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浸润了很深的情绪和情感;他结合古典、民歌的传统和现代诗歌自由的表达,建立了明晰而深情的诗句群落,融合叙事、抒情与沉思,使他们的光彩尽可能地具象化呈现出来,用质朴的诗句呈现着一方地域民族坚毅而柔软的精神气质;这方地域上的老人、女人、大德们的身上散逸的“人性”之光,与自然物的精神交相映衬,传承着一种生生不息、熠熠生辉的“神性”,犹如存在于人类和万物中的——黑格尔命名的——客观精神,使人凝目,使人冥思。
结语
在扎西才让着力营造的“桑多镇”文学世界里,“悲悯”情怀是他的伦理底色和哲思基础。这种悲悯,在写作诗歌时,表现为浓厚的古典情结,持审美的视角,关注着民族的许多“善”的美好的一面,含情脉脉;在写作小说时,他有理性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更多地关注了民族当下落后、遗憾的遗存,在揭示着许多“恶”的一面,想呼唤文明。在诗歌中,他用冲淡和温润的语言激活了我们对民族历史人物的人文想象;在小说中,他用更多的或戏剧化或诗意化的故事激发着人们的理性沉思。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扎西才让是甘南一域民族历史的诗意守望者,也是历史民族的文学改良者。
原刊于《甘南日报》2020年10月28日

知否,本名张斌,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甘南州政协理论研究室。

扎西才让,70后藏族作家,甘肃甘南人,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诗歌八骏之一。作品见于《诗刊》《民族文学》《十月》《芳草》《飞天》《山花》《散文》《红豆》《西藏文学》《文学港》《文艺报》等报刊,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小说选刊》《诗收获》《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并入选80余部年度选本。曾获第四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第四届海子诗歌奖、第八届敦煌文艺奖、首届三毛散文奖、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文学奖项。著有诗集《七扇门》《大夏河畔》《当爱情化为星辰》,散文集《诗边札记:在甘南》,中短篇小说集《桑多镇故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