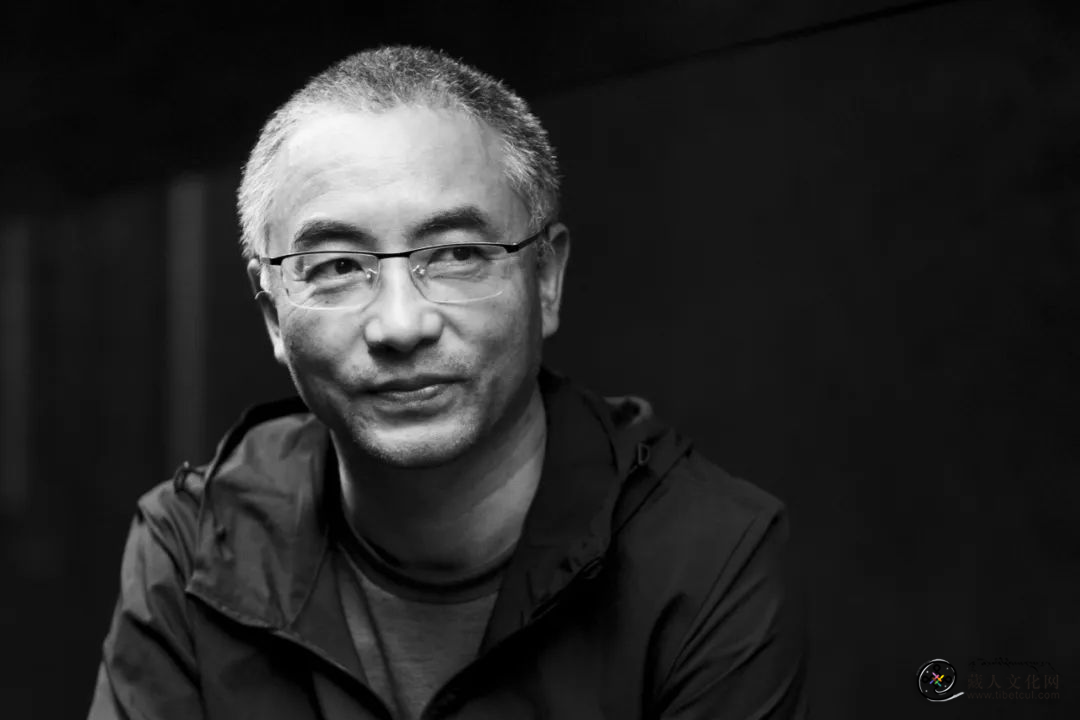去年开始的疫情,于每个人而言都改变了太多本质的东西,包括我们平素的日常生活与内里的精神世界。感恩伟大的国家,在世界疫情及其他因素的动荡之下,我们仍有机缘有坐在一起,在隆冬的青海高原,在温暖和煦的空间,真诚倾听彼此的文学心声。这已不仅仅是奢侈,几乎就是时代的神话,且这神话,足以成为当下每个作家最为深刻的时代精神认知。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细数起来,几乎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如何看待并有效挖掘、有效呈现这些宝贵的资源,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作用,是当今语境下,文学向每个作者提出的重要命题,同样也堪称我们青稞散文流派,未来发展与创作深度的重要命题。
显然在青海这片古老神秘的山河大地上,关于方向我们已经有了关键性的确立,那就是我们的青稞。今天我们的青稞散文流派,这支成熟又年轻、笃定而蓬勃的青稞作家群队伍,这些“青稞的子孙”,以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特质书写,创造并诠释着一种高原特有的文学特质,青稞一样的文学特质:坚韧而蓬勃,沉默而博大,丰富而内敛,素朴而神性。
藏族、土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融汇,形成了青海地区特有的丰富斑斓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质;昆仑神话,更使得青海高原文化有了核心的审美灵魂,这一切都为青海地域文学蕴藉了神秘博大丰厚绚烂的艺术土壤。如今青稞文学流派的诞生与成长,更加使得青海的地域文学有了更为多维的精神视域,也势必会增加青海地域文学的艺术力量。
在大家的心中作品的笔下,青稞早已不再是高原的植物和作物,早已成了与每个人命脉相连的挚爱血亲,更加堪称文学语境下某种意味深长的文学精神符码。
文学是人的心灵、精神与活生生的生活,与沸腾的世界,所发生的精神化学反应。是灵魂的低飞,文学的两翼是对经典的阅读和思考,对素常生活的深入捕捉与自觉的美学探寻。
文学最忌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更忌流于纸上理论空对空。也因此今天我们有意愿坐在一起,从19篇具体作品出发,从神话性、现实性与地域性三个维度,寻找作品中丰富的文学秘密,倾听作者深切真挚地心灵倾诉,从而捕捉作家与高原“神粮”青稞,血脉基因中凝重深沉的艺术渊源。作为一年一度的作品分享会,还将探索梳理,青稞散文流派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符号的美学意义。
一、神话性:美学意义上的青稞
关于青稞之源,流传最为深广的也许便是源于神话中神明的赋予,也或许这样的流传本身就是一种意愿。海北门源才登主席说,青海高原的藏族亲人们每每用餐之前都会郑重感恩,感恩西王母为后世儿女赐予的食物,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西王母的后裔。可见青稞的源头源自神话,有着足够悠久的历史与地域文化传统。
这一点在祁建青最新发表在《民族文学》的作品《炫舞青稞》中,更加体现得酣畅恣意,淋漓尽致。将青稞的标志品相大长芒,视作一帧图腾青鸟的袖珍秘藏版;将青稞视为华夏西域创世神为世界所创的植物;更是西海瑶池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使得几千年后依旧香飘高原的青稞酒,因此应运而生。
“满地的童话寓言,而每一株稞麦,都在时时悉心啄理呵护着羽毛,多么珍稀华贵的羽毛,多么神异炫彩的翠鸟群落”;“承蒙智慧勇敢美丽善良的她们,从一开始就给青稞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深处草山草原的青稞,以动物的样态破解植物的皮相,撂下一连串抖翅、挣脱、盘旋的意象。品质决定的纯粹本性与表现意义,一次从神话到现实的“植物中的植物”式美学递进,一种从现实到神话的“植物中的动物”式诗意度化。”“天域祥云缭绕下的老神话片段,亦是高原农家田野与草木河山苍远飘渺的遗存钩沉。……悄然转型中的人与社会,从神话走出,又将以新的姿态,走进始料未及的神话”……
作品通篇句词严谨考究,意境炫目激荡,古今交相辉映间,神话与现实彼此互文,辽阔跌宕中纵横捭阖复目不暇接。正如班果主席评语称:文章读来如痴如醉,不由感叹作者与青稞似乎有着今生前世一般的深切情缘,或者这种植物中仿佛就住着一位作者为之痴迷的青稞女神,以至于表达得如此情感浓烈,深入骨髓。此刻作者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作家,同时是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神话学家、历史学家、植物学家等等。
“神粮”稞麦赋予了作者情意满怀,情之所至,此刻的青稞仿佛成了命运的一张面孔,既真而切,既温柔而庄严,真实复玄幻。并承载着作者长久以来对青稞宿命般的繁复情感,因此作者的书写,从来便是对这来自神话的植物,最为深切刻骨的无尽倾诉。
作者经由植物内部对神话的进入,堪称以文学之名对“神粮”稞麦进行的一次酣畅磅礴的神话考。无疑这样的书写已然远远出离了散文书写的普泛边界,更加不仅仅限于对青稞源头的文学探寻和考量,反而从美学维度,对源自自我精神中的、深入个体骨髓的命运般的青稞,神话的青稞,“这众神恩典照看与供养的神粮与献食”,进行了美学解释,充满决绝的坚韧与深沉的力量。而神话性也因此成为了青稞美学维度上的审美蕴含之一。
语言华彩绚样,情意喷薄激荡,读来如饮甘醇,汪洋恣意。仿佛已经完成了现实与神话的对接,并因而衍生出一种簇新的文学形态,并且显然,这样的形态自神话的到来而来,却不会随神话的远去而去。正如作者所言,这种植物本身就是一种“从现实到神话的诗意度化”。而反之似乎依然如此,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也许正有此意荡漾其间。
王海燕《青稞地里的向日葵》:月儿像一颗露珠一样从草尖上滚落,没有影踪了。青稞地里神秘出现的向日葵,亦真亦幻的少年,亦真亦幻的狸猫,失而复回,回而复失的月儿,同样具有了神话似的意境,作者于文中似有若无的意境铺排,为文本平添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也恰恰与青稞的美学蕴含之一的神话性有了内在的精神贯通。某种意义而言,这样的神话性是青稞书写中最为关乎灵魂的要素之一。
青稞与神话的渊源,在关于起源的不倦探究中愈走愈远,曲径通幽诗意繁复而引人追随。周尚俊在《青稞情结》中同样将青稞的起源置放于笔墨的核心,在神话中走进现实世界中的稞麦。同样这是因由神话的光对现实的映照,凡俗的生活因而玉熟悉中变得陌生,从而充满异样之魅,一切起始与终结都不再是直线,而成了绾在心头的那个结。那朝庆的《青稞氤氲的乡愁》中,则是经由一滴青稞酒同样回到了神话源头,酒是五谷之魂,青稞酒更是青稞之魂,是青稞另一世的性命。沾染了酒香的文字,由此而生发出酒一样的气蕴、神话一样的超然,仿佛对生命的思考也亦被瞬间拓展开来,并最终凝结成了青稞深处的绵绵乡愁:“这一生命群体,犹如一粒饱满的青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汇成了长江、黄河,澎湃成了生命繁衍的根系,生命由此变得更加伟大。” 以及山客的《青稞,一个被激活的记忆》等作品,皆是于神话及现实中出走并返回,在神话中照应现实,在现实中凝练青稞刻骨的乡愁。作者对植物的观想,出离了生物意义上的维度,从而有了精神的敬畏与灵魂的觉悟。
如果一种植物,便可令作家们坐拥上古的神话,那么可不可以将文学的意义,理解为一种以美学的视域,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之重释?
若果真有一种这样的可能,那么这样的重释,必定饱涵作家内在精神中巨大而真切的美学力量,以及笃定深邃的精神诉求。与神话性作为青稞美学意义同等,作家们从高原植物的内部出发,从神话深处出发,转而回到当下时代,由此也引领我们认知到了古老神话的真实维度,以及青稞于艺术视域之下的现实意义。
二、现实性:作为精神符码的青稞
青稞的现实性是丰富且不言而喻的,同样其隐于现实性之后的精神意义,也令人有着书写不尽的眷爱。源自素常生活的真切认知与发现,以艺术的力量表达内心的情愫,青稞作为高原精神的一种符码,与熟悉的生活进行着对抗。也正是这样的对抗,使得日复一日的人生不致沦为苍白的重复,甚至因此有了弥足珍贵的诗意。这也是这期多篇作品中的共性之一。
那些遍布生活每个细节的青稞,仿佛无时不刻不在与作家们产生精神的交互。是稞麦提醒了人心,还是人心唤醒了稞麦,有时候谁能说得清?尤以青稞面为食材的各种生活细节,经由作者的心灵萃取与文学表达,也成为青稞文学一种重要的文化表现。马文卫《香不过家乡的青稞面》,董德红《青稞的苦涩与香甜》,朱嘉华《那一碗清香的麦索儿哟》,西月《天边的青稞》,老梅《怀念青稞》,清香《向西,靠近那片青稞地》,山客《青稞,一个被激活的记忆》,苏贤梅《梦里青稞香》,王明菊《麦索儿饭》等作品,皆是将青稞面的生物滋味,透过文学的洗礼,沉淀成心灵中意犹未尽的五味杂陈。
当然如何将这一切表达得更具文学的审美意义,甚至是更为深远的哲思性,仍然是我们所有门类的文学书写,恒久而古老的命题之一。
青稞的另一世性命必然是酒。同样古老同样传奇的青稞酒,为文学持续提供着艺术作品所弥散而出的美美醉意。梅尔《酒乡人,酒乡情》,李静的《父亲和酒》箫扬青青的《如今》等作品,无不将文学与酒的渊源,在青稞酒的今生此世,诠释得愈发浓烈持久。那些粮食的灵魄精髓,显然早已镌刻于作家的心魂之上,并因而窖藏于作者心神之间,只待窖藏足够的时限,一盏盏酒香四溢的佳酿,洋溢着“神粮”青稞的历史往昔,就这样登上了文学的舞台,闪烁在艺术的追光灯之下了。
东永学《另类的一棵青稞》中,将一株偶然生长于草地的青稞的命运,以四季的章节进行诗意而深切地铺成,稞麦的一生,因此成为一首生命之诗,更蕴含着思考。赵元奎的《青稞岁月》中,百转柔肠的花儿,沁人心肺的酩馏酒,丰收的舞蹈,这一切在命运的辗转之内,使得青稞具有精神意义上的敬畏与觉悟。同时还有相金玉的《那些青稞》等作品,这些与青稞息息相通的空间与时间,生活与心路,既有着作者内心的恳切,也散逸着不为人知的恬淡,同时更不乏炽赤乡情的交织与补充。作家的使命之一,无疑是赋予世间以美学的意义,并以此来对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并使白驹过隙的人生,不致沦为匆匆过客;以使我们喜忧参半的生活,时而便呈现出不屈的文学光亮。
饮食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缘由必定源于食物与人类生命的息息相关。不止是息息相关,几乎就是人类的血亲。是从舌尖到肠胃、从味蕾到肺腑、从精气到血脉的至爱血亲。作品中青稞面的食物内部所藏匿着的,是作者道不尽的生活情爱,生命历史,灵魂悲喜,如此跌宕流转也百感交集。因此对食物的文学考量与书写,事实上承载着的是一个个体生命,对生活对时间的心灵镌刻,对源自命运过往的不绝的精神追忆。
这些作品有令人欣喜的华彩笔墨,有真切深情的心灵倾诉,当然有的作品也略显单一浅显。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源自情感深处的、挚爱血亲的“神粮”青稞,此刻对作者产生的心灵力量,蘸着酒香的芳醇,已经足以对抗素常生活的平庸与虚无。其力量近乎朴拙,由内而外生发而出,时而如月光清明,时而如弦落音符,时而掷地有声。青稞的一生,是植物的一生,酒的一生,神话的一生,因而也更像大地的一种史诗。高原青稞亦因此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精神符码,这符码既是一种承载,一种指向,更仿佛是对青海高原的万种生灵,一种最为古老的揭示。
三、地域性:不可复制的高原“神粮”
当下时代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上的每个领域都在发生着目不暇接的巨变,表现在地域上,便是地域之间界线的日益模糊,而这样的模糊也使得历史意义上的地域文化本土文化,渐渐不再是远年相对纯粹意义上的本土地域文化,而是在各种变化之间,不自觉地融入到更为宽泛的国际化语境,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显然是时代进步的标尺,但是无疑全球化对于任何有着悠久历史传承历史积淀的本土文化而言,无异于是双刃剑。因为这样的国际化语境在为文化提供了创新与发展的同时,无疑会使本土地域文化的内涵与意蕴发生微妙的嬗变,而面对这种嬗变,作家应该是最早捕捉到的那一部分人,并更深地感受到隐忧的那一部分。
全球化势必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外来文化的洪流,当下更有速朽的毫无营养可言的快餐文化之肆虐,此刻追溯本土地域文化的源头,挖掘地域文化博大精深之蕴含,不仅仅是试图创造文学精品所必经的通道,更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庄严的责任与使命。
写作固然是很个人的事情,但是在创作时却离不开作家生命与精神所依赖的文化环境,任何的无本之源都不可能有延续,而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尤其如此。唯有立足本土文化,充分利用本土地域文化资源,将这些资源有机地融合在作品中,作家的写作生命才会更为久长,也才能创作出具有自我辨识度,同时具有普世意义的真正经典之作。这样朴素的真理无疑是人尽皆知的,毋庸赘语。
从莎士比亚的斯特拉德福小镇,福克纳的南方小城约克纳帕塔法县,康德的哥尼斯堡,到鲁迅的乌篷船上摇摇晃晃的绍兴,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乡,高邮的汪曾祺等等,无一不在为此做出佐证,地域文化为作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与精神哺育,是人类在历史发展前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生活及文化结晶,是人们生命赖以生存,精神赖以活动的承载,更包含人们日常生活和思维理念之下意识地呈现。
因此于地域文化维度而言,我们青稞散文作家群应更为深切地认知到,深入探索青稞文化的多维意义,已然成了我们探索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关系的必然前提与必经之路。反之,从某种意义而言,探索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也成了我们青稞散文创作必要的精神源头。因为文学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地域上的文化与生活,永远有着责无旁贷的庄严使命,而对地域的熟悉的一切之发现与表达,才最有可能贴近人心,贴近灵魂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此刻我们坐拥的,是本土的地域的、我们魂魄身心最为熟悉的“至尊稞麦”,这独独脱胎于昆仑神话,诞生于青海高原,不可复制的、象征着坚韧而蓬勃,沉默而博大,丰富而内敛,素朴而神性的高原精神的海拔最高作物“神粮”青稞,无疑必将作为我们今天青稞文学作家群,书之不尽的文学土壤与精神母题。
并我们对青稞的书写,必定是由古至今由内而外,青稞的精神值得我们更为恒久地开掘,但其精神并不会遮蔽青稞本身所带来的美学价值。英雄固然是旗帜,但英雄本身从来更值得收到最高的尊重与景仰,更何况青稞本身从来就是重要的艺术审美对象之一。
今天青稞与人的关系结构,已然与从前有着不可忽视的变化,故而源自父辈一脉相承下来的心灵浸润,也势必将成为作者生命成长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作者心灵史的一部分,更将成为作者文学经验的一部分,这是永远无法区分与割裂的。而生长青稞的高原河湟谷地,以及其他一切青稞生长的地方,亦因此成了我们至此之后,心神为之关照、脚步为之抵达,手笔为之书写的文学沃土与精神疆域。
我们的青稞文学散文流派,在打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然在成长,并即将成长为高原之上的“文学的青稞”,已然可见那漫天漫野与生机勃勃。今天我们的青稞书写,涉猎了神话性,现实性,地域性,其实更有其隐含的文学性与文化性等等有待我们去不断深入与趋近。因此可以说,青稞散文流派的书写,无论其角度、维度及深度,都堪称是一种意义深刻的精神复古与文化唤醒。
灵魂的意志是文学的种子,文学的表达是最后的果实,之前是漫长、寂静而深邃的孕育历程。阳光,雨水,夜露,肥料,微风,甚至漫天星光,甚至一些不期而至的风暴,都是文学的必须。期待我们青稞散文流派,这个充满地域辨识度的高原作家群体,在灵魂中播种下更为强有力的文学意志,在青海高原这片地域文化磅礴缤纷的圣境之地,创作出同样具有辨识度的质地殊异之艺术佳作,成为连接当下生活与古老神话的神秘符码。以自我灵魂倾听着这片古老山河的灵魂,倾听赋予我们文学灵感的高原“神粮”,以及青海高原古老而年轻的昆仑神话;以精神的多维思考,关照植物灵魂深处的诉求,以华彩有力的文字,蕴藉出深邃丰盈浑厚的信仰书写。当然,或许这也正是青稞散文流派,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符号的美学意义之所在。
原刊于《青海湖》2021年2月

贺颖,女,七十年代生于辽宁。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高研班学员,辽宁作协签约评论家,大连艺术学院特聘教授。有散文、评论、诗歌、美学随笔等作品公开发表于全国多家杂志报刊,多篇部作品入选重要文学选本,有作品被翻译外文海外发表。曾获《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优秀论文奖、2018首届《十月》散文双年奖、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诗歌奖、首届“纳兰性德诗歌奖”一等奖等奖项。现居北京,供职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