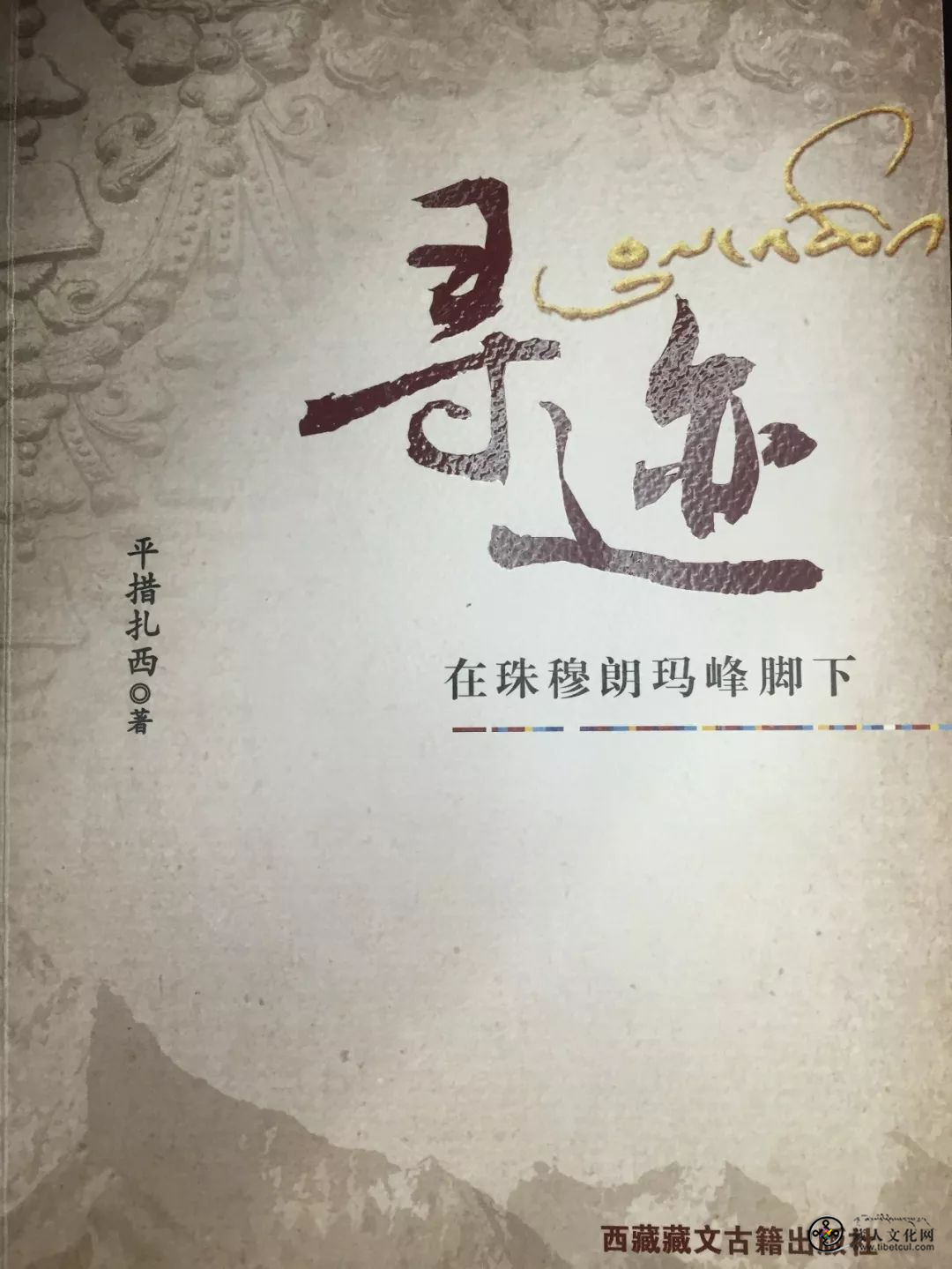
2019年11月,西藏文联在拉萨组织召开了我的文化散文《寻迹》一书的研讨会,对于将写作视为生命最重要使命的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来自区内外的评论家和作家同仁纷纷撰文或发言,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我静静地回味他们的评价时,出书后渐渐平静下来的家乡情结又一次涌动。七年间,拥抱岗巴啦以西广袤大地的历程,一次次浮现脑海,随之而来的还有小时候在家乡温暖的怀抱,吸吮乳汁、初学知识,并滋生文学梦的起始因缘。散文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寻迹》也处处蕴含着我成长的足迹和生活的体验。
我是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60年代开始懵懂世间之事。这个时间段正是西藏迈入新社会的节点,这个时期的人们,原有的观念、生活方式、礼仪习俗、言语交流方式还未改变,但同时,又在努力接受全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在这么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对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讲,俨然拥有了别人无法复制的文学矿藏。在我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文化、习俗、礼仪,从来都不是写作的难题,除了后天的学习外,这个时期的文化熏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是十岁才上的学,不知道我的家人因为什么耽误了我的上学年龄。那时候没有上学名额一说,每年招生季节,居委会组长就会跑到有适龄儿童的家庭,催着他们送孩子上学;那时候又没有学费一说,上学分文不用交,和我同龄的伙伴早已上学,我每天看着他们背着书包三三两两上学去。
因为上学愿望强烈,我对上学第一天的事情记忆犹新。那是一所民办小学,不用等到招生季节,只要适龄,随时可以上学。上学第一天,我起得很早。前一天约好朋友来叫我,吃完糌粑喝完茶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好朋友才过来叫我。那时候没有学前教育,上学第一天就开始学习藏文字母。孩子们从自家带来书写板——“讲星”,依次排队走到老师跟前,请老师用竹笔在上面书写藏文30个字母,然后又依次回到幽深的教室,盘腿坐在垫子上,用竹笔在上面干描。一两天后,老师的字体被描得不成样子,就到院子里用水清洗书写板,晾干后再用碳黑把“讲星”涂黑,没有经验的孩子,一会儿摸“讲星”,一会儿摸鼻子,弄得鼻梁乌黑,又请老师往书写板书写字母。这种传统初学藏文书写的全程,我没来得及全程感受,就又赶上了废弃这种练习方法,从此,我们又开始在纸上练习书写。
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宽大的藏式院落,原先的主人好像专门为办学堂而盖的,大小房舍都围绕着正中的大院,一至四年级的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分布在各房间,正好一间都不空。学校只有两位老师,在我的印象里,他俩全勤的日子很少,大多是一个老师在上班,轮流进人各教室,在这个教室里,领读字母十几分钟,又去另外一个教室里,教算术十几分钟。老师不在的时候,就是属于孩子们的自习时间,也是爱捣鬼的孩子们发挥“专长”的时候,他们在前面孩子的背上画画,或者揪旁边孩子的耳朵,更有甚者,用垫子击打女孩子,弄得满屋尘烟四起,叫喊声不断。这时候,若有老师突然出现,教室倏地鸦雀无声。
在民办学校升级,不像正规学校学期满后统一考试,这里主要看老师的评价,他觉得哪个学生可以升级,就会直接带到高一级班。上民办学校那阵,外面经常敲锣打鼓,随处可以看到大字报和漫画,我们经常逃学去看热闹,学了一年多,大多时间都在玩耍,感受不到任何学习压力,那时候,我特别希望能上日喀则唯一的公办小学——格萨拉康。
以现在的观念来讲,格萨拉康小学算得上是当地的重点学校,那时候却没有这种概念。这个小小的愿望,在舅舅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有一天,舅舅带我来到早已开学的格萨拉康,敲开挂有“二年级”门牌的教室,一位老师打开门,把我领到全班同学跟前,他们手背后,齐刷刷地看着我,老师把我的座位安排在一个女生旁边。这样,我终于成为了格萨拉康小学的一名学生。
在这个学校,我上了十年的学,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业。在这所学校,我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青年,不止打下了各门功课的基础,还萌生了文学爱好。我们那时候,三年级才开始学拼音字母,一句汉语都不会讲,也听不懂,我在《寻迹》中写的秦老师和李老师们,都是用藏文藏语教我们汉语文课。我找到当时废弃的《三国演义》等小人书时,完全靠看图展开想象,不仅自己看图编故事讲,还哼曲编背景音乐,讲得孩子们很是入迷,如果当时有心人把我讲的故事记下来,一定特别有意思。后来,这些书我拿给已经小学毕业了的我的姐姐和她的同学看,她俩念文字给我讲故事时,我才知道其中的故事,是那么好听好玩。从此,我想尽办法,花上一两角钱,从其他孩子手里买来小人书,让姐姐们给我讲故事。她们有时很不耐烦,只看不讲。这时候,我哭闹,在地上打滚,迫使她们给我讲。后来才知道,她们不是不愿意讲,她们也是一知半解,只会念,讲起来很吃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懂得了文学作品的魅力,明白了想看懂其中的故事,必须要学好汉文的道理。
在所有功课中,我最偏爱汉语文课,由此也在偏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初一开始,我一心着迷于汉语文课和阅读汉文读物。我刚开始读《高玉宝》《闪闪的红星》《南海潮》等长篇小说,非常吃力,跳过一句或一段是常事,但这些书给我的乐趣,远大于给我的困惑,我常常入了迷忘了时间,看得字迹模糊方知天色已晚。读了一本本后,我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少,我收获,喜悦、动情、欢畅,我问自己是否算得上是遨游在藏汉两种文字之间的人?
后来,我到日喀则师范学校念书,正值全国上下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思想开放推动新思潮涌现,我们能读到的作品越来越多,改革文学、伤痕文学,还有西方的经典作品等等,西藏传统经典作品也被编成藏文读物,《青春之歌》《红岩》《家》《复活》以及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都是同学之间传阅最多的作品,热爱文学的同学们写作热情空前高涨,各种体裁都有人试手。我是班里的汉语文课代表,自然不甘落后,努力把布置的作文,写得很长,恨不得把所有学会的形容词都用上。教我们语文的曹老师说,我的汉语文已经达到了内地高中学生的水平,并在班里范读我的作文。曹老师是山东来的援藏教师,他的表扬可能言过其实,但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极大增加了我的自信,点燃了我的文学创作理想之火。也就是这个时候,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藏文文学刊物《西藏文艺》正式创刊,它像一块缤纷春园,把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年轻学子深深吸引了,大家争相阅读,把每个作品从头到尾看完后,又翘首期待下一期的到来。《西藏文艺》开设有学生习作栏目,推出各种学生习作,于是同学中胆大者就给杂志社投稿。当时,我们能看到的汉文西藏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西藏日报副刊上,看多了也奢望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和写作,我终于写出了一篇短文,我隐约记得那是一篇写校园好人好事的小稿。我把沉甸甸的稿子装进厚实的信封,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也投进了我全部的期盼。那封承载着满腔希望的信,终于有去无回,把我置于不断的猜测中,我想,也许信丢失在了路上,也许压在了编辑部堆积如山的信件中,更大的可能就是我写的没有达到发表水平,只是当时过于自信。我一直感激这份自信,假如,当时的我没有这股自信,我将不是现在的我,我的职业就不可能是神圣的作家。当时,我的同龄们一窝蜂梦里都想成为穿上制服的公安、工商、税务和银行职员,随后的下海经商潮,更让我与周围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文学青年也拉开了距离。孤单寂寞最容易让人思索,我想,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学,我们太缺少文艺的滋养,需要伺机恶补,犹如我读师专时,《西藏文艺》上的文学作品,给予我的生活乐趣、精神寄托!
在西藏,藏文读者还是很大的群体,他们需要具有民族风格、当代情怀的文学作品滋养。于是,我暗自决定写藏文小说。1987年,我大学毕业,青春的激情燃放,我忍不住创作冲动,写下了我的藏文小说处女作《索多和她们》,写下了一群大学生的生活和朦胧的爱情,第二年,金色麦浪滚滚的收获季节,刊载着《索多和她们》的《西藏文艺》第五期,从三百多公里之远的拉萨,翻过崎岖的岗巴拉山路,颠簸在灰尘四散的土路,来到我的身边。当我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铅字,自己的名字真真切切出现在标题之下,激动得坐立不安,拿着刊物行走在路上,觉得路人都在朝我微笑,都在为我高兴,等心情平静下来后,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能在这个爱好上奋斗吗?我暗自给自己打气,决心加倍努力,一定要实现我的文学梦。我很幸运,第二年的《西藏文艺》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小说评论,评价我那篇小说给藏文小说增添了耳目一新的活力。这个评价给了我巨大的动力,紧接着我的构思贴近所处的环境,周边的人和事,创作了一篇城镇家庭守旧保守的父亲和几个女儿们的矛盾,在外部社会环境激烈变化的气息,像挡不住的春风吹进庭院时,孤独的女儿们渴望爱情渴望自由的言行,给父亲的声望和权威构成了威胁。中篇小说《果热巴热院的悲曲》连载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反响。我尝到了创作的甜头,又悟到了写作的经验,我深感要在文学写作这条道路上走稳走好,除了自己的人生积累外,更重要的是,要深入下沉到最底层,到现实生活中感悟人生,寻找题材。
1992年,西藏自治区开展“社教”活动,我主动要求加入工作组,驱车辗转千里,来到海拔四千多米的纯牧区——阿里措勤县曲强乡。28年前那里的条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一条榜曲河把曲强乡与外界隔绝,没有电没有燃料,生活用水需要到几百米远的泉口去舀,从拉萨带来的土豆、萝卜,必须节省着吃。草原上牧民居住分散,工作组组织学习宣讲,只有等到牧民暮归、天空布满星星时才能开始,到偏远的自然村宣讲,需要只身跟着领路的牧民,骑马翻山过坝。工作组成员也参与乡里的日常工作,跟着乡干部走村串户,协助乡党支部加强党组织建设,了解群众的冷暖,根据牧民的家庭情况,出点子,想办法,让他们早日摆脱贫困。巡游了整个乡,跟牧民零距离接触,逐渐了解了社情民意后,牧民群众才跟你交朋友,愿意向你倾诉心里话,把你当成亲人,把个人的经历、家庭的情况、生活的忧愁都摆出来跟你讲,让你时常感动于群众的真挚情怀中。
一次次接地气的牧区体验,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家庭故事,催生了我的数篇牧区题材小说,有反映歧视妇女行为的《斯曲和她五个孩子的父亲们》,表现城市大学生从教牧区的《平常日子》,城里年轻人从不适应牧区生活到热爱牧区的《未得到的想得到》等。1997年,我的中短篇小说选《斯曲和她五个孩子的父亲们》出版,深受读者喜爱,至今读者不断,常有牧区出生的读者给我讲:“你的斯曲形象塑造得太逼真,我原以为作者是牧民出身,没想到你是城里人。”这些都是六个月的“社教”生活馈赠给我的,何止这几篇小说,那段既艰苦,又充满意义的生活,既锻炼了我的意志,又给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从我的这段亲身经历,领会到了习总书记指出的“文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大地和人民,就是我们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的意义所在。
从实践中领悟到了生活与创作的真谛后,近30年来,深入生活和挂职成为我自觉的践行,一旦能抽身,十几天或几个月下基层,从来没要过单位的车,更没有下乡补贴之类,我深知作家要下去,作品才能上来,这不仅关乎作品的真实性,还关乎如何站在至高点,对历史、对现实认真进行思考和把握,也对日后创作各种作品,起到了贮存素材、攒下底气的作用。
大多数基层群众认识我,是因为曲艺作品。我是在非常偶然的际遇下“触曲”的。1991 年,西藏举办了首届小品大赛,大赛的征稿通知发出去几个月,收来的作品却不够组织一台赛事。戏剧家协会主席知道我是搞创作的,就约我写几个作品。我口头答应了,却没怎么往心里去,无奈他几次催稿,我推辞不掉,就开始涉足了全新领域。我凭着积累的素材,创作了两个小品。待我交稿时,他又说现在人力不够,投稿的作品作者要承担排练任务,形成成熟的节目再提交。我只有拿着作品,到处去找表演的单位。后来,拉萨水泥厂和西藏大学承接了表演任务。于是,我调动身上潜藏的所有表演细胞,导演了两个小品。意想不到的是,比赛结果公布时,我的小品《我们的女婿是个大学生》获得了一等奖,不枉我两个月的辛苦付出,这无心插柳的结果,把我引上了曲艺创作,从此向我约稿者不断。刚开始,我心里很纠结,大多数作家对类似曲艺创作不屑一顾,它花时多成果少,需要协调的人事多。当时,西藏的戏剧小品刚刚起步,广大群众非常喜欢曲艺这种艺术形式,对它表现出出乎寻常的热情。从观众的广泛度看,任何艺术比不过曲艺。我想,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需要是我们创作的目标,人民的满意是我们创作的标准,人民不买账的艺术作品,即使再高的艺术水准,也只能孤芳自赏。于是,我决定坚持曲艺小品的创作,继而埋头创作了《醉鬼拉巴啦》,这个小品在西藏电视台藏历年晚会播出后,引起了轰动,妇孺皆知且津津乐道,人们期待后续翘首以待,我乘势创作了第二、三集。当时在全国电视舞台上,还没有曲艺小品连续戏的形式,我的《醉鬼拉巴啦》成了里程碑式小品。业界评价,至此西藏的曲艺小品,真正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群众的喜爱是我在这条路上继续奋斗的动力,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我深感曲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强大,它能起到引领人们追求高尚,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净化社会风气,倡导人们摒弃丑陋,批判不良行为的作用。因此,我不仅坚持小品创作,还捡起了小品的姊妹艺术——相声的创作,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在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人们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焕然一新。但由于私欲膨胀,法律意识的淡薄,缺乏崇尚科学文明的意识,丑与恶的行为也时常做怪,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为社会文明进步鼓与呼,对不良行为进行揭露和警醒,是一个作家的担当,于是,我把小品相声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除了表现酗酒赌博不思进取的小品《醉鬼拉巴啦》外,唤醒人们保护文物古迹意识的相声《逛议八廓街》《文物的呼声》,推进生态和环境保护建设的《拉萨的肺》《公共设施的悄悄话》,劝导青少年懂得父母养育辛劳、走身心健康成长之路的小品《谁的错》《成长之路》,提倡人们过文明生活的《书吧趣闻》《健康是福》,展示西藏悠久文化、揭示陋习的相声《西藏之最》《日喀则之最》,驻寺驻村排忧解难、帮助村民摆脱贫困的《驻寺日记》《结亲》等等,不少作品成了群众的最爱,常播常乐。
几十年来,我创作了80多个曲艺作品,出版了两本剧本选,培养了一批曲艺新人,我觉得我在这个领域的使命差不多完成了,可时有观众关切地问:“今年藏历年电视晚会你有什么作品?我们非常期待。”面对观众的厚爱,我又深受感动,继续深入生活,继续寻找群众普遍关注的现实话题,进入枯燥又快乐的创作时光中,如此循环,“不再写相声小品”的决定便一次次失言。
近年来,西藏热引发了旅游热,旅游热又催生了西藏题材图书出版热,这些图书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把西藏描述成笼罩在浓郁宗教气息的神秘境地,另一种是浮光掠影的行走描述,快餐式的介绍西藏,这两种描述在客观表现西藏上,都有欠缺或不准确性。在这些书里,西藏是与神灵对话的地方,藏族人的生活完全被宗教烟雾所笼罩。其实,西藏人的日常与其他地方没什么大的不同,共性大于个性,也奔波忙碌在尘世生活中,也沉迷烟火气息中,比如,布达拉宫脚下的“雪”村,曾经是附属于布达拉宫的一个世俗村落,布达拉宫的日常生活起居所需制作,以及劳力支出都是雪区提供,而世代居住这里的是一群世俗人,他们跟其他人一样生儿育女,为生计四季奔忙,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日常劳作和作息时间,完全按照布达拉宫的运转节奏进行。
又如水井,它曾分布在城镇和乡村的深院窄巷,有方形的、圆形的,深邃的、低浅的,是滋润高原人的圣泉,那时的井口边,是左邻右舍的交际场所,短暂的聚拢,家长里短,又匆匆背水离开,张罗各家的柴米油盐。而短短几年间,它们销声匿迹,仿佛从不曾出现过。
想的多了自然有创作冲动,许多隐蔽在历史深处的生活点滴,沉匿于岁月尘土的习俗仪式涌进脑海,作为西藏本土作家,把这些散发世间烟火气息的藏地景象写下来,揭开神秘面纱,让外界客观了解西藏,是责任也是义务。于是,我开始了全新的尝试与挑战——用汉文写作。这其间所遭遇的又怎能用一个“难”字概括,庆幸的是,我最终坚持了下来,把所有业余时间投人到这本描写藏地世俗百态的书,怀胎六年后,这个孩子终于诞生,我为它取名《世俗西藏》。有读者说:“这是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它以全新的视角,为平淡多年的西藏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春风。”不到一年,该书的印数达到13000本,在文学图书市场普遍不景气的时候,一部写边地文化的书能达到这个印数,让我感到欣慰。
《世俗西藏》的成功着实给了我信心,有这本书打底,我敢列出一系列汉文写作计划。当然,《藏地追梦人》一书,是计划之外。土登老师是西藏曲艺界泰斗级的人物,我跟他合作差不多有30年。他是个特别有故事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坎坷,但自始至终,没有与艺术脱离过关系,直到生命终结那一刻,他牵挂的仍然只是舞台。感动于土登老师对艺术的执着,我萌发了为他写传的念头,恰好西藏还未有过写西藏人的非虚构类文本,这又是一种新的尝试。经过近两年的采访与写作,《藏地追梦人》藏汉文版顺利完成,还被改编成了纪录片《随风起舞》,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写作计划中的《寻迹》耗时却近7年。
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故乡是他写作的永恒源泉,他的素材库应该堆满故乡的记忆。我也不例外,随着岁月的增长,对故乡的情愫越来越强。
我的故乡在岗巴啦以西的日喀则,是西藏最具特色,农牧文化交相辉映的地方,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古迹众多,民俗礼仪缤纷,语言服饰多样,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藏族文化史上,建树颇多或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诸如藏医、藏戏、绘画、建桥、语言文法等领域的开创者,大多诞生在这片土地。对于他们的记述,史书上只有零星几笔,若想把他们重新塑造起来,填补这个空白,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当我真正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的时候,我诧异于它的博大与精深,也迷茫于它的复杂与丰富,我几次退却,却又心有不甘,如果我们不承担文化延续这份责任,许多历史文化记忆势必消失于岁月的尘土中。
为了《寻迹》,我必须出发。
在不断行走与求证的路上,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自然景观,日喀则市的18个县各有特点和亮点。为了能够将一个地方写好,不留遗憾,我保持最大限度的体力和精力,踏访实地寻找智者,找到一丝线索,便穷追不舍。我整天忙于走村串户,求访的对象不分童叟,在简陋的茶馆与村民交谈,在路上与行人交谈。有个朋友曾对我说:“你浑身尘土,满脸疲倦地采访的样子,一点都不像个厅级干部。”其实类似的话,我也听到不少,除了工作上需要,我从没对人说过我的职务。在我心中,作家这个职业是第一位的,一旦选择了这个职业,还需要摆什么架子呢?与采访对象打成一片,零距离与他们亲近,他们才愿意将自己的心、自己所知的交给你。
写到这儿,我的眼前总浮现《寻迹》中写过的那些人,他们有的是为西藏文化倾其一生的智者,有的是为藏汉文化交流贡献智慧的现代人,也有常年在基层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我把这群人艺术地呈现给读者,把他们身上鲜为人知的感动点介绍给读者,我想让读者了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收起“我”这个字,选择了在奉献中实现生命的价值。
《寻迹》藏汉文版共计一百余万字的写作,是我七年努力的成果,能得到读者的喜爱,不仅肯定了我个人的努力,也是对这些人物、这片高天厚土的敬意。
原文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二辑

平措扎西,西藏日喀则人,国家一级作家,西藏文联原副主席,西藏曲艺家协会主席。用藏汉两种文字创作小说、散文、曲艺作品等约三百万字。曾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曹禺戏剧奖、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创作一等奖、“西藏十年文学奖”、“西藏新世纪文学奖”、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最高奖——珠穆朗玛文学艺术金奖、西藏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和全国优秀青年曲艺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有文化散文《寻迹》《世俗西藏》《西藏古风》,中短篇小说集《斯曲和她五个孩子的父亲们》,报告文学《藏地追梦人——曲艺表演艺术家土登的艺术人生》藏汉两种文本。曲艺作品《平措扎西小品相声集》之一、之二两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