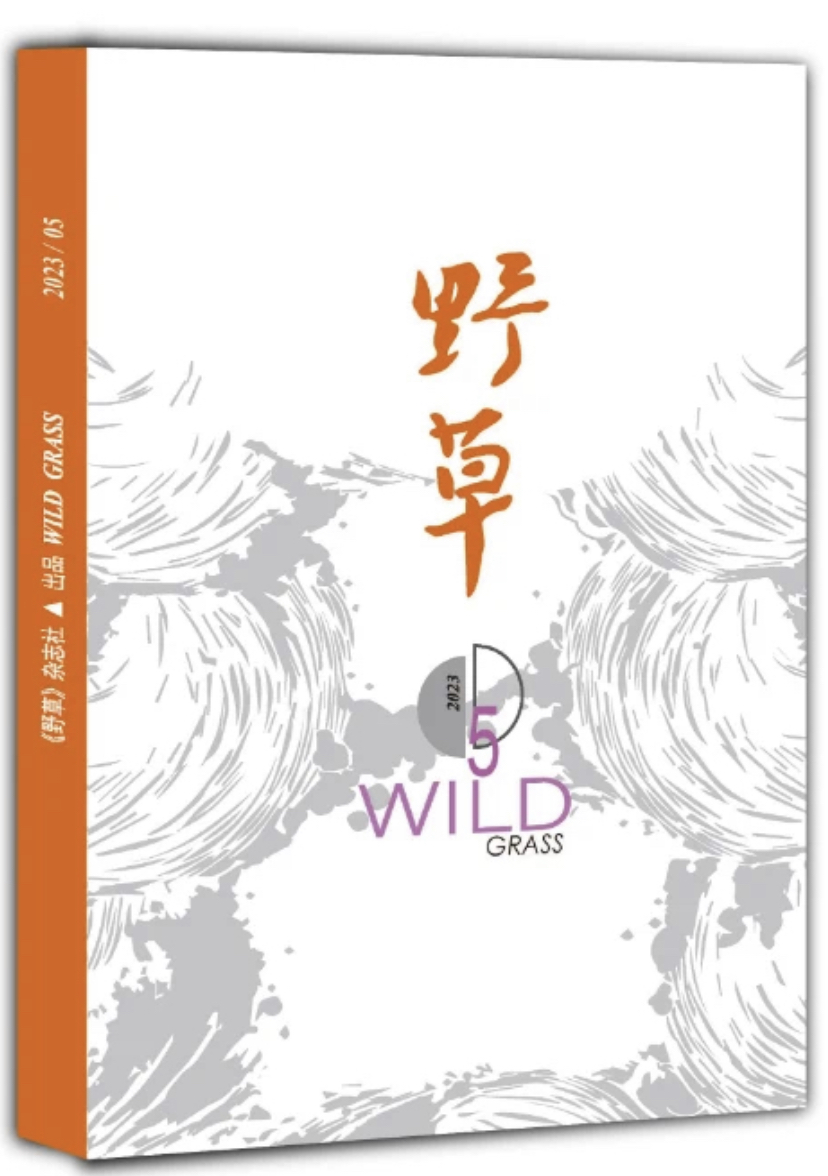
索南巴杂用摩托车犁地的消息,传遍了卓香卡和周围的村庄——甚至更远的地方。
这也是后来的事了。
索南巴杂还不叫索南巴杂的时候,我刚踏入卓香卡小学不久。他是阿妈才姆改嫁给才让叔叔时带过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卓香卡的人们叫他“才姆的拖油瓶”。
索南巴杂又瘦又高,像一支迎风摇晃的经幡杆,背着他那用牦牛毛制成的黑色书包,穿着宽松破烂的藏袍,站在风口时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那时,我们都背着墨绿色的单肩包去上学,没有墨绿色单肩包的只有索南巴杂。大人们背后悄悄说:那是因为他是拖油瓶。
索南巴杂喜欢在垃圾堆里捡瓶子,或拾废旧电池玩。他一个人的时候,常对着一堆废铁自言自语:“这是车,开着这个车可以去县城。”又拿起一只空瓶子,“这是酒,咱们喝两杯吧!”说着把瓶子对在悬着鼻涕的嘴唇上。
有一次,索南巴杂拿着一块磁铁在垃圾堆里搜来搜去。一会儿工夫,磁铁上沾满了曲别针、大头针、钉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很羡慕他手中的磁铁,请求他让我们也摸一摸。索南巴杂用力吸了吸鼻涕,脏兮兮的脸上露出夸张的表情,说:“你们不要做梦了。”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那里继续用磁铁搜来搜去。
他就是那样在垃圾堆里长大的。我们想在他和垃圾之间找个相同点,给他起个绰号,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有一天,达杰老师让我们给“巴杂”(巴杂:藏语音译,意为肮脏)两个字造句。第二天交作业的时候,同学们都写下:索南是个巴杂的人。从此,他得到了“巴杂”这个绰号。
阿爸阿妈们要起早贪黑地去做农活,中午我们便回不了家。早上上学时要带点馍馍和水,当作午餐。同学们到学校后,把书包里的水瓶拿出来放在教室的窗台上。那天,索南巴杂故意把我的瓶子给打碎了。我说:“索南巴杂,你要赔我的瓶子!”他很生气地看着我说:“小子,你叫我什么?”我重复了一遍:“索南巴杂,你要赔我的瓶子!”他一言不发,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劈头盖脸就是一耳光。我对达杰老师说:“索南打我。”达杰老师问:“他为什么打你?”我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达杰老师。达杰老师说:“你给别人起绰号,不打你打谁?活该!”
我从达杰老师的办公室里擦着眼泪往教室走去时,索南巴杂正在门口等着我。他吸了一下又黄又粗的鼻涕,掏出拳头猛捶我的额头,逼得我后退了几步,他说:“你去告啊,这是你自找的,活该!”
我想着一定要报复他。但打架我不是他的对手。
我思考了许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索南巴杂在四年级,我在二年级,但我们学校只有三个教室,二年级和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里。我们经常玩的那个水坑周围,有许多青蛙。有一天,我抓到了一只青蛙,课间,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了他的书包里。
挂在沙枣树上的破钟叮叮当当响了几声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教室。随后,达杰老师拿着教棍走了进来。那天早上,达杰老师给四年级布置完作业后,开始给我们二年级讲新的课文。老师刚上讲台不久,索南巴杂的书包里传来“呱呱呱”的叫声。
“谁?”达杰老师急促地说,“这是什么声音?”
我侧眼望了望索南巴杂,他正在东张西望。这时他书包里的青蛙又开始叫起来。
达杰老师很生气。“谁?是谁?”说着,他走下讲台,在教室里转了一圈。然后在索南巴杂旁边停住了脚步。
“这狗屎!”
索南巴杂不知道达杰老师在骂自己,他还向同桌久美做了个鬼脸。
达杰老师生气的时候,喉咙里总会发出“啊啊嗯嗯”的声音。他接着说:“啊——嗯——起来,听不见吗?啊——嗯——你是聋子,还是瞎子?”
索南巴杂仍望着同桌久美的脸。
达杰老师用他铁叉一样的手抓起索南巴杂的头发,狠狠地拎了起来。他不知所措地望了望达杰老师的脸,随后便把头低了下去。
“你的破书包里装的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
“真没有吗?”
“没有。”
索南巴杂说话的语气很坚定。
达杰老师拿起他那牛毛制成的破书包用力抖了两下,书本、馍馍,当然还有一只脏兮兮的青蛙,全都掉地上了。“啊——嗯——”达杰老师往后跳了两下。“啊——嗯——”达杰老师大发雷霆,满脸通红地说:“你这个狗屎,啊——嗯——你把青蛙装在书包里,要吃它吗?”说完便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
索南巴杂像是触了电一样,脸都变了形。
“不是……”索南巴杂很沮丧地说,“不……不是我放的。”
达杰老师说话的声音像牦牛吼叫一样。
“这破书包是不是你的?”
“是。”
“这破书包是装书的,还是装青蛙的?”
“是装书的……”
“你明知是装书的,那你还装青蛙?”
“不是我装的。”
“啊——嗯——你还嘴硬?”
索南巴杂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有那么一瞬间,我担心他会朝达杰老师扑去。可最后,他只是动了动嘴巴,没说什么话。
……
又有一次,学校快要放暑假的一天,达杰老师让我们大家一起打扫教室,他在教室里守着我们,突然,达杰老师喊道:“你们不要打扫了。”我们看着达杰老师的脸,不敢放下手中的扫把。
“你们把课桌里的干馍馍都装到书包里。”达杰老师做了个手势说,“一点馍馍渣都不要留下。”
我们不知道达杰老师用意何在,但还是把课桌里的干馍馍都装了进去。
大家都知道,索南巴杂的课桌里是一点馍馍渣都不可能有的,他连吃饱都很困难,怎么可能会剩下呢?他站在课桌前不知所措。来到我的跟前,低声说:“给我一点干馍馍吧!”他就那样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可我怎么可能答应呢?我很傲慢地回答:“不可能,你想都别想!”说完就拿起书包向门口走去。
“都装好了吗?”达杰老师问道。
“装好了。”同学们齐声回答。
“大家背上书包,跟我来。”达杰老师说,“今天我们到学校外面的草地上去好好玩一玩。”
大家一听到达杰老师说“玩一玩,”都高兴极了。到了学校外面的草地上,达杰老师让同学们围成一圈坐下。然后,让同学们把自己的干馍馍倒在跟前。
达杰老师看见索南巴杂坐着不动,对他说:“你的干馍馍呢?”
“我没有干馍馍。”索南巴杂说着便低下了头。
“好!那你到这儿来。”
索南巴杂颤颤巍巍地走过去。
我们都想着,达杰老师那铁叉一样的手又要落到索南巴杂的头上了。可万万没想到,达杰老师很温和地对他说:“你来监督他们。”说完对着我们大喊道,“谁让你们这样糟蹋父母的血汗!”
索南巴杂明白了达杰老师的意思,开心地笑了。
达杰老师把手里的教棍交给了索南巴杂,然后对索南巴杂说:“让他们吃完干馍馍,要是谁不吃你就用这个棍子狠狠地打他们,听见了吗?”
“好的,老师!”他的回答铿锵有力。
达杰老师留下我们便离开了。
我们立刻拿起馍馍往嘴里塞,嚼得牙都疼。
索南巴杂围着我们走来走去。“快点吃!”他说着便用棍子狠狠抽了两下久美。久美虽然很不情愿,但也不敢说什么,只是盯了他两眼。
“你这是不服是吗?”索南巴杂说着又打了一下。
我们不敢说什么,低下头忙着吃干馍馍。
我们快要吃完那些干馍馍时,达杰老师背着手来了。
“你们吃完了吗?”
“吃完了。”
达杰老师看我们,说:“你们排成一队,给我好好站着。”他让索南巴杂去捡来一块大石头。
我们不知道他要干啥,每个人都吓坏了。
“你出来!”达杰老师指着我喊道。我吓得哆嗦了起来,感觉心要跳出来了。
“你们每人要把这石块高举一百次。”达杰老师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起来说,“同时要喊‘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大家高声喊道。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
我一次次地高举石块,终于喊够了。额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模糊了我的眼睛,眼前的一切像是在雾中飘。我的两只手已经没有知觉了,四周静悄悄的,索南巴杂吸鼻涕的声音格外清晰。我擦了擦眼睛,下午的阳光斜照在同学们的脸上,像一个个红色的朵玛(朵玛:藏语音译,用糌粑做成的供品)。我看见索南巴杂那恶心的鼻涕又挂在他的嘴上。
……
还有一次,索南巴杂的一句狂言,炸震了我们的耳朵。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学校快要放学了,我们等着达杰老师叮叮当当地敲那个破钟时,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一会儿工夫,有人骑着一个“轰隆隆”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从学校铁门里进来了——后来才知道那叫摩托车。他是来找达杰老师的。
索南巴杂第一个跑出去了,我们也跟着他跑出去看。那是一个有着三个轮子,后面还挂着一个轮子的军绿色的铁家伙。有些同学说,这像个青蛙。还有些同学说,像蜻蜓。
我们正在争论的时候,索南巴杂上去摸了一把那家伙,说:“我长大了一定要买这样的。”
“你在做梦吧?”久美说,“巴杂烧得有点严重。”
回家的路上,同学们嘲笑他:“索南巴杂要买铁青蛙了。”“索南巴杂骑着铁青蛙去上学了。”“索南巴杂,到时候你买上铁青蛙让我们也骑一骑……” “哈哈……”
“你们等着瞧吧!”索南巴杂拍了两下自己的胸说,“到时候我让你们刮目相看。”说完大步向前走了。
同学们看着他的背影,笑个不停。
索南巴杂快要小学毕业时,他的继父才让叔叔不让他上学了。对这件事,达杰老师不止一次反对:“索南巴杂虽然调皮,但是他的脑瓜子还算聪明,你这是在害他。”但是才让叔叔怎么也不听,说:“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索南巴杂的脑瓜子很聪明。谁都没有给他传授过那些民间说唱,但是,索南巴杂就喜欢说唱故事。自从他认识字后,他手里总是捧着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他时不时地唱着书里的内容,《达尼多》《端智加罗与叶喜卓玛》《格萨尔》等等,他都能倒背如流。
村子里的姑娘们把索南巴杂拦在田间地头,让他唱《达尼多》,或者《端智加罗与叶喜卓玛》,他都很乐意。那些村口晒太阳的老人让他唱《格萨尔》,他能唱得让老人们掉眼泪。他的手势很讲究,什么时候要举起来,什么时候要放下去,什么时候要双手合十顶在额头,他都做得得心应手。
在我的印象中,卓香卡的人们从来不把索南巴杂当一个好人来看待。大人们时不时地对孩子们说:“你说的是索南巴杂吗?他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不要跟他玩,他会把你带坏的……”
虽然我不喜欢索南巴杂,可我也无法理解大人们的说法,他们需要时,叫索南巴杂唱那些民间说唱故事,还听得如痴如醉。不需要的时候,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每当大人们说他不好时,我就想起一句谚语:需要时是神仙,不要时是魔鬼。这谚语肯定是专门说给那些大人们听的。
但是,有个人例外,那就是老密咒师仁增。每次村里人在他面前说索南巴杂的坏话时,老密咒师说:“他的言行举止虽然怪异,但是他的灵魂很干净。”老密咒师不时地叫索南巴杂到他的修行室来唱《格萨尔》,唱完了给他一把糖,或者点心什么的。
索南巴杂辍学后,成了一个羊倌。他绝对是个优秀的羊倌,他们家的羊个个像牛犊一样健壮。那些羊贩子一进村就专挑他们家的羊。可索南巴杂时常说:“没有比放羊更无聊的事了。”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一人在家里写作业。出去小便时,发现我家菜园里有个身影在移动。我猜到了,肯定是索南巴杂。过去一看,果然是他。
“喂!小偷!”我喊道。
索南巴杂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很不自然。他做了个逃跑的动作,转瞬间他又不逃跑了。大概发现家里就我一个人,他清清嗓子反问道:“谁是小偷,谁家没有萝卜,我还用得着偷?”
“你不是小偷,你在我家菜园里干啥?”我说。
“我是来叫你的。”
“叫我,叫我干啥?”
“我俩去玩吧!”
“不!我才不跟你玩。”
“你见过格萨尔王的脚印吗?”他走过来说。
我不作声,心想他想说什么呢?
“你不想去看格萨尔王的脚印吗?”他又说。
我听大人们说过,在村子后方有个叫唐乃亥的大草滩,那里有块大石头,上面印着格萨尔王的脚印。但那个草滩离村子较远,我就一直没有去过。索南巴杂对我说:“跟我走吧,让你开开眼界。”我经不起诱惑,就跟他去了。
一路上他都在说格萨尔王的各种传奇故事:“格萨尔王飞起来像雄鹰,钻到地下去像条蛇,他喊一声就能惊天动地,他跨一步就到江那边。”我被格萨尔王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突然,他停住脚步,耸耸肩膀,说道:“如果你不想去,我也不勉强,你回去吧。”说完他便加快了脚步。我紧跟着他喊道:“等等我……”
现在回想起来,他就是在故意吊我的胃口。
走了很久,终于到了草滩。碎石遍地的草滩上到处长满了芨芨草,他们家的羊群就陷在芨芨草深处。
那块巨石,从远处看去很壮观——像头雄狮。那头雄狮的背上印着一个巨大的脚印,格萨尔王的脚印终于显现在眼前了。我兴高采烈地脱下鞋踩在上面,心想这只大脚就算要跨过黄河也不成问题。
随后,索南巴杂站在石头上,擤了擤鼻子,给我唱了《格萨尔》里的一个片段。他虽然管不住鼻涕,唱起《格萨尔》来,嗓音却像被甘露洗涤过一般清澈。
……
白雪山不留要远走,
丢下白狮子放哪里?
江河水不留要远走,
丢下金银鱼放哪里?
大草原不留要远走,
留下花母鹿放哪里?
……
索南巴杂讲述了格萨尔为救护生灵、降妖伏魔、锄强扶弱,投身下界,完成人间使命后返回天国的经历。我的视线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身着铠甲、佩带武器、骑着大枣红骏马、伴着五彩霞光扑面而来的武士幻影。随着这个奇特幻觉的来临,我像失去了魂似的,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我和格萨尔王分别骑在枣红的骏马上,四周的人群向我们鞠躬致敬,我高兴地叫了几声,感觉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人们也开始模仿我叫喊。格萨尔王对我说:“这是我的臣民,我要去霍尔,从今天起,你要管理这个地方。”说完便双腿夹紧马肚,轻呼一声,马儿四蹄翻腾,长鬃飞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从长梦中醒来时,四处寂静无声,索南巴杂不见了。我独自躺在大石头上,四处黑咕隆咚一片,夜,像怪兽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我吓得从大石头上跳下来就跑。越用力跑,越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快追上来了。我大声骂索南巴杂:“我要把你抛到黄河里——我要剥了你的皮——我要打断你的腿——我要扭断你的脖子……”边跑边回头看,心里发毛。到家时已满头大汗,过了好一阵,我才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当晚,我一夜没睡好。
许多虫子从四面八方向我爬来,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阿爸把一本经书放在我头上,嘴里念着什么,阿妈点燃了一盏酥油灯,我看见那些虫子被酥油灯灼伤了。我对阿爸说:“还有一只虫子呢!”阿爸一下子把虫子给烧了。我又用手指着炕头:“阿爸,那边还有一只。”阿爸拿着酥油灯不停地灼着虫子。阿爸说:“不要害怕,我会把虫子一个一个地烧掉。”
第二天,我醒来时,阳光已照在窗户玻璃上,很是扎眼。我眯着眼睛看窗外,一群山雀落在对面的屋檐上,叽叽喳喳地啁鸣不已。我脑子里莫名地混乱,我问阿爸:“我昨晚怎么了?”阿爸说:“你一定是产生幻觉了,怎么会有虫子呢?”我说:“我真的看见了,有很多虫子。”阿妈满是疑惑的脸上夹杂着恐慌。她摸了摸我的头,对阿爸说:“我们应该去密咒师仁增那里算个卦,昨晚我梦见一只花猫往我怀里钻,就在那一刻,儿子尖叫起来,是不是泰乌让(泰乌让:藏语音译,意为猫鬼神)在害儿子?”
密咒师仁增对于我们卓香卡村来说,不像挂在佛龛里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唐卡,而是活生生的佛。凡有事,人们都会跑到密咒师那里请教。阿爸带我去密咒师跟前,双手合掌,向他说了我的遭遇。年迈的密咒师看了看我的脸,然后闭上眼睛诵了一段咒语。他从旁边的黄色小木柜里拿出来一个护身符送给我,说:“回去把这护身符戴在脖子上。”
回到家,阿妈说:“你以后不要再跟索南巴杂玩,他家的家神是泰乌让,泰乌让是专害儿童的。”
从那之后,我看见索南巴杂就远远地绕着走。感觉索南巴杂不是索南巴杂,而是那个叫泰乌让的可怕的独脚鬼。我对同学们说了,索南巴杂是泰乌让。同学们问我:“什么是泰乌让?”我说:“泰乌让是一种鬼,身体像猫,只有一只脚。”同学们都吓得说:“啊啧啧,再也不跟索南巴杂玩了,真可怕。”
索南巴杂再也没有朋友了,他成了一个孤独的牧羊人。
再后来,我到县城去上初中,见索南巴杂的机会就很少了。
再次见到索南巴杂时,已经看不到晃来晃去的鼻涕了,但他的头上留着一根长而粗的辫子。
那年夏天,索南巴杂的继父才让叔叔给他盖了三间瓦房,还分了二十几只羊。让他独自生活。村里的一些老人说:“索南巴杂虽然是个拖油瓶,才让对他还是很不错的。”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才让怕别人说他闲话。不管怎么说,才让叔叔给索南巴杂安置了一个家,一个还不错的家。
可是,分家后,索南巴杂做了一件惊掉大家下巴的事,他把二十几只羊全部卖给了羊贩子。
听说,村里的几个老人为这事专门跑到才让叔叔家里说:“你们两个怎么不阻止他,把羊全卖了,以后怎么生活?”才让叔叔反问道:“现在是各自的家了,怎么生活那是他的事,我今天可以管住他,明天后天谁来管他呢?”老人们也无话可说了。阿妈才姆也说:“男到十五不问父,女到十五不问母。他都十六岁了,也管不住了。”
既然他们这么说了,卓香卡的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那以后,索南巴杂跟之前判若两人,他比之前精神了。他镶了一口金牙。不管在哪儿碰到他,他都满嘴金光闪闪地对人们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会过得越来越好的。你们知不知道有句谚语‘夏琼寺在岩石上,我的算盘在心里’?”说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就在那年春节,乡里组织了一次大型文艺活动。要求每个村子都要准备一出节目。村长找到我说:“你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又正好是寒假期间,这事就拜托给你了。”我不好拒绝,勉强答应了。村长走后,我想着怎么交这差事,我除了诗歌朗诵,再也没有什么特长。乡里的文艺活动,观众基本上都是老百姓,这种场合朗诵诗歌显然有点不合适。这事的确难住我了。我左思右想,脑子里突然蹦出索南巴杂来:他不是唱《格萨尔》唱得非常好吗?
我立刻去找索南巴杂。
“我的大学生,您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索南巴杂说。
“机会来了,你要把握住……”我说。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好事还会轮到我?”索南巴杂说。
“你代表我们村,到乡上去演唱《格萨尔》。”
“不去。”索南巴杂不假思索地说。
“这是个好机会,村长说了,一等奖有1000元的奖金。”我说。
“您怎么知道我会拿奖?”索南巴杂说。
“你的嗓音像布谷鸟的鸣声,你不拿奖谁还能拿奖?”
我好好夸了一顿索南巴杂:“你是方圆十里最有潜力的说唱艺人,一等奖非你莫属。”说得索南巴杂有点晕晕乎乎的。
“您确定我能拿奖?”索南巴杂有点犹豫地说。
“相信我吧!”我说,“村长说了,村里还会给300元的补贴。”
索南巴杂高兴了。
那次文艺活动的场地,就设在乡政府后方的赛马场里。平日里空空荡荡的赛马场,那天人山人海。当索南巴杂身着金黄缎袍、头戴皇冠,画着浓妆走上戏台,当他的双手举起做着手势,唱起格萨尔有名的大鹏翱翔曲调的刹那间,好像英雄格萨尔王回来了。观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人在喊着他的名字。那天的演出非常成功,他为我们卓香卡争了光,他得了一等奖。活动结束后,乡上的领导给他颁奖时,他的身体不住地战栗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索南巴杂真出名了。乡上的,甚至县上的各种文艺活动也邀请他去唱《格萨尔》。
“格萨尔,你这是去哪里呀?”
“格萨尔,你的皇冠真好看!”
“格萨尔……”
那之后,人们把他的名字改成格萨尔了。
过了几年,索南巴杂把嫁过好几次,最后没人要的卓玛娶进家门。他们成为夫妻这件事,成了很多人的笑料。人们都讽刺地说:“这两口子的确是天生的一对啊!哈哈哈……”
老实说,卓玛几次出嫁都不算什么。嫁过几次的女人在我们村子也不止她一个。但是,她是一个不愿吃苦的懒女人,这才是最要命的。而且,她还带着一个拖油瓶。
村里的小伙子们对索南巴杂说:“格萨尔,你真有福气,不用自己折腾,老天爷白白给你送了个儿子。”他把长长的辫子往背后一甩,笑着说:“我是不幸中的幸运儿,老天总是照顾我。”
人们听了他的这番话后,或低头私语,或哈哈大笑。
那年夏天,索南巴杂如愿以偿地买了一辆旧的三轮摩托车。
这对整个村子来说,是一个重大新闻。它抹掉了卓香卡没有摩托车的历史。
那时正值暑假,我也去了。人们挤在索南巴杂家的门口看热闹,左邻右舍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索南巴杂骑在摩托车上,右把手使劲地拧动了一下,摩托车瞬间“轰轰”地响个不停,有些胆怯的孩子哭了起来。站在一旁的卓玛和她的儿子得意洋洋地看着人们。索南巴杂瞄了一眼卓玛后,把摩托车的油门拧到底,比刚才更响了。之前哭的那些孩子们被吓跑了。
索南巴杂在人群中喊我:“恩人,你要不要骑一下我的铁马!”听着真有意思,他把摩托车称作“铁马”。自从我推荐他去演出之后,不管在哪儿,只要见我就喊“恩人”,我有点难为情地摇了摇头,匆匆离开了。身后传来一阵阵摩托车猛加油门的“轰轰”声。
索南巴杂娶了卓玛后,形影不离。他对卓玛的拖油瓶呵护有加,不管去哪儿都带着那个像他小时候一样瘦的男孩。如果遇到村里的人,他喊道:“儿子,今天阿爸带你到乡上去吃面片。”或者:“儿子,你长大,这个摩托车就归你了。”一次,学校新来的一个年轻老师,用教棍把小拖油瓶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第二天,索南巴杂冲到学校,对那位老师一通大骂后,把他手中的教棍抢过来折断,并警告学生们“以后谁敢欺负我的儿子,我就像折断这教棍一样,折断你们的脖子”!
有一天,我在村口遇到了儿时的伙伴久美,久美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我俩很长时间没碰面。正在叙旧时,索南巴杂身着金黄缎袍、头戴皇冠,骑着摩托车,哼着《格萨尔》过来了,侧边的偏斗里坐着小拖油瓶。我向他招了招手。
索南巴杂便把摩托车停在路边,露出金色的牙齿:“恩人,好久不见,你好!”和我握了握手。
“格萨尔,骑着铁马去哪儿?”我笑着说。
“我的大恩人,托你的福我要去县上演出。”索南巴杂说。
“最近忙啊?”我说。
“到处请我,我不得不去啊。”索南巴杂说。
就在这时,站在我身旁的久美插了一句:“伟大的格萨尔,睡在珠姆(珠姆:藏语音译,格萨尔的妃子)的怀里感觉怎么样?”。
“真带劲儿。”索南巴杂昂着头说。
“怎么个带劲儿,你说说!”久美说。
“你骑着马,挑着灯,也找不到这样的女人。”索南巴杂不紧不慢地说。
“你不要再吹牛了。”久美说。
“就算我吹牛,也不会跟你这样的人吹。”索南巴杂说。
这两个冤家又开始针锋相对了。小拖油瓶一会儿看着索南巴杂,一会儿又看着我和久美。
“新婚夫妇,旧家什,有什么不一样的。”久美仍在调侃他。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索南巴杂说。
“你怎么说话呢?”久美说。
“我说的是人话呀,你听不懂?”索南巴杂说。
我示意久美不要再说了,但他不听。
“你这个巴杂,你真以为你是格萨尔吗?你连格萨尔的一只脚都不如。”久美说。
小拖油瓶用一种敌视的目光看着久美。
“你叫我什么……”索南巴杂飞快地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一手掐住久美的脖子,往后推了几下。久美把手伸向索南巴杂的头部,挣扎着。但是最后也没有够着索南巴杂的头发。我劝他俩,怎么也劝不了。索南巴杂可能用力过猛了,久美的喉咙里响着“嗬嗬”的憋气声,脸涨得通红。
久美打架的本领远不如嘴上的功夫。
“以后敢叫我巴杂,我就掐死你。”索南巴杂说完便放开了久美。久美“扑通”一下倒在尘土中,不停地喘着气。索南巴杂对我说:“我的大恩人,不要跟着这种没本事的人瞎混。我们藏族人有个谚语‘近塔者白,近锅者黑’难道你不懂吗?”
索南巴杂说完便骑上摩托车“轰轰”地离开了。
下午时分,听人说索南巴杂死了。也有人说索南巴杂在医院抢救。
“这怎么可能呢?早上还好好的。”我说,“你们不要瞎说!”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等到晚上时,去县上开会回来的村长详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村长说:“没事了。我们的格萨尔命硬着呢!”
原来,索南巴杂去县城的路上遇到一个溺水的小孩。他虽然不识水性,但赶忙停下摩托车,跳到河里去救那个小孩。小孩救上了,可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他这是,什么勇为来着?”村长问我。
“见义勇为。”我连忙答道。
“对对,见义勇为,这下索南巴杂成了真正的格萨尔。”村长说。
……
第二天大家在电视里看到了格萨尔——索南巴杂。索南巴杂躺在病床上说:“大家叫我格萨尔,格萨尔是什么?格萨尔是藏族人们引以为豪的旷世英雄。一个英雄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过了几天,索南巴杂骑着摩托车,脸色红润地回卓香卡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卓香卡一带的青稞熟了。大片大片的青稞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这是个小孩没时间成长,老人没时间衰老的季节。唯独我们的格萨尔清闲着,他仍穿着那件金黄缎袍,骑着摩托车,后座椅上坐着卓玛,侧面的偏斗里坐着小拖油瓶。在村子下方的田边瞎转悠,小拖油瓶不停地甩着手,嘴里唱着什么。卓玛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皮上抹着色彩斑斓的眼影,双手搂着索南巴杂的腰,脸紧紧地贴在索南巴杂的背上,好像没谁能把他们分开。久美看见后,骂道:“呸,什么格萨尔,三个白痴!”
索南巴杂骑在摩托上得意忘形地高声唱道:
我是东方的太阳,
曾把西方的雪山化成水,
没遇见凶狠的白狮,
你这黑狗却在后面追赶,
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
……
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索南巴杂用摩托车犁地的事儿。
阳光很好,远处高高的雪山俯瞰着卓香卡的动静。万物复苏中的大地,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人们又开始新一轮的耕作。那天我正好在帮哥哥犁地,索南巴杂家的地就在我家的地下面。我看见索南巴杂骑着摩托车,让小拖油瓶坐在犁耙上,在地里“突突”地拖来拖去。人们丢下手中的活儿,跑来围观。他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这之前谁也没有见过,用摩托车犁地这样的新鲜事,这在卓香卡的历史上绝对算是一件奇事。
“我们的格萨尔疯了!”
“哈哈,格萨尔就是与众不同!”
“好一个格萨尔!”
“我的天呐!”
……
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还不时奇怪地看着他俩。
小拖油瓶坐在犁耙上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满是汗。夕阳下,那个男孩犹如一座镀了金的佛像。他滑稽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唱起《格萨尔》中的一段来:
脱缰野马奔驰时,
獾猪如何能阻止;
暴雨念骤下降时,
微风如何能阻止;
岭军向北进兵时,
野牛如何能阻止。
看见这情景,人们都在摇头,说:“这小子简直跟索南巴杂一模一样。”
就在那一刻,摩托车“突突”的响声中,小拖油瓶看着围观的人们兴奋地叫起来。
我看着这对父子,忽然一股酸楚莫名地涌上心头,我的眼窝里不知不觉地装满了泪水,只要眼睛一闭,就会溢出来。

才让扎西,笔名:赤﹒桑华,青海贵德人。 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翻译家协会委员。青海省自然文学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分别在《民族文学》《文艺报》《诗歌月刊》《山西文学》《西藏文学》《青海湖》《章恰尔》《西藏文艺》《岗尖梅朵》等报刊网站发表。其他多部作品曾先后获得第七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奖、第五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二届青海省野牦牛原创作品提名奖、第七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第五届章恰尔文学奖、第一届岗尖梅朵文学奖、西藏文艺双年奖、第三届达赛尔文学奖、第三届全国岗坚杯藏语文学奖等多种奖项。2023入选青海省“昆仑英才·拔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