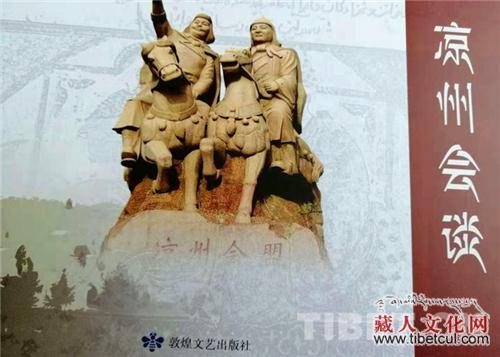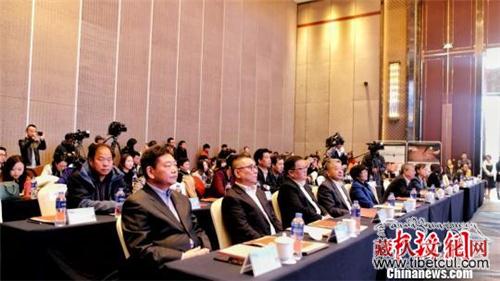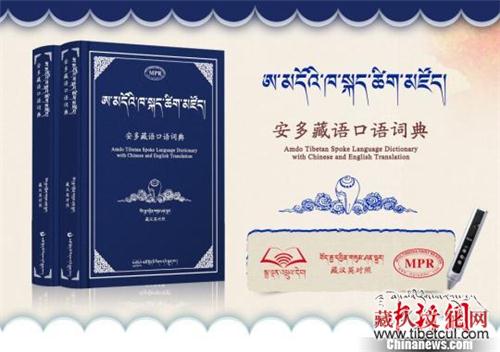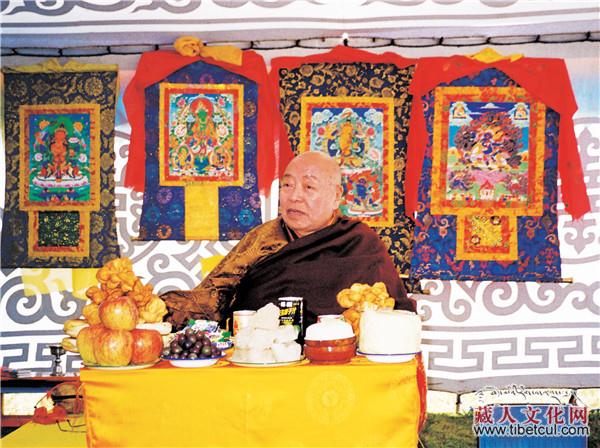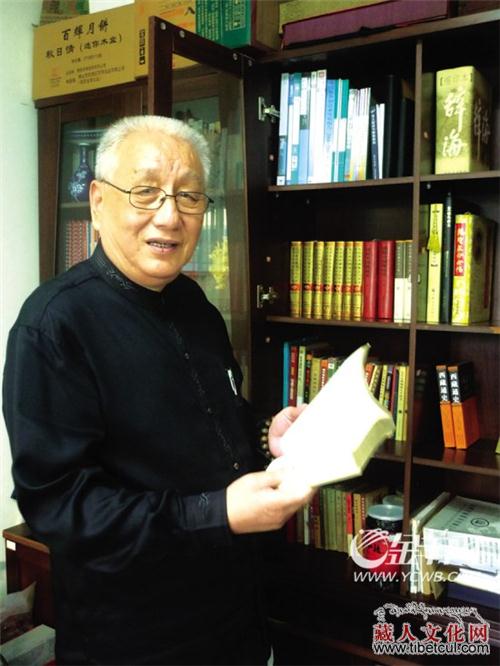在北京香山附近、北京植物园、曹雪芹故居等处游览过的人,应该会在无意间见过那里耸立着不少座梯形立方体形状的砖石建筑物,乍看之下,有点像“炮楼”,仔细端详,更像四川西部藏区的“碉楼”。这就是遗留至今的西山健锐营军事训练设施,用于士兵练习攻打“碉楼”的战术动作。这些特殊的训练设施,源自乾隆时期两次攻打大小金川的战役。在战争中,清军发现当地藏族人的碉楼非常难打,就在香山专门训练了一支山地特种作战部队,健锐营。主要训练内容就是如何攻打碉楼。碉楼在先期俘获的藏族人指导下修建,后来,被俘藏人越来越多,又押送到碉楼附近驻扎。
金川战役结束后,北京西山地区就多了不少藏族人。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一般自己归于满族,主要是正红旗和正白旗。但许多人能够记得自己的祖上是“苗族”,却不不知道是藏族后裔。
这就涉及到清代的民族识别,四川西部的藏族,其民族习惯许多方面和西藏的藏族不同,当时没有被归入藏族,却误打误撞被算成苗族。其实,和现代的苗族,各方面来看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据说,七十年代初,中国煤矿文工团的两位同志在西山一带采风时,发现红旗村、正白旗村有些农民会唱一种与北京地区民歌迥异的歌曲,歌词亦非汉语,询问其词义,则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无人懂得。问其祖上来历,也说不清楚,有的说原是南方的苗族,与清朝打仗,战败被俘而来,有的人过年节要专门进宫表演民族歌舞,所以南方的民歌保留下来了,但现在都使用汉语了,所以无人知道歌词内容了。煤矿文工团的同志将他们唱的歌曲录了音,到中央民族学院遍询从南方来的各族师生,期望能确定这种歌曲究竟属于什么民族的。正好有西南民族学院的赞拉·阿旺同志,是四川小金川地区(今小金县)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古藏文专业进修班攻读,他鉴别出这种歌曲应是四川金川地区藏族的歌曲。此后,中央民族学院部分藏族师生曾到红旗村一带调查访问,了解更多的情况,认为当地有一部分农民是从金川迁来的藏族人的后裔,大约是清代乾隆年间两次平定金川时有一部分藏族被俘,被迁来此处定居。从当地附近山上建有金川藏族风行的石碉房,可以得到佐证。
由于藏族人具有修筑碉楼、能歌善舞等特长,特别是会藏语,这批战俘相当一部分被发挥余热,送到了北京,编入八旗。
当时,北京西郊的香山、圆明园、颐和园一带皇家园林,一时间藏族式碉楼林立,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日下旧闻考》记载:“健锐营衙门在静宜园东南,围墙四角有碉楼四座,共房二十二楹。皇上阅兵演武厅一座,后有看城及东西朝房,放马黄城”,“园城……内设碉楼七处”,“健锐营官兵营房在静宜园之左右翼,共三千五百三十二楹,碉楼六十八所”。除健锐营的衙门和营房建有碉楼外,八旗印房亦建有碉楼,“静宜园南楼门外有八旗印房”,“八旗印房四隅皆有碉楼一座,乾隆十四年建。合之东四旗、西四旗各营碉楼,共计六十有七”,“静宜园东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之制,镶黄旗在佟峪村西,碉楼九座,正白旗在公车府西,碉楼九座,镶白旗在小府西,碉楼七座,正蓝旗在道公府西,碉楼七座。香山东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乾隆十四年奉命建设,后四旗同”,“静宜园西四旗健锐云梯营房之制:正黄旗在永安村西,碉楼九座,正红旗在梵香寺东,碉楼七座,健红旗在宝相寺南,碉楼七座,镶蓝旗在镶红旗南,碉楼七座”。
以上记载证明,从乾隆十四年起,清廷有计划地在香山一带兴建了一批金川藏族式样的碉楼,现今西山红旗村、正白旗村附近的碉楼即是其中一部分的遗存。建碉楼,主要由藏族人指导修建,后期俘获的藏族人,又驻扎在这些碉楼附近。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战俘被押来。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将被押送到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百八十九人编为一个佐领,归入内务府正白旗,加上唱番曲跳锅庄的二十八人以及第一次金川之役后留京的修筑碉房的十一人,该佐领共辖金川藏族二百二十八人。他们归人旗籍,成为内务府三旗中的旗人。
金川藏族佐领的住房是在香山附近,由管理健锐营大臣指定地方由健锐营公项支给费用,令其自行建造碉楼,实际上就是在香山形成了一个金川藏族村,这大约是因为香山的地形气候比较适合这些迁来北京的金川藏族人居住的缘故。
香山的金川藏族佐顿设骁骑校一员,催领四员,应在藏人中择人担任,由于暂时没有适宜的人选,所以先由健蜕营前锋章京书臣担任。
除了修筑碉楼、表演民族歌舞之外,香山的藏族佐领还负责出人担任藏汉、藏满的翻译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编入八旗,并处在北京西郊各村镇的八旗堆里,尽管有清一代他们一直延续着藏语翻译、藏族舞蹈等传统职业,整体却极速的满化,并在清亡后整体又汉化了。遥想大小金川战役,距今不过两百多年,比美国历史只长一点。如今,香山地区的藏族后裔,其实已经成为既不会满语、也不会藏语,而且还自认为是“苗族”后代的,却与周边汉族人没什么区别的满族人了。泯然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