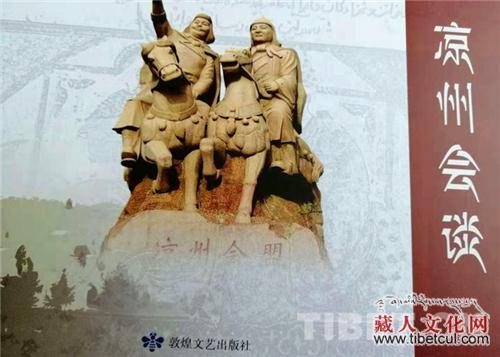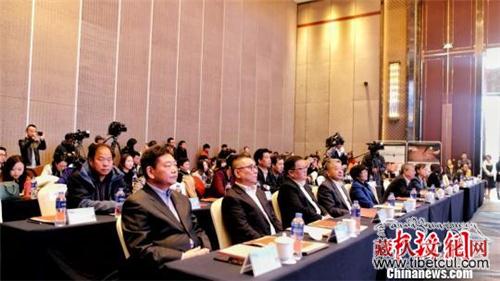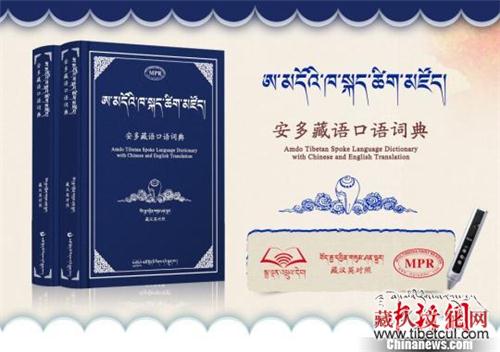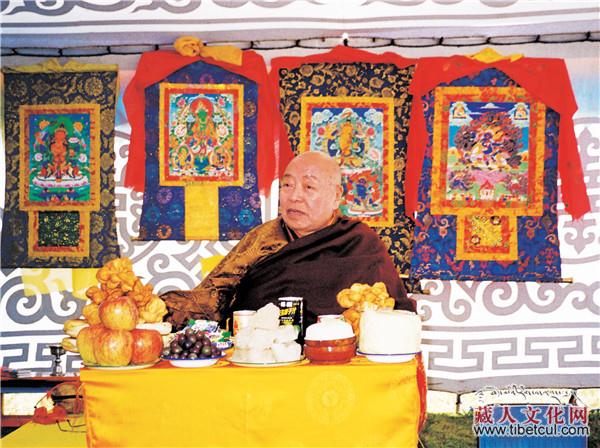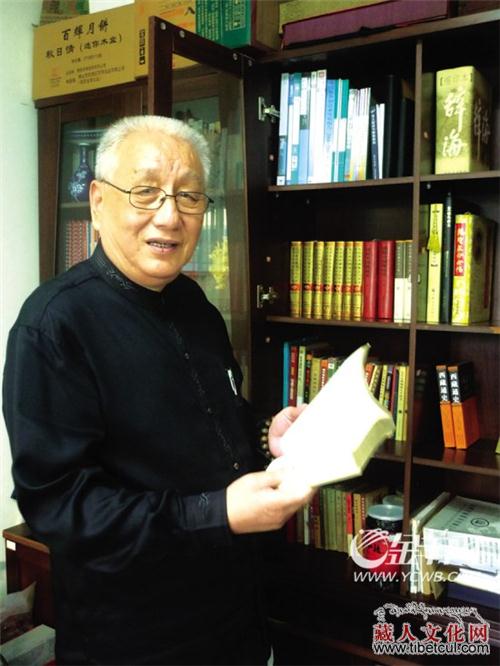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分为广义的法律文化和狭义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体现了一定社会、一定民族的人们为实现有利于生存发展而创造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以及对该社会进行的有目的的控制。广义的法律文化包括所有与法律相关的制度、思想体系、观念、行为模式、知识、习惯和心理,而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仅指法律观念、法律心理、法律经验与知识、法律传统,以及一些与它们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体系的部分。我们在这里谈的主要是狭义的藏族法律文化。
从近几年的藏族法律研究而言,其上限大多起于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时,忽略了对松赞干布以前数千年的法文化生成演变和传承历史的研究。探讨藏族法律和法律文化的缘起,史前时期和邦国时期的法律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
任何社会在管理过程中都表现为法的现象,归根结底都属于该社会的法律文化现象之一。从观念形态讲,法律文化之缘起可以追溯到远古氏族部落的禁忌习俗和宗教仪式,原始法律有许多方面是基于对神的敬畏。社会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大众舆论和知耻之心也起着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法律产生于习俗。它的活力既来自于大多数人的承认,它的效力亦来自于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产生的特定约束力和强制力,即它早己通过社会和文化转化为每一个人的心理强制,这是比有形的国家暴力强制要有效得多的保障。因此,表面上看,似乎一项法律、特别是国家法的执行是由外在的、特别是暴力强制所保障,但实际上,它更多地为长期形成的社会习俗和内化了的社会心理所维系。假定一个人要公然触犯一项法律,对于他来说,最难的莫过于冲破自己的心理防线,其次是社会公众的谴责,最后才是法律的威慑力。”[1]
法律在初始即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藏族的原始宗教认为人死后灵魂有三个去处:一是升入天界;二是托生为人类;三是堕入地狱。这一切取决于人的行为之善与恶。从而在人们的内心树立了杜绝恶的防线。后来传入的佛教认为人是由于前世今生的业(罪业)而不断轮回于六道中,要得到解脱,取决于个人在身、语、意(行为或行动、语言的表达、思想或心理活动)方面的行善积德、远离犯罪,最终获得佛果。认为人在世间的一切行为都被一一记载于每个人的阿来耶识中,无法逃过冥界阎罗法王的业镜,倘若一个人在世间犯的罪孽深重,在中阴阶段,经过审判、核实罪行,将被打入地狱,受到无尽的折磨。相反如果做了许多的善事,则会转生天界或成佛。这种思想在人的内心树立了预防犯罪的防线。而西方社会中的基督教则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和万物,人由于违背上帝犯了原罪而被贬到人间,需要从罪里被救赎,将来还要由上帝进行审判,等等。可见宗教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在尚未产生法律之前,社会的有序主要还是基于一定的宗教仪式和禁忌习俗。
同其他民族一样,藏族法律的最初发端也是与巫术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仪式制裁与法律的制裁之间无疑有一定的或必然的联系。在尚未出现成文法之前的数千年间,藏族先民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但可以肯定的是,史前时期藏族先民的社会中有一套风俗习惯或宗教禁忌在起着法律的功效或者可以说起着法律尚不可及的作用,维持着原始社会的秩序,史前宗教存在的可能性证实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宗教虽然只是社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宗教本身的真实与虚妄也并无必然联系,尽管宗教行为的本身或许并未产生仪式参与者所期望的结果,只是起到一种慰籍或震慑的作用,即在我们认为是虚妄的宗教和宗教仪式里,宗教的行为却产生了其他的效果,其中的一些效果是具有法律或社会效益的。譬如在原始社会对宗教神灵的敬畏之心对人们行为产生的约束和威慑的作用,使人们内心中的精神内核外化于他们的行为中,因之宗教在构成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其实起到和超出了法律的作用。学界一般将原始宗教或史前宗教归入苯教的体系中,看起来古代藏族社会中的宗教似乎只有苯教与佛教了。但是藏人的苯教也是在原始的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史前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在的藏传佛教则是在吸收古代藏人史前宗教和原始苯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期的苯教几乎囊括了原始宗教所有的神灵。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所产生的泛灵观念标志着当时藏族先民的社会状况,与统一的一神教产生时的社会形态必然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不仅对研究青藏高原这个特殊的地理单元中宗教史的发端发展有价值,而且对我们研究藏族法律文化的缘起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原始社会的宗教、禁忌、仪式和风俗习惯使古代藏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之中。
二
法是社会的产物,是为了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恩格斯云:“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 公共权利,即国家。”[2]按照恩格斯的理论,法律是先于国家产生的,而国家的出现须符合两个特征:“第一点它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不是按血缘关系来划分统治区);第二个特征是公共权利的设立,这是一种脱离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3]"根据这一理论,早在藏族历史上的12邦国时期之前,藏族的法已经产生了。
根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引《大史记》记载,在遥远的古代,雪域高原最初由十个王朝先后执政,玛桑九兄弟执政时期是第七个王朝,据《汉藏史集》记载:藏族社会早期由于谷物分配上产生不和而分为原始四氏族或原始六氏族,接着又是各有其特征的原始四种人,后即由玛桑九兄弟执政。这时西藏出现了箭套、剑、铠甲及小盾等武器。此后藏族社会即进入了小邦统治时代。此时,先后出现了“十二小邦”、“四十小邦”。每一小邦各有自己的王与大臣,分布在青藏高原的 “藏”(今年楚河流域)、“罗”(同上)、“吉”(今拉萨河流域)、“森布”(今拉萨以北的彭波地方)、“贡”(今灵芝地区)、“娘”(今灵芝地区的尼洋河流域)、“达”(今灵芝境内)、“牙松”(今唐古拉山南北一带)。这些小邦处在占山为王,兵戎相见,互相兼并的状态,形成了割据统治的局面。据《敦煌文书·小邦表》载:“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着一个个堡寨”。[4]从以上史料可知,当时的吐蕃在部落战争的基础上,出现了小邦及其政体形式,小邦的王与大臣们居住在堡寨里。[5]《五部遗教》说:“此时西藏仍被小邦统治,不能抵抗四边大王、产生三舅臣四大臣及父民六族,由二位智者顶礼王者”。《贤者喜宴》说:“上述诸小邦喜争战格杀,不计善恶,定罪之后遂即投入监狱,四边诸王时而压迫伤害”。同时反映当时已有了人为法的形式、有了监狱,但是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律规范,定罪标准也不一致。当时西藏各地的小邦由于兵燹不断,使西藏社会处在“赞普忧虑”、“百姓流离”的状态。 “小邦不给众生住地,居草地也不允许,惟依持坚硬山岩居住,饮食不获,饥饿干渴,藏地众生极为艰苦”民众和小邦之间于是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时在雅隆地方有 “以勇悍著称之浴氏与雅氏,以信义著称之琼〈库〉氏与努氏,以威严著称之索氏与波氏”。[6]等6个氏族部落聚居,即“吐蕃六牦牛部”。他们因缺少一位谋勇兼备的人为首领而经常遭受其他小邦的侵凌袭扰。于是他们便决定派人去寻觅一位能降敌抚民之士做“六牦牛部落”的首领。当时寻找首领的这些人正好碰上了聂赤赞普。据现存的西藏最早的史籍 《德乌宗教源流》及 《雍布拉岗目录》记载:“昔,波沃地方有一名为恰姆尊之妇女,生有九子,最幼者取名‘乌白热’,眉目俊秀,指间有蹼,具大德力,乡人不容,逐之出。前往蕃地时,适逢蕃人寻求王者,于强朗雅列空相遇,众人问,‘汝为何人?自何而来?’答曰‘从波沃地方来,欲往蕃地去’。又问,‘汝可否做蕃地之王’?答曰:‘尔等以颈载吾,吾自有法力与神变也’。众人便遵其命,以肩舆之,尊其为王,并上尊号为聂赤赞普。”聂赤赞普成了吐蕃六牦牛部的王,号称 “鹘提悉补野”和 “悉补野赞普”。
聂赤赞普被推为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后,当时的“聂墀赞普他有六种忧虑:即偷盗者、怒气、敌人、牦牛、毒和诅咒”。他首先“建造了最早的堡寨雍布拉岗,降服了苏毗之苯教徒卧雍杰瓦,又将努王所有小邦收为属民,”[7]其次,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五部遗教》载,“当时对偷者治罪,对怨怒者施以仁慈,对敌人加以压服,对牦牛予以管束,以药除毒,以及消解诅咒”。《拉达克王系》中云:“聂赤赞普之时,以四戍部保卫赞普,‘桂东岱’四十四部征服外敌,‘庸东岱’四十四部管理内务,于四哨所设哨卡,并以八队军旅征伐哨所之敌。于容多以二十二甲士保卫仓库,十二商市献来财宝,以好坏之奖品区别智勇,恶者惩罚罪责,杜绝欺诈之源,对于五种贤慧者以金玉及告身奖之,对于五类勇者饰之以狮、虎、五种骑士乘马奔驰”。[8]从而统一了周围诸部落,这样,雅隆悉补野部发展为定居于吐蕃雅砻琼结一带的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的强大部落。从此到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子孙世袭赞普称号,开创了藏族历史上世袭宗族的统治。毫无疑问,不论国之大小,定有一套基本的国家机器为之服务,其中即包括法律和行政体系,但是有关聂赤赞普时期法律与政体的史料阙如,苯教典籍《协玛》中云:“苯教法早于国法。”《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这样记载:“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护持国政。”另外藏文典籍《德乌教法史》中择其要云:“(王臣于是)到了雍布拉康宫,在原本的夏仓。—— 庐和雅的基础上在青瓦达孜宫于九重白布围护中,以神的教义为法,产生了仲、德吾和苯(三者与法相辅相成),各种神奇智慧之想法出现,制定了桑缀南森的议事会。以两种惩罚形式和五种褒奖方式制定了吐蕃的法律,根据王谕分别授予九种告身和八种英雄称号,世上四方的国王于是向聂墀赞普进贡。”用短短几句话对聂墀赞普时制定法律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记载。根据这段史料,聂墀赞普最初建立吐蕃雅砻王朝时,有两个称为夏仓的官辅佐他执政,随之鉴于原有机构的弊端以及制定法律和健全机构对治政的重要性,遂召集大小众臣来到青瓦达孜宫秘密协商了法律的制定和机构的健全等问题。从“九重白布围护”可以看出,当时法律的制定是在严密的重重保护之下完成的。聂墀赞普时称为桑缀南森的议事会是最高的执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向赞普负责,其主要职责是对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法律和文化等方面出现重大事物进行研究和议商。按照事情的轻急缓重分别由三级议会商议,因而称之为桑缀南森即三级秘密议会。主管宗教和文化的机构称为泽拉康,主持苯教教义的念诵、祈神、求福驱邪等,口唱历史和故事的仲和启发民智的德吾也属于泽拉康的职责范围。另外尚有施行两种惩罚的形式和五种褒奖方式的机构,以及给予九种告身和八种英雄称号的军事机构。聂赤赞普时期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对当时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三
藏族早期的法的渊源和特点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间的战争不断,小邦割据,对异部落的征伐及战后对征服者的处置一般是用杀戮等手段达到消灭和震慑的目的,而对于作战中懦弱的本部落人员也采取处罚的手段,因而,战争中的军法成为藏族古代刑法的渊源之一。
祭祀是古代很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人们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的最初认识,古代藏族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控制着一切,于是产生了繁杂的神灵系统,为了获得神的护佑,镇伏鬼怪的侵扰,兴起了种种的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的兴起产生了完善、严格的祭祀仪式,成为人们遵循的规范,也成为藏族神判法等的渊源。
藏族早期的法以口唱等形式传承。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法律进化论》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西刹尔于其《科尔战记》载有的布列顿人及科尔人中,其司宗教、道德、法律之僧徒,能谙记一切法律而口传之事实,由是观之,英法两国,于西历纪元之顷,已行记忆法,布莱克斯通于其 《英国法注释》第一卷,论英国不成文法之起源,谓往昔蒙昧之西世界,一切法律,是为口唱的,且引用前揭西刹尔之记事而附记之。并谓萨克逊人之祖先及在大陆之同胞,仅依记忆及惯行而保存其法律;又同书之第四卷,谓口授不成文法之观念之起因,缘于僧徒不载其教法于记录之惯例之所致也。”[9]在藏族的史籍记载中亦云:在遥远的古代,由仲、德吾和苯三者主持国政,其中的仲即指口唱的史诗 (其中包括许多法律方面的内容)等,而德吾则是指以谜语等形式启发民智,苯是指通过念诵、祭祀和举行宗教仪式来达到护持国政的目的。
藏族早期的法及其立法思想以神的教义为基础,教法合一,以仲、德吾和苯等形式宣传神的教义,与法相辅相成,据史书记载从聂墀赞普到第七代藏王塞赤赞普 (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五世纪)“笃本”盛行于藏区,苯教史书记载,当时还建造了第一座苯教寺院—— 雍仲拉孜寺。(见手抄本《雍仲本教史》)“笃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苯教巫师参与国政,享有很大的权力。[10]苯教法师不仅参与国政,而且苯教法师一般居家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直接参与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褒奖善者,惩罚恶者是藏族早期法律的独特性。邦国时期政法不分,诸法合体,对守法者予以奖励、对犯法者进行惩罚。聂墀赞普时以两种处罚形式和五种褒奖方式制定了吐蕃的法律,法律形式为誓(以言语相约束,主要指军事行动前对将士发布的军事命令和军事纪律。)、诰(即告诫)和训(赞普的命令),两种处罚形式即对善行予以财物的嘉奖和褒奖,对于恶行则予以体罚和没收财产的处罚。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有利于统治的五种褒奖方式和基础五法,其具体内容已佚失。九种告身类似于松赞干布时期以官位的高低予以不同的告身 (金字、绿松石字、银字、金饰银、铜和铁字告身,其中每一个分大小两种,共十二种),松赞干布时期的告身制度当起源于聂墀赞普时的九种告身。八种英雄称号即如同松赞干布时期为了表彰对政权稳定、固守边境有重大贡献的勇士,根据大小勇士分别赐予虎皮褂、虎皮裙、缎鞍垫、马蹬缎垫、虎皮袍和豹皮袍。
法律做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是为统治者的精神思想及社会大众的安宁生活服务的,在履行法律的过程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谚语、格言、神话和史诗等相结合的形式是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形式,对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培养起了积极的作用。藏族的传统法律文化中也还残存着原始的宗教哲学观和宇宙观、原始禁忌习俗及传统的道德观等。法律制度的变化同物质层面的法律一样是较快的,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但突然建立的制度可能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脱节,在法律观念上不会被人们认同,在法律实践中亦不为人们所遵守。这从赔命价的习惯法在内的民间俗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中可以得知。而长期形成的法律观念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譬如具有史前性质的万物有灵观念至今影响着藏人的意识形态,对藏人的神判法、环保法或环保习俗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尹伊君 . 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11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8.
[3]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168.
[4]王尧、陈践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161-162.
[5]恰白·次旦彭措.聂墀赞普本是蕃人[J]西藏研究,1987.(1)
[6][7]巴卧·祖拉陈哇 .贤者喜宴 [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1980.(4)
[8]群宗编辑 .拉达克王系 [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27.
[9]穗积陈重 . 法律进化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81.
[10]五世达赖喇嘛.郭和卿译 .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