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藏族诗歌”地理版图与知识分子的乡土写作上,刚杰•索木东的诗集《故乡是甘南》描绘了不可重复的精神原乡——“甘南”。本文将从恋地甘南与中年写作的角度,探讨《故乡是甘南》的书写意义。
【关 键 词】恋地甘南 中年写作 乡土记忆
2017年12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该诗丛推出了来自四川、甘肃、青海、云南、西藏等五个省份/自治区的10名藏族青年诗人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不同地域藏区青年诗人作品的一次集体亮相,加上汉藏双语的对照排版,对阅读者与研究者而言,都可谓新鲜丰盛的文学佳宴。因为地理空间、民族身份、文化传统与日常经验为诗人提供的资源和际遇,10名藏族诗人的写作皆表现出深厚的文学文化传统,如对地方知识、民族文化、区域历史、史诗以及地方歌谣的重述与借用,但他们的诗歌写作仍然有自己的独特声音和腔调。 譬如嘎代才让的《西藏集》与刚杰•索木东的《故乡是甘南》,都对生养于斯的青藏高原情有所寄,却在个体经验、语言修辞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各有特色。嘎代才让以西藏为自己的“精神高地”,钟情于书写隐秘的传统、自我的地理学以及令人兴奋的绝望 ;刚杰•索木东则以甘南为自己的“精神原乡”,执着于甘南乡土人文地理景观的记忆重构、乡愁的层层铺展与不断重述。
在“藏族诗歌”地理版图与知识分子的乡土写作上,刚杰•索木东的诗集《故乡是甘南》描绘了不可重复的精神原乡——“甘南”。本文将从恋地甘南与中年写作的角度,探讨《故乡是甘南》的乡土写作意义。
一、恋地甘南与“水泥的缝隙里植长绿色”
刚杰•索木东又名来鑫华。在藏语里,“刚杰”是雪域,“索木东”是“青松”,合起来,“刚杰•索木东”即是雪域青松之意。诗人署名郑重,写诗时署藏语名“刚杰•索木东”,其他场合才会用到汉语名“来鑫华”。署名,是选择一种身份、一种态度和一种立场,署名“刚杰•索木东”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献给故乡甘南的严肃又深情的诗歌。
诗人生于甘南、长于甘南,成年后因为求学与工作方面的原因离开甘南,此后便不断地在甘南与兰州之间折返。表现在诗作上,则是诗人对故乡甘南从未间断的记忆重构,对兰州这座现代城市的排斥与反感,以及不断的“离乡”-“折返”-“离乡”的纠扯往复。甘南是原乡,兰州是成年后寓居的城市,甘南与兰州地理空间的交错与并置,构成了“都市与原乡的双重地理意象” 。相较都市,诗人的笔触充满了温情与感伤,他眷恋着甘南及其往昔的一切,尽管这一“恋”字从未直接言明。段义孚先生在《恋地情结》中曾指出,尽管“恋地情结”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但它能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 可以说,甘南是诗人情感抒发的主要载体,甘南亦是诗集中随处可见的重要符号。恋地甘南,即是诗人生命中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之一。
在写作于1997年的诗作《故乡是甘南》中,诗人就钟情于对甘南记忆的书写。其时,诗人刚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大学,因此便有了“生活于甘南—走出甘南—回到甘南”的叙述结构。诗人笔下,甘南贫穷又苍凉,充满了苦难。想到甘南,诗人就会想到风雪、篝火与大草原的牛羊;想到黑色的大地上,同胞的弟弟坐守马背;想到一地格桑在空旷的甘南心般怒放。 正当少年的诗人为何钟情于甘南日常生活记忆的罗列呢?因为时空拉开了距离,因为“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 ,通过回忆甘南的日常生活,在还原并建构甘南特有人文地理的同时,诗人的认同感才得以存在。在《故乡是甘南》一诗中,诗人不停追问自己:走出故里就能摆脱困苦吗?诗人虽未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即便是如此困苦与贫瘠的故乡,当诗人回望的时候,它却成为诗人对幸福的向往。于是,“守望甘南”成为诗人一辈子不变的姿势。与此相关的,是诗人的灵魂及其寓居的身体找不到恰切的位置安放,就像是“永在水泥的缝隙里植长绿色” ,或者说“就如一片不合时令的叶片/在这个遥远的城市/既不能永立枝头又不能潇洒的落地” 。
绿色的、自然的生命,就如青稞,本应生活在田野,一旦在田野之外,在密密麻麻栽种水泥高楼的城市里,必将难以存活,也就“无法点头”了(《青稞点头的地方》)。此外,《十个蝈蝈,或远离的高原》中的蝈蝈也不例外,远离了高原与大地后,在兰州这座不夜喧嚣的、临水干涸的城市里,蝈蝈和“我”一样,无法享受真实的黑夜,也无法做到优美的高歌。青稞、蝈蝈既是故乡的意象,亦是诗人自我的隐喻。远离了田野的青稞、蝈蝈和“我”都不属于充满汽车尾气的现代都市,却又无可逃遁,只能委屈又别扭地在水泥的缝隙里挣扎而生。
或正因为身在城市心在故乡的缘故,诗人乐于用温情的笔调铺陈甘南的乡土人事。除了前面提到的《故乡是甘南》一诗,《甘南屋檐下》中,诗人写到草地、青稞、牛羊和牧人,写到雪山、鹰隼、经幡和桑烟,写到村庄、歌谣、炊烟和黄昏。 在《听说你去了玛曲》中,诗人写到老阿妈的黑帐篷,写到灵魂和露珠一样清脆欲滴的早晨,写到格桑花无私的芬芳,写到青稞成排倒向大地,写到玛尼堆旁与生死佛揭,写到怀抱弦子走过身旁的民间艺人与转经筒。 从这些诗作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诗人保存着自己在甘南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日常生活场景记忆的不断再现,就像是要“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既展现甘南特有的人文地理风貌,呈现藏人独有的乡愁,亦使其“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 。
如果说诗人把温情柔软的语词给了故乡甘南,那么,对于都市和南方,他却充满了敌意与厌弃。《都市面孔》中,诗人笔下的花朵是“媚俗的”,都市面孔“不随岁月更改”,一切都矫揉造作; 《阳光下的庙宇》中,南方是现代的、浮躁的;北方的兰州污染严重;雪域才是家乡,因为有牦牛骨头的念珠,有古老的寺庙。庙宇是人类精神的安慰剂,对在城市找不到回家路的中年游子更是如此。
可以说,故乡甘南的人事风物既是诗人乡愁的症结,也是诗人疗愈乡愁的良方。在不断回望甘南的人文地理与乡土人事中,诗人的乡愁被治愈结痂,又不断地被揭开,如此循环往复,时痛时缓,纠扯难安。正如诗人在《只是一个恰当的比方》中写到的一样,人近中年,“我还是不能/把岁月一份为二/一半交给城市/一半还给青藏”, 诗人找不到和解的方式,只能在故乡甘南与现代城市间不断撕扯,有一种宿命的悲情与哀伤。
二、中年写作:踩着岁月走进少年的往昔
《故乡是甘南》这本诗集中,时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目前,已有学者从刚杰•索木东诗歌对四季隐喻化的书写、童年—青年—中年贯穿性时间的诗化表达,以及诗人对黑夜的偏爱三方面,指出时间概念是诗人感受和思考人生的一种方式。 因为“时间”是理解《故乡是甘南》的重要维度之一,笔者将在此基础上延展论述。
《故乡是甘南》收录了诗人1997—2016年间写作的88首诗歌。其中,与诗集同名的诗歌《故乡是甘南》写于1997年,《青稞点头的地方》与《守望名叫甘南的那片草原》写于2002年,其余大部分诗歌均写作于2010年以后,即诗集中的诗歌基本上写于诗人30岁以后。诗集呈现了两种自成轨迹又彼此关联的时间概念:一是自然的四季流转,它们朝着时间轴做周期性的循环闭合运动;一是个体生命成长的时间,这类时间延时间轴线性向前。与此相关的诗歌书写,表现为季节性的思乡病、30岁前的“青藏咏叹调”与30岁后中年心境的“人世温润”写作 。一般来讲,少年时,我们生活在一个鲜活的世界中,我们对待世间万物的态度与方式是完全开放的。随着生命周期的延展,我们对世界的探索与感应不断拓宽。 因此,随着年岁渐长,诗人对待人世万物的态度便会有所不同,诗歌表达亦会呈现不同的特征。
《甘南:用四季的四种方式怀念》 这首诗歌中,其时间概念与时间隐喻尤为显著。诗歌中,诗人从冬天的甘南写起,写“一盆牛粪火燃起的冬天”里,“一个新的生命需要诞生”;接着写春天里“十八年前的那个少年”与“大金瓦殿的桑烟刚刚升起”;然后写夏天里“牧场愈走愈远,情歌愈走愈远”以及“一碗奶茶再也煮不出久远的味道”;最后写秋天里“成排的青稞扑倒在地,高原一高再高”,而“我只能选择一个远走的方向”。从冬春到夏秋,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这种几近圆形的、周期性流转的时间观有意无意地逗引诗人患上季节性的慢性病症——思乡病;与此交叠的另一条时间轴上,个体依循生命阶段成长着。诗人笔下,草原上落满大雪的冬天蛰伏着生命的新生,丰收的秋天同时还意味着人事的衰老以及诗人的远走。从诗人对甘南四季日常生活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的心灵时时牵系故乡甘南,身体却无奈地选择了背离的姿势。诗人从青年时期离乡求学就经受的撕裂与痛楚从未得到完全的治愈,在季节性的时间之轮中,不断地添加新的“伤疾”,于是,诗人便只好在时间流转里一次次回返,借助回忆和书写故乡来疗愈自己。
诗集中,与四季、时间相关的诗歌有《秋天,给我的故乡》《在春天想起圣哲仓央嘉措》《春天,走过一个山村》《这个季节,请你来到草原》等。诗人的思乡情绪常由四季的物候兴起。他写风,说“风把四季的门次第打开”(《青稞点头的地方》),或是“风从四季的四个方向捎来口信”(《甘南:用四季的四种方式怀念》),或是“风把头向四季的四个方向伸着”(《秋天:给我的故乡》),又或是“北山的垭口,裸露着的狂风四处流窜”(《生命唤不醒的回忆》)。四季流转,风儿亘古,诗人的乡愁与守望亦亘古。除了写四季的风,诗人也常写青藏高原冬日的大雪,诗人呢喃“这个季节的雪一直没有落下/妈妈,这个季节/你远游的爱子/依旧不能回家”(《这个季节的雪没有落下》),诗人感慨,“甘南啊,这个不落雪的冬日/ 我再一次向你一步步靠拢/ 其实就是为了寻觅那滴名叫归去的浊泪”(《故乡是甘南》)。除了大雪,甚至是四季中的一场大雨,也会让诗人“靠近高原,靠近遍地泥泞的甘南”(《在一场大雨里靠近高原》)。可以说,诗人的整个身心都在及时又敏感地回应自然时序的节奏与变化,回应时间节令的唤醒与感召。
在循环往复的四季流转中,诗人亦从少年步入青年及至中年,表现在诗歌上,“中年”字眼开始频频出现。诗人独处的夜晚“梦开始增多”(《青稞点头的地方》),骨头里有了缝隙,甚至能听到“碎裂”的声音(《这个季节,请你来到草原》)。故乡,越来越像一段未醒的梦,当诗人在宿醉的夜半偷偷醒来时,会在静谧的院落里数童年的星星(《故乡,只是一段未醒的梦》)。或许是身体与精神的中年状态以及时时渴求回返记忆中的甘南之故,诗人笔下,与童年有关的人事物逐渐增多,时空层叠并置的情景亦愈来愈多。在《记梦》一诗中,诗人写道:
昨夜,又梦到奶奶了
三十年前的老木屋
仍旧漏着风——
想把冻伤的童年
伸进被窝,这个暖冬
却没有一片雪落下
童年、三十年前的老木屋与中年、三十年后城市的高楼,通过梦境得到瞬时的共存。在《这个季节的雪没有落下》一诗中,故事是“昨夜的故事”,草地亦是“昨天的草地”,而中年的“我”还在“等着用花手帕包藏远去的童年”,渴望在“牧歌悠扬的夜晚”,“摸着一缕熟悉的炊烟回家”。在城市无所依傍的“我”,执着地用词语和形象表现童年,自然是为了保存童年以及童年时代的甘南村庄。在《春天,走过一个山村》中,诗人自我追问:“我还能踩两脚泥泞/走进故乡的大门吗?/我还能,踩着岁月/走进少年的往昔吗?”少年往昔,在诗人中年后,不自觉地成为了诗人回返故乡的钥匙。中年身体里不断跳将出来的童年,就这样成为了连接诗人与故乡并治愈其乡愁的药方。
可以说,四季的流转往复与个体生命的线性成长、故乡甘南与寓居城市的空间阻隔,都是不可更改的。不过,诗人却巧妙地通过童年与中年时空的多次层叠、并置与转换,弥合了现实生活中诗人与故乡甘南物理的时空阻隔,也一并补偿了诗人思乡却不能随时回返的心理缺憾。这种情思与睿智,与诗人离乡廿载,人到中年的生活状态不无关系。
三、故乡甘南书写的意义
刚杰•索木东的家乡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诗人对甘南的深情书写,既属于知识分子的乡土写作,亦是藏地书写的一部分。在《袖起来的双手,一言不发》中,诗人写道:
很早就明白
离去,只是一个
多么简单的抉择
该回去的时候
才知道,太阳
早已西斜
“有谁知道,一个藏人
真正的乡愁呢?”
——掩卷而泣的长者
点亮,一盏酥油灯
他满头的银发里
我望不到,喜马拉雅
山顶的雪
就乡愁而言,诗人清楚自己的乡愁是藏人的乡愁,其身后有着深厚的藏族文化的根基与影子,因此,字里行间必然会呈现藏族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晨间沐手、焚香、敬佛、点酥油灯,为扎西达杰出(即“八吉祥”)写诗,这些都是藏族知识分子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情。与那些刻意描写藏族文化元素来凸显藏地的神圣与神秘的作品不同,刚杰•索木东有藏族知识分子的警惕与自觉,他希望自己的诗歌呈现的不是异质化了的青藏,而是一块自然存在、真实明亮的土地,就像每个人心中的家乡一样。 因此,为了避免放大和渲染藏地的神秘,诗人专注于个体日常生活记忆的书写,在温情灵动的、可以触摸的甘南布景中,表达其对家园故土的深情眷恋。
刚杰•索木东曾自称自己是一个游子、一个写作者,是目睹了沧桑巨变的游离者。 世事变迁,诗人的故乡甘南亦不例外。作为一个写作者,诗人并未停留在对故乡人事的“凭吊”上,而是通过记忆的回溯与时空的层叠并置,记录并建构了属于作者的不可重复的故乡甘南。作为一个游子,守望故乡固然是一种姿态,能否回乡却是其无法回避的中心话题。《故乡是甘南》诗集的最后一首诗作是2017年写就的《路发白的时候,就可以回家》,诗人写道:
我们站在草地上唱歌
天色就慢慢暗了下来
再暗一点,路就会发白
老人们说——
路发白的时候
就可以回家了
多年以后,在城里
我所能看到的路
都是黑色的
我所能遇到的夜
都是透亮的
而鬓角,却这么
轻易就白了
鬓角已经发白,城市道路却全都是黑色的,回家之日似乎遥遥无期。故乡,还能回得去吗?对此,刚杰•索木东坦言,回不去故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因为今日之故乡已经不是儿时的故乡。从地缘上来讲,是回不去的。能回去的,还是记忆中的那颗“故乡心”。 于是,对天真烂漫的童年的渴望,像梦一样辽远又切近的记忆,成为诗人回返故乡、逃离都市的一种途径。尽管就地缘而言,诗人回不去故乡甘南了,但是有关故乡甘南的书写却从未间断,因为四季流转往复,生命延展向前,“我们随时都可以从过去当中自由地选择我们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不论何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能随心所欲地唤起对它的回忆” 。诗人刚杰•索木东对于故乡甘南的回忆与书写即是如此,从未间断,也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吉狄马加:《一切诗歌都从“当地”产生》,“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2.邱婧:《嘎代才让与属于他的西藏:嘎代才让诗歌创作论》,《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6期。
3.邱婧:《藏地记忆与混血诗学:重读刚杰索木东的早期诗作》,《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4.[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6页。
5.[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3页。
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7.张晓琴:《尚未抵达的返乡者:刚杰•索木东论》,《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8.[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80-83页。
9..刚杰•索木东:《故乡是甘南》,才让公保译,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年。
10.刚杰•索木东部分访谈。
原刊于《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年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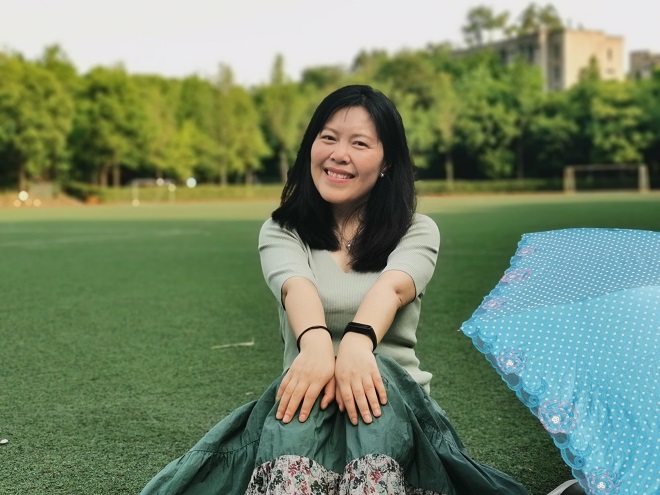
付海鸿,女,四川邻水人,文学人类学博士,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鱼鳞滩往事”公众号发起人与主编。

刚杰·索木东,藏族,又名来鑫华,甘南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