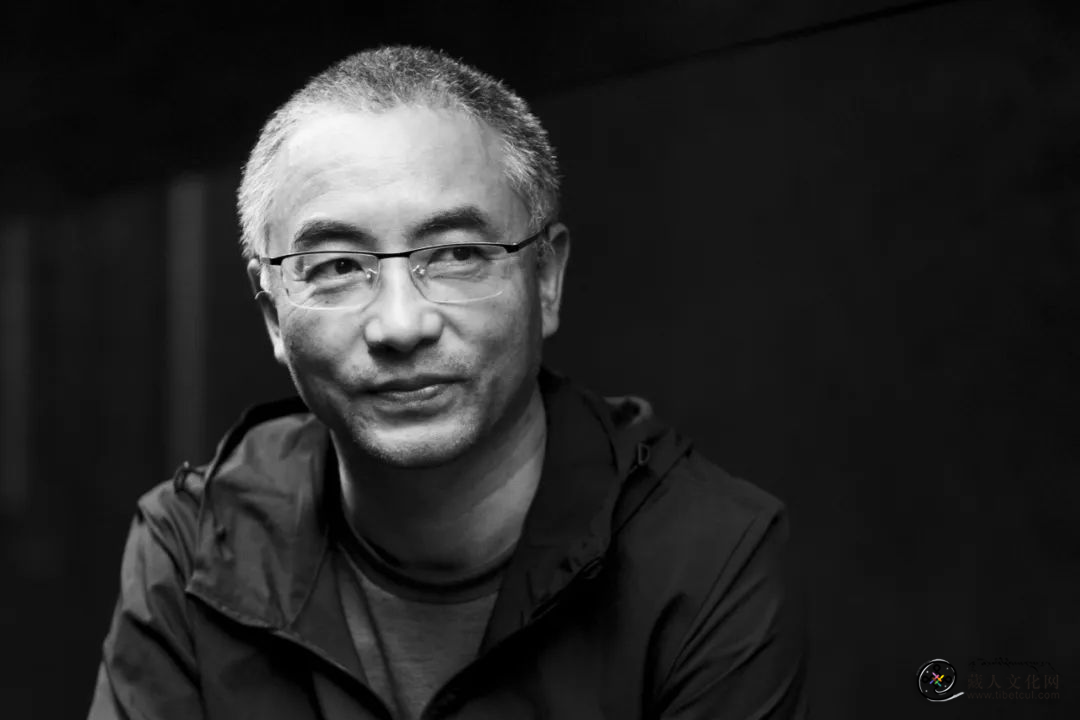一
历史是一个民族对自己过去的客观和主观的再现和表现,历史的客观性会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大概框架的记忆,从而形成基本认知,并适当进行还原,对一个有史官记载历史的民族,其历史的还原可以通过文字的记载和考古的挖掘获得,其客观性远远大于主观性。官方的正史记载和民间的野史记忆有着不同角度的记载,我们可以通过辩证性的认识得到历史的客观性的认识。但少数民族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大多数都是口头传承,因此,民间的主观性较强,它基本上是以世代传承的方式获得历史的记忆,是一种精神的记忆。
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虽然有着古老的文字,但由于文字基本上掌握在少数僧侣、贵族和王族手中,因此,历史的承传基本上是由大多数的民众来完成的。而大多数民众在解放前并没有掌握文字,故历史的书写一般都是口口相传为形式的,主观的精神记忆就是藏民族对历史的理解。藏民族对历史的记载有很好的口传系统,这就是以神话、民间故事、藏传佛教为恒定系统的传承理念。在宗教、医学、科学、心理学、艺术、文学等学科领域中,神话、藏传佛教都用强大的定式维系着各个学科的正面性,显示出民意的总趋向,“神话是知识、权力;神话是集团史;神话是道德史,其目的是要使生产了它的,且使它的听众的那个集团和谐一致。事实上,在某些历史、文化条件下,当形象对于作家或某一集团,对于某一整体,具有一种解释性的、起规范作用的、伦理的价值时,上述定义的每一成分就都可用来构成这些形象的特点”。在神话和宗教为主导理念的藏民族那里,价值判断、思想定位的形象特征都以此为准。历史就是在这两者的精神记忆中形成了英军的“魔”的形象传承,并通过等级的否定、故事情节中的阴谋、残忍与真诚、善良的斗争过程,将英军的形象固定下来。魔的形象,在中外小说中很多见,如著名的撒旦、靡菲斯特,其特点是诱惑人类犯罪。在藏族历史中,从《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众魔的周旋中,在释迦牟尼与魔的斗争中,魔的侵略内涵已经深入人心,洋魔成为对侵略者形象的固定的话语指称。在藏民族文化思维、集体想象中,魔的形象就是破坏和平和佛道的具有恶心、恶行、恶业的魔鬼,所以,藏民族对魔有着强烈的谴责和否定之意。我们就以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次仁罗布的《曲米辛果》为例做一些分析阐述。这两部作品都以英国人侵略西藏的历史作为主线,其客观性和主观性就是以民间的口传为精神记忆的。
100多年前,西藏曾遭受过三次英国的殖民侵略,这些侵略的缘由都是英国殖民者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倾销在国内滞销的茶叶,意欲用基督教代替藏传佛教,以军事占领西藏来威胁当时的中国,从而达到从经济上、思想上、政治和军事上殖民西藏的目的。这场战争以英军的洋枪洋炮对阵藏军的土枪、飞石,最终以阴谋、欺骗和残酷、血腥大肆屠杀了善良、淳朴而毫无防备的藏族士兵,侵占了西藏。在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中,首次将西藏曾经经历的三次非常重大的战役进行了英雄浪漫主义的书写。在开篇的首页中,有这样一段话,“喜马拉雅,你旷古的绵延容纳了雪域所有的爱恨与创伤,雅鲁藏布江,你无声的流淌孕育了藏民所有的沉默与信仰,西藏的战争,是否能承载人类丢弃对抗,走向融洽的理想?那么多生命,一一离去,如同掉落地面的果实,枪炮过后,西藏还是原来的西藏,经幡高昂地飘扬着,胜利属于宁静与默想,战争中,爱情、人性、神灵、信仰将如何走向终极,走向死亡与再生,归一与大同。”杨志军用近500多页的内容详描述了隆吐山战役、曲米辛国战役、江孜战役这较大的三场战役。这对三场战役的描述中,作者在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英国人的形象进行了塑造,形象涉及到英国国会、英国商人、英国传教士、英国军官、英国士兵等。个体的英国军官和群体的英军士兵是主体形象,他们都是破坏和平、毫无廉耻、恶心、恶业的魔之形象。从具体的个体形象而言,有为敛财和占有异国文物以满足私心的英国指挥者———麦高丽上尉,战争不过是自己迅速敛财的工具而已,其形象贪婪、无耻,他将自己侵略西藏的目的毫无廉耻的表露出来“让白金汉宫拥有西藏的佛像,因为它是大英帝国征服世界最高山河的象征,让麦高丽将军的私人博物馆拥有比北京皇宫里的桌椅、瓷器、黄缎绣屏更有价值的犍陀罗雕塑,即使不是纯金打造的,也一定是宝石镶嵌的古老鎏金。”于是,他将戈蓝上校攻陷的紫宁寺、萨玛寺、白居寺的金佛和贝叶经及佛像,全部带走。还有为了让藏民族屈服,大举进犯西藏、以残酷屠杀、欺骗的方式镇压藏民族的反抗的戈蓝上校,其形象是阴谋者、屠杀者、殖民者。这是个善用阴谋而且非常残忍的殖民者,在他眼里,所有的国土都属于英帝国,他率领十字精兵用洋枪洋炮不断攻击藏族的村落和寺庙,他假装与藏军谈判,用所谓的咖啡和酥油茶之间的友好商谈麻痹了藏军,继而突然袭击藏军军官和藏军,开始了卑鄙的大肆屠杀,造成血流成河的曲米辛果战役。他也不断地用枪炮推进着战争的脚步,血腥屠杀了毫无防备的藏兵。戈蓝上校在语言中透露着凶狠、狂妄、残忍及虚伪,“戈蓝上校恶狠狠地收敛起眼睛里明锐的蓝光说‘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上帝的刀枪,基督的子弹是无所不穿的’”,戈蓝上校对自己臭名昭著而露骨的殖民意识也毫不忌讳,“我们为最后的胜利而来,西藏划归英国的日子并不遥远,上帝已确定了”。不论是利己者对异国财富的掠夺,还是殖民者对异国土地的占有,他们身上的恶心、恶业已昭然若揭,他们就是侵略者、破坏和平者,是毁坏善心、善业的魔鬼。面对蓄谋已久、悄然而至的英军,藏族民众表现出最原始、最淳朴的战争理念———公平合理的通知和双方准备好的公平合理的交战。在文中,驻守边境的连长欧珠准备面对英军挑起的侵略战争时,他“对战争的理解还没有掺杂阴谋、诡计、智取、诈夺,而是堂堂正正、公平合理的通知这正是在善心、善业的宗教理念下,善人行为的战争,但英军却是在恶心指导下的恶业,是属于魔鬼的行为,于是在作品中,英军的外形就是魔之形象,西藏边防守军连长这样描述刚见到英军时的感受,“魔鬼,不是形容坏人时的说的那种魔鬼,而是货真价实的魔鬼,只有魔鬼的眼睛才是蓝的,惊人的豺狼的阴险、幽蓝,忽闪忽闪亮着,骨碌骨碌转着,似乎马上就要摄走你的灵魂”。于是,通篇的洋魔成为英军的代名词,在藏民族反抗洋魔的侵略时,其作战时体现出英军魔之行为,“《圣史》指出,英国人在说明战争理由时,总强调是西藏军队首先开枪,却隐瞒了最重要的事实,西藏军队是守卫,他们是进攻,西藏军队是朝天打,他们是朝人打”,栜而英军则是在指挥官的命令下,任意用机枪扫射着无辜的藏族民众,对保卫家园的藏族村民和僧侣进行血腥的屠村、屠寺,其惨烈让人不忍直视。每到一个村庄、每到一个寺庙,英军在毫无人性的屠杀中侵占着西藏的每一寸土地,英军的残忍、破坏和平,伤害众生灵的恶性、恶业的魔之形象跃然纸上,藏民众用“恶魔”来形容英军的侵略。在次仁罗布的《曲米辛果》中,作为21世纪西藏历史的研究者,“我”从英国人写的《拉萨的真面目》中去了解所谓真实的曲米辛果战役。正在疑惑时,一个百年前的战争冤魂穿越时空而来,让“我”看到了西藏战争的真相。亡魂阿牛郭达,曾与转世前的我,一起参加了曲米辛果战役,一起浴血奋战,抗击英国侵略者,并死在战场上。“我”转世为现代人,而他承担了女神的承诺,要向百年后的藏族人告知战争的真相,故以没有转世的冤魂的状态沉默了一百年。百年后,他穿越时空来找转世的“我”,向研究百年前西藏战争的转世的“我”详细叙述了战争的经过。冤魂或理智、或沉思、或激情、或悲哀地叙述当时的战争,从“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我”用强烈的谴责、愤恨来否定英军的侵略、欺骗、残忍和血腥,认为英军是阴谋者、血腥屠杀者、无人性的恶魔。在作品中,也对亡魂阿牛郭达眼中的英军做了描述,“我们是要去拉萨,说是大鼻子的英国人跑到了我们的地盘上”,“大鼻子黄头发的英国人”等。可看出,在藏民族的心里,他们对英国人的古怪、厌恶之感非常明显。小说进而描述英军为了麻痹善良的藏民众,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侵略的目的,先进行谈判,让双方放下武器。善良的藏军在和善的意愿下,放下了土枪,结果,英军用先进的机枪突然袭击,大肆屠杀了毫无防备的藏军。其中英军上层军官用心险恶的层层布局,将其狡诈和阴谋的魔之恶心凸显出来。而后,用魔之恶行对曲米辛果的民众进行了残忍和毫无人性的大肆屠杀,对曲米辛果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英国兵提着步枪在追杀后撤的藏兵,马克沁机枪刺耳的声响在曲米辛果上空震荡,在枪声大作中,藏兵像被收割的庄稼一样,一大片一大片地栽倒下来”。魔之恶心、恶行、恶业在英军身上得到最全面的诠释。
纵观两位作家的作品,它们都涉及了英国侵略者的形象,都以恶魔、不怀好意、阴谋者、骗子这些非正义的形象出现;当然,这都是以英国军人的形象为主体,侵犯者、掠夺者构成了英军的主要形象特征;作品对英军在外貌上进行了相似的描述,红发魔鬼、妖魔。这些形象在藏传佛教中都是护法神铲除的对象,这种对侵略者客观因素的主观精神描述,符合了形象学中关于异国形象是主体在主客观意识的混合下而形成的情感形象,它渗透着主体在既定文化模式影响下对客体的塑造。
与此同时,两位作家又有不同点。杨志军用浪漫主义手法将英军形象进行爱憎分明的表述,而把恶魔般的英军统帅的描写与善良真诚的佛性道德的藏民众的描写的对比,以佛魔的对立战斗来表现善心、善行、善业与恶心、恶行、恶业的持久斗争。而在次仁罗布的笔下,又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将英军的形象进行群体化的描述。具体过程则是:百年亡魂阿达生前经历了曲米新果战役;但历史的民间记忆,使阿达成为向转世者传达真实历史的冤魂;于是阿达作为前世的记忆,向“我”这个已忘记前世记忆的转世者描述了真实的战争场面,在阿牛郭达唤起前世记忆的那一刻,“我”既成为被呼唤者,又成为呼唤者,从而将这种意识继续传承下去。这种意识流的写法,是以藏传佛教中轮回转世理念为基础,也是藏民族对英军侵略者、欺骗者、残酷者认知的集体记忆,它在时空的流转中永不泯灭。不论是对西藏三大战役的英军个体形象情感性和发展性的描述,还是群体性形象模式化的描述;不管是浪漫主义手法,还是意识流的手法,其形象的描述在“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以主观性和客观性混合的表达方式创作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否定形象,既言说了魔之象征形象的恶心、恶行、恶业,又言说了自己的善心、善行、善业。这种叙事逻辑,反映了藏民族在思想和艺术上富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言说方式。二元对立的否定和肯定,使藏民族的精神书写更侧重于对善恶的伦理表达。
魔之形象,在杨志军和次仁罗布两位作家的笔下有了传承的套话定式,使魔之形象在两个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共识,并通过各种艺术手法中的情感因素将魔之形象丰富化、生动化。而形象中的“套话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释放出信息的一个最小形态以进行最大限度的、尽可能大的交往。它直指事物最主要的部分。因此它是一种摘要、概述,是对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标志的表述。它在一种简化了的文化表述和一个社会间建立起了一致的关系。将表述提升到本质的地位,要求尽可能广的社会文化协调。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对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希望有效的所谓集体知识的陈述。套话不是多语义的;相反,他却是多语境的,可在每一个时刻反复使用”。魔作为一种套话,既以世界共性存在,又以民族共性存在,两位作家将藏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标志以最简化的概述进行表达,并在特殊语境中反复使用。战争作为善恶较量的特殊语境,佛魔对立的集体知识陈述,再一次将英军侵略者、阴谋者、屠杀者作为魔的载体,使魔成为他者的文化表述,它最大限度地反映了藏民族在宗教情结下的恒定思维。
二
藏民族一直将佛性追求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目标,对一切违反佛性、破坏佛性的灵魂和行为是否定的。因此,对历史中曾发生的影响藏民族精神和生活的事件也有自己的定义和想象,他们用自己民族特有的对历史的精神记忆进行了历史的陈述。在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就有许多关于英军先后侵略西藏的隆吐山、曲米辛果、江孜的相关记载。这三次侵略直接导致了西藏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损伤巨大,中国的领土被践踏,西藏民众被大肆屠杀,寺庙被毁,珍贵文物被掠夺,信仰被亵渎。
1888年,英国发动了对隆吐山的武装进攻,驻守隆吐山的藏军,仅靠火绳枪、弓箭、刀矛等十分落后的武器,同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但是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前线藏军得不到有力支援,藏军失败,并导致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1904年3月11日,1300余名英国侵略军开始向曲眉仙郭藏军营地推进。当时西藏代表作最后一次努力,要求荣赫鹏谈判,以避免使用武力,而荣赫鹏则一面伪装谈判,一面派其步兵、骑兵、炮兵偷偷向藏军阵地推进,等到开始谈判之时,藏军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了。英军谈判代表到来后,首先声称:‘既然要议和,为表示诚意,我军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贵军指挥官下令将火绳枪的点火绳熄灭!’英军指挥官即当场命令子弹退出一发,殊不知,在一刹那间英军又将子弹推上了膛,而藏军并未发觉,依然下令将点火绳全部熄灭,于是,英军谈判代表荣赫鹏把藏军指挥官拖住。当英军的机枪开始向藏军疯狂扫射时,英军谈判代表也突然拔出手枪将藏军谈判代表拉丁色代本、朗色林代本、班禅代表苏康努、如本康萨及三大寺的一名谈判代表通通击毙。”第一声枪响后,英军使用来复枪和大炮在约180米处,向善良和毫无防备的藏军展开了赤裸裸的血腥大屠杀,并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藏军近千人。江孜战役中,雄伟的紫金寺毁于英军的战火中,但这对侵略来说还不够。西藏文史资料选辑是这样记载的,他们将寺内的文物抢劫一空。计有:高达四米,小至十厘米的铜制镀金佛像一千多尊,唐嘎、堆绣佛像、金粉书写的《甘珠尔》(大藏经),蒙古地方和祖国内地以及尼泊尔国出产的各种佛事乐,金、银、铜制的大小神灯和圣水碗等器皿,有银质“曼扎”、铜制“唢呐”以及各种缎绣神龛和祭品等。这伙英国强盗甚至连该寺大殿内僧众坐的长垫子也抢走,致使幸存下来的扎巴到处流浪行乞。藏历五月,英军在紫金、江热一带驻扎期间,任意将其战马放在农民庄稼地里,造成成千上万克(克约等于亩)青稞颗粒无收。凡英军所到之处,人民惨遭蹂躏,住在孜雪利康扎丁的差巴户家里的英军强奸妇女,抢夺占据群众财物,撤离时还将他家的羊群赶走。人们随时都能听到受害者凄惨的哭声。一首民谣描述了此番惨景:“江孜地方美如仙境,如今到处哭叫声声;聚宝只为乐享太平,哪料成为镜花水月”。
这不可辩驳的历史性事件,在西藏的历史资料的叙述中,虽然有一些情感因素的涉及,但还是保留了当时历史的真实。而在《喇嘛王国覆灭记》中,美国人对这段英军侵略西藏的历史也进行了客观而精确的陈述,“英属印度沟通与西藏联系的企图促使英藏之间于1903年至1904年发生了战争,英国侵入西藏,促使一系列冲突,无法控制的力量操纵了西藏历史直至今日。刚刚脱离遥远的中亚又卷入到了中国、英国和俄国的外部事务中,侵略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和目光转向了中国、西藏与印度以及欧洲列强俄国等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上。”英国侵入西藏,意欲将西藏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的侵略目的非常明显,而掠夺和倾销的经济利益使侵略西藏的目的更加迫切,侵略者的政治目的、经济目的使英国人的形象被固定在“邪恶”中。
不论是中外历史的文本记载,还是藏民族的精神记载,英军的魔的形象已是共识;但藏民族在集体传承的精神记忆中又将这个形象进行文学表述化,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文化意象,用宗教的象征、史诗的象征使之成为一种藏民族共识的形象。这实际上也反映了藏民族在特殊时期经受了几次外敌的侵略,但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认同感使藏民族将英军的侵略行为作为他们的信仰的对立面,从而表达了藏民族反对侵略,主张国家主权,誓不与魔为伍的情感。
西藏的这种精神记忆与社会制度有关。由于在解放后才有大量的藏族子弟入学受教育。因此,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只有少量的的文本记载,大部分都是口传记忆,也就是世代相传的精神记忆。这种精神记忆与具体文字表述有一定区别。用大量的谚语和诗歌,用传说和民间故事,是口传文学的特点;因此情感色彩非常强,尤其是爱憎分明的情感非常突出。在藏民族的意识中,对战争有着本能厌恶和反感,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精神非常乐观,在思想和情感上比较趋同于当时国家的定位和宗教的定位。由于当时清政府虽然有妥协之举,但对国家和平统一的民族认同,使他们对民族分裂者和侵略者深恶痛绝。所以,在藏民族的记忆中,善良者是不会侵略他国的,即使是最凶恶的动物,藏民族都会用最仁慈的话语形容它,因为动物的凶恶是因为人类的侵犯,所以动物和人是和平相处的。《西藏的战争》中以一头非常凶猛的熊与侵略者对比,藏族姑娘被熊所救,并与熊友好相处;但熊被英军射杀,因为在英军的眼中,熊是可怕而危险的凶残的动物。藏民族能和熊和谐共生,但英军的残酷和阴谋是藏民族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对英军的比喻从来不用动物,而是用现实中不存在,但在宗教中存在的可怕的妖魔鬼怪作比喻,这些妖魔鬼怪的特点是,祸害人,杀死人。
“在这一阶段,这个用词汇构成的形象或这个想象的词汇表所反映出的集体想象物就是一种形象汇编或辞典:这是一代和几代人,一个社会阶级或多个社会文化阶层共有的观念、情感和工具。使用某个词就将首先反映出某种宗教、政治、哲学的选择,这种选择还具有可合并和可互换的效应。”苯教和藏传佛教是藏族对世界认知的源泉和思维方式。苯教以神话传说深藏在藏民族的精神记忆中,随时都会被唤起,而藏传佛教作为系统化、普及化和灵魂化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藏民族的意识深处。魔的形象作为非常有情感色彩的词,他反映出藏民族的自觉选择。套话是形象学的具体术语,表明了在群体意识的影响下,在既定文化模式的影响下,个体形成的刻板印象,从而在集体的包装下固定化和统一化。在苯教中,藏族文献《斯巴左普》作为藏族创世神话,其中也有恶魔之说,其名为闷巴色丹那保。他是从黑卵(迷惑、愚昧、疯狂)的中心产生的黑光人,他与从自己影子中生出的黑暗女神结合,生下八儿八女,这八儿八女又与异性相结合,繁衍构成了恶魔世界。对于恶行,用咒语驱散魔鬼,提倡万物的平等,万物有灵,藏族民众从不伤害人,在骨子里,是与人为善。试图用善业为来世的转世做努力,因此认为破坏善业的魔,就是破坏善业的修行。自然界最凶残的动物都有善心和善行,所以藏民族从不用动物来比喻恶人,魔在藏民族眼中就是没有善根的恶人,如果用魔来比喻英军,可见英军的恶性和恶行是何等的不人道,甚至超越了凶残动物的伤人。在藏传佛教中,关于魔鬼的概念是这样表述的:“魔罗的略称,来自于梵文,意译‘扰乱’‘破坏’‘障碍’等,佛教指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大智度论》卷五:‘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魔之恶业与佛之善业背道而驰,魔总与佛的身心口合一、做善事、行善法相冲突,并对佛最终的无私利他、和平善良进行破坏和扰乱,而战争、侵略、分裂、欺骗、自私利己、祸害他人恰恰是魔的本质所在。佛教传说中的魔王———魔波旬,“被称为欲界六王之一,他常常率眷属到人间破坏佛道以战争破坏佛道是魔波旬的恶业,在古老的婆罗门神话中就有天神与恶魔的战争的主题,当佛修法或讲法时,魔王波旬乔装打扮,以“我今宁可,往坏其意”或“我今当往,乱其道意”的目的,扰乱释迦牟尼的修行,破坏其获得无上正觉的过程。释迦牟尼识破魔王的身份,曰:“此是恶魔,欲来乱我。”后来,释迦牟尼在道树下,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众,得胜菩提果佛与魔之战,是善与恶之战,故魔之业为黑业,佛之业为白业。藏民族对于魔的集体认识来自于深层文化内涵的共识,而英军的行为是魔的恶业表现,他破坏和扰乱了宁静、和平、善良的佛国之境,使西藏陷入了动乱、血腥、争斗中,这是藏民族不愿看到的。对佛的向往和对魔的厌恶使藏民族在对立冲突中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爱憎情感。这种情感在神话传说和宗教教义中得到不断强化,《格萨尔王传》中花花邻国是佛国,而霍尔国是魔国,故霍尔王是侵犯他国领土,掠夺他国资源,并凌辱他国民众,造成他国灾难的罪魁祸首。在藏民族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这种对魔的概念以河床式的积淀深藏在藏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当相似情境出现时,就会被唤醒,从而形成集体共识。
历史的记忆在藏族精神的记忆中,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完全虚构。对一个形象集中地进行魔的形象的建构,是来源于生活中形象化的记忆。对一个始终以感性理解历史、理解生活的民族来说,其形象诠释来源于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二元论的佛魔对立,使藏民族对于善恶世界有着非常明晰的观念,并将这种观念作为评判世界是否有价值意义的标准;而信仰则使这种观念成为稳定的评价系统。杨志军、次仁罗布作为文化身份的认同者,作为拥有当代文化知识的作家,将历史进行了文学化的真诚表述。历史的精神记忆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唤起,经过两位作家的各有侧重点的描述,使西藏百年前的三次战役重新浮出水面。两位作家的作品作为藏民族精神记忆的载体,使英军的“魔”之形象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色彩。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七辑)

卓玛,1966年生,藏族,青海省西宁市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在《外国文学研究》 《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外比较视阈下的当代西藏文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