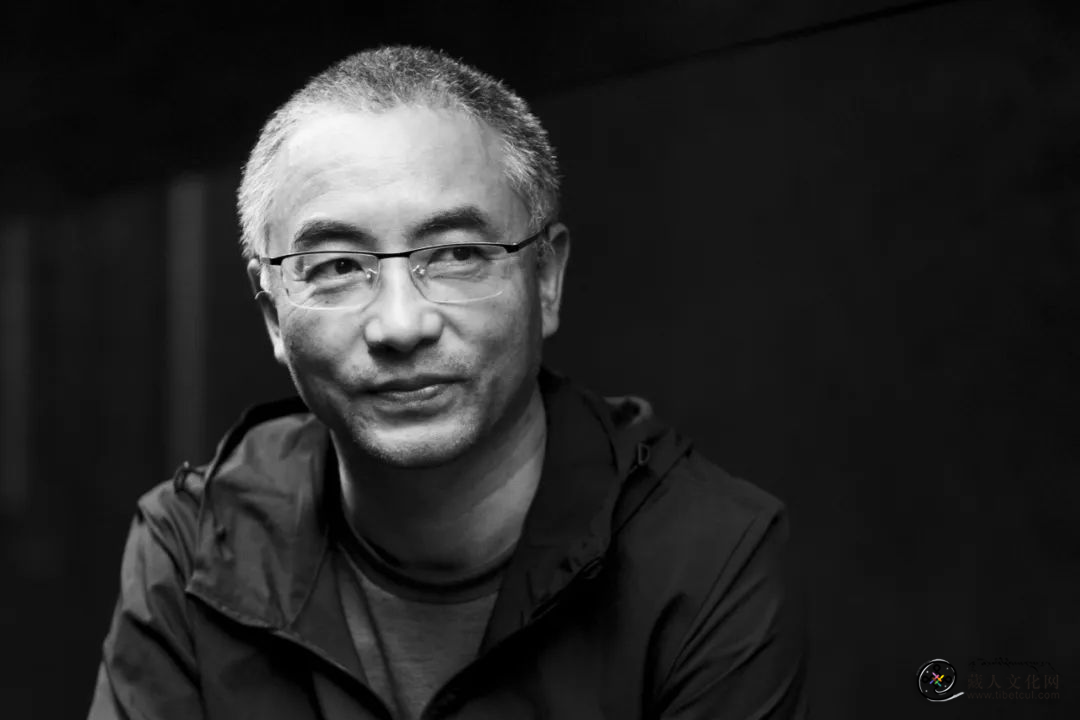在同龄诗人中,陈人杰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出生于1968年的陈人杰,到目前为止只出版了《回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西藏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三部诗集,与其他一些动辄出版十几本甚至几十本诗集的同龄诗人相比,在数量上相差很大。在数量并不突出的创作中,陈人杰及其作品获得了较多的关注,2008年参加了《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诗集《回家》2009年获得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组诗《仰望星空》获得《诗刊》社2010年度诗人奖,由他作词的大型组歌《极地放歌中国梦》2016年获得第六届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特别奖,《山海间》2020年获得第五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文本奖,2022年获得第四届昌耀诗歌奖·诗歌创作奖,诗集《山海间》2022年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虽然现在的各种奖项如汗牛充栋,关于各种奖项的批评、质疑也不少,获奖并不能全然代表创作者的真实成就,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在人数众多的诗歌写作队伍中,希望获奖的人应该不少,尤其是在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奖项中,要冲出重围最终获奖,作品的艺术质量肯定还是占据了较大的分量。
关于陈人杰的诗歌创作,很多诗人、评论家有过关注,韩作荣、叶延滨 、曾凡华 、吴思敬 、耿占春 、罗振亚 、沈苇 、曹宇翔 、胡弦 、西渡 、霍俊明等撰写过或长或短的文章予以评介,他们对诗人的前期探索、援藏工作、藏地书写[1]、人文情怀、话语方式等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大多是感悟式的,可以为我们进入陈人杰的诗歌世界提供一些思路和角度,不过总体来说还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作为当下书写藏族地区最有特色的诗人之一,陈人杰的诗歌还有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话题。
陈人杰的藏地书写展现了藏族地区的历史、现实、自然 、人文 、宗教 、风物 、风俗等众多领域。大多数读者很难获得对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直接了解,很多时候只能通过阅读、想象等方式来实现。通过陈人杰的诗,我们可以在想象、联想中完成一次难得的精神之旅。
一 、以“外来者”视角发现西藏
青藏高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被称为世界屋脊,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由于地理、气候、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原因,青藏高原有很多地方还属于没有开垦的处女地,甚至属于生命的禁区。但这片土地又是滋养生命的沃土,亚洲的很多大江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成为滋养生命的源泉,也使西藏(以及其他藏族地区)满足人们对于圣洁、纯净、天堂、世外桃源的想象,成为人们心中的诗与远方。虽然很多人难以亲身在藏族地区寻觅诗与远方,不过,这种梦想使许多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有关的诗与其他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一直受到读者(观众)的关注和喜爱。他们通过艺术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次精神之旅和心灵的净化。
藏地题材的新诗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广受关注。这些诗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土生土长的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诗人创作的作品,以他们为中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具有影响的雪域诗群,至今还有不少藏族诗人活跃在诗坛上;二是外地诗人到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之后创作的作品,洋滔、马丽华、魏志远等都奉献了不少优秀的诗篇,如今我们又读到了刘萱、陈人杰、黎勇、北乔等人的作品,他们是作为援藏人员进入西藏或者其他藏族地区的,在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待的时间相对较长,有些甚至最终调到了藏族地区生活和工作。至于作为游客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创作的作品,更是难以数计。
对于西藏来说,陈人杰是一个外来者。在藏地书写上,他和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具有不一样的视角。作为浙江人,他骨子里拥有江南文化的基因,这种文化和其他地方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形成冲突,但如果能够带着这种 “前文化”基因,打量陌生的土地与文化,也可以为艺术的发现提供不同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促成艺术的创新。陈人杰本来是从事金融工作的,曾经担任中信金通证券金华营业部总经理,长期生活在江南 。按照世俗的眼光,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日子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他却去了海拔5000米的地方参与援藏工作,而且持续了两个工作周期。如果说第一次去西藏,他多少是带着任务去的,那么他接下来的继续参与就应该是一种主动行为,是一种情怀使然了。关键是,六年援藏之后,他申请调到西藏工作,把自己变为一个西藏人,至少是 “新西藏人”。除了援藏干部、工作人员身份之外,陈人杰还是一个诗人。他关注藏族地区,是带着诗人的独特心态、视角的,而且带着曾经的人生底色。这种独特的切入角度使他的作品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
“外来者”视角带来的是新鲜,是独特,是不一样的感悟和表达方式,可以为诗歌艺术探索提供独特的创作经验。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坛上,随着人员流动的增加,不少诗人迁移到故土之外的地方工作、生活,创作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诗篇,广受诗歌界关注的“打工诗歌”大多属于这种情形。其中有两个浙江人以“外来者”视角切入陌生的(至少是不熟悉的)地域和文化,都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一个是诗人沈苇[2],他从浙江到新疆,走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和散文,融合了江南文化的细腻和大漠戈壁的粗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另一个是陈人杰,他一路向西,十多年的时光里,他用身体和心灵去拥抱西藏,在时空交织中去感受独特的青藏高原,同样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
这种身份转换使他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江南文化、西北文化或者西南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从文化、文学的地域特征来看,不同地区的文化观念的冲突肯定是存在的,而且自然环境、气候、文化基因、生活方式等也存在很大差异。他们带着江南文化的“模子”,或者说是个人的“前文化”积淀,去打量别样的文化,从别样的文化形态中发现了独特的元素,比如新疆文化的粗犷、西藏文化的神秘,这些具有差异性的文化形态就成为艺术创新的重要资源。“模子”的说法来自叶维廉先生,他主要谈论的是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隔膜主要源于西方人喜欢以自己的文化“模子”打量东方文化,于是出现了很多偏见。因此他说:“一个思维‘模子’或语言‘模子’的决定力,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加以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3]在中华文化的不同区域间,文化存在差异是很明显的。在文学创作中,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弥合差异,寻找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往往可以在艺术创新上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陈人杰前往西藏之前就已经是知名诗人,曾写过《在底层》这样充满疼痛和悲悯情怀的诗,在诗坛上引起了较大反响。他的诗集《回家》书写了一个诗人对故乡的感悟,表达了对生他养他的故土的深切关注和怀想。他心中装着众生,装着他人,关注现实生存,书写民生疾苦。他的藏地书写,从诗集《西藏书》到《山海间》,将他的人生感悟、生命体验、精神高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如果说他前期的创作主要是向下的深入,向外的拓展,主要关注充满烟火气的现实与人生,那么他的藏地书写则多了向上的寻觅,向内的挖掘,通过自我感悟获得对生命的思考。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由现实关怀逐渐走向生命书写,是一个不小的转型,但在陈人杰那里,似乎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带着江南文化的“模子”走进藏族地区,以 “外来者” 视角打量别样的文化并逐渐将这种文化纳入自己的生命之思,既弥合了文化之间的差异,获得了创新的资源,又实现了艺术方式的转换。
陈人杰的藏地诗歌涉及题材非常广泛,尤其是对西藏的自然、山水、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打量,让个人融入博大的自然、文化之中,并由此反观个人生命的渺小。这种转换有一个过程:“刚刚到达西藏时的艰难,比如高原反应、疾病、孤独、寂寞、思念等,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首先给了诗人一个‘下马威’。但寂寞和痛苦历练了他的沉静和深邃。病中的沉思,看窗帘和阳光,‘吃饭,散步,都是拿肉体打比方/拿西藏当食粮’(《日子》),以后他一个人在旷野上读书,仰望蓝天,捡石头,于是就有了身体的清澈、轻盈,有了灵与肉的分离,有了从天空朝向大地的凝视等换位和超脱。”[4]经过实地历练的“外来者”渐渐和藏地文化达成了和解,心态、情感都发生了转变,诗歌的格调也发生了变化。《冻红的石头》[5]写的是高原景色,其主题是“高原并不寂寞”。诗人说,“世界上,不存在真正荒凉的地方/孤独,只是人感到孤独”,他发现夜里“雪峰在聚会”,“旷野里的石头冻得通红/像孩童的脸”,另外一些石头“黑得像铁/像老去的父亲”,简单的勾勒将西藏的风光幻化成人类。而且“它们散落在高原上,安然在/地老天荒的沉默中/从不需要人类那样的语言”,这些“石头”已经在高原存在了无数年,依然存在着,留下了生命的启示,但这些启示是隐含在它们的沉默中的,诗人从中发现了更加恒久的生命意味。《岗巴》[6]写道:“藏西南,高原上的高山/金丝黄贡菊,艽野、冷凝的庇护/弹性的乳房//雀姆亚青,父山;雀姆雍青,母山/干城章嘉,是远走锡金的子山/蓝天上娇嗔欲滴的雪乳/供晚归的岗巴羊吸吮,娇酣半边雪域银轮”。这首诗篇幅很短,但视野很开阔。在诗人笔下,遥远而神秘的岗巴好像一个人类家庭在自然中的放大,高天流云、晚归的羊群更是给空旷的世界赋予了人间滋味。从这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陈人杰的藏地书写有其特殊的内涵。一方面,诗人依然把人作为诗歌书写的中心,无论是通过石头写孩童和老去的父亲,还是通过山峰写父母、儿子,都没有脱离对人类世界的思考,没有超越红尘;另一方面,对于外表硬邦邦的石头、山峰,诗人见到的不只是它们的本来面貌,而是以柔美的方式去解读它们,发现它们,赋予它们以生命的意义,或者从中获得生命的启示,揭示了高原的另一种面貌。在这种表达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以前的人生阅历、人生思考在他打量青藏高原、感悟人生中所留下的明显印痕,更可以感受到他在青藏高原上获得的新的感悟。二者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感悟方式,也获得了新鲜的诗意。
新鲜感、代入感是陈人杰藏地书写的突出特色之一。对于西藏,他不是过客,也不是世居者,而是一个外来者、新来者,拥有外来者、新来者的新鲜眼光,既避开了世居者的习惯性接受姿态,又不同于过客的表面感受。同时,他拥有在地者的切肤体验,也拥有外来者所具有的他种文化基因,使他不是正面地、毫无选择地接受一切,而是将原生基因与新的体验进行诗意比对,通过投入、怀疑、提升等情感演变轨迹,使自己的诗歌作品具有了别的诗人所难以写出的独特的美,包括感悟之美、思考之美、选择之美、升华之美,等等。
在陈人杰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江南文化底蕴,包括感悟方式、情感方式、话语方式等,渗透在他的藏地书写中,为书写藏地体验带来了一些新的文化和艺术气息,尽可能避开了单纯的宏大、神秘,而是将藏地的神秘和对生命发展、生命价值的思考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取向。需要说明的是,陈人杰作为“外来者”的身份只是相对于藏地而言的,他不是“旁观者”。在观照藏地历史、文化、现实的时候,诗人更多是以一个“新西藏人”的身份,以新鲜的眼光进入一个新鲜的世界,自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新奇而独到的发现。
如果说诗集《回家》主要是立足于现实之家,书写对家的感受,那么诗集《西藏书》《山海间》则更多地书写心灵之家、生命之家,在艺术立足点、精神取向、艺术视野等方面与前期创作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内、向上、向天成为陈人杰藏地诗歌的基本精神取向。
二、在“回望”与“在地”的纠缠中寻找心灵皈依
陈人杰是浙江人,那里有他的生命之根、生命之源,即使到西藏生活、工作,他也不可能忽略对现实中的家乡的关注和书写。相反,他依然回望过去,回望藏地之外的地方。不过,由于藏地经历的加入,这种回望使他进藏前后的作品出现了很大的区别,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以一个西藏人的心态、视野感悟既往的人生和藏地之外的世界。换一个角度说,这种书写是他接受了藏地文化熏陶之后的一种新的尝试,构成了他藏地书写的重要部分。
如果说陈人杰对藏地的书写是以仰望的方式展开的,那里的高天流云、雪山草原都使他获得了新鲜的体验,那么当他吸收了高原的独特文化,站在高原之上打量来时之路,他就不再以仰望的方式回望过去,而是以俯瞰的视角打量一切。一方面,他在现实之中站到了自然世界的最高平台上,回望来路和他乡,只能以俯瞰的方式打量;另一方面,他在接受了藏地文化洗礼之后拥有了更纯净的心态,更开阔的视野,更独特的人生思考,反观漫漫红尘,就拥有了更高的境界。基于此,他到西藏之后书写的故乡、亲人、朋友以及世界,都拥有了别样的形态、色彩。从对同类题材的不同书写中,可以见出诗人在艺术探索上的变化,更是诗人的藏地书写的独特呈现方式,其中蕴含着对藏地文化的发现与接受。
陈人杰的前期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现实中的家乡有关,韩作荣曾有过这样的概括:“这个普通的总被回忆和思念覆盖的地方,尽管老屋坍塌,门板挣脱了被锁的命运,只留下亲人的骨殖被掩埋多年后的安静,却是他精神的家园与心灵的故土,披霜的月亮般尾随着他的足迹,甚至有着体积和疼痛的重量的小村置根于心中,诗人的流浪就是一颗心所承载着的小村在流浪。”[7]诗集《回家》包括“仰望星空” “俯瞰大地”两个部分,前者是对家乡的书写,家乡犹如他的“星空”;后者是对现实人生的打量,涉及现实人生的方方面面,尤其关注社会底层,体现了诗人的悲悯情怀。他在《回家》[8]一诗中写道:“母亲,我心中翻滚着稻芒、瓦片、流萤、星光/这是在异地,在金华空洞的小房子里/夜深了,我的一声无音的呼喊/只有您能听到,并在另一个世界坐起身来/而远在杭州的女儿,我希望她像水滴一样安睡/以美梦为家,不要梦见远方的小城里/一个失落在黑暗中未老先衰的父亲”。母亲去世了,女儿在杭州,诗人在金华,于是对“家”有了一种茫然。故土虽然在他心里,但已经不算他的家;虽然女儿带给他一份亲情的柔软,但现实中的“家”却成为他回不去的地方,“就这样,一座坚硬的城市,因我女儿的呼吸/给我的心带来少许柔软/就像故土,因我记住您的皱纹而愈加沧桑/大地高远,灯火闪烁/而当我说:我想回家/所有的屋顶都突然飞走了”。没有屋顶的家肯定不算家,至少不是完美的家,我们由此读出了诗人内心的迷茫,心灵的流浪。那个时候的陈人杰虽然写出了人世的沧桑,但还没有从现实的沧桑中超脱出来,更多是书写具有现实意味的悲凉。他所写的家乡、故土,也主要是现实意义上的,那样的“家”肯定是一种寄托,但只能算是心灵之家、情感之家,和大多数书写者的情感取向、艺术质地没有太多本质的差别。
到了西藏之后,陈人杰对现实与生命的思考有了很大的变化,视野、境界、情怀都因为新的体验而发生了新变。藏族地区的高山、河流、蓝天、白云以及独特的文化,给他带来了新的人生思考。“家”的意味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现实之家,甚至心灵之家、情感之家,逐渐变成生命之家。叶延滨说,“一个诗人,只有把身体和灵魂扎进这片土地,才能俯下身用心用情体会这里每一个带着温情的生命”[9],“身体” “灵魂”的投入就已经不是曾经的心灵、情感状态,而是更全面、更本质的一种全身心升华。这是一种互动,如果没有雪域高原特殊的地理与文化,陈人杰无法接受独特的洗礼;同样,如果诗人只是一个过客、一个“旁观者”,他也难以接受特殊的地理与文化带给他的深入骨子的洗礼。环境的变迁和诗人自我的提升共同引领了诗人的转型。“这片圣洁的土地也同时滋养着陈人杰的内心世界,给予他叩击诗歌奥妙之门的钥匙,在这片抬头即是漫天星空的大地上,在无数个群山寂寂、流水淙淙的深夜里,一位苦吟诗人审视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以星夜为酒,靠文字取暖,为一棵树喊疼,坚强的内心藏着最柔软的宇宙。”[10]在陈人杰的藏地书写中,诗人和高山、雪域融合在一起,个人的悲喜已经成长为具有普遍意味的生命的悲喜,他所发现的灵魂、生命的依托之处已经超越了曾经的现实中的家,是一种更高远、更本质的生命之所。
陈人杰在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言说:“面对万里芜塘草原上白云与羊群交融的地平线,面对冰雪高原一片片地衣开出的小花,面对西藏神秘、深邃,和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千年巨变,当我跋涉,我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我留在雪域里的那些脚印,是个体生命向辽阔世界的致敬。那些诗,是我和大地、万物建立的联系,是为一个伟大的时代献出的声音。”[11]在高原上建立起和大地、万物的联系之后,诗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逐渐转向了“向辽阔世界的致敬”,这样的视野、胸怀,和他前期的作品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突破,新的超越。
在陈人杰的藏地书写中,长诗《与妻书》[12]能够较好地传达诗人对“家”的重新省思 。远离家人,对家和家人的思念肯定是每个人重要的情感,陈人杰也是。但是,面对雪域高原,面对高天流云,诗人的胸怀是敞亮的,除了现实中的家和家人,还增加了对更多人的关爱,多了一份悲悯的情怀。作为正常的人,他对亲人的思念之浓郁不减当年,“在高处,所得的月光更多/却无一缕送你/请原谅,这白银的皎洁/由风雪炼制,让你承受凋零” “无论如何,风轻云淡/父爱不懂细节/针线在最需要暖的时候/缝了一场雪/补丁,无法弥补的肚兜/无休止地缱绻、悔恨/悲痛的蓝,早晨吁请黄昏宽恕”。无论对妻子,还是对儿子,诗人都怀有一份歉疚,但妻子的话语却带给他鼓励和温暖:“放心,我们的孩子/我照顾好,白云上的孩子/你轻轻擦去忧伤……”在深爱、孤独、纠结的情感中,诗人获得的是支持,是温暖,是对“白云上的孩子”的关爱。更主要的是,诗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对现实、生命、亲情的重新思考:“并非为了挣脱被锁的命运/而是你的嘱托/需要月亮作为偏旁//从此,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舍家进藏,分飞各天涯/残缺之美,维纳斯的断臂留在了布达拉”。这种感觉带给诗人开阔与敞亮,使诗人获得了精神的舒展和生命的重新唤醒:“因为你撕开我的闪电/一片羽毛越飞越高/从此,雪域是碧海的帆/雪花在浪花里浮沉/西去东归,永远在你的航线上/我递给你的清单/像北斗七星,用金勺开销岁月”。艰难的环境因此而拥有了独特的魅力:“远方近在眼前/缺氧被缺失代替/边境线画着同心圆/恍惚中,珠穆朗玛/有一把家的银钥/打开那皎洁、清莹、宁静的欢乐/以及天宇的魂魄”。妻子的关爱、理解给诗人带来了人生的复活、精神的提升,这里的“家”已经超越了现实意义的家,而是灵魂之家、生命之家,是人与世界融合之后而重新获得的一种提升。从精神质地来看,这种诗意的境界是高远的,包容的,超越了物质的拘囿而实现了灵魂的升腾。如果说在陈人杰前期的作品中,现实中的家是他唯一的家,在想念这个家的时候,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苦楚,那么在他的藏地书写中,即使同样远离现实中的家,他还拥有更大的“家”,那是天地万物化为一体的“家”。那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已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生命的思考,“也许你我这朵东海的浪花/只有化身为雪域的羽毛/才能置身绝顶/安顿好肉身的家”[13] 。其实,他安置的不仅仅是 “肉身的家”,更包括精神之家、生命之家,与天地贯通的灵魂之家 。诗人的情感方式、生命感悟所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藏地文化的洗礼,换一个角度看,这种变化所体现的是诗人对藏地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诗人已经从一个 “外来者”转型为一个“新西藏人”。
而《山海间》[14]则在开阔的视野中书写了对历史、现实、生命的深度感悟。《山海间》是一首长诗,题材来自诗人在八宿县叶巴村的驻村经历,背景是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其中的“山”指的是青藏高原的山,“海”是诗人家乡的海,作品串联起曾经与当下、记忆与现实,书写了诗人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 。这是一首和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但诗人并没有拘泥于现实,而是将个人经历、历史沉思和当下现实有机融合,拓展了现实题材作品的深度与厚度。
诗人到西藏,是为了“寻找神性的源头”,而要找到叶巴村,“需要一个被黄叶安排的秋天/也需要贯穿周身的血管/牵动一颗正在撞击的心脏”,暗示了叶巴村的偏远,以及到达那里的艰难,而诗人却在那里发现了博大、开阔,“太平洋、印度洋/一如既往地,接纳/万里高原的馈赠与汹涌/长江,湄公河,羌塘草原的丹心/奔赴不同的海岸。而我来了/万水归宗,又通过/指间风雨,携回洋底渊流/在江河、雪山、一颗泪珠里/放上深邃的眼眸”,高原的水奔赴不同的海洋,遥远的大洋接纳了青藏高原的水,同时又“万水归宗”,通过“我”带回了“洋底渊流”,这不是真正的“水”,而是“深邃的眼眸”,是一个外来者的深情关注。面对 “母系的秘密”,面对不知名的村庄,面对荒野,诗人反思自己的经历与心灵:“一个人的生命线到底有多长/从杭州到西藏/乃至根本无法预知的村落/从碧海到雪域、浪花到雪花/后现代到文明倩影/呼风唤雨到藏地风情/于高冷、孤绝、自省中/一次次拓宽内心的精神疆域”。不同的现实、文化形成强烈对比,“仿佛故乡和他乡/一半在九霄高悬,一半在体内下沉/以我为虹,架起两个天堂之间的对话/神性和苦难,都在用闪电划开诗行”,故乡与他乡、神性与苦难在诗人的生命里纠缠、拥抱,山与海的情结成为陈人杰诗歌的情感寄托、生命皈依,也促使他的生命重新开启。这是生命的再次打开,更是生命的净化与提升。
在藏地,生存都是极为艰难的,对于诗人来说,这是一种超越经验积淀的特殊历练,“——凿冰取水,借灶做饭/牛羊肉冷藏在山洞/巴掌大的猪肉吃半年/门从窗户进出 /分家,分出了撕裂、疼痛/孩子辍学,树叶嚼泡泡糖/人生的第一堂课程/学会了用白石灰抹伤口/牧歌嘹亮,通讯基本靠喊/冠心病、痛风/自由地支配着生前死后”。但是,就是在这种恶劣、艰苦的环境之下,因为视野的拓展、关注对象的调整,诗人发现了自己的卑微,更生长出对生命的尊重、挚爱,而且这不只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生命,而是朝向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存在。“哦,我在无限地靠近/又怕未能真正地抵达/凌乱荒野里的灵魂图谱/交织着一颗牛羊的心”,不过,他更知道自己的使命:
我的卑微是所有人的,葳蕤也是
洁白的哈达,为我端出酥油奶茶
沉甸甸的嘱托里
我是客,又是汉藏之和
唐蕃古道运送家国的重量
铁马冰河穿越血管和史诗
鹰隼不需要履历,而我不能
只有冷漠是贫穷的角落
和日渐荒废的家园
帐篷花开在孩子放学路上
幼儿园,仿佛一颗天上的小心脏
欢笑加上鸟鸣就是黎明
这个时候,诗人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藏地之人,他的“卑微”和“所有人”的“卑微”是一体的;他既是“客”,更是“汉藏之和”,肩负的是“家国的重量”。他发现“只有冷漠是贫穷的角落/和日渐荒废的家园”,但他不能“冷漠”,他渴望的是“欢笑加上鸟鸣”一样的“黎明”。这中间有回顾,有现实,有纠结,有期待,有梦想,多重体验的聚合增加了文字的重量和诗篇的分量,脱离了单纯的个人情感好恶,而是将个体命运和西藏的命运深深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诗具有了广度与厚度,这样的生命具有了包容与悲悯,这样的情怀具有了温度与向度,体现了陈人杰诗歌的新视野、新境界、新高度。
诗人最终发现,“我得到的比给予的更多/每一朵雪花都刻着你的名字/世界屋脊的瓦片/像闪亮的鳞游在幸福里//阒寂之时,方言嗓子里打嗝/黑夜用琴弦虚拟生活/天际线吸纳水源和月光/渡口,倾其一生,守望边界/又是圆月,所有的残缺都已被修补/生命,就是无法计数的爱又回到一”。诗人没有失去家乡,更是和足下的土地水乳交融,在情感中、灵魂里将山与海合为一体了 。“所有的残缺都已被修补”,这是经过了无数煎熬之后的发现与收获,这是视野与境界提升之后的敞亮与开阔。“人在哪儿,根即在哪里”,家乡还是家乡,他乡也成了家乡,诗人成了一个同时拥有山与海的人,一个拥有江南文化与藏地文化的“新人”。
从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并不容易,必须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找到可以融合的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和情感、生命的发展相互搅拌,这种搅拌的目的不是粉碎而是生长,不是坍塌而是上升 。陈人杰在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感纠缠、生命感悟、使命意识从分裂到一体,使他在面对异乡的时候,从一个“外来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实现了“回望”与“在地”的转换。新生的生命元素中既有江南文化的细腻、柔美,也有藏地文化的神秘、粗犷,诗人因此完成了一次人生的转型,其实也是艺术的转型。到了西藏,陈人杰还是陈人杰,但那是再生的陈人杰,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写得更好的陈人杰,是一个既像江南人又像西藏人,但最终是一个崭新复合体的陈人杰。
三、“我” 的隐现与客观化呈现
在诗歌创作中,独特的表达策略往往是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诗歌的表达策略涉及的元素很多,包括取材、语言、结构、篇幅等,每个方面的不同策略都可能影响诗歌的呈现效果和艺术价值。追求突破与创新是诗歌艺术探索的基本目标,也是选择和确定作品表达策略的主要参照。在众多关注青藏高原的写作者中,陈人杰及其作品之所以受到更多关注,与他在艺术呈现上的独特探索有关。
陈人杰的藏地诗篇涉及题材多、范围广,表达方式多样,篇幅长短不一,但诗人都试图在过去的探索基础上获得新的推进。
始终以“我”的视角参与藏地书写是陈人杰诗歌的基本切入方式 。创作主体始终是诗歌情感、手法、取向的主导者,无论是客观化、叙述性、生活化、细节化,还是直抒胸臆,诗歌都无法离开“我”。诗歌的“客观”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选择表达方式的始终是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在过去的一些书写藏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大量感受到“顺应”心态,就是诗人关注藏地历史、文化、现实甚至自然山水,都是顺应着对象去书写,将自己幻化为藏地历史、文化、现实的元素。而在陈人杰的藏地书写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我”的存在,而且是新生的创作主体,是融合了江南文化、藏地文化的“我”。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是一个不断回望、不断反思、不断新生的“我”。这种主体性既体现了诗人对外在世界的尊重,也体现了诗人内心的感悟、思考、选择。《孜珠山》[15]说:“心在高处,路即在高处/天门洞的心象,据说/牛羊循着仪轨转回了人间/一如我不管走多远,总要回来”;《通天河》[16]写道:“西风冷,已无面目可循 /日子更加坚硬,呼应满目苍色/我来了,带着前世的雪花/羽翼般的幻觉无处安放/从雪域下坠的块垒上掠过”……诗人的直接出场,自然是要表达他对观照对象的认知,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人生与现实的思考。还有一些作品没有直接出现“我”,但是对题材的剪裁、其中的思考却是“我”的,比如《萨普冰川》[17]写道:“村庄如星,情歌缥渺/格桑花,如流浪的胎记/高处的波澜翻卷入人神两岸/爱是人间虚拟的音符/又像是天上的事”。面对神山,诗人展开对爱的思考,但他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发现“浓雾紧闭天国的足音/回眸者被面纱锁住”,留给读者自己去感悟。即使在这样的关注神性的作品中,诗人依然将其和人间相勾连,感悟人间事,书写人间情,在超然之中多了一分烟火气息。
有效处理“陌生”与“熟悉”的关系,是陈人杰诗歌沟通神性与人性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藏地题材作品中,神性、超然是很多诗人乐意呈现的主题,不过,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藏地书写题材是陌生的,很多地名、人名、神名以及历史故事都由藏语翻译而来,如果没有较为详细的解释,我们很难理解其中的历史渊源、文化底蕴、生命象征。有些诗人为了表达自己所理解的神秘,表现自己的见识,往往使用很多这类信息,使读者难以进入其中,最终也就难以实现艺术创新的目的。陈人杰的作品尽量不在陌生的语境之中过度炒作陌生事物、陌生形象,而是尽可能在陌生之中发现熟悉,挖掘藏地文化、藏地阅历中具有普遍性的人生思考、生命感悟,尽力从个别中发现和提炼出一般。 但这个“一般”不是简单的哲理,而是具有诗人个性的艺术发现。因此,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很少使用陌生的意象,除了极少数地名之外,诗人尽可能将藏地风光、藏地文化转化为通用表达。这种表达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深,而是揭示生命体验,书写生命价值。
陈人杰说:“能够用简单的意象来表达最细致的情感、最深刻的思想的诗人才是大诗人,最普通的语言在诗歌的万花筒里,有无数种组合方式,但最穿透人心的神奇的美可能只有一种。”[18]我们不能说陈人杰找到的方式就是表达“最穿透人心的神奇的美”的那一种,但他对“简单” “组合”的理解,在其作品中确实随处都有体现。《申扎河》[19]写道:“凝视,直抵心灵的寒冷/一生中最安静的时光/让人生有了清澈的深度”,我们不需要知道具体的申扎河在哪里,只需要感受诗人从中获得的人生思考。《拉萨河》[20]只有四行:“地下的河水贴着俗世/天上的云彩带着信仰/无主见的风和一团团旅人/在这中间吹来荡去”,诗人并没有细致刻画拉萨河的样貌,只是抓住拉萨河提供给诗人的启示,书写了“俗世”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在河水与云彩、俗世与信仰之间“吹来荡去”的状态。这种发现是新鲜的,既有西藏元素,又书写了大多数人的生命状态。在《高原之树》[21]中,诗人并没有找到一棵具体的树,而是提炼了高原之树的共同特征,书写了高原之树的独特与坚毅:“风吹不走它的影子/风找不到它孤独的理由”。诗歌创新的路径很多,与诗人的人生阅历、文化积淀、诗歌观念密切相关,陈人杰试图将人生经验的个别性、个人性转换为诗歌体验的共通性,既体现了艺术个性,又弥合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为藏地书写提供一条有效的艺术探索路径。叶延滨说: “ 精神的多种维度,人生的多个侧面,一一感受着雪域的光照,并折射出诗歌的反光——言语纯净、意象明洁。”[22]这正是陈人杰诗歌的情感、语言、意象特色。他关注的主要不是具体的对象,而是它们在“雪域的光照”之下的艺术 “反光”。
这种尝试的结果很明显。陈人杰写的是独特的山,独特的水,但他只去抓住山水之魂,抓住山水与生命的联系,不在概念上炒作,尽可能消除字面的陌生感。他使用的那些意象和平常的意象没有多少区别,甚至还有江南山水的意蕴,但它们所蕴含的生命意识却是来自诗人在西藏的体验。
消除意象、语言的芜杂、枝蔓,直接切入对象的生命蕴含,化繁为简,是陈人杰处理复杂题材的有效方式之一。陈人杰的藏地书写涉及很多本来具有神奇意蕴的对象,神山、神水、雪原、牛羊、雄鹰、寺庙以及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形式等,每一个话题都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但是,叙述性甚至叙事性的展开主要不是诗歌的任务。诗歌不是讲故事,不是刻画人物,不是叙述历史,而是从对象中发现生命意蕴,寻觅生命启示。在具体的表达中,诗人不先入为主地为观照对象赋予人生感悟、人生哲理,而是让山水、自然自己生长,自己演出,诗人的发现通过独特的笔触慢慢流淌出来。这和叶维廉所说的传统山水诗对山水的尊重有点类似。尊重山水、自然,其实也就是尊重生命自身,是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化、艺术化体现。陈人杰在创作中,有时要自己站出来说话,不过,这些情感性的话语不是他强加上去的,而是和他感受的对象密切相关;在更多的时候,作者是隐藏着的,以观照对象的形态、口吻来呈现自己想要表达的内涵。因此,在陈人杰的藏地作品中,我们基本上见不到那种口号化、理念化诗句,想象的丰富、联想的奇妙为观照对象的自我“演出”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使作品尽可能地避免了直白、单调的弊端。比如《秘境》[23] :
南迦巴瓦朝人间张望
雅鲁藏布为大海洋分泌胆汁
白天鹅带来雪
晚归的豹子让夕阳迟疑
怒江去了云南,一条鱼留在那曲
吼声、深壑、幽暗鱼鳞
都是秘境
扎加藏布,央金笑着,小腹隆起
高原上多汁的人儿
比大地更清楚水系的甜蜜
这首诗所表达的有点类似于叶维廉所说的“天机”,就是现象世界自身具足的特征及其演变规则,如果我们人为地对这些特征、规则进行分类、命名,就会打破“天机”的完整性,使其“分化破碎为片段的单元”[24] 。在这种时候,诗人最有效的表达方式就是尊重自然的特征,采用演出式的呈现,让自然之物自己来呈现自己。叶维廉说:“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25]他所说的就是这种呈现方式。在这首诗中,诗人站在现象世界之外,以开阔的视野打量世界,让诗人所认为的具有诗意的观照对象自己展示自己,由此形成了一个自然的神秘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存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这不是自然主义的呈现,而是蕴含着诗人对世界的认知。诗人是隐身的,也是在场的,选择哪些对象,对象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如何延展,其实都是诗人在操控,都是诗人的人生智慧、艺术机智、语言感觉等在发挥作用。
优秀诗歌文本的构成元素很多,构成方式很复杂,诗人的表达策略是建构诗歌内部元素之间独特关系的关键。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主题,在不同诗人的呈现之中,可以展示出不同的效果。构成诗歌文本的任何一个环节、元素如果没有达到完整安排的效果,诗篇整体都可能失败,至少会存在瑕疵。陈人杰在尊重中国诗歌的抒情性特征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诗歌中的客观化、跳跃性、变形转换等手段,一方面尊重了藏地文化的自在状态,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种超越客体、超然物外的艺术效果,避免了抒情的直白化、空洞化,为现代抒情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结 语
陈人杰的藏地诗歌受到了较多关注,但这并不是说他的诗歌已经达到了完美的水准。只要诗歌还在,只要还有诗人在创作,诗歌艺术探索就永远在路上。事实上,综合打量陈人杰的创作,还有一些方面值得诗人进一步思考、摸索。
总体看,陈人杰的诗歌文本处于一种相对完熟的状态,没有明显的缺陷,但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的探索还缺乏艺术上的冒险意识,追求平淡、谦和而缺乏锋芒,这或许是受到了藏地宗教文化的影响,也和他经历过人生风雨之后的淡定、超脱有关。这不是说他信仰某种宗教,而是说在较为浓郁的宗教氛围的陶冶之下,他的诗歌出现了看待世界的新的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为淡然、超然,现实意味淡薄了许多,但对生命的体验却深入了几分,少了些冲突,少了些烟火气,多了一份旷达。这是一种可以用“成熟”来描述的艺术方式,但在诗歌艺术发展中,某一个阶段的成熟往往是对过去艺术探索成就的综合吸纳,也可能就是一个探索阶段的结束。
陈人杰的诗之所以能够较快地得到诗歌界的认可,是因为具有不同诗歌观念、诗学观念的人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一些熟悉的气息,又有一些陌生的元素,让人觉得新鲜 。对于陈人杰来说,如何完善甚至走出已经形成的感悟方式、表达方式,是他今后的诗歌艺术探索面临的新课题。他需要在展示情感、生命的稳定状态的同时,更多地思考现实生命所面临的冲突、纠结、无奈、茫然等,通过切入某种“撕开”的状态,实现生命的更好的“弥合”,这就需要他在处理个人阅历、人生体验、文化底蕴、生命观念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融合、创造。
一个成熟阶段的结束,是另一个新探索阶段的开始。在诗歌艺术探索中,陈人杰可做的事情还很多。
注释
[1]书写西藏的诗歌是陈人杰到西藏之后的诗歌创作的主体,但他的作品所打量的不只是西藏,还包括其他藏族地区。本文使用“藏地书写”“藏地诗歌”等说法,试图涵盖诗人关于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的诗歌作品,有时也使用“藏族地区”。
[2]沈苇在新疆工作期间创作了大量独特的诗歌、散文,其诗集《在瞬间逗留》1998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1995—1996)。
[3]叶维廉:《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5页。
[4]蒋登科:《超越情怀与纯净之美——试论陈人杰诗歌的西藏书写》,《名作欣赏》2018年第16期。
[5]陈人杰:《冻红的石头》,《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6]陈人杰:《岗巴》,《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页。
[7]韩作荣:《在现实与想象力之间》,陈人杰,《回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2-3页
[8]陈人杰:《回家》,《回家》,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9]叶延滨:《在雪域之巅仰望星空——读陈人杰诗集<山海间>》,《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0月13日。
[10]叶延滨:《在雪域之巅仰望星空——读陈人杰诗集<山海间>》,《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0月13日。
[11]陈人杰:《青春课》, 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1121/c448024- 32570623.html。
[12]陈人杰:《与妻书》,《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5-126页。
[13]陈人杰:《看望牦牛——赠吴雨初》,《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页。
[14]陈人杰:《山海间》,《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4-107页。
[15]陈人杰:《孜珠山》,《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4-55页。
[16]陈人杰:《通天河》,《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5-66页。
[17]陈人杰:《萨普冰川》,《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
[18]《西藏在上,赤子赤心——普布昌居对话陈人杰》,陈人杰,《西藏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后记,第326页。
[19]陈人杰:《申扎河》,《西藏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20]陈人杰:《拉萨河》,《西藏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21]陈人杰:《高原之树》,《西藏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22]叶延滨:《分享伟大事物的光芒》,陈人杰,《西藏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8页。
[23]陈人杰:《秘境》,《山海间》,西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24]叶维廉:《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95页。
[25]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中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9页。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8辑

蒋登科,四川巴中恩阳人,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陈人杰,浙江天台人。西藏文联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协会员。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刊》青年诗人奖、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第四届昌耀诗歌奖、第三届《扬子江诗刊》奖、2021年度中国作家集团·全国报刊联盟优秀作家贡献奖、中国诗歌网2021年度十佳诗集、第五届中国长诗奖、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特别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