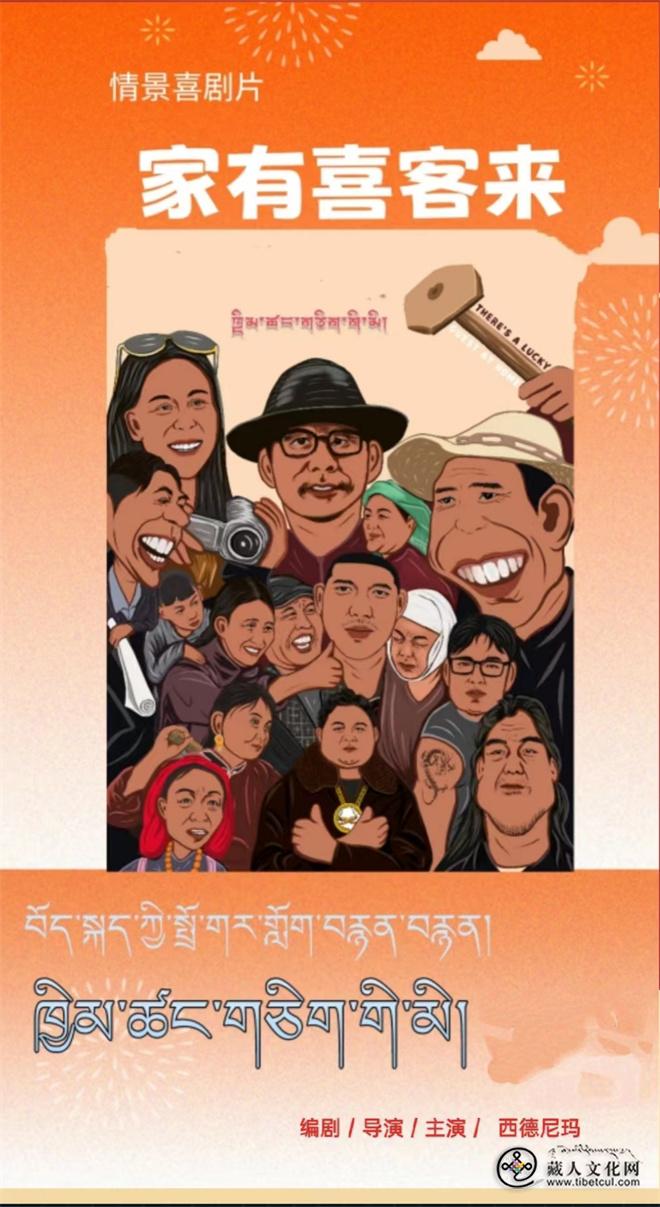гҖҖгҖҖеҜјжј”пјҡиөөй№ҸйҖҚ
гҖҖгҖҖзүҮй•ҝпјҡ90еҲҶй’ҹ
гҖҖгҖҖдё»жј”пјҡеӨҡеёғжқ°гҖҒе®—еҗүгҖҒеҗүеҗүгҖҒеҫ·йқ’еҚ“зҺӣгҖҒжҙӣжЎ‘еҝөжүҺгҖҒжЎ‘зҸ гҖҒж–ҜиҝӘжҺӘ
гҖҖгҖҖж•…дәӢжў—жҰӮпјҡ
гҖҖгҖҖжң¬зүҮеңЁдё–з•ҢжңҖй«ҳеі°зҸ з©Ҷжң—зҺӣеі°е®һжҷҜжӢҚж‘„пјҢеҺҶж—¶4е№ҙгҖӮзҷ»еұұдәәжңүдёҖдёӘж®Ӣй…·зҡ„й«ҳеұұжі•еҲҷпјҡдёҖж—Ұжө·жӢ”и¶…иҝҮ8000зұіпјҢйқўеҜ№еӨұдәӢзҡ„йҳҹеҸӢжҲ–дәІдәәе°ұеҸӘиғҪ“и§Ғжӯ»дёҚж•‘”пјҢз”ұжӯӨдә§з”ҹзҡ„дәәжҖ§зў°ж’һдёҺдјҰзҗҶзҹӣзӣҫеҸ‘дәәж·ұзңҒ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иҘҝи—Ҹзҷ»еұұйҳҹеҫҒжңҚе…Ёдё–з•Ң14еә§8000зұід»ҘдёҠй«ҳеі°зҡ„зҷ»еұұжҙ»еҠЁдёӯпјҢй«ҳеұұж‘„еҪұеёҲд»Ғйқ’иў«еӣ°еңЁдәҶзҸ еі°дёҠзҡ„еҶ°иЈӮзјқдёӯпјҢеҰ»еӯҗеҫ·еҗүе’Ңз”ҹжӯ»е…„ејҹгҖҒзҷ»еұұйҳҹйҳҹй•ҝе·ҙжЎ‘ж— еҘҲж”ҫејғдәҶиҗҘж•‘гҖӮдҪҶдёӢеұұеҗҺпјҢ他们еҚҙйҷ·е…ҘдәҶеҝҸжӮ”дёҺзә з»“д№ӢдёӯпјҢж— жі•йқўеҜ№д»Ғйқ’зҡ„е„ҝеӯҗеІ—зғӯгҖӮ
гҖҖгҖҖеІ—зғӯжҳҜж–°дёҖд»Јзҷ»еұұдәәпјҢдёҖзӣҙеңЁиҝҪжҹҘзҲ¶дәІзҡ„жӯ»еӣ гҖӮеҪ“еҫ—зҹҘзҲ¶дәІзҡ„е°ёдҪ“еңЁзҸ еі°дёҠйҮҚзҺ°зҡ„ж—¶еҖҷпјҢд»–еҶіе®ҡеҶ’йҷ©зҷ»зҸ еі°пјҢдҪҶжҜҚдәІеҫ·еҗүжғіе°ҪдёҖеҲҮеҠһжі•йҳ»жӯўд»–зҷ»еұұгҖӮ
гҖҖгҖҖеІ—зғӯзҡ„еҘіеҸӢеҚ“еҳҺеҚ–жҺүдәҶз”ңиҢ¶йҰҶпјҢдёҺеІ—зғӯдёҖиө·еҸӮдёҺдәҶдёҖж¬Ўе•Ҷдёҡзҷ»еұұгҖӮеңЁзҸ еі°дёҠпјҢ他们еҗҢж ·д№ҹйҒӯйҒҮдәҶй«ҳеұұжі•еҲҷпјҢдёӨйҡҫзҡ„еӨ„еўғеҗҢж ·ж‘ҶеңЁдәҶ他们зҡ„йқўеүҚ……
гҖҖ йҮҮи®ҝиҖ…пјҡиғЎи°ұеҝ пјҢйҰ–йғҪеёҲиҢғеӨ§еӯҰж–ҮеӯҰйҷўеүҜж•ҷжҺҲгҖӮ
еҸ—и®ҝиҖ…пјҡиөөй№ҸйҖҚпјҢз”өеҪұгҖҠеӨ©и„ҠгҖӢеҜјжј”гҖӮ
гҖҖгҖҖиғЎи°ұеҝ пјҡиҜ·дҪ д»Ӣз»ҚдёҖдёӢеҲ¶дҪңгҖҠеӨ©и„ҠгҖӢиҝҷйғЁз”өеҪұзҡ„зјҳиө·гҖӮ
гҖҖгҖҖиөөй№ҸйҖҚпјҡжҲ‘第дёҖж¬ЎеҺ»иҘҝи—ҸжҳҜеңЁдёҠдё–зәӘ90е№ҙд»ЈеҲқпјҢеҪ“ж—¶иҝҳжҳҜдёҖдёӘж–ҮеӯҰйқ’е№ҙпјҢеҜ№жңқжӢңзҡ„ж„ҹи§үеҫҲиҝ·жҒӢгҖӮжҲ‘жңүдёӘжўҰжғіпјҢе°ұжҳҜеҺ»зңӢзҸ еі°гҖӮ1998е№ҙпјҢжҲ‘еңЁеҢ—дә¬з”өи§ҶеҸ°еҒҡеҜјжј”зҡ„ж—¶еҖҷи®ӨиҜҶдәҶдёҖжү№жҗһжһҒйҷҗиҝҗеҠЁзҡ„жңӢеҸӢгҖӮиҝҮдәҶ10е№ҙпјҢ他们еҸҲи®ӨиҜҶдәҶиҘҝи—Ҹзҷ»еұұйҳҹзҡ„жңӢеҸӢпјҢдәҺжҳҜе°ұжғіеңҶжҲ‘们еӨ§е®¶зҡ„дёҖдёӘжўҰпјҢеҺ»зҸ еі°жӢҚдёҖйғЁз”өеҪұгҖӮеңЁдёҺ他们жІҹйҖҡзҡ„иҝҮзЁӢдёӯеҗ¬иҜҙдәҶдёҖдәӣж•…дәӢпјҢе…¶дёӯеҘҘиҝҗзҒ«зӮ¬жүӢеҗүеҗүзҡ„ж•…дәӢеҫҲеҗёеј•жҲ‘гҖӮеҗүеҗүзҡ„дёҲеӨ«еӣ зҷ»еұұиҖҢдәЎпјҢеҗүеҗүдёәеңҶеҘ№дёҲеӨ«зҡ„дёҖдёӘжўҰпјҢиҮӘе·ұеҸҲдёҠдәҶзҸ еі°гҖӮиҝҷжҳҜжҲ‘们жӢҚиҝҷйғЁз”өеҪұзҡ„зјҳиө·гҖӮ
гҖҖгҖҖдҪҶжҳҜеңЁеҲӣдҪң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дј иҜҙдёӯзҡ„й«ҳеұұжі•еҲҷпјҢдёҖдёӢеӯҗеҲәжҝҖеҲ°дәҶжҲ‘гҖӮ他们и°ҲеҲ°пјҢеҰӮжһңжҳҜеңЁжө·жӢ”8000зұід»ҘдёҠпјҢе°ұеҸҜд»Ҙи§Ғжӯ»дёҚж•‘——иҝҷжҳҜзҷ»еұұз•Ңзҡ„дёҖдёӘжі•еҲҷпјҢд№ҹжҳҜжҲ‘жӢҚиҝҷйғЁз”өеҪұзҡ„еҸҰдёҖдёӘзјҳиө·гҖӮеҸҜжҳҜпјҢиҝҷдёӘзү№ж®Ҡжғ…еўғдёӢзҡ„дәәжҖ§дё»йўҳпјҢдёҺзҷ»еұұйҳҹзҡ„иҒҢдёҡеҪўиұЎдёҚжҳҜеҫҲдёҖиҮҙгҖӮеҲ°дәҶиҘҝи—Ҹд»ҘеҗҺпјҢжҲ‘жӣҙеҠ еқҡе®ҡдәҶпјҢеҪұзүҮдё»йўҳе°ұжҳҜжҺўи®ЁиҮӘ然е’Ңдәәзҡ„е…ізі»гҖӮжҲ‘дёҖзӣҙи®ӨдёәпјҢйғҪеёӮйҮҢзҡ„дәәжҳҜиў«ејӮеҢ–дәҶзҡ„гҖӮдёӯеӣҪжҳҜдёҖдёӘзү№еҲ«и®Із©¶еұұж°ҙз”°еӣӯзҡ„еӣҪеәҰпјҢиҮӘеҸӨд»ҘжқҘе°ұжіЁйҮҚиҮӘ然дёҺдәәзҡ„е…ізі»пјҢиҘҝи—ҸжӣҙжҳҜдёҖдёӘејәи°ғеӨ©дәәеҗҲдёҖзҡ„ең°ж–№пјҢиҝҷдәӣйғҪжҝҖеҸ‘жҲ‘жғіеҺ»жӢҚдёҖйғЁз”өеҪұпјҢиЎЁзҺ°еңЁиҝҷз§ҚжһҒиҮҙзҡ„иҮӘ然зҠ¶жҖҒдёӢпјҢдәәе’ҢиҮӘ然зҡ„е…ізі»еҲ°еә•жҳҜд»Җд№Ҳж ·зҡ„гҖӮ
гҖҖгҖҖжҲ‘иҝҳзү№еҲ«жғіжҺўи®Ёзҷ»еұұзҡ„ж„Ҹд№үгҖӮдёӯеӣҪиҮӘ1960е№ҙејҖе§Ӣ第дёҖж¬Ўзҷ»дёҠзҸ еі°пјҢиҘҝи—Ҹзҷ»еұұйҳҹд№ҹжҳҜйӮЈж—¶еҖҷжҲҗз«Ӣзҡ„пјҢеҰӮд»Ҡз®—иө·жқҘжӯЈеҘҪжҳҜ50е‘Ёе№ҙгҖӮжҲ‘жӣҫ问他们пјҢз«ҷеҲ°дё–з•ҢжңҖй«ҳеі°еҲ°еә•жҳҜд»Җд№Ҳж„ҹи§үпјҢжңүдәәеӣһзӯ”иҜҙпјҡ“ж„ҹеҠЁгҖӮе…¶е®һзҷ»еұұе°ұи·ҹеӣһ家дёҖж ·пјҢз«ҷеңЁеұұйЎ¶дёҠе°ұи§үеҫ—иҮӘе·ұе°ұеә”иҜҘз«ҷеңЁйӮЈйҮҢпјҢжҲ–иҖ…и§үеҫ—зҷ»еұұе°ұжҳҜиҮӘе·ұз”ҹжҙ»зҡ„дёҖйғЁеҲҶгҖӮжҲ‘дёҚзҹҘйҒ“еҲ°еә•дёәд»Җд№ҲиҰҒиҝҷд№ҲеҒҡпјҢдҪҶжҳҜдёҚи®©жҲ‘зҷ»еұұжҲ‘дјҡжӯ»жҺүгҖӮ”他们жңҙзҙ зҡ„иҜӯиЁҖж„ҹеҠЁдәҶжҲ‘гҖӮеҪ“жҲ‘们йқўеҜ№иҮӘ然зҡ„ж—¶еҖҷпјҢдјҡж„ҸиҜҶеҲ°дәәзұ»зҡ„зӢӮеҰ„е’Ңжёәе°ҸгҖӮ
гҖҖгҖҖеҸҰеӨ–пјҢжҲ‘зү№еҲ«и®ӨеҗҢиҘҝи—Ҹзҡ„з”ҹжӯ»и§ӮпјҢе°ұжҳҜ“еҗ‘жӯ»иҖҢз”ҹ”гҖӮзҺ°д»ЈдәәжҜҸеӨ©жҙ»зқҖе°ұжҳҜиҖғиҷ‘иҮӘе·ұжҖҺд№ҲиғҪеӨҹеҲ©зӣҠжңҖеӨ§еҢ–пјҢзү©иҙЁдёҠжҖҺд№ҲиғҪеӨҹиҠӮиҠӮж”ҖеҚҮпјҢеҸҜжҳҜиҘҝи—ҸдәәдёҚжҳҜиҝҷж ·зҡ„гҖӮеңЁд»–们зҡ„д»·еҖјдҪ“зі»йҮҢпјҢжӯ»дәЎе№¶дёҚжҳҜз”ҹе‘Ҫзҡ„з»“жқҹпјҢиҖҢжҳҜеҸҰеӨ–дёҖз§Қж„Ҹд№үзҡ„ејҖе§ӢпјҢиҝҷзӮ№еҗёеј•дәҶжҲ‘гҖӮ
гҖҖгҖҖиғЎи°ұеҝ пјҡд»ҺжҠҖжңҜи§’еәҰжқҘиҜҙпјҢдҪ зҡ„з”өеҪұеҫҲе–ңж¬ўз”Ёж·ұз„Ұй•ңеӨҙпјҢ讲究й•ңеӨҙеҶ…йғЁзҡ„еӨҡеұӮж¬Ўж„Ҹд№үдј иҫҫеҸҠе…¶д№Ӣй—ҙзҡ„зӣёдә’е…ізі»гҖӮиҝҷз§ҚиүәжңҜз”өеҪұзү№жңүзҡ„еҪұеғҸйЈҺж јпјҢдёҺдёҖиҲ¬и§Ӯдј—еҜ№гҖҠеӨ©и„ҠгҖӢзү№е®ҡйўҳжқҗзҡ„жңҹеҫ…дјҡдёҚдјҡеҸ‘з”ҹеҶІзӘҒпјҹ
гҖҖгҖҖиөөй№ҸйҖҚпјҡжӢҚзҷ»еұұзүҮжңҖе®№жҳ“еҒҡеҮәзҡ„ж–№жЎҲе°ұжҳҜеғҸеӣҪеӨ–зҡ„и®ёеӨҡз”өеҪұйӮЈж ·пјҢжҜ”еҰӮгҖҠз”ҹжӯ»жһҒйҷҗгҖӢгҖӮдёҖиҲ¬дәәзҗҶи§Јзҷ»еұұйўҳжқҗпјҢеҫҲиҮӘ然ең°дјҡи®Өдёәй•ңеӨҙеә”иҜҘжҳҜеҝ«еҲҮзҡ„пјҢйӮЈз§ҚеҮ з§’й’ҹдёҖжҚўзҡ„еҝ«йҖҹи’ҷеӨӘеҘҮпјҢиҝҷиӮҜе®ҡжҳҜеңЁжҲ‘们жҠҖе·§иғҪеҠӣиҢғеӣҙеҶ…зҡ„гҖӮдҪҶжҳҜжҲ‘йҖүжӢ©еҸҚе…¶йҒ“иҖҢиЎҢд№ӢгҖӮжҲ‘дёҺжҲ‘зҡ„еҲӣдҪңеӣўйҳҹйҳҗиҝ°зҡ„ж—¶еҖҷиҜҙпјҢжҲ‘们иҰҒеҒҡзҡ„дёҚжҳҜдёҖйғЁзҷ»еұұзүҮ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йғЁиө°еҶ…еҝғзҡ„з”өеҪұпјҢжүҖд»ҘиҰҒйҖүжӢ©еҸҰеӨ–дёҖз§ҚжӣҙзәҜеҮҖзҡ„жӢҚж‘„ж–№ејҸгҖӮжҲ‘еҒҸзҲұйӮЈз§ҚеҶ…еңЁзҡ„еј еҠӣпјҢеүҚжҷҜгҖҒеҗҺжҷҜпјҢеҢ…жӢ¬жӣҙиҝңзҡ„ең°ж–№пјҢз”ұеҮ еұӮзҡ„жҲҸеү§з©әй—ҙдә§з”ҹзү№жңүзҡ„еҸҷдәӢгҖӮдҪҶжҳҜе®ғдёҚејәи°ғгҖҒдёҚжёІжҹ“пјҢиҝҷжҳҜжҲ‘еҪ“ж—¶зҡ„е®ҡдҪҚгҖӮеҒҡеҫ—е®ўи§ӮдёҖзӮ№пјҢд№ҹз¬ҰеҗҲжҲ‘еҜ№иҘҝи—Ҹж–ҮеҢ–зҡ„жҖҒеәҰгҖӮжҲ‘и®ӨдёәиҘҝи—Ҹдәәзҡ„з”ҹжҙ»жңүе®ғзҡ„еёёжҖҒпјҢиҝҷз§ҚеёёжҖҒдёҚеә”иҜҘжҳҜдёҖз§ҚеҘҮи§Ӯзҡ„еұ•зӨәгҖӮеҰӮжһңжҳҜзӮ«иҖҖзҡ„жҲ–иҖ…жҳҜеҘҮи§Ӯеұ•зӨәзҡ„пјҢиӮҜе®ҡжңүеӨ–еңЁзҡ„йҹід№җгҖҒе……ж»ЎдәҶиҘҝи—Ҹзү№зӮ№зҡ„и„ёеәһпјҢжңүе”җеҚЎгҖҒи—ҸзҚ’пјҢдҪҶжҲ‘йғҪж”ҫејғдәҶгҖӮеӣ дёәжҲ‘и§үеҫ—еӨ§еӨҡж•°дәәдјҡйӮЈд№ҲеҒҡпјҢжҲ‘жғіеҒҡеҫ—зӢ¬зү№пјҢжҲ–иҖ…иҜҙпјҢжҲ‘жғіеҒҡеҫ—жӣҙдәәж–ҮдёҖзӮ№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жҲ‘йҖүжӢ©зҡ„жҳҜе°ҪйҮҸиҖғиҷ‘еҲ°й•ҝй•ңеӨҙпјҢжҲ–иҖ…иҲ’еұ•дёҖзӮ№пјҢеҲ«йӮЈд№ҲеҢ ж°”пјҢйӮЈд№Ҳдё“жіЁдәҺзӮ«иҖҖиҝҷдәӣ“ејӮеҹҹйЈҺжғ…”гҖӮеҪ“然иҝҷз§Қе®ҡдҪҚе°ұдјҡеҪұе“ҚеҲ°е®ғжңҖеҗҺзҡ„е‘ҲзҺ°гҖӮи§Ӯдј—дјҡеҸ‘зҺ°пјҢеңЁз”өеҪұйҮҢйқўпјҢжҲ‘жһҒеҠӣжҠҠдёҺзҷ»еұұзӣёе…ізҡ„й•ңеӨҙжҺ§еҲ¶еңЁдёүеҲҶд№ӢдёҖзҜҮе№…д»ҘеҶ…гҖӮ
гҖҖгҖҖиғЎи°ұеҝ пјҡз”өеҪұзңӢиө·жқҘдјјд№ҺеҒҡдәҶдёҚе°‘ж”№еҠЁгҖӮ
гҖҖгҖҖиөөй№ҸйҖҚпјҡеҜ№пјҢжңүеҮ ж¬ЎеӨ§и°ғж•ҙпјҢжңҖеҗҺе‘ҲзҺ°зҡ„еҮ д№ҺдёҺеҺҹе§Ӣеү§жң¬е®Ңе…ЁдёҚеҗҢгҖӮиҝҷе…¶дёӯзҡ„еӣ зҙ еҫҲеӨҚжқӮпјҢеҪ“然иҝҷд№ҹжҳҜжҲ‘们е№ҙиҪ»еҜјжј”зҡ„ж— еҘҲпјҢжҲ‘жғіиЎЁиҫҫзҡ„жІЎжңүе®Ңе…ЁиЎЁиҫҫеҮәжқҘгҖӮ
гҖҖгҖҖиғЎи°ұеҝ пјҡдёәд»Җд№ҲжІЎжңүз”Ёи—ҸиҜӯеҜ№зҷҪпјҹ
гҖҖгҖҖиөөй№ҸйҖҚпјҡеҪ“ж—¶йҖҒе®Ўж—¶жҳҜжҜҚиҜӯеҜ№зҷҪпјҢдҪҶжҳҜеҗҺжқҘеӣ еӨҡж–№еҺҹеӣ ж”№з”ЁдәҶжҷ®йҖҡиҜқзүҲгҖӮжҲ‘们д№ҹжҳҜеёҢжңӣеҪұзүҮиғҪе…·еӨҮжӣҙжңүеҲ©зҡ„еҸ‘иЎҢе’Ңж”ҫжҳ жқЎд»¶гҖӮ
гҖҖгҖҖиғЎи°ұеҝ пјҡиҝҷдёӘз”өеҪұзҡ„жҠ•иө„еә”иҜҘдёҚе°ҸпјҢжј”е‘ҳйғҪжҳҜдёҖдәӣи—Ҹж—Ҹи‘—еҗҚжј”е‘ҳгҖӮ
гҖҖгҖҖиөөй№ҸйҖҚпјҡеҜ№пјҢжҲ‘зҡ„иҝҗж°”иҝҳдёҚй”ҷгҖӮеҪ“ж—¶ж•ҙдёӘиҘҝи—Ҹзҷ»еұұйҳҹйғҪеҠЁе‘ҳиө·жқҘдәҶпјҢеӣ дёәеҫҲеӨҡй•ңеӨҙеҝ…йЎ»еңЁзҷ»еұұйҳҹжӢҚж‘„гҖӮиҝҳжңүиҘҝи—ҸиҜқеү§еӣўпјҢдёәдәҶжҲ‘们зҡ„жӢҚж‘„пјҢ他们жҠҠеҫҲеӨҡдёӢд№Ўжј”еҮәзҡ„д»»еҠЎйғҪеҒҡдәҶи°ғж•ҙгҖӮиҝҳжңүжӢүиҗЁзҡ„дёҖдёӘзҷ»еұұеӯҰж ЎгҖҒзҸ з©Ҷжң—зҺӣеі°еӨ§жң¬иҗҘзӯүзӯүпјҢеҠЁйқҷиҝҳжҳҜеҫҲеӨ§зҡ„гҖӮ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иҝҷз§ҚйўҳжқҗеҘҪеғҸжҳҜеҗғеҠӣдёҚи®ЁеҘҪпјҢеӨ§е®¶еҸҜиғҪе–ңж¬ўе•Ҷдёҡе–ңеү§пјҢе–ңж¬ўйӮЈз§ҚеӨ§зүҮгҖҒдҫ зүҮпјҢзңҹжӯЈжңүж–ҮеҢ–жҖқиҖғзҡ„з”өеҪұпјҢеҸ—дј—зҫӨиҝҳжІЎжңүе®Ңе…Ёеҹ№е…»иө·жқҘгҖӮжҲ‘и§үеҫ—жҲ‘们жӢҚеҫ—иҝҳжҳҜжҜ”иҫғзәҜзІ№зҡ„пјҢдҪҶжҳҜи§Ӯдј—дёҚдјҡеӣ дёәдҪ зәҜзІ№е°ұд№°иҙҰгҖӮдё»жөҒи§Ӯдј—еҸӘеңЁд№ҺеҘҪзҺ©дёҚеҘҪзҺ©пјҢжҲ–иҖ…жңүжІЎжңү笑пјҢжңүжІЎжңүе“ӯгҖӮеғҸжҲ‘们иҝҷз§ҚдёҚжғіи®©дҪ е“ӯпјҢд№ҹдёҚжғіи®©дҪ 笑пјҢи®©дҪ жғізӮ№дәӢзҡ„з”өеҪұпјҢи§Ӯдј—е°ұеҸҜиғҪдёҚзҲұзңӢгҖӮ
гҖҖгҖҖиғЎи°ұеҝ пјҡеңЁдә§дёҡеҢ–зҡ„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з”өеҪұйҮҚи§Ҷж¶Ҳиҙ№пјҢиҘҝи—Ҹйўҳжқҗз”өеҪұжҳҜеҗҰе…·еӨҮеӨ©з„¶зҡ„“еҸҜзңӢжҖ§”пјҹ
гҖҖгҖҖиөөй№ҸйҖҚпјҡжҲ‘жң¬з§‘еңЁдёҠжө·жҲҸеү§еӯҰйҷўеӯҰзҡ„жҳҜж–ҮеӯҰпјҢеҪ“жҲ‘дёҠдәҶз”өеҪұеӯҰйҷўеҜјжј”зі»з ”з©¶з”ҹд»ҘеҗҺпјҢжіЁж„ҸеҲ°еҜјжј”зі»зҡ„зјәйҷ·жҳҜиҝҮеҲҶиҝ·жҒӢй•ңеӨҙпјҢйҮҚи§ҶжҠҖжңҜдёҠзҡ„ж•ҷиӮІпјҢзјәе°‘дәәж–Үзҡ„ж¶өе…»гҖӮжҲ‘дёҚеӨӘиөһеҗҢе”ҜжҠҖжңҜи®әгҖӮжҠҠз”өеҪұеҒҡеҫ—еҫҲзӮ«гҖҒеҫҲжјӮдә®е№¶дёҚйҡҫпјҢйӮЈжҳҜжҠҖе·§иҢғеӣҙеҶ…зҡ„дәӢпјҢеҸӘиҰҒж‘„еҪұеёҲжҳҺзҷҪпјҢеүӘиҫ‘жҮӮпјҢеҫҲе®№жҳ“еҒҡеҲ°гҖӮжүҖд»ҘжҲ‘жғіпјҢиғҪдёҚиғҪеңЁж–ҮеӯҰе’Ңз”өеҪұдёӯй—ҙжүҫеҲ°дёҖз§ҚзҠ¶жҖҒпјҹжҲ‘жҳҜжҜ”иҫғжҺЁеҙҮж–Үеӯ—зҡ„пјҢжҲ‘и§үеҫ—ж–Үеӯ—иЎЁиҫҫжҳҜй«ҳзә§зҡ„иүәжңҜпјҢеӣ дёәе®ғдёҚе…·еғҸпјҢиғҪз»ҷдәәеҫҲеӨҡз©әй—ҙпјҢжңүдә’еҠЁгҖӮжүҖд»ҘжҲ‘еңЁжҖқиҖғпјҢжҖҺд№ҲиғҪеӨҹеңЁдёӢдёҖж¬ЎеҒҡзүҮеӯҗж—¶е…јйЎҫдёҖдёӢгҖӮ
гҖҖгҖҖиғЎи°ұеҝ пјҡд»ҘеҗҺиҝҳдјҡеҺ»иҘҝи—ҸжӢҚз”өеҪұеҗ—пјҹ
гҖҖгҖҖиөөй№ҸйҖҚпјҡжҲ‘дёҖе®ҡиҝҳдјҡеҺ»иҘҝи—ҸпјҢиҝҳдјҡеҺ»жӢҚгҖӮжҲ‘зҡ„жғіжі•жҳҜеңЁжҲ‘жңүдёҖе®ҡзҡ„еҪұе“ҚеҠӣд»ҘеҗҺпјҢеҒҡдёҖдёӘжӣҙзәҜзІ№зҡ„е…ідәҺиҘҝи—Ҹж–ҮеҢ–зҡ„еҪұзүҮгҖӮжҲ‘еҜ№еӨҸе°”е·ҙдәәзү№еҲ«ж„ҹе…ҙи¶ЈпјҢе°ұжҳҜиҝҷзҫӨдәәеғҸзүҰзүӣдёҖж ·пјҢжҠҠзҷ»еұұиҖ…йҖҒдёҠеұұпјҢ他们жҳҜжІЎжңүиў«дәәи®°дҪҸзҡ„дёҖзҫӨдәә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