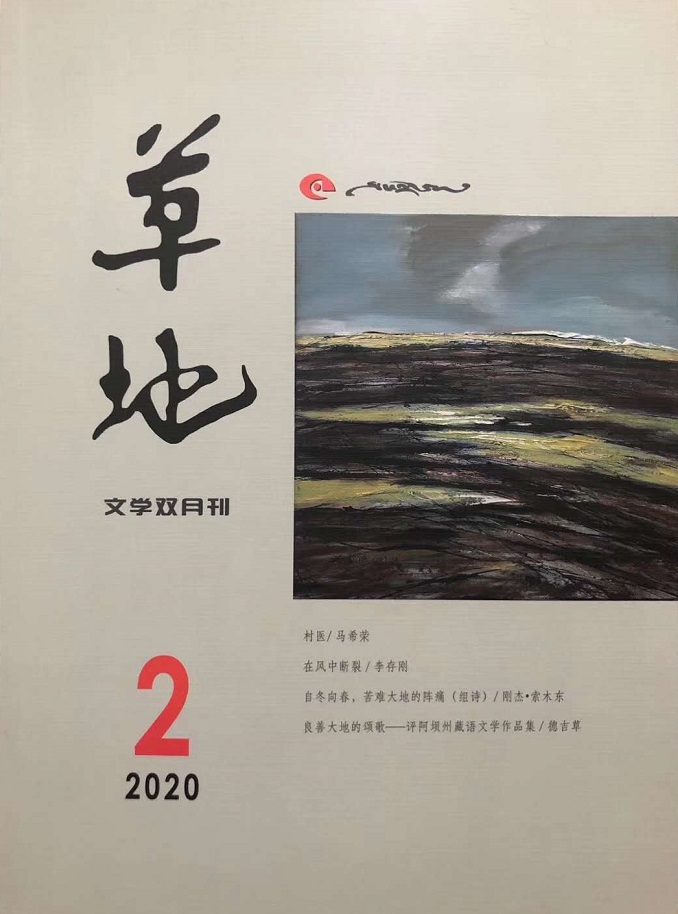
小雪
有冰凌挂上残枝,有雪片覆于败叶
在太阳尚未升起之前,整个北方
冬天,就显得如此落拓
更大的雪,在这座临水的城市
始终没能遇到。这足以使得
宽窄不一的巷道,暧昧不清的灯火
甚至,零落这个世界的尘埃
都能各安其命
而我是有多久没有看到莽原了呢?
积雪覆压的莽原,了无边际的莽原
所有的山川河流,都卸下了
封疆拓土的桎梏
又一片雪落入纸上,这些年
伏案太久,颈肩僵硬
无法低首,不能回头
大雪
靠近风花,或者雪月,总能
把一些句子描得完美。靠近泥土
雪,总是化得很慢。靠近黑色的路面
我们都得坚硬地走下去。靠近那些
随处啄食的麻雀,一掠而起的斑鸠
还有,盘旋于记忆之外的鹰隼
在人间,尚能获得片刻安宁
又一片雪,从枝头脱落
又一条生命,在严寒中走失
从积雪覆压的山头下来,我的兄弟
只能互道珍重,隔着遥远的长空
甚至忘却,亲人的祭日,或者生辰
——挂满霓虹的树,站在街头
张灯结彩的日子,又扑面而来
冬至
阳光透过冬日的缝隙
就有长寿的花迎风盛开
沿黄河走去,那么多的沉默
在季节的尽头,波光粼粼
“一九一阳生。”老人们都说
走完四时,再厚的冰雪都会渐次消融
既然,所有的希望都许给了未来
所有的过往,就只能留给
生死轮回
“云蒸霞蔚又是什么意思呢?”
少年啊!天空越来越明亮了
我却依旧无法,带你重返故园
重返那些亲人们都健在的美好晨间
古老的藏地,一盏酥油灯里
端坐着六百年前的甘丹赤巴
我栖身的这座城市,火树和银花
已提前抵达,下一个春天
小寒
有候鸟栖于河畔,不知其名
有飞雪漫卷北方,不知其名
有病疫和炮火轻取的生命,亦不知其名
地铁在地底下运行,这座临水的城市
据说有一段路程,必须要在河底通行
如此,就能窥见故乡,窥见流水和沙砾
窥见隐晦的历史,不便在风中传递
无处不在的风,不知寂灭的风
果真还能吹动那片慈悲吗?
这些年,远离高原,步履沉重
即便循着一盏灯火,业已不能
找回那段轻盈的人生……
“雁北乡。鹊始巢。雉始鸲。”
所有的吉象都在指向梦中家园
所有的面容,都在朝着数九寒天
这一场雪,就愈发显得
空空荡荡
大寒
千里岷山大雪覆压,天地又回到了
混沌初开的模样。沿洮水北上
你会看到,成群的牛羊在原野上踟蹰
啃食着大地最后的口粮。你会看到
冰河解冻,低头饮水的老马
长长的鬃毛垂下第一缕暮色
你会看到,黑色的鹰隼游于天际
苍穹变得愈发空旷。莫名的忧伤
还是会伴随着我们,靠近梦中家园
“大寒日,斗指丑。——
鸡乳;征鸟厉疾;水泽腹坚。”
所有的吉象,都在指向年关
美好的祝语正被孩子们记住
又一片雪,悄然落入
寂静的村庄
立春
站在窗前,站在因为一场疫情
而变得分外宁静的夜晚
站在那么多的担忧、无奈和感动里
只能这么看着,戴着王冠的病毒
肆虐着众生皆苦的大地
只能这么看着,母亲的河流
依旧沉默,迟缓地向东方蠕动
一盏盏清冷的街灯下
又该如何写下
人世温润……
立春!东风解冻
蜇虫始振。鱼陟负冰
——再厚的冰雪
都会,渐次消融
雨水
大风尚未停歇。疾呼者
高亢的痛感,正在快速退去
病毒仍旧在大地上肆虐
等待狂欢的大门,却已半开半掩
那么多的人涌上街头
又是为了什么?!
如此容易忘却的人世间
似乎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黄钟大吕
斗指壬。天一生水。春始属木。
今夜,果真会有甘霖自天而降吗?!
刚刚学会沉默的那个人,仔细擦拭着
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和远逝的生命
用心写下,“般若”二字
惊蛰
阳光逐渐温暖,人们开始走动
背阴处的积雪也在慢慢融化
已经有着急的花朵,把手伸到窗外
万物出乎震,震为雷——
被病毒窒息了的那些人,却只能
把霹雳留给延口残喘的亲友
我们的生活浸泡在消毒水中
逐渐苍白,无力挣扎
蛰虫初醒的午后
我的孩子,又该如何给你解释
这个支离破碎的春天……
春分
白色的海螺向右旋转
据说就能,止战,弘法
吹响吉祥圆满的大安谧
这个春天,一场又一场大火
吞噬着青草初生的山冈
纵使有再多的鲜花和祈祷
我一样无法,坦然面对
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告别
北方的天空一贫如洗
植在城市表皮的那些花木
在春雨里,继续绽放
乍暖还寒的美意——
这些年远离泥土,稼穑难成
纵使再给我一双黑色的耳朵
又能如何,用心聆听
大地深处
真实的回响
清明
移植的花木,已经在
拥堵的城里开花了
编制的谎言,早已
让我们如沐春风
溯河而上,到高原
才能看到,所有的河流
尚未解冻的源头
到高原,我不得不
继续披上,那件
御寒的衣服
在北方,纵使有
再多的人,聚拢地头
可苍茫大地,依旧
四野荒芜——
凭什么,还要让我继续说出
春天,早已来到?!
原刊于《草地》2020年2期

刚杰·索木东,藏族,又名来鑫华,甘南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