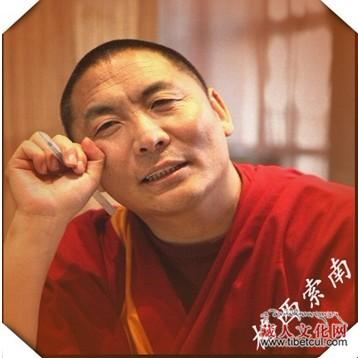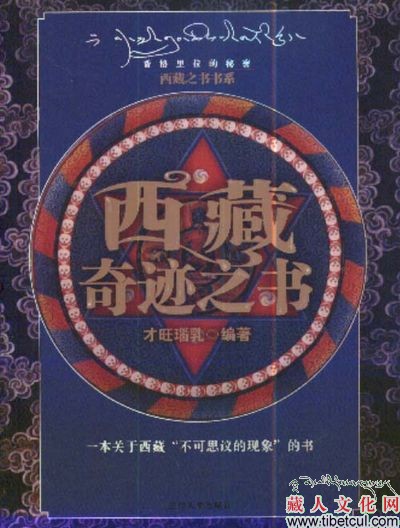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Қ—дә¬гҖҒдә”еҸ°еұұеҸҠе…¶дёҺжҳҺжҲҗзҘ–е…ізі»еҸІе®һиҖғиҝ°
гҖҖгҖҖпј»еҶ…е®№ж‘ҳиҰҒпјҪжҳҺжҲҗзҘ–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пјҲ1414е№ҙпјүпјҢе®—е–Җе·ҙеӨ§ејҹеӯҗйҮҠиҝҰиҖ¶еҚҸеә”иҜҸд»ЈеёҲе…ҘжңқгҖӮйҮҠиҝҰиҖ¶еҚҸдәҺиҜҘе№ҙжҳҘеӨ©е…ҲжҠөиҫҫдә”еҸ°еұұпјҢй©»дә”еҸ°еұұ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еҗҺдәҺ12жңҲеҘүиҜҸиөҙеҚ—дә¬жңқи§җж°ёд№җзҡҮеёқгҖӮжҳҺжҲҗзҘ–еҫ…д№Ӣд»Ҙж®ҠзӨјпјҢж••йҮҠиҝҰиҖ¶еҚҸй©»й”ЎеҚ—дә¬иғҪд»ҒеҜәгҖӮеңЁеҚ—дә¬жңҹй—ҙ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жӣҫеңЁе®«е»·еҶ…еӨ–дёҫиЎҢзӣӣеӨ§дҪӣж•ҷжі•дәӢжҙ»еҠЁпјҢ并дёәжҳҺжҲҗзҘ–ж–Ҫй•ҝеҜҝзҒҢйЎ¶еҜҶжі•гҖӮ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пјҲ1415е№ҙпјүпјҢжҳҺжҲҗзҘ–ж••е°ҒйҮҠиҝҰиҖ¶еҚҸдёәвҖңеҰҷи§үеңҶйҖҡж…§ж…Ҳжҷ®еә”иҫ…еӣҪжҳҫж•ҷзҒҢйЎ¶ејҳе–„иҘҝеӨ©дҪӣеӯҗеӨ§еӣҪеёҲвҖқе°ҒеҸ·гҖӮе…¶еҗҺдёҚд№…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зҰ»ејҖеҚ—дә¬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дј жі•пјҢд»Қй©»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ж°ёд№җеҚҒдёүе№ҙпјҲ1416е№ҙпјү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д»Һдә”еҸ°еұұиҝ”еҪ’д№ҢжҖқи—ҸгҖӮеңЁ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ұ…з•ҷдә”еҸ°еұұжңҹй—ҙпјҢжҳҺжҲҗзҘ–еӨҡж¬ЎйҒЈдҪҝиҮҙд№Ұ并иөҗиө зӨјзү©гҖӮе…ідәҺиҝҷж–№йқўеҶ…е®№еӣ еҸІд№ҰйІңжңүи®°иҪҪпјҢдёҖеҗ‘зјәе°‘з ”з©¶гҖӮ笔иҖ…еңЁе№ҝжіӣж·ұе…ҘиЈ’йӣҶи—Ҹжұүж–ҮзҢ®иө„ж–ҷеҹәзЎҖдёҠпјҢжӢҹжҗһжё…жҘҡйҮҠиҝҰиҖ¶еҚҸ第дёҖж¬Ўе…Ҙжңқж—¶еңЁеҚ—дә¬еҸҠдә”еҸ°еұұдёӨең°дј ж•ҷжҙ»еҠЁзҡ„еҹәжң¬жғ…еҶөпјҢ并д»ҘиҖғиҝ°жҳҺжҲҗзҘ–дёҺйҮҠиҝҰиҖ¶еҚҸд№Ӣй—ҙзҡ„дәӨеҫҖе…ізі»пјҢд»ҺиҖҢдёәиҝӣдёҖжӯҘи®ӨиҜҶгҖҒзҗҶи§ЈжҳҺжҲҗзҘ–зЎ®з«Ӣ并е®Ңе–„еӨҡе°Ғдј—е»әзҡ„жІ»и—Ҹж”ҝзӯ–жҸҗдҫӣзЎ®еҮҝеҸҜдҝЎзҡ„и®әжҚ®гҖӮ
гҖҖгҖҖпј»е…ій”®иҜҚпјҪжҳҺжҲҗзҘ–пјӣйҮҠиҝҰиҖ¶еҚҸпјӣеҚ—дә¬пјӣиғҪд»ҒеҜәпјӣдә”еҸ°еұұпјӣеӨ§жҳҫйҖҡеҜә
гҖҖгҖҖпј»дёӯеӣҪеӣҫд№ҰеҲҶзұ»еҸ·пјҪK81пј»ж–ҮзҢ®ж ҮиҜҶз ҒпјҪAпј»ж–Үз« зј–еҸ·пјҪ1000-0003пјҲ2004пјүпјҚ03пјҚ099пјҚ08
гҖҖгҖҖдёҖгҖҒжҳҺжҲҗзҘ–дёҺи—Ҹдј дҪӣж•ҷ
гҖҖгҖҖиҮӘдҪӣж•ҷдј е…ҘдёӯеӣҪд»ҘжқҘпјҢе…¶еңЁдёӯеӣҪзҡ„е…ҙиЎ°дёҖзӣҙдёҺз»ҹжІ»иҖ…жүҖеҘүиЎҢзҡ„дҪӣж•ҷж”ҝзӯ–жңүеҫҲеӨ§е…ізі»гҖӮиҜҡеҰӮгҖҠе…ғеҸІгҖӢжүҖиЁҖпјҡвҖңйҮҠгҖҒиҖҒд№Ӣж•ҷпјҢиЎҢд№ҺдёӯеӣҪд№ҹеҚғж•°зҷҫе№ҙпјҢиҖҢе…¶зӣӣиЎ°пјҢжҜҸзі»д№Һж—¶еҗӣд№ӢеҘҪжҒ¶вҖқгҖӮв‘
гҖҖгҖҖжҳҺжңқзҡ„е»әз«ӢиҖ…жңұе…ғз’Ӣз”ұдәҺе…¶зү№еҲ«зҡ„иә«дё–пјҢдёҺдҪӣж•ҷжңүзқҖеүІдёҚж–ӯзҡ„жғ…ж„«гҖӮж•ҙдёӘжҙӘжӯҰе№ҙй—ҙпјҢжҳҺеӨӘзҘ–ж—¶ж—¶дёҚеҝҳеҸ‘жҢҘдҪӣж•ҷвҖңйҳҙзҝҠзҺӢеәҰвҖқпјҢвҖңжҡ—зҗҶзҺӢзәІвҖқзҡ„дҪңз”ЁпјҢйҮҮеҸ–з§Қз§ҚжҺӘж–ҪдҝқжҠӨ并еҖЎе…ҙдҪӣж•ҷгҖӮиҜёеҰӮжҙӘжӯҰеҲқжңҹиҮідёӯжңҹпјҢжҳҺеӨӘзҘ–еӨ§йҮҸеәҰеғ§пјҢ并з»ҸеёёдёҫеҠһеҗ„з§ҚдҪӣж•ҷжі•дјҡпјӣиҷҪеӣҪдәӢз№ҒеҶ—пјҢдҪҶд»–д»Қ然з»ҸеёёеҸ¬еғ§дәәе…Ҙе®«пјҢдёҺдҪӣж•ҷй«ҳеғ§и®Із»Ҹи®әйҒ“пјҢиөӢиҜ—е”ұе’ҢпјҢдјҳе®№зӨјйҒҮпјҢеҺҡдәҲиөҸиөҗпјӣеңЁйғҪеҹҺеҚ—дә¬еӨ§е…ҙеңҹжңЁпјҢж–°е»әгҖҒдҝ®еӨҚдҪӣж•ҷеҜәйҷўпјҢ并йўҒеёғи®ёеӨҡдҝқжҠӨеҜәйҷўеҸҠеҜәйҷўжүҖеұһеңҹең°иҙўдә§зҡ„жі•д»ӨгҖӮеҪ“然пјҢеҗҺжқҘдёәйҳІжӯўдҪӣж•ҷжіӣж»Ҙд№ӢеҠҝпјҢжҳҺеӨӘзҘ–д№ҹжӣҫе»әз«ӢеәҰaеҲ¶еәҰпјҢеҜ№еғ§дәәеҮә家дёҘж јз®ҖйҖүпјҢеҜ№еҒҮеҶ’зҠҜжҲ’иҖ…дёҘжғ©дёҚиҙ·гҖӮ
гҖҖгҖҖз”ұдәҺжңҖй«ҳз»ҹжІ»иҖ…зҡ„еҖЎеҜјпјҢеҙҮдҪӣд№ӢйЈҺжө“еҺҡпјҢиҮіжҳҺжҲҗзҘ–ж°ёд№җж—¶жңҹпјҢжҜ”д№ӢеүҚжңқпјҢжӣҙжҳҜжңүиҝҮд№Ӣж— дёҚеҸҠгҖӮжҳҺжҲҗзҘ–дёҺеғ§дәәйҒ“иЎҚиҝҮд»Һз”ҡеҜҶпјҢй•ҝжңҹзҡ„иҖіжҝЎзӣ®жҹ“пјҢжңүдёҖе®ҡзҡ„дҪӣеӯҰеҹәзЎҖпјҢд№ҹдәІиҮӘз ”з©¶зј–ж’°дҪӣе…ёи‘—дҪңпјҢеңЁж°ёд№җе№ҙй—ҙеҲ»йҖ жұүж–ҮеӨ§и—Ҹз»ҸгҖҠеҚ—и—ҸгҖӢгҖҒгҖҠеҢ—и—ҸгҖӢгҖӮв‘ЎдҪҶжҳҺжҲҗзҘ–жңұжЈЈжңҖеҙҮе°ҡзҡ„иҝҳжҳҜи—Ҹдј дҪӣж•ҷпјҢд»–еҜ№и—Ҹдј дҪӣж•ҷй«ҳеғ§зҡ„еҙҮ敬еҮ д№ҺеҲ°дәҶж— д»ҘеӨҚеҠ зҡ„зЁӢеәҰгҖӮд»–иҝҺиҜ·еҷ¶зҺӣе·ҙдә”дё–еҫ—银еҚҸе·ҙпјҢ并е°Ғд№ӢдёәвҖңеӨ§е®қжі•зҺӢвҖқпјҢ并敕е‘Ҫе…¶еңЁеҚ—дә¬зҒөи°·е»әеҜәжҷ®еәҰеӨ§ж–ӢпјҢдёәжҳҺеӨӘзҘ–еҸҠ马зҡҮеҗҺиҚҗзҰҸгҖӮе…¶еҗҺпјҢеҸҲе‘Ҫеҷ¶зҺӣе·ҙеӨ§е®қжі•зҺӢиөҙдә”еҸ°еұұе»әеӨ§ж–ӢпјҢеҶҚдёәеӨ§иЎҢзҡҮеёқдёҺзҡҮеҗҺиҚҗзҰҸ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жҳҺжҲҗзҘ–дёәе…¶еҰғеҫҗж°ҸиҝҪиҚҗеҶҘзҰҸиҖҢйҒ—дҪҝиҘҝи—ҸпјҢжұӮи—Ҹж–ҮеӨ§и—Ҹз»ҸпјҢ并дәҺж°ёд№җе…«е№ҙпјҲ1410е№ҙпјүеңЁи”Ўе·ҙгҖҠз”ҳзҸ е°”гҖӢжүӢжҠ„жң¬зҡ„еҹәзЎҖдёҠзј–зәӮгҖҠи—Ҹж–ҮеӨ§и—Ҹз»ҸгҖӢпјҢжҖ»зј–зәӮдәәеҚіжҳҜдә”дё–еҷ¶зҺӣе·ҙжҙ»дҪӣгҖӮж°ёд№җзүҲгҖҠи—Ҹж–ҮеӨ§и—Ҹз»ҸгҖӢдёәзәўиүІжңұз ӮзүҲпјҢжҳҜгҖҠи—Ҹж–ҮеӨ§и—Ҹз»ҸгҖӢдёӯйҮҮз”Ёйӣ•зүҲеҚ°еҲ·жңҜеҚ°йҖ зҡ„第дёҖдёӘзүҲжң¬гҖӮиҜҘзүҲгҖҠз”ҳзҸ е°”гҖӢе…ұ108еёҷпјҢжҜҸдёҖеёҷйғҪжңүжҳҺжҲҗзҘ–жүҖдҪңгҖҠеӨ§жҳҺзҡҮеёқеҫЎеҲ¶и—Ҹз»ҸиөһгҖӢе’ҢгҖҠеҫЎеҲ¶еҗҺеәҸгҖӢгҖӮв‘ўеә”иҜҘиҜҙиҝҷжҳҜдёҖйЎ№дәҶдёҚиө·зҡ„ж–ҮеҢ–дәӢдёҡпјҢе®ғеҜ№дәҺи—Ҹжұүж–ҮеҢ–дәӨжөҒд№ғиҮіз»ҙжҠӨзҘ–еӣҪз»ҹдёҖдёҺж°‘ж—Ҹеӣўз»“жңүзқҖйҮҚеӨ§дҪңз”Ёе’Ңж·ұиҝңж„Ҹд№үгҖӮжӯӨеҗҺпјҢдәҺж°ёд№җеҚҒдёҖе№ҙпјҲ1413е№ҙпјүпјҢжҳҺжҲҗзҘ–еҸҲ延иҜ·иҗЁиҝҰжҙҫй«ҳеғ§иҙЎеҷ¶жүҺиҘҝпјҲгҖҠжҳҺеҸІгҖӢдҪңжҳҶжіҪжҖқе·ҙпјүпјҢ并е°Ғд№ӢдёәвҖңеӨ§д№ҳжі•зҺӢ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йҮҠиҝҰиҖ¶еҚҸжҳҜжҳҺжҲҗзҘ–еҸ¬иҜ·зҡ„第дёүдҪҚи—Ҹдј дҪӣж•ҷй«ҳеғ§пјҢд»–дәҺ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еә•жқҘеҲ°еҚ—дә¬пјҢдәҺж°ёд№җеҚҒдёүе№ҙпјҲ1415е№ҙпјүеӣӣжңҲиў«е°ҒдёәвҖңеҰҷи§үеңҶйҖҡж…§ж…Ҳжҷ®еә”иҫ…еӣҪжҳҫж•ҷзҒҢйЎ¶ејҳе–„иҘҝеӨ©дҪӣеӯҗеӨ§еӣҪеёҲвҖқгҖӮз”ұдәҺеүҚйқўе·Із»ҸжҸҗеҲ°иҝҮзҡ„и®ёеӨҡзјҳз”ұ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дёҚеҸҜиғҪеҫ—еҲ°еӨ§жі•зҺӢзҡ„з§°еҸ·пјҢеҸӘиғҪжҳҜзЁҚйҖҠдёҖзӯүзҡ„вҖңиҘҝеӨ©дҪӣеӯҗеӨ§еӣҪеёҲвҖқгҖӮдҪҶ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е»·дёӯд№ғиҮіеңЁеҚ—дә¬жңҹй—ҙжүҖеҸ—еҲ°зҡ„зӨјйҒҮд№ҹжҜ«дёҚйҖҠиүІгҖӮ
гҖҖгҖҖ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и®°иҪҪ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иҮіеҚ—дә¬еҗҺпјҢжҳҺжҲҗзҘ–еҸ¬е…¶вҖңе…ҘеҶ…пјҢйў„иөҗе…ҚжӢңпјҢиөҗеә§еӨ§е–„ж®ҝпјҢеә”еҜ№з§°ж—ЁпјҢдёҠеӨ§еҳүеҸ№гҖӮж••е®үиғҪд»ҒеҜәж–№дёҲпјҢдёҠеҲ¶д№Ұж…°еҠіпјҢжүҖиөҗз”ҡеҺҡвҖқгҖӮв‘Ј
гҖҖгҖҖеҸҰжҚ®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и®°иҪҪпјҡвҖңжҳҺ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иҮіжҳҫйҖҡеҜәпјҢеҶ¬еҚҒдёҖжңҲжҳҺеёқйҒЈеӨӘзӣ‘дҫҜжҳҫиҜҸиҮідә¬еёҲе…ҘеӨ§еҶ…пјҢе…ҚжӢңиөҗеқҗпјҢдәҺеӨ§е–„ж®ҝеҘҸеҜ№з§°ж—ЁпјҢж••дё»иғҪд»Ғж–№дёҲгҖӮеҲ¶д№Ұж…°еҠіпјҢиөҗдәҲз”ҡеҺҡвҖқгҖӮв‘Ө
гҖҖгҖҖдәҢгҖҒ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Қ—дә¬иғҪд»ҒеҜә
гҖҖгҖҖеҚ—дә¬иғҪд»ҒеҜәжҳҜи‘—еҗҚеҸӨеҲ№д№ӢдёҖпјҢеҺҹеңЁеҚ—дә¬еҸӨеҹҺиҘҝй—ЁпјҢе»әдәҺеҲҳе®Ӣе…ғеҳүдёӯпјҢжҙӘжӯҰеҚҒдёҖе№ҙжҜҒдәҺзҒ«зҒҫпјҢжҳҺеӨӘзҘ–дёӢд»Өе°ҶеҜәеҫҷдәҺеҹҺеҚ—иҒҡе®қй—ЁеӨ–дәҢйҮҢд№Ӣең°гҖӮв‘Ҙд»ҠиҖғгҖҠйҮ‘йҷөжўөеҲ№еҝ—гҖӢжңүе…іи®°иҪҪпјҢзҹҘжҳҺд»ЈеҚ—дә¬жңүе…«еӨ§и‘—еҗҚжўөеҲ№пјҢдҫқж¬ЎжҳҜзҒөи°·гҖҒеӨ©з•ҢгҖҒжҠҘжҒ©гҖҒйёЎйёЈгҖҒиғҪд»ҒгҖҒж –йңһгҖҒејҳи§үгҖҒйқҷжө·гҖӮв‘ҰжҚ®иҪҪпјҢиҝҷдәӣеҜәеәҷеңЁжҳҺд»ЈйғҪжңүжёёж–№з•Әеғ§й©»й”ЎиҝҮпјҢеҰӮеӨ©з•ҢеҜәжң¬дёәе…ғд»ЈеӨ§йҫҷзҝ”йӣҶеәҶеҜәпјҢжҳҺжҙӘжӯҰе№ҙй—ҙжӣҫдәҺжӯӨеҜәи®ҫз«Ӣе–„дё–йҷўпјҢеҗҺж”№з«Ӣеғ§еҪ•еҸёпјҢжҳҺиҝҒйғҪеҢ—дә¬еҗҺпјҢд»ҚдёәеҚ—дә¬еғ§еҪ•еҸёиЎҷзҪІжүҖеңЁпјӣ⑧зҒөи°·еҜәеҲҷжҳҜж°ёд№җеӣӣе№ҙеӨ§е®қжі•зҺӢй©»й”Ўд№ӢеҜәпјҢ并еңЁйӮЈйҮҢеҘүж—ЁдёәжҳҺеӨ§иЎҢзҡҮеёқгҖҒзҡҮеҗҺдёҫиЎҢ规模зӣӣеӨ§зҡ„жҷ®еәҰеӨ§ж–ӢпјӣйёЎйёЈеҜәд№ҹж—¶еёёжҺҘеҫ…д»ҺиҘҝи—ҸжқҘеҶ…ең°зҡ„жёёж–№еғ§дәәгҖӮв‘ЁиғҪд»ҒеҜәд№ҹеұһжҳҺд»ЈеҚ—дә¬и‘—еҗҚжўөеҲ№пјҢеңЁжҙӘжӯҰе№ҙй—ҙеҚіеӨҮеҸ—йҮҚи§ҶпјҢгҖҠйҮ‘йҷөжўөеҲ№еҝ—гҖӢдёӯжңүиҝҷж ·дёҖж®өи®°иҪҪпјҢжҳҺеӨӘзҘ–жңұе…ғз’Ӣж••е‘ҪзӨјйғЁеҠ еғ§иЎҢжһңдёәйўқеӨ–е·Ұйҳҗж•ҷпјҢеғ§еҰӮй”ҰдёәйўқеӨ–еҸіи§үд№үпјҢиЎ”е‘ҪдәҺеӨ©з«әеұұиғҪд»ҒеҜәејҖи®ҫеә”дҫӣйҒ“еңәпјҢеӢ’д»ӨпјҡвҖңеҮЎдә¬еҹҺеҶ…еӨ–еӨ§е°Ҹеә”иөҙеҜәйҷўеғ§дәәпјҢиҝҒе…ҘиғҪд»ҒеҜәдјҡдҪҸзңӢз»ҸпјҢдҪңдёҖеҲҮдҪӣдәӢгҖӮиӢҘдёҚз”ұжӯӨпјҢеҸҰиө·еҗҚиүІз§ҒдҪңдҪӣдәӢиҖ…пјҢе°ұд»°иғҪд»ҒеҜәе®ҳй—®зҪӘвҖқгҖӮв‘©з”ұжӯӨпјҢеҪ“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ҘжңқеҗҺпјҢжҳҺжҲҗзҘ–еҜ№д»–зӨјйҒҮжңүеҠ пјҢж••жҺҲд»–дёәиғҪд»ҒеҜәж–№дёҲд№ҹжҳҜеҚҒеҲҶжӯЈеёёзҡ„гҖӮ
гҖҖгҖҖе…ідәҺ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Қ—дә¬иғҪд»ҒеҜәеұ…з•ҷжңҹй—ҙжүҖд»ҺдәӢзҡ„дҪӣдәӢжҙ»еҠЁпјҢеңЁжұүж–Үж–ҮзҢ®дёӯеҮ д№ҺжүҫдёҚеҲ°д»»дҪ•и®°иҪҪпјҢдёҖдёӘеҺҹеӣ жҳҜз”ұдәҺи—Ҹдј дҪӣж•ҷеҜҶе®—ж•ҷжі•д»ӘиҪЁдёҺдёӯеҺҹдҪӣж•ҷеӨ§зӣёеҫ„еәӯпјҢжұүж–Үж–ҮзҢ®дёӯйҷӨдҪңдёҖдәӣеңәйқўжҸҸиҝ°еӨ–пјҢж— жі•еҫ—зҹҘе…¶е…·дҪ“еҶ…е®№пјӣеҸҰдёҖдёӘеҺҹеӣ жҳҜпјҢжңқе»·и®ёеӨҡе„’еӯҰд№ӢеЈ«жң¬еҜ№жңқе»·еҙҮдҝЎи—Ҹдј дҪӣж•ҷжү№иҜ„еӨҡеӨҡпјҢи®Өе®ҡи®ёеӨҡжі•дәӢжҙ»еҠЁиҚ’иҜһж— зЁҪпјҢдёҚеұ‘е…·иҪҪгҖӮдҪҶиҮӘж°ёд№җеҲқе№ҙе§ӢпјҢеӨ§жү№и—Ҹең°й«ҳеғ§жҙ»дҪӣеҸ—еҲ°жңқе»·е°ҒиөҸпјҢ并驻иөҗдә¬еҹҺпјҢи®Із»ҸжҺҲеҫ’пјҢзҪ®еҠһжі•дјҡйҒ“еңәпјҢеңЁе®«е»·еҶ…еӨ–зЎ®е®һеҹ№е…»дәҶзӣёеҪ“ж•°йҮҸзҡ„дҝЎдј—гҖӮеҰӮжһңиҜҙ延иҜ·и—Ҹдј дҪӣж•ҷй«ҳеғ§дәәжңқд»ҺдёҖејҖе§ӢжҳҜдёәдәҶжӢӣеҫ•иҝңдәәпјҢдёәдәҶеҫҒжңҚиҫ№з–Ҷең°еҢәзҡ„йңҖиҰҒпјҢиҖҢиҝҷдәӣй«ҳеғ§зҡ„дёңжқҘеҶ…ең°еҗҺпјҢе…¶еёҰжңүжө“еҺҡзҘһз§ҳиүІеҪ©зҡ„е®—ж•ҷеҶ…е®№д№ҹдјҡеҗёеј•еӨ§жү№зҡ„е–„з”·дҝЎеҘіпјҢжҳҺжҲҗзҘ–дёҺе…¶иә«иҫ№зҡ„и®ёеӨҡе®Ұе®ҳд№ҹжҲҗдёәи—Ҹдј дҪӣж•ҷзҡ„еҙҮдҝЎиҖ…гҖӮ
гҖҖгҖҖи—Ҹж–ҮеҸІзұҚи®°иҪҪ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Қ—дә¬еұ…з•ҷжңҹй—ҙпјҢжҳҺжҲҗзҘ–жӣҫж••е‘Ҫ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иғҪд»ҒеҜәвҖңе»әеӣӣз»ӯйғЁеқӣеҹҺдҝ®дҫӣвҖқгҖӮпј»11пјҪдәҺжҳҜвҖ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еёҲеҫ’е№ҝеҒҡеҜҶйӣҶгҖҒиғңд№җгҖҒеӨ§иҪ®пјҲеҚіж—¶иҪ®пјүгҖҒеӨ§еЁҒеҫ·еӣӣеҚҒд№қе°ҠгҖҒиҚҜеёҲдҪӣзҡ„дҝ®дҫӣжі•дәӢвҖқгҖӮпј»12пјҪеҪ“дёҫиЎҢжі•дәӢж—¶пјҢвҖңеӨ©з©әдј жқҘеӨ©з•Ңйј“д№җеЈ°пјҢдёәдј—дәәжүҖй—»гҖӮеӨ©з©әдёӯиҝҳдёҖеҶҚеҮәзҺ°жңүжі•е№ўгҖҒйҮ‘еҲҡиҪ®гҖҒиҺІиҠұзӯүйҮ‘еҲҡз•Ңж Үеҝ—д№ӢеҪ©иҷ№пјҢдёәдј—з”ҹдәІзңје…ұзқ№пјҢеҸҲд»Һжҷҙз©әд№ӢдёӯеӨҡж¬ЎйҷҚдёӢиҠұйӣЁпјҢдҪҝдј—дәәжһҒдёәдҝЎд»°вҖқгҖӮпј»13пјҪ
гҖҖгҖҖд»Һиҝҷдәӣи®°иҪҪ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Қ—дә¬жүҖеҒҡжі•дәӢе·ІдёҚеҗҢдәҺеҷ¶зҺӣе·ҙеӨ§е®қжі•зҺӢзҡ„еқӣеҹҺжі•дјҡпјҢпј»14пјҪе·ІжҳҺжҳҫеёҰжңүж јйІҒжҙҫзҡ„зү№иүІгҖӮжүҖи°“вҖңеӣӣз»ӯйғЁвҖқпјҢеҚіжҳҜж јйІҒжҙҫеҜҶе®—зҡ„дәӢйғЁгҖҒиЎҢйғЁгҖҒз‘ңдјҪйғЁе’Ңж— дёҠз‘ңдјҪгҖӮиҖҢвҖңеҜҶйӣҶвҖқгҖҒвҖңиғңд№җвҖқгҖҒвҖңж—¶иҪ®вҖқе’ҢвҖңеӨ§еЁҒеҫ·вҖқд№ҹжӯЈжҳҜж јйІҒжҙҫеҜҶе®—жңҖдёәжҺЁеҙҮзҡ„еӣӣеӨ§йҮ‘еҲҡеҜҶжі•жң¬е°ҠгҖӮ
гҖҖгҖҖи—ҸеҸІдёӯиҝҳи®°иҪҪпјҢдәҺжі•дјҡд№ӢеҗҺпјҢжҳҺжҲҗзҘ–жўҰи§ҒеңЁиғҪд»ҒеҜәвҖңдёҠз©әжңүеҚҒж–№дҪӣйҷҖиҸ©иҗЁдјҡиҒҡвҖқпјҢеӣ иҖҢеҝғдёӯж¬ўе–ңпјҢз”ҹиө·еӨ§дҝЎд»°пјҢдәҺжҳҜе°ҒйҮҠиҝҰиҖ¶еҚҸвҖңеҰҷи§үеңҶйҖҡж…Ҳж…§жҷ®еә”иҫ…еӣҪжҳҫж•ҷзҒҢйЎ¶ејҳе–„иҘҝеӨ©дҪӣеӯҗеӨ§еӣҪеёҲеӨ§ж…Ҳжі•зҺӢвҖқпјҢ并иөҗз»ҷд»–д№ҢйҮ‘еҚ°дҝЎпјҢвҖңе°Ҷд»–еҘүдёәиҜёжү§жҺҢж•ҷжі•иҖ…зҡ„йЎ¶йҘ°вҖқгҖӮзҡҮеёқиҝҳиҝҺиҜ·йҮҠиҝҰиҖ¶еҚҸиҮіе®«дёӯпјҢи®©д»–еқҗдәҺиҮӘе·ұзҡ„зҡҮеёқе®қеә§дёҠпјҢ并жҢүжұүдәәйЈҺдҝ—д№ жғҜпјҢдёәйҮҠиҝҰиҖ¶еҚҸдёҫиЎҢзӣӣеӨ§е®ҙдјҡгҖӮ
гҖҖгҖҖдёүгҖҒйҮҠиҝҰиҖ¶еҚҸдёәжҳҺжҲҗзҘ–дј й•ҝеҜҝзҒҢйЎ¶жі•
гҖҖгҖҖеңЁжӯӨд№ӢеҗҺпјҢжҳҺжҲҗзҘ–иҜ·йҮҠиҝҰиҖ¶еҚҸдёәд»–жҺҲвҖңеәҰжҜҚжүҖдј зҡ„й•ҝеҜҝзҒҢйЎ¶е’ҢеӨ§жҲҗе°ұиҖ…еә•жҙӣе·ҙжүҖдј зҡ„иғңд№җй•ҝеҜҝдёҚжӯ»зҒҢйЎ¶пјҢеҪ“жҠҠзҒҢ顶瓶ж”ҫеҲ°зҡҮеёқеӨҙдёҠж—¶пјҢ瓶дёӯз”ҳйңІиҮӘ瓶еҸЈжәўеҮәпјҢй•ҝеҜҝдёёж”ҫе°„еҮәе…үжҳҺпјҢдҪҝзҡҮеёқжһҒдёәиҷ”дҝЎпјҢеҘүзҢ®дәҶеӨ§йҮҸиҙўзү©дҪңдёәжҺҘеҸ—зҒҢйЎ¶зҡ„дҫӣе…»вҖқгҖӮпј»15пјҪ
гҖҖгҖҖвҖңзҒҢйЎ¶вҖқпјҢи—ҸиҜӯз§°пјҢж„ҸдёәвҖңжҺҲжқғвҖқгҖӮеҸ–иҮӘеҸӨеҚ°еәҰеӣҪзҺӢеҚідҪҚж—¶з”ЁеӣӣеӨ§жө·д№Ӣж°ҙжөҮзҒҢе…¶еӨҙйЎ¶пјҢд»ҘзӨәиҮӘжӯӨеҚіжңүжқғжІ»зҗҶеӣҪ家д№Ӣж„ҸгҖӮеҗҺжј”еҢ–дҝ®д№ еҜҶжі•ж—¶еҝ…йЎ»з»ҸеҺҶзҡ„дёҖз§Қе®—ж•ҷд»ӘејҸгҖӮеҜҶе®—жҳҜйҖҡиҝҮзҡҲдҫқйҮ‘еҲҡдёҠеёҲпјҢжҢүеёҲжүҖдј зңҹиЁҖеҜҶе’’д»ҘеҸҠдёҘж јзҡ„зЁӢеәҸгҖҒд»ӘиҪЁпјҢи§Ӯдҝ®дҪӣжҲ‘дёҖдҪ“пјҢд»ҘжұӮеҚіиә«жҲҗдҪӣзҡ„дёҖз§ҚжңҖй«ҳжі•й—ЁгҖӮеҸӘжңүдёҠж №еҲ©жҷәеҫ—йҮ‘еҲҡдёҠеёҲзҡ„зҒҢйЎ¶гҖҒеҠ жҢҒпјҢжҲҗзҶҹиә«еҝғзӣёз»ӯпјҢж°ёеҮҖзҪӘеһўпјҢжүҚеҸҜд»Ҙдҝ®жҢҒиҝҷз§ҚвҖңиӢҘж— еёҲжүҝпјҢдёҚеҸҜж»ҘеӯҰпјӣжңӘз»ҸзҒҢйЎ¶пјҢзӘғжі•ж— зӣҠвҖқзҡ„е®ҳжі•гҖӮз»ҸиҝҮе…Ҙй—ЁзҒҢйЎ¶пјҢж„Ҹе‘ізқҖеҸ–еҫ—дҝ®д№ еҜҶжі•иө„ж јпјҢеңЁдҝ®жі•дёӯеҸҜд»Ҙеҫ—еҲ°йҮ‘еҲҡдёҠеёҲзҡ„еҠ жҢҒпјҢдёҚеҸ—йӯ”йҡңдҫөжү°пјҢеўһзӣҠиҜҒжӮҹеҠҹеҫ·гҖӮз”ұдәҺжҜҸдҝ®д№ дёҖз§ҚеҜҶжі•пјҲе·Іе…¬ејҖдј жҺҲзҡ„еҜҶжі•йҷӨеӨ–пјүжҲ–иҝӣе…ҘдёҖдёӘж–°зҡ„дҝ®иЎҢ次第时пјҢйғҪйңҖиҰҒжұӮеҫ—ж–°зҡ„зҒҢйЎ¶гҖӮеӣ иҖҢпјҢдёҖдёӘдҝ®еҜҶзҡ„еғ§дәәдёҖз”ҹдёӯиҰҒжҺҘеҸ—еӨҡж¬ЎзҒҢйЎ¶гҖӮ
гҖҖгҖҖзҒҢйЎ¶зҡ„з§Қзұ»еҫҲеӨҡпјҢд»Ҙзӣ®зҡ„еҲҶпјҢжңүз»“зјҳзҒҢйЎ¶гҖҒзҡҲдҫқзҒҢйЎ¶гҖҒдј жі•зҒҢйЎ¶гҖҒжҺҲиҒҢзҒҢйЎ¶зӯүпјӣд»Ҙж–№жі•еҲҶпјҢжңүж‘©йЎ¶зҒҢйЎ¶гҖҒж”ҫе…үзҒҢйЎ¶гҖҒз”ҳйңІзҒҢйЎ¶гҖҒжҷәеҚ°зҒҢйЎ¶гҖҒжі•еҷЁзҒҢйЎ¶гҖҒз§ҚеӯҗзҒҢйЎ¶зӯүпјӣд»Ҙдҝ®йҒ“次第еҲҶеҸҲжңүи®ёеӨҡдёҚеҗҢз§Қзұ»пјҢж јйІҒжҙҫеҜҶд№ҳж— дёҠз‘ңдјҪйғЁжңү瓶зҒҢйЎ¶гҖҒз§ҳеҜҶзҒҢйЎ¶гҖҒжҷәж…§зҒҢйЎ¶е’ҢеҸҘд№үзҒҢйЎ¶зӯүеӣӣзҒҢйЎ¶жі•гҖӮпј»16пјҪ
гҖҖгҖҖзҒҢйЎ¶зҡ„е…·дҪ“иҝҮзЁӢе’ҢеҒҡжі•еӣ дј жі•дёҠеёҲе’Ңд»ҳжі•еӣ зјҳдёҚеҗҢиҖҢжңүе·®еҲ«гҖӮжңҖжҷ®йҖҡзҡ„зҒҢйЎ¶жі•дёәпјҡдёҠеёҲдәҺеқӣеңәдёӯжҢҒ瓶и§Ӯжғіиҷҡз©әдёӯйЈһжқҘеӣӣйҫҷеҗҗж°ҙе…Ҙ瓶пјҢеҖ’зҒҢејҹеӯҗеӨҙйЎ¶иҖҢеҫ—еҠ жҢҒпјҢдҪҝеҸ—жі•ејҹеӯҗиә«еҝғжё…еҮҖж— еһўпјҢдёҺдҪӣж„ҹеә”пјҢдҪӣжҲ‘дёҖдҪ“гҖӮдёҖиҲ¬дј жі•зҒҢйЎ¶еҲҶеүҚиЎҢгҖҒжӯЈиЎҢгҖҒз»“иЎҢдёүдёӘйҳ¶ж®өгҖӮзҒҢйЎ¶еүҚиЎҢпјҢеҚіеҮҖең°гҖҒи®ҫеқӣгҖҒжІҗжөҙгҖҒжҢҒж–Ӣзӯүд»ӘејҸеүҚзҡ„дёҖеҲҮеҮҶеӨҮе·ҘдҪңпјҢд№ҹз§°вҖңеҠ иЎҢвҖқпјӣзҒҢйЎ¶жӯЈиЎҢпјҢеҚіи®ҫдҫӣгҖҒе…ҘеқӣгҖҒиҝҺиҜ·жң¬е°ҠгҖҒеҸ—дёүжҳ§иҖ¶жҲ’зӯүжӯЈдҝ®д»ӘејҸпјӣзҒҢйЎ¶з»“иЎҢпјҢеҚійҖҒзҘһи°ўжҒ©гҖҒжүҝи®ёе®ҲиӘ“пјҢзҢ®дёүй—Ёд»Ҙдёәд»ҶеҪ№гҖҒеӣһеҗ‘иҸ©жҸҗзӯүдәӢзӣёгҖӮ
гҖҖгҖҖйҮҠиҝҰиҖ¶еҚҸдёәжҳҺжҲҗзҘ–жүҖжҺҲзҒҢйЎ¶еҚіжҳҜдёәзҘҲжұӮй•ҝеҜҝдёәзӣ®зҡ„зҡ„й•ҝеҜҝзҒҢйЎ¶пјҢдәҰеұһ瓶зҒҢйЎ¶пјҲеҷЁзҡҝзҒҢйЎ¶пјүд№ӢдёҖз§ҚгҖӮе…ғж—¶д»Һе…ғдё–зҘ–еҝҪеҝ…зғҲеҸҠе…¶еҗҺеҰғгҖҒи’ҷеҸӨзҺӢе…¬еӨ§иҮЈд»Һи—Ҹдј дҪӣж•ҷйҮ‘еҲҡдёҠеёҲжҺҘеҸ—зҒҢйЎ¶д№ӢдәӢеҸёз©әи§ҒжғҜпјҢеӣ жұүи—Ҹж–ҮеҢ–е·®ејӮиҫғеӨ§пјҢд»Ҙе Ӯе ӮеӨ§жҳҺзҡҮеёқеҘүиҘҝз•Әеғ§дәәдёәйҮ‘еҲҡдёҠеёҲпјҢжңқиҮЈиҷҪж— жі•йҳ»жӯўпјҢдҪҶи®іиЁҖе…¶дәӢпјҢгҖҠжҳҺеҸІгҖӢдёӯеҸӘз®ҖеҚ•иҜҙжҳҺжҲҗзҘ–вҖңе…јеҙҮе…¶ж•ҷвҖқгҖӮз”ұи—Ҹж–Үж–ҮзҢ®дёӯе…ідәҺжҳҺжҲҗзҘ–еҸ—й•ҝеҜҝзҒҢйЎ¶зҡ„и®°иҪҪпјҢиҜҙжҳҺжҳҺжҲҗзҘ–дёҚжҳҜз®ҖеҚ•ең°еҙҮдҝЎпјҢиҖҢжҳҜиә«дҪ“еҠӣиЎҢпјҢжҲҗдёәзңҹжӯЈзҡ„и—Ҹдј дҪӣж•ҷеҜҶе®—зҡ„дј жі•ејҹеӯҗгҖӮйҮҠиҝҰиҖ¶еҚҸдёәжҳҺжҲҗзҘ–жҺҲзҒҢйЎ¶еҜҶжі•пјҢ并дёҚжҳҜжҲҗзҘ–第дёҖж¬ЎжҺҘеҸ—зҒҢйЎ¶гҖӮж—©еңЁж°ёд№җдә”е№ҙиҝҺиҜ·д№ҢжҖқи—Ҹеҷ¶зҺӣе·ҙеӨ§е®қжі•зҺӢж—¶пјҢд»–е°ұе·Ід»Һеҷ¶зҺӣе·ҙеҸ—иҝҮвҖңж— йҮҸзҒҢйЎ¶вҖқгҖӮпј»17пјҪдёҫиЎҢе®ҢдёҠиҝ°е®—ж•ҷжҙ»еҠЁеҗҺ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иҫһеҲ«жҳҺжҲҗзҘ–пјҢзҰ»ејҖеҚ—дә¬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гҖӮ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Қ—дә¬еұ…дҪҸеӨ§зәҰеҚҠе№ҙеӨҡж—¶й—ҙгҖӮд»–дәҺ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дәҢжңҲе…ҘжңқпјҢж°ёд№җеҚҒдёүе№ҙеӣӣжңҲеҸ—е°ҒеӨ§еӣҪеёҲпјҢж°ёд№җеҚҒеӣӣе№ҙдә”жңҲиҫһеҪ’д№ҢжҖқи—ҸгҖӮдҪҶжҚ®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и®°иҪҪеҲҶжһҗпјҢйҮҠиҝҰиҖ¶еҚҸеңЁеҸ—е°ҒеҗҺдёҚд№…пјҢеҚі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пјҢиҖҢж°ёд№җеҚҒеӣӣе№ҙиҫһеҪ’д№ҢжҖқи—ҸжҳҜеңЁдә”еҸ°еұұгҖӮжІЎжңүеңЁеҚ—дә¬еұ…з•ҷжӣҙй•ҝж—¶й—ҙпјҢйҷӨдәҶи—Ҹдј дҪӣж•ҷеғ§дәәеҜ№дә”еҸ°еұұзҡ„еҗ‘еҫҖд№Ӣжғ…еӨ–пјҢиҝҳжңүж°”еҖҷеӣ зҙ пјҢеҚ—дә¬еӨҸеӯЈй…·зғӯйҡҫеҪ“пјҢжүҖд»Ҙж—©дәӣеҠЁиә«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пјҢд№ҹжңүйҒҝжҡ‘зҡ„йңҖиҰҒгҖӮ
гҖҖеӣӣгҖҒдә”еҸ°еұұдёҺи—Ҹдј дҪӣж•ҷ
гҖҖгҖҖеңЁжұүең°дҪӣж•ҷдёӯпјҢдә”еҸ°еұұиў«жҜ”йҷ„дёәдҪӣж•ҷе…ёзұҚдёӯжүҖиҜҙзҡ„ж–Үж®ҠеҢ–е®Үзҡ„вҖҳжё…еҮүеұұвҖқпјҢ并е°Ҷдә”еҸ°дёҺж–Үж®ҠдҝЎд»°иҒ”зі»иө·жқҘгҖӮжҷӢдҪӣй©®и·ӢйҷҖзҪ—иҜ‘гҖҠеӨ§ж–№е№ҝдҪӣеҚҺдёҘз»ҸгҖӢ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дёңеҢ—ж–№жңүиҸ©иҗЁдҪҸеӨ„еҗҚжё…еҮүеұұгҖӮиҝҮеҺ»иҜёиҸ©иҗЁеёёдәҺдёӯеҫҖпјҢеҪјзҺ°жңүиҸ©иҗЁеҗҚж–Үж®ҠеёҲеҲ©пјҢжңүдёҖдёҮиҸ©иҗЁзң·еұһпјҢеёёдёәиҜҙжі•вҖқгҖӮпј»18пјҪдә”еҸ°еұұдёҺи—Ҹдј дҪӣж•ҷд№Ӣй—ҙзҡ„е…ізі»еҸҜиҜҙжҳҜеҚҒеҲҶеҜҶеҲҮдё”жәҗиҝңжөҒй•ҝгҖӮж–Үж®ҠиҸ©иҗЁеңЁдҪӣж•ҷдёӯзҡ„ең°дҪҚжһҒдёәзү№еҲ«пјҢж—ўжҳҜдёҮиЎҢеңҶдҝ®гҖҒиҮӘд»–е…јеҲ©еҚҙеҸҲе®…еҝғжі•з•Ңзҡ„иҸ©иҗЁпјҢеҸҲжҳҜе…·жңүдёүеҚҒдәҢзӣёгҖҒе…«еҚҒз§ҚеҘҪпјҢзӣёеҘҪеҰӮеҗҢдҪӣзҘ–зҡ„еҮәдё–д№ӢеңЈгҖӮж–Үж®Ҡиҝҷз§ҚдәҰдҪӣдәҰиҸ©иҗЁзҡ„иә«д»ҪпјҢдҪҝдҝЎдј—зЎ®дҝЎд»–ж•‘еәҰдј—з”ҹзҡ„ж…ҲжӮІд№ӢеҠӣпјҢж— йҮҸж— иҫ№гҖӮе”җд»ЈеҜҶе®—дј е…Ҙжұүең°пјҢеҜҶе®—жҸҗеҖЎдҪӣж•ҷеҫ’дёҚд»…иҰҒжұӮиҜҒдёӘдәәи§Ји„ұпјҢжӣҙиҰҒйҮҮеҸ–еҗ„з§ҚзҒөжҙ»зҡ„ж–№жі•жқҘвҖңи„ұеәҰвҖқдј—з”ҹпјҢеҚіжүҖи°“вҖңж–№дҫҝжҷәж…§вҖқжҲ–вҖңж–№дҫҝйҒ“вҖқгҖӮиҖҢд»ҘвҖңжҷә慧第дёҖвҖқзҡ„ж–Үж®ҠиҸ©иҗЁеҲҷжҲҗдёәеҜҶе®—жңҖеҙҮжӢңзҡ„иҸ©иҗЁпјҢе…¶еҪўиұЎдёҖиҲ¬йЎ¶з»“дә”й«»гҖҒжүӢжҢҒе®қеү‘гҖҒеқҗйӘ‘зӢ®еӯҗпјҢиЎЁзӨәжҷәж…§гҖҒй”җеҲ©е’ҢеЁҒзҢӣгҖӮеҗҺжқҘдҪӣж•ҷеҫ’жӣҙжҠҠгҖҠйҮ‘еҲҡйЎ¶з»ҸгҖӢдёӯвҖңдә”дҪӣжҳҫдә”жҷәвҖқзҡ„жҖқжғіз»“еҗҲеҲ°дә”еҸ°еұұеҙҮжӢңдёӯпјҢи®Өдёәдә”еә§еұұеі°жҳҜж–Үж®ҠиҸ©иҗЁеӨ§жҳҫеҸ—иә«д№ӢжһҒеҮҖдә”дҪ“пјҢжҳҜжҳҫзӨәдә”з§Қе№»еҢ–жҷәж…§д№Ӣе…үе№»зҡ„дә”з§Қиә«еғҸпјҢе…¶дёӯгҖҒдёңгҖҒеҚ—гҖҒиҘҝгҖҒеҢ—еҸ°еҲҶеҲ«д»ЈиЎЁвҖңиә«вҖқгҖҒвҖңж„ҸвҖқгҖҒвҖқжҷәж…§вҖқгҖҒвҖңиҜӯвҖқгҖҒвҖңдёҡвҖқгҖӮдҪӣж•ҷеҫ’е®Ңе…Ёе°Ҷдә”еҸ°еұұи®ӨдҪңж–Үж®ҠеҢ–зҺ°д№ӢжүҖпјҢдёҚд»…еҸ°еҸ°зҡҶжңүж–Үж®ҠеҢ–зҺ°зҒөиҝ№гҖҒеҜәеҜәйғҪеЎ‘жңүж–Үж®ҠеңЈеғҸпјҢе°ұиҝһдә”еҸ°еұұзҡ„иҚүжңЁеңҹзҹіеқҮдёҺж–Үж®ҠиҸ©иҗЁзӣёе…іиҒ”гҖӮжӣҙеҠ дёҠдә”еҸ°еұұжҪңиӮІзҷҫзҒөгҖҒйқҷи°·е№Ҫжһ—зҡ„з§ҖдёҪжҷҜиүІпјҢж–Үж®ҠеңЈең°дә”еҸ°еұұд№ӢзӣӣиӘүе№ҝж’ӯеӣӣж–№пјҢйҰҷзҒ«е…ҙж—әгҖӮеҗҗи•ғеңЁдёҺе”җзҺӢжңқдәӨеҫҖдёӯпјҢд№ҹд№…й—»дә”еҸ°еұұзӣӣеҗҚпјҢдәҺе”җз©Ҷе®—й•ҝеәҶе№ҙй—ҙпјҢеҗҗи•ғиөһжҷ®жӣҫ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гҖӮпј»19пјҪи—Ҹж–ҮеҸІд№Ұдёӯд№ҹжңүзӣёеә”зҡ„и®°иҪҪпјҡдәҺеҗҗи•ғиөһжҷ®иөӨжқҫеҫ·иөһеҚідҪҚд№ӢеҲқпјҢдҝЎеҘүиӢҜж•ҷзҡ„еӨ§иҮЈдёҖеәҰжҺҢж”ҝпјҢеҲ¶е®ҡдәҶжҜҒзҒӯдҪӣжі•зҡ„ж”ҝзӯ–пјҢжӢҶжҜҒдәҶжүҺзҺӣзҡ„зңҹжЎ‘жң¬е°ҠдҪӣе ӮгҖӮиөӨжқҫеҫ·иөһжҙҫйҒЈжЎ‘е–ңдёәйҰ–зҡ„дә”дҪҚдҪҝиҖ…еҲ°вҖңеҫ·д№ҢеұұвҖқеҚідә”еҸ°еұұйЎ¶зҡ„ж–Үж®ҠиҸ©иҗЁж®ҝдёӯжұӮеҸ–еҜәйҷўеӣҫж ·пјҢи—ҸеҸІгҖҠжӢ”еҚҸгҖӢдёӯиҝҳиҜҰз»ҶжҸҸз»ҳдәҶеҮ дҪҚдҪҝиҮЈеҸ–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зҡ„з»ҸиҝҮгҖӮпј»20пјҪ
гҖҖгҖҖжүҖи°“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е°ұжҳҜз»ҳжңүдә”еҸ°еұұеҸҠе…¶еҗ„еӨ„зҘһзҒөеңЈиҝ№зҡ„дҪӣз”»пјҢжҚ®е”җи“қи°·жІҷй—Ёзҡ„гҖҠеҸӨжё…еҮүдј гҖӢзӯүи®°иҪҪпјҢеңЁе”җй«ҳе®—йҫҷжң”е№ҙй—ҙпјҲ661пҪһ663е№ҙпјүпјҢжңүиҘҝе®үжІҷй—ЁдјҡиөңеҘүе‘ҪеёҰз”»еёҲеј е…¬иҚЈзӯүдәәеҲ°дә”еҸ°еұұиҖғеҜҹеңЈиҝ№пјҢдјҡиөңе°Ҷз”»еёҲжүҖз»ҳдә”еҸ°еұұеӣҫж ·еҒҡжҲҗвҖңе°ҸеёҗвҖқпјҲеҚіеұҸйЈҺз”»пјү并且й…ҚдёҠиҜҙжҳҺж–Үеӯ—пјҢдҪҝ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еңЁдёӯеҺҹеҗ„ең°е№ҝдёәжөҒдј гҖӮеңЁж•Ұз…Ңж–ҮзҢ®дёӯд№ҹжңүи®°иҪҪпјҢиҜҙеҪ“ж—¶жңүи®ёеӨҡз”»е·Ҙ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з”»еӣҫпјҢеңЁеӨӘеҺҹзӯүең°иҝҳеҮәзҺ°дәҶд»Ҙз”»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дёәдёҡзҡ„дё“й—Ёз”»еҢ гҖӮпј»21пјҪеҗҗи•ғ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д№ӢдәӢеҜ№и—Ҹдј дҪӣж•ҷеҪұе“ҚйўҮеӨ§гҖӮиөһжҷ®иөӨжқҫеҫ·иөһж—¶жүҖдҝ®е»әзҡ„еҗҗи•ғ第дёҖеә§еүғеәҰеғ§дәәеҮә家зҡ„дҪӣж•ҷеҜәйҷўжЎ‘иҖ¶еҜәе°ұд»ҘжӯӨдёәи“қжң¬гҖӮд»ҘеҗҺпјҢжЎ‘иҖ¶еҜәеңЁеҺҶеҸІдёҠеӣ еҗ„з§ҚеҺҹеӣ еӨҡж¬Ўиў«жҜҒпјҢдҪҶж–Үж®ҠвҖңеҢ–е®ҮвҖқдә”еҸ°еұұд№Ӣеӣҫе§Ӣз»ҲжҳҜжҒўеӨҚйҮҚе»әиҜҘеҜәж—¶ж®ҝеҶ…еЈҒз”»дёӯдёҚеҸҜжҲ–зјәзҡ„еҶ…е®№гҖӮеңЁеёғиҫҫжӢүе®«иҮід»Ҡд№ҹдҝқз•ҷзқҖ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пјҲж—Ҙе…үж®ҝиҘҝеҚ—й—ЁеҚ—дҫ§пјүгҖӮж•Ұз…ҢиҺ«й«ҳзӘҹеЈҒз”»дёӯзҺ°еӯҳ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7е№…пјҢз»Ҹйүҙе®ҡжҺЁжөӢпјҢе…¶дёӯжңү4е№…жҳҜдёӯе”җеҗҗи•ғз»ҹжІ»ж•Ұз…Ңж—¶жңҹз•ҷдёӢзҡ„гҖӮпј»22пјҪеӣ иҖҢпјҢ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еҸҜиҜҙжҳҜи—Ҹжұүж°‘ж—Ҹд№Ӣй—ҙж–ҮеҢ–дәӨжөҒеҸІдёҠзҡ„дёҖдёӘеҺҶеҸІи§ҒиҜҒгҖӮ
гҖҖгҖҖеҗҗи•ғзҺӢжңқеҙ©жәғд№ӢеҗҺпјҢдҪӣж•ҷеңЁеҗҗи•ғжң¬еңҹеҸ—еҲ°жҜҒзҒӯжҖ§жү“еҮ»пјҢи—Ҹжұүд№Ӣй—ҙзҡ„дҪӣж•ҷдәӨжөҒд№ҹдёӯж–ӯдәҶеҫҲй•ҝж—¶й—ҙгҖӮдҪҶдә”еҸ°еұұеңЁи—Ҹж—Ҹеғ§дҝ—еӨ§дј—еҝғзӣ®дёӯзҡ„зҘһеңЈең°дҪҚеҚҙжІЎжңүеҸ—еҲ°еҪұе“ҚгҖӮиҮӘе…ғд»Јиө·пјҢи—Ҹдј дҪӣж•ҷеҗҚеғ§еӨ§еҫ·иөҙдә”еҸ°еұұжңқзӨјиҖ…з»ңз»ҺдёҚз»қгҖӮеҰӮгҖҠиҗЁиҝҰдё–зі»еҸІгҖӢеҸҠгҖҠиҗЁиҝҰдә”зҘ–е…ЁйӣҶгҖӢзӯүи—Ҹж–ҮеҸІдј и®°иҪҪпјҢеӨ§е…ғеёқеёҲе…«жҖқе·ҙжӣҫдәҺ23еІҒпјҲ1257е№ҙпјүж—¶пјҢ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еҗ¬еҸ—еӨ§еЁҒеҫ·гҖҒзҺӣе“Ҳеҷ¶жӢүгҖҒйҮ‘еҲҡз•ҢгҖҒж—¶иҪ®зӯүе…ЁеҘ—еҜҶжі•е’Ңз–ҸйҮҠпјҢд»ҘеҸҠдёӯи§Ӯи®әгҖҒиөһйўӮгҖҒдҝұиҲҚзӯүз»Ҹи®әгҖӮе…«жҖқе·ҙиҝҳеңЁжүҖи‘—иөһж–Үдёӯе°Ҷдә”еҸ°еұұе–»дёәеҜҶжі•йҮ‘еҲҡз•Ңдә”йғЁдҪӣзҡ„дҪӣеә§гҖӮ继еҗҺпјҢеҸҲжңүе–„дј зҺӣе“Ҳеҷ¶жӢүеҜҶжі•зҡ„иғҶе·ҙеӣҪеёҲеёёй©»дә”еҸ°еұұеҜҝе®ҒеҜәпјҢ并е»әз«ӢдәҶи—Ҹдј дҪӣж•ҷ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и®ІиҜҙеҲ¶еәҰгҖӮе…¶еҗҺеҸҲжңүе…ғеёқеёҲзӣҠеёҢд»Ғй’ҰгҖҒеҷ¶зҺӣе·ҙй»‘еёҪзі»дёүдё–жҙ»дҪӣи®©иҝҘеӨҡеҗүзӯүй•ҝжңҹеңЁдә”еҸ°еұұжҙ»еҠЁпјҢдҪҝдә”еҸ°еұұ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и—Ҹдј дҪӣж•ҷеңЁдёӯеҺҹжұүең°зҡ„дёҖдёӘдј ж’ӯдёӯеҝғгҖӮ
гҖҖгҖҖеҸҠиҮіжҳҺж°ёд№җдә”е№ҙдёғжңҲпјҢжҳҺжҲҗзҘ–вҖңе‘ҪеҰӮжқҘеӨ§е®қжі•зҺӢе“Ҳз«Ӣйә»дәҺеұұиҘҝдә”еҸ°еұұе»әеӨ§ж–ӢпјҢиө„иҚҗеӨ§иЎҢзҡҮеҗҺвҖқгҖӮпј»23пјҪйҡҸзқҖжҳҺжңқж••е°Ғзҡ„еҷ¶зҺӣе·ҙеӨ§е®қжі•зҺӢжқҘдә”еҸ°еұұй©»й”Ўдј жі•пјҢдә”еҸ°еұұзҡ„и—Ҹдј дҪӣж•ҷжӣҙеҠ е…ҙзӣӣпјҢеҮәзҺ°дәҶ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иҫүз…ҢгҖӮе…ідәҺеӨ§е®қжі•зҺӢ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дәӢиҝ№пјҢи—Ҹж–ҮеҸІзұҚи®°иҪҪиҫғз®ҖеҚ•пјҢ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и®°иҪҪиҫғиҜҰз»ҶпјҡвҖңжҳҺеӨ§е®қжі•зҺӢпјҢеҗҚи‘ӣе“©йә»пјҲе“Ҳз«Ӣйә»пјҢеқҮдёәеҷ¶зҺӣе·ҙд№ӢејӮиҜ‘пјүпјҢд№ҢжҖқи—ҸдәәгҖӮйҒ“жҖҖеҶІжј пјҢзҘһз”ЁеҸөжөӢпјҢеЈ°й—»дәҺдёӯеӣҪгҖӮж°ёд№җй—ҙпјҢдёҠйҒЈдҪҝиҘҝеңҹиҝҺд№ӢпјҢеёҲйҖӮжңүдә”еҸ°д№ӢжёёпјҢеә”е‘ҪиҮійҮ‘йҷөпјҢйҒ“еҗҜеңЈиЎ·пјҢиҜ°е°ҒеҰӮжқҘеӨ§е®қжі•зҺӢпјҢиҘҝеӨ©еӨ§е–„иҮӘеңЁдҪӣгҖӮеёҲжҖ§д№җжһ—жіүпјҢжңқе»·д№ӢдёӢпјҢжҒҗеҰЁзҰ…дёҡпјҢеҘҸиҫһпјҢжёёдә”еҸ°гҖӮдёҠзң·жіЁж®·еӢӨпјҢз•ҷд№ӢдёҚе·ІпјҢд№ғиөҗйҠ®иҲҶж—Ңе№ўдјһзӣ–д№Ӣд»ӘпјҢйҒЈдҪҝеҚ«йҖҒдәҺдә”еҸ°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жӣҙж••еӨӘзӣ‘жқЁеҚҮпјҢйҮҚдҝ®е…¶еҜәпјҢе…јдҝ®иӮІзҺӢжүҖзҪ®дҪӣиҲҚеҲ©еЎ”пјҢд»ҘйҘ°жі•зҺӢд№Ӣеұ…вҖқгҖӮпј»24пјҪ
гҖҖгҖҖеӨ§жҳҫйҖҡеҜәдҪҚдәҺдә”еҸ°еұұеҸ°жҖҖй•ҮеҢ—дҫ§пјҢдёәдә”еҸ°еұұдә”еӨ§зҰ…жһ—д№ӢдёҖпјҢе§ӢеҲӣдәҺдёңжұүж°ёе№іе№ҙй—ҙпјҲ58пҪһ75е№ҙпјүпјҢеҲқеҗҚвҖңеӨ§еӯҡзҒө鹫еҜәвҖқпјҢзӣёдј дә”еҸ°еұұдёҺеҚ°еәҰзҒө鹫峰зӣёдјјпјҢж•…еңЁжӯӨе»әеҜә并е‘ҪеҗҚдёәдә”еҸ°еұұдҪӣеҲ№ејҖеұұд№ӢзҘ–гҖӮиҮіеҢ—йӯҸеӯқж–Үеёқж—¶еҶҚе»әпјҢвҖңзҺҜеҢқ鹫峰пјҢзҪ®еҚҒдәҢйҷўгҖӮеүҚжңүжқӮиҠұеӣӯпјҢж•…дәҰеҗҚ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гҖӮе”җеӨӘе®—е№ҙй—ҙеҸҲйҮҚж–°дҝ®е»әиҝҮпјҢжӯҰеҲҷеӨ©еӣ ж–°иҜ‘гҖҠеҚҺдёҘз»ҸгҖӢдёӯжңүдә”еҸ°еұұеҗҚпјҢж”№еҜәеҗҚдёәеӨ§еҚҺдёҘеҜәгҖӮжҳҺжҲҗзҘ–еҸҲж••е‘ҪйҮҚдҝ®пјҢеӣ еӨ§е®қжі•зҺӢдәҺжӯӨең°дёҫеҠһеӨ§жі•дјҡпјҢвҖңж„ҹйҖҡзҘһеә”вҖқпјҢж•…иөҗеҗҚвҖңеӨ§жҳҫйҖҡеҜәвҖқгҖӮж°ёд№җдёүе№ҙж—¶пјҢи®ҫеғ§зәІеҸёдәҺеӨ§жҳҫйҖҡеҜәпјҢвҖңзҺҮеҗҲеұұеғ§зҘқеҺҳпјҢжң¬е·һжңҲз»ҷеғ§зІ®вҖқгҖӮпј»25пјҪд»Һиҝҷдәӣи®°иҪҪпјҢеҸҜзҹҘеӨ§жҳҫйҖҡеҜә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ең°дҪҚеҸҠе…¶йҮҚиҰҒжҖ§гҖӮеңЁжҳҫйҖҡеҜәеҚ—йқўпјҢеҸҲжңүдёҖеә§вҖңеӨ§е®қеЎ”йҷўеҜәвҖқпјҢеҜәдёӯе®қеЎ”зӣёдј дёәйҳҝиӮІзҺӢжүҖзҪ®дҪӣиҲҚеҲ©еЎ”еҸҠж–Үж®ҠеҸ‘еЎ”гҖӮж°ёд№җдә”е№ҙеӨ§е®қжі•зҺӢжқҘдә”еҸ°еұұж—¶пјҢжҳҺжҲҗзҘ–ж••е‘ҪеӨӘзӣ‘жқЁеҚҮйҮҚдҝ®еӨ§еЎ”пјҢе§Ӣе»әеҜәгҖӮ
гҖҖгҖҖдә”гҖҒ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ёҺдә”еҸ°еұұ
гҖҖгҖҖйҮҠиҝҰд№ҹеӨұжҳҜ继еӨ§е®қжі•зҺӢд№ӢеҗҺжқҘдә”еҸ°еұұзҡ„第дәҢдҪҚжҳҺд»Ји—Ҹдј дҪӣж•ҷй«ҳеғ§пјҢд№ҹжҳҜжқҘеҲ°дә”еҸ°еұұзҡ„第дёҖдҪҚж јйІҒжҙҫй«ҳеғ§гҖӮ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ёҺдә”еҸ°еұұзҡ„е…ізі»йқһжҜ”еҜ»еёёпјҢе–»и°Ұ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дёӯдёәе…¶з«Ӣдј пјҢзӣҙиЁҖгҖҠдә”еҸ°еұұжҳҫйҖҡеҜәжІҷй—Ё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пјҢпј»26пјҪеҪ“然пјҢдј и®°жһҒдёәз®ҖеҚ•пјҢиҖҢдё”иҝҳжңүдёҘйҮҚй”ҷиҜҜз”ҡиҮіжҠ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и®ӨдҪңжҳҜеӨ©з«әеғ§дәәпјҢдёҺдҪӣзҘ–йҮҠиҝҰзүҹе°јеҮәиә«дәҺеҗҢдёҖ家ж—ҸгҖӮд»ҠиҖғ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дёӯе…ідә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и®°иҪҪеҮ д№Һе…ЁйғЁжқҘиҮӘ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пјҢдёәиҜҒжҳ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жҙ»еҠЁзҡ„зӣёе…іеҸІдәӢпјҢд№ҹдёәзә жӯЈеҶ…ең°жүҖдј й«ҳеғ§дј дёӯ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и®°иҪҪзҡ„жҹҗдәӣи°¬иҜҜпјҢе…№е°Ҷ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зҡ„гҖ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移еҪ•дәҺдёӢпјҡ
гҖҖгҖҖжҳ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пјҢеӨ©з«әиҝҰжҜ—зҪ—еӣҪпјҢдё–е°Ҡд№ӢиЈ”д№ҹгҖӮеҠҹеҫ·зҪ”жһҒпјҢзҘһз”ЁйҡҫжөӢгҖӮд»°ж–Үж®Ҡд№ӢйҒ“пјҢжқҘжёёжё…еҮүгҖӮ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жҳҘпјҢе§ӢиҫҫжӯӨеңҹпјҢж –жӯўеҸ°еұұ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еҶ¬еҚҒдёҖжңҲпјҢй—»дәҺдёҠпјҢйҒЈеӨӘзӣ‘дҫҜжҳҫиҜҸиҮідә¬пјҢе…ҘеҶ…пјҢйў„ж••е…ҚжӢңпјҢиөҗеә§еӨ§е–„ж®ҝеә”еҜ№з§°ж—ЁпјҢдёҠеӨ§еҳүеҸ№гҖӮж••е®үиғҪд»Ғж–№дёҲпјҢдёҠеҲ¶д№Ұж…°еҠіпјҢжүҖиөҗз”ҡеҺҡгҖӮжҳҺе№ҙдёҠеҲ¶д№ҰпјҢиөҗйҮ‘еҚ°е®қиҜ°пјҢе°ҒеҰҷи§үеңҶйҖҡж…§ж…Ҳжҷ®еә”иҫ…еӣҪжҳҫж•ҷзҒҢйЎ¶ејҳе–„иҘҝеӨ©дҪӣеӯҗеӨ§еӣҪеёҲд№ӢеҸ·гҖӮж— дҪ•пјҢиҫһдёҠе…ҘеҸ°пјҢжҜҸе…Ҙе®ҡпјҢдёғж—Ҙд№ғиө·гҖӮдёҠж•°еҲ¶д№ҰйҒЈдҪҝиҮҙж…°гҖӮиҮідәҺе®Је®—пјҢе°ӨеҠ й’ҰеҙҮпјҢзӨјеҮәеёёж јгҖӮе®Јеҫ·е…ӯе№ҙпјҢж—ӢиҘҝеҹҹз„үпј»27пјҪгҖӮ
иҝҷдёҖж®өи®°иҪҪдёӯжңүжӯЈзЎ®зҡ„еҶ…е®№пјҢд№ҹжңүй”ҷиҜҜд№ӢеӨ„пјҢйҰ–е…Ҳ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жқҘеҺҶдёҚз”ҡдәҶдәҶпјҢд»Ҙдёәд»–жҳҜеӨ©з«әеғ§дәәпјҢеӣ дёәвҖңйҮҠиҝҰвҖқд№ӢйҹізЎ®зі»жўөиҜӯпјҢз”ұжӯӨдҫҝжңӣж–Үз”ҹд№ү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д»Ҙдёәд»–дёҺдҪӣзҘ–дё–е°ҠеҮәиә«дәҺдёҖдёӘ家ж—ҸгҖӮжұүең°еғ§дәәдёҚжё…жҘҡпјҢи—Ҹж—Ҹеғ§дәәиө·жўөж–ҮеҗҚеӯ—иҖ…д»ҺжқҘе°ұжңүпјҢиҜёеҰӮвҖңйҮҠиҝҰе®ӨеҲ©вҖқпјҢвҖңеӨҡзҪ—йӮЈд»–вҖқпјҢзӯүзӯүпјҢдёҚиғңжһҡдёҫгҖӮеҸҰеӨ–пјҢиЁҖе®Јеҫ·е…ӯе№ҙпјҢвҖңж—ӢиҘҝеҹҹз„үвҖқпјҢиӮҜе®ҡжҳҜдёҚжӯЈзЎ®зҡ„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дәҺе®Јеҫ·д№қе№ҙеҸ—е°ҒеӨ§ж…Ҳжі•зҺӢпјҢиҖҢгҖ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дёӯеҜ№еҰӮжӯӨйҮҚеӨ§д№ӢдәӢз«ҹ然еҸӘеӯ—жңӘи‘—пјҢдјјд№ҺеҫҲд»Өдәәиҙ№и§ЈгҖӮе…¶е®һпјҢиӢҘд»”з»ҶеҲҶжһҗпјҢд№ҹеҸҜд»Ҙи®Іеҫ—йҖҡпјҢеҚідәҺе®Јеҫ·е…ӯе№ҙ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ёҖиЎҢ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пјҢиҮідәҺеҲ°е“ӘйҮҢеҺ»дәҶпјҢеҢ…жӢ¬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ҪңиҖ…еңЁеҶ…зҡ„дә”еҸ°еұұжұүеғ§д»¬е№¶дёҚеҫ—иҖҢзҹҘпјҢдёҖж–№йқўжңүиҜӯиЁҖйҡңзўҚпјӣеҸҰдёҖж–№йқўж¶үеҸҠжңқе»·д№ӢдәӢд№ҹдјҡдҝқе®Ҳз§ҳеҜҶпјҢдёҚдјҡеӨ§еј ж——йј“ең°е®Јжү¬гҖӮиҖҢдё”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жӯӨз•Ә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д№ӢеҗҺпјҢе°ұеҶҚд№ҹжІЎеӣһдә”еҸ°еұұгҖӮиҷҪ然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еҢ—дә¬жңүи®ёеӨҡжҙ»еҠЁпјҢд№ҹйўҮеҫ—жңқе»·иөҸиҜҶгҖҒдҝЎйҮҚпјҢдҪҶеңЁйӮЈдёҖж—¶д»ЈпјҢдәӨйҖҡдёҚдҫҝпјҢж¶ҲжҒҜй—ӯеЎһпјҢжӣҙе…јжұүи—ҸдҪӣж•ҷж–ҮеҢ–д№Ӣе·®ејӮпјҢеңЁдә”еҸ°еұұй©»й”Ўе®үзҰ…зҡ„еғ§дәәж— жі•жӣҙеӨҡең°дәҶи§Ј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иЎҢиёӘжҳҜеҫҲе®№жҳ“зҗҶи§Јзҡ„гҖӮдҪҶйҮҠиҝҰд№ҹеӨұжӣҫз»ҸеҮ з•ӘжқҘй©»дә”еҸ°еұұпјҢеҸҲеҫ—жңқе»·е°ҒеҸ·пјҢеҸҲеҫ—жҳҺжҲҗзҘ–гҖҒжҳҺе®Је®—дёӨзҡҮеёқзӨјйҒҮпјҢж— з–‘жҳҜдёӘйҮҚиҰҒдәәзү©пјҢж’°еҶҷдә”еҸ°еұұеҺҶеҸІиҮӘ然еә”еӨ§д№ҰдёҖ笔пјҢдҪҶеҸҲдёҚзҹҘе…¶жүҖз»ҲпјҢеҸӘжҺЁжөӢд»–еӣһеӨ©з«әиҖҒ家дәҶеҗ§пјҒ
иҮідәҺдј и®°дёӯжүҖи®°иҪҪзҡ„е…¶д»–еҶ…е®№еә”жҳҜжҜ”иҫғеҸҜйқ зҡ„пјҢеӣ дёәжҳҜдҫқжҚ®дә”еҸ°еұұеғ§дәә们зҡ„жүҖи§ҒжүҖй—»иҖҢеҶҷгҖӮиҜёеҰӮ第дёҖж¬ЎжқҘдә”еҸ°еұұзҡ„ж—¶й—ҙпјҢд»ҘеҸҠзҰ»ејҖзҡ„ж—¶й—ҙпјӣзү№еҲ«жҳ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й•ҝиҫҫ23дёӘеӯ—зҡ„е°ҒеҸ·е®Ңе…Ёж— иҜҜгҖӮиҮідә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еӯҰдҝ®жғ…еҶөпјҢд№ҹжҳҜдёҚз”ҡдәҶдәҶпјҢе…ҲжҳҜиҜҙд»–вҖңеҠҹеҫ·зҪ”жһҒпјҢзҘһз”ЁйҡҫжөӢвҖқпјҢеҶҚжҸҸеҶҷд»–вҖңжҜҸдәәе®ҡпјҢдёғж—Ҙд№ғиө·вҖқпјҢиҮідәҺдҝ®иЎҢе…·дҪ“еҶ…е®№пјҢ他们еҸҲеҰӮдҪ•жҗһеҫ—жё…жҘҡе‘ўпјҒ
гҖҖгҖҖд»Ҡж №жҚ®жұүи—Ҹж–ҮзҢ®жңүе…іи®°иҪҪ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ә”жҳҜеүҚеҗҺ3ж¬ЎжқҘеҲ°дә”еҸ°еұұгҖӮ第дёҖж¬ЎжҳҜеңЁ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пјҲ1414е№ҙпјүжҳҘеҲ°иҫҫдә”еҸ°еұұпјҢиҖҢдәҺеҪ“е№ҙ12жңҲ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пјҢеә”иҜҸиөҙеҚ—дә¬е…Ҙжңқпјӣ第дәҢж¬ЎжҳҜеңЁж°ёд№җеҚҒдёүе№ҙпјҲ1415е№ҙпјүеӨ§зәҰ5жңҲе·ҰеҸіпјҢд»ҺеҚ—дә¬еҶҚиөҙдә”еҸ°еұұпјҢиҖҢ第дәҢж¬Ў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жҳҜзәҰеңЁж°ёд№җеҚҒеӣӣе№ҙпјҲ1416е№ҙпјүзҡ„з§ӢеӯЈпјӣ第3ж¬ЎжқҘдә”еҸ°еұұжҳҜеңЁжҙӘзҶҷе…ғе№ҙпјҲ1425е№ҙпјүжҲ–е®Јеҫ·е…ғе№ҙпјҲ1426е№ҙпјүеүҚеҗҺпјҢ第дёүж¬Ў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зҡ„ж—¶й—ҙжҳҜзәҰеңЁе®Јеҫ·е…ӯе№ҙпјҲ1431е№ҙпјүгҖӮзӣ®еүҚеҸҜд»Ҙи®Өе®ҡзҡ„жҳҜ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үҚеҗҺ3ж¬ЎдёҠдә”еҸ°еұұдёҚдјҡжңүй”ҷпјҢдҪҶжҜҸдёҖж¬Ўзҡ„е…·дҪ“ж—¶й—ҙиҝҳ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еҲқжӯҘзҡ„жҺЁжөӢпјҢиҝҳжңӣд»ҠеҗҺиғҪеҸ‘зҺ°ж–°зҡ„зәҝзҙўпјҢеҶҚиҝӣдёҖжӯҘжҳҺзЎ®е…·дҪ“ж—¶й—ҙгҖӮ
гҖҖгҖҖ第дәҢдёӘй—®йўҳжҳҜйҮҠиҝҰд№ҹеӨұ3ж¬ЎжқҘдә”еҸ°еұұпјҢй©»й”ЎдәҺе“ӘдёӘеҜәйҷўпјҹжҚ®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Ҹ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иҪҪпјҢиҮӘ然д№ҹжҳҜй©»иөҗдәҺ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иҖғеӨ§жҳҫйҖҡеҜәзҡ„еҺҶеҸІпјҢзҹҘе…¶жӣҫеҗҚдёә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е’ҢвҖңеҚҺдёҘеҜәвҖқпјҢжүҖд»Ҙ笔иҖ…и®Өдёәд»Өз ”з©¶иҖ…еӣ°жғ‘е·Ід№…зҡ„и—Ҹж–ҮеҸІдј дёӯзҡ„еә”дёә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жҲ–вҖңеҚҺдёҘеҜәвҖқд№ӢеҜ№йҹіпјҢиҖҢдё”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дёӯд№ҹи®°иҪҪ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жұүең°дә”еҸ°еұұе…ҙе»әдәҶ6еә§еӨ§еҜәйҷўпјҢ并еңЁвҖңзҫҺжңөеӨҡзғӯвҖқпјҲж„ҸдёәвҖңиҠұеӣӯвҖқпјүйҷ„иҝ‘е»әз«ӢдәҶеҗҚдёәзҡ„еҜәйҷўгҖӮпј»28пјҪй•ҝжңҹд»ҘжқҘпјҢи—ҸеҸІз ”究иҖ…еӣ дёҚжё…жҘҡ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еңЁдҪ•ең°пјҢеӣ иҖҢдёҖиҲ¬иҜ‘д№ӢдёәвҖңжі•йҹіеҜәвҖқпјҢиҝӣиҖҢжҺЁжөӢдёәеҢ—дә¬д№Ӣжі•жёҠеҜәгҖӮ笔иҖ…д»ҘдёәпјҢз”ұи—ҸжұүеҸІж–ҷзӣёдә’е·§еҰҷеҚ°иҜҒпјҢеҸҜд»Ҙж–ӯе®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й©»й”Ўдә”еҸ°еұұд№ӢеҜәйҷўеҚіжҳҜ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пјҢеҚівҖңеҚҺдёҘеҜәвҖқпјҢд№ҹе°ұжҳҜж°ёд№җе№ҙй—ҙзҡ„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е…ідәҺзҡ„жӮ¬еҝөеҸҜд»Ҙе‘ҠдёҖж®өиҗҪ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йҷӨжҳҫйҖҡеҜәгҖҒеӨ§е®қеЎ”еҜәйҷўеӨ–пјҢдё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е…ізі»еҜҶеҲҮзҡ„иҝҳжңүеӨ§еңҶз…§еҜәе’ҢеӨ§ж–Үж®ҠеҜәпјҢиҝҷдёӨеә§еҜәйҷўд№ҹжҳҜдә”еҸ°еұұйҮҚиҰҒзҡ„и—Ҹдј дҪӣж•ҷеҜәйҷўгҖӮ
гҖҖгҖҖ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ідәҺеӨ§еңҶз…§еҜәжүҖй©»жўөеғ§зҡ„и®°иҪҪдё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дәӢиҝ№зӣёеғҸпјҡвҖңжҳҫйҖҡд№Ӣе·ҰпјҢеҸӨз§°жҷ®е®ҒеҜәгҖӮж°ёд№җеҲқпјҢеҚ°еәҰеғ§е®ӨеҲ©жІҷиҖ…жқҘжӯӨеңҹпјҢиҜҸе…ҘеӨ§е–„ж®ҝпјҢеқҗи®әз§°ж—ЁпјҢе°ҒеңҶи§үеҰҷеә”иҫ…еӣҪе…үиҢғеӨ§е–„еӣҪеёҲпјҢиөҗйҮ‘еҚ°пјҢж—Ңе№ўйҒЈйҖҒеҸ°еұұпјҢеҜ“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иҮіе®Јеҫ·еҲқпјҢеӨҚиҜҸе…Ҙдә¬пјҢе№ҝе®Јз§ҳеҜҶгҖӮж— дҪ•пјҢиҫһеҪ’еұұпјҢдёҠжңӘи®ёгҖӮжҳҺж—ҘзӨәеҜӮпјҢдёҠй—»пјҢз—ӣжӮјд№ӢгҖӮеҫЎзҘӯзҒ«еҢ–пјҢж••еҲҶиҲҚеҲ©дёәдәҢгҖӮдёҖеЎ”дәҺйғҪиҘҝпјҢе»әеҜәжӣ°зңҹи§үгҖӮдёҖеЎ”дәҺеҸ°еұұжҷ®е®ҒеҹәпјҢе»әеҜәжӣ°еңҶз…§гҖӮжӯЈеҫ·й—ҙе°Ғеј еқҡеҸӮдёәжі•зҺӢпјҢиөҗ银еҚ°пјҢе…јжңүйғҪзәІеҚ°вҖқгҖӮпј»29пјҪиҝҷж®өи®°иҪҪз®Җзӣҙе°ұжҳҜгҖ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зҡ„еҸҰдёҖдёӘзүҲжң¬пјҢеҸӘжҳҜй”ҷиҜҜд№ӢеӨ„жӣҙеӨҡпјҢйҷҗдәҺж—¶й—ҙпјҢ笔иҖ…иҝҳжңӘеҸҠеҜ№еҸІж–ҷдёӯжүҖж¶үеҸҠзҡ„й—®йўҳиҝӣиЎҢд»”з»ҶиҖғзҙўгҖҒиҫЁжһҗпјҢе…№еӨҮеӯҳејӮиҖҢе·ІгҖӮиҖҢдё”д№ҹжңүе°ҶеңҶз…§еҜәдё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зӣёиҒ”зі»зҡ„дёҖдәӣиҜҙжі•пјҢиҜёеҰӮгҖҠдёӯеӣҪе®—ж•ҷеҗҚиғңгҖӢдёҖд№Ұдёӯзҡ„вҖңеңҶз…§еҜәвҖқдёҖжқЎзҡ„йҮҠж–Үдёӯе°ұиҜҙпјҡвҖңжҳҺж°ёд№җж—¶е–Үеҳӣж•ҷй»„ж•ҷзҘ–еёҲе®—е–Җе·ҙеӨ§ејҹеӯҗи’Ӣе…ЁжӣІе°”и®ЎпјҲеҚіеӨ§ж…Ҳжі•зҺӢд№Ӣи—Ҹж–ҮиҜ‘йҹівҖ”вҖ”笔иҖ…еҠ пјүеҲ°дә”еҸ°з”ұдј жү¬й»„ж•ҷдҪӣжі•еұ…жӯӨеҜәпјҢдёәй»„ж•ҷдј е…Ҙдә”еҸ°еұұд№Ӣе§ӢвҖқгҖӮпј»30пјҪе°ҡдёҚзҹҘе…¶д№ҰдҪңиҖ…жҳҜж №жҚ®д»Җд№Ҳеҫ—жӯӨз»“и®әпјҢжҲ–и®ёеҸ—дәҶдёҠиҝ°и®°иҪҪзҡ„еҪұе“ҚгҖӮ
гҖҖгҖҖеӨ§ж–Үж®ҠеҜәпјҢеҸҲз§°иҸ©иҗЁйЎ¶зңҹе®№йҷўгҖӮжң¬жҳҜе”җд»ЈеҸӨеҲ№пјҢеҺҶд»ЈеұЎжңүдҝ®йҘ°гҖӮиҮіжҳҺж°ёд№җеҲқе№ҙпјҢж••ж—Ёж”№е»әеӨ§ж–Үж®ҠеҜәгҖӮ并вҖңж••иөҗиҙқеҸ¶зҒөж–ҮгҖҒжўөж–Үи—Ҹз»ҸпјҢжңұд№ҰжЁӘеҲ—пјҢеҫЎеҲ¶еәҸиөһгҖӮжҜҸеёҷзӣӣд»Ҙй”ҰеӣҠпјҢзәҰд»Ҙй”ҰжқЎпјҢжҠӨд»Ҙз¶ӘжҜЎгҖӮ并й’ҰйҖ ж–Үж®Ҡй•ҖйҮ‘еғҸвҖқгҖӮпј»31пјҪиҮідёҮеҺҶе№ҙй—ҙзҡҮеёқиҝҳе‘ҪеӨӘзӣ‘жқҺеҸӢйҮҚдҝ®еӨ§ж–Үж®ҠеҜәгҖӮеңЁжҳҺжңқе»·зҡ„жү¶жӨҚдёӢпјҢж–Үж®ҠеҜәзҡ„ең°дҪҚи¶ҠеҠ жҳҫиө«пјҢеҲ°жё…еҲқж—¶пјҢе·ІеңЁдә”еҸ°еұұдј—еӨҡзҡ„и—Ҹдј дҪӣж•ҷеҜәйҷўдёӯеӨ„дәҺйҰ–иҰҒең°дҪҚгҖӮ
гҖҖгҖҖ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еұ…з•ҷжңҹй—ҙжүҖд»ҺдәӢзҡ„жі•дәӢжҙ»еҠЁпјҢжҚ®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еҸҠ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зӯүи®°иҪҪпјҢдё»иҰҒжңүд»ҘдёӢеҮ ж–№йқўеҶ…е®№пјҡ
гҖҖгҖҖ1гҖҒ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еҮ е№ҙжҳҜдә”еҸ°еұұи—Ҹдј дҪӣж•ҷзҡ„з№ҒиҚЈеҸ‘еұ•ж—¶жңҹгҖӮйҮҠиҝҰд№ҹеӨұжүҖеҒҡзҡ„йҮҚиҰҒе·ҘдҪңд№ӢдёҖе°ұжҳҜдҝ®е»әеҜәйҷўгҖӮи—Ҹж–Үж–ҮзҢ®дёӯиЁҖ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дҝ®е»ә6еә§еҜәйҷўпјҢжүҖи°“дҝ®е»әе®һйҷ…дёҠжҳҜжҢҮдҝ®и‘әжҲ–ж”№жү©е»әпјҢ6еә§еҜәйҷўеӨ§жҰӮеҢ…жӢ¬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ҒеӨ§е®қеЎ”йҷўеҜәгҖҒеӨ§еңҶз…§еҜәе’ҢеӨ§ж–Үж®ҠеҜәзӯүгҖӮз”ұдә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ёҺжңқе»·еҸҠжҳҺжҲҗзҘ–дёӘдәәзҡ„дәІеҜҶе…ізі»пјҢе»әеҜәжүҖйңҖиө„иҙўдё»иҰҒжҳҜз”ұжңқе»·дҫӣз»ҷпјҢд№ҹжңүйғЁеҲҶжҳҜдҝЎеҫ’дҫӣж–Ҫзҡ„гҖӮ
гҖҖгҖҖ2гҖҒжҚ®з§°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дҝ®жі•жңҹй—ҙпјҢдәІи§Ғж–Үж®ҠиҸ©иҗЁпјҢ并且照и§ҒдәҶйҳҝеә•еіЎеёҲеҫ’еҸҠдёҠеёҲе…«жҖқе·ҙгҖӮйҖҡиҝҮй•ҝжңҹзҡ„иә«гҖҒиҜӯгҖҒж„ҸдёүеҜҶзҡ„дҝ®иЎҢпјҢзү№еҲ«жҳҜи§Ӯжғізҡ„дҝ®иЎҢпјҢжңҖеҗҺиҫҫеҲ°е…Ҙе®ҡпјҢеҚіжҳҜдёҖз§Қи—ҸеҜҶдҝ®жҢҒзҡ„жңҖй«ҳжі•й—ЁжҲ–жңҖй«ҳеўғз•ҢпјҢиҝҗз”ЁвҖңиҪ¬иҜҶжҲҗжҷәвҖқзҡ„еҺҹзҗҶпјҢеј•еҸ‘ж„ҸиҜҶжҪңиғҪиҖҢиҫҫеҲ°и¶…然зү©еӨ–зҡ„еўғз•ҢгҖӮеҚіе…Ҳз”ұж„ҸиҜҶзҡ„дёҖеҝөдё“зІҫзҡ„и§ӮжғіејҖе§ӢпјҢеҶҚ次第ең°иҪ¬еҸҳеӣәжңүзҡ„д№ ж°”пјҢжһ„жҲҗиҮӘжҲ‘超然зҺ°е®һзҡ„зІҫзҘһеўғз•ҢгҖӮеңЁи—Ҹж—Ҹй«ҳеғ§еҸІдј дёӯдёҚд№ҸжңүдәІи§Ғж–Үж®ҠиҸ©иҗЁзҡ„и®°иҪҪпјҢиҜёеҰӮе…ғеёқеёҲе…«жҖқе·ҙгҖҒе®—е–Җе·ҙеӨ§еёҲгҖҒдә”дё–DLе–Үеҳӣзӯүи—Ҹдј дҪӣж•ҷйўҶиў–зә§зҡ„дәәзү©йғҪжңүжӯӨзұ»з»ҸеҺҶпјҢдәІи§Ғж–Үж®ҠиҸ©иҗЁеҮ д№ҺжҲҗдәҶдҝ®иЎҢеҜҶжі•иҮіжңҖй«ҳеўғз•Ңзҡ„дёҖз§Қж Үеҝ—гҖӮдҪҶз”ұдәҺеҫҲйҡҫд»ҺзҗҶи®әдёҠи§ЈйҮҠе…¶дёӯзҡ„еҘҘз§ҳпјҢз ”з©¶иҖ…д№ҹеӨҡеҚҠйҒҝејҖжӯӨзұ»иҜқйўҳгҖӮ
гҖҖгҖҖйҮҠиҝҰд№ҹеӨұжҳҜдёҖдҪҚеҜҶжі•дҝ®жҢҒзҡ„еӨ§еёҲпјҢжұүж–Үдј и®°дёӯиЁҖе…¶еңЁдә”еҸ°еұұвҖңжҜҸе…Ҙе®ҡпјҢдёғж—Ҙд№ғиө·вҖқпјҢи¶ід»ҘиҜҙжҳҺд»–зҡ„е®ҡеҠӣйқһеҗҢеҜ»еёёгҖӮиҖҢи—Ҹж–Үж–ҮзҢ®дёӯжӣҙе°Ҷд»–зҡ„еҜҶжі•дҝ®жҢҒзҡ„еҠҹеӨ«иҜҙеҫ—зҘһд№Һе…¶зҘһпјҢиҜҙвҖңд»–е°ҶдёҖзүҮеқҡзЎ¬зҡ„йқ’зҹіжқҝеғҸзЁҖжіҘдёҖж ·жҗ“жқҘжҸүеҺ»пјҢеңЁзҹіжқҝдёҠз•ҷдёӢдәҶжүӢеҚ°пјҢдҪҝеҪјж–№д№Ӣдј—з”ҹеӨ§дёәжғҠејӮвҖқпјҢдә‘дә‘гҖӮпј»32пјҪ
гҖҖгҖҖ3гҖҒ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еұ…з•ҷдә”еҸ°еұұжңҹй—ҙпјҢз»ҸеёёдёәжқҘиҮӘеҗ„ең°зҡ„дҝЎдј—пјҲе…¶дёӯеҢ…жӢ¬и®ёеӨҡең°ж–№е®ҳе‘ҳгҖҒи’ҷеҸӨзҺӢе…¬пјүзӯүдј жҺҲзҒҢйЎ¶жі•пјҢеҗҢж—¶иҝҳдёәеғ§дәәдј жҺҲиҝ‘дәӢгҖҒжІҷејҘгҖҒжҜ”дёҳгҖҒзҰҒйЈҹзӯүжҲ’еҫӢпјҢвҖңжҢү照他们еҗ„иҮӘзҡ„зјҳеҲҶйҷҚдёӢдҪӣжі•д№Ӣз”ҳйӣЁпјҢеј•йўҶ他们иө°дёҠжҲҗзҶҹи§Ји„ұд№ӢйҒ“вҖқгҖӮпј»33пјҪдёӯеӣҪжңүеҸҘдҝ—иҜӯпјҡвҖңиҝңжқҘе’Ңе°ҡдјҡеҝөз»ҸвҖқгҖӮи—Ҹеғ§иҝңжқҘиҮӘйӣӘеҹҹй«ҳеҺҹпјҢжңүдёҖж•ҙеҘ—зӢ¬зү№зҡ„ж–ҮеҢ–дј жүҝпјҢзү№еҲ«жҳҜи—Ҹдј дҪӣж•ҷдёӯзҡ„еҜҶе®—д№Ӣд»ӘиҪЁз№ҒжқӮзҘһз§ҳгҖҒеҘҘеҰҷй«ҳж·ұпјҢеҫҲиғҪд»Өдәәеҝғеҗ‘еҫҖд№ӢгҖӮе№іж°‘зҷҫ姓гҖҒе–„з”·дҝЎеҘідёәзҘҲзҰҸзҰізҒҫеүҚжқҘйЎ¶зӨјпјӣиҖҢеҜ№жұүең°е№ҝеӨ§зҡ„еғ§дәәжқҘиҜҙпјҢиҝҪжұӮвҖңеҚіиә«жҲҗдҪӣвҖқзҡ„и—Ҹдј еҜҶж•ҷд№ҹжҳҜйҡҫд»ҘжҠөжҢЎзҡ„иҜұжғ‘гҖӮе…ідә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дёәдҝЎдј—дј жҺҲеҜҶжі•д»ҘеҸҠдёәејҹеӯҗдј жҺҲжҲ’жі•дәӢпјҢж–ҮзҢ®дёӯжІЎжңүиҜҰз»Ҷи®°иҪҪпјҢдҪҶеңЁж°ёд№җе№ҙй—ҙд»ҺзҡҮеёқеҲ°жңқиҮЈпјҢзү№еҲ«жҳҜе®Ұе®ҳеҜ№и—Ҹдј дҪӣж•ҷзҡ„зӨјж•¬зЁӢеәҰжқҘжҺЁжөӢпјҢеүҚжқҘиҰҒжұӮзҡҲдҫқзҒҢйЎ¶зҡ„дҝЎеҫ’дёҖе®ҡеҫҲеӨҡ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дә”еҸ°еұұпјҢи—Ҹдј дҪӣж•ҷзңҹжӯЈеҪўжҲҗ规模еҢ–зҡ„еҸ‘еұ•пјҢеҚіжҳҜд»ҺжҳҺж°ёд№җе№ҙй—ҙејҖе§ӢпјҢзӣёжҜ”иҫғиҖҢиЁҖ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еұ…дҪҸж—¶й—ҙиҫғй•ҝпјҢеҪұе“Қд№ҹиҫғеӨ§гҖӮеӣ жңүжңқе»·зҡ„жү¶жҢҒпјҢжң¬жқҘеҗ‘еҫҖдә”еҸ°еұұзҡ„и’ҷи—ҸдҝЎдј—й©ұиө¶й©јгҖҒ马гҖҒзүӣгҖҒзҫҠж•°еҚғйҮҢиҖҢжңқеұұиҝӣйҰҷиҖ…пјҢжӘҖж–Ҫдә‘йӣҶпјҢз»ңз»ҺдёҚз»қгҖӮиҮӘе…№д»ҘйҷҚпјҢж јйІҒжҙҫ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еҸ‘еұ•ж—Ҙи¶Ӣе…ҙзӣӣгҖӮжҚ®з»ҹи®ЎпјҢиҮіжё…жңқдё–е®—йӣҚжӯЈж—¶пјҢдә”еҸ°еұұ仅规模иҫғеӨ§зҡ„и—Ҹдј дҪӣж•ҷеҜәеәҷе°ұжңү26еә§пјҢеғ§дәәеҚғдҪҷд№ӢеӨҡгҖӮеҲ°ж°‘еӣҪж—¶жңүвҖңй»„иЎЈеғ§пјҲжҢҮи—Ҹдј дҪӣж•ҷж јйІҒжҙҫеғ§дәәпјүеӨ§еҜәе…ӯдёғпјҢдёӯе°Ҹж•°еҚҒпјҢз»ји®Ўеғ§еҫ’зәҰдёүеӣӣеҚғдәәвҖқгҖӮпј»34пјҪ
гҖҖгҖҖе…ӯгҖҒжҳҺжҲҗзҘ–еҶҷз»ҷ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еӣӣе°Ғд№ҰдҝЎ
гҖҖгҖҖжұүж–ҮеҸІдј дёӯиЁҖеҸ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жңҹй—ҙпјҢзҡҮеёқвҖңж•°еҲ¶д№ҰйҒЈдҪҝиҮҙж…°вҖқпјҢеңЁ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жё…жҘҡең°и®°иҝ°дәҶжҳҺжҲҗзҘ–еҸҠе®Је®—зҡҮеёқжӣҫеҮ ж¬ЎиҮҙеҮҪ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еҶ…е®№пјҢз•Ҙиҝ°еҰӮдёӢпјҡ
гҖҖгҖҖж°ёд№җеҚҒдёүе№ҙпјҲ1415е№ҙпјүе…ӯжңҲпјҢвҖңдёҠеҲ¶д№ҰдәҺдә”еҸ°еҰҷи§үеңҶйҖҡж…§ж…Ҳжҷ®еә”иҫ…еӣҪжҳҫж•ҷзҒҢйЎ¶ејҳе–„иҘҝеӨ©дҪӣеӯҗеӨ§еӣҪеёҲйҮҠиҝҰд№ҹеӨұвҖқгҖӮдҝЎ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зӣёеҲ«йҒҪе°”ж•°жңҲпјҢжғіеҫ’д»Һе·ІиҫҫеҸ°еұұпјҢе®ҙеқҗй«ҳеі°пјҢзҘһжёёе…«жһҒпјҢдёҺж–Үж®ҠиҖҒдәәзҝұзҝ”дәҺеӨ§жј д№Ӣд№ЎпјҢ超然дәҺдёҮеҢ–д№Ӣе§ӢгҖӮжң•еІӮиғңзң·еҝөпјҢи–„иөҚз“ңжһңпјҢд»Ҙи§ҒжүҖжҖҖйҒЈд№ҰеҢҶеҢҶпјҢж•…дёҚеӨҡиҮҙ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ж°ёд№җеҚҒдә”е№ҙпјҲ1417е№ҙпјүз§ӢпјҢвҖңдёҠеҲ¶д№ҰеҰҷи§үеңҶйҖҡеӣҪеёҲвҖқгҖӮдҝЎ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з§ӢйЈҺжҫ„иӮғпјҢдә”еҸ°ж—©еҜ’пјҢиҝңжғҹдҪӣеўғжё…иҷҡпјҢжі•дҪ“е®үжі°гҖӮд»ҠеҲ¶иўҲиЈ…зҰ…иЎЈпјҢйҒЈдҪҝзҘ—йҖҒпјҢд»ҘиЎЁжң•жҖҖвҖқпјҢдҝЎжң«е°ҫеӨ„вҖңеҲ—ејӮиүІиЎЈе…«з§Қ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ж°ёд№җеҚҒдёғе№ҙпјҲ1419е№ҙпјүпјҢвҖңдёҠеҲ¶д№ҰеҰҷи§үеңҶйҖҡеӣҪеёҲвҖқгҖӮдҝЎ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иҮӘеёҲиҘҝиЎҢпјҢеҝҪи§Ғж–°еІҒпјҢдҪҝиҖ…иҝҳпјҢд№ғзҹҘеұҘеҶөе®үзҹҘпјҢйҖӮж…°жң•жҖҖгҖӮе…№д»Ҙй•ҖйҮ‘иҺІеә§пјҢз”ЁиЎЁиҝңиҙ¶пјҢ并系д№ӢиөһвҖқ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зңҒз•ҘдәҶиөһж–ҮгҖӮ
гҖҖгҖҖж°ёд№җеҚҒд№қе№ҙпјҲ1421е№ҙпјүеӨҸпјҢвҖңдёҠеҲ¶д№ҰеҰҷи§үеңҶйҖҡеӣҪеёҲвҖқгҖӮдҝЎ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жң•жғҹеӨ§еёҲпјҢи§үиЎҢеңҶиһҚпјҢж…ҲжӮІеҲ©жөҺгҖӮжң•еҝғзһ»дјҒпјҢеӨҷеӨңдёҚеҝҳгҖӮе…№д»ҘеІҒеәҸз»ҙж–°пјҢзү№йҒЈзҰ…еёҲзҸӯз«№зӯүпјҢзҘқиөһдәҺжң•пјҢ并д»ҘдҪӣеғҸзӯүзү©жқҘпјҢйүҙе…№еӢӨиҜҡпјҢиүҜж·ұеҳүжӮҰгҖӮд»ҠйҒЈеҶ…е®ҳжҲҙе…ҙзӯүпјҢиөҚдҪӣеғҸзӯүзү©пјҢ并иҮҙеҒҲиөһпјҢз”ЁиЎЁжң•жҖҖвҖқгҖӮиөһж–ҮдәҰз•ҘиҖҢдёҚеҪ•гҖӮпј»35пјҪ
гҖҖгҖҖзңҹдёҚзҹҘеҰӮдҪ•ж„ҹи°ўжҳҺдёҮеҺҶе№ҙй—ҙдә”еҸ°еұұз«№жһ—еҜәзҡ„иҝҷдҪҚй•Үжҫ„е’Ңе°ҡ1547пҪһ1617е№ҙпјүпјҢпј»36пјҪеңЁд»–з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дҝқеӯҳдәҶеҰӮжӯӨйҮҚиҰҒзҡ„еҸІж–ҷпјҢзңҹжӯЈејҘиЎҘдәҶжұүи—ҸеҸІж–ҷи®°иҪҪдёӯйҮҚеӨ§зҡ„зјәжҶҫгҖӮ笔иҖ…и®ӨдёәпјҢиҝҷдәӣи®°иҪҪжҳҜеҸҜд»ҘдҝЎд»»зҡ„пјҢй•Үжҫ„иҷҪж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жҷҡз”ҹдёҖдёӘдё–зәӘпјҢдҪҶд»ҚеұһеҗҢж—¶д»ЈдәәпјҢиҷҪ然ж•ҷжҙҫжңүејӮпјҢдҪҶд»–жҠ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ҹдҪңдёәдә”еҸ°еұұеғ§дәәгҖӮдә”еҸ°еұұиҷҪеҫ—еҲ°еҺҶд»ЈжңҖй«ҳз»ҹжІ»иҖ…зҡ„е…іжҠӨпјҢдҪҶжҜ”иө·йӮЈдәӣдҪ“зҺ°зҡҮжқғеЁҒдёҘзҡ„иҜҸиҜ°ж••е‘Ҫд№Ӣзұ»пјҢжҳҺжҲҗзҘ–еҶҷз»ҷ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д№ҰдҝЎеҲҷжҳҜеҰӮжӯӨзҡ„е№іжҳ“дҪ“иҙҙпјҢи°ҰжҒӯжңүеҠ пјҢе®һеңЁжҳҜд»Өдәәж„ҹеҠЁгҖӮ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еҮә家еғ§дәәпјҢжҫ„й•ҮжӣҙдјҡжҠҠиҝҷдәӣзҸҚиҙөзҡ„д№ҰдҝЎзңӢдҪңжҳҜдә”еҸ°еұұзҡ„дёҖд»ҪиҚЈе…үе’ҢиҮӘиұӘгҖӮйӮЈдәӣдҝ®жӯЈеҸІиҖ…иҮӘ然дёҚж„ҝи§ҒеҲ°д»–们дёүжӢңд№қеҸ©гҖҒиҮій«ҳж— дёҠзҡ„зҡҮеёқеҶҷиҝҷж ·зҡ„д№ҰдҝЎз»ҷдёҖдҪҚи—Ҹж—Ҹеғ§дәәпјҢжҜҸжҜҸжңүж„Ҹи®ійҘ°пјҢеҚҙж–ҷдёҚеҫ—д»ҚеңЁ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з•ҷдёӢдәҶиӣӣдёқ马иҝ№пјҢзңҹеҸҜи°“еұұй«ҳзҡҮеёқиҝңе•ҠпјҒиҒ”жғіеҲ°дҝқеӯҳеңЁи—Ҹж–ҮеҸІзұҚдёӯжҳҺжҲҗзҘ–еҶҷз»ҷе®—е–Җе·ҙеҸҠеӨ§е®қжі•зҺӢзҡ„д№ҰдҝЎпјҢд№ҹжҳҜејӮжӣІеҗҢе·ҘгҖӮ
дёҠиҝ°жҳҺжҲҗзҘ–еҶҷз»ҷ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4е°ҒдҝЎд»¶дёӯпјҢеүҚ2ж¬ЎжҳҜйҒЈдҪҝйҖҒеҫҖдә”еҸ°еұұйҮҠиҝҰд№ҹеӨұй©»й”Ўд№ӢжүҖпјҢдҝЎдёӯ委е©үиЎЁиҫҫдәҶ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зң·еҝөд№Ӣжғ…пјҢиҜӯж°”иҜҡжҒіпјҢдҪ“жҒӨе…Ҙеҫ®гҖӮдјҙйҡҸзқҖ2е°Ғд№ҰдҝЎзҡ„зӨјзү©жҳҜж¶Ҳжҡ‘зҡ„з“ңжһңе’ҢеҫЎеҜ’зҡ„иўҲиЈҹзҰ…иЎЈгҖӮеӨҡе°‘жңүдәӣз–‘й—®зҡ„жҳҜ第дәҢе°Ғд№ҰдҝЎжҳҜеҶҷдәҺж°ёд№җеҚҒдә”е№ҙз§ӢпјҢеҰӮжһңиҝҷдёҖж—¶й—ҙзЎ®еҲҮж— иҜҜпјҢеҲҷйҮҠиҝҺиҝҰеӨұжӯӨеҗҺиҝ…еҚіеҗҜзЁӢиҝ”еҪ’д№ҢжҖқи—ҸпјҢиҮіз§ӢеҶ¬д№Ӣйҷ…жҠөиҫҫжӢүиҗЁз”ҳдё№еҜәгҖӮиҖҢгҖҠжҳҺе®һеҪ•гҖӢдёӯжҳҺзЎ®и®°иҪҪпјҢж°ёд№җеҚҒеӣӣе№ҙпјҲ1416е№ҙпјүдә”жңҲ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иҫһеҪ’гҖӮдёӨз§Қи®°иҪҪдёӯжңүдёҖе№ҙеӨҡзҡ„е·®иҜҜгҖӮ笔иҖ…д»Ҙдёә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иҫһеҪ’д№ӢдәӢпјҢжҳҜдёҖ件еҚҒеҲҶйҮҚеӨ§зҡ„дёҫеҠЁпјҢйңҖиҰҒжҸҗж—©зҰҖе‘Ҡжңқе»·пјҢд»Ҙдҫҝжңқе»·еҒҡеҮәзӣёеә”зҡ„е®үжҺ’дёҫжҺӘгҖӮд»Һи—ҸжұүеҸІзұҚдёӯйғҪеҚ°иҜҒжҳҺжҲҗзҘ–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иөҸиөҗеҚҒеҲҶдё°еҺҡпјҢзү№еҲ«еҢ…жӢ¬йҮ‘жұҒд№ҰеҶҷзҡ„гҖҠи—Ҹж–ҮеӨ§и—Ҹз»ҸгҖӢе’ҢеҚҒе…ӯж—ғжӘҖе°ҠиҖ…еғҸзӯүпјҢжңқе»·дёҚд»…йңҖиҰҒж—¶й—ҙеҮҶеӨҮиҝҷдәӣзү©е“ҒпјҢиҖҢдё”иҝҳиҰҒе®үжҺ’зӣёеә”зҡ„д»Әд»—йҖҒе…¶д»ҺйғҪеҹҺеҚ—дә¬жҠөдә”еҸ°еұұпјҢз”ұдәҺдәӨйҖҡзјҳж•…пјҢд»Һд№ҢжҖқи—ҸеҲ°еҶ…ең°зҡ„еҫҖиҝ”еёёеңЁж·ұз§ӢиҮіеҶ¬еӯЈпјҢеҰӮжһңй”ҷиҝҮдәҶеҗҲйҖӮж—¶й—ҙпјҢжӣҙй•ҝж—¶й—ҙзҡ„延жҗҒд№ҹжҳҜйЎәзҗҶжҲҗз« гҖӮиҖҢиҖғ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зӯүи—Ҹж–ҮеҸІдј еҫ—зҹҘ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д№ҹзЎ®е®һжҳҜж°ёд№җеҚҒдә”е№ҙж·ұз§Ӣж—¶д»ҺеҶ…ең°иҝ”еҪ’д№ҢжҖқи—Ҹзҡ„гҖӮеӣ иҖҢпјҢ笔иҖ…д»Ҙдёәе®һеҪ•жүҖи®°ж—¶ж—Ҙжҳ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җ‘жңқе»·зҰҖе‘ҠиҫһеҪ’зҡ„ж—Ҙжңҹ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д»Һдә”еҸ°еұұиҝ”и—Ҹзҡ„ж—¶ж—ҘгҖӮ
гҖҖгҖҖжҳҺжҲҗзҘ–зҡ„еҸҰеӨ–2е°ҒдҝЎжҳ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иҝ”еҪ’д№ҢжҖқи—ҸеҗҺеҶҷзҡ„гҖӮж°ёд№җеҚҒдёғе№ҙпјҲ1419е№ҙпјүжҳҘеӨ©зҡ„дҝЎдёӯиЎЁиҫҫдәҶжҳҺжҲҗзҘ–еҫ—зҹҘ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үе…ЁжҠөиҫҫд№ҢжҖқи—ҸеҗҺзҡ„ж…°й—®д№Ӣжғ…пјҢйҡҸдҝЎиөҗиө й•ҖйҮ‘иҺІиҠұеә§пјҢеӨ§жҰӮжҳҜдёә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Қіе°Ҷдё»жҢҒдҝ®е»әиүІжӢүеҜәзҡ„иҙәзӨјпјӣж°ёд№җеҚҒд№қе№ҙпјҲ1421е№ҙпјүеӨҸеӯЈзҡ„жҳҜдёҖе°Ғ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жүҖиЎЁзҺ°зҡ„еҜ№зҡҮеёқвҖқеӢӨиҜҡвҖқзҡ„иөһжү¬е’ҢеӣһиөҗгҖӮд»ҺдҝЎеҮҪеҶ…е®№еҸҜзҹҘ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жӣҫзү№жҙҫзҰ…еёҲжқҝз«№еҗ‘жҳҺжҲҗзҘ–зҘқиөһпјҢ并иҙЎзҢ®дҪӣеғҸпјҢжҲҗзҘ–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жӯӨдёҫвҖңиүҜж·ұеҳүжӮҰвҖқпјҢеӣ иҖҢжҙҫйҒЈеҶ…е®ҳжҲҙе…ҙиөҙд№ҢжҖқи—ҸпјҢдҪҝиҖ…йҖҒеҺ»жҲҗзҘ–еҶҷз»ҷ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дҝЎеҮҪиөһж–ҮпјҢеҗҢж—¶еёҰеҺ»жҲҗзҘ–еӣһиөҗзҡ„дҪӣеғҸзӯүзӨјзү©гҖӮеҶ…е®ҳжҲҙе…ҙеңЁж°ёд№җдәҢеҚҒдёҖе№ҙпјҲ1423е№ҙпјүжӣҫеҮәдҪҝд№ҢжҖқи—ҸпјҢжҳҜдёҺйҳҗеҢ–зҺӢжүҺе·ҙеқҡиөһжүҖйҒЈжңқиҙЎдҪҝиҮЈдёҖйҒ“еҺ»и—Ҹең°пјҢд»»еҠЎжҳҜеёҰеҺ»зҡҮеёқз»ҷйҳҗеҢ–зҺӢзҡ„ж••е‘ҪдёҺеӣһиөҗгҖӮпј»37пјҪдҪҶж°ёд№җеҚҒд№қе№ҙиҝҷдёҖж¬ЎеҮәдҪҝпјҢе®һеҪ•дёӯзјәиҪҪгҖӮ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зҡ„иҝҷе°ҒдҝЎдҪҝ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гҖҒ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зӯүи—Ҹж–ҮеҸІдј дёӯе…ідәҺж°ёд№җеҚҒд№қе№ҙпјҲиҫӣдё‘пјҢи—ҸеҺҶй“Ғзүӣе№ҙпјүвҖңеҸҲжңүеӨ§зҡҮеёқжүҖжҙҫиҝҺиҜ·дҪҝиҖ…еүҚжқҘвҖқ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Ҷ委任ејҹеӯҗиҫҫеҗүжЎ‘еёғдёәиүІжӢүеҜә第дәҢд»»жі•еҸ°пјҢиҮӘе·ұжҗәејҹеӯҗйҳҝжңЁеҷ¶зӯүйҡҸдҪҝиҖ…еҶ…е®ҳжҲҙе…ҙзӯүеүҚеҫҖжұүең°зҡ„и®°иҪҪжңүдәҶж №жҚ®гҖӮд»ҺдёҠиҝ°дҝЎж–ҮеҶ…е®№жқҘзңӢпјҢжҳҺжҲҗзҘ–зЎ®е®һиЎЁзӨәдәҶ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иғҪеӨҹеҶҚж¬ЎжқҘжңқзҡ„вҖңзһ»дјҒвҖқд№Ӣжғ…гҖӮжңүдәҶеӨ§зҡҮеёқзҡ„иҝҷд»ҪиҜҡж„Ҹ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жүҚз«ӢеҚіеҒҡеҮәе®үжҺ’пјҢжһңж–ӯең°йҡҸдҪҝиҮЈеҶҚж¬ЎдёңжқҘеҶ…ең°гҖӮ
жіЁйҮҠпјҡ
в‘ гҖҠе…ғеҸІгҖӢеҚ·дәҢв—ӢдәҢгҖҠйҮҠиҖҒеҝ—гҖӢгҖӮ
в‘ЎгҖҠеҚ—и—ҸгҖӢеҸҲз§°гҖҠжҳҺеҚ—жң¬еӨ§и—Ҹз»ҸгҖӢпјҢиҜҘи—ҸеҲ»дәҺж°ёд№җеҚҒе№ҙпјҲ1412е№ҙпјүиҮіеҚҒдә”е№ҙпјҲ1417е№ҙпјүпјҢе…ұ636еҮҪпјҢ收еҗ„зұ»дҪӣж•ҷи‘—дҪң1610йғЁгҖҠеҢ—и—ҸгҖӢеҸҲз§°гҖҠжҳҺеҢ—жң¬еӨ§и—Ҹз»ҸгҖӢпјҢж°ёд№җеҚҒд№қе№ҙпјҲ1421е№ҙпјүиҝҒйғҪеҢ—дә¬еҗҺпјҢжҳҺжҲҗзҘ–дёӢд»ӨйҮҚж–°зј–йӣҶеӨ§и—Ҹз»ҸпјҢиҮіжӯЈз»ҹдә”е№ҙпјҲ1440е№ҙпјүз»Ҳе‘Ҡе®ҢжҲҗпјҢ收д№Ұ1621йғЁгҖӮ
в‘ўеҸӮи§Ғй»„жҳҺдҝЎпјҡгҖҠж°‘ж—Ҹж–ҮеҢ–е®«еӣҫд№ҰйҰҶи—Ҹи—Ҹж–Үе…ЁйӣҶжҖ»зӣ®еҪ•еәҸгҖӢжӢүиҗЁзҺ°и—Ҹжңү2йғЁж°ёд№җзүҲгҖҠи—Ҹж–ҮеӨ§и—Ҹз»ҸгҖӢпјҢе…¶дёӯдёҖйғЁи—ҸдәҺеёғиҫҫжӢүе®«пјҲеҺҹи—ҸдәҺиҗЁиҝҰеҜәпјүпјҢж°ёд№җеҚҒдёҖе№ҙпјҲ1413е№ҙпјүз”ұжҳҺжҲҗзҘ–иөҗдәҲиҗЁиҝҰжҙҫй«ҳеғ§гҖҒжҳҺе°ҒеӨ§д№ҳжі•зҺӢиҙЎеҷ¶жүҺиҘҝпјӣеҸҰдёҖйғЁи—ҸдәҺиүІжӢүеҜәпјҢеҚіж°ёд№җеҚҒеӣӣе№ҙпјҲ1416е№ҙпјүз”ұжҳҺжҲҗзҘ–иөҗдәҲж јйІҒжҙҫй«ҳеғ§гҖҒе®—е–Җе·ҙејҹеӯҗгҖҒжҳҺе°ҒеӨ§ж…Ҳжі•зҺӢйҮҠиҝҰд№ҹеӨұгҖӮ
в‘Ј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ёүгҖӮ
в‘Өе–»и°Ұпј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еҚ·еҚҒд№қпјҢгҖҠжҳҺдә”еҸ°еұұжҳҫйҖҡеҜәжІҷй—Ё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гҖӮ
в‘ҘеҸӮзңӢдҪ•еӯқиҚЈпјҡгҖҠжҳҺд»ЈеҚ—дә¬еҜәйҷўз ”究гҖӢпјҢ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еҮәзүҲзӨҫ2000е№ҙзүҲпјҢ第35йЎөгҖӮжҢүжҳҺиҝҒйғҪеҢ—дә¬еҗҺпјҢеҚ—дә¬иғҪд»ҒеҜәд»ҚеӯҳгҖӮеҢ—дә¬зҡ„еӨ§иғҪд»ҒеҜәжӯЈжҳҜжүҝиўӯеҚ—дә¬иғҪд»ҒеҜәиҖҢжқҘпјҢиҜҘеҜәеңЁеҢ—дә¬иҘҝеҹҺе…ө马еҸёиғЎеҗҢд»ҘеҢ—пјҢе…¶ең°еӣ еҜәиҖҢеҗҚдёәиғҪд»ҒеҜәиғЎеҗҢгҖӮеҢ—дә¬еӨ§иғҪд»ҒеҜәд»Ҡе·ІдёҚеӯҳгҖӮ
в‘ҰгҖҠйҮ‘йҷөжҘҡеҲ№еҝ—гҖӢеҚ·еҚҒе…ӯпјӣпјҲжҳҺпјүеҚ—зҘ йғЁйғҺй’ұеЎҳи‘ӣеҜ…дә®пјҡгҖҠе…«еӨ§еҜәйҮҚи®ҫе…¬еЎҫзў‘и®°гҖӢгҖӮ
⑧йҷҲжҘ пјҡгҖҠжҳҺеҲқеә”иҜҸдҪҝи—Ҹй«ҳеғ§е®—жіҗдәӢиҝ№иҖғеҸҷгҖӢпјӣйҷҲжҘ пјӣгҖҠи—ҸеҸІдёӣиҖғгҖӢпјҢж°‘ж—ҸеҮәзүҲзӨҫ1998е№ҙзүҲпјҢ第202гҖҒ222йЎөгҖӮ
гҖҖгҖҖи°ўйҮҚе…үгҖҒзҷҪж–ҮеӣәпјҡгҖҠдёӯеӣҪеғ§е®ҳеҲ¶еәҰеҸІгҖӢ第249йЎөпјҡвҖңж°ёд№җиҝҒйғҪд»ҘеҗҺеҪўжҲҗдәҶеҢ—дә¬е’ҢеҚ—дә¬дёӨеҘ—ж”ҝеәңжңәжһ„пјҢеҸҚжҳ еңЁеғ§е®ҳдҪ“еҲ¶дёӯпјҢдәҰжңүеҢ—дә¬еғ§еҪ•еҸёе’ҢеҚ—дә¬еғ§еҪ•еҸёд№ӢеҲ«гҖӮеҢ—дә¬еғ§еҪ•еҸёжҳҜеғ§еҸёжӯЈжң¬жүҖеңЁгҖӮвҖқ
в‘ЁгҖҠжҳҺеӨӘзҘ–е®һеҪ•гҖӢеҚ·дёҖдёғе…ӯпјҢжҙӘжӯҰеҚҒе…«е№ҙеҚҒдәҢжңҲдёҒе·іпјҡвҖңе»әйёЎйёЈеҜәдәҺйёЎйёЈеұұпјҢд»ҘзҘ жўҒеғ§е®қе…¬пјҢе‘Ҫеғ§еҫ·з‘„дҪҸжҢҒгҖӮз‘„еҚ’пјҢйҒ“жң¬з»§д№ӢгҖӮеҲқпјҢжңүиҘҝз•Әеғ§жҳҹеҗүзӣ‘и—ҸдёәеҸіи§үд№үпјҢеұ…жҳҜеұұпјҢиҮіжҳҜпјҢеҲ«дёәйҷўеҜәиҘҝд»Ҙеұ…д№ӢвҖқгҖӮжҢүпјҡи§үд№үдёәеғ§еҪ•еҸёиЎҷзҪІең°дҪҚиҫғдҪҺзҡ„еғ§е®ҳгҖӮжҳҺж°ёд№җзҡҮеёқзӯүз»Ҹеёёд»ҘвҖңйўқеӨ–зјәвҖқзҡ„ж–№жі•жҠҠеғ§еҪ•еҸёдёӯзҡ„вҖңи®Із»ҸвҖқгҖҒвҖңи§үд№үвҖқзӯүе“ҒдҪҚиҫғдҪҺзҡ„еғ§иҒҢжҺҲз»ҷиҘҝз•Әе–Үеҳӣеғ§дәәпјҢдёҚеӨұдёәдёҖз§ҚзҫҒзё»з¬јз»ңзҡ„жүӢж®өгҖӮ
в‘©гҖҠйҮ‘йҷөжўөеҲ№еҝ—В·й’ҰеҪ•йӣҶгҖӢгҖӮ
пј»11пјҪеӣәе§Ӣеҷ¶дёҫе·ҙВ·жҙӣжЎ‘жіҪеҹ№пјҡ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пјҢйҷҲеәҶиӢұгҖҒд№ҢеҠӣеҗүиҜ‘жіЁ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90е№ҙзүҲпјҢ第62йЎөгҖӮ
пј»12пјҪеҗҢжіЁпј»11пјҪгҖӮ
пј»13пјҪеҗҢжіЁпј»12пјҪгҖӮ
пј»14пјҪи—Ҹж–ҮеҸІзұҚгҖҠиҙӨиҖ…е–ңе®ҙгҖӢдёӯжӣҫиҜҰз»ҶеҸҷиҝ°еҷ¶зҺӣе·ҙеңЁеҚ—дә¬дёҫиЎҢжі• дјҡд№ӢзӣӣеҶөпјҡвҖңвҖҰвҖҰж¬ЎжңҲдә”ж—Ҙе§ӢпјҢеј№еҶ…еӨ–еқӣеҹҺд№ӢеўЁзәҝпјҢе°ҡеёҲд№ғи®ҫеҚҒдәҢеқӣеҹҺпјҢжӯӨеҚіиғңжө·гҖҒе®қзЎ•ж©ӣгҖҒй«ҳж—Ҙз“Ұдј дёӢд№ӢеҜҶйӣҶгҖҒеӨ§еёҲдј дёӢд№ӢеҜҶжңӯгҖҒд»–еҰӮйҮ‘еҲҡз•Ңжі•з•Ңд№ӢзҒҢйЎ¶гҖҒе–ңйҮ‘еҲҡгҖҒе°ҠиғңжҜҚгҖҒжҷ®жҳҺгҖҒиҚҜеёҲдҪӣгҖҒеәҰжҜҚд»ӘиҪЁгҖҒи§Ӯйҹіе’’гҖӮпј»дҪңжі•пјҪд№ӢеҲқпјҢзҡҮеёқдәІдёҙпјҢеҗ‘е°ҡеёҲдёүдәәеҘүиө е…ЁйғЁзӨје“ҒпјҢиөҗеғ§дәәиЎЈжңҚиЎЁйҮҢеӣӣиўӯпјҢе…¶д»–е®ҲеқӣеҹҺиҖ…иЎЈжңҚиЎЁйҮҢдёҖиўӯпјҢзҡҶзҡҮеёқеҸ–иө гҖӮд»ӘиҪЁиҝӣиЎҢзӣҙиҮіеҚҒе…«ж—ҘпјҢз»Ҳж—ҘеҗҒиҜ·й«ҳзҡҮеёқгҖҒй«ҳзҡҮеҗҺд№ӢзҒөйҷҚдёҙпјҢе°ҡеёҲеҗ„дәҲд»ҘзҒҢйЎ¶пјҢд»–дәәеҲҷдҪңи§Ји„ұд»ӘиҪЁвҖҰвҖҰвҖқиҪ¬еј•иҮӘйӮ“й”җйҫ„пјҡгҖҠпјңиҙӨиҖ…е–ңе®ҙпјһжҳҺж°ёд№җж—¶е°ҡеёҲе“Ҳз«Ӣйә»жҷӢдә¬зәӘдәӢз¬әиҜҒгҖӢпјҢиҪҪгҖҠдёӯеӣҪи—ҸеӯҰгҖӢ1992е№ҙ第3жңҹгҖӮ
пј»15пјҪеӣәе§Ӣеҷ¶дёҫе·ҙВ·жҙӣжЎ‘жіҪеҹ№пјҡ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пјҢйҷҲеәҶиӢұгҖҒд№ҢеҠӣеҗүиҜ‘жіЁ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90е№ҙзүҲпјҢ第63йЎөгҖӮеҸҰдёҺ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дёӯзҡ„и®°иҪҪеӨ§иҮҙзӣёеҗҢгҖӮеәҰжҜҚпјҡи—ҸиҜӯиҪЁвҖңеҚ“зҺӣвҖқпјҢжўөж–ҮдёәTaraпјҢжұүиҜ‘вҖңж•‘еәҰдҪӣжҜҚвҖқжҲ–вҖңеӨҡзҪ—иҸ©иҗЁвҖқгҖӮвҖңеӨҡзҪ—вҖқеңЁжўөж–Үдёӯж„ҸдёәзңјзқӣпјҢеӣ е…¶дә§з”ҹдәҺеӨ§жӮІи§Ӯдё–йҹіиҸ©иҗЁд№Ӣзӣ®иҖҢжқҘпјҢеҸҲеӣ еәҰжҜҚжҳҜи§Ӯдё–йҹіеҢ–иә«иҸ©иҗЁзҡ„ж•‘еәҰиӢҰйҡҫзҡ„жң¬е°ҠпјҢж•‘жөҺиҜёйҡҫпјҢ并е°ҶиҜёйҡҫйҖҒиҮіеҪјеІёпјҢж•…иҖҢеҫ—ж•‘еәҰд№ӢеҗҚгҖӮж №жҚ®е”җд»ЈжүҖиҜ‘гҖҠж•‘еәҰдҪӣжҜҚдәҢеҚҒдёҖз§ҚзӨјиөһз»ҸгҖӢпјҢеәҰжҜҚеӨҡд»ҘеҢ–иә«жҳҫзҺ°пјҢдёҖиҲ¬дёә21зӣёпјҢдҪҶеңЁ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дёӯжүҖеҮәзҺ°зҡ„еәҰжҜҚзәҰжңү30з§Қд№ӢеӨҡпјҢжҳҜйҮҚиҰҒзҡ„еҘіжҖ§е°ҠзҘһгҖӮеңЁи—Ҹдј дҪӣж•ҷеҜҶе®—з»Ҹе…ёдёӯеҸҲз”Ёд»Ҙз§°и°“жҳҺеҰғпјҲйҷҖзҪ—е°јпјүгҖӮ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йҖ еһӢдёӯпјҢжңҖеёёи§Ғзҡ„еәҰжҜҚеғҸдёәз»ҝеәҰжҜҚе’ҢзҷҪеәҰжҜҚгҖӮ
пј»16пјҪеҸӮи§Ғпј»ж„ҸпјҪеӣҫйҪҗгҖҒпј»еҫ·пјҪжө·иҘҝеёҢпјҡгҖҠиҘҝи—Ҹе’Ңи’ҷеҸӨзҡ„е®—ж•ҷгҖӢпјҢиҖҝжҳҮиҜ‘гҖҒзҺӢе°§ж Ўи®ў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89е№ҙзүҲпјҢ第80гҖҒ82йЎөгҖӮ
пј»17пјҪгҖҠиҙӨиҖ…е–ңе®ҙгҖӢпјҲи—Ҹж–ҮпјүпјҢж°‘ж—ҸеҮәзүҲзӨҫ1986е№ҙзүҲпјҢ第1007йЎөпјҡвҖңвҖҰвҖҰ延иҜ·иҝӣе®«пјҢе»әз«ӢеқӣеҹҺпјҢдёәзҡҮеёқеҸ—ж— йҮҸзҒҢйЎ¶гҖӮдёӢжңҲпјҲдёүжңҲпјүдёҠж—¬е…«ж—ҘпјҢејҖе§Ӣи®Іи§Је…ӯжі•пјҢзҡҮеёқеҘүиЎҢз„үвҖқгҖӮ
пј»18пјҪгҖҠеӨ§ж–№е№ҝдҪӣеҚҺдёҘз»ҸгҖӢеҚ·дәҢеҚҒд№қгҖҠиҸ©иҗЁдҪҸе“ҒеӨ„гҖӢпјҢи§ҒгҖҠеӨ§жӯЈж–°дҝ®еӨ§и—Ҹз»ҸгҖӢеҚ·д№қпјҢ第9йЎөгҖӮ
пј»19пјҪгҖҠж—§е”җд№ҰгҖӢеҚ·еҚҒдёғгҖҠ敬宗жң¬зәӘгҖӢпјҡвҖңпјҲй•ҝеәҶеӣӣе№ҙпјүд№қжңҲз”ІеӯҗпјҢеҗҗи•ғ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вҖқпјӣгҖҠеҶҢеәңе…ғйҫҹгҖӢеҚ·д№қд№қд№қгҖҠеӨ–иҮЈйғЁВ·иҜ·жұӮгҖӢпјҡвҖңз©Ҷе®—й•ҝеәҶеӣӣе№ҙд№қжңҲз”ІеӯҗпјҢзҒөжӯҰиҠӮеәҰдҪҝжқҺиҝӣиҜҡеҘҸпјҢеҗҗи•ғ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гҖӮеұұеңЁд»Је·һпјҢеӨҡжө®еӣҫд№Ӣиҝ№пјҢиҘҝжҲҺе°ҡжӯӨж•ҷпјҢж•…жқҘжұӮд№ӢвҖқгҖӮ
пј»20пјҪе·ҙВ·иөӣеӣҠгҖҠжӢ”еҚҸгҖӢпјҲи—Ҹж–ҮпјүпјҢж°‘ж—ҸеҮәзүҲзӨҫ1980е№ҙзүҲгҖӮ
пј»21пјҪж•Ұз…ҢеҶҷеҚ·P4648еҸ·пјҢиҜҘеҚ·еҶ…е®№и®°еҪ•ж•Ұз…Ңеғ§дәәжңқзӨјдә”еҸ°еұұзҡ„з»ҸиҝҮпјҢеҚ·ж–Үдёӯжңүи®°пјҡвҖңеҸҲиЎҢеҚҒйҮҢпјҢеҲ°еӨӘеҺҹеҹҺвҖҰвҖҰдәҢжңҲе»ҝе…«ж—ҘдёӢжүӢз”»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пјҢе»ҝд№қж—Ҙй•ҝз”»иҮіз»ҲвҖқпјӣеҸӮи§Ғжқңж–—иҜҡпјҡгҖҠж•Ұз…Ңдә”еҸ°еұұж–ҮзҢ®ж ЎеҪ•з ”究гҖӢпјҢеұұиҘҝдәәж°‘еҮәзүҲзӨҫ1991е№ҙзүҲпјҢ第141йЎөгҖӮ
пј»22пјҪжқңж–—иҜҡпјҡгҖҠж•Ұз…Ңдә”еҸ°еұұж–ҮзҢ®ж ЎеҪ•з ”究гҖӢпјҢеұұиҘҝдәәж°‘еҮәзүҲзӨҫ1991е№ҙзүҲпјҢ第141йЎөпјӣеҸҰи§ҒжүҺжҙӣпјӣгҖҠеҗҗи•ғжұӮдә”еҸ°еұұеӣҫеҸІдәӢжқӮиҖғгҖӢпјҢиҪҪгҖҠж°‘ж—Ҹз ”з©¶гҖӢ1998е№ҙ第1жңҹгҖӮ
пј»23пјҪгҖҠжҳҺеӨӘе®—е®һеҪ•гҖӢеҚ·дә”дёҖпјҢж°ёд№җдә”е№ҙдёғжңҲзҷёй…үжқЎгҖӮ
пј»24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ёүгҖҠеӨ§е®қжі•зҺӢдј гҖӢгҖӮ
пј»25пјҪеҗҢдёҠд№ҰпјҢеҚ·дәҢгҖӮ
пј»26пјҪе–»и°Ұпј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еӣӣйӣҶеҚ·еҚҒд№қгҖӮ
пј»27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ёүгҖ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гҖӮ
пј»28пјҪ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пјҲи—Ҹж–ҮжҠ„жң¬пјүпјҢ第13йЎөдёҠгҖӮ
пј»29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әҢгҖӮ
пј»30пјҪд»»е®қж №гҖҒжқЁе…үж–Үзј–гҖҠдёӯеӣҪе®—ж•ҷеҗҚиғңгҖӢпјҢеӣӣе·қдәәж°‘еҮәзүҲзӨҫ1989е№ҙзүҲпјҢ第88йЎөгҖӮ
пј»31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әҢгҖӮ
пј»32пјҪеӣәе§Ӣеҷ¶дёҫе·ҙВ·жҙӣжЎ‘жіҪеҹ№пјҡ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пјҢйҷҲеәҶиӢұгҖҒд№ҢеҠӣеҗүиҜ‘жіЁ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90е№ҙзүҲпјҢ第63йЎөгҖӮ
пј»33пјҪеҗҢжіЁпј»35пјҪгҖӮ
пј»34пјҪжІҢи°·пјҡгҖҠдә”еҸ°еұұеҸӮи®°ж—Ҙи®°гҖӢпјҢи§ҒгҖҠж–°жёёи®°зі»еҲ—з»ӯзј–гҖӢпјҢдёӯеҚҺд№ҰеұҖеҮәзүҲпјҢ第2еҶҢгҖӮ
пј»35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ә”гҖӮ
пј»36пјҪе…¶дәӢиҝ№еҸӮи§Ғе–»и°Ұпј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еӣӣйӣҶеҚ·дёғгҖӮ
пј»37пјҪгҖҠжҳҺеӨӘе®—е®һеҪ•гҖӢеҚ·дёҖдәҢдә”пјҢж°ёд№җдәҢеҚҒдёҖе№ҙеӣӣжңҲе·ұе·іжқЎгҖӮ
гҖҖеӣӣгҖҒдә”еҸ°еұұдёҺи—Ҹдј дҪӣж•ҷ
гҖҖгҖҖеңЁжұүең°дҪӣж•ҷдёӯпјҢдә”еҸ°еұұиў«жҜ”йҷ„дёәдҪӣж•ҷе…ёзұҚдёӯжүҖиҜҙзҡ„ж–Үж®ҠеҢ–е®Үзҡ„вҖҳжё…еҮүеұұвҖқпјҢ并е°Ҷдә”еҸ°дёҺж–Үж®ҠдҝЎд»°иҒ”зі»иө·жқҘгҖӮжҷӢдҪӣй©®и·ӢйҷҖзҪ—иҜ‘гҖҠеӨ§ж–№е№ҝдҪӣеҚҺдёҘз»ҸгҖӢдёӯиҜҙпјҡвҖңдёңеҢ—ж–№жңүиҸ©иҗЁдҪҸеӨ„еҗҚжё…еҮүеұұгҖӮиҝҮеҺ»иҜёиҸ©иҗЁеёёдәҺдёӯеҫҖпјҢеҪјзҺ°жңүиҸ©иҗЁеҗҚж–Үж®ҠеёҲеҲ©пјҢжңүдёҖдёҮиҸ©иҗЁзң·еұһпјҢеёёдёәиҜҙжі•вҖқгҖӮпј»18пјҪдә”еҸ°еұұдёҺи—Ҹдј дҪӣж•ҷд№Ӣй—ҙзҡ„е…ізі»еҸҜиҜҙжҳҜеҚҒеҲҶеҜҶеҲҮдё”жәҗиҝңжөҒй•ҝгҖӮж–Үж®ҠиҸ©иҗЁеңЁдҪӣж•ҷдёӯзҡ„ең°дҪҚжһҒдёәзү№еҲ«пјҢж—ўжҳҜдёҮиЎҢеңҶдҝ®гҖҒиҮӘд»–е…јеҲ©еҚҙеҸҲе®…еҝғжі•з•Ңзҡ„иҸ©иҗЁпјҢеҸҲжҳҜе…·жңүдёүеҚҒдәҢзӣёгҖҒе…«еҚҒз§ҚеҘҪпјҢзӣёеҘҪеҰӮеҗҢдҪӣзҘ–зҡ„еҮәдё–д№ӢеңЈгҖӮж–Үж®Ҡиҝҷз§ҚдәҰдҪӣдәҰиҸ©иҗЁзҡ„иә«д»ҪпјҢдҪҝдҝЎдј—зЎ®дҝЎд»–ж•‘еәҰдј—з”ҹзҡ„ж…ҲжӮІд№ӢеҠӣпјҢж— йҮҸж— иҫ№гҖӮе”җд»ЈеҜҶе®—дј е…Ҙжұүең°пјҢеҜҶе®—жҸҗеҖЎдҪӣж•ҷеҫ’дёҚд»…иҰҒжұӮиҜҒдёӘдәәи§Ји„ұпјҢжӣҙиҰҒйҮҮеҸ–еҗ„з§ҚзҒөжҙ»зҡ„ж–№жі•жқҘвҖңи„ұеәҰвҖқдј—з”ҹпјҢеҚіжүҖи°“вҖңж–№дҫҝжҷәж…§вҖқжҲ–вҖңж–№дҫҝйҒ“вҖқгҖӮиҖҢд»ҘвҖңжҷә慧第дёҖвҖқзҡ„ж–Үж®ҠиҸ©иҗЁеҲҷжҲҗдёәеҜҶе®—жңҖеҙҮжӢңзҡ„иҸ©иҗЁпјҢе…¶еҪўиұЎдёҖиҲ¬йЎ¶з»“дә”й«»гҖҒжүӢжҢҒе®қеү‘гҖҒеқҗйӘ‘зӢ®еӯҗпјҢиЎЁзӨәжҷәж…§гҖҒй”җеҲ©е’ҢеЁҒзҢӣгҖӮеҗҺжқҘдҪӣж•ҷеҫ’жӣҙжҠҠгҖҠйҮ‘еҲҡйЎ¶з»ҸгҖӢдёӯвҖңдә”дҪӣжҳҫдә”жҷәвҖқзҡ„жҖқжғіз»“еҗҲеҲ°дә”еҸ°еұұеҙҮжӢңдёӯпјҢи®Өдёәдә”еә§еұұеі°жҳҜж–Үж®ҠиҸ©иҗЁеӨ§жҳҫеҸ—иә«д№ӢжһҒеҮҖдә”дҪ“пјҢжҳҜжҳҫзӨәдә”з§Қе№»еҢ–жҷәж…§д№Ӣе…үе№»зҡ„дә”з§Қиә«еғҸпјҢе…¶дёӯгҖҒдёңгҖҒеҚ—гҖҒиҘҝгҖҒеҢ—еҸ°еҲҶеҲ«д»ЈиЎЁвҖңиә«вҖқгҖҒвҖңж„ҸвҖқгҖҒвҖқжҷәж…§вҖқгҖҒвҖңиҜӯвҖқгҖҒвҖңдёҡвҖқгҖӮдҪӣж•ҷеҫ’е®Ңе…Ёе°Ҷдә”еҸ°еұұи®ӨдҪңж–Үж®ҠеҢ–зҺ°д№ӢжүҖпјҢдёҚд»…еҸ°еҸ°зҡҶжңүж–Үж®ҠеҢ–зҺ°зҒөиҝ№гҖҒеҜәеҜәйғҪеЎ‘жңүж–Үж®ҠеңЈеғҸпјҢе°ұиҝһдә”еҸ°еұұзҡ„иҚүжңЁеңҹзҹіеқҮдёҺж–Үж®ҠиҸ©иҗЁзӣёе…іиҒ”гҖӮжӣҙеҠ дёҠдә”еҸ°еұұжҪңиӮІзҷҫзҒөгҖҒйқҷи°·е№Ҫжһ—зҡ„з§ҖдёҪжҷҜиүІпјҢж–Үж®ҠеңЈең°дә”еҸ°еұұд№ӢзӣӣиӘүе№ҝж’ӯеӣӣж–№пјҢйҰҷзҒ«е…ҙж—әгҖӮеҗҗи•ғеңЁдёҺе”җзҺӢжңқдәӨеҫҖдёӯпјҢд№ҹд№…й—»дә”еҸ°еұұзӣӣеҗҚпјҢдәҺе”җз©Ҷе®—й•ҝеәҶе№ҙй—ҙпјҢеҗҗи•ғиөһжҷ®жӣҫ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гҖӮпј»19пјҪи—Ҹж–ҮеҸІд№Ұдёӯд№ҹжңүзӣёеә”зҡ„и®°иҪҪпјҡдәҺеҗҗи•ғиөһжҷ®иөӨжқҫеҫ·иөһеҚідҪҚд№ӢеҲқпјҢдҝЎеҘүиӢҜж•ҷзҡ„еӨ§иҮЈдёҖеәҰжҺҢж”ҝпјҢеҲ¶е®ҡдәҶжҜҒзҒӯдҪӣжі•зҡ„ж”ҝзӯ–пјҢжӢҶжҜҒдәҶжүҺзҺӣзҡ„зңҹжЎ‘жң¬е°ҠдҪӣе ӮгҖӮиөӨжқҫеҫ·иөһжҙҫйҒЈжЎ‘е–ңдёәйҰ–зҡ„дә”дҪҚдҪҝиҖ…еҲ°вҖңеҫ·д№ҢеұұвҖқеҚідә”еҸ°еұұйЎ¶зҡ„ж–Үж®ҠиҸ©иҗЁж®ҝдёӯжұӮеҸ–еҜәйҷўеӣҫж ·пјҢи—ҸеҸІгҖҠжӢ”еҚҸгҖӢдёӯиҝҳиҜҰз»ҶжҸҸз»ҳдәҶеҮ дҪҚдҪҝиҮЈеҸ–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зҡ„з»ҸиҝҮгҖӮпј»20пјҪ
гҖҖгҖҖжүҖи°“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е°ұжҳҜз»ҳжңүдә”еҸ°еұұеҸҠе…¶еҗ„еӨ„зҘһзҒөеңЈиҝ№зҡ„дҪӣз”»пјҢжҚ®е”җи“қи°·жІҷй—Ёзҡ„гҖҠеҸӨжё…еҮүдј гҖӢзӯүи®°иҪҪпјҢеңЁе”җй«ҳе®—йҫҷжң”е№ҙй—ҙпјҲ661пҪһ663е№ҙпјүпјҢжңүиҘҝе®үжІҷй—ЁдјҡиөңеҘүе‘ҪеёҰз”»еёҲеј е…¬иҚЈзӯүдәәеҲ°дә”еҸ°еұұиҖғеҜҹеңЈиҝ№пјҢдјҡиөңе°Ҷз”»еёҲжүҖз»ҳдә”еҸ°еұұеӣҫж ·еҒҡжҲҗвҖңе°ҸеёҗвҖқпјҲеҚіеұҸйЈҺз”»пјү并且й…ҚдёҠиҜҙжҳҺж–Үеӯ—пјҢдҪҝ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еңЁдёӯеҺҹеҗ„ең°е№ҝдёәжөҒдј гҖӮеңЁж•Ұз…Ңж–ҮзҢ®дёӯд№ҹжңүи®°иҪҪпјҢиҜҙеҪ“ж—¶жңүи®ёеӨҡз”»е·Ҙ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з”»еӣҫпјҢеңЁеӨӘеҺҹзӯүең°иҝҳеҮәзҺ°дәҶд»Ҙз”»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дёәдёҡзҡ„дё“й—Ёз”»еҢ гҖӮпј»21пјҪеҗҗи•ғ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д№ӢдәӢеҜ№и—Ҹдј дҪӣж•ҷеҪұе“ҚйўҮеӨ§гҖӮиөһжҷ®иөӨжқҫеҫ·иөһж—¶жүҖдҝ®е»әзҡ„еҗҗи•ғ第дёҖеә§еүғеәҰеғ§дәәеҮә家зҡ„дҪӣж•ҷеҜәйҷўжЎ‘иҖ¶еҜәе°ұд»ҘжӯӨдёәи“қжң¬гҖӮд»ҘеҗҺпјҢжЎ‘иҖ¶еҜәеңЁеҺҶеҸІдёҠеӣ еҗ„з§ҚеҺҹеӣ еӨҡж¬Ўиў«жҜҒпјҢдҪҶж–Үж®ҠвҖңеҢ–е®ҮвҖқдә”еҸ°еұұд№Ӣеӣҫе§Ӣз»ҲжҳҜжҒўеӨҚйҮҚе»әиҜҘеҜәж—¶ж®ҝеҶ…еЈҒз”»дёӯдёҚеҸҜжҲ–зјәзҡ„еҶ…е®№гҖӮеңЁеёғиҫҫжӢүе®«иҮід»Ҡд№ҹдҝқз•ҷзқҖ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пјҲж—Ҙе…үж®ҝиҘҝеҚ—й—ЁеҚ—дҫ§пјүгҖӮж•Ұз…ҢиҺ«й«ҳзӘҹеЈҒз”»дёӯзҺ°еӯҳ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7е№…пјҢз»Ҹйүҙе®ҡжҺЁжөӢпјҢе…¶дёӯжңү4е№…жҳҜдёӯе”җеҗҗи•ғз»ҹжІ»ж•Ұз…Ңж—¶жңҹз•ҷдёӢзҡ„гҖӮпј»22пјҪеӣ иҖҢпјҢ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еҸҜиҜҙжҳҜи—Ҹжұүж°‘ж—Ҹд№Ӣй—ҙж–ҮеҢ–дәӨжөҒеҸІдёҠзҡ„дёҖдёӘеҺҶеҸІи§ҒиҜҒгҖӮ
гҖҖгҖҖеҗҗи•ғзҺӢжңқеҙ©жәғд№ӢеҗҺпјҢдҪӣж•ҷеңЁеҗҗи•ғжң¬еңҹеҸ—еҲ°жҜҒзҒӯжҖ§жү“еҮ»пјҢи—Ҹжұүд№Ӣй—ҙзҡ„дҪӣж•ҷдәӨжөҒд№ҹдёӯж–ӯдәҶеҫҲй•ҝж—¶й—ҙгҖӮдҪҶдә”еҸ°еұұеңЁи—Ҹж—Ҹеғ§дҝ—еӨ§дј—еҝғзӣ®дёӯзҡ„зҘһеңЈең°дҪҚеҚҙжІЎжңүеҸ—еҲ°еҪұе“ҚгҖӮиҮӘе…ғд»Јиө·пјҢи—Ҹдј дҪӣж•ҷеҗҚеғ§еӨ§еҫ·иөҙдә”еҸ°еұұжңқзӨјиҖ…з»ңз»ҺдёҚз»қгҖӮеҰӮгҖҠиҗЁиҝҰдё–зі»еҸІгҖӢеҸҠгҖҠиҗЁиҝҰдә”зҘ–е…ЁйӣҶгҖӢзӯүи—Ҹж–ҮеҸІдј и®°иҪҪпјҢеӨ§е…ғеёқеёҲе…«жҖқе·ҙжӣҫдәҺ23еІҒпјҲ1257е№ҙпјүж—¶пјҢеүҚеҫҖдә”еҸ°еұұеҗ¬еҸ—еӨ§еЁҒеҫ·гҖҒзҺӣе“Ҳеҷ¶жӢүгҖҒйҮ‘еҲҡз•ҢгҖҒж—¶иҪ®зӯүе…ЁеҘ—еҜҶжі•е’Ңз–ҸйҮҠпјҢд»ҘеҸҠдёӯи§Ӯи®әгҖҒиөһйўӮгҖҒдҝұиҲҚзӯүз»Ҹи®әгҖӮе…«жҖқе·ҙиҝҳеңЁжүҖи‘—иөһж–Үдёӯе°Ҷдә”еҸ°еұұе–»дёәеҜҶжі•йҮ‘еҲҡз•Ңдә”йғЁдҪӣзҡ„дҪӣеә§гҖӮ继еҗҺпјҢеҸҲжңүе–„дј зҺӣе“Ҳеҷ¶жӢүеҜҶжі•зҡ„иғҶе·ҙеӣҪеёҲеёёй©»дә”еҸ°еұұеҜҝе®ҒеҜәпјҢ并е»әз«ӢдәҶи—Ҹдј дҪӣж•ҷ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и®ІиҜҙеҲ¶еәҰгҖӮе…¶еҗҺеҸҲжңүе…ғеёқеёҲзӣҠеёҢд»Ғй’ҰгҖҒеҷ¶зҺӣе·ҙй»‘еёҪзі»дёүдё–жҙ»дҪӣи®©иҝҘеӨҡеҗүзӯүй•ҝжңҹеңЁдә”еҸ°еұұжҙ»еҠЁпјҢдҪҝдә”еҸ°еұұ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и—Ҹдј дҪӣж•ҷеңЁдёӯеҺҹжұүең°зҡ„дёҖдёӘдј ж’ӯдёӯеҝғгҖӮ
гҖҖгҖҖеҸҠиҮіжҳҺж°ёд№җдә”е№ҙдёғжңҲпјҢжҳҺжҲҗзҘ–вҖңе‘ҪеҰӮжқҘеӨ§е®қжі•зҺӢе“Ҳз«Ӣйә»дәҺеұұиҘҝдә”еҸ°еұұе»әеӨ§ж–ӢпјҢиө„иҚҗеӨ§иЎҢзҡҮеҗҺвҖқгҖӮпј»23пјҪйҡҸзқҖжҳҺжңқж••е°Ғзҡ„еҷ¶зҺӣе·ҙеӨ§е®қжі•зҺӢжқҘдә”еҸ°еұұй©»й”Ўдј жі•пјҢдә”еҸ°еұұзҡ„и—Ҹдј дҪӣж•ҷжӣҙеҠ е…ҙзӣӣпјҢеҮәзҺ°дәҶ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иҫүз…ҢгҖӮе…ідәҺеӨ§е®қжі•зҺӢ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дәӢиҝ№пјҢи—Ҹж–ҮеҸІзұҚи®°иҪҪиҫғз®ҖеҚ•пјҢ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и®°иҪҪиҫғиҜҰз»ҶпјҡвҖңжҳҺеӨ§е®қжі•зҺӢпјҢеҗҚи‘ӣе“©йә»пјҲе“Ҳз«Ӣйә»пјҢеқҮдёәеҷ¶зҺӣе·ҙд№ӢејӮиҜ‘пјүпјҢд№ҢжҖқи—ҸдәәгҖӮйҒ“жҖҖеҶІжј пјҢзҘһз”ЁеҸөжөӢпјҢеЈ°й—»дәҺдёӯеӣҪгҖӮж°ёд№җй—ҙпјҢдёҠйҒЈдҪҝиҘҝеңҹиҝҺд№ӢпјҢеёҲйҖӮжңүдә”еҸ°д№ӢжёёпјҢеә”е‘ҪиҮійҮ‘йҷөпјҢйҒ“еҗҜеңЈиЎ·пјҢиҜ°е°ҒеҰӮжқҘеӨ§е®қжі•зҺӢпјҢиҘҝеӨ©еӨ§е–„иҮӘеңЁдҪӣгҖӮеёҲжҖ§д№җжһ—жіүпјҢжңқе»·д№ӢдёӢпјҢжҒҗеҰЁзҰ…дёҡпјҢеҘҸиҫһпјҢжёёдә”еҸ°гҖӮдёҠзң·жіЁж®·еӢӨпјҢз•ҷд№ӢдёҚе·ІпјҢд№ғиөҗйҠ®иҲҶж—Ңе№ўдјһзӣ–д№Ӣд»ӘпјҢйҒЈдҪҝеҚ«йҖҒдәҺдә”еҸ°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жӣҙж••еӨӘзӣ‘жқЁеҚҮпјҢйҮҚдҝ®е…¶еҜәпјҢе…јдҝ®иӮІзҺӢжүҖзҪ®дҪӣиҲҚеҲ©еЎ”пјҢд»ҘйҘ°жі•зҺӢд№Ӣеұ…вҖқгҖӮпј»24пјҪ
гҖҖгҖҖеӨ§жҳҫйҖҡеҜәдҪҚдәҺдә”еҸ°еұұеҸ°жҖҖй•ҮеҢ—дҫ§пјҢдёәдә”еҸ°еұұдә”еӨ§зҰ…жһ—д№ӢдёҖпјҢе§ӢеҲӣдәҺдёңжұүж°ёе№іе№ҙй—ҙпјҲ58пҪһ75е№ҙпјүпјҢеҲқеҗҚвҖңеӨ§еӯҡзҒө鹫еҜәвҖқпјҢзӣёдј дә”еҸ°еұұдёҺеҚ°еәҰзҒө鹫峰зӣёдјјпјҢж•…еңЁжӯӨе»әеҜә并е‘ҪеҗҚдёәдә”еҸ°еұұдҪӣеҲ№ејҖеұұд№ӢзҘ–гҖӮиҮіеҢ—йӯҸеӯқж–Үеёқж—¶еҶҚе»әпјҢвҖңзҺҜеҢқ鹫峰пјҢзҪ®еҚҒдәҢйҷўгҖӮеүҚжңүжқӮиҠұеӣӯпјҢж•…дәҰеҗҚ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гҖӮе”җеӨӘе®—е№ҙй—ҙеҸҲйҮҚж–°дҝ®е»әиҝҮпјҢжӯҰеҲҷеӨ©еӣ ж–°иҜ‘гҖҠеҚҺдёҘз»ҸгҖӢдёӯжңүдә”еҸ°еұұеҗҚпјҢж”№еҜәеҗҚдёәеӨ§еҚҺдёҘеҜәгҖӮжҳҺжҲҗзҘ–еҸҲж••е‘ҪйҮҚдҝ®пјҢеӣ еӨ§е®қжі•зҺӢдәҺжӯӨең°дёҫеҠһеӨ§жі•дјҡпјҢвҖңж„ҹйҖҡзҘһеә”вҖқпјҢж•…иөҗеҗҚвҖңеӨ§жҳҫйҖҡеҜәвҖқгҖӮж°ёд№җдёүе№ҙж—¶пјҢи®ҫеғ§зәІеҸёдәҺеӨ§жҳҫйҖҡеҜәпјҢвҖңзҺҮеҗҲеұұеғ§зҘқеҺҳпјҢжң¬е·һжңҲз»ҷеғ§зІ®вҖқгҖӮпј»25пјҪд»Һиҝҷдәӣи®°иҪҪпјҢеҸҜзҹҘеӨ§жҳҫйҖҡеҜәеңЁдә”еҸ°еұұзҡ„ең°дҪҚеҸҠе…¶йҮҚиҰҒжҖ§гҖӮеңЁжҳҫйҖҡеҜәеҚ—йқўпјҢеҸҲжңүдёҖеә§вҖңеӨ§е®қеЎ”йҷўеҜәвҖқпјҢеҜәдёӯе®қеЎ”зӣёдј дёәйҳҝиӮІзҺӢжүҖзҪ®дҪӣиҲҚеҲ©еЎ”еҸҠж–Үж®ҠеҸ‘еЎ”гҖӮж°ёд№җдә”е№ҙеӨ§е®қжі•зҺӢжқҘдә”еҸ°еұұж—¶пјҢжҳҺжҲҗзҘ–ж••е‘ҪеӨӘзӣ‘жқЁеҚҮйҮҚдҝ®еӨ§еЎ”пјҢе§Ӣе»әеҜәгҖӮ
гҖҖгҖҖдә”гҖҒ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ёҺдә”еҸ°еұұ
гҖҖгҖҖйҮҠиҝҰд№ҹеӨұжҳҜ继еӨ§е®қжі•зҺӢд№ӢеҗҺжқҘдә”еҸ°еұұзҡ„第дәҢдҪҚжҳҺд»Ји—Ҹдј дҪӣж•ҷй«ҳеғ§пјҢд№ҹжҳҜжқҘеҲ°дә”еҸ°еұұзҡ„第дёҖдҪҚж јйІҒжҙҫй«ҳеғ§гҖӮ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ёҺдә”еҸ°еұұзҡ„е…ізі»йқһжҜ”еҜ»еёёпјҢе–»и°Ұ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дёӯдёәе…¶з«Ӣдј пјҢзӣҙиЁҖгҖҠдә”еҸ°еұұжҳҫйҖҡеҜәжІҷй—Ё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пјҢпј»26пјҪеҪ“然пјҢдј и®°жһҒдёәз®ҖеҚ•пјҢиҖҢдё”иҝҳжңүдёҘйҮҚй”ҷиҜҜз”ҡиҮіжҠ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и®ӨдҪңжҳҜеӨ©з«әеғ§дәәпјҢдёҺдҪӣзҘ–йҮҠиҝҰзүҹе°јеҮәиә«дәҺеҗҢдёҖ家ж—ҸгҖӮд»ҠиҖғ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дёӯе…ідә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и®°иҪҪеҮ д№Һе…ЁйғЁжқҘиҮӘ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пјҢдёәиҜҒжҳ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дә”еҸ°еұұжҙ»еҠЁзҡ„зӣёе…іеҸІдәӢпјҢд№ҹдёәзә жӯЈеҶ…ең°жүҖдј й«ҳеғ§дј дёӯ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и®°иҪҪзҡ„жҹҗдәӣи°¬иҜҜпјҢе…№е°Ҷ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ёӯзҡ„гҖ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移еҪ•дәҺдёӢпјҡ
гҖҖгҖҖжҳ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пјҢеӨ©з«әиҝҰжҜ—зҪ—еӣҪпјҢдё–е°Ҡд№ӢиЈ”д№ҹгҖӮеҠҹеҫ·зҪ”жһҒпјҢзҘһз”ЁйҡҫжөӢгҖӮд»°ж–Үж®Ҡд№ӢйҒ“пјҢжқҘжёёжё…еҮүгҖӮ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жҳҘпјҢе§ӢиҫҫжӯӨеңҹпјҢж –жӯўеҸ°еұұ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еҶ¬еҚҒдёҖжңҲпјҢй—»дәҺдёҠпјҢйҒЈеӨӘзӣ‘дҫҜжҳҫиҜҸиҮідә¬пјҢе…ҘеҶ…пјҢйў„ж••е…ҚжӢңпјҢиөҗеә§еӨ§е–„ж®ҝеә”еҜ№з§°ж—ЁпјҢдёҠеӨ§еҳүеҸ№гҖӮж••е®үиғҪд»Ғж–№дёҲпјҢдёҠеҲ¶д№Ұж…°еҠіпјҢжүҖиөҗз”ҡеҺҡгҖӮжҳҺе№ҙдёҠеҲ¶д№ҰпјҢиөҗйҮ‘еҚ°е®қиҜ°пјҢе°ҒеҰҷи§үеңҶйҖҡж…§ж…Ҳжҷ®еә”иҫ…еӣҪжҳҫж•ҷзҒҢйЎ¶ејҳе–„иҘҝеӨ©дҪӣеӯҗеӨ§еӣҪеёҲд№ӢеҸ·гҖӮж— дҪ•пјҢиҫһдёҠе…ҘеҸ°пјҢжҜҸе…Ҙе®ҡпјҢдёғж—Ҙд№ғиө·гҖӮдёҠж•°еҲ¶д№ҰйҒЈдҪҝиҮҙж…°гҖӮиҮідәҺе®Је®—пјҢе°ӨеҠ й’ҰеҙҮпјҢзӨјеҮәеёёж јгҖӮе®Јеҫ·е…ӯе№ҙпјҢж—ӢиҘҝеҹҹз„үпј»27пјҪгҖӮ
иҝҷдёҖж®өи®°иҪҪдёӯжңүжӯЈзЎ®зҡ„еҶ…е®№пјҢд№ҹжңүй”ҷиҜҜд№ӢеӨ„пјҢйҰ–е…Ҳе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жқҘеҺҶдёҚз”ҡдәҶдәҶпјҢд»Ҙдёәд»–жҳҜеӨ©з«әеғ§дәәпјҢеӣ дёәвҖңйҮҠиҝҰвҖқд№ӢйҹізЎ®зі»жўөиҜӯпјҢз”ұжӯӨдҫҝжңӣж–Үз”ҹд№ү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д»Ҙдёәд»–дёҺдҪӣзҘ–дё–е°ҠеҮәиә«дәҺдёҖдёӘ家ж—ҸгҖӮжұүең°еғ§дәәдёҚжё…жҘҡпјҢи—Ҹж—Ҹеғ§дәәиө·жўөж–ҮеҗҚеӯ—иҖ…д»ҺжқҘе°ұжңүпјҢиҜёеҰӮвҖңйҮҠиҝҰе®ӨеҲ©вҖқпјҢвҖңеӨҡзҪ—йӮЈд»–вҖқпјҢзӯүзӯүпјҢдёҚиғңжһҡдёҫгҖӮеҸҰеӨ–пјҢиЁҖе®Јеҫ·е…ӯе№ҙпјҢвҖңж—ӢиҘҝеҹҹз„үвҖқпјҢиӮҜе®ҡжҳҜдёҚжӯЈзЎ®зҡ„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дәҺе®Јеҫ·д№қе№ҙеҸ—е°ҒеӨ§ж…Ҳжі•зҺӢпјҢиҖҢгҖ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дёӯеҜ№еҰӮжӯӨйҮҚеӨ§д№ӢдәӢз«ҹ然еҸӘеӯ—жңӘи‘—пјҢдјјд№ҺеҫҲд»Өдәәиҙ№и§ЈгҖӮе…¶е®һпјҢиӢҘд»”з»ҶеҲҶжһҗпјҢд№ҹеҸҜд»Ҙи®Іеҫ—йҖҡпјҢеҚідәҺе®Јеҫ·е…ӯе№ҙ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ёҖиЎҢ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пјҢиҮідәҺеҲ°е“ӘйҮҢеҺ»дәҶпјҢеҢ…жӢ¬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дҪңиҖ…еңЁеҶ…зҡ„дә”еҸ°еұұжұүеғ§д»¬е№¶дёҚеҫ—иҖҢзҹҘпјҢдёҖж–№йқўжңүиҜӯиЁҖйҡңзўҚпјӣеҸҰдёҖж–№йқўж¶үеҸҠжңқе»·д№ӢдәӢд№ҹдјҡдҝқе®Ҳз§ҳеҜҶпјҢдёҚдјҡеӨ§еј ж——йј“ең°е®Јжү¬гҖӮиҖҢдё”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жӯӨз•Ә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д№ӢеҗҺпјҢе°ұеҶҚд№ҹжІЎеӣһдә”еҸ°еұұгҖӮиҷҪ然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еҢ—дә¬жңүи®ёеӨҡжҙ»еҠЁпјҢд№ҹйўҮеҫ—жңқе»·иөҸиҜҶгҖҒдҝЎйҮҚпјҢдҪҶеңЁйӮЈдёҖж—¶д»ЈпјҢдәӨйҖҡдёҚдҫҝпјҢж¶ҲжҒҜй—ӯеЎһпјҢжӣҙе…јжұүи—ҸдҪӣж•ҷж–ҮеҢ–д№Ӣе·®ејӮпјҢеңЁдә”еҸ°еұұй©»й”Ўе®үзҰ…зҡ„еғ§дәәж— жі•жӣҙеӨҡең°дәҶи§Ј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иЎҢиёӘжҳҜеҫҲе®№жҳ“зҗҶи§Јзҡ„гҖӮдҪҶйҮҠиҝҰд№ҹеӨұжӣҫз»ҸеҮ з•ӘжқҘй©»дә”еҸ°еұұпјҢеҸҲеҫ—жңқе»·е°ҒеҸ·пјҢеҸҲеҫ—жҳҺжҲҗзҘ–гҖҒжҳҺе®Је®—дёӨзҡҮеёқзӨјйҒҮпјҢж— з–‘жҳҜдёӘйҮҚиҰҒдәәзү©пјҢж’°еҶҷдә”еҸ°еұұеҺҶеҸІиҮӘ然еә”еӨ§д№ҰдёҖ笔пјҢдҪҶеҸҲдёҚзҹҘе…¶жүҖз»ҲпјҢеҸӘжҺЁжөӢд»–еӣһеӨ©з«әиҖҒ家дәҶеҗ§пјҒ
иҮідәҺдј и®°дёӯжүҖи®°иҪҪзҡ„е…¶д»–еҶ…е®№еә”жҳҜжҜ”иҫғеҸҜйқ зҡ„пјҢеӣ дёәжҳҜдҫқжҚ®дә”еҸ°еұұеғ§дәә们зҡ„жүҖи§ҒжүҖй—»иҖҢеҶҷгҖӮиҜёеҰӮ第дёҖж¬ЎжқҘдә”еҸ°еұұзҡ„ж—¶й—ҙпјҢд»ҘеҸҠзҰ»ејҖзҡ„ж—¶й—ҙпјӣзү№еҲ«жҳҜ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й•ҝиҫҫ23дёӘеӯ—зҡ„е°ҒеҸ·е®Ңе…Ёж— иҜҜгҖӮиҮідә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зҡ„еӯҰдҝ®жғ…еҶөпјҢд№ҹжҳҜдёҚз”ҡдәҶдәҶпјҢе…ҲжҳҜиҜҙд»–вҖңеҠҹеҫ·зҪ”жһҒпјҢзҘһз”ЁйҡҫжөӢвҖқпјҢеҶҚжҸҸеҶҷд»–вҖңжҜҸдәәе®ҡпјҢдёғж—Ҙд№ғиө·вҖқпјҢиҮідәҺдҝ®иЎҢе…·дҪ“еҶ…е®№пјҢ他们еҸҲеҰӮдҪ•жҗһеҫ—жё…жҘҡе‘ўпјҒ
гҖҖгҖҖд»Ҡж №жҚ®жұүи—Ҹж–ҮзҢ®жңүе…іи®°иҪҪ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ә”жҳҜеүҚеҗҺ3ж¬ЎжқҘеҲ°дә”еҸ°еұұгҖӮ第дёҖж¬ЎжҳҜеңЁж°ёд№җеҚҒдәҢе№ҙпјҲ1414е№ҙпјүжҳҘеҲ°иҫҫдә”еҸ°еұұпјҢиҖҢдәҺеҪ“е№ҙ12жңҲ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пјҢеә”иҜҸиөҙеҚ—дә¬е…Ҙжңқпјӣ第дәҢж¬ЎжҳҜеңЁж°ёд№җеҚҒдёүе№ҙпјҲ1415е№ҙпјүеӨ§зәҰ5жңҲе·ҰеҸіпјҢд»ҺеҚ—дә¬еҶҚиөҙдә”еҸ°еұұпјҢиҖҢ第дәҢж¬Ў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жҳҜзәҰеңЁж°ёд№җеҚҒеӣӣе№ҙпјҲ1416е№ҙпјүзҡ„з§ӢеӯЈпјӣ第3ж¬ЎжқҘдә”еҸ°еұұжҳҜеңЁжҙӘзҶҷе…ғе№ҙпјҲ1425е№ҙпјүжҲ–е®Јеҫ·е…ғе№ҙпјҲ1426е№ҙпјүеүҚеҗҺпјҢ第дёүж¬ЎзҰ»ејҖдә”еҸ°еұұзҡ„ж—¶й—ҙжҳҜзәҰеңЁе®Јеҫ·е…ӯе№ҙпјҲ1431е№ҙпјүгҖӮзӣ®еүҚеҸҜд»Ҙи®Өе®ҡзҡ„жҳҜпјҢ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үҚеҗҺ3ж¬ЎдёҠдә”еҸ°еұұдёҚдјҡжңүй”ҷпјҢдҪҶжҜҸдёҖж¬Ўзҡ„е…·дҪ“ж—¶й—ҙиҝҳ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еҲқжӯҘзҡ„жҺЁжөӢпјҢиҝҳжңӣд»ҠеҗҺиғҪеҸ‘зҺ°ж–°зҡ„зәҝзҙўпјҢеҶҚиҝӣдёҖжӯҘжҳҺзЎ®е…·дҪ“ж—¶й—ҙгҖӮ
гҖҖгҖҖ第дәҢдёӘй—®йўҳжҳҜйҮҠиҝҰд№ҹеӨұ3ж¬ЎжқҘдә”еҸ°еұұпјҢй©»й”ЎдәҺе“ӘдёӘеҜәйҷўпјҹжҚ®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Ҹ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иҪҪпјҢиҮӘ然д№ҹжҳҜй©»иөҗдәҺ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иҖғеӨ§жҳҫйҖҡеҜәзҡ„еҺҶеҸІпјҢзҹҘе…¶жӣҫеҗҚдёә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е’ҢвҖңеҚҺдёҘеҜәвҖқпјҢжүҖд»Ҙ笔иҖ…и®Өдёәд»Өз ”з©¶иҖ…еӣ°жғ‘е·Ід№…зҡ„и—Ҹж–ҮеҸІдј дёӯзҡ„еә”дёә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жҲ–вҖңеҚҺдёҘеҜәвҖқд№ӢеҜ№йҹіпјҢиҖҢдё”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дёӯд№ҹи®°иҪҪйҮҠиҝҰд№ҹеӨұеңЁжұүең°дә”еҸ°еұұе…ҙе»әдәҶ6еә§еӨ§еҜәйҷўпјҢ并еңЁвҖңзҫҺжңөеӨҡзғӯвҖқпјҲж„ҸдёәвҖңиҠұеӣӯвҖқпјүйҷ„иҝ‘е»әз«ӢдәҶеҗҚдёәзҡ„еҜәйҷўгҖӮпј»28пјҪй•ҝжңҹд»ҘжқҘпјҢи—ҸеҸІз ”究иҖ…еӣ дёҚжё…жҘҡ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еңЁдҪ•ең°пјҢеӣ иҖҢдёҖиҲ¬иҜ‘д№ӢдёәвҖңжі•йҹіеҜәвҖқпјҢиҝӣиҖҢжҺЁжөӢдёәеҢ—дә¬д№Ӣжі•жёҠеҜәгҖӮ笔иҖ…д»ҘдёәпјҢз”ұи—ҸжұүеҸІж–ҷзӣёдә’е·§еҰҷеҚ°иҜҒпјҢеҸҜд»Ҙж–ӯе®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й©»й”Ўдә”еҸ°еұұд№ӢеҜәйҷўеҚіжҳҜвҖңиҠұеӣӯеҜәвҖқпјҢеҚівҖңеҚҺдёҘеҜәвҖқпјҢд№ҹе°ұжҳҜж°ёд№җе№ҙй—ҙзҡ„еӨ§жҳҫйҖҡеҜә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е…ідәҺзҡ„жӮ¬еҝөеҸҜд»Ҙе‘ҠдёҖж®өиҗҪ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йҷӨжҳҫйҖҡеҜәгҖҒеӨ§е®қеЎ”еҜәйҷўеӨ–пјҢдёҺйҮҠиҝҰд№ҹеӨұе…ізі»еҜҶеҲҮзҡ„иҝҳжңүеӨ§еңҶз…§еҜәе’ҢеӨ§ж–Үж®ҠеҜәпјҢиҝҷдёӨеә§еҜәйҷўд№ҹжҳҜдә”еҸ°еұұйҮҚиҰҒзҡ„и—Ҹдј дҪӣж•ҷеҜәйҷўгҖӮ
жіЁйҮҠпјҡ
в‘ гҖҠе…ғеҸІгҖӢеҚ·дәҢв—ӢдәҢгҖҠйҮҠиҖҒеҝ—гҖӢгҖӮ
в‘ЎгҖҠеҚ—и—ҸгҖӢеҸҲз§°гҖҠжҳҺеҚ—жң¬еӨ§и—Ҹз»ҸгҖӢпјҢиҜҘи—ҸеҲ»дәҺж°ёд№җеҚҒе№ҙпјҲ1412е№ҙпјүиҮіеҚҒдә”е№ҙпјҲ1417е№ҙпјүпјҢе…ұ636еҮҪпјҢ收еҗ„зұ»дҪӣж•ҷи‘—дҪң1610йғЁгҖҠеҢ—и—ҸгҖӢеҸҲз§°гҖҠжҳҺеҢ—жң¬еӨ§и—Ҹз»ҸгҖӢпјҢж°ёд№җеҚҒд№қе№ҙпјҲ1421е№ҙпјүиҝҒйғҪеҢ—дә¬еҗҺпјҢжҳҺжҲҗзҘ–дёӢд»ӨйҮҚж–°зј–йӣҶеӨ§и—Ҹз»ҸпјҢиҮіжӯЈз»ҹдә”е№ҙпјҲ1440е№ҙпјүз»Ҳе‘Ҡе®ҢжҲҗпјҢ收д№Ұ1621йғЁгҖӮ
в‘ўеҸӮи§Ғй»„жҳҺдҝЎпјҡгҖҠж°‘ж—Ҹж–ҮеҢ–е®«еӣҫд№ҰйҰҶи—Ҹи—Ҹж–Үе…ЁйӣҶжҖ»зӣ®еҪ•еәҸгҖӢжӢүиҗЁзҺ°и—Ҹжңү2йғЁж°ёд№җзүҲгҖҠи—Ҹж–ҮеӨ§и—Ҹз»ҸгҖӢпјҢе…¶дёӯдёҖйғЁи—ҸдәҺеёғиҫҫжӢүе®«пјҲеҺҹи—ҸдәҺиҗЁиҝҰеҜәпјүпјҢж°ёд№җеҚҒдёҖе№ҙпјҲ1413е№ҙпјүз”ұжҳҺжҲҗзҘ–иөҗдәҲиҗЁиҝҰжҙҫй«ҳеғ§гҖҒжҳҺе°ҒеӨ§д№ҳжі•зҺӢиҙЎеҷ¶жүҺиҘҝпјӣеҸҰдёҖйғЁи—ҸдәҺиүІжӢүеҜәпјҢеҚіж°ёд№җеҚҒеӣӣе№ҙпјҲ1416е№ҙпјүз”ұжҳҺжҲҗзҘ–иөҗдәҲж јйІҒжҙҫй«ҳеғ§гҖҒе®—е–Җе·ҙејҹеӯҗгҖҒжҳҺе°ҒеӨ§ж…Ҳжі•зҺӢйҮҠиҝҰд№ҹеӨұгҖӮ
в‘Ј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ёүгҖӮ
в‘Өе–»и°Ұпј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еҚ·еҚҒд№қпјҢгҖҠжҳҺдә”еҸ°еұұжҳҫйҖҡеҜәжІҷй—Ё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гҖӮ
в‘ҘеҸӮзңӢдҪ•еӯқиҚЈпјҡгҖҠжҳҺд»ЈеҚ—дә¬еҜәйҷўз ”究гҖӢпјҢдёӯеӣҪзӨҫдјҡ科еӯҰеҮәзүҲзӨҫ2000е№ҙзүҲпјҢ第35йЎөгҖӮжҢүжҳҺиҝҒйғҪеҢ—дә¬еҗҺпјҢеҚ—дә¬иғҪд»ҒеҜәд»ҚеӯҳгҖӮеҢ—дә¬зҡ„еӨ§иғҪд»ҒеҜәжӯЈжҳҜжүҝиўӯеҚ—дә¬иғҪд»ҒеҜәиҖҢжқҘпјҢиҜҘеҜәеңЁеҢ—дә¬иҘҝеҹҺе…ө马еҸёиғЎеҗҢд»ҘеҢ—пјҢе…¶ең°еӣ еҜәиҖҢеҗҚдёәиғҪд»ҒеҜәиғЎеҗҢгҖӮеҢ—дә¬еӨ§иғҪд»ҒеҜәд»Ҡе·ІдёҚеӯҳгҖӮ
в‘ҰгҖҠйҮ‘йҷөжҘҡеҲ№еҝ—гҖӢеҚ·еҚҒе…ӯпјӣпјҲжҳҺпјүеҚ—зҘ йғЁйғҺй’ұеЎҳи‘ӣеҜ…дә®пјҡгҖҠе…«еӨ§еҜәйҮҚи®ҫе…¬еЎҫзў‘и®°гҖӢгҖӮ
⑧йҷҲжҘ пјҡгҖҠжҳҺеҲқеә”иҜҸдҪҝи—Ҹй«ҳеғ§е®—жіҗдәӢиҝ№иҖғеҸҷгҖӢпјӣйҷҲжҘ пјӣгҖҠи—ҸеҸІдёӣиҖғгҖӢпјҢж°‘ж—ҸеҮәзүҲзӨҫ1998е№ҙзүҲпјҢ第202гҖҒ222йЎөгҖӮ
гҖҖгҖҖи°ўйҮҚе…үгҖҒзҷҪж–ҮеӣәпјҡгҖҠдёӯеӣҪеғ§е®ҳеҲ¶еәҰеҸІгҖӢ第249йЎөпјҡвҖңж°ёд№җиҝҒйғҪд»ҘеҗҺеҪўжҲҗдәҶеҢ—дә¬е’ҢеҚ—дә¬дёӨеҘ—ж”ҝеәңжңәжһ„пјҢеҸҚжҳ еңЁеғ§е®ҳдҪ“еҲ¶дёӯпјҢдәҰжңүеҢ—дә¬еғ§еҪ•еҸёе’ҢеҚ—дә¬еғ§еҪ•еҸёд№ӢеҲ«гҖӮеҢ—дә¬еғ§еҪ•еҸёжҳҜеғ§еҸёжӯЈжң¬жүҖеңЁгҖӮвҖқ
в‘ЁгҖҠжҳҺеӨӘзҘ–е®һеҪ•гҖӢеҚ·дёҖдёғе…ӯпјҢжҙӘжӯҰеҚҒе…«е№ҙеҚҒдәҢжңҲдёҒе·іпјҡвҖңе»әйёЎйёЈеҜәдәҺйёЎйёЈеұұпјҢд»ҘзҘ жўҒеғ§е®қе…¬пјҢе‘Ҫеғ§еҫ·з‘„дҪҸжҢҒгҖӮз‘„еҚ’пјҢйҒ“жң¬з»§д№ӢгҖӮеҲқпјҢжңүиҘҝз•Әеғ§жҳҹеҗүзӣ‘и—ҸдёәеҸіи§үд№үпјҢеұ…жҳҜеұұпјҢиҮіжҳҜпјҢеҲ«дёәйҷўеҜәиҘҝд»Ҙеұ…д№ӢвҖқгҖӮжҢүпјҡи§үд№үдёәеғ§еҪ•еҸёиЎҷзҪІең°дҪҚиҫғдҪҺзҡ„еғ§е®ҳгҖӮжҳҺж°ёд№җзҡҮеёқзӯүз»Ҹеёёд»ҘвҖңйўқеӨ–зјәвҖқзҡ„ж–№жі•жҠҠеғ§еҪ•еҸёдёӯзҡ„вҖңи®Із»ҸвҖқгҖҒвҖңи§үд№үвҖқзӯүе“ҒдҪҚиҫғдҪҺзҡ„еғ§иҒҢжҺҲз»ҷиҘҝз•Әе–Үеҳӣеғ§дәәпјҢдёҚеӨұдёәдёҖз§ҚзҫҒзё»з¬јз»ңзҡ„жүӢж®өгҖӮ
в‘©гҖҠйҮ‘йҷөжўөеҲ№еҝ—В·й’ҰеҪ•йӣҶгҖӢгҖӮ
пј»11пјҪеӣәе§Ӣеҷ¶дёҫе·ҙВ·жҙӣжЎ‘жіҪеҹ№пјҡ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пјҢйҷҲеәҶиӢұгҖҒд№ҢеҠӣеҗүиҜ‘жіЁ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90е№ҙзүҲпјҢ第62йЎөгҖӮ
пј»12пјҪеҗҢжіЁпј»11пјҪгҖӮ
пј»13пјҪеҗҢжіЁпј»12пјҪгҖӮ
пј»14пјҪи—Ҹж–ҮеҸІзұҚгҖҠиҙӨиҖ…е–ңе®ҙгҖӢдёӯжӣҫиҜҰз»ҶеҸҷиҝ°еҷ¶зҺӣе·ҙеңЁеҚ—дә¬дёҫиЎҢжі• дјҡд№ӢзӣӣеҶөпјҡвҖңвҖҰвҖҰж¬ЎжңҲдә”ж—Ҙе§ӢпјҢеј№еҶ…еӨ–еқӣеҹҺд№ӢеўЁзәҝпјҢе°ҡеёҲд№ғи®ҫеҚҒдәҢеқӣеҹҺпјҢжӯӨеҚіиғңжө·гҖҒе®қзЎ•ж©ӣгҖҒй«ҳж—Ҙз“Ұдј дёӢд№ӢеҜҶйӣҶгҖҒеӨ§еёҲдј дёӢд№ӢеҜҶжңӯгҖҒд»–еҰӮйҮ‘еҲҡз•Ңжі•з•Ңд№ӢзҒҢйЎ¶гҖҒе–ңйҮ‘еҲҡгҖҒе°ҠиғңжҜҚгҖҒжҷ®жҳҺгҖҒиҚҜеёҲдҪӣгҖҒеәҰжҜҚд»ӘиҪЁгҖҒи§Ӯйҹіе’’гҖӮпј»дҪңжі•пјҪд№ӢеҲқпјҢзҡҮеёқдәІдёҙпјҢеҗ‘е°ҡеёҲдёүдәәеҘүиө е…ЁйғЁзӨје“ҒпјҢиөҗеғ§дәәиЎЈжңҚиЎЁйҮҢеӣӣиўӯпјҢе…¶д»–е®ҲеқӣеҹҺиҖ…иЎЈжңҚиЎЁйҮҢдёҖиўӯпјҢзҡҶзҡҮеёқеҸ–иө гҖӮд»ӘиҪЁиҝӣиЎҢзӣҙиҮіеҚҒе…«ж—ҘпјҢз»Ҳж—ҘеҗҒиҜ·й«ҳзҡҮеёқгҖҒй«ҳзҡҮеҗҺд№ӢзҒөйҷҚдёҙпјҢе°ҡеёҲеҗ„дәҲд»ҘзҒҢйЎ¶пјҢд»–дәәеҲҷдҪңи§Ји„ұд»ӘиҪЁвҖҰвҖҰвҖқиҪ¬еј•иҮӘйӮ“й”җйҫ„пјҡгҖҠпјңиҙӨиҖ…е–ңе®ҙпјһжҳҺж°ёд№җж—¶е°ҡеёҲе“Ҳз«Ӣйә»жҷӢдә¬зәӘдәӢз¬әиҜҒгҖӢпјҢиҪҪгҖҠдёӯеӣҪи—ҸеӯҰгҖӢ1992е№ҙ第3жңҹгҖӮ
пј»15пјҪеӣәе§Ӣеҷ¶дёҫе·ҙВ·жҙӣжЎ‘жіҪеҹ№пјҡ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пјҢйҷҲеәҶиӢұгҖҒд№ҢеҠӣеҗүиҜ‘жіЁ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90е№ҙзүҲпјҢ第63йЎөгҖӮеҸҰдёҺ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дёӯзҡ„и®°иҪҪеӨ§иҮҙзӣёеҗҢгҖӮеәҰжҜҚпјҡи—ҸиҜӯиҪЁвҖңеҚ“зҺӣвҖқпјҢжўөж–ҮдёәTaraпјҢжұүиҜ‘вҖңж•‘еәҰдҪӣжҜҚвҖқжҲ–вҖңеӨҡзҪ—иҸ©иҗЁвҖқгҖӮвҖңеӨҡзҪ—вҖқеңЁжўөж–Үдёӯж„ҸдёәзңјзқӣпјҢеӣ е…¶дә§з”ҹдәҺеӨ§жӮІи§Ӯдё–йҹіиҸ©иҗЁд№Ӣзӣ®иҖҢжқҘпјҢеҸҲеӣ еәҰжҜҚжҳҜи§Ӯдё–йҹіеҢ–иә«иҸ©иҗЁзҡ„ж•‘еәҰиӢҰйҡҫзҡ„жң¬е°ҠпјҢж•‘жөҺиҜёйҡҫпјҢ并е°ҶиҜёйҡҫйҖҒиҮіеҪјеІёпјҢж•…иҖҢеҫ—ж•‘еәҰд№ӢеҗҚгҖӮж №жҚ®е”җд»ЈжүҖиҜ‘гҖҠж•‘еәҰдҪӣжҜҚдәҢеҚҒдёҖз§ҚзӨјиөһз»ҸгҖӢпјҢеәҰжҜҚеӨҡд»ҘеҢ–иә«жҳҫзҺ°пјҢдёҖиҲ¬дёә21зӣёпјҢдҪҶеңЁ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дёӯжүҖеҮәзҺ°зҡ„еәҰжҜҚзәҰжңү30з§Қд№ӢеӨҡпјҢжҳҜйҮҚиҰҒзҡ„еҘіжҖ§е°ҠзҘһгҖӮеңЁи—Ҹдј дҪӣж•ҷеҜҶе®—з»Ҹе…ёдёӯеҸҲз”Ёд»Ҙз§°и°“жҳҺеҰғпјҲйҷҖзҪ—е°јпјүгҖӮи—Ҹдј дҪӣж•ҷиүәжңҜйҖ еһӢдёӯпјҢжңҖеёёи§Ғзҡ„еәҰжҜҚеғҸдёәз»ҝеәҰжҜҚе’ҢзҷҪеәҰжҜҚгҖӮ
пј»16пјҪеҸӮи§Ғпј»ж„ҸпјҪеӣҫйҪҗгҖҒпј»еҫ·пјҪжө·иҘҝеёҢпјҡгҖҠиҘҝи—Ҹе’Ңи’ҷеҸӨзҡ„е®—ж•ҷгҖӢпјҢиҖҝжҳҮиҜ‘гҖҒзҺӢе°§ж Ўи®ў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89е№ҙзүҲпјҢ第80гҖҒ82йЎөгҖӮ
пј»17пјҪгҖҠиҙӨиҖ…е–ңе®ҙгҖӢпјҲи—Ҹж–ҮпјүпјҢж°‘ж—ҸеҮәзүҲзӨҫ1986е№ҙзүҲпјҢ第1007йЎөпјҡвҖңвҖҰвҖҰ延иҜ·иҝӣе®«пјҢе»әз«ӢеқӣеҹҺпјҢдёәзҡҮеёқеҸ—ж— йҮҸзҒҢйЎ¶гҖӮдёӢжңҲпјҲдёүжңҲпјүдёҠж—¬е…«ж—ҘпјҢејҖе§Ӣи®Іи§Је…ӯжі•пјҢзҡҮеёқеҘүиЎҢз„үвҖқгҖӮ
пј»18пјҪгҖҠеӨ§ж–№е№ҝдҪӣеҚҺдёҘз»ҸгҖӢеҚ·дәҢеҚҒд№қгҖҠиҸ©иҗЁдҪҸе“ҒеӨ„гҖӢпјҢи§ҒгҖҠеӨ§жӯЈж–°дҝ®еӨ§и—Ҹз»ҸгҖӢеҚ·д№қпјҢ第9йЎөгҖӮ
пј»19пјҪгҖҠж—§е”җд№ҰгҖӢеҚ·еҚҒдёғгҖҠ敬宗жң¬зәӘгҖӢпјҡвҖңпјҲй•ҝеәҶеӣӣе№ҙпјүд№қжңҲз”ІеӯҗпјҢеҗҗи•ғ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вҖқпјӣгҖҠеҶҢеәңе…ғйҫҹгҖӢеҚ·д№қд№қд№қгҖҠеӨ–иҮЈйғЁВ·иҜ·жұӮгҖӢпјҡвҖңз©Ҷе®—й•ҝеәҶеӣӣе№ҙд№қжңҲз”ІеӯҗпјҢзҒөжӯҰиҠӮеәҰдҪҝжқҺиҝӣиҜҡеҘҸпјҢеҗҗи•ғйҒЈдҪҝжұӮ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гҖӮеұұеңЁд»Је·һпјҢеӨҡжө®еӣҫд№Ӣиҝ№пјҢиҘҝжҲҺе°ҡжӯӨж•ҷпјҢж•…жқҘжұӮд№ӢвҖқгҖӮ
пј»20пјҪе·ҙВ·иөӣеӣҠгҖҠжӢ”еҚҸгҖӢпјҲи—Ҹж–ҮпјүпјҢж°‘ж—ҸеҮәзүҲзӨҫ1980е№ҙзүҲгҖӮ
пј»21пјҪж•Ұз…ҢеҶҷеҚ·P4648еҸ·пјҢиҜҘеҚ·еҶ…е®№и®°еҪ•ж•Ұз…Ңеғ§дәәжңқзӨјдә”еҸ°еұұзҡ„з»ҸиҝҮпјҢеҚ·ж–Үдёӯжңүи®°пјҡвҖңеҸҲиЎҢеҚҒйҮҢпјҢеҲ°еӨӘеҺҹеҹҺвҖҰвҖҰдәҢжңҲе»ҝе…«ж—ҘдёӢжүӢз”»гҖҠдә”еҸ°еұұеӣҫгҖӢпјҢе»ҝд№қж—Ҙй•ҝз”»иҮіз»ҲвҖқпјӣеҸӮи§Ғжқңж–—иҜҡпјҡгҖҠж•Ұз…Ңдә”еҸ°еұұж–ҮзҢ®ж ЎеҪ•з ”究гҖӢпјҢеұұиҘҝдәәж°‘еҮәзүҲзӨҫ1991е№ҙзүҲпјҢ第141йЎөгҖӮ
пј»22пјҪжқңж–—иҜҡпјҡгҖҠж•Ұз…Ңдә”еҸ°еұұж–ҮзҢ®ж ЎеҪ•з ”究гҖӢпјҢеұұиҘҝдәәж°‘еҮәзүҲзӨҫ1991е№ҙзүҲпјҢ第141йЎөпјӣеҸҰи§ҒжүҺжҙӣпјӣгҖҠеҗҗи•ғжұӮдә”еҸ°еұұеӣҫеҸІдәӢжқӮиҖғгҖӢпјҢиҪҪгҖҠж°‘ж—Ҹз ”з©¶гҖӢ1998е№ҙ第1жңҹгҖӮ
пј»23пјҪгҖҠжҳҺеӨӘе®—е®һеҪ•гҖӢеҚ·дә”дёҖпјҢж°ёд№җдә”е№ҙдёғжңҲзҷёй…үжқЎгҖӮ
пј»24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ёүгҖҠеӨ§е®қжі•зҺӢдј гҖӢгҖӮ
пј»25пјҪеҗҢдёҠд№ҰпјҢеҚ·дәҢгҖӮ
пј»26пјҪе–»и°Ұпј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еӣӣйӣҶеҚ·еҚҒд№қгҖӮ
пј»27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ёүгҖҠйҮҠиҝҰд№ҹеӨұдј гҖӢгҖӮ
пј»28пјҪгҖҠеӨ§ж…Ҳжі•зҺӢдј гҖӢпјҲи—Ҹж–ҮжҠ„жң¬пјүпјҢ第13йЎөдёҠгҖӮ
пј»29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әҢгҖӮ
пј»30пјҪд»»е®қж №гҖҒжқЁе…үж–Үзј–гҖҠдёӯеӣҪе®—ж•ҷеҗҚиғңгҖӢпјҢеӣӣе·қдәәж°‘еҮәзүҲзӨҫ1989е№ҙзүҲпјҢ第88йЎөгҖӮ
пј»31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әҢгҖӮ
пј»32пјҪеӣәе§Ӣеҷ¶дёҫе·ҙВ·жҙӣжЎ‘жіҪеҹ№пјҡгҖҠи’ҷеҸӨдҪӣж•ҷеҸІгҖӢпјҢйҷҲеәҶиӢұгҖҒд№ҢеҠӣеҗүиҜ‘жіЁпјҢеӨ©жҙҘеҸӨзұҚеҮәзүҲзӨҫ1990е№ҙзүҲпјҢ第63йЎөгҖӮ
пј»33пјҪеҗҢжіЁпј»35пјҪгҖӮ
пј»34пјҪжІҢи°·пјҡгҖҠдә”еҸ°еұұеҸӮи®°ж—Ҙи®°гҖӢпјҢи§ҒгҖҠж–°жёёи®°зі»еҲ—з»ӯзј–гҖӢпјҢдёӯеҚҺд№ҰеұҖеҮәзүҲпјҢ第2еҶҢгҖӮ
пј»35пјҪпјҲжҳҺпјүйҮҠй•Үжҫ„пјҡгҖҠжё…еҮүеұұеҝ—гҖӢеҚ·дә”гҖӮ
пј»36пјҪе…¶дәӢиҝ№еҸӮи§Ғе–»и°ҰпјҡгҖҠж–°з»ӯй«ҳеғ§дј гҖӢеӣӣйӣҶеҚ·дёғгҖӮ
пј»37пјҪгҖҠжҳҺеӨӘе®—е®һеҪ•гҖӢеҚ·дёҖдәҢдә”пјҢж°ёд№җдәҢеҚҒдёҖе№ҙеӣӣжңҲе·ұе·іжқЎ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