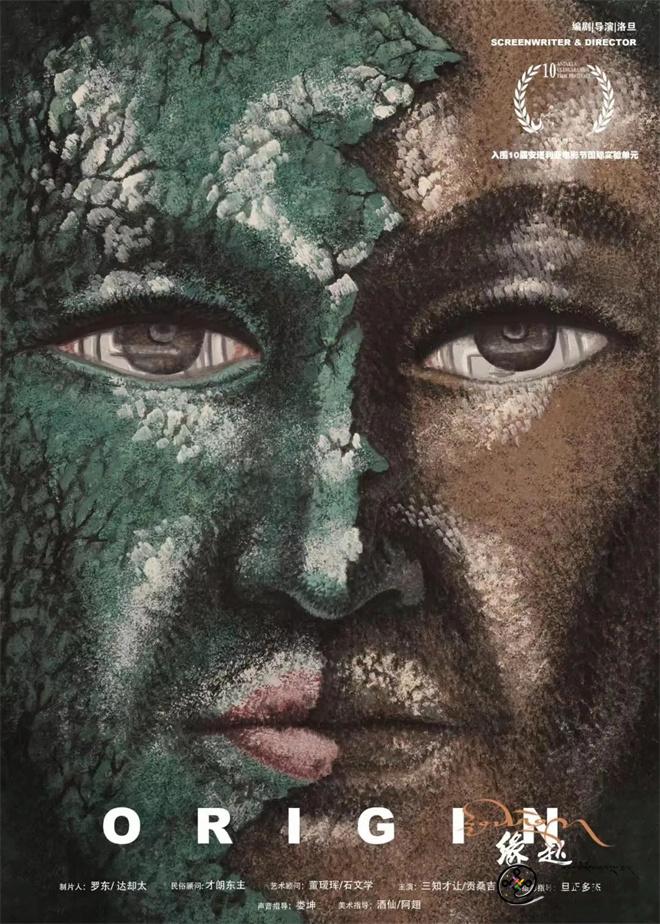在今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藏语黑白电影《塔洛》获得世界媒体的格外关注,该片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与来自全世界的30多部影片一起角逐该奖项。《塔洛》于北京时间9月4日在威尼斯影展举行了首映式,当时放映厅1000多个座位几近坐满,电影结束后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首次携作品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9月8日晚,本报记者拨通万玛才旦在意大利威尼斯居住的德尔菲诺酒店的房间电话,电话那头的他,声音低缓、态度谦和,与他的电影保持着一致的风格。

身份的迷失焦虑
《塔洛》是万玛才旦的第五部长片,沿袭了他作品一贯的藏族背景和藏语对白形式,全片使用固定镜头,用缓慢的节奏讲述孤独的牧羊人塔洛的故事:单纯质朴的塔洛在县城邂逅一位女孩并与其相爱,不料惨遭背叛并被女孩骗走所有钱财。之后,塔洛迷失了自我,深陷悔恨和纠结。
万玛才旦说,塔洛的遭遇在如今的边远藏区年轻人身上有着普遍性:他们被从未体验过的现代文明所吸引,却又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新奇。一些人想要寻求未知的生活,但又躲不过内心对自己原生状态和传统文化的认可,最终迷失自我。
作为一名离开家乡的藏族人,万玛才旦比塔洛更有身份焦虑感。“因为你走出自己的空间,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会形成一个参照,焦虑感会更强。很多时候,我和塔洛一样,是一种无所适从,有时候也会迷茫,很难找到一个出口。”他告诉本报记者。

《国际先驱导报》:《塔洛》通过一个去城镇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牧羊人的故事,来表达藏族人的身份焦虑,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还是你创造的人物?
万玛才旦:电影《塔洛》改编自我三年前写的一个同名短篇小说,塔洛也没有什么原型,是完全虚构的一个人物,先是有了这样一个意象——塔洛有个小辫子,然后就开始慢慢设置这个人物,在设置过程中就想到藏族村民办身份证的事件,然后在办身份证过程中,叫到他真名塔洛的时候,村民和村长都记不起来村里有这样一个人,后来就是到处打听之后,大家才突然想起:塔洛不就是“小辫子”吗?
Q:电影结尾,塔洛用鞭炮自残,基调比较悲观暗淡,是否意味着你想表达现代文明对传统藏族文化中那些好的价值观的冲击?
A:从大的方面可以这样理解,像塔洛这样一个人物经历过这样的现实生活后,他的结局我觉得只能是这样了;另一方面,也是对人性中很多事情的一个态度。
Q:塔洛的扮演者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名喜剧演员,由他来演一个悲剧性人物,你作为导演是不是要花很大工夫把演员最好的一面带出来?
A:这是我们当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一直演喜剧小品、相声,他的表演包括说话的语气语调有很多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主要是看准他的一些特征和我想象中的塔洛的形象比较接近,比如说,他本身就有一个小辫子,另外他的年龄也比较接近塔洛。
我和他是朋友,了解他平时生活中的状态,与他做喜剧演员有很大的反差,这是我看中他的一点。他自己看了剧本也有些担心,觉得挑战很大,跟他以前的表演经验完全不一样,但是他非常想出演这个角色。

藏地实际生活节奏决定电影风格
Q:你被称为“现在最好的西藏题材导演”,你拍的藏语电影形成了自己较为统一的纪实美学的电影风格。你是如何探索自己的电影风格的?
A:这和我自己的经历、所选择的题材方向,以及在电影学院学习电影的几年有关系,具体到每部电影,是和电影的内容有关系,是内容决定了形式。表面看起来“藏地三部曲”有一些相似性,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几部电影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每个故事有一个适合它的表现方式。
我的电影风格和藏地实际的生活状况或者生活节奏、文化的状态有关系。《塔洛》不可能用商业片的镜头语言去呈现,它更适合于缓慢的固定的镜头语言来呈现。在那样的节奏之中,才能凸显出塔洛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他在山上一个人的生活,那么多场戏,却几乎没有一句台词,全是他一个人孤独生活的状态。
Q:拍这种电影会不会担心观众比较少?普通观众比较习惯于情节紧凑、戏剧性强的商业电影。
A:这个倒没有担心,主要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创作,这样的内容还得用适合它的一种方式。这样一个故事,这样的对人物的把握,如果用那种方式呈现的话,那就不对了,也没有必要。
我所做的是一个本能的创作,这样的创作有相应的观众,我们没有必要去拍适合每个观众看的电影,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Q:你下一部电影是类型化的电影吗?
A:我正在筹备《永恒的一天》,不是那种很商业型的所谓的类型片,但在形态、内容上和前面的电影不一样,内容层面上有点魔幻现实主义,是彩色电影。它改编自我一个朋友的两部小说,是讲一个人在一天时间经历了一生,也是藏语电影,也是藏族人的故事。这个剧本已经立项了,今年年底开始筹拍,会断断续续拍摄一年。

藏语电影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万玛才旦的电影刻意避开地域风光、民族风情等外界对西藏的猎奇期待,而是聚焦人的情感和处境。在他看来,关于人性的主题,能够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心灵触动和情感共鸣,这也是他的电影走出国门、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的原因之一。“《塔洛》能够入选威尼斯,肯定不是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而是对它的内容和艺术性的综合考量。”万玛才旦说。
Q:《塔洛》入选威尼斯地平线单元,是否意味着藏语电影的现状好起来了?
A:一方面可以代表一部分,但也不能代表全部,一部电影进入了威尼斯也不能说整个藏语电影好起来了,后面还需要很多其他工业体系的支撑。藏语电影还处在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在慢慢形成规模。
我的电影和国内其他小成本电影制作的状况是一样的,按照电影的题材和规模来制定成本。上一部电影《五彩神箭》成本就比较大,是九百多万元,《永恒的一天》大概是六百万元,每个片子的状况都不一样。
Q:演员对你非常信任,你是如何请到巨焕仓活佛这样一位真正的活佛来出演《静静的嘛呢石》?
A:首先,因为大家都认识,有共同语言,交流接近起来很方便,大家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来合作,中间没有任何利益的关系,而是朝着一个共同目标来完成这个事情。大家基本上都是纯粹为了这部电影来参与工作的,整个过程没有我们以前听说过的剧组里很复杂的关系。
大家首先是有一种信任感,对相互的一个信任,同时也有一种自身的使命感,齐心协力去完成一个好的藏族母语电影。
Q:在你看来,藏族人是不是更能拍好纯粹的藏族电影?藏族电影人在自身的身份认同和电影专业方面如何平衡?
A:(我的电影)主创大部分是藏族人,也有很多汉族人,《塔洛》的摄影师、灯光师都是汉族。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电影作为一个工业,需要各种部门的人才汇聚起来。(是否藏族电影人更懂藏语和藏族的文化?)强调的就是这个,这样的考虑是为了更深入地创作,也不是说只是强调民族身份。你是一个藏族,但是你对你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深入地了解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对录音师的要求是首先他要会藏语,对藏族文化了解,才能把握演员台词,他能清晰地摸到里面细微的情感的东西,如果对语言不熟的话,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
Q:歌舞、影视剧等藏族文化今天在世界上的影响如何?
A:其实走出去的还是比较少。这两年的对外交流正在增多,大家对西藏文化的认知还是比较表面。像我的电影的话,可能就是对藏区当下的现实反映得更多一些。
Q:在你看来,汉藏两种文化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
A:有人说“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提法本身就比较片面。
首先,它不是单纯地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冲突这么简单的事,而是一个更大的东西:现代文明和原有传统文明的冲突,或是它们在一起的状态。除了藏族地区,汉族的很多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也会面临这样的状况。对此我很难马上提出解决的办法,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能在过程中看看怎么找到一个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