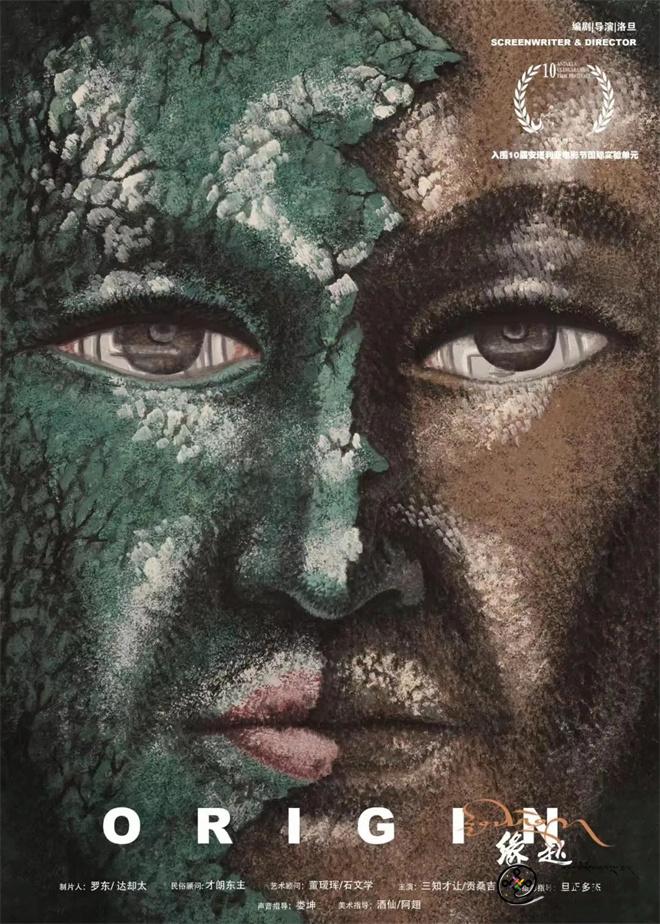采è®؟ç؛ھه½•ç‰‡م€ٹه¤©و²³م€‹ن¼—ن¸»هˆ›ï¼Œه‡ ن½چه¯¼و¼”说ه¾—眉é£è‰²èˆï¼Œهچ´è®©è®°è€…هگ¬ه¾—ه؟ƒوœ‰ن½™و‚¸ï¼Œé¢‘频é€په‡؛وƒٹ诧çڑ„眼ç¥م€‚هگ¬ن؛†ن»–ن»¬و»”و»”ن¸چç»çڑ„讲è؟°ï¼Œن»»è°پ都ن¼ڑهڈ‘ه‡؛è؟™و ·çڑ„و„ںو…¨ï¼ڑè؟™ç»ه¯¹وک¯ن¸ھن¸چوƒœهٹ›çڑ„و‘„هˆ¶ç»„,而و¤و¬،ç؛ھه½•ç‰‡çڑ„و‹چو‘„ن¹ںه ھ称وک¯وگڈه‘½ن¹‹و—…م€‚
ن¸€è؟›و°çژ›ه¤®ه®—
و°çژ›ه¤®ه®—ه†°ه·ï¼Œç›®ه‰چه…¬è®¤çڑ„é›…é²پè—ڈه¸ƒو±ںن¸»و؛گه¤´ï¼Œم€ٹه¤©و²³م€‹و‹چو‘„و—¶هچ وœ‰é‡چè¦پهˆ†é‡ڈçڑ„部هˆ†م€‚و—©هœ¨ه‡ ه¹´ه‰چ,è؟™éƒ¨ç؛ھه½•ç‰‡ç«‹é،¹و—¶ï¼Œو€»ه¯¼و¼”ن؛“ه…‹هگ›ه°±çژ‡éکںه¤ڑو¬،و¥هˆ°è؟™é‡Œهپڑه‰چوœں采é£ژم€‚هڈ¯ن¹ںو£ه¦‚ن؛“ه…‹هگ›و‰€è¨€ï¼Œو— è®؛ه‰چوœںçڑ„è°ƒç ”ه’Œé‡‡é£ژه¤ڑو‰ژه®ï¼Œن¹ںوŒ،ن¸چن½ڈçھپهڈ‘çٹ¶ه†µï¼Œو›´ن½•ه†µè؟™é‡Œوک¯ه¹³ه‡وµ·و‹”ç؛¦5600ç±³çڑ„é«کهژںم€‚
م€€ ه¯¼و¼”éƒè·ƒéھڈه¸¦é¢†çڑ„و‹چو‘„ه°ڈهˆ†éکںه…ˆهگژن¸‰و¬،هژ»و°çژ›ه¤®ه®—و‹چو‘„,除وœ€هگژن¸€و¬،و¯”较é،؛هˆ©ه¤–,ه‰چن¸¤و¬،都وک¯وƒٹه؟ƒهٹ¨é„çڑ„م€‚“وˆ‘و‹چن؛†30ه¹´ç‰‡هگ,ه“ھن¸€و¬،都و²،è؟™ن¸€و¬،ç…ژ熬ه•ٹï¼پ”ه›وƒ³ه½“هˆن¸‰è؟›و°çژ›ه¤®ه®—,éƒè·ƒéھڈéڑ¾وژ©ه£°éں³ن¸çڑ„و— ه¥ˆم€‚
م€€ è¦پهژ»و°çژ›ه¤®ه®—,ه°±ه؟…é،»هœ¨è·ç¦»ه†°ه·ه‡ ه…¬é‡Œه¤–çڑ„ن¸€ه¤„وµ·و‹”5200ç±³çڑ„ه¤ڈه£ç‰§هœ؛ه®‰èگ¥و‰ژه¯¨م€‚牧و°‘ه»؛è®®و‘„هˆ¶ç»„用و‘©و‰ک车è؟گ设ه¤‡ï¼Œهڈ¯ن»¥ن؟è¯په½“ه¤©ه›و¥م€‚
م€€ ن¸€è؟›و°çژ›ه¤®ه®—,ه› ن¸؛و²ںé€ڑن¸چ畅,牧و°‘çگ†è§£é”™ن؛†ï¼Œه¸¦ç€éƒè·ƒéھڈç‰ن؛؛ه…ˆهژ»ن؛†ن¸€ه؛§ه¯؛ه؛™è€Œéه†°ه·م€‚è‹¥هڈھوک¯ه¾’و¥èµ°ه¹³هœ°ï¼Œèµ°é”™ن؛†ن¹ںه°±ç½¢ن؛†ï¼Œن½†ن»–ن»¬وک¯è¶ںè؟‡ن؛†ه†°و²³و‰چهˆ°è¾¾è؟™é‡Œم€‚éƒè·ƒéھڈ说,و²³éپ“ن¸‹é¢è¦پن¸چه°±وک¯ه¾ˆهژڑçڑ„ç ‚çں³ه±‚,è¦پن¸چه°±وک¯و‰“و»‘çڑ„çں³ه¤´ï¼Œéپ‡هˆ°و°´ç¨چو·±ç‚¹çڑ„هœ°و–¹و‘©و‰ک车و ¹وœ¬èµ°ن¸چن؛†هڈھ能脱é‹وژ¨ç€è½¦è؟‡و²³م€‚é›…é²پè—ڈه¸ƒو±ںن¸ٹو¸¸و²³و®µçڑ„ن¸€ه¤§ç‰¹è‰²ه°±وک¯è¾«çٹ¶و²³éپ“,简هچ•è¯´ه°±وک¯وœ‰ه¾ˆه¤ڑو²³éپ“م€پهˆ†و”¯ه’Œن؛¤و±‡م€‚“وœ€هˆن¸چن؛†è§£ï¼Œهگژو¥è¶ںن؛†ن؛”و،ه†°و²³و‰چهˆ°ç›®çڑ„هœ°ï¼Œç«ں然è؟کèµ°é”™ن؛†م€‚ه¤ڑèµ°ن؛†ن¸¤ن¸‰ن¸ھه°ڈو—¶ï¼Œهڈˆه¾—è¶ںç€ه†°و²³هژںè·¯è؟”ه›م€‚”و¤هگژ,ن»–ن»¬éœ€è¦په†چè¶ںè؟‡ن¸€و،و›´ه¤§çڑ„ه†°و²³ï¼Œو²³و°´و¹چو€¥ï¼Œه؟…é،»و‰‹وŒ½و‰‹ن¸€èµ·èµ°Uه‹ç؛؟,و‰چ能ن¸چ被ه†²èµ°م€‚éƒè·ƒéھڈه¹¶ن¸چه‡†ه¤‡وٹٹه½“هˆçڑ„艰辛هٹ ن»¥èµکè؟°ï¼Œن½†ç…§ç‰‡ن¸ٹه†»ه¾—ç؛¢è‚؟çڑ„ه°ڈè…؟م€پ痛苦çڑ„é¢éƒ¨è،¨وƒ…هچ´è¯´وکژن؛†ن¸€هˆ‡م€‚“ه†°و°´هˆ؛éھ¨وک¯ه°ڈن؛‹ï¼Œè„ڑن¸‹çڑ„çں³ه¤´هڈˆه†·هڈˆو»‘,و»‘ن¸‹هژ»وک¯و›´ه¤ڑه°–çں³ï¼Œè‹¦ن¸چه ھ言م€‚”éƒè·ƒéھڈçژ°هœ¨وƒ³èµ·و¥è؟که؟چن¸چن½ڈçڑ±çœ‰ه¤´م€‚
م€€ ه¥½ن¸چه®¹وک“هœ¨وژ¥è؟‘ن¸هچˆو—¶هˆ°è¾¾ن؛†ه†°ه·ن¸‹é¢ï¼Œه¤§ه®¶ه¼€ه§‹و£ه¼ڈو‹چو‘„م€‚هژںè®،هˆ’éƒè·ƒéھڈه¸¦ه¤§و‘„هƒڈوœ؛هœ¨ه†°ه·ن¸‹çڑ„ه†°و¹–ه‡؛و°´ه¤„و‹چو‘„,و‘„هƒڈه¸ˆèŒƒوˆگو¦ه¸¦ه°ڈوœ؛ه™¨ن¸ژهگ‘ه¯¼ن»ژه†°èˆŒه¤„è؟›ه…¥ه†°ه·و‹چو‘„م€‚éƒè·ƒéھڈه†چن¸‰هڈ®هک±ن»–,ن¸چè®؛و‹چه¾—و€ژو ·ï¼Œن¸‹هچˆ4点ه‰چه؟…é،»ه‡؛و¥ï¼Œن؟وŒپé€ڑ讯畅é€ڑم€‚è°پçں¥ه‡ ن¸ھه°ڈو—¶è؟‡هژ»ن؛†ï¼ŒèŒƒوˆگو¦ه’Œهگ‘ه¯¼هچ´ه¹¶و²،ه‡؛و¥ï¼Œو‰‹وœ؛هœ¨é‚£é‡Œو²،وœ‰ن؟،هڈ·ï¼Œه¯¹è®²وœ؛ن¹ںèپ”ç³»ن¸چن¸ٹم€‚眼看è؟‡ن؛†16点,ه¤ھéک³ه؟«ن¸‹ه±±ن؛†ï¼Œç‰§و°‘说ه†چن¸چ走,وپگو€•ن¼ڑه†»و»هœ¨è؟™é‡Œم€‚éƒè·ƒéھڈه‡ è؟‘ه´©و؛ƒï¼ڑ“è°پن¹ںن¸چه‡†èµ°ï¼پç‰ه°ڈ范ï¼پ”
م€€ éڑڈهگژ,ن»–و‹؟ç€ه¯¹è®²وœ؛ه¤§ه–ٹï¼ڑ“ه°ڈ范ï¼په°ڈ范ï¼په›ç”ï¼پ”هڈ¯وک¯ن¸€ç‚¹ه£°éں³éƒ½و²،وœ‰م€‚ه¤©è‰²هڈکé’,ن¹Œن؛‘ç؟»و»ڑ,ن»–وژ¥è؟‘ç»وœ›م€‚çھپ然,ن¹Œن؛‘ç¼éڑ™ن¸ه°„ه‡؛وœ€هگژن¸€ç¼•éک³ه…‰ï¼Œه†°èˆŒه¤„çھپ然ه‡؛çژ°ن¸¤ن¸ھن؛؛ه½±م€‚“وک¯ه°ڈ范ï¼پé‚£è،£وœچوˆ‘认识ï¼پ”ن¹ںé،¾ن¸چن¸ٹé«کهژںهڈچه؛”ن؛†ï¼Œéƒè·ƒéھڈه†²è؟‡هژ»وٹ±ن½ڈه·²ç»ڈه¤±èپ”5ن¸ھه°ڈو—¶çڑ„范وˆگو¦م€‚
هگژو¥èŒƒوˆگو¦ه‘ٹ诉ه¤§ه®¶ï¼Œن»–çں¥éپ“وœ؛ن¼ڑéڑ¾ه¾—,و‰€ن»¥هœ¨ه†°ه·ن¸‹هپڑه»¶و—¶و‹چو‘„,èٹ±è´¹ن؛†ه¤ھé•؟و—¶é—´ï¼Œه¯¹è®²وœ؛هڈˆو²،电ن؛†ï¼Œé€”ن¸و›´وک¯éپéپ‡èگ½çں³ï¼Œè‚©è†€è¢«ç ¸ن¼¤ï¼Œé™©ن؛›èگ½ه…¥ه†°و¹–,能و´»ç€ه‡؛و¥ه¤ھن¸چوک“م€‚“é‚£ه¤©ه¤œé‡Œ12点و‰چه›هˆ°ç‰§هœ؛,و¤هگژ,وˆ‘هڈچه¤چه‘ٹ诉组里çڑ„ه¹´è½»ن؛؛,هڈھè¦پ能ن؟éڑœç”ںه‘½ه®‰ه…¨ï¼Œن»€ن¹ˆن¸œè¥؟都ن¸چé‡چè¦پï¼پ”éƒè·ƒéھڈ说éپ“م€‚

ه†چè؟›و°çژ›ه¤®ه®—
م€€ و€»ه¯¼و¼”ن؛“ه…‹هگ›هœ¨م€ٹه¤©و²³م€‹و£ه¼ڈه¼€و‹چه‰چ,ه°±و¥è؟‡و°çژ›ه¤®ه®—ن¸‰و¬،م€‚而هœ¨éƒè·ƒéھڈن¸€è،Œن؛؛و‹چو‘„ه®Œو¯•هگژ,هœ¨èˆھو‹چن¸ٹوœ‰ç€ن¸°ه¯Œç»ڈéھŒçڑ„ن»–هڈˆه¸¦ç€èˆھو‹چ组و¥هˆ°è؟™é‡Œو‹چو‘„م€‚ن؛“ه…‹هگ›çڑ„è؟گو°”و²،وœ‰éƒè·ƒéھڈه¥½ï¼Œن»–ن»¬هˆ°و¥و—¶وک¯ن¹هچپوœˆن»½ï¼Œç‰§و°‘ه·²ç»ڈ转هœ؛,ه¤ڈه£ç‰§هœ؛里ç©؛و— ن¸€ن؛؛,و²،وœ‰و‘©و‰ک车ه’Œç‰¦ç‰›ه¸®ه؟™èƒŒè®¾ه¤‡م€‚و±½è½¦ن¹ںهڈھ能ه¼€هˆ°ن¸€ه®ڑçڑ„è·ç¦»ï¼Œو‰€ن»¥è¦پوƒ³هˆ°ه†°ه·ن¸‹و‹چو‘„,ه؟…é،»é و‘„هˆ¶ç»„وˆگه‘که…¨ç¨‹ه¾’و¥م€‚“هچ•ç¨‹èµ°ن؛†8ن¸ھه°ڈو—¶ï¼Œو‹چو‘„ن¸€ن¸¤ن¸ھه°ڈو—¶ن¹‹هگژ,ه†چèµ°8ن¸ھه°ڈو—¶ه›و¥ï¼Œو¯ڈن¸ھن؛؛è؛«ن¸ٹ背ç€هگ„ç§چه™¨وگ,هŒ…و‹¬èˆھو‹چ用çڑ„و— ن؛؛وœ؛م€‚ن؛؛و•°وœ‰é™گ,背设ه¤‡ه°±èƒŒن¸چن؛†è،¥ç»™ï¼Œو‰€ن»¥ن¹ںن¸چ能ه®؟èگ¥هœ¨é‚£é‡Œï¼Œه؟…é،»ه›ن½ڈهœ°م€‚”ن؛“ه…‹هگ›è¯´م€‚
8ن¸ھه°ڈو—¶çڑ„é«کهژںè´ںé‡چه¾’و¥ï¼Œوک¯éڑ¾ن»¥وƒ³هƒڈçڑ„艰éڑ¾ï¼Œه¹´è½»ن؛؛ه’¬ç‰™و’‘ن؛†ن¸‹و¥ï¼Œ58ه²پçڑ„ن؛“ه…‹هگ›èµ°هˆ°é‚£é‡Œه°±هڈ‘çژ°ï¼Œè†ç›–ه·²ç»ڈè‚؟èµ·و¥م€‚èˆھو‹چé،؛هˆ©ه®Œوˆگهگژ,ن؛“ه…‹هگ›çڑ„è†ç›–ه‡ ن¹ژه¼¯ن¸چن؛†ن؛†ï¼Œوژ¥ن¸‹و¥8ن¸ھه°ڈو—¶ه¾’و¥ه›هژ»وˆگن؛†ه¤§é—®é¢کم€‚“وˆ‘è¦پوک¯ن¸چ走,è؟™ç¾¤ه¹´è½»ن؛؛è°پن¹ںن¸چن¼ڑ走,و‰€ن»¥è‚¯ه®ڑن¸چ能ه®³ن؛†ن»–ن»¬ï¼ŒوŒھن¹ںه¾—وŒھه›هژ»ï¼پ”ن؛“ه…‹هگ›ه؟چç€ه·¨ه¤§çڑ„疼痛è·ںç€éکںن¼چه¾€ه›èµ°م€‚ه®هœ¨èµ°ن¸چهٹ¨ن؛†ï¼Œن¸¤ن¸ھéکںه‘کو‹–ç€ن»–ن¸¤و،胳è†ٹ,ن¸€ن¸ھéکںه‘کوژ¨ç€ن»–è…°ه¸®ن»–,走هچپو¥ن¼‘وپ¯ن¸€ن¸‹م€‚ه¹¸ه¥½ه½“هœ°çڑ„هڈ¸وœ؛ه¸®ه؟™وٹٹ车هگهڈˆه¾€è؟‘ه¤„ه¼€ن؛†ه¼€ï¼Œن؛“ه…‹هگ›ه’Œéکںه‘که°±è؟™ن¹ˆهچپو¥هچپو¥هœ°وŒھن؛†ه‡؛و¥م€‚
ن»–è؟کè®°ç€ï¼Œهژ»ه¹´çڑ„ن¸ç§‹èٹ‚ه°±وک¯هœ¨é‚£و®µو‹چو‘„çڑ„و—¥هگ里ه؛¦è؟‡çڑ„م€‚ن»–说ï¼ڑ“وˆ‘ن»¬ه›هˆ°èگ¥هœ°ï¼Œو¯ڈن¸ھن؛؛وµ‘è؛«ç–¼ه¾—ن¸چè،Œï¼Œçœ‹ç€هڈˆه¤§هڈˆهœ†çڑ„وœˆن؛®ï¼Œوœ‰ن¸ھن؛؛用ه¯¹è®²وœ؛说ن؛†ن¸€هڈ¥ï¼ڑن»ٹه„؟ه…«وœˆهچپن؛”م€‚然هگژه†چو²،وœ‰ن¸€ن¸ھن؛؛说è¯ï¼Œه¤§ه®¶هڈھوک¯çœ‹ç€وœˆن؛®م€‚”
采è®؟ه‰§ç»„ه½“ه¤©ï¼Œن؛“ه…‹هگ›è¯·و¥4ن¸ھه¯¼و¼”ه’Œè®°è€…ç•…èپٹن؛†ه¤§ç؛¦8ن¸ھه°ڈو—¶ï¼Œè€Œو¯ڈو¯ڈ记者问起ن»–çڑ„و•…ن؛‹ï¼Œن»–و€»وک¯è½»وڈڈو·،ه†™هœ°ه¸¦è؟‡م€‚ن½†è®°è€…辗转ه¾—çں¥ï¼Œه› ن¸؛é«کهژںهڈچه؛”ه’Œه·¥ن½œçڑ„هٹ³ç´¯ï¼Œن؛“ه…‹هگ›çœ¼ه؛•ن¸¥é‡چه‡؛è،€ï¼Œç»ڈè¯ٹو–视网膜病هڈکن¸‰ç؛§ï¼Œوژ¥è؟‘ه¤±وکژ,هœ¨ç»ڈè؟‡ه¾ˆé•؟ن¸€و®µو—¶é—´çڑ„و²»ç–—هگژ,ن¸€هڈھ眼ç›çں«و£è§†هٹ›0.6,ن¸€هڈھ眼ç›هچ´ن»چهڈھوœ‰0.2م€‚“هŒ»ç”ںو—©ه°±ن¸چ让وˆ‘看电脑م€پ看و‰‹وœ؛ن؛†ï¼Œهڈ¯è؟™ن¹ˆه¤§ن¸€ن¸ھé،¹ç›®ç‰ç€وˆ‘ه‘¢ï¼Œم€ٹه¤©و²³م€‹وک¯وˆ‘çڑ„هˆ›و„ڈم€پوˆ‘وڈگه‡؛çڑ„é،¹ç›®ï¼Œو€»ن¸چ能甩و‰‹ن¸چç®،هگ§ï¼ںè؟™وک¯ه…³ن؛ژه°ٹن¸¥ه’ŒèپŒن¸ڑéپ“ه¾·çڑ„é—®é¢ک,وˆ‘هڈ¯ن»¥و‹چç€èƒ¸è„¯è¯´ï¼Œè؟™ç‰‡هگ里و‰€وœ‰çڑ„èˆھو‹چ都وک¯ç»ڈè؟‡وˆ‘ç–هˆ’çڑ„ه¹¶ن؛²è‡ھه¸¦éکںوŒ‡وŒ¥ï¼Œن»ژو°çژ›ه¤®ه®—هˆ°و—èٹ,و‹چç؛ھه½•ç‰‡ه°±ه¾—è؟™ن¹ˆه®ه®هœ¨هœ¨هژ»و‹چم€‚”ن؛“ه…‹هگ›è¯´ه¾—é“؟锵م€‚
ن؛Œè؟›و°çژ›ه¤®ه®—
éƒè·ƒéھڈن¸€è،Œن؛؛第ن؛Œو¬،è؟›و°çژ›ه¤®ه®—و‹چو‘„وک¯è·ںè¸ھو‹چو‘„ن¸€ن½چه†°ه·ç§‘ه¦ه®¶و‰چن¸œهچڑه£«ه¾€ه†°ه·ç¼ن¸و”¾ç½®و ‡و†çڑ„è؟‡ç¨‹م€‚هگ¸هڈ–第ن¸€و¬،çڑ„ç»ڈéھŒï¼Œن»–ن»¬ه¼€ن؛†ن¸¤è¾†è¶ٹé‡ژ车م€‚è·ںç€و—¢وœ‰ç»ڈéھŒهڈˆç†ںو‚‰è·¯ه†µçڑ„و‰چن¸œهچڑه£«ï¼Œن¼—ن؛؛هœ¨çں³ه¤´ه †ن¸ن¸€ç‚¹ç‚¹هگ‘ه†°ه·é©¶هژ»م€‚然而由ن؛ژèˆھو‹چه¸ˆè´ھوپ‹و™¯è‰²ï¼Œو‘„هˆ¶ç»„ن¸ژو‰چن¸œهچڑه£«èµ°و•£م€‚
م€€ ن¸؛ن؛†è؟½ن¸ٹو‰چن¸œهچڑه£«ï¼Œéƒè·ƒéھڈه’Œن»–çڑ„ه›¢éکںو‹¼ن؛†ه‘½هœ°ه¾€ه‰چ赶م€‚هœ¨وµ·و‹”5300ç±³çڑ„هœ°و–¹ï¼Œç©؛و°”ن¸çڑ„هگ«و°§é‡ڈن¸چهˆ°ه¹³هژںهœ°هŒ؛çڑ„ن¸€هچٹ,هٹ ن¸ٹه†²هˆ؛般çڑ„و€¥è،Œه†›ï¼Œه·²ç»ڈه¤§ه¤§è¶…ه‡؛ن؛†و‹چو‘„ه›¢éکںçڑ„ن½“هٹ›وپé™گم€‚é—®é¢کوژ¥è¸µè€Œو¥م€‚ه½•éں³ه¸ˆèژ«و´ھه¤ن¸€éکµه¤´و™•ï¼Œهœ¨ه†°و¹–è¾¹ن¸€è„ڑ踩و»‘,وژ‰ه…¥ن؛†ه†°ه†·çڑ„ه†°و¹–ن¸م€‚ه½“ن؛؛ن»¬وٹٹن»–و‹‰ن¸ٹو¥و—¶ï¼Œن»–ه·²هچٹè؛«و¹؟é€ڈ,ه†·ه¾—说ن¸چه‡؛è¯و¥م€‚
م€€ هڈ¦ن¸€è¾¹و‘„هƒڈن»کن¹™ç•™30ه²پن¸ٹن¸‹ï¼Œçœ‹ن¸ٹهژ»وک¯ه…¨éکںè؛«ن½“ç´ è´¨è¾ƒه¥½çڑ„ن¸€ن¸ھ,ن½†و¤و—¶ن»–ن¹ںو„ںهˆ°ن¸چه¯¹هٹ²ن؛†م€‚“脑袋هƒڈè¦پ炸ه¼€ن¸€و ·çڑ„疼,ه‘¼هگ¸çڑ„و—¶ه€™و„ں觉è‚؛里وœ‰ه°ڈو³،و²«ه‘¼ه™œه‘¼ه™œçڑ„ه£°éں³ï¼Œه’³ه—½ï¼Œè؟که’³ن؛†ن¸€هڈ£ه¸¦è،€ن¸çڑ„ç—°م€‚وˆ‘ن»¥ن¸؛ه°±وک¯ن¸€èˆ¬çڑ„é«کهژںهڈچه؛”,و²،ه¤ڑوƒ³م€‚”ن»کن¹™ç•™ه›ه؟†ï¼Œه½“و—¶وک¯ن»–ن¸ٹé«کهژںçڑ„第ن؛”ه¤©ï¼ŒوŒ‰çگ†è¯´ï¼Œن»–ن¸چه؛”该直ه¥”و°çژ›ه¤®ه®—,و›´ن¸چه؛”ه‰§çƒˆè؟گهٹ¨م€‚éƒè·ƒéھڈ说,ه½“ن»–看è§په°ڈن»کهگگه‡؛و¥çڑ„粉ç؛¢è‰²و³،و²«و—¶ï¼Œن»–ه؟ƒé‡Œه’¯ه™”ن¸€ن¸‹ï¼Œ“هˆ«ه†چه¾—ن؛†è‚؛و°´è‚؟ï¼پ”
م€€ و‘„هˆ¶ç»„ç«‹هˆ»ن¸‹و’¤هˆ°وµ·و‹”4600ç±³çڑ„ه¸•ç¾ٹ镇,组里و‰€وœ‰çڑ„و°§و°”都و‹؟ç»™ه°ڈن»ک,“هگژو¥و‰چçں¥éپ“,那هڈھوک¯هژ‹ç¼©ç©؛و°”,و ¹وœ¬ن¸چوک¯ç؛¯و°§و°”م€‚”éƒè·ƒéھڈن¸چو•¢è€½è¯¯ï¼Œç»§ç»ه¸¦و‘„هˆ¶ç»„è؟ه¤œèµ¶هˆ°éک؟里هœ°هŒ؛هŒ»é™¢ï¼ŒهŒ»ç”ںçڑ±ç€çœ‰ه¤´è¯´ï¼ڑç،®ه®وک¯è‚؛و°´è‚؟,هڈ¯ن»¥وڑ‚و—¶هپڑه؛”و€¥ه¤„çگ†ï¼Œن½†ه¦‚وœوکژو—©ن¸چن¸‹و’¤ï¼Œن»کن¹™ç•™çڑ„è‚؛و°´è‚؟ه°±ن¼ڑهڈکوˆگè„‘و°´è‚؟,هگژوœوک¯ه¤±ه؟†م€‚“وˆ‘ه½“و—¶ه·²ç»ڈن¸چç–¼ن¸چç—’ن؛†ï¼Œè؟کوœ‰ç‚¹و†‹ن¹ںن¸چ觉ه¾—و€ژو ·ï¼Œو¥è؟™ن¹ˆن¸€è¶ںن¸چه®¹وک“م€‚”ن»کن¹™ç•™هڈھو±‚éƒè·ƒéھڈهˆ«è®©è‡ھه·±ن¸‹و’¤م€‚“وˆ‘ç®،ن»–ن¹گن¸چن¹گو„ڈ,ه‘½وœ€é‡چè¦پ,هچٹ点ه•†é‡ڈن½™هœ°éƒ½و²،وœ‰ï¼ŒهŒ»ç”ںو‰چوک¯وƒه¨پçڑ„,وˆ‘هڈھن؟،ن»–ï¼پ”éƒè·ƒéھڈه’Œو€»ه¯¼و¼”ن؛“ه…‹هگ›ç«‹هˆ»é€ڑ电è¯ï¼Œèپ”系车辆ه’Œوœ؛票çڑ„ن؛‹وƒ…,终ن؛ژهœ¨ç¬¬ن؛Œه¤©وٹٹه°ڈن»کé€پهˆ°ن؛†وˆگ都م€‚“ن¸€ن¸‹é«کهژںه•¥و¯›ç—…都و²،ن؛†ï¼Œوˆ‘و‹ژç€è،Œوژه¤§و¥وµپوکںهœ°èµ°ï¼Œهژ»هŒ»é™¢ن¸€çœ‹ن¹ںو²،ن»€ن¹ˆن؛‹ن؛†م€‚”ن»کن¹™ç•™çژ°هœ¨è¯´èµ·و¥è؟کوک¯ن¸€è„¸çڑ„وƒ‹وƒœم€‚

وŒ؛è؟›ه¤§ه³،è°·
م€€ ه’Œن؛“ه…‹هگ›م€پéƒè·ƒéھڈو¯”,金é’وک±وک¯ç»„里çڑ„ه¹´è½»ç¼–ه¯¼ï¼Œهچ´ن¹ںوک¯ن¸هڑهٹ›é‡ڈم€‚ن»–و‰€çژ‡é¢†çڑ„و‘„هˆ¶ç»„ه°±ه®Œوˆگن؛†ه¾’و¥ç©؟è¶ٹه¯†و—è؟›ه…¥é›…é²پè—ڈه¸ƒه¤§ه³،è°·çڑ„و‹چو‘„م€‚
م€€ 2014ه¹´11وœˆï¼Œو‘„هˆ¶ç»„ن»ژوژ’龙门ه·´ه‡؛هڈ‘,ن¸€ç›´è¦پèµ°هˆ°é›…é²پè—ڈه¸ƒو±ںه¤§و‹گه¼¯çڑ„é‚£ن¸ھé،¶ç‚¹ن½چ置,途ن¸è¦پèٹ±è´¹ن¸¤ه¤©çڑ„و—¶é—´ï¼Œهœ¨و£®و—里露èگ¥ن¸€و™ڑم€‚除ن؛†و‘„هˆ¶ç»„وˆگه‘ک,ن»–ن»¬è؟ک请ن؛†11ن¸ھه½“هœ°é—¨ه·´و—ڈçڑ„背ه¤«ه¸®ه؟™èƒŒè®¾ه¤‡ن¸€èµ·èµ°م€‚ه¥½èµ°çڑ„è·¯ن¸چه¤ڑ,ن¸€هچٹن»¥ن¸ٹçڑ„路都وک¯é™،ه³çڑ„ه²©ه£پم€پو»‘ه،è·¯و®µم€پçں³هگè·¯ç‰ï¼Œ“ه½“هœ°ن؛؛هƒڈé£وھگèµ°ه£پن¸€و ·ï¼Œوˆ‘ن»¬هچ´هڈھ能هڈŒو‰‹هڈŒè„ڑ爬ç€è؟‡هژ»م€‚”金é’وک±è¯´م€‚è·¯è؟‡ه³ه£پو—¶ï¼Œè؛«ن¸‹ه°±وک¯و¹چو€¥çڑ„é›…é²پè—ڈه¸ƒو±ں,背ه¤«ه¼€çژ©ç¬‘说,ن¸€ه®ڑه°ڈه؟ƒن¸€ç‚¹ï¼Œه¦‚وœوژ‰ن¸‹هژ»ه°±هڈھ能هژ»هچ°ه؛¦وچن؛؛ن؛†م€‚
م€€ 途ن¸وœ‰ه‡ و¬،,éکںه‘کن»¬هœ¨هژںه§‹ه¯†و—里è؟·è·¯ن؛†م€‚وœ€و‚¬çڑ„ن¸€و¬،,金é’وک±èƒŒç€و‘„هƒڈوœ؛è¶ٹèµ°è¶ٹ累,و¸گو¸گوژ‰هœ¨ن؛†éکںه°¾م€‚眼看ç€ç¦»ه‰چé¢çڑ„éکںه‘کè¶ٹو¥è¶ٹè؟œï¼Œن»–وƒ³ç€é—·ه¤´èµ¶ن¸ٹهژ»م€‚茂ه¯†çڑ„و£®و—里,看ن¼¼هڈھوœ‰è„ڑن¸‹çڑ„ن¸€و،路,ه†چو— ن»»ن½•ه²”路,è°پçں¥éپ“ن»–èµ°ç€èµ°ç€ه‰چé¢و²،è·¯ن؛†ï¼Œن¸”هڈھه‰©ن»–ن¸€ن؛؛,ه†چ看و‰‹ن¸çڑ„ه¯¹è®²وœ؛,ن؟¨ç„¶و²،电罢ه·¥ن؛†م€‚“وŒ؛ç»وœ›ï¼Œن¸€ن¸چç•™ç¥è؟ک被çپ«é؛»ن¸›و‰ژن؛†ن¸€è„‘袋م€‚çپ«é؛»çڑ„هˆ؛ç•™هœ¨çڑ®è‚¤é‡Œï¼Œهƒڈ被电ن؛†ن¸€و ·çڑ„疼,و‹”ن¸چه‡؛و¥ه°±ن¸€ç›´ç–¼م€‚”金é’وک±é،¶ç€ن¸€è„‘袋çپ«é؛»هˆ؛ç‰ن؛†ن¸€ن¸ھه°ڈو—¶ï¼Œç»ˆن؛ژç‰هˆ°ن؛†ه›و¥ه¯»ن»–çڑ„ن؛؛م€‚هژںو¥هœ¨ن¸€ه¤„ن¸چوک¾çœ¼çڑ„هœ°و–¹ï¼Œè·¯هˆ†وˆگن؛†ن¸¤è¾¹ï¼Œن¸چن»”细看ه¾ˆéڑ¾هڈ‘çژ°م€‚è؟›ه³،谷用ن؛†ن¸¤ه¤©ï¼Œه‡؛ه³،è°·ن¸€و ·è¦پن¸¤ه¤©م€‚è®°ه¾—ه¾€ه›èµ°çڑ„و—¶ه€™ï¼Œه¤§ه®¶è؛«ن¸ٹو–°ن¼¤و—§ç—›è¶ٹو¥è¶ٹه¤ڑم€‚金é’وک±çڑ„ن¸¤ن¸ھè†ç›–ه…¨ç£•ن؛†ï¼Œن¸¤هڈھè„ڑن¹ںه…¨éƒ½ه´´ن؛†ï¼Œèµ°èµ·è·¯و¥ه·¦هڈ³هˆ«ç€هٹ²م€‚
م€€ “è؟™هڈ¯وک¯ه¾’و¥è؟›ه‡؛ه³،è°·ه•ٹï¼پوˆ‘ن»¬ن¸€ن¸ھéکںه‘کهœ¨ه³،谷里ه®Œوˆگو‹چو‘„هگژهگçں³ه¤´ن¸ٹوƒ†و€…,وˆ‘é—®و€ژن¹ˆن؛†ï¼Œن»–说وˆ‘و€•ه’±ن»¬ن¸چ能و´»ç€ه‡؛هژ»م€‚”金é’وک±ç¬‘ç€è¯´ï¼Œ“و‰€ن»¥ه•ٹ,能ه¹³ه®‰ه‡؛و¥ه°±ن¸‡ه¹¸ن؛†ï¼Œç£•ç£•ç¢°ç¢°è؟کç®—ن؛‹ه„؟هگ—ï¼ں”م€€م€€م€€م€€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