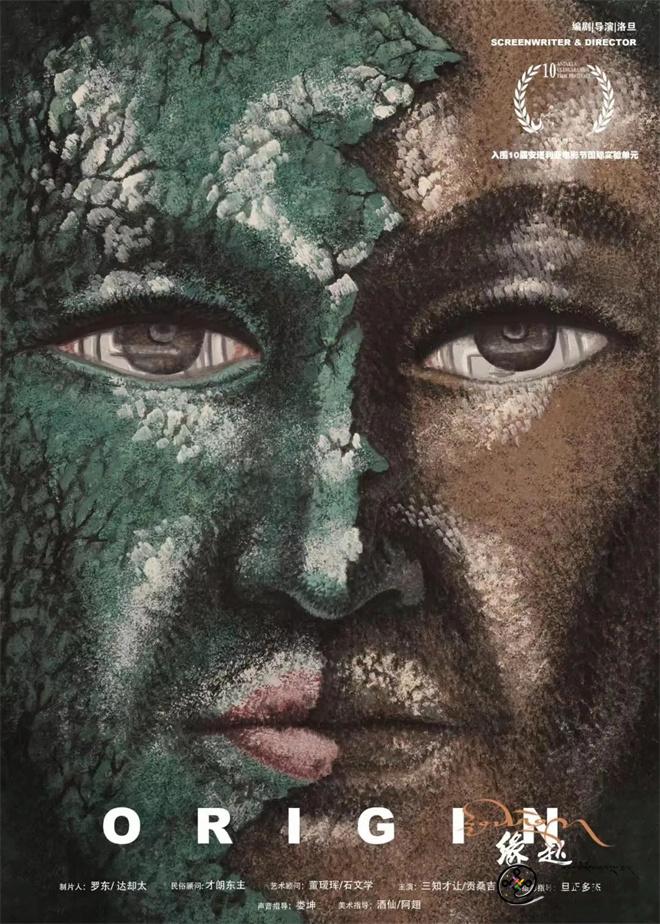гАКзЂ•иѓЭгАЛеБЪеЃМдЇЖпЉМдЄ§дЄ™е§ЪжЬИзЪДжЬЇжИњзФЯжіїзїУжЭЯпЉЫжШО姩дЉЪжШѓдїАдєИж†ЈпЉЯжИСеЃ≥жАХйЭҐеѓєжШО姩зЭБеЉАзЬЉзЭЫдЄНзЯ•йБУиѓ•еОїеУ™пЉБжИСињЩжШѓжАОдєИдЇЖпЉЯжИСзО∞еЬ®иЗ™еЈ±зЪДжДПењЧеЉАеІЛеПШеЊЧиЦДеЉ±дЇЖпЉМжЕҐжЕҐеЬ∞еЬ®жБРжГІвА¶вА¶
жЬАињСпЉМжИСдЄАзЫіеЬ®еТМйЯ≥дєРеИґдљЬдЇЇзОЛжЦМпЉИйШњжШМжЧПпЉЙеРИдљЬпЉМеПСзО∞иЗ™еЈ±жКЧжЛТеТМдЇЇдЇ§жµБпЉМжѓП姩йГљеЬ®жГ≥ињЩдЄ™зЙЗе≠РзїУжЭЯдЇЖпЉМйВ£дЄ™зЙЗе≠РдїАдєИжЧґеАЩиГљеЃМпЉМе¶ВжЮЬињЩдЇЫзЙЗе≠РйГљеЃМдЇЖпЉМжИСеПИжАОдєИеКЮпЉЯи¶Беі©жЇГдЇЖпЉМдЇЇзЪДиі™жђ≤еЬ®иЖ®иГАпЉМеЃМеЕ®ж≤°жЬЙеЛЗж∞ФйЭҐеѓєиЇЂиЊєзЪДеЛЗе£ЂпЉМеПЧдЄНдЇЖеХ¶пЉБпЉБпЉБ
еПЧиАБйҐЬеІФжЙШпЉМеЬ®жЬЛеПЛдЄ≠жЙЊеѓїе£ЃзИЈзЪДзФµиѓЭпЉЫдїК姩ењЩдЄ≠еБЈйЧ≤жЧґз™БзДґжГ≥иµЈжИСзЪДиЧПжЧПе§ІеУ•дЄЗзОЫжЙНжЧ¶е∞±жШѓе£ЃзИЈзЪДз†Фз©ґзФЯпЉМзЯ≠дњ°еПСеЗЇиЃЄдєЕеРОеЫЮе§НпЉМе£ЃзИЈзЪДиБФз≥їжЦєеЉПжЬЙдЇЖпЉМеРМжЧґдєЯеЊЧзЯ•е§ІеУ•еЬ®и•њиЧПпЉЫжЦЧе£ЂеПѓиГљеЗЇеЊБдЇЖпЉМжИСдєЯиѓ•еПНжАЭдЇЖпЉБ
дЄЗзОЫжЙНжЧ¶
жГЯдЄАеЬ®жЛНзФµељ±зЪДиЧПжЧПеѓЉжЉФ
гААгААиЧПиѓ≠зО∞еЬ®еЉХеЕ•е§ІйЗПзЪДж±Йиѓ≠еТМиЛ±иѓ≠пЉМеОЯеЕИзЪДдЄАдЇЫз¶БењМиѓ≠еєіиљїдЇЇйГљдЄН姙зЯ•йБУдЇЖвА¶вА¶зЙЗе≠РйЗМзЪДиЧПжИПгАКжЩЇзЊОжЫізЩїгАЛжШѓињЗиКВжЧґжѓПдЄ™жЭСеЇДйГљи¶БжЉФзЪДжИПпЉМиАБеєідЇЇеТМдЄ≠еєідЇЇзЬЛдЇЖйГљдЉЪжµБж≥™пЉМдљЖеєіиљїдЇЇеЈ≤зїПж≤°жЬЙжДЯиІЙдЇЖгАВзО∞еЬ®жШѓињЮеРМз≤ЊеНОйГ®еИЖдєЯеЃМеЕ®дЄҐеЉГпЉМжґИ姱дЇЖпЉМињЩдЄАеИЗзЬЛиµЈжЭ•иЗ™зДґиАМзДґпЉМдљЖжљЬдЉПзЭАеН±йЩ©вА¶вА¶
гАА жЬђеИКиЃ∞иАЕ жЭОеЃЧйЩґеПСиЗ™еМЧдЇђгАБдЄКжµЈ
гААгААвАЬеПИжЬЙ300дЇЇжЭ•зЬЛзФµељ±дЇЖпЉБвАЭ
гААгААиЧПжЧПеѓЉжЉФдЄЗзОЫжЙНжЧ¶иѓіпЉЪвАЬжИСдЄНеЦЬ搥僺йЩМзФЯдЇЇиѓіеЊИе§ЪгАВвАЭдЄ§жђ°йЗЗиЃњзїУжЭЯпЉМдїЦжДЯиІЙжЬЙзВєдЄКељУпЉЪвАЬжИСиѓіеЊЧ姙е§ЪдЇЖгАВвАЭеПѓиЃ∞иАЕдєЯдЄНиљїжЭЊпЉМйЭҐеѓєдЄАдЄ™еЗ†дєОдЄНзФ®дїОеП•еТМ嚥偺иѓНзЪДдЇЇгАВ
гААгАА6жЬИ13жЧ•жЩЪпЉМдЄЗзОЫжЙНжЧ¶еЬ®еЫЮеЃґиЈѓдЄКй°ЇдЊњдЄАжЛРпЉМињЫдЇЖеМЧдЇђзФµељ±е≠¶йЩҐе∞Пе∞ПзЪДж†°еЫ≠гАВ2002-2004еєіпЉМдїЦеЬ®ињЩйЗМиµ∞ињЫиµ∞еЗЇгАВжХЩе≠¶ж•Љ7ж•ЉпЉМжШѓдїЦдЄКиѓЊзЪДеЬ∞жЦєгАВж†°йЧ®жЧБиЊєзЪДжФЊжШ†еОЕпЉМгАКйЭЩйЭЩзЪДеШЫеСҐзЯ≥гАЛжФЊињЗдЄ§йБНгАВдїЦжККеЈ•дљЬеЃ§еЃЙеЬ®е≠¶ж†°жЧБиЊєпЉМдЄНињЬе§ДжШѓиіЊж®ЯжЯѓзЪДгАВ
гААгААдє¶жЮґдЄКжЬЙ35mmзФµељ±иГґзЙЗзЫТпЉМињШзЂЛзЭАдЄАеП™иЇЂзЉ†еУИиЊЊзЪДвАЬйЗСйЄ°вАЭеТМе•љеЗ†еЇІе•ЦжЭѓгАВдїО2005еєі8жЬИеЃМжИРеРОжЬЯдї•жЭ•пЉМгАКйЭЩйЭЩзЪДеШЫеСҐзЯ≥гАЛеЈ≤зїПиОЈеЊЧпЉЪзђђ14е±КдЄ≠еЫљзФµељ±йЗСйЄ°е•ЦжЬАдљ≥еѓЉжЉФе§Де•≥дљЬе•ЦгАБйЯ©еЫљйЗЬе±±зФµељ±иКВвАЬжЦ∞жљЃжµБзЙєеИЂе•ЦвАЭгАБзђђ30е±Кй¶ЩжЄѓеЫљйЩЕзФµељ±иКВвАЬеЫљйЩЕељ±иѓДдЇЇиБФзЫЯе•ЦвАЭз≠Й6дЄ™е•Цй°єгАВ
гААгААйВ£дЇЫдє¶пЉМдїОгАКиИђиЛ•ењГзїПгАЛгАБгАКж†ЉиР®е∞ФзОЛгАЛгАБгАКиЧПеМїйАЪеП≤гАЛгАБдљЩеНОеИ∞еН°е§ЂеН°пЉМйВ£дЇЫе§ІзЫТе•Чи£ЕзҐЯзЙЗпЉМдїОеЯЇиАґжЦѓжіЫе§ЂжЦѓеЯЇгАБж≥ХжЦѓеЃЊеЊЈгАБеЇУеЄГйЗМеЕЛгАБеС®йШ≤ж≠£и°МгАБйШње∞ФиОЂе§ЪзУ¶еИ∞жЛЙжЦѓ¬ЈеЖѓ¬ЈзЙєйЗМе∞ФпЉМдЄАдЄНе∞ПењГж≥ДйЬ≤зІШеѓЖвАФвАФињЩдЇЫеєізЪДжИРеЮЛеТМзІѓзіѓгАВ
гААгААзЊ§е±ЕзКґжАБзЪДеЈ•дљЬеЃ§йЗМињШжЬЙеП¶дЄАе±ВзІШеѓЖпЉМдЄЗзОЫж≠£еЬ®еЯєиВ≤дЄАдЄ™еМЕжЛђйЯ≥дєРгАБзЊОжЬѓгАБељХйЯ≥зФЪиЗ≥жСДеГПзЪДиЧПжЧПзФµељ±зП≠еЇХпЉМжЬЙжљЬеКЫзЪДеРМжЧПеЉЯеЕДзЬЉдЄЛж≠£еЬ®еМЧдЇђзФµељ±е≠¶йЩҐжО•еПЧзЫЄеЕ≥зЪДдЄУдЄЪиЃ≠зїГпЉМдЄ§дЄЙеєіеРОпЉМдїЦеЄМжЬЫиГљеЬ®дЄАиµЈеРИдљЬгАВ
гААгАА6жЬИ20жЧ•дЄЛеНИпЉМдЄЗзОЫжЙНжЧ¶еЗЇзО∞еЬ®дЄКжµЈељ±еЯОжФЊжШ†еОЕзЪДиИЮеП∞дЄКгАВдїЦиѓідЇЖдЄАдЄ§еП•иѓЭпЉМе∞±вАЬи∞Ґи∞Ґе§ІеЃґвАЭдЇЖгАВдЄАдЄ™300дЄЗеЕГзЪДе∞ПеИґдљЬпЉМжЧ†еКЫињЫйЩҐзЇњпЉМеП™иГљеАЯдЄКжµЈеЫљйЩЕзФµељ±иКВеЬ®дЄКжµЈй¶ЦжШ†гАВ
гААгААдЄЗзОЫжЙНжЧ¶еЬ®йҐСзєБжФґеПСзЯ≠дњ°пЉМдїЦжЫіеЬ®жДПеП¶дЄАжЛ®иІВдЉЧгАВгАКйЭЩйЭЩзЪДеШЫеСҐзЯ≥гАЛ6жЬИ1жЧ•еЉАеІЛеЬ®дїЦзЪДжХЕдє°йЭТжµЈзЬБдЄКжШ†пЉМи•њеЃБз•®дїЈ15еЕГпЉМдЄЛйЭҐеЈЮеОњ10еЕГпЉМжЬЙдЇЫеГІдЇЇдїОеЊИињЬзЪДеЬ∞жֺ赴еОїзЬЛзФµељ±пЉМжЬЙзЪДеЈ≤зїПзЬЛдЇЖеЫЫдЇФйБНдЇЖгАВељУеЬ∞дЇЇдЉЪеПКжЧґеРСдїЦйАЪжК•пЉМвАЬеПИжЬЙ300дЇЇжЭ•зЬЛзФµељ±дЇЖпЉБвАЭињЩжЧґеАЩпЉМдїЦеП§йУЬиЙ≤зЪДиДЄдЄКдЉЪжЉЊиµЈдЄАзВєзВєеєЄз¶ПпЉМжЬАе§ІзЪДжДњжЬЫе∞±жШѓиЃ©вАЬдїЦдїђвАЭиГљзЬЛеИ∞ињЩйГ®зФµељ±пЉМжЬђжЭ•е∞±жШѓжЛНзїЩвАЬдїЦдїђвАЭзЬЛзЪДгАВ
гААгАА6жЬИ24жЧ•зЪДйҐБе•ЦжЩЪдЉЪдЄКпЉМгАКйЭЩйЭЩзЪДеШЫеСҐзЯ≥гАЛиОЈеЊЧжЬђе±КдЄКжµЈеЫљйЩЕзФµељ±иКВдЇЪжі≤жЦ∞дЇЇе•ЦжЬАдљ≥еѓЉжЉФе•ЦгАВ
гААгААдЄЇиЗ™еЈ±зЪДж∞СжЧПеѓїжЙЊдљНзљЃ
гААгААзЙЗе§іжЙУеЗЇиЧПжЦЗпЉМйЉУе£∞пЉМиѓµзїПе£∞пЉМжВ†ињЬйХњи∞ГпЉМй£ОеРєзїПеє°пЉМдЄАеПМж≠£еЬ®жХ≤еЗњеШЫеСҐзЯ≥зЪДиАБдЇЇзЪДжЙЛгАВйЭТйУЬеЩ®иИђзЪДиі®жДЯгАВ
гААгААжИСзЬЛдЄ≠жЦЗе≠ЧеєХпЉМжИСиЇЂжЧБзЪДзФµељ±иКВзЊОеЫље•≥иѓДеІФзЬЛиЛ±жЦЗе≠ЧеєХгАВиЧПиѓ≠еѓєзЩље¶Вж≠§зЃАжіБпЉМеЕЈе§ЗдЇЖжЯРзІНеП§иАБеЬ£еЕЄзЪДеКЫйЗПгАВйХњйХЬе§іиИТзЉУпЉМзФЯжіїзЪДиі®жДЯз≤Тз≤ТеСИзО∞гАВ
гААгААеЬ®дЄАдЄ™еНКеЖЬеНКзЙІзЪДиЧПеМЇпЉМдЄАдЄ™жЭСдЉЪиЃ°жЬЙ4дЄ™е≠©е≠РпЉМдїЦе∞ЖеЕґдЄ≠дЄАдЄ™зФЈе≠©йАБеИ∞еѓЇйЩҐйЗМеБЪдЇЖж†Љй≤БжіЊе∞ПеЦЗеШЫгАВжЄЕиЛ¶е≠¶зїПдЄАеєіпЉМеєідЄЙеНБпЉМзИґдЇ≤жЭ•еѓЇйЩҐжО•еДње≠РеЫЮеЃґпЉМжХЕдЇЛе∞±дїОеєідЄЙеНБиЃ≤еИ∞еєіеИЭдЄЙгАВ
гААгААжЬЙдЄАеЬЇжИПпЉМе∞ПеЦЗеШЫи¶БзЬЛеЉЯеЉЯзЪДдє¶еМЕпЉМдїЦзњїеИ∞жХ∞е≠¶дє¶пЉМйЧЃињЩжШѓдїАдєИзЃЧжЬѓпЉЯеЉЯеЉЯиѓіпЉМе≠¶е•љдЇЖеПѓдї•еГПзИЄзИЄйВ£ж†ЈељУжЭСдЉЪиЃ°гАВе∞ПеЦЗеШЫиѓіпЉМжИСдїђеѓЇйЩҐйЗМзЪДжХ∞е≠¶жШѓзЃЧжЧ•жЬИжШЯиЊ∞зЪДгАВиЗ≥дЇОиѓ≠жЦЗпЉМеЉЯеЉЯй£ЮењЂеЬ∞зФ®ж±Йиѓ≠ењµдЇЖдЄАйБНвАЬеЉѓеЉѓзЪДжЬИдЇЃеГПе∞Пе∞ПзЪДиИєпЉМе∞Пе∞ПзЪДиИєеДњдЄ§е§іе∞ЦвАЭпЉМиѓіпЉМе≠¶е•љж±Йиѓ≠пЉМеПѓдї•еОїе§ІеЯОеЄВгАВдЄЗзОЫжЙНжЧ¶иѓіпЉМдїК姩жЬЙдЇЫзФЯжіїеЬ®еЯОеЄВйЗМзЪДиЧПжЧПеРОдї£еЈ≤зїПдЄНдЉЪиѓіиЧПиѓ≠дЇЖгАВ
гААгААеП¶дЄАеЬЇжИПпЉМе∞ПеЦЗеШЫиЈЯеЉЯеЉЯе¶єе¶єдЄАйБУеОїељХеГПеОЕзЬЛй¶ЩжЄѓжЮ™жИШзЙЗпЉМзЬЛеИ∞зФЈе•≥жГЕиКВпЉМиІЙеЊЧеИЂжЙ≠пЉМиљђиЇЂйААеЗЇпЉМйЧЃеНЦз•®зЪДеПФеПФйААињШдЄАеЭЧйТ±пЉЪвАЬдљ†жАОдєИиЃ©жИСеЗЇеЃґдЇЇзЬЛињЩдЄ™еСҐпЉЯвАЭйВ£иЧПжЧПзО∞дї£йЭТеєіеЉАеІЛдЄНиВѓпЉМеРОжЭ•иѓіпЉЪвАЬзЬЛдљ†жШѓдЄ™еЗЇеЃґдЇЇпЉМйААдљ†еРІгАВвАЭдЄЗзОЫиѓіпЉМдљ†ж≥®жДПж≤°жЬЙпЉМе∞ПеЦЗеШЫеЫЮеЃґдЄКеЭСжЧґпЉМзИЈзИЈиЃ©дїЦеЭРдЄКй¶ЦпЉЫе∞ПжіїдљЫжСЄй°ґиµРз¶ПжЧґпЉМеєійХњиАЕи°МеП©жЛЬдєЛз§ЉгАВиЧПдЉ†дљЫжХЩпЉМеЯЇжЬђжШѓеЕ®ж∞СжЧПзЪДдњ°дї∞пЉМдїЦдїђжЬЙжХђзХПгАВ
гААгАА4еєіеЙНпЉМдЄЗзОЫеЬ®жЦЗе≠¶зЉЦеѓЉдЄУдЄЪдЄАеєізЇІжЧґпЉМиЛПзЙІиАБеЄИиЃ©е≠¶зФЯдїђеБЗжЬЯеРДиЗ™еЫЮеЃґжЛНзЙЗгАВдЄЗзОЫзђђдЄАжђ°дљњзФ®жЙЛжОМе§ІзЪДеЃґзФ®SONY DVжЛНдЇЖдЄАдЄ™зЯ≠зЙЗпЉМзі†жЭРеЊИе§ЪпЉМеЙ™жИР50еИЖйТЯпЉМеПИеОЛзЉ©жИР30еИЖйТЯпЉМињЩжШѓзФµељ±гАКйЭЩйЭЩзЪДеШЫеСҐзЯ≥гАЛзЪДеЙНиЇЂгАВеѓЇйЩҐйЗМдЄАиАБдЄАе∞ПдЄ§дЄ™еЦЗеШЫпЉМйГљжШѓйВ£жЧґеАЩиЃ§иѓЖзЪДгАВ
гААгААжѓХдЄЪеРОпЉМжЭЬеЇЖжШ•иАБеЄИз≠ЙдЇЇйГљиІЙеЊЧињЩзЯ≠зЙЗеПѓдї•е±ХеЉАгАВ2005еєі1жЬИпЉМдЄЗзОЫеЄ¶зЭАеНБе§ЪдЇЇзЪДеИЫдљЬеЫҐйШЯеЉАињЫйЭТжµЈзЬБйїДеНЧеЈЮпЉМжЙЊеИ∞еП§йЊЩ冧жЭСзЪДжЭСйХњпЉМжЭСйХњеЊИжФѓжМБжЛНзФµељ±гАВ42姩еРОпЉМзЙЗе≠РжЭАйЭТгАВе∞ПеЦЗеШЫеЈ≤зїПйХње§ІдЇЖдЇЫпЉМдљЖдїЦзЪДжЬђиЙ≤и°®жЉФдЄНйЬАи¶БињЗе§Ъи£БеЙ™гАВзФµељ±дЄ≠жЙАжЬЙзЪДиІТиЙ≤йГљжШѓйЭЮиБМдЄЪжЉФеСШпЉМ80е≤БзЪДзИЈзИЈиЃ∞дЄНдљПеП∞иѓНпЉМжЬАз≥Яз≥ХжЧґдЄАеП•иѓЭжЛНдЇЖдЄАдЄЛеНИпЉМеЗ†еНБжЭ°пЉМељХйЯ≥еЄИйГљжЬЙзВєзФЯж∞ФдЇЖпЉМдљЖжЙАжЬЙдЇЇпЉМеМЕжЛђеНБеЗ†е≤БзЪДеЈ®зДХдїУжіїдљЫи°®жЉФйГљеЊИеИ∞дљНгАВ
гААгААеЬ®иЧПеМЇжЛНе§ЦжЩѓе•љиЙ∞йЪЊгАВжµЈжЛФдЄЙеНГе§Ъз±≥пЉМеЃ§е§ЦйЫґдЄЛ20е§ЪеЇ¶пЉМжЧ©жЩ®10зВєжЙНеǯ姙йШ≥пЉМдЄЛеНИ5зº姙йШ≥е∞±иРље±±гАВдЇСељ©дЄАдЉЪеДњињЗжЭ•пЉМиљђзЬЉйЧіжґИ姱пЉМеЫ†дЄЇиµЈй£ОдЇЖпЉМзЙЗдЄ≠зМОзМОдљЬеУНзЪДзїПеє°жПРз§Їй£ОеКЫжЬЙе§Ъе§ІгАВдЄЗзОЫеЬ®зЙЗеЬЇиГ°е≠РжЛЙ祳пЉМеЊИе§ЪдЇЇйГљиГ°е≠РжЛЙ祳гАВдїЦеРОжЭ•иѓіпЉМеѓєдїїдљХдЄАйГ®зФµељ±жИРеУБдїЦйГљењГжААжХђжДПпЉМеЫ†дЄЇеП™и¶БжШѓжЛНеЗЇжЭ•зЪДпЉМйГљдЄНеЃєжШУгАВ
гААгААгАКйЭЩйЭЩзЪДеШЫеСҐзЯ≥гАЛеЯЛдЄЛеЗ†е§ДдЉПзђФпЉМдЄАжШѓиАБеЦЗеШЫдЄЇдЇЖ10еєіењГжДњпЉМи¶БеЬ®иЧПеОЖжЦ∞еєіеРОеОїжЛЙиР®жЬЭеЬ£пЉМиАМдЄФи¶БеЄ¶е∞ПеЦЗеШЫдЄАиµЈеОїпЉМеПѓиГљжШѓзЬЛдЇЖгАКи•њжЄЄиЃ∞гАЛVCDпЉМжЬЙдЇЖвАЬе≠ЩжВЯз©ЇжК§еНЂеФРеò蕜姩еПЦзїПвАЭзЪДењµе§ігАВдЇОжШѓдЄЗзОЫжЙНжЧ¶жЬЙдЇЖеБЪдЄЙйГ®жЫ≤зЪДењµе§іпЉМзђђдЇМйГ®еПѓиГљеПЂвАЬеОїжЛЙиР®зЪДиЈѓдЄКвАЭпЉМзђђдЄЙйГ®е∞±жШѓвАЬжЉЂжЉЂиљђзїПиЈѓвАЭгАВдЉЪдЄНдЉЪиЃ©е∞ПеЦЗеШЫеЬ®жЬЭеЬ£иЈѓдЄКйБЗиІБдЄАдЄ™иЃ©дїЦеК®дЇЖеЗ°ењГзЪДе•≥е≠РеСҐпЉЯдЄЗзОЫиѓіпЉМжЬЙеПѓиГљпЉМдљЖе∞ПеЦЗеШЫзЯ≠жЪВ蜣姱еРОзїИдЇОжЙЊеИ∞дЇЖиЗ™еЈ±зЪДдљНзљЃгАВ
гААгААжЙЊеИ∞иЗ™еЈ±зЪДдљНзљЃпЉМжШѓињЩдЄ™37е≤БгАБзЫЃеЙНжГЯдЄАеЬ®жЛНзФµељ±зЪДиЧПжЧПеѓЉжЉФжЙІзЭАзЪДдЄїйҐШгАВдїЦзЪДеП¶дЄАйГ®еЈ≤зїПеЖЩеИ∞дЇМз®њзЪДдЄАдЄ™еЙІжЬђпЉМж†єжНЃж≥ХеЫљиЧПе≠¶еЃґзЪДе∞ПиѓігАКдЇФжЩЇеЦЗеШЫеЉ•дЉідЉ†е•ЗгАЛжФєзЉЦпЉМдєЯжШѓиЃ≤ињ∞вАЬжЬАзїИжЙЊеИ∞иЗ™еЈ±дљНзљЃвАЭзЪДжХЕдЇЛгАВдїЦеЬ®дЄЇдїЦзЪДж∞СжЧПеѓїжЙЊдљНзљЃпЉМзФ®дЄАзІНйЭЩйїШзЪДгАБдЄНдЇЛеЉ†жЙђзЪДиѓ≠ж≥ХгАВ
гААгААжЧ©еєізЪДдЄЗзОЫељУињЗе∞Пе≠¶жХЩеЄИеТМжФњеЇЬеЕђеК°еСШпЉМжѓХдЄЪдЇОи•њеМЧж∞СжЧПе§Іе≠¶иЧПиѓ≠и®АжЦЗе≠¶дЄУдЄЪпЉМз°Хе£ЂиѓїзЪДжШѓиЧПгАБж±ЙзњїиѓСдЄУдЄЪгАВдїЦзЪДзђђдЄАйГ®е∞ПиѓіеПЂгАКдЇЇдЄОзЛЧгАЛпЉМиЃ≤дЇЖдЄАдЄ™вАЬжЃЛйЕЈзЪДдЇЇвАЭзЪДжХЕдЇЛгАВеРОжЭ•зЬЛжЙОи•њиЊЊе®ГеТМй©ђеОЯпЉМеПЧй≠ФеєїзО∞еЃЮдЄїдєЙзЪДзЫЕжГСпЉМжЬђж∞СжЧПжЦЗеМЦжЄКжЇРйЗМзЪДз•Юе•ЗдЄОеЕЙељ©дЄАдЄЛе≠РеРСдїЦжЙУеЉАпЉМињЮзЭАеЖЩдЇЖеЫЫеНБе§ЪдЄ™дЄ≠зЯ≠зѓЗпЉМеЊЧдЇЖдЄНе∞СвАЬе∞Пе•ЦвАЭгАВдїЦеЦЬ搥дљЩеНОеТМеН°е§ЂеН°гАВдїЦзЪДеЖЕењГпЉМдєЯиЃЄжЫідЇ≤ињСжЦЗе≠ЧпЉМйВ£жШѓеП¶дЄАзІНиѓ≠ж≥ХпЉМеПѓдї•йЂШй£ШеИ∞еЊИињЬзЪДеЬ∞жЦєгАВе¶ВжЮЬиГље§ЯиД±еЉАзєБзРРдЇЛеК°пЉМдїЦжГ≥еЖЩдЄАйГ®йХњзѓЗпЉМдљЖжЧ•е≠РйЭЩдЄНдЄЛжЭ•гАВ
гААгААе§ЦжЭ•иАЕзЬЉдЄ≠зЪДи•њиЧПпЉМ
гААгААеТМиЧПдЇЇзЬЉдЄ≠зЪДи•њиЧПжШѓдЄНдЄАж†ЈзЪД
гААгААдЇЇзЙ©еС®еИКпЉЪеЬ®зЫЃеЙНжЙАжЬЙеЕ≥дЇОдљ†зЪДжК•йБУдЄ≠пЉМзЂ•еєізїПеОЖдЄАзЙЗз©ЇзЩљгАВ
гААгААдЄЗзОЫжЙНжЧ¶пЉЪжИСзЪДеЃґпЉМе∞±еГПзЙЗе≠РйЗМеНКеЖЬеНКзЙІзЪДйЭТжµЈиЧПеМЇгАВжИСдїђиАХзІНпЉМе∞ПйЇ¶гАБйЭТз®ЮгАБж≤єиПЬпЉМжИСдєЯжФЊињЗзЊКгАВжИСзїПеОЖдЇЖвАЬжЦЗйЭ©вАЭзЪДе∞ЊеЈіпЉМеѓєзФЯдЇІйШЯжѓПеєізЪДеЖ≥зЃЧгАБеИЖйТ±ињШжЬЙеН∞и±°гАВе∞Пе≠¶иѓЊе†Ве∞±еЬ®еѓЇйЩҐйЗМпЉМйВ£йЗМдєЯжФЊињЗзФµељ±гАКжИСдїђжЭСйЗМзЪДеєіиљїдЇЇгАЛгАВйВ£жШѓдЄАдЄ™дЄ§е±ВзЪДеЃБзОЫжіЊеѓЇйЩҐпЉМеѓЇйЩҐйЗМзЪДдљЫеГПеТМйЫХе°СвАЬжЦЗйЭ©вАЭдЄ≠йÚ襀жѓБжОЙдЇЖгАВжХЩеЃ§йЗМжМВињЗжѓЫдЄїеЄ≠еТМеНОеЫљйФЛзЪДеГПгАВвАЬеЫЫдЇЇеЄЃвАЭеАТеП∞жЧґи°ЧдЄКиіідЇЖиЃЄе§ЪжЉЂзФїгАВ
гААгААе∞Пе≠¶еЫЫдЇФеєізЇІпЉМжЬЙдЄА姩еЬ®иЈѓдЄКжЛ£еИ∞дЄАжЬђдє¶пЉМж≤°жЬЙе∞БйЭҐпЉМзњїеЊЧеЊИзГВдЇЖпЉМжШѓдЄАжЬђзЂ•иѓЭйЫЖе≠РгАВжИСзђђдЄАжђ°зЬЛеИ∞гАКзЩљйЫ™еЕђдЄїгАЛпЉМеИЂзЪДиЃ∞дЄНжЄЕдЇЖпЉМињЩжШѓдЄК姩зїЩжИСзЪДдЄАдЄ™з§ЉзЙ©гАВеИЭдЄ≠еЉАеІЛжО•иІ¶е§ЦеЫљдљЬеУБпЉМеЈіе∞ФжЙОеЕЛгАБжЙШе∞ФжЦѓж≥∞гАБе•СиѓГе§ЂдєЛз±їпЉМеРОжЭ•зЬЛдЇЖеЊИе§ЪзО∞дї£жіЊе∞ПиѓігАВ
гААгААзЬЛзФµељ±жШѓеЬ®еЊИе∞ПзЪДжЧґеАЩпЉМжИСдїђеЃґе∞±еЬ®йїДж≤≥иЊєдЄКпЉМељУжЧґж∞іеИ©йГ®и¶БжЭ•еїЇдЄАдЄ™зФµзЂЩпЉМе∞±дљПеЬ®жИСдїђжЭСе≠РйЗМпЉМжЩЪдЄКдЉЪжФЊдЄАдЇЫйЬ≤姩зФµељ±пЉМжИСе∞±иЈЯзЭАзЬЛдЇЖе•љдЇЫе§ЦеЫљзФµељ±пЉМеГПеНУеИЂжЮЧзЪДгАКжС©зЩїжЧґдї£гАЛпЉМињШжЬЙгАКдљРзљЧгАЛдїАдєИзЪДпЉМйГљиЃ©жИСжГКе•ЗгАВдЄ≠е≠¶еИ∞дЇЖеОњдЄКпЉМзЬЛдЇЖе•ље§ЪеЫљдЇІзФµељ±пЉМеИ∞дЄКеИЭдЄ≠жЧґпЉМжИСеЈ≤зїПзЬЛдЇЖдЄ§дЄЙзЩЊйГ®зФµељ±дЇЖгАВ
гААгААдЇЇзЙ©еС®еИКпЉЪдљ†иѓіињЗдЄНеЦЬ搥дїЦдЇЇиЃ≤ињ∞зЪДдљ†зЪДжХЕдє°пЉМдїЦдїђиµЛдЇИзЪДз•ЮзІШгАБиНТиЫЃеТМдЄОдЄЦйЪФзїЭпЉМдљњиЧПжЧПеПШеЊЧйЭҐзЫЃж®°з≥КпЉМжЙАдї•дљ†и¶БзФ®иЗ™еЈ±зЪДжЦєеЉПжЭ•иЃ≤ињ∞йВ£йЗМзЪДзЬЯеЃЮйЭҐи≤МеТМжХЕдє°дЇЇзЪДзФЯе≠ШзКґеЖµгАВ
гААгААдЄЗзОЫжЙНжЧ¶пЉЪеПѓдї•ињЩдєИиѓіеРІпЉМињЩжШѓжИСе§ЪеєізЪДењГжДњгАВе§ЦжЭ•иАЕеЕ≥ж≥®дЇЖдЄАдЇЫе§ЦеЬ®зЪДдЄЬи•њпЉМеѓєж†ЄењГзЪДдЄЬи•њзРЖиІ£еЊЧдЄНеЊИйАПељїпЉМи°®иЊЊдЄКе∞±жЬЙдЇЖиѓѓеЈЃгАВе∞±жШѓеП™зЬЛеИ∞жЮЭеє≤еТМеПґе≠РпЉМж≤°жЬЙзЬЛеИ∞ж†єгАВеѓєиЧПжЧПжЭ•иѓіпЉМи°АзЉШгАБжЦЗеМЦгАБдЉ†зїЯињЩдЇЫдЄЬи•њпЉМжШѓжЬЙж†єзЪДгАВжЬЙдЇЇдЄНзРЖиІ£пЉМиѓіиЧПдЇЇдЄАзФЯиѓµзїПгАБз£ХйХње§ігАБеѓєжЭ•дЄЦжЬЙеЖАжЬЫпЉМињШдЄНе¶ВеОїеБЪзВєвАЬжЬЙзФ®зЪДдЇЛвАЭгАВдїЦдїђзЬЉдЄ≠зЪДи•њиЧПпЉМеТМдЄАдЄ™иЧПдЇЇзЬЉдЄ≠зЪДи•њиЧПжШѓдЄНдЄАж†ЈзЪДгАВиЧПжЧПжЦЗеМЦжШѓдЄАзІНеМЕеЃєжАІеЊИеЉЇзЪДгАБдї•дЇЇдЄЇжЬђзЪДжЦЗеМЦпЉМе§Де§ДдљУзО∞еѓєдЇЇгАБеѓєзФЯеСљзЪДеЕ≥жААпЉМи≠ђе¶ВдЄ§йГ®зЙЗе≠РйЗМйГљжПРеИ∞зЪДвАЬжФЊзФЯвАЭгАВжИСиІЙеЊЧзФ®жЕИжВ≤жЩЇжЕІгАБеЃБйЭЩеТМи∞РжЭ•ж¶ВжЛђиЧПжЦЗеМЦжѓФиЊГеЗЖз°ЃгАВ
гААгААдЇЇзЙ©еС®еИКпЉЪеѓєдЇОзО∞дї£жЦЗжШОзЪДйЧѓеЕ•пЉМдљ†зЪДзЙЗе≠РйЗМдЉЉдєОжµБйЬ≤еЗЇдЄАзІНењІиЩСеТМдЉ§жДЯгАВ
гААгААдЄЗзОЫжЙНжЧ¶пЉЪжИСеРОжЭ•еЬ®еМЧељ±дЄКе≠¶пЉМжѓПдЄ™е≠¶жЬЯйГљдЉЪеЫЮеЃґпЉМжѓПжђ°еЫЮеОїйГљдЉЪеПСзО∞дЄАдЇЫеПШеМЦгАВдЉ†зїЯзЪДдЄЬи•њж≠£еЬ®жґИ姱гАВиЇЂеЬ®еЕґдЄ≠зЪДдЇЇдєЯиЃЄж≤°жЬЙжДЯиІЙпЉМдљЖеЄЄеєіеЬ®е§ЦеБґе∞ФеЫЮеЃґзЪДдЇЇдЄАдЄЛе≠Ре∞±иГљжДЯиІЙеИ∞гАВжѓПжђ°еЫЮеОїпЉМйГљжЬЙдЄАдЄ§дЄ™иАБдЇЇйАЭеОїпЉМе∞±еГПзФµељ±йЗМеИїеШЫеСҐзЯ≥зЪДиАБдЇЇпЉМињШжЬЙе∞±жШѓзФЯжіїжЦєеЉПзЪДеПШеМЦгАВ
гААгААдЇЇзЙ©еС®еИКпЉЪдљ†иѓізЪДж≠£еЬ®жґИ姱зЪДдЉ†зїЯеМЕжЛђеУ™дЇЫпЉЯ
гААгААдЄЗзОЫжЙНжЧ¶пЉЪи≠ђе¶ВдЄАдЇЫиБМдЄЪзО∞еЬ®ж≤°жЬЙдЇЖпЉМжИСдЄЇDiscoveryжЛНињЗдЄАдЄ™зЇ™ељХзЙЗгАКжЬАеРОзЪДйШ≤йЫєеЄИгАЛпЉМе∞±жШѓж∞СйЧіеПѓдї•йШїж≠ҐеЖ∞йЫєзЪДеЈЂеЄИгАВжИСеРОжЭ•е∞±жГ≥еБЪдЄАдЄ™вАЬжЬАеРОзЪДвАЭз≥їеИЧпЉМеГПйЩНз•ЮгАБеН¶еЄИгАБзЫЄеЄИгАБиѓіеФ±иЙЇдЇЇгАБеФРеН°иЙЇдЇЇпЉМз≠Йз≠ЙгАВйЩНз•ЮдєЯжШѓеЈЂеЄИпЉМдЉЪжЬЙдЄАдЄ™дї™еЉПпЉМзДґеРОз•ЮзБµйЩДдљУпЉМдїЦдЉЪиѓіеЗЇдЄАдЇЫдЄЬи•њпЉМдљ†йЧЃдїЦпЉМдїЦиГљеЫЮз≠ФпЉМйЖТжЭ•еРОзЙєеИЂзЦ≤еА¶пЉМеАТеЬ®еЬ∞дЄКгАВ
гААгААдЇЇзЙ©еС®еИКпЉЪдї•еЙНдЇЇдїђеѓєзФЯиАБзЧЕж≠їгАБиЗ™зДґзО∞и±°жЧ†ж≥ХиІ£йЗКпЉМжЙАдї•йЬАи¶БеЈЂеЄИгАВзО∞еЬ®зІСе≠¶еПСе±ХеИ∞дЄАеЃЪйШґжЃµпЉМеЊИе§ЪдЄЬи•њйГљжѓФиЊГжЄЕж•ЪдЇЖпЉМињЩдЇЫиБМдЄЪзЪДжґИ姱䚆дЄНиІЙеЊЧдєЯеЊИиЗ™зДґеРЧпЉЯ
гААгААдЄЗзОЫжЙНжЧ¶пЉЪињЩзІНе≠ШеЬ®жЬЙеЃГзЪДеРИзРЖжАІпЉМдЄНжШѓжЙАжЬЙзЪДдЄЬи•њйГљиГљзФ®зІСе≠¶иІ£йЗКзЪДгАВ
гААгААдЇЇзЙ©еС®еИКпЉЪжЦѓеЃЊж†ЉеЛТиѓіињЗпЉМдЄ§зІНдЄНеРМжЦЗеМЦзЪДдЇЇпЉМйГље≠ШеЬ®дЇОеРДиЗ™зЪДз≤Њз•Юе≠§еѓВйЗМгАВйЭҐеѓєе§ЦжЭ•жЦЗеМЦпЉМиЧПж∞СжЧПиѓ•жАОдєИеКЮеСҐпЉЯдљ†е•љеГПдєЯжМЇзЯЫзЫЊзЪДгАВ
гААгААдЄЗзОЫжЙНжЧ¶пЉЪжИСжГ≥е±ХзО∞зЪДеПѓиГље∞±жШѓзЫЃеЙНжХідЄ™иЧПеМЇзЪДињЩж†ЈдЄАзІНзЯЫзЫЊзКґжАБгАВиЧПиѓ≠зО∞еЬ®еЉХеЕ•е§ІйЗПзЪДж±Йиѓ≠еТМиЛ±иѓ≠пЉМеОЯеЕИзЪДдЄАдЇЫз¶БењМиѓ≠еєіиљїдЇЇйГљдЄН姙зЯ•йБУдЇЖпЉМдЄІиСђеТМе©ЪеЂБдЄ≠зЪДдЄАдЇЫзЙєжЬЙдє†дњЧдєЯж≤°жЬЙдЇЖгАВзЙЗе≠РйЗМзЪДиЧПжИПгАКжЩЇзЊОжЫізЩїгАЛжШѓињЗиКВжЧґжѓПдЄ™жЭСеЇДйГљи¶БжЉФзЪДжИПпЉМиАБеєідЇЇеТМдЄ≠еєідЇЇзЬЛдЇЖйГљдЉЪжµБж≥™пЉМдљЖеєіиљїдЇЇеЈ≤зїПж≤°жЬЙжДЯиІЙдЇЖгАВе•ље§ЪдЄЬи•њеПѓдї•дЄОжЧґдњ±ињЫпЉМдљЖзО∞еЬ®жШѓињЮеРМз≤ЊеНОйГ®еИЖдєЯеЃМеЕ®дЄҐеЉГпЉМжґИ姱дЇЖпЉМињЩдЄАеИЗзЬЛиµЈжЭ•иЗ™зДґиАМзДґпЉМдљЖжљЬдЉПзЭАеН±йЩ©гАВеѓєдЄАдЄ™ж∞СжЧПжЭ•иѓіпЉМжЬЙж≤°жЬЙиГљеКЫдњЭжМБиЗ™еЈ±пЉМжЯРзІНз®ЛеЇ¶дЄКеЖ≥еЃЪдЇЖеЃГиГљдЄНиГљзФЯе≠ШдЄЛеОїгАВиЧПеМЇдї•еЙНж≤°жЬЙе≠¶ж†°пЉМеѓЇйЩҐе∞±жШѓеЃГзЪДе≠¶ж†°пЉМеЃГжЙАжЬЙзЪДжЦЗеМЦдЉ†жЙњйГљжШѓйАЪињЗеѓЇйЩҐжЭ•еЃМжИРзЪДпЉМйВ£йЗМжШѓиЧПжЧПдЉ†зїЯжЦЗеМЦзЪДеЯЇеЬ∞гАВеЬ®еЃЧжХЩзФЯжіїдЄОдЄЦдњЧзФЯжіїдєЛйЧіпЉМеЇФиѓ•жЬЙдЄАжЭ°йАЪйБУпЉМиГљињЫеЕ•дЄЦдњЧпЉМдєЯиГљзЉУжЕҐеЫЮељТеЃЧжХЩзФЯжіїзЪДеЇДдЄ•еТМз•ЮеЬ£гА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