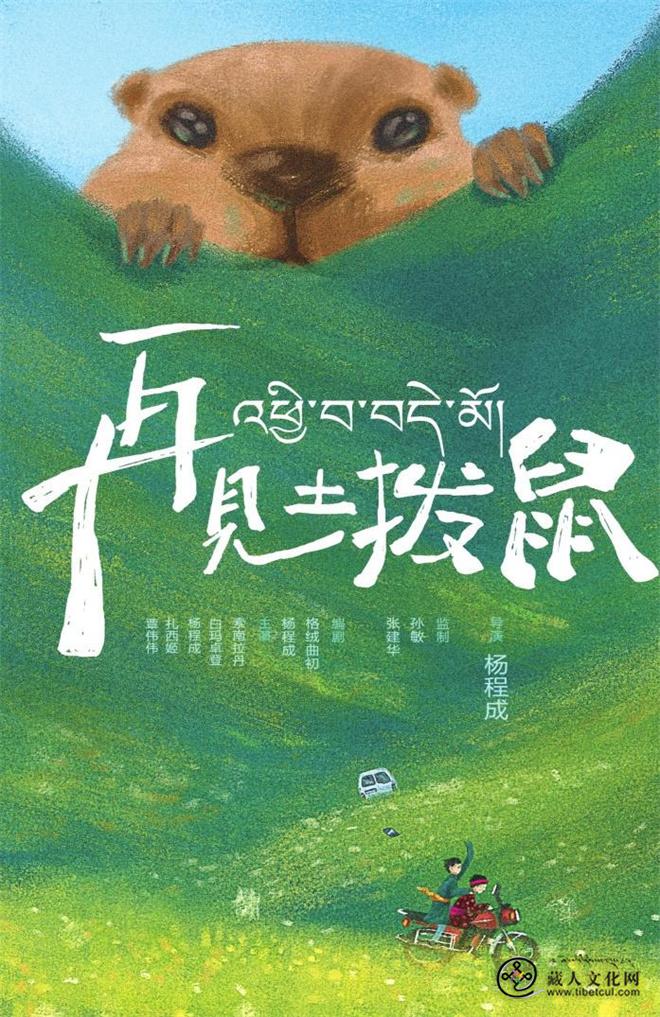жңұжҷ¶иҝӣпјҲ1983-пјүжұҹиӢҸиӢҸе·һдәәпјҢдё–з•ҢеҸІеҚҡеЈ«пјҢеӣӣе·қеӨ§еӯҰеӣҪйҷ…е…ізі»еӯҰйҷўдёӯеӣҪиҘҝйғЁиҫ№з–Ҷе®үе…ЁдёҺеҸ‘еұ•еҚҸеҗҢеҲӣж–°дёӯеҝғеҠ©зҗҶз ”з©¶е‘ҳпјҢе…іжіЁи—Ҹең°з”өеҪұзҡ„жң¬еңҹеҲӣдҪңгҖҒдә§дёҡеҸ‘еұ•е’Ңи·Ёж–ҮеҢ–дј ж’ӯгҖӮ
1990е№ҙеҮәз”ҹдәҺйқ’жө·жө·еҢ—зҡ„еҲҮйҳід»Җе§җпјҢжӢҘжңүзқҖеңЁз«һиө°йЎ№зӣ®дёҠжһҒдёәйӘ„дәәзҡ„жҲҳз»©пјҢиҮӘд»ҺеңЁ2012е№ҙдјҰж•ҰеҘҘиҝҗдјҡдёҠиҺ·еҫ—еҘіеӯҗ20е…¬йҮҢз«һиө°еӯЈеҶӣпјҲ2016е№ҙйҖ’иЎҘдёәдәҡеҶӣпјүеҗҺпјҢдёҚж–ӯеңЁеҗ„зұ»жҜ”иөӣдёӯж‘ҳйҮ‘еӨә银пјҢжҳҜи—Ҹж°‘ж—ҸеҠӘеҠӣжӢјжҗҸзҡ„дјҳз§Җд»ЈиЎЁе’ҢйӘ„еӮІгҖӮ2015е№ҙпјҢиҘҝи—ҸеҜјжј”жҹҜе…Ӣ·йҳҝж—әдё№еўһж‘„еҲ¶е®ҢжҲҗ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пјҢе°ҶеҲҮйҳід»Җе§җзҡ„жҲҗй•ҝж•…дәӢжҗ¬дёҠ银幕гҖӮиҜҘзүҮдәҺд»Ҡе№ҙ3жңҲ30ж—ҘиҮі4жңҲ1ж—ҘеңЁе…ЁеӣҪе…¬жҳ пјҢйӮЈд№ҲпјҢеңЁеҫ®еҚҡдёҠжӢҘжңүиҝ‘9дёҮеҗҚзІүдёқзҡ„еҲҮйҳід»Җе§җпјҢеҘ№зҡ„з”өеҪұиғҪеҗҰеҶҚж¬ЎжҝҖеҸ‘еҮәж°‘ж—ҸиҮӘиұӘж„ҹпјҢжҺҖиө·и§ӮеҪұзғӯжҪ®е‘ўпјҹжҹҜе…ӢеҜјжј”зҡ„йҰ–ж¬Ўж•…дәӢй•ҝзүҮеҲӣдҪңпјҢиғҪеҗҰиҫҫеҲ°йў„жңҹж•Ҳжһңе‘ўпјҹ
дёҖгҖҒе®ҸеӨ§зҡ„еҲ¶дҪңйў„жңҹ
д»Һ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дё»еҲӣжһ„жҲҗдёҠзңӢпјҢиҜҘзүҮжңүзқҖеҚҒеҲҶе®ҸеӨ§зҡ„йў„жңҹгҖӮ
йҰ–е…ҲпјҢиҜҘзүҮеҲ¶зүҮж–№дёәиҘҝи—ҸеҪұи§ҶеҸ‘еұ•жңүйҷҗе…¬еҸёгҖӮдҪңдёәжңүзқҖиҘҝи—Ҹз”өи§ҶеҸ°е®ҳж–№иғҢжҷҜгҖҒ2014е№ҙж–°жҲҗз«Ӣ并жүҝжӢ…зқҖиҮӘжІ»еҢәж–ҮеҢ–дә§дёҡи·Ёи¶ҠеҸ‘еұ•йҮҚеӨ§д»»еҠЎзҡ„еҚ•дҪҚпјҢе…¶еҜ„жңӣдәҺ第дёҖйғЁй•ҝзүҮ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иғҪеӨҹдёҖзӮ®жү“е“ҚгҖӮе®һйҷ…дёҠпјҢиҜҘзүҮж—©е·ІдәҺ2015е№ҙж‘„еҲ¶е®ҢжҜ•пјҢ并е…ҲеҗҺеҸӮеҠ дәҶеҢ—дә¬еӣҪйҷ…дҪ“иӮІз”өеҪұе‘ЁгҖҒзұіе…°еӣҪйҷ…дҪ“иӮІз”өеҪұз”өи§ҶиҠӮеҶіиөӣгҖҒдёҠжө·еӣҪйҷ…з”өеҪұиҠӮзҡ„еұ•жҳ гҖӮ
е…¶ж¬ЎпјҢиҜҘзүҮеҜјжј”дёәдёҠиҝ°е…¬еҸёеҪұи§ҶйғЁжҖ»з»ҸзҗҶжҹҜе…Ӣ·йҳҝж—әдё№еўһгҖӮжҹҜе…ӢжҳҜеңЁжӢүиҗЁз”өи§ҶеҸ°е’ҢиҘҝи—Ҹз”өи§ҶеҸ°жҲҗй•ҝ并е·ҘдҪңеӨҡе№ҙгҖҒе…·жңүжһҒдёәдё°еҜҢжү§еҜјз»ҸйӘҢзҡ„дёҖдҪҚеҜјжј”пјҢеңЁ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пјҢжҳҜиҘҝи—Ҹе№ҝз”өз•Ңзҡ„дёҖеј зҺӢзүҢгҖӮж–°еҚҺзӨҫ2015е№ҙзҡ„зЁҝ件пјҢжӣҫе°ҶжҹҜе…ӢдёҺдёҮзҺӣжүҚж—ҰзӣёжҸҗ并и®әпјҢз§°пјҡ“еҰӮд»Ҡ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ҢжҹҜе…Ӣ·йҳҝж—әдё№еўһиғҢеҗҺпјҢи¶ҠжқҘи¶ҠеӨҡзҡ„и—Ҹж—Ҹйқ’е№ҙејҖе§Ӣй—Ҝе…Ҙз”өеҪұиЎҢдёҡпјҢз”ЁеҪұеғҸиЎЁиҫҫзқҖ他们еҜ№дё–з•Ңзҡ„зңӢжі•гҖӮ”жҡӮдё”дёҚи®әж–°еҚҺзӨҫзҡ„иҝҷзҜҮзЁҝ件дҪңиҖ…жҳҜеҗҰзңҹзҡ„еҜ№и—Ҹең°з”өеҪұе…·еӨҮе®ўи§ӮзҗҶи§ЈпјҢд№ҹжҡӮдё”дёҚи®әжҹҜе…Ӣд»ҘеүҚжңӘжӣҫеҒҡиҝҮз”өеҪұж•…дәӢзүҮеҜјпјҢдҪҶз”ұжҹҜе…ӢйўҶиЎ”иҜҘзүҮзҡ„ж‘„еҲ¶пјҢиө„ж јж–№йқўжҳҜе®Ңе…ЁжІЎжңүй—®йўҳзҡ„гҖӮ
еҶҚж¬ЎпјҢиҜҘзүҮзҡ„зј–еү§е’Ңдё»жј”д№ҹдёҚеӯҳеңЁ“ж–°жүӢ”й—®йўҳгҖӮ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зҡ„зј–еү§е…јз”·дё»и§’иөөе®Ғе®ҮпјҢе…·жңүеҢ—дә¬з”өеҪұеӯҰйҷўж•ҷжҺҲгҖҒеҚҡеҜјзҡ„еӯҰиҖ…иә«д»ҪпјҢд№ҹжӣҫжҳҜи—Ҹж—Ҹйўҳжқҗж•…дәӢй•ҝзүҮгҖҠйӣӘеҹҹдё№йқ’гҖӢзҡ„зј–еү§е…јеҜјжј”пјҢд»Һе…¶жүҖиҺ·еҘ–йЎ№е’ҢеҸ‘иЎЁзҡ„и®әж–ҮзңӢпјҢеұһдәҺз”өеҪұиүәжңҜеӯҰ科йўҶеҹҹзҡ„йҮҚиҰҒ专家гҖӮд»–иғҪжҲҗдёәиҘҝи—ҸеҪұи§ҶеҸ‘еұ•е…¬еҸёзҡ„йҰ–йғЁй•ҝзүҮзҡ„зј–еү§е…јдё»и§’пјҢеҸҜз®—жҳҜ“йҮҚйҮҸзә§”гҖӮд»Һжј”е‘ҳзңӢпјҢйҘ°жј”еұҖй•ҝзҡ„еӨҡеёғжқ°жҳҜи—Ҹж—Ҹи§Ӯдј—еҚҒеҲҶзҶҹжӮүзҡ„“иҖҒжҲҸйӘЁ”дәҶпјҢеңЁеӨҡйғЁдё»ж—ӢеҫӢи—Ҹж—ҸйўҳжқҗеҪұи§Ҷдёӯжү®жј”иҝҮйҮҚиҰҒи§’иүІгҖӮйҘ°жј”й•ҝеӨ§еҗҺзҡ„еҲҮйҳід»Җе§җзҡ„еҫ·е§¬пјҢеҲҷжҳҜж–°дёҖд»Ји—Ҹж—ҸеҘіжј”е‘ҳпјҢеңЁиҝ‘е№ҙж–°зүҮгҖҠеҫ·е…°гҖӢгҖҒгҖҠиҙЎеҳҺж—ҘеҷўгҖӢгҖҒгҖҠдә”еҪ©зҘһз®ӯгҖӢдёӯжңүзқҖйқһеёёеҮәеҪ©зҡ„иЎЁзҺ°пјҢжҳҜе№ҙиҪ»и—Ҹж—Ҹи§Ӯдј—зңјдёӯзҡ„еҒ¶еғҸгҖӮ
既然жңүзқҖеҰӮжӯӨејәеӨ§зҡ„йҳөе®№пјҢйӮЈд№ҲжҲҗзүҮж•ҲжһңжҳҜеҗҰиғҪеӨҹж»Ўи¶ійў„жңҹе‘ўпјҹ
дәҢгҖҒжң¬ең°е…ғзҙ зҡ„“еҗҚ”“е®һ”з–ҸзҰ»
дҪңдёәдёҖйғЁиҘҝи—ҸдёҺйқ’жө·жө·еҢ—е·һеҗҲдҪңж‘„еҲ¶гҖҒд»ҘеҸҠж°‘ж—ҸжҲҗе‘ҳеңЁдё»еҲӣеӣўйҳҹдёӯеҚ еҫҲеӨ§жҜ”дҫӢзҡ„з”өеҪұпјҢ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дёҚд»…д»…жҳҜи—Ҹж—Ҹзҡ„“йўҳжқҗ”дәҶгҖӮд»ҺиҜҘзүҮжғ…иҠӮзңӢпјҢйҷӨи—Ҹж—ҸиҖҢеӨ–пјҢжұүж—ҸгҖҒи’ҷеҸӨж—ҸгҖҒеӣһж—Ҹзӯүж°‘ж—ҸеқҮжү®жј”дәҶйҮҚиҰҒи§’иүІгҖӮд»Һж•…дәӢеҸ‘з”ҹзҡ„ең°зӮ№——жө·еҢ—е·һзңӢпјҢиҝҷйҮҢд№ҹ并йқһжҳҜзәҜи—Ҹж—Ҹеұ…дҪҸең°еҢәпјҢиҖҢжҳҜдёҖдёӘи—ҸгҖҒеӣһгҖҒи’ҷеҸӨгҖҒжұүж—Ҹе…ұеҗҢз”ҹжҙ»зҡ„иө°е»ҠгҖӮе°Ҫз®ЎеҰӮжӯӨпјҢ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иҝҳжҳҜеӯҳеңЁзқҖ“еҗҚ”дёҺ“е®һ”д№Ӣй—ҙдёҖе®ҡзЁӢеәҰзҡ„з–ҸзҰ»гҖӮ
е°ұ“еҗҚ”иҖҢиЁҖпјҢеҸҜд»Ҙи®Өдёә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д»ҺиЎЁйқўдёҠзңӢжҳҜдёҖйғЁи—Ҹең°з”өеҪұгҖӮ第дёҖпјҢиҜҘзүҮжө·жҠҘдёҠжңҖеӨ§зҡ„еӯ—дҪ“жҳҜи—Ҹж–ҮпјӣжӯЈзүҮе‘ҲзҺ°еҪұзүҮж Үйўҳж—¶пјҢи—Ҹж–ҮеңЁеүҚпјҢжұүж–ҮеңЁеҗҺпјҢдёӨиҖ…еӯ—дҪ“еӨ§е°ҸзӣёеҗҢпјӣи—Ҹж–Үж Үйўҳз”ұеӨҡиҜҶд»ҒжіўеҲҮйўҳеҶҷгҖӮ第дәҢпјҢиҜҘзүҮж•…дәӢдё»зәҝжҳҜи—Ҹж—ҸиҝҗеҠЁе‘ҳеҲҮйҳід»Җе§җзҡ„жҲҗй•ҝеҺҶзЁӢгҖӮ第дёүпјҢиҜҘзүҮеҲ¶зүҮж–№гҖҒдё»еҲӣеӣўйҳҹе’Ңдё»иҰҒжј”е‘ҳзҡ„ж°‘ж—ҸеұһжҖ§д»Ҙи—Ҹж—Ҹдёәдё»гҖӮ
然иҖҢпјҢе°ұ“е®һ”иҖҢиЁҖпјҢ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дёҺеҗҢж—¶жңҹеҸ—еҲ°и—Ҹж—Ҹи§Ӯдј—еҘҪиҜ„зҡ„и—Ҹең°з”өеҪұпјҲдё»иҰҒжҳҜжҢҮ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жқҫеӨӘеҠ гҖҒеӨҡеҗүеҪӯжҺӘзӯүи—Ҹж—ҸеҜјжј”дҪңе“ҒеҸҠеј жқЁгҖҒжўҒеҗӣеҒҘзӯүжұүж—ҸеҜјжј”дҪңе“ҒпјүзӣёжҜ”пјҢеңЁе‘ҲзҺ°жң¬ең°е…ғзҙ ж–№йқўд»ҚжңүиӢҘе№ІеҸҜе®Ңе–„д№ӢеӨ„гҖӮ
йҰ–е…ҲеңЁжң¬ең°иҜӯиЁҖж–№йқўгҖӮдёҚеҸҜеҗҰи®ӨпјҢеңЁжө·еҢ—е·һиҝҷдёҖеӨҡж°‘ж—Ҹиө°е»Ҡең°еҢәпјҢжұүиҜӯжҳҜдёҖз§ҚйҖҡз”ЁиҜӯиЁҖпјҢдҪҶ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еңЁд»Ҙи—Ҹж—Ҹдёәдё»зҡ„еӨҡдёӘеңәжҷҜдёӯд»Қ然е°ҶжұүиҜӯдҪңдёәеҸ°иҜҚпјҢжң¬ең°жҖ§жҲ–жӣ°зңҹе®һжҖ§е°ұеҸ—еҲ°дәҶжҚҹе®ігҖӮжҲ‘们еҸ‘зҺ°пјҢи—ҸиҜӯеҸ°иҜҚеңЁе…ЁзүҮдёӯе‘ҲзӮ№зјҖејҸж•ЈеёғпјҢиҝҷз§ҚеҒҡжі•дёҺе№Іи„Ҷе…ЁйғЁдҪҝз”Ёж ҮеҮҶзҡ„жұүиҜӯжҷ®йҖҡиҜқй…ҚйҹіпјҢжӣҙжҳҫеҫ—“иҷҡжғ…еҒҮж„Ҹ”гҖӮи°ўйЈһеҜјжј”зҡ„гҖҠзӣҠиҘҝеҚ“зҺӣгҖӢгҖҒз”°еЈ®еЈ®еҜјжј”зҡ„гҖҠзӣ—马иҙјгҖӢпјҢеқҮжңүи—ҸгҖҒжұүиҜӯдёӨдёӘй…ҚйҹізүҲжң¬пјҢд»ҘйҖӮеә”з”өеҪұе…¬жҳ еҲ¶еәҰпјҢ并满足дәҶдёҚеҗҢи§Ӯдј—зҡ„йңҖжұӮгҖӮ笔иҖ…и®ӨдёәпјҢ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既然иҰҒеұ•зҺ°еӨҡж°‘ж—Ҹиө°е»ҠйЈҺиІҢпјҢйӮЈжӣҙеә”иҜҘеңЁеҗҲйҖӮзҡ„еңәеҗҲдёӯдҪҝз”ЁзәҜзІ№зҡ„ж°‘ж—ҸиҜӯиЁҖ——дҫӢеҰӮз«Ҙе№ҙеҲҮйҳід»Җе§җеҸ°иҜҚгҖҒеҲҮйҳід»Җе§җ家дёӯеҸ°иҜҚгҖҒз”ІзғӯзҲ¶еӯҗеҜ№иҜқгҖҒз”ІзғӯдёҺеҲҮйҳід»Җе§җеҜ№иҜқзӯүзӯүгҖӮ
жңүдёҖзӮ№д№ҹеә”жҢҮеҮәпјҢеҲҮйҳід»Җе§җпјҲаҪҶаҪјаҪҰајӢаҪ‘аҪ–аҫұаҪІаҪ„аҪҰајӢаҪҰаҫҗаҫұаҪІаҪ‘ајҚпјҢchos dbyings skyidпјүд№ӢжүҖд»ҘеҸ–жұүеҗҚдёә“еҲҮйҳід»Җе§җ”пјҢиҮӘ然жңүжө·еҢ—е·һжө·жҷҸеҺҝж–№иЁҖзҡ„еӣ зҙ пјҢжҲ–еҸҜиғҪжҳҜйңҖиҰҒејәи°ғи—ҸеҗҚдёӯзҡ„еӯ—жҜҚ“аҪҰ”пјҢд»ҘдҫҝеҢәеҲ«дәҺе…¶д»–жӢјжі•гҖӮиҜҘзүҮе°Ҷе…¶и—ҸеҗҚзӣҙжҺҘжҢүз…§жӢүиҗЁиҜқзҡ„еҸ‘йҹіж–№ејҸиҜ‘дёә“жӣІжҙӢеҗү”пјҲиҝҷз§ҚйҹіиҜ‘е®һйҷ…дёҠд»ҚдёҚеҮҶзЎ®пјүпјҢеңЁиҘҝи—ҸеҲ¶дҪңж–№жқҘзңӢдјјд№ҺжІЎжңүй—®йўҳпјҢжҲ–и®ёд№ҹжңүиҘҝи—ҸеҲ¶дҪңж–№еңЁдј ж’ӯдёҠзҡ„зӣёе…іиҖғиҷ‘пјҢдҪҶд№ҹжҚҹе®ідәҶеҪ“ең°жҖ§пјҢжӣҙдёҚз¬ҰеҗҲзҝ»иҜ‘еӯҰ“еҗҚд»Һдё»дәә”зҡ„еҺҹеҲҷгҖӮеҜ№дәҺжұүж—Ҹи§Ӯдј—иҖҢиЁҖпјҢ“жӣІжҙӢеҗү”е’Ң“еҲҮйҳід»Җе§җ”дјјд№ҺжҳҜдёӨдёӘдёҚеҗҢзҡ„дәәпјҢеҪұзүҮжҳҜжғід»ҘжӯӨжҸҗйҶ’и§Ӯдј—иҜҘзүҮзҡ„жғ…иҠӮжңүеҫҲеӨ§иҷҡжһ„еҗ—пјҹеҸҜжҳҜпјҢжҲ‘жІЎжңүжіЁж„ҸеҲ°е…ЁзүҮжңүд»»дҪ•е…ідәҺ“зәҜеұһиҷҡжһ„”жҲ–“ж №жҚ®еҲҮйҳід»Җе§җдәӢиҝ№ж”№зј–”зҡ„еӯ—ж ·пјҢеҚҙеҮәзҺ°дәҶ“жӣІжҙӢеҗүеӨәеҫ—еҘҘиҝҗдјҡй“ңзүҢ”зҡ„иҜҙжҳҺж–Үеӯ—пјӣеҰӮжӯӨдёҖжқҘпјҢдёҚд»…зңҹе®һе’Ңиҷҡжһ„д№Ӣй—ҙиў«жЁЎзіҠпјҢд№ҹдёҚеҲ©дәҺеҗ‘жұүж—Ҹи§Ӯдј—е®Јдј еҲҮйҳід»Җе§җзҡ„зңҹе®һдәӢиҝ№——иҮіе°‘д»ҺзҪ‘з»ңжҗңзҙўзңӢпјҢеҲҮйҳід»Җе§җжң¬дәәд»ҺжңӘд»Ҙ“жӣІжҙӢеҗү”зҡ„жұүеҗҚеҮәзҺ°еңЁжӯЈејҸжҠҘйҒ“дёӯгҖӮ
е…¶ж¬ЎеңЁж•…дәӢзәҝж–№йқўгҖӮж•…дәӢзәҝзҡ„еұ•ејҖж–№ејҸпјҢе°ұжҳҜеҪұзүҮи®Іж•…дәӢзҡ„и§Ҷи§’д»ҘеҸҠи®ІиҝҷдёӘж•…дәӢзҡ„зӣ®зҡ„гҖӮиҰҒдҪҝ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жҲҗдёәдёҖйғЁеҗҚеүҜе…¶е®һзҡ„и—Ҹең°з”өеҪұпјҢйӮЈд№ҲеҲҮйҳід»Җе§җзҡ„жҲҗй•ҝеә”иҜҘжҲҗдёәдё»зәҝпјҢеҘ№зҡ„и§’иүІеә”жҲҗдёәдёҖеҸ·и§’иүІжҲ–иҖ…дёҺдҪ•еҝ—еі°пјҲеёҲзҲ¶пјүең°дҪҚе№ізӯүзҡ„и§’иүІгҖӮдҪҶжҳҜд»ҺиҜҘзүҮе®һйҷ…е‘ҲзҺ°зҡ„ж•…дәӢзңӢпјҢзј–еү§иөөе®Ғе®Үж•ҷжҺҲйҘ°жј”зҡ„дҪ•еҝ—еі°жҲҗдёәдәҶз»қеҜ№зҡ„дёҖеҸ·гҖӮжӣҙд»Өдәәе°ҙе°¬зҡ„жҳҜпјҢеј еҳүпјҲеј иҖҒеёҲпјҢиөөе®ҒйҘ°пјүдёҺдҪ•еҝ—еі°д№Ӣй—ҙзҡ„зҲұжғ…зәҝпјҢдёҠеҚҮеҲ°дәҶдёҺеҲҮйҳід»Җе§җжҲҗй•ҝзәҝе№іиЎҢзҡ„ең°дҪҚпјҢдҪ•еҝ—еі°зҡ„иҮӘжҲ‘е®һзҺ°иЎЁзҺ°еҫ—жҜ”еҲҮйҳід»Җе§җзҡ„жҲҗеҠҹжӣҙдёәеЈ®йҳ”пјҲиҮіе°‘д»ҺеҮ дёӘй•ңеӨҙзҡ„з”ЁеҝғзЁӢеәҰзңӢзЎ®е®һжҳҜиҝҷж ·пјүгҖӮ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иҜҒжҚ®жҳҜпјҡеҪұзүҮз»“е°ҫеӨ„еҮәзҺ°дәҶ“и°Ёд»ҘжӯӨзүҮзҢ®з»ҷжӣҫз»Ҹе’ҢжӯЈеңЁдёәиҘҝйғЁеҹәеұӮдҪ“иӮІдәӢдёҡеҒҡеҮәиҙЎзҢ®д»ҘеҸҠеҚіе°ҶеҘ”иөҙиҘҝйғЁзҡ„еҹәеұӮдҪ“иӮІе·ҘдҪңиҖ…”зҡ„еӯ—幕д»ҘеҸҠ他们зҡ„зҫӨеғҸгҖӮеҪұзүҮзӣ®зҡ„еҲ°жӯӨе·Із»ҸйқһеёёжҳҺжҳҫпјҡе®ғжӯҢйўӮзҡ„жҳҜдҪ•еҝ—еі°иҝҷж ·зҡ„жұүж—Ҹж”Ҝж•ҷиҖ…д»ҘеҸҠеј еҳүиҝҷж ·зҡ„жұүж—ҸеҢ»з–—жҸҙи—ҸиҖ…пјҢеҲҮйҳід»Җе§җжҲҗй•ҝзәҝе®һйҷ…дёҠе·Із»ҸйҖҖеҢ–дёәдәҶеёҰжңүдёҖе®ҡжң¬ең°иүІеҪ©зҡ„“иЈ…йҘ°”гҖӮдёҚз®ЎеҲ¶дҪңиҖ…зҡ„еҲқиЎ·жҳҜд»Җд№ҲпјҢдҪҶдёҠиҝ°еҒҡжі•жүҖиҫҫеҲ°зҡ„ж•Ҳжһң——иҮіе°‘еҜ№и—Ҹж—Ҹи§Ӯдј—зҡ„дј ж’ӯж•Ҳжһң——并дёҚе°ҪеҰӮдәәж„ҸгҖӮ
е°ұиҝҷдёҖзӮ№е»¶дјёејҖеҺ»пјҢ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жҲҗдәҶдёҖйғЁзәҜе®ўдҪҚи§Ҷи§’зҡ„дҪңе“ҒгҖӮ笔иҖ…и®ӨдёәпјҢйқһи—Ҹж—ҸеҜјжј”дёҚжҳҜдёҚиғҪжӢҚи—Ҹж—ҸйўҳжқҗеҪұзүҮпјҢйқһи—Ҹж—Ҹзј–еү§дёҚжҳҜдёҚиғҪеҶҷи—Ҹж—Ҹйўҳжқҗеү§жң¬пјҢеҗҢж—¶д№ҹдёҚеҸҜиғҪйҒҝе…Қ“еӨ–жқҘиҖ…”зҡ„е®ўдҪҚи§Ҷи§’пјӣе…ій”®еңЁдәҺпјҢйқһи—Ҹж—ҸеҲӣдҪңдәәе‘ҳиҰҒеҰӮдҪ•е°ҠйҮҚиҝҷдёҖ“ејӮж–ҮеҢ–”йўҳжқҗпјҢдәҰеҚіеҰӮдҪ•еҠӘеҠӣз»“еҗҲ“еӨ–жқҘиҖ…”зҡ„е®ўдҪҚи§Ҷи§’дёҺ“жң¬ең°дәә”зҡ„дё»дҪҚи§Ҷи§’гҖӮеҰӮеј жқЁзҡ„гҖҠеҶҲд»ҒжіўйҪҗгҖӢгҖҒгҖҠзҡ®з»ідёҠзҡ„йӯӮгҖӢпјҲ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зј–еү§пјүгҖҒиҗ§еҜ’дёҺжўҒеҗӣеҒҘзҡ„гҖҠе–ң马жӢүйӣ…еӨ©жўҜгҖӢжҳҜйқһи—Ҹж—ҸеҜјжј”дҪңеҮәдёҠиҝ°еҠӘеҠӣзҡ„дјҳз§ҖжҲҗжһңпјӣеӨҡеҗүеҪӯжҺӘеҜјжј”гҖҒжһ—ејәзј–еү§зҡ„гҖҠиҙЎеҳҺж—ҘеҷўгҖӢпјҢиҫҫжқ°дёҒеўһеҜјжј”гҖҒзҺӢеҶҚе®Ҹзј–еү§зҡ„гҖҠзәўдёқеёҰгҖӢпјҢеҲҷжҳҜйқһи—Ҹж—Ҹзј–еү§зҡ„жқ°дҪңпјӣйӣ…е…Ӣ·иҙқжұүзҡ„гҖҠе–ң马жӢүйӣ…гҖӢжӣҙжҳҜеҖҫеҗ‘дәҺеҠӘеҠӣжҠ№еҺ»еӨ–жқҘиҖ…з—•иҝ№пјҢжҲҗдёәдёҖйғЁж ҮжқҶејҸ“дјӘдё»дҪҚ”дҪңе“Ғ——иҝҷдәӣеҪұзүҮйғҪжҳҜз»“еҗҲдәҶдё»гҖҒе®ўдҪҚи§Ҷ角并иҺ·еҫ—и—Ҹж—ҸеҸҠйқһи—Ҹж—Ҹи§Ӯдј—еҘҪиҜ„зҡ„еҪұзүҮгҖӮзӣёжҜ”д№ӢдёӢпјҢ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зҡ„жұүж—Ҹзј–еү§е…јз”·дё»и§’иөөе®Ғе®ҮжңӘиғҪе……еҲҶеј•е…Ҙдё»дҪҚи§Ҷи§’пјӣеҜјжј”жҹҜе…ӢжҲ–з”ұдәҺиөөе®Ғе®Үжң¬дәәзҡ„“жқғеЁҒжҖ§”иҖҢеҜ№ж‘„еҲ¶ж–№еҗ‘еҮәзҺ°“еӨұжҺ§”иҝ№иұЎпјҢиҝҷеҜјиҮҙе…ЁзүҮи§Ӯж„ҹи¶Ӣеҗ‘дәҺдәҶдё»ж—ӢеҫӢпјҢеҗҢж—¶еҚҙжІЎиғҪеҫҲеҘҪең°дҝқдҪҸиүәжңҜжҖ§гҖӮ
йӮЈд№ҲпјҢеҲ¶дҪңж–№зҡ„иҘҝи—ҸиҮӘжІ»еҢәе№ҝз”өйғЁй—Ёе®ҳж–№иғҢжҷҜпјҢжҳҜеҗҰдёҺеҪұзүҮзҡ„иө°еҗ‘зӣёе…іе‘ўпјҹжңүдёҖе®ҡзӣёе…іжҖ§пјҢдҪҶе°ҡдёҚжһ„жҲҗеӣ жһңй“ҫгҖӮеӣ дёәеҗҢж ·жҳҜе…·жңүе®ҳж–№еҲ¶дҪңиғҢжҷҜзҡ„гҖҠиҙЎеҳҺж—ҘеҷўгҖӢпјҲеӨҡеҗүеҪӯжҺӘпјүдёҺгҖҠдә”еҪ©зҘһз®ӯгҖӢпјҲ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үпјҢдёҚз®ЎжҳҜдё»дҪҚи§Ҷи§’иҝҳжҳҜиүәжңҜжҖ§пјҢйғҪдҝқеӯҳеҫ—зӣёеҜ№е®Ңж•ҙпјҢе°Ҫз®ЎжҲ‘们д»ҚеҸҜеңЁе…¶дёӯеҸ‘зҺ°дёҖдәӣеҲ¶дҪңж–№дё»ж—ӢеҫӢж„Ҹеӣҫзҡ„иӣӣдёқ马иҝ№гҖӮ
еҶҚж¬ЎпјҢжң¬ең°е…ғзҙ д№Ӣ“еҗҚ”“е®һ”зӣёз¬ҰпјҢиҝҳдҪ“зҺ°еңЁжӯӨзұ»е…ғзҙ зҡ„дёҚеҸҜжӣҝд»ЈжҖ§дёҠ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ҰӮжһңжҲ‘们е°Ҷ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дёӯзҡ„и—Ҹж—Ҹе…ғзҙ е…ЁйғЁжӣҝжҚўжҲҗе…¶д»–ж–ҮеҢ–е…ғзҙ пјҢең°зӮ№жӣҝжҚўжҲҗеҸҰдёҖдёӘд№Ўжқ‘жҲ–зү§еңәпјҢеҸҷдәӢиғҪеҗҰжӯЈеёёе®ҢжҲҗпјҹзӯ”жЎҲжҳҜиӮҜе®ҡзҡ„гҖӮ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еҜ№жң¬ең°е…ғзҙ зҡ„иЎЁйқўеҢ–еӨ„зҗҶж–№ејҸд»ҘеҸҠз”·дё»и§’зҡ„ең°дҪҚпјҢеҶіе®ҡдәҶиҜҘзүҮжүҖиҜҙзҡ„дёӘдәәжҲҗй•ҝиҝҮзЁӢпјҢд№ғжҳҜ“ж”ҫд№Ӣеӣӣжө·иҖҢзҡҶеҮҶ”зҡ„“жҷ®дё–д»·еҖј”гҖӮиҝӣдёҖжӯҘиҖҢиЁҖпјҢеҰӮжһңжң¬ең°е…ғзҙ зҡ„еҸҜжӣҝд»ЈжҖ§еҫҖеҫҖж„Ҹе‘ізқҖеҪұзүҮзІҫзҘһеҶ…ж¶өзҡ„е…ұйҖҡжҖ§пјҢйӮЈд№Ҳе®ғиғҪеҗҰдёәеҪұзүҮзҡ„и·Ёж–ҮеҢ–дј ж’ӯжҸҗдҫӣжқЎд»¶е‘ўпјҹ笔иҖ…и®ӨдёәпјҢж¬ зјәжң¬еңҹж°”жҒҜгҖҒжҲ–жң¬еңҹж°”жҒҜиЎЁзҺ°еҫ—иҝҮдәҺеҲ»ж„Ҹзҡ„дҪңе“ҒпјҢеҸҚиҖҢдјҡдҪҝи·Ёж–ҮеҢ–дј ж’ӯдё§еӨұ“и·Ё”иҝҷдёҖж ёеҝғж„Ҹд№үгҖӮ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еҜ№жң¬ең°е…ғзҙ зҡ„ж·ЎеҢ–пјҢе·Із»ҸиҫҫеҲ°дәҶиҝһ“зҢҺеҘҮ”йғҪи°ҲдёҚдёҠзҡ„зЁӢеәҰгҖӮеҪ“д»ҠпјҢеҺ»иҝҮи—Ҹең°зҡ„и§Ӯдј—гҖҒзҶҹжӮүи—Ҹең°еҹәжң¬зү№иҙЁзҡ„йқһи—Ҹж—Ҹи§Ӯдј—и¶ҠжқҘи¶ҠеӨҡпјӣиҝҷж ·дёҖйғЁеҪұзүҮпјҢж—ўжІЎжңү“ж–ҮеҢ–зҢҺеҘҮ”“жҷҜи§ӮзҢҺеҘҮ”еёҰжқҘзҡ„еҶІеҮ»ж„ҹпјҢеҸҲж— жі•дҪҝиҮӘе·ұдј йҖ’зҡ„зІҫзҘһеҶ…ж ё“жҺҘең°ж°””пјҢйӮЈе®ғе°ұдёҚиғҪз®—жҳҜжҲҗеҠҹзҡ„и·Ёж–ҮеҢ–дј ж’ӯжЎҲдҫӢгҖӮз®ҖеҚ•иҖҢиЁҖпјҢиҝһ“йқ’жө·ж•…дәӢ”йғҪи®ІдёҚеҘҪпјҢжҖҺд№Ҳи°Ҳеҫ—дёҠ“и®ІеҘҪдёӯеӣҪж•…дәӢ”е‘ўпјҹ
дёүгҖҒдҪҷи®ә
2015е№ҙиө·пјҢ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еңЁеҗ„ең°еұ•жҳ жҲ–зӮ№жҳ иӢҘе№Іж¬ЎпјҢдҪҶжңӘиғҪеңЁ2017е№ҙе…¬жҳ ж—¶иҺ·еҫ—еёӮеңәе’Ңи§Ӯдј—йқ’зқҗгҖӮиҜҘзүҮеңЁз¬”иҖ…жүҖеңЁзҡ„жҲҗйғҪе…ұжҺ’зүҮ3еңәпјҲе…ЁеӣҪжҺ’зүҮдёә3жңҲ30ж—ҘиҮі4жңҲ1ж—ҘдёүеӨ©пјүпјҢе°Ҫз®ЎжҲҗйғҪеҸҢжҘ еңәеә§еёӯе…ЁйғЁе”®еҮәпјҲе…ұ52еә§пјүпјҢдҪҶйғҪжұҹе °жЁӘеә—еңәд»…е”®еҮә1еј зҘЁпјҲе·ҘдҪңж—ҘдёҠеҚҲ第дёҖеңәпјҢеҚіз¬”иҖ…жң¬дәәд№°дәҶ1еј зҘЁпјүгҖӮжҲӘжӯў4жңҲ2ж—Ҙ20ж—¶пјҢиҜҘзүҮеңЁ“зҢ«зңјдё“дёҡзүҲ”зҡ„зҙҜи®ЎзҘЁжҲҝдёә0.5дёҮгҖӮж №жҚ®“зҢ«зңј”ж•°жҚ®пјҢиҜҘзүҮеңәеқҮдәәж¬ЎеӨҡдёә0-3дәәпјҢжңҖеӨҡзҡ„дёӨеңәеҲҶеҲ«жҳҜжҲҗйғҪ3жңҲ30ж—Ҙзҡ„11дәәд»ҘеҸҠ3жңҲ31ж—Ҙзҡ„52дәәпјҲжҲ–дёәеҢ…еңәпјүпјӣ“иұҶз“Ј”зҷ»и®°зңӢиҝҮдәәж•°дёә25дәәгҖӮиҝҷдёҺе…ЁеӣҪиүәжңҜз”өеҪұиҒ”зӣҹ/дёӯеӣҪз”өеҪұиө„ж–ҷйҰҶеңЁжҲҗйғҪеҒҡ“и—Ҹең°еҜҶз Ғ”е·Ўеұ•ж—¶д»ҘеҸҠжҲҗйғҪ“иҝҰе…Ҙз©әй—ҙ”еҒҡ“еҚҡиҜӯеҪұеұ•”ж—¶зҡ„и§Ӯдј—зғӯжғ…д№ҹеҪўжҲҗејәзғҲеҜ№жҜ”гҖӮеӣ жӯӨпјҢдҪңдёәиҘҝи—ҸеҪұи§ҶеҸ‘еұ•жңүйҷҗе…¬еҸёйҰ–йғЁй•ҝзүҮзҡ„гҖҠе…«дёҮйҮҢгҖӢпјҢ究з«ҹжҳҜе“ӘдёӘзҺҜиҠӮеҮәдәҶй—®йўҳпјҢеҲ¶дҪңж–№е’Ңдё»еҲӣеӣўйҳҹжҲ–еә”иҜҘи®ӨзңҹжҖ»з»“пјҢд»Ҙе…ҚиҜҘе…¬еҸёеҸҲжҲҗдәҶеҸҰдёҖдёӘ“ж”ҝеәңжҠ•иө„дёҚе·®й’ұ”зҡ„иҘҝи—Ҹдә§дёҡеҸ‘еұ•е…ёеһӢпјҢи·ідёҚеҮәиҘҝи—Ҹ“йқһе…ёеһӢдәҢе…ғз»“жһ„”пјҲеӯҷеӢҮж•ҷжҺҲиҜӯпјүзҡ„еҸ‘еұ•жҖӘеңҲ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