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жӢүжҜӣеҗүпјҢе…°е·һеӨ§еӯҰеҢәеҹҹз»ҸжөҺеӯҰзЎ•еЈ«пјҢе…°е·һеӨ§еӯҰж°‘ж—ҸеӯҰз ”з©¶йҷў 2009зә§еҚҡеЈ«з”ҹпјҢдё»иҰҒз ”з©¶ж–№еҗ‘жҳҜи—Ҹж—Ҹзҡ„еӨ©ж–ҮеҺҶз®—гҖҒи—Ҹж—ҸеҺҶеҸІж–ҮеҢ–гҖӮиҝ‘е№ҙжқҘпјҢдё»жҢҒ并е®ҢжҲҗеӣҪ家зӨҫ科еҹәйҮ‘йЎ№зӣ®вҖңиҘҝи—Ҹзҡ„еӨ©ж–ҮеҺҶз®—з ”з©¶вҖқпјҢж•ҷиӮІйғЁдәәж–ҮзӨҫ科еҹәйҮ‘йЎ№зӣ®вҖңжӢүеҚңжҘһеҜәдёҒ科尔жүҺд»“з ”з©¶вҖқпјҢиҘҝи—ҸиҮӘжІ»еҢәй«ҳж Ўдәәж–ҮзӨҫ科项зӣ®вҖңи—Ҹж—ҸжңҜж•°еӯҰеңЁж°‘й—ҙзҡ„е®һи·өеә”з”Ёз ”з©¶вҖқд»ҘеҸҠеј•иҝӣдәәжүҚйЎ№зӣ®пјӣеңЁж ёеҝғжңҹеҲҠдёҠеҸ‘иЎЁеӯҰжңҜи®әж–ҮеҚҒдҪҷзҜҮгҖӮ
еңЁйҮҮи®ҝжӢүжҜӣеҗүд№ӢеүҚпјҢжҲ‘并дёҚзҹҘйҒ“еҘ№е·Із»Ҹеұ…家йҡ”зҰ»дәҶ80дҪҷеӨ©пјҢеҪ“еҗ¬еҲ°еҘ№иҜҙеҘ№еңЁиҝҷ80еӨ©йҮҢиҝҮеҫ—еҫҲе№ёзҰҸж—¶пјҢжҲ‘зҡ„жғҠ讶жҳҜиЎЁйқўзҡ„пјҢеҘ№жүҖиҜҙзҡ„е№ёзҰҸдәҺжҲ‘иҖҢиЁҖд№ҹд»…д»…еҸӘжҳҜдёҖз§Қдҝ®иҫһпјҢиҝҷе°ұеҘҪжҜ”жҲ‘дёҚдјҡеңЁиҖғиҜ•ж—¶еҰ„жғіиҖҒеёҲдјҡз»ҷжҲ‘ж»ЎеҲҶпјҢдәҺиҮӘе·ұиҖҢиЁҖз»қж— еҸҜиғҪзҡ„дәӢжғ…жҲ‘е·Із»Ҹд№ жғҜдәҶдёҚеҺ»ж·ұжҖқгҖӮдҪҶеҪ“жҲ‘ејҖе§ӢзқҖжүӢеҶҷиҝҷзҜҮзЁҝ件зҡ„ж—¶еҖҷпјҢжҲ‘еҚҙеҸ‘зҺ°пјҢжғіжё…жҘҡеҘ№дёәд»Җд№Ҳдјҡе№ёзҰҸпјҢжүҚжҳҜиҝҷзҜҮзЁҝ件зҡ„ж„Ҹд№үжүҖеңЁгҖӮ
2021е№ҙ5жңҲ21ж—ҘпјҢе№ҝдёңж•ҷиӮІеҮәзүҲзӨҫзҡ„еӣҪ家еҮәзүҲеҹәйҮ‘йЎ№зӣ®вҖ”вҖ”90еҲҶй’ҹзәӘеҪ•зүҮгҖҠеұӢи„Ҡзҡ„ж…§зңјгҖӢпјҲEyes of Wisdom in TibetпјүеңЁе№ҝдёң科еӯҰдёӯеҝғдәҡжҙІжңҖеӨ§зҡ„3D巨幕еҪұеҺ…йҰ–жҳ пјҢиҝҷйғЁзәӘеҪ•зүҮз”ұ马еҫ·йҮҢеӣҪйҷ…з”өеҪұиҠӮжңҖдҪізәӘеҪ•зүҮеҜјжј”з”°е–ҶеңЁйӣӘеҹҹй«ҳеҺҹеҺҶж—¶еҚҒе№ҙиү°иӢҰи·ҹжӢҚиҖҢжҲҗпјҢи®Іиҝ°дәҶжңҖйЎ¶зә§зҡ„зҺ°д»ЈеӨ©ж–Үи§ӮжөӢи®ҫж–ҪдёҺ延з»өеҚғдҪҷе№ҙи—Ҹдј еӨ©ж–ҮеҺҶз®—зҡ„зҘһз§ҳдәӨжұҮгҖӮжӢүжҜӣеҗүдҪңдёәдёҖдҪҚдј з»ҹеӨ©ж–ҮеӯҰзҡ„з ”з©¶дәәе‘ҳпјҢжҳҜиҜҘзүҮзҡ„дё»дәәе…¬д№ӢдёҖпјҢзүҮдёӯи®Іиҝ°дәҶеҘ№дёҺи—ҸеҺҶз»“зјҳзҡ„еҚҒе№ҙпјҢи®°еҪ•еҘ№д»ҺйҖүжӢ©и—ҸеҺҶдҪңдёәеҚҡеЈ«з ”з©¶ж–№еҗ‘еҲ°д»ҺдәӢи—ҸеҺҶз ”з©¶е·ҘдҪңзҡ„зӮ№ж»ҙгҖӮ
2002е№ҙ9жңҲ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иҖғе…Ҙйҷ•иҘҝеёҲиҢғеӨ§еӯҰзү©зҗҶдёҺдҝЎжҒҜжҠҖжңҜеӯҰйҷўеӯҰд№ з”өеӯҗжҠҖжңҜж•ҷиӮІдё“дёҡпјӣ2006е№ҙ9жңҲ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и·Ёдё“дёҡйҖүжӢ©дәҶе…°е·һеӨ§еӯҰеҢәеҹҹз»ҸжөҺеӯҰдё“дёҡж”»иҜ»зЎ•еЈ«пјӣ2009е№ҙ9жңҲ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еҶҚж¬Ўи·ЁиҖғпјҢиҝӣе…Ҙе…°е·һеӨ§еӯҰж°‘ж—ҸеӯҰз ”з©¶йҷўеӯҰд№ ж°‘ж—ҸеӯҰВ·и—ҸеӯҰдё“дёҡж”»иҜ»еҚҡеЈ«гҖӮд»Һжң¬з§‘еҲ°еҚҡеЈ«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зҡ„жҜҸдёӘйҖүжӢ©зңӢдјји·ЁеәҰеҫҲеӨ§пјҢеҚҙеҸҲеңЁеҶҘеҶҘд№Ӣдёӯи—Ҹжңүжңәзјҳе·§еҗҲд№Ӣж„ҸгҖӮ2014е№ҙ8жңҲиҮід»Ҡ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дёҖзӣҙеңЁиҘҝи—ҸеӨ§еӯҰи—ҸеӯҰз ”з©¶жүҖд»ҺдәӢеӨ©ж–ҮеҺҶз®—зӣёе…ізҡ„з ”з©¶е·ҘдҪңпјҢжң¬з§‘ж—¶еӯҰд№ зҡ„зү©зҗҶзҹҘиҜҶеұһдәҺзүӣйЎҝе®Үе®ҷи§ӮпјҢиҖҢеҚҡеЈ«ж—¶жңҹжүҖз ”з©¶зҡ„и—Ҹж—ҸеӨ©ж–ҮеҺҶз®—еұһдәҺдј з»ҹе®Үе®ҷи§ӮпјҢйғҪжҳҜжӢүжҜӣеҗүзҺ°еңЁз ”究йўҶеҹҹзҡ„йҮҚиҰҒз»„жҲҗйғЁеҲҶгҖӮ
жӢүжҜӣеҗүжҳҜйқ’жө·дәәпјҢи—Ҹж—ҸпјҢдёәдәҶжӣҙиҝӣдёҖжӯҘең°дәҶи§ЈиҮӘе·ұж°‘ж—Ҹзҡ„ж–ҮеҢ–пјҢеҘ№иҮӘ2008е№ҙејҖе§Ӣз ”з©¶и—ҸиҜӯпјҢиҖғдёҠеҚҡеЈ«д№ӢеҗҺеҸҲйҖүжӢ©дәҶи—Ҹж—ҸеӨ©ж–ҮеҺҶз®—з ”з©¶ж–№еҗ‘гҖӮеңЁеҪ“ж—¶зҡ„еӯҰз•ҢпјҢе”Ҝй»„жҳҺдҝЎе…Ҳз”ҹеҒҡиҝҮиҜҘж–№еҗ‘зҡ„дё“йўҳжҖ§з ”究пјҢжӯӨеҗҺйҡ”дәҶиҝ‘дәҢеҚҒе№ҙзҡ„ж—¶й—ҙзӣёе…із ”究жҲҗжһң并дёҚеӨҡгҖӮд№ӢжүҖд»ҘеҫҲе°‘жңүдәәж¶үи¶іиҜҘйўҶеҹҹпјҢжҳҜеӣ дёәжӯӨзұ»з ”究еҫҖеҫҖйңҖиҰҒж–ҮзҗҶе…јеӨҮзҡ„з§‘з ”еһӢдәәжүҚпјҢиҖҢзҗҶ科еҮәиә«еҸҲеҜ№и—Ҹж—Ҹдј з»ҹж–ҮеҢ–е……ж»Ўе…ҙи¶Јзҡ„жӢүжҜӣеҗүеҶҘеҶҘд№ӢдёӯжіЁе®ҡдәҶеҘ№йҖүжӢ©зҡ„з ”з©¶ж–№еҗ‘гҖӮ
д»Һдәәзұ»еӯҰзҡ„и§Ҷи§’з ”з©¶еӨ©ж–ҮеҺҶз®—
еҲҡејҖе§Ӣз ”з©¶и—Ҹж—ҸеӨ©ж–ҮеҺҶз®—ж—¶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зҡ„з ”з©¶ж–№жі•жҳҜе…ҲзІҫиҜ»й»„жҳҺдҝЎе…Ҳз”ҹзҡ„и‘—дҪңгҖҠиҘҝи—Ҹзҡ„еӨ©ж–ҮеҺҶз®—гҖӢгҖҠи—ҸеҺҶеҺҹзҗҶдёҺе®һи·өгҖӢпјҢ然еҗҺж·ұе…Ҙз”°йҮҺжӢңеҚЎе°”еҶҲВ·жҙӣжЎ‘йҮ‘е·ҙдёәеёҲзі»з»ҹеӯҰд№ и—ҸеҺҶпјҲж—¶иҪ®еҺҶпјүпјҢеңЁжӯӨеҹәзЎҖдёҠд»Ҙж°‘ж—ҸеӯҰзҡ„еӯҰ科зү№иүІж’°еҶҷеҚҡеЈ«и®әж–ҮгҖӮдҪҶиҝ‘дәӣе№ҙжӢүжҜӣеҗүеңЁеҒҡз ”з©¶ж—¶жҖ»жғізқҖеҰӮдҪ•е°ҶеӨ©ж–ҮеҺҶз®—дёҺдәәзұ»еӯҰзҡ„зҹҘиҜҶиҒ”зі»иө·жқҘгҖӮеӣһеҝҶиө·еңЁе…°е·һжұӮеӯҰзҡ„е…«е№ҙ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е§Ӣз»Ҳи®ӨдёәвҖңиҜ»еҚҡзҡ„з»ҸеҺҶжҳҜдёҖдёӘдёҚж–ӯжҸҗеҚҮзҡ„иҝҮзЁӢпјҢд№ӢеүҚеҜ№з ”究еҚҒеҲҶжҮөжҮӮпјҢдҪҶйҖҡиҝҮеӯҰд№ ж°‘ж—ҸеӯҰдёҺи—Ҹж—ҸеҺҶеҸІпјҢзү№еҲ«жҳҜдәәзұ»еӯҰдҪңе“Ғзҡ„йҳ…иҜ»еҜ№иҮӘе·ұпјҢеҜ№дәәйғҪжңүдәҶжӣҙеҠ ж·ұе…Ҙзҡ„и®ӨиҜҶпјҢе®ғ们дјҡеғҸеҗ‘еҜјдёҖж ·дёҖзӣҙеј•йўҶзқҖжҲ‘еҺ»и®ӨиҜҶиҮӘе·ұе’ҢзӨҫдјҡзҡ„жң¬иҙЁвҖқгҖӮ
дҪңдёәз ”з©¶дәәе‘ҳ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еҺҹжң¬дёҚз”ЁжҺҲиҜҫпјҢдҪҶд»Һ2021ејҖе§ӢеҘ№дё»еҠЁз”іиҜ·еҺ»дёҠж–ҮеӯҰйҷўж°‘ж—ҸеӯҰдё“дёҡзҡ„иҜҫзЁӢпјҢдё»иҰҒи®ІжҺҲвҖңж°‘ж—ҸеӯҰйҖҡи®әвҖқвҖңж°‘ж—ҸеӯҰпјҲдәәзұ»еӯҰпјүеҺҹи‘—йҖүиҜ»вҖқгҖӮд№ӢжүҖд»ҘйҖүжӢ©еҺ»дёҠиҜҫпјҢжҳҜеӣ дёәвҖңиҮӘе·ұдёҖдёӘдәәеҒҡз ”з©¶жңүж—¶дјҡеҫҲй—ӯеЎһпјҢжҖқз»ҙжҜ”иҫғзӢӯзӘ„вҖқпјҢд»Ҙж•ҷдҝғеӯҰзҡ„иҙ№жӣјеӯҰд№ жі•и®©жӢүжҜӣеҗү收иҺ·йўҮдё°гҖӮ
еҺҹжң¬е№¶дёҚж“…й•ҝдәәзұ»еӯҰзҗҶи®әзҡ„жӢүжҜӣеҗүпјҢдёәдәҶж•ҷеӯҰе’Ңз ”з©¶ејҖе§ӢиҮӘеӯҰдәәзұ»еӯҰгҖӮж—©жңҹиҜ»з»“жһ„дё»д№үдәәзұ»еӯҰ家еҲ—з»ҙ-ж–Ҝзү№еҠіж–Ҝзҡ„гҖҠеҝ§йғҒзҡ„зғӯеёҰгҖӢж—¶пјҢеҗёеј•жӢүжҜӣеҗүзҡ„еҸӘжҳҜд№ҰдёӯдёҚж—¶й—ӘзҺ°зҡ„дә®зңјеҸҘеӯҗпјҢеҜ№дәҺдә”еҚҒеӨҡйЎөйғҪеҸӘжҳҜжҸҸеҶҷдә‘еҪ©еҸҳеҢ–зҡ„笔法еҚҙдјҡеҫҲеҝ«еӨұеҺ»иҖҗеҝғгҖӮдҪҶеҪ“еҘ№ејҖе§Ӣд»Һдәәзұ»еӯҰзҡ„и§Ҷи§’еҒҡз ”з©¶ж—¶пјҢеҘ№и®ӨиҜҶеҲ°дәҶд№Ұдёӯжӣҙдёәе®Ҹи§ӮеҸҚжҖқе’ҢжӣҙеҠ з»Ҷи…»зҡ„иЎЁиҫҫпјҢд№ҹз”ұжӯӨжҺўзҙўеҮәдәҶдёҖжқЎеӯҰд№ дәәзұ»еӯҰзҡ„ж–№жі•пјҢвҖңеӯҰд№ дәәзұ»еӯҰзҡ„дҪңе“ҒдёҖе®ҡиҰҒд»ҺеҸ‘家еҸІејҖе§Ӣзі»з»ҹең°йҳ…иҜ»зӣёе…ізҡ„з»Ҹе…ёеҺҹи‘—пјҢиҝҷж ·жүҚиғҪжӣҙеҘҪең°дәҶи§ЈеҗҺжқҘзҡ„з ”з©¶еҸҠжҙҫеҲ«еҮәзҺ°зҡ„еҺҹеӣ пјҢеӨ§йғЁеҲҶдәәзҡ„з ”з©¶е№¶дёҚжҳҜеңЁжҠҠ0еҸҳжҲҗ1пјҢиҖҢжҳҜеңЁ1зҡ„еҹәзЎҖдёҠеҠ 2еҠ 3вҖҰвҖҰвҖқ
вҖңжҠҠи—Ҹж—Ҹзҡ„еӨ©ж–ҮеҺҶз®—дҪңдёәд№Ұжң¬дёҠзҡ„з”°йҮҺвҖқ
дј з»ҹзҡ„еӨ©ж–ҮеҺҶз®—еҫҖеҫҖдјҡиў«и®ӨдёәжҳҜе‘Ёжҳ“гҖҒе…«еҚҰзұ»зҡ„вҖңдјӘ科еӯҰвҖқпјҢдәӢе®һдёҠпјҢвҖңжІЎжңүеҚ жҳҹжңҜд№ҹе°ұжІЎжңүеӨ©ж–ҮеӯҰпјҢж—©жңҹзҡ„еӨ©ж–ҮеӯҰжҳҜж –жҒҜдәҺеҚ жҳҹжңҜд№ӢдёӢзҡ„вҖқгҖӮеҜ№дәҺ科еӯҰ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жңүиҮӘе·ұзҡ„зҗҶи§ЈпјҢвҖңзҺ°д»Јз§‘еӯҰжҳҜдё»е®ўдәҢеҲҶдёӢзҡ„е®һиҜҒ科еӯҰпјҢжҳҜйңҖиҰҒе®ҡйҮҸеҲҶжһҗпјҢе®һйӘҢиҜҒжҳҺж–№иғҪеҫ—еҮәжңүж•Ҳз»“и®әзҡ„科еӯҰпјӣиҖҢдёңж–№зҡ„з»“и®әжҳҜжҖқиҫЁиҺ·еҫ—зҡ„пјҢжҳҜеұһдәҺе®ҡжҖ§еҲҶжһҗзҡ„пјҢжҳҜдё»е®ўиһҚдёәдёҖдҪ“зҡ„еҪ’зәійҖ»иҫ‘вҖқгҖӮ
еңЁдёӯеӣҪпјҢвҖң科еӯҰвҖқзҡ„жҰӮеҝөеұһдәҺиҲ¶жқҘе“ҒпјҢиў«е®ҡд№үдёәе»әз«ӢеңЁеҸҜжЈҖйӘҢзҡ„и§ЈйҮҠе’ҢеҜ№е®ўи§ӮдәӢзү©зҡ„еҪўејҸгҖҒз»„з»ҮзӯүиҝӣиЎҢйў„жөӢзҡ„жңүеәҸзҹҘиҜҶзі»з»ҹпјҢжҳҜе·Ізі»з»ҹеҢ–е’Ңе…¬ејҸеҢ–дәҶзҡ„зҹҘиҜҶгҖӮдҪҶеңЁдёӯеӣҪзҡ„ж–ҮеҢ–дј жүҝдёӯпјҢ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е‘Ёжҳ“гҖҒе…«еҚҰд№Ӣзұ»зҡ„дј з»ҹж–ҮеҢ–е°ұжІЎжңүзҺ°еҰӮд»ҠжүҖ谓科еӯҰзҡ„еӨ©ж–ҮеҺҶз®—гҖӮвҖңз”ұдәҺиҝ‘д»ЈжҲ‘们жӣҫеҸ—еҲ°еқҡиҲ№еҲ©зӮ®зҡ„摧жҜҒпјҢеҜјиҮҙжҲ‘们еҜ№иҮӘе·ұзҡ„ж–ҮеҢ–зјәд№ҸиҮӘдҝЎпјҢдҪҶдј з»ҹж–ҮеҢ–жүҚжҳҜжҲ‘们ж–ҮеҢ–зҡ„ж №гҖӮдёҖеҲҮ科еӯҰйғҪжҳҜд»Һдәәзұ»ејҖе§Ӣи§ӮеҜҹиҮӘиә«еҸҠе®Үе®ҷдјҠе§Ӣзҡ„пјҢжј«й•ҝеІҒжңҲдёӯвҖҳ科еӯҰвҖҷзҡ„е®ҡд№үеҮ еәҰеҸҳжӣҙпјҢеҚідҪҝжҳҜеҪ“дёӢжҲ‘们жүҖеқҡдҝЎзҡ„科еӯҰпјҢеңЁеҗҺзҺ°д»ЈиҜӯеўғдёӢд№ҹеҸҜиғҪиў«жҺЁзҝ»пјҢеӣ жӯӨвҖҳ科еӯҰвҖҷиҝҷдёӘжҰӮеҝөжң¬иә«е°ұйңҖиҰҒдёҚж–ӯиў«еҸҚжҖқгҖӮвҖқ
第дёүдё–з•Ңзҡ„еӣҪ家дёҖзӣҙеӨ„дәҺдёҖз§Қзҹӣзӣҫзҡ„зҠ¶жҖҒпјҢдёҖиҫ№иҰҒдҝқжҢҒдј з»ҹпјҢдёҖиҫ№еҸҲиҰҒд»ҘиҘҝж–№зҡ„规еҲҷдёҺиҘҝж–№ејҖеұ•з«һиөӣгҖӮеӣ жӯӨ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и®ӨдёәвҖңдј з»ҹж–ҮеҢ–зҡ„з ”з©¶ж—ўиҰҒи®©дәәи®ӨиҜҶеҲ°дј з»ҹж–ҮеҢ–зҡ„зІҫй«“пјҢеҸҲиғҪи®©дј з»ҹж–ҮеҢ–дёәжңӘжқҘзҡ„科еӯҰжҸҗдҫӣдёҖз§Қе“ІжҖқе’ҢзҒөж„ҹзҡ„еҸҜиғҪгҖӮвҖқ
иҘҝи—ҸжҳҜдё–з•ҢеӨ©ж–ҮеӯҰж–ҮеҢ–зҡ„дәӨйҖҡжһўзәҪпјҢи—Ҹж—Ҹзҡ„еӨ©ж–ҮеҺҶжі•жҳҜиһҚжұҮдәҶдёңиҘҝеҗ„ж–№еӨ©ж–ҮеӯҰзҹҘиҜҶзҡ„ж–ҮеҢ–з»“жҷ¶гҖӮеңЁжӢүжҜӣеҗүзңӢжқҘпјҢвҖңжҠҠи—Ҹж—Ҹзҡ„еӨ©ж–ҮеҺҶз®—дҪңдёәд№Ұжң¬дёҠзҡ„з”°йҮҺпјҢйҖҡиҝҮи§ӮеҜҹе®ғиғҪзңӢеҲ°еҺҶж—¶жҖ§е’Ңе…ұж—¶жҖ§зҡ„ж–ҮеҢ–дәӨжұҮпјҢд№ҹиғҪи®©жҲ‘们зңӢеҲ°еңЁе…ЁзҗғеҢ–д№ӢеүҚе°ұе·Із»ҸеӯҳеңЁзҡ„е…ЁзҗғжҖ§зҡ„жҖқжғідәӨжөҒпјҢзү№еҲ«жҳҜжұүи—ҸдёӨз§Қж–ҮеҢ–зҡ„дәӨеҫҖдәӨжөҒдёҺдәӨиһҚвҖқгҖӮ
вҖңеұ…家йҡ”зҰ»зҡ„80еӨ©йҮҢжҲ‘зҡ„жғ…з»ӘдёҖзӣҙзү№еҲ«еҘҪвҖқ
жҢҒз»ӯдёүе№ҙзҡ„е…Ёзҗғз–«жғ…еҠ ж·ұдәҶдәә们дёҚе®үдёҺз„Ұиҷ‘зҡ„жғ…з»ӘпјҢдҪҶжӢүжҜӣеҗүдёҖзӣҙеңЁеҫҲеҘҪең°дёҺиҮӘе·ұзӣёеӨ„гҖҒдёҺдё–з•ҢзӣёеӨ„пјҢвҖңеұ…家йҡ”зҰ»зҡ„80еӨ©йҮҢжҲ‘зҡ„жғ…з»ӘдёҖзӣҙзү№еҲ«еҘҪпјҢ并没жңүд»Җд№Ҳжғ…з»ӘжіўеҠЁпјҢиҜҘдёҠиҜҫдёҠиҜҫгҖҒиҜҘеҶҷдёңиҘҝеҶҷдёңиҘҝгҖҒиҜҘзңӢд№ҰзңӢд№ҰпјҢе°ұеҫҲе№ёзҰҸгҖӮеҪ“дёӢзҡ„жҲ‘пјҢеӨ„еңЁдёҖдёӘйқһеёёж»Ўж„Ҹзҡ„зҠ¶жҖҒвҖқгҖӮ
жӣҫз»Ҹзҡ„жӢүжҜӣеҗүд№ҹжӣҫжӢ…еҝғеӣӣеҚҒеІҒзҡ„еҲ°жқҘпјҢе®іжҖ•иҮӘе·ұдјҡеҸҳиҖҒпјҢдҪҶеҪ“еҘ№зңҹжӯЈеҲ°дәҶеӣӣеҚҒеІҒж—¶еҚҙж„ҹи§үеҫҲе№ёзҰҸпјҢвҖңд»ҘеүҚзңӢдёҚжҮӮзҡ„д№ҰзҺ°еңЁиғҪзңӢжҮӮдәҶпјҢд»ҘеүҚиҜ»д№Ұзҡ„йҖҹеәҰеҫҲж…ўпјҢзҺ°еңЁдёҖе№ҙеҸҜд»ҘиҜ»еҚҒеҮ жң¬д№ҰпјҢе°ұдјҡи§үеҫ—еҫҲжңү收иҺ·гҖӮеӣӣеҚҒеІҒеёҰз»ҷжҲ‘зҡ„жҳҜдё°зӣҲпјҢж„ҹи§үеҫҲж»Ўи¶івҖқгҖӮ
жӢүжҜӣеҗүиҮід»Ҡд»Қжё…жҷ°ең°и®°еҫ—иҮӘе·ұеңЁе…°еӨ§ж—¶зҡ„зЎ•еЈ«жҜ•дёҡи®әж–ҮвҖ”вҖ”гҖҠд»ҺGDPеҲ°GNH:дёҚдё№еҸ‘еұ•жЁЎејҸз ”з©¶гҖӢпјҢвҖңеӣҪж°‘е№ёзҰҸжҖ»еҖјвҖқпјҲGross National HappinessпјҢGNHпјүеңЁеҪ“ж—¶иҝҳжҳҜдёҖдёӘжңӘиў«е…¬дј—е……еҲҶзҶҹжӮүзҡ„зӨҫдјҡеҸ‘еұ•жЁЎејҸжҰӮеҝөпјҢе®ғе…іжіЁеӣҪж°‘ж•ҙдҪ“е№ёзҰҸж„ҹпјҢжіЁйҮҚзү©иҙЁе’ҢзІҫзҘһе№іиЎЎеҸ‘еұ•зҡ„зӨҫдјҡз»ҸжөҺеҸ‘еұ•зҗҶеҝөпјҢз”ұдёҚ丹第еӣӣдё–еӣҪзҺӢд№…зҫҺеғ§ж јж—әз§ҖеңЁ1972е№ҙйҰ–е…ҲжҸҗеҮәпјҢ并еңЁд»–йўҶеҜјзҡ„еӣҪ家иҝӣиЎҢе®һи·өгҖӮеҪ“ж—¶зҡ„жӢүжҜӣеҗүи®ӨдёәпјҢжҜ”иө·GDPпјҢGNHеҜ№и—ҸеҢәиҝҷж ·дёҺдёҚдё№жңүзӣёдјјж–ҮеҢ–иғҢжҷҜзҡ„зү№ж®Ҡж°‘ж—Ҹең°еҢәзӨҫдјҡз»ҸжөҺеҸ‘еұ•жңүзқҖйҮҚиҰҒзҡ„еҸӮиҖғд»·еҖјгҖӮеңЁжӢүжҜӣеҗүзңӢжқҘпјҢвҖңеҶҷиҝҷзҜҮи®әж–Үж—¶жҲ‘并дёҚдәҶи§ЈиҘҝи—ҸпјҢеҜ№иҘҝж–№ж–ҮеҢ–д№ҹеҫҲжҮөжҮӮпјҢеҸӘжҳҜж–°еҘҮдәҺдёҚдё№дёҚеҗҢзҡ„зӨҫдјҡеҸ‘еұ•жЁЎејҸпјҢдҪҶзҺ°еңЁзҡ„жҲ‘дёҚеҶҚзә з»“дәҺе№ёзҰҸжҲ–дёҚе№ёзҰҸзҡ„й—®йўҳпјҢGNHзҡ„еҸ‘еұ•жЁЎејҸеҖјеҫ—жҲ‘们еҸҚжҖқпјҢдҪҶд№ҹдёҚжҳҜеңӯиҮ¬пјҢзәөи§ӮиҘҝж–№дёҺдёӯеӣҪзҡ„еҸ‘еұ•еҺҶзЁӢпјҢе°ұдјҡзңӢеҲ°йҰ–е…ҲдёәдәҶз»ҸжөҺзҡ„еҸ‘еұ•еҠҝеҝ…иҰҒд»ҘGDPдёәиҝҪжұӮзӣ®ж ҮпјҢиҖҢеңЁж–°ж—¶д»ЈдёӢзҡ„дёӯеӣҪд№ҹи¶ҠжқҘи¶ҠйҮҚи§ҶвҖҳйқ’еұұз»ҝж°ҙвҖҷдёҺвҖҳдәәж°‘е…ұеҗҢе№ёзҰҸвҖҷвҖқгҖ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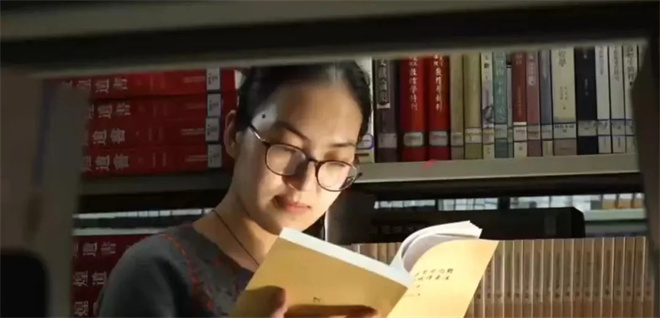
вҖңзҰ»дё–дҝ—иҝңдёҖзӮ№еҸҜиғҪдјҡжӣҙе№ёзҰҸвҖқ
жӢүжҜӣеҗүйӘЁеӯҗйҮҢе°ұжҳҜе–ңж¬ўзҗҶ科пјҢдҪҶеҶ…еҝғеҚҙжң¬иғҪең°дёҚе–ңж¬ўзҺ°д»ЈеҢ–зҡ„и®ёеӨҡдә§е“ҒпјҢеңЁеҘ№зңӢжқҘпјҢи¶…еёӮзҡ„еҫҲеӨҡдёңиҘҝйғҪдёҚеҒҘеә·пјҢжүӢжңәгҖҒе№іжқҝзӯүз”өеӯҗдә§е“ҒдјҡеҜ№дәәдә§з”ҹдјӨе®і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жӢ’з»қз”өеӯҗдә§е“Ғ并дёҚиЎЁзӨәжҠөеҲ¶зҺ°д»ЈеҢ–пјҢеҮ д№ҺдёҚз”ЁжҠ–йҹізҡ„еҘ№пјҢдјҡиҝҗз”ЁBз«ҷеҺ»зі»з»ҹең°еӯҰд№ иҮӘе·ұж„ҹе…ҙи¶Јзҡ„иҜҫзЁӢгҖӮвҖңеӣ дёәжҲ‘们дёҚеҸҜиғҪеӣһеҲ°еҺҹе§ӢзӨҫдјҡеҺ»пјҢжҲ‘们еңЁжј©ж¶ЎйҮҢпјҢеҸӘиғҪиҮӘе·ұе°ҪйҮҸеҺ»е№іиЎЎгҖӮиҝҷдёӘдё–з•ҢжҳҜдёӨйқўзҡ„пјҢжңүеҘҪжңүеқҸпјҢжңүзҺ°д»Јзҡ„дә«еҸ—д№ҹеҝ…е®ҡеҫ—жҺҘеҸ—зӣёеә”зҡ„еүҜдҪңз”ЁвҖқгҖӮ
дҪӣж•ҷи®Өдёә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жңүжҲҗдҪӣзҡ„еҸҜиғҪпјҢеҸӘжҳҜеӣ дёәдёҠйқўзӣ–дәҶеҫҲеӨҡзҡ„зҒ°пјҢиҖҢдәәйңҖиҰҒжҠҠйӮЈдәӣзҒ°ж“ҰжҺүгҖӮеңЁжӢүжҜӣеҗүзңӢжқҘпјҢдәәеңЁж»Ўи¶ідәҶеҹәжң¬зҡ„ж¬Іжңӣд№ӢеҗҺпјҢдјҡеҸ‘зҺ°еӯҰд№ жҳҜиҝҷдё–з•ҢдёҠжңҖеҝ«д№җзҡ„дәӢжғ…пјҢвҖңзңӢеҲ°еҘҪзҡ„дҪңе“ҒгҖҒжҖқжғіпјҢдјҡдә§з”ҹдёҖз§Қе–ңжӮҰпјҢиҖҢиҝҷз§Қе–ңжӮҰжҳҜе…·жңүжҢҒд№…жҖ§е’ҢжҝҖеҠұжҖ§зҡ„пјҢдәәжғіиҰҒж‘Ҷи„ұз—ӣиӢҰзҡ„иҜқпјҢзҰ»дё–дҝ—иҝңдёҖзӮ№еҸҜиғҪдјҡжӣҙе№ёзҰҸвҖқгҖӮ
д»Ҡе№ҙжҳҜжӢүжҜӣеҗүе®ҡеұ…иҘҝи—Ҹзҡ„第八е№ҙпјҢеҲқеҲ°иҘҝи—ҸпјҢж·іжңҙзҡ„ж°‘йЈҺд№ҹжӣҫйў иҰҶеҘ№еҜ№еҹҺеёӮзҡ„и®ӨиҜҶпјҢдҪҶйҡҸзқҖж—¶й—ҙзҡ„жөҒйҖқпјҢеҘ№еҸӘжҳҜд№ жғҜдәҶиҝҷдёӘеҘ№жүҖе–ңж¬ўзҡ„еҹҺеёӮгҖӮеңЁжӢүжҜӣеҗүзңӢжқҘпјҢиҘҝи—Ҹж—ўдҝқжңүиҮӘе·ұзҡ„дј з»ҹеҸҲеҫҲе°‘еҺ»иҪ»и§ҶиҮӘе·ұзҡ„дј з»ҹпјҢеҗҢж—¶иҝҳдёҖзӣҙеңЁжҺҘеҸ—зҺ°д»ЈеҢ–зҡ„еҪұе“ҚгҖӮд№ҹи®ёжӯЈжҳҜеңЁиҝҷж ·дёҖдёӘзҺҜеўғдёӯпјҢжӢүжҜӣеҗүзҡ„з ”з©¶и§ҶйҮҺиҝӣдёҖжӯҘжү©еӨ§пјҢеҘ№дёҖж–№йқўз”Ёдәәзұ»еӯҰзҡ„ж–№жі•е’Ңи§ҶйҮҺеҺ»жҖқиҖғ科еӯҰеҸІзҡ„й—®йўҳпјҢеҸҰдёҖж–№йқўиҝҳиҝӣдёҖжӯҘиЎҘе……з ”з©¶и—Ҹж—ҸеӨ©ж–ҮеҺҶз®—дёҺдёӯиҘҝеӨ©ж–ҮеҺҶз®—д№Ӣй—ҙзҡ„иҒ”зі»гҖӮ
еҜ№дәҺиҘҝи—Ҹ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зҪ‘зәўжү“еҚЎең°пјҢжӢүжҜӣеҗү并дёҚжҺ’ж–ҘпјҢвҖңз”ҹжҙ»е°ұжҳҜе……ж»ЎдәҶз”ҹиҖҒз—…жӯ»пјҢдәәйңҖиҰҒе·ҘдҪңе’Ңдј‘жҒҜзӣёи°ғиҠӮпјҢз”ҹжҙ»йңҖиҰҒеј№жҖ§е’Ңзј“еҶІпјҢзЁіе®ҡзҡ„зӨҫдјҡд№ҹи®ёжҳҜеӨ§е®¶жңҖеҗ‘еҫҖзҡ„пјҢдҪҶжІЎжңүиҝҮжёЎзҡ„еҸҚз»“жһ„зҠ¶жҖҒпјҢз”ҹжҙ»д№ҹжҳҜжІЎжңүеҠһ法继з»ӯзҡ„гҖӮд»»дҪ•дәӢжғ…йғҪжңүе…¶дёӨйқўжҖ§пјҢеҸҚйқўйңҖиҰҒжӯЈйқўиЎ¬жүҳпјҢеҰӮжһңжІЎжңүз—ӣиӢҰе°ұдёҚдјҡзҹҘйҒ“д»Җд№ҲжҳҜе№ёзҰҸгҖӮеҰӮжһңжҲ‘们дёҚжҳҜиә«еӨ„вҖҳжЈ®жһ—вҖҷзңӢдё–з•ҢпјҢиҖҢжҳҜд»ҘвҖҳдёҠеёқвҖҷзҡ„и§Ҷи§’зңӢдё–з•ҢпјҢдјҡеҸ‘зҺ°дё–з•ҢеҪ“дёӢзҡ„зҠ¶жҖҒе’Ңд№ӢеүҚзҡ„зҠ¶жҖҒеҮ д№ҺжҳҜдёҖиҮҙзҡ„пјҢе°ұеғҸж°ҙжөҒдёҖж ·зҡ„зҠ¶жҖҒпјҢжҲ‘们дёҚиғҪиҜҙж°ҙжөҒи¶ҠиҝҮзҹіеӨҙж—¶жҳҜдёҚзЁіе®ҡзҠ¶жҖҒпјҢиҖҢжөҒж·ҢеңЁе№іеқҰзҡ„и·ҜйқўдёҠж—¶жҳҜдёҖдёӘзЁіе®ҡзҡ„зҠ¶жҖҒгҖӮвҖқ
жӢүжҜӣеҗүдҪңдёәдёҖеҗҚеӨ©ж–ҮеҺҶз®—з ”з©¶иҖ…пјҢдёҖйқўд»Ҙд»°жңӣжҳҹз©әзҡ„е§ҝжҖҒеҚҒе№ҙеҰӮдёҖж—Ҙең°жҺўзҙўзқҖи—Ҹж—ҸеӨ©ж–ҮеҺҶз®—зҡ„зңҹи°ӣпјҢдёҖйқўеҸҲд»ҘеӯҰд№ дёҺзҗҶи§Јзҡ„еҝғжҖҒйЎәеә”зқҖж—¶д»Јзҡ„жҙӘжөҒпјҢд№ҹи®ёиҝҷжӯЈжҳҜеҘ№еңЁеҫҲеӨҡеўғеҶөдёӢйғҪж„ҹеҲ°е№ёзҰҸзҡ„еҺҹеӣ пјҢдёҚеҺ»жҢ‘йҖүдәәз”ҹпјҢе‘ҪиҝҗиҮӘжңүеӨ©ж„ҸпјҢдёҖеҚҠд»°жңӣжҳҹз©әпјҢдёҖеҚҠи„ҡиёҸе®һең°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