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吉坚赞(1960—2009)藏族,甘肃夏河人。出版有小说集《小镇轶事》。作品曾获得多种奖项:1982年获甘肃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二等奖,1985年获全国五省区藏族文学评奖优秀作品二等奖,1985年获首届格桑花文艺评奖文学奖,1986年获甘肃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1987年获第二届格桑花文艺评奖文学奖,1989年获甘肃省第三届“敦煌青年文学奖”二等奖,1989年获甘肃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二等奖,2006年获甘南州黄河首曲“格萨尔文艺奖”优秀奖。
甘南本土小说中现代意识的开拓者
——道吉坚赞小说论
安少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甘南小说的创作进入黄金期,出现了若干位重要作家,既为甘南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把甘肃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道吉坚赞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家之一。
道吉坚赞(1960—2009)曾创作发表了许多优秀的诗歌、散文、小说,出版有小说集《小镇轶事》。曾获五省区藏族文学评奖优秀作品二等奖、甘肃省首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二等奖、甘肃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甘肃省第三届“敦煌青年文学奖”二等奖、甘肃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二等奖。其中中篇小说《金顶的象牙塔》《小镇逸事》《漂逝的彼岸》等在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小镇轶事》曾被《小说月报》转载,《金顶的象牙塔》改编后拍成数字电影《拉卜楞人家》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
道吉坚赞的短篇小说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他把所借鉴的西方文学和当代先锋文学资源,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思考相结合,都转化为本土的写作资源。因此,他是用新的手法、新的视角描写甘南的最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尽管他的主要作品都创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但他的小说理念是超前的,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时代的气息,准确地传达了世纪之交那种激情、理想、天真混杂在一起的浪漫而充满活力的时代氛围。他的短篇小说集《小镇轶事》就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文本。
《小镇轶事》是集子中的开篇之作。小说的情节很简单,是三个藏族青年男子在茶馆里的一场聊天,主体是桑吉扎西的爱情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经济转型还没开始,但社会氛围已经相当宽松。故事里的三个男人在草原上长大,又一起读过书、插过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篇小说写了三个成长中的男人(大男孩)之间的情义,有一种粗犷、浪漫的西部氛围,还有一种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特有的,特别是屠格涅夫迪康卡夜话般的诗意氛围。小说在很短的篇幅中涉及到青春、叛逆、勇气、爱、道义、责任等男性的成长话题,作者显然是用一种跨文化的视角来处理这样一个本土题材,使小说有了特别的意义。而且,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是在1984年写于玛曲的,在那样的年代那样一种环境里,能突破题材和思想的藩篱,用先锋手法写出这样一篇小说来,的确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集子中的一部分小说是描写草原的自然与人性之美的,至今读来仍能令人感受到浓郁的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
其中《西部的河,没有波浪》与其说是一篇小说,不如说它是一幅草原风情画,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小说充满浪漫的抒情气息,但几乎没有什么戏剧冲突。小说主要的叙事部分写了辽阔的草原上,黄河上游一个摆渡的船工格尔玛,和一个等待渡河的姑娘在帐篷里度过的两天两夜。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因为情感的克制而充满人性的优美和力量。小说中的一段歌词也提示出这篇小说的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西部的河,没有波浪……”这篇小说写作之际,正是文坛上“西部文学”概念性创作蓬勃兴起的时期,所以作者也有意识地要突出小说中的那种“西部氛围”,无疑,黄河上游的草原,是最具有西部气质的地域。小说把“玛曲”放到“西部”的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中去审视,使得这篇小说有了超越草原、超越地域的意义。这篇小说的氛围,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沈从文的《边城》。那份纯粹,那份悠远,那份诗情画意:“空旷的天地,一条河、一只船、一个皮袍脱至腰际的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组成了这片世界的生命……”可以说这是一篇道吉坚赞式的《边城》。
《不见了田园牧歌》由三个微型小说构成,《卡尔旺》写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吉姆的故事。所谓故事,并无情节,只是几个片段。小说围绕一个十五岁少年攥着十块钱去集市上“找相好”的情节,勾勒了乡村少年天性的淳朴、懵懂,少女的天真、可爱。小说笔触简洁,线条明快,氛围灵动。在几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的自然转换中,少年美好的窘迫,少女纯净的活泼跃然纸上。小说写出了一种未受现代生活“浸染”的源自天性的纯真人性,和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淳朴生活境界。这篇小说的意境同样有沈从文小说的单纯、美好,是一篇上乘之作。《猎人笔记》则像一则优美的童话,一首单纯的诗,它把自然之美,人性之善,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是一首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的诗篇。《不见了田园牧歌》则通过一个有着优美歌喉的少女从牧区到城市的经历,表达了对城市生活中堕落的一面的批判。
而小说集中最有分量的是几篇描写现实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既有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精微书写,又有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因此无论从时代主题、叙事技巧、美学风格哪个方面来看,都达到了同时代小说的上乘水平。
《隆钦镇的晴晴雨雨》这部中篇小说在道吉坚赞的小说里具有特殊的意义,主要在于题材上的转变。道吉坚赞以往的小说偏爱具有传奇色彩的题材,或有意突出草原风情,以及不同寻常的人和事,或者生活中审美意味强烈、诗意浓郁的一面。而在这部小说中,他转向了现实题材,而且流露出少见的冷峻和批判意味。
在这样一部篇幅介于短篇和中篇之间的小说里,他以开阔的视角,几乎是全景式地反映了一个民族地区的小城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生活波澜。纵向来看,这部写于1992年的小说,对于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有一种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言性。
其后的中篇小说《金顶的象牙塔》,既是道吉坚赞小说的代表作,也是当代甘南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金顶的象牙塔》这部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甘南小镇的一个日常生活剖面,呈现了一组五色杂陈的世相百态。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只有若干生活片段,只有一个个生活场景。因此,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当代生活的民俗画卷。
小说写了镇上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的几个小人物的故事:故事的叙述者“我”是小镇上的一名公务员,也是小镇生活的观察者。“我”又是一个串联故事情节的枢纽人物,通过“我”的活动,把画家贡布、生意人红果儿、巴廓尔草原上的牧人桑尕等几个不同职业、不同角色的主要人物的故事都串联起来了。小说侧重表现的是小镇上人的变化,大杂院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时代和社会的一个缩影。
作者给叙事者安排了一个适当的角色:“我”是大杂院里的住户,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小镇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作者让“我”保持了一个与小镇人平行的视角。事实上,这个限制视角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保有理解、宽容、同情的内部视角。虽然这个“我”经常处在惊讶、困惑、失望之中,却能够以发展的心态看问题,对一切变化都持宽容、乐观的态度。他对小镇的态度,是既陌生又亲切,既恨又爱,既蔑视又迷恋。
联系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年代(1991年),可以说它是作家近距离(或置身其中)观察,体验时代的产物。八十年代,社会正处在转型的起步阶段,但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之快、之迅猛,却是令人措手不及的,草原上的这个小镇正是如此。用作者的一个比喻来说“尽管我的小城还那么粗俗,但她毕竟抹了那么一笔淡淡的轻妆,虽不华贵,也迈进了现代。”
作者在叙事中有意识地克制了同时代作家面对现代化这个主题时常见的焦虑心态和忧患意识,尽可能保留了一份乐观和从容。这份自信一方面来自于遥远的巴廓尔草原。作者对巴廓尔草原做了富有诗意的描写,那里宁静、辽阔、闲适、自由,人们率性而活,敢爱敢恨,体验着生命本真的快乐。草原上的牧人桑尕是自由不羁的、充满生命强大的本能活力的、无视俗世的虚伪道德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带有理想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小说中最有魅力的人物之一。小说中对巴廓尔草原与小城生活的描写是平行交替穿插的,喧闹的小城与宁静的巴廓尔草原处处形成了对照。这是草原与城市的对比,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也是淳朴人性与物质欲望的对比。当然,巴廓尔草原不过是一个诗化意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作者真正秉持的,则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是源自民族深厚博大文化的一种自信力。
这份文化自信在书写中表现为一种叙事语言的张力和活力,作家的叙事才华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汪洋恣肆的展现。场景的鲜活生动,人物的多姿多彩,对话的妙趣横生,动作的轻灵到位,叙事时空的转换自如,使整篇小说犹如一部热闹精彩,全景立体呈现的电影。道吉坚赞这种调控所有叙事元素的本领在当时的本土作家中是罕见的。更主要的,是从他的小说语言中洋溢出来的那份幽默、机智、圆润,犹如醇厚浓香的酥油奶茶,散发着魔力。这种魔力究竟来自何方?我们在小说的末尾,在作者情不自禁的流露的一番话中窥见了部分的秘密:“我曾经看过一本歌谣集,节奏明快,妙趣横生,纯正而富于人道气息,正像我们居住的大院。……我们不正生活在这许多首妙趣横生的歌谣中吗?唱你的歌谣吧!”
在1991年,道吉坚赞就写出了《金顶的象牙塔》这样的小说,实在令人惊讶。惊讶于这篇小说之先锋,因为“先锋”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令人仰羡却遥不可及的词。但是这部小说从手法到观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把“先锋”娴熟地琢磨透了,把几乎所有的“先锋”元素都当一盘什锦菜一锅烩了。至少在今天来看,这部小说在不少方面依然是令人望尘莫及的。
不仅是在《金顶的象牙塔》中,还包括在其它许多小说中,道吉坚赞写出了这方土地上人们乐观、幽默的一面。他们随遇而安,心地单纯,好奇心强,喜欢捉弄别人,开别人的玩笑,也常常成为别人捉弄的对象。他们的乐观天性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调和剂,使平淡的生活也有了亮色和暖色。这也许来自他们独特的生命观和生活观,和万物浑然一体的世界观,这使他的小说在审视现实时,在批判的锋芒后面又带着一种宽容、悲悯的意味。这无疑是博大的文化包容力在道吉坚赞小说中的体现。
作为一个本土作家,道吉坚赞能常常跳出本土视角打量一切。因此他的视角,有时是内部透视的,有时是外来者的审视的,有时是现代的,有时是古老的,有时是文化的,有时是批判的。这样宽广的视角就使他获得了充分的叙事自由度、广阔的话语空间,和驾驭题材时游刃有余的从容。也使他的小说层次厚重,意味深长。
以上这些方面,都是道吉坚赞作为一个优秀的本土作家打通内外部视角,来观察、书写民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他留给后来者的一种宝贵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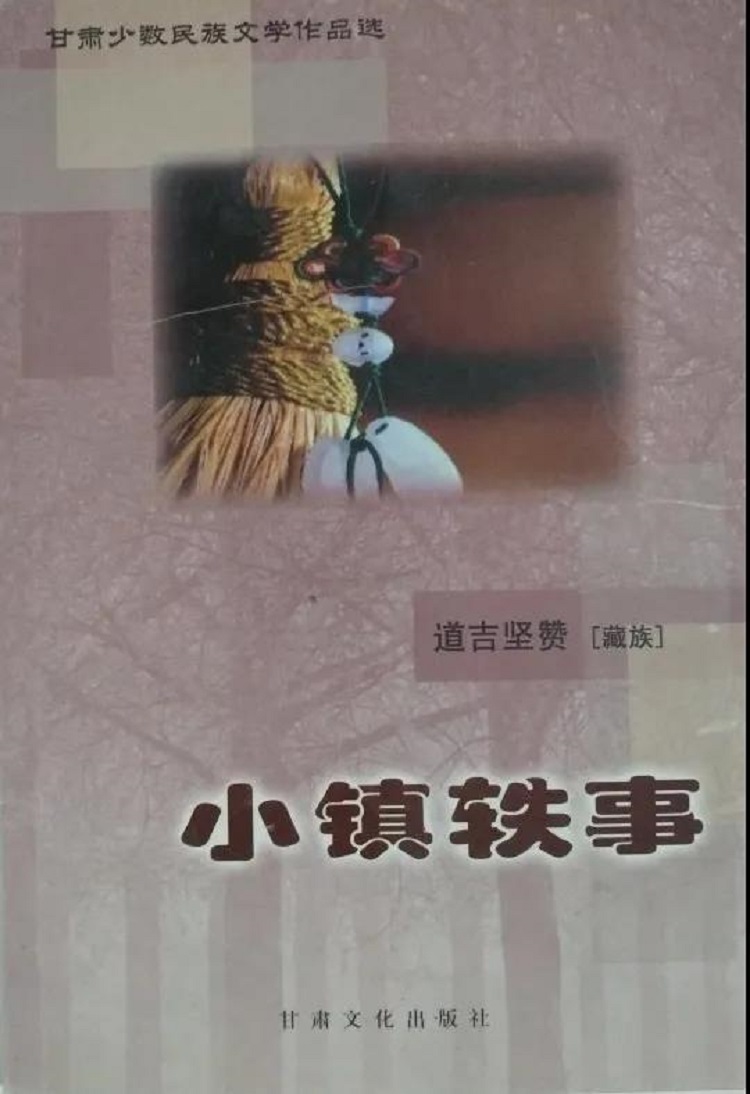
佳作选读
小镇轶事(节选)
道吉坚赞
他们三人选择了角落的一张小桌坐了下来,一反从前那种大大咧咧的神气,都显得非常拘谨和客气,互相推让着不肯落入上座。
“嗨,真是的,怎么都成了这样?”桑吉扎西一步跨了进去,坐在上首:“用不着再推辞了。”那两位也坐了下来,三人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的感觉,禁不住地同时笑了起来。
他们还清楚地记得以前分手时的情景,那是在插队时接到回城通知的时候,尽管通知上明确写着不负责分配工作,但那种似乎是解脱了的想法仍旧使人无比兴奋,几个不到二十岁的人在最后一个晚上把全部的积蓄统统换成了酒肉,在一间肮脏黑暗的房间里拼命地灌了一整夜廉价的劣等酒。第二天一早,昏昏沉沉,相互间连一声再见都没道,就匆匆各自奔去,心里也没有一点遗憾,再见有什么用呢》那种样子不如不见的好。
今天终于“再见”了,可又该谈点什么呢?酒仍旧在喝,可是已换成了价钱昂贵的名酒,于是,便以喝酒为遮掩,谁也不愿提及当年那段充满了痛苦和丑恶的生活,他们几乎都差点成了罪人。
“结过婚了吗?”性急的桑吉扎西终于向华桑道吉发问了。
真奇怪,什么是“结过婚了吗?”难道结过了还能再结吗?华桑道吉默默地把刚点完烟的那根火柴梗放在桌上,两伙伴同时叹了一口气。
汪洛一仰头灌进一杯酒,接着又把酒杯斟满,放在华桑道吉面前:“讲讲吧,讲讲你曾遇到了怎样的姑娘,为她们伤过心吗?”
华桑道吉觉得这情景熟悉得叫人伤心,在知青点上,他常编一些离奇的故事给两个朋友听,虽然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在听一个人胡扯,可总是十分认真地随着故事的情节而紧张、轻松、伤感、高兴,那时候,汪洛也常把酒杯斟满放在他面前,催他讲故事。
他轻轻摇了摇头,把酒杯端起递给桑吉扎西。
“以前总是我一个人说,今天咱们听听扎西的吧?”
桑吉扎西习惯地咬了咬嘴唇,抖了抖宽阔的肩膀。汪洛在一旁怀疑地望着他,自打他们相识以来,桑吉扎西从未给别人讲过故事,他担心这个老实的朋友会不会讲。
“好,那我就讲。”桑吉扎西喝下了那杯酒。
“请你们相信,今天我要讲的都是真事,华桑不妨记下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篇值得写出来的故事,但对你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他慢慢地喝了一口茶,考虑该从那儿讲起。
“我没你俩这样幸运的经历,华桑大学毕业,如今已跨入青年作家的行列,而汪洛也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是从一条小路上走过来的,当然并不是完全不顺利,我想讲一件其中的小事,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可它却决定了当时我的生活,直到今天还在决定着我的归宿。
灌完那场酒后,我就回到家里,不久就碰上地质队在我们那儿招工,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那个工作,可是我知道自己肚子里的墨水仅够勉强写一封安慰母亲的家信,因此就去了,我这身体当地质队的钻井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一见我,连问都没仔细问就点头让我钻进被录取的行列。
我随着这个井队东奔西跑,两年之后终于在尕森克勃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接受了长期打井的任务,那时候我已是个熟练的工人了。”
“你们知道,尕森克勃草原上的姑娘是迷人的,而我自己也不安稳,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和镇子上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认识了,镇子里像她那样富有的家庭只有那么几户,那时人们都还在为一点可怜的口粮在拼命干活。
我于是就像一条狗似的经常在晚上往她家里跑,这一切当然得瞒着她的父母亲,我的那点可怜的工资几乎全花到她身上了,那些苛刻的条件往往使我负债累累,但我爱她,也就没觉得有什么损失。”
……
(原载《西藏文学》1985年第4期,《小说月刊》1985年第10期转载。)
原刊于《甘南日报》2021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