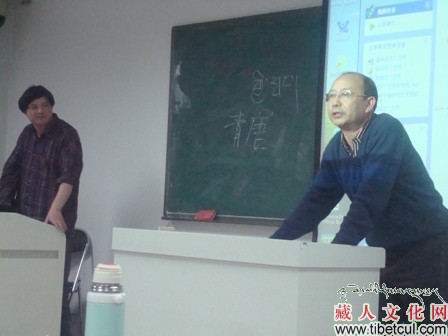гҖҖгҖҖдёӯеӣҪдәәж°‘еӨ§еӯҰеӣҪеӯҰйҷўиҘҝеҹҹеҺҶеҸІиҜӯиЁҖз ”з©¶жүҖжүҖй•ҝгҖҒи—ҸеӯҰ家жІҲеҚ«иҚЈж•ҷжҺҲ,ж—ҘеүҚеӣһеҲ°е®¶д№Ўж— й”Ў,еңЁеҶҜе…¶еәёеӯҰжңҜйҰҶдёҫеҠһдәҶ“еӣҪеӯҰдёҺиҘҝеҹҹз ”з©¶”з ”и®Ёдјҡзӯүзі»еҲ—еӯҰжңҜж–ҮеҢ–жҙ»еҠЁгҖӮ
гҖҖгҖҖ1962е№ҙеҮәз”ҹзҡ„жІҲеҚ«иҚЈз»ҷдәәзҡ„ж„ҹи§үиҮіе°‘жҜ”е®һйҷ…е№ҙйҫ„е°ҸеҚҒеІҒпјҢеңЁжҙ»еҠЁзҺ°еңә,д»–зІҫеҠӣе……жІӣгҖҒзғӯжғ…жҙӢжәўгҖҒеҫ…дәәйҡҸе’ҢпјҢеҲ·ж–°дәҶеӨ§е®¶еҜ№еӯҰжңҜеңҲдәәеЈ«еҪўжҲҗзҡ„еӮІж…ўжҲ–иҖ…дёҚе–„иЁҖиҫһзҡ„з§Қз§ҚеҚ°иұЎгҖӮ
гҖҖгҖҖжІҲеҚ«иҚЈиҜҙпјҢдёҚзҹҘйҒ“д»ҺдҪ•ж—¶ејҖе§ӢпјҢж— и®әеңЁдёӯеӣҪиҝҳжҳҜеӣҪйҷ…дёҠпјҢи°Ҳи®әи—ҸеӯҰдјјд№ҺжҲҗдәҶдёҖз§ҚжҪ®жөҒгҖӮдёҚз®ЎжҳҜе®—ж•ҷзҡ„иҝҳжҳҜж–ҮеҢ–зҡ„“и—ҸеӯҰзғӯ”пјҢе®ғ们йғҪеҜ№зӣ®еүҚдё–з•ҢиҢғеӣҙеҶ…зҡ„иҘҝи—Ҹз ”з©¶жңүзқҖз§ҜжһҒзҡ„жҺЁеҠЁдҪңз”ЁгҖӮ
гҖҖгҖҖжңүж„ҹдәҺдёңиҘҝж–№еңЁи®ӨиҜҶиҘҝи—Ҹж–№йқўдёҠеӯҳеңЁдёҚе°Ҹзҡ„иҜҜеҢәпјҢиҝ‘е№ҙжқҘжІҲеҚ«иҚЈиҮҙеҠӣдәҺйҖҡиҝҮи®Іе ӮгҖҒжҠҘзәёжқӮеҝ—зӯүеҗ„з§Қе…¬е…ұиҲҶи®әе№іеҸ°пјҢе°Ҷд»–жүҖдәҶи§Јзҡ„иҘҝи—Ҹе‘ҠзҹҘдәҺдј—гҖӮ
гҖҖгҖҖиө°еҮәдёӯеӣҪзңӢи—ҸеӯҰ
гҖҖгҖҖжІҲеҚ«иҚЈеҮәз”ҹдәҺж— й”Ўз”ҳйңІй•ҮгҖӮеӣһжңӣиҝҮеҺ»пјҢд»–и§үеҫ—дҪңдёәеҶң家еӯҗејҹпјҢеӨ§еӯҰе®һеңЁжҳҜдёҖе®ҡиҰҒдёҠзҡ„пјҢиҖҢдё”жңүиғҪеҠӣзҡ„иҜқдёҖе®ҡиҰҒдёҠдёҖжүҖеҘҪеӨ§еӯҰгҖӮ“иҰҒжҳҜжҲ‘жІЎжңүиҖғдёҠеҚ—дә¬еӨ§еӯҰпјҢеӨ§жҰӮжҲ‘зҡ„д»ҠеӨ©дёҖе®ҡжҳҜе®Ңе…ЁеҸҰеӨ–дёҖдёӘж ·еӯҗпјҢиҮӘеӯҰжҲҗжүҚеңЁжҲ‘иә«дёҠ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еҸ‘з”ҹзҡ„гҖӮ”
гҖҖгҖҖи°ҲеҲ°и—ҸеӯҰз ”з©¶ж–№еҗ‘пјҢжІҲеҚ«иҚЈеқҰиЁҖеҸҜиғҪжҳҜдёҖз§ҚзјҳеҲҶпјҢеӣ дёәеңЁеӯҰжңҜж–№йқўе№¶жІЎжңүзү№еҲ«зҡ„规еҲ’гҖӮиҜ»еҚ—дә¬еӨ§еӯҰеҺҶеҸІзі»дёҺдёӘдәәзҡ„зҲұеҘҪж— е…іпјҢеҸӘжҳҜеҪ“ж—¶д»–й«ҳиҖғж—¶еҗ„科иҖғеҲҶдёӯеҺҶеҸІжңҖй«ҳгҖӮеңЁеӨ§еӯҰжңҹй—ҙжҲҗз»©е№ҙе№ҙдјҳз§ҖпјҢдҪҶд№ҹ并没жңүзңҹжӯЈеҹ№е…»еҮәеҜ№е“ӘдёҖдёӘдё“й—ЁеҸІзҡ„зү№ж®Ҡе…ҙи¶ЈгҖӮ“жңҖеҗҺжҲ‘еҶіе®ҡжҠҘиҖғжң¬ж Ўзҡ„и’ҷе…ғеҸІдё“дёҡпјҢе…¶еҺҹеӣ жҳҜеӣ дёәеҚ—еӨ§зҡ„и’ҷе…ғеҸІдё“дёҡе…ЁеӣҪдёҖжөҒгҖҒдё–з•ҢжңүеҗҚгҖӮ”жІҲеҚ«иҚЈиҜҙпјҢеҪ“ж—¶д»–зү№еҲ«д»°ж…•еҚ—еӨ§еҺҶеҸІзі»жңҖжқғеЁҒзҡ„еӯҰиҖ…йҹ©е„’жһ—е…Ҳз”ҹпјҢжңҖз»Ҳд»–жҲҗдәҶйҹ©е„’жһ—зҡ„й«ҳи¶ійҷҲеҫ—иҠқе…Ҳз”ҹзҡ„ејҹеӯҗпјҢеңЁд»–зҡ„жҢҮеҜјдёӢжІҲеҚ«иҚЈеңЁеүҚеҗҺеҚ—еӨ§е…ғеҸІе®ӨеӯҰд№ гҖҒе·ҘдҪңдәҶиҝ‘7е№ҙж—¶й—ҙгҖӮ
гҖҖгҖҖжңҹй—ҙпјҢйҷҲеҫ—иҠқжҺЁиҚҗжІҲеҚ«иҚЈеҲ°дёӯеӨ®ж°‘ж—ҸеӯҰйҷўйҡҸзҺӢе°§е…Ҳз”ҹеӯҰд№ и—Ҹж–ҮгҖӮеҜ№жІҲеҚ«иҚЈжқҘиҜҙпјҢзҺӢе°§е…Ҳз”ҹд№ҹжҳҜдҪҚйҡҫеҫ—зҡ„еҘҪиҖҒеёҲпјҢдёҖе№ҙй—ҙд»–дёҚд»…еӯҰеҲ°еҹәжң¬зҡ„иҘҝи—ҸиҜӯж–ҮзҹҘиҜҶпјҢжӣҙйҮҚиҰҒзҡ„жҳҜд»–еҸ‘зҺ°иҘҝи—ҸеӯҰзҠ№еҰӮдёҖзүҮе№ҝйҳ”зҡ„еңҹең°пјҢеҚҙе°‘жңүдәәеҺ»ејҖеһҰпјҢжңүеҫ…еЎ«иЎҘзҡ„з©әзҷҪеӨӘеӨҡгҖӮдёҚзҹҘдёҚи§үй—ҙд»–зЎ®з«ӢдәҶиҮӘе·ұж–°зҡ„з ”з©¶ж–№еҗ‘пјҢд»Һи’ҷе…ғеӯҰиҪ¬еҗ‘иҘҝи—ҸеӯҰгҖӮ
гҖҖгҖҖ1989е№ҙпјҢжҢүз…§иҮӘе·ұзҡ„еӯҰд№ и§„еҲ’пјҢжІҲеҚ«иҚЈеҰӮж„ҝжқҘеҲ°еҫ·еӣҪжіўжҒ©еӨ§еӯҰж”»иҜ»дёӯдәҡиҜӯиЁҖж–ҮеҢ–еӯҰеҚҡеЈ«еӯҰдҪҚгҖӮз”ұдәҺеңЁеӣҪеҶ…и·ҹйҡҸйҷҲеҫ—иҠқе’ҢзҺӢе°§дёӨдҪҚиҖҒеёҲжү“дёӢдәҶжүҺе®һзҡ„дё“дёҡеҹәзЎҖ,жүҖд»ҘеҲ°дәҶеӣҪеӨ–пјҢ他并没жңүи§үеҫ—иҮӘе·ұеңЁеӣҪеҶ…жүҖеӯҰе’Ңеҫ·еӣҪзҡ„и’ҷгҖҒи—ҸеӯҰжңҜжңүеӨҡеӨ§зҡ„йҡ”йҳӮгҖӮдҪҶжҳҜз•ҷеӯҰеҫ·еӣҪ并没жңүжІҲеҚ«иҚЈжғіиұЎзҡ„йӮЈд№ҲйЎәеҲ©пјҢдёҖдёӘдәәзҪ®иә«дәҺиҜӯиЁҖгҖҒж–ҮеҢ–иғҢжҷҜиҝҘејӮзҡ„йҷҢз”ҹеӣҪеәҰпјҢд»–еңЁз”ҹжҙ»дёӯдёҺеӣҪеӨ–дәәзӣёеӨ„дёҠж—¶еёёж„ҹи§үдёҚйҖӮеә”пјҢ“йӮЈдёӘж—¶еҖҷеӣҪйҷ…й—ҙзҡ„дәӨжөҒжІЎжңүд»ҠеӨ©иҝҷд№ҲејҖж”ҫе’ҢеҢ…е®№пјҢе…ҚдёҚдәҶеҸ—еҲ°еҲ«дәәжӯ§и§Ҷзӯүзӯү”пјҢзӣҙеҲ°еҚҡеЈ«и®әж–Үе®ҢжҲҗд№ӢеҗҺпјҢд»–жүҚж„ҹи§үеҲ°иҮӘе·ұеңЁеҫ·еӣҪз«ҷдҪҸдәҶи„ҡгҖӮйӮЈж—¶д»–еңЁи—ҸиҜӯж–ҮзҹҘиҜҶгҖҒиғҪеҠӣж–№йқўеҫ—еҲ°еӨ§е№…еәҰжҸҗй«ҳпјҢеӯҰжңҜз ”з©¶д№ҹйҖҗжӯҘдёҺеӣҪйҷ…жҺҘиҪЁпјҢи§ӮеҜҹй—®йўҳжңүдәҶеӣҪйҷ…и§ҶйҮҺгҖӮ
гҖҖгҖҖдәҶи§ЈеҲ°еӣҪйҷ…еӯҰжңҜз ”з©¶зҡ„ж•ҙдҪ“жғ…еҶөд№ӢеҗҺпјҢжІҲеҚ«иҚЈеҜ№иҮӘе·ұзҡ„еӯҰжңҜд№Ӣи·ҜжӣҙеҠ еқҡе®ҡгҖӮд»–жё…йҶ’ең°и®ӨиҜҶеҲ°пјҢи—ҸеӯҰдёҚжҳҜдёҖй—ЁеӣҪйҷ…жҳҫеӯҰпјҢиҘҝж–№дәәжңү他们иҮӘе·ұзҡ„“еӣҪеӯҰ”,“дёңж–№еӯҰ”жң¬иә«е°ұжҳҜдҪңдёәиҘҝеӯҰзҡ„“д»–иҖ…”иҖҢеӯҳеңЁзҡ„,иҜҙеҲ°еә•е®ғдёҚиҝҮжҳҜиҘҝеӯҰзҡ„дёҖдёӘз»„жҲҗйғЁеҲҶгҖӮд»ҠеӨ©зҡ„и—ҸеӯҰжҜ”дј з»ҹзҡ„еҚ°еәҰеӯҰгҖҒи’ҷеҸӨеӯҰгҖҒзӘҒеҺҘеӯҰгҖҒж»ЎеӯҰзӯүзғӯеҫ—еӨҡ,дҪҶиҝҷдәӣеӯҰ科йғҪиғҪдёҖи„үзӣёжүҝпјҢз»өз»өдёҚз»қгҖӮ“еӯҰжңҜеҪ“жңүиҮӘе·ұзҡ„дј з»ҹ,дёҚеә”еҸ—еӨ–еңЁжқЎд»¶еҲ¶зәҰиҖҢеҝҪеҶ·еҝҪзғӯгҖӮ”
гҖҖгҖҖиҘҝи—Ҹзҡ„иҷҡе№»дёҺзҺ°е®һ
гҖҖгҖҖеңЁеҫ·еӣҪеҸ–еҫ—еҚҡеЈ«еӯҰдҪҚд№ӢеҗҺпјҢжІҲеҚ«иҚЈжқҘеҲ°зҫҺеӣҪгҖӮз”ұдәҺзҫҺеӣҪе’Ң欧жҙІзҡ„еӯҰжңҜдј з»ҹжңүжүҖдёҚеҗҢпјҢеғҸжІҲеҚ«иҚЈиҝҷж ·еҶ·й—Ёдё“дёҡзҡ„еҚҡеЈ«з”ҹеҸӘиғҪеҺ»дёҖдәӣе°Ҹзҡ„еӯҰйҷўжӢ…д»»зұ»дјјдәҡжҙІеҸІиҝҷж ·еҹәзЎҖиҜҫзЁӢзҡ„иҖҒеёҲпјҢдёҖиҠӮиҜҫйҖҡеёёжңүеҘҪеҮ зҷҫеҗҚеӯҰз”ҹгҖӮиҝҷе’ҢжІҲеҚ«иҚЈй’ҹжғ…дәҺи—ҸеӯҰдё“дёҡз ”з©¶зҡ„еҲқиЎ·жҳҫ然жҳҜзӣёжӮ–зҡ„пјҢйҡҸеҗҺеңЁж”¶еҲ°еүҚеҫҖеҫ·еӣҪжҙӘе ЎеӨ§еӯҰдёӯдәҡзі»жӢ…д»»д»ЈзҗҶж•ҷжҺҲзҡ„йӮҖиҜ·еҗҺпјҢжІҲеҚ«иҚЈжҜ…然еӣһеҲ°еҫ·еӣҪпјҢй’»иҝӣиҮӘе·ұзҡ„дё“дёҡйҮҢеҺ»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2005е№ҙд№ӢеүҚпјҢжІҲеҚ«иҚЈиҫ—иҪ¬еңЁеҫ·еӣҪдёҺж—Ҙжң¬зҡ„еӨҡжүҖй«ҳж Ўд»ҺдәӢз ”з©¶е·ҘдҪңгҖӮ2005е№ҙеә•пјҢ他收еҲ°еҶҜе…¶еәёе…Ҳз”ҹзҡ„йӮҖиҜ·пјҢеҠ зӣҹж–°жҲҗз«Ӣзҡ„дәәеӨ§еӣҪеӯҰйҷўпјҢзӯ№е»әиҘҝеҹҹжүҖгҖӮеҶҜе…¶еәёе‘ҠиҜүд»–пјҢеӣҪеӯҰдёҚжҳҜзӢӯйҡҳзҡ„жұүеӯҰпјҢиҖҢжҳҜеҢ…жӢ¬дёӯеӣҪжүҖжңүж°‘ж—Ҹж–ҮеҢ–дј з»ҹзҡ„еӨ§еӣҪеӯҰгҖӮиҘҝеҹҹж–ҮеҢ–иҚҹйӣҶдёӯиҘҝж–ҮжҳҺд№ӢзІҫеҚҺпјҢжҳҜдёӯеҚҺж–ҮеҢ–дј з»ҹзҡ„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жҲҗйғЁеҲҶгҖӮйҮҚе…ҙеӣҪеӯҰпјҢеҪ“然д№ҹеә”иҜҘйҮҚи§ҶеҜ№иҘҝеҹҹж–ҮеҢ–зҡ„з ”з©¶гҖӮжҢүз…§еҶҜе…¶еәёзҡ„жңҹзӣјпјҢдёӯеӣҪеӯҰиҖ…еә”иҜҘеңЁиҘҝеҹҹз ”з©¶йўҶеҹҹеҸ–еҫ—жқғеЁҒзҡ„и§ЈйҮҠжқғпјҢи®©дё–з•ҢиғҪеӨҹеҖҫеҗ¬дёӯеӣҪеӯҰиҖ…зҡ„еЈ°йҹігҖӮжІҲеҚ«иҚЈж„ҹеҸ—еҲ°еҶҜе…¶еәёиҝҷдҪҚж— й”ЎиҖҒд№ЎгҖҒеүҚиҫҲеӯҰжңҜеӨ§е®¶зҡ„иҝңи§ҒеҚ“иҜҶпјҢйҒӮдёӢе®ҡеҶіеҝғпјҢз»“жқҹй•ҝиҫҫ16е№ҙзҡ„жө·еӨ–жјӮжіҠпјҢеӣһеҲ°еӣҪеҶ…пјҢеңЁеӯҰжңҜд№Ӣи·ҜдёҠйҮҚж–°еҮәеҸ‘гҖӮ
гҖҖгҖҖеӣһеҲ°еӣҪеҶ…д№ӢеҗҺпјҢжңүзқҖеӣҪйҷ…еӯҰжңҜиғҢжҷҜзҡ„жІҲеҚ«иҚЈпјҢеҜ№иҘҝи—ҸеӯҰжңүзқҖзӢ¬еҲ°зҡ„и§Ғи§ЈпјҢжңүж„ҹдәҺдёңиҘҝж–№дәәеҜ№иҘҝи—Ҹи®ӨиҜҶдёҠеӯҳеңЁзҡ„е·ЁеӨ§иҜҜи§ЈпјҢеӨҡе№ҙжқҘпјҢд»–еңЁеӯҰжңҜз ”з©¶дёҺж•ҷеӯҰд№ӢдҪҷжӢҝиө·жүӢдёӯзҡ„笔е°ҶиҮӘе·ұеҜ№иҘҝи—Ҹзҡ„дёҖз•Әи§Ғи§ЈйҖҡиҝҮдёҖзҜҮзҜҮж–Үз« йҳҗеҸ‘дәҶеҮәжқҘгҖӮ
гҖҖгҖҖ“жҲ‘们еҸЈдёӯзҡ„иҘҝи—ҸжҳҜзҺ°е®һдёӯзҡ„иҘҝи—ҸпјҢиҖҢиҘҝж–№дәәеҸЈдёӯзҡ„иҘҝи—Ҹе®һйҷ…дёҠжҳҜдёҖз§Қж–ҮеҢ–з¬ҰеҸ·пјҢжҳҜдёҖз§ҚиҷҡжӢҹеҮәжқҘзҡ„д№ҢжүҳйӮҰпјҢжң¬иҙЁдёҠжҳҜдёҖз§ҚжғіиұЎгҖӮ”жІҲеҚ«иҚЈиҜҙгҖӮ1933е№ҙпјҢдёҖдҪҚеҗҚеҸ«JamesHiltonзҡ„дәәеҸ‘иЎЁдәҶдёҖйғЁйўҳдёәгҖҠеӨұиҗҪзҡ„ең°е№ізәҝгҖӢзҡ„е°ҸиҜҙпјҢдёҖи·Ҝз•…й”ҖиҮід»ҠпјҢиў«еҗҺдәәз§°дёәйҒҒдё–дё»д№үе°ҸиҜҙд№ӢжҜҚгҖӮиҝҷйғЁе°ҸиҜҙе°ҶйҰҷж јйҮҢжӢүеҚіиҘҝи—Ҹиҷҡжһ„дёәдёҖдёӘдё–еӨ–жЎғжәҗгҖӮз»ҸиҝҮдёӨж¬Ўдё–з•ҢеӨ§жҲҳд№ӢеҗҺпјҢеҜ№зү©иҙЁз№ҒиҚЈдә§з”ҹжҖҖз–‘е’ҢйҘұеҸ—жҲҳдәү摧ж®Ӣзҡ„иҘҝж–№дәәи¶ҠжқҘи¶ҠйҮҚи§ҶеңЁзІҫзҘһеұӮйқўзҡ„иҝҪжұӮгҖӮз»ҸиҝҮдёҚж–ӯйҳҗеҸ‘пјҢеҫҲеӨҡиҘҝж–№дәәе°ҶйҰҷж јйҮҢжӢүжғіиұЎжҲҗдёҖеқ—е®ҒйқҷзҫҺеҘҪзҡ„дјҠз”ёеӣӯпјҢеңЁиҝҷйҮҢеҝғзҒөеҸҜд»Ҙеҫ—еҲ°зҡ„жҠҡж…°гҖӮ
гҖҖгҖҖ“йҰҷж јйҮҢжӢүжҳҜдәҢеҚҒдё–зәӘ欧жҙІдәәеҜ№дәҺдёңж–№е’Ңдёңж–№дј з»ҹж–ҮеҢ–зҡ„е№»жғіпјҢжҳҜиҘҝж–№дәәеҲӣйҖ зҡ„дёҖдёӘзІҫзҘһ家еӣӯгҖӮ”жІҲеҚ«иҚЈиҜҙпјҢиҘҝж–№йҖҡеёёеҸӘжҳҜе°Ҷдёңж–№еҪ“дҪңдёҖеј еұҸ幕пјҢеҖҹжӯӨ他们еҸҜд»Ҙи®ҫ计他们еҜ№иҘҝж–№иҮӘиә«зҡ„зҗҶи§ЈгҖӮдёҚз®ЎжҳҜиғңеҲ©ең°еҸ‘зҺ°иҘҝж–№иҝңиҝңдјҳи¶ҠдәҺдёңж–№иҖҢеҰ–йӯ”еҢ–иҘҝи—ҸпјҢиҝҳжҳҜдёҚж— дјӨж„ҹең°жүҝи®Өдёңж–№дҫқ然жӢҘжңүиҘҝж–№ж—©е·ІдёҚеӯҳеңЁзҡ„йӯ”еҠӣе’Ңжҷәж…§зҘһиҜқеҢ–иҘҝи—ҸпјҢжҲ–иҖ…жӣҙз»Ҹеёёзҡ„жҳҜе·ҰеҸіж‘Үж‘ҶеңЁеҜ№дёңж–№зҡ„иҪ»и”‘е’Ңзғӯжңӣд№Ӣй—ҙпјҢжҖ»иҖҢиЁҖд№ӢйҶүзҝҒд№Ӣж„ҸдёҚеңЁй…’пјҢ他们еҸЈеӨҙдёҠи°Ҳзҡ„жҳҜдёңж–№пјҢеҸҜеҝғеә•йҮҢеұһж„Ҹзҡ„жҳҜиҘҝж–№пјҢдёңж–№дёҚиҝҮжҳҜ他们用жқҘеҸ‘зҺ°иҮӘе·ұгҖҒи®ӨиҜҶиҮӘе·ұзҡ„е·Ҙе…·е’ҢеҸӮз…§еҖјгҖӮ
гҖҖгҖҖ“е…¶е®һпјҢеҸӘжңүеҺ»жҺүиҘҝж–№дәәејәеҠ з»ҷиҘҝи—Ҹзҡ„йӮЈдәӣиҷҡе№»зҡ„дёңиҘҝпјҢиҘҝи—ҸжүҚиғҪеӣһеҲ°зҺ°е®һдёӯжқҘгҖӮ”жІҲеҚ«иҚЈиҜҙпјҢд»Ҡж—ҘеӣҪдәәдәҰеҜ№иҘҝи—ҸжҳҫйңІеҮәдәҶи¶…д№ҺеҜ»еёёзҡ„зғӯжғ…пјҢеёҢжңӣ他们дёҚд»…д»…жҳҜжҠҠиҘҝи—ҸеҪ“дҪңеҜ„жүҳиҮӘе·ұжўҰжғізҡ„ең°ж–№пјҢиҖҢжҳҜзңҹжӯЈең°е…іеҝғиҝҷзүҮеңҹең°гҖӮ
гҖҖгҖҖзӮ№дёҖзӣҸи—ҸеӯҰд№ӢзҒҜ
гҖҖгҖҖжІҲеҚ«иҚЈеӨҡж¬ЎеңЁе…¬ејҖеңәеҗҲиЎЁиҫҫиҝҷж ·зҡ„ж„ҹжғіпјҢиҘҝи—ҸжҳҜдёӯеӣҪйўҶеңҹзҡ„дёҖдёӘз»„жҲҗйғЁеҲҶпјҢи—ҸиҜӯж–ҮжҳҜе…ӯзҷҫдёҮи—Ҹж—ҸеҗҢиғһзҡ„жҜҚиҜӯпјҢдёҚдҪҶи—Ҹж–Үж–ҮзҢ®жҳҜи—ҸеӯҰз ”з©¶зҡ„еҹәжң¬жқҗж–ҷпјҢиҖҢдё”жұүж–ҮеҸӨж–ҮзҢ®д№ҹжҳҜз ”з©¶и—ҸеӯҰеҝ…дёҚеҸҜе°‘зҡ„иЎҘе……е’Ңеё®еҠ©пјҢеә”иҜҘиҜҙдёӯеӣҪи—ҸеӯҰе…·жңүеҫҲеӨҡеҫ—еӨ©зӢ¬еҺҡзҡ„жҪңеңЁдјҳеҠҝпјҢжң¬иҜҘеңЁеӣҪйҷ…и—ҸеӯҰз•ҢеҚ дё»еҜјең°дҪҚгҖӮеҸҜжҳҜпјҢиҝ„д»ҠдёәжӯўдёӯеӣҪи—ҸеӯҰжҳҫ然并没жңүе°ҶиҝҷдәӣжҪңеңЁзҡ„дјҳеҠҝеҢ–дҪңзҺ°е®һгҖӮеҸҜд»ҘиҜҙпјҢйҷӨдәҶдәәеӨҡеҠҝдј—д»ҘеӨ–пјҢзҺ°йҳ¶ж®өзҡ„дёӯеӣҪи—ҸеӯҰ并没жңүеңЁеӣҪйҷ…и—ҸеӯҰз•Ңе‘ҲзҺ°еҮәе…¶д»–д»ӨдәәжіЁзӣ®зҡ„дјҳеҠҝпјҢзӣёеҸҚеңЁеӯҰжңҜдёҠе®ғдҫқ然еӨ„дәҺзӣёеҜ№иҗҪеҗҺзҡ„ең°дҪҚгҖӮжҜҸж¬ЎеҸӮеҠ еӣҪйҷ…и—ҸеӯҰдјҡзҡ„дёӯеӣҪд»ЈиЎЁдәәж•°дј—еӨҡпјҢдҪҶе…¶дёӯзңҹжңүиғҪеҠӣе’Ңд»–дәәеҜ№иҜқгҖҒиҝӣиЎҢеӯҰжңҜдәӨжөҒиҖ…еҲҷеҜҘеҜҘж— еҮ пјҢжӣҙдёҚз”ЁиҜҙжү®жј”йўҶеҜјиҖ…зҡ„и§’иүІдәҶ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ж°‘еӣҪж—¶жңҹпјҢеӣ йҷҲеҜ…жҒӘгҖҒзҺӢеӣҪз»ҙгҖҒйҷҲеһЈзӯүеӨ§еёҲиә«дҪ“еҠӣиЎҢпјҢеӮ…ж–Ҝе№ҙгҖҒйЎҫйўүеҲҡзӯүжқ°еҮәеӯҰжңҜз»„з»ҮиҖ…з§ҜжһҒеҖЎеҜјпјҢдёӯеӣҪиҘҝеҹҹеҺҶеҸІиҜӯиЁҖз ”з©¶жҲҗжһңеңЁеӣҪйҷ…дёҠжӣҫеӨ„дәҺдёҖжөҒж°ҙе№іпјҢиҖҢж—¶иҮід»Ҡж—ҘпјҢиҝҷз§ҚеӯҰжңҜзӣӣеҶөж—©е·ІдёҚеҶҚгҖӮ”жІҲеҚ«иҚЈж„ҹеҸ№пјҢеңЁж•Ұз…Ңд»ҘеҸҠдёҺе…¶зӣёе…ізҡ„дёқз»ёд№Ӣи·ҜгҖҒиҘҝеҹҹеҗ„з§ҚеҸӨд»ЈйқһжұүиҜӯж–ҮзҢ®з ”究пјҢзӘҒеҺҘгҖҒиҘҝи—ҸгҖҒиҘҝеӨҸгҖҒи’ҷеҸӨгҖҒж»ЎжҙІз ”究зӯүйўҶеҹҹпјҢиө°еңЁдё–з•ҢеүҚеҲ—зҡ„дёӯеӣҪеӯҰиҖ…еҜҘеҜҘпјҢдё–з•ҢдёҖжөҒзҡ„жҲҗжһңеҢ®д№ҸгҖӮиҝҷд№ҹжҳҜеҶҜе…¶еәёе…Ҳз”ҹиҮҙеҠӣдәҺжҢҜе…ҙеӣҪеӯҰзҡ„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еҺҹеӣ гҖӮ
гҖҖгҖҖиҜҙеҲ°дёӯиҘҝж–№и—ҸеӯҰз ”з©¶еңЁеӯҰжңҜдёҠзҡ„дё»иҰҒеҲҶжӯ§пјҢжІҲеҚ«иҚЈи®ӨдёәжҳҜдёӯеӣҪзҡ„и—ҸеӯҰз ”з©¶иҖ…жҷ®йҒҚзјәд№ҸиүҜеҘҪзҡ„иҜӯж–ҮеӯҰ(Philology)и®ӯз»ғпјҢиҝҷжҲ–и®ёд№ҹжҳҜдёӯиҘҝеӯҰжңҜй—ҙдёҖдёӘеёҰжңүжҷ®йҒҚжҖ§зҡ„еҲҶжӯ§пјҢиҖҢиҜӯж–ҮеӯҰжҒ°жҒ°жҳҜиҘҝж–№зҺ°д»ЈеӯҰжңҜзҡ„еҹәзЎҖгҖӮ“еҝ…йЎ»иҰҒе°ҶдёҖдёӘж–Үжң¬ж”ҫеҲ°е…¶еҺҹжң¬зҡ„иҜӯиЁҖж–ҮеҢ–иғҢжҷҜдёӯеҺ»зҗҶи§Је…¶жң¬жәҗж„Ҹд№үпјҢдёҚиғҪз”Ёд»ҠеӨ©зҡ„ж–ҮеҢ–иғҢжҷҜеҺ»и§ЈиҜ»е’ҢйҳҗйҮҠдёҖдёӘеҸӨд»Јзҡ„ж–Үжң¬пјӣжӣҙж·ұдёҖеұӮпјҢиҜӯж–ҮеӯҰжҳҜдёҖз§Қдё–з•Ңи§ӮпјҢжҳҜдёҖз§ҚдәӨжөҒе’ҢзҗҶи§Јзҡ„ж–№жі•и®ә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жІҲеҚ«иҚЈз ”究з»ҸйӘҢзңӢжқҘпјҢеә”иҜҘиҜҙи—ҸеӯҰжҳҜдёҖй—Ёе…Ҙй—Ёзҡ„й—Ёж§ӣжҜ”иҫғй«ҳзҡ„еӯҰй—®пјҢе®ғиҮіе°‘иҰҒжұӮд»ҺдёҡиҖ…жңүи—ҸиҜӯж–ҮгҖҒжўөж–ҮжҲ–иҖ…жұүиҜӯж–Үзҡ„и®ӯз»ғпјҢиҝҳиҰҒжұӮ他们еҜ№дҪӣж•ҷеӯҰе’Ңе®—ж•ҷз ”з©¶жңүеҹәжң¬зҡ„дәҶи§ЈгҖӮиҝҳжңүпјҢи—ҸеӯҰжҳҜдёҖй—ЁеӣҪйҷ…еҢ–еҫҲејәзҡ„еӯҰй—®пјҢдёӯеӣҪзҡ„и—ҸеӯҰ家ејҖе§Ӣд»»дҪ•дёҖдёӘиҜҫйўҳзҡ„з ”з©¶пјҢйҰ–е…Ҳеҝ…йЎ»иҰҒжңүиғҪеҠӣдәҶи§Је’Ңеҗёж”¶иҘҝж–№гҖҒж—Ҙжң¬и—ҸеӯҰз•Ңзҡ„зӣёе…іжҲҗжһңпјҢ然еҗҺиҝҳиҰҒжңүиғҪеҠӣе°ҶиҮӘе·ұзҡ„з ”з©¶жҲҗжһңз”ЁиҘҝж–№е…ұйҖҡзҡ„еӯҰжңҜиҜӯиЁҖпјҢз”Ёз¬ҰеҗҲиҘҝж–№зҺ°д»ЈеӯҰжңҜ规иҢғзҡ„ж–№ејҸиЎЁиҫҫеҮәжқҘгҖӮиҖҢзӣ®еүҚзҡ„зҺ°зҠ¶жҳҜпјҢдёӯеӣҪзҡ„и—ҸеӯҰ家дёӯеҫҲеӨҡдәәжҲ–иҖ…дёҚжҮӮи—Ҹж–ҮгҖҒжҲ–иҖ…дёҚжҮӮжўөж–ҮгҖҒжҲ–иҖ…дёҚжҮӮиӢұж–ҮпјҢиҰҒжұӮ他们еңЁеӣҪйҷ…еӯҰжңҜиҲһеҸ°дёҠе’ҢиҘҝж–№гҖҒж—Ҙжң¬йӮЈдәӣжҺҘеҸ—иҝҮй•ҝжңҹе’ҢдёҘж јзҡ„иҜӯж–ҮеӯҰи®ӯз»ғзҡ„и—ҸеӯҰ家用иҘҝж–№дәәзҡ„еӯҰжңҜиҜӯиЁҖжқҘжҜ”жӢјпјҢе…¶йҡҫеәҰдёҚиЁҖиҖҢе–»гҖӮ
гҖҖгҖҖи®ӨиҜҶеҲ°иҝҷдёҖзӮ№д№ӢеҗҺпјҢеңЁжІҲеҚ«иҚЈзҡ„з ”з©¶еӣўйҳҹдёӯпјҢжҺҢжҸЎи—Ҹж–ҮгҖҒи’ҷж–ҮгҖҒж»Ўж–ҮгҖҒжўөж–ҮгҖҒеҗҗзҒ«зҪ—ж–Үд»ҘеҸҠиҘҝеӨҸж–Үдёӯзҡ„дёҖй—ЁжҲ–ж•°й—Ёе·Із»ҸжҲҗдёәж•ҷеёҲзҡ„еҹәжң¬еҠҹгҖӮеңЁз ”究дёӯпјҢжІҲеҚ«иҚЈеёҰйўҶд»–зҡ„еӯҰжңҜеӣўйҳҹпјҢиҮҙеҠӣдәҺжұүи—ҸдҪӣеӯҰз ”з©¶иҝҷдёҖж–°еӯҰ科зҡ„е»әз«Ӣе’ҢеҸ‘еұ•гҖӮйүҙдәҺеӣҪйҷ…еӯҰз•Ң“еҚ°и—ҸдҪӣеӯҰз ”з©¶”зҡ„з»қеҜ№ејәеҠҝе’ҢеҜ№“жұүи—ҸдҪӣеӯҰз ”з©¶”зҡ„еҝҪи§ҶпјҢжІҲеҚ«иҚЈеңЁеӣҪйҷ…еӯҰжңҜз•ҢзҺҮе…ҲжҸҗеҮәдәҶ“жұүи—ҸдҪӣеӯҰз ”з©¶”зҡ„еӯҰжңҜжҰӮеҝөпјҢдё»еј жҠҠжұүдј дҪӣж•ҷдёҺи—Ҹдј дҪӣж•ҷ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ҙдҪ“жқҘз ”з©¶пјҢе·Із»ҸеҸ–еҫ—йҳ¶ж®өжҖ§жҲҗжһңгҖӮзӣ®еүҚпјҢиҝҷдёҖеӯҰжңҜзҗҶеҝөе·Іиў«еӣҪеҶ…еӨ–и¶ҠжқҘи¶ҠеӨҡзҡ„еӯҰиҖ…и®ӨеҗҢ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