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达真近年来创作了《康巴》《落日时分》《命定》等一系列表现藏地历史、文化的作品。《康巴》让读者领略了康巴这个杂居地区多个民族的秘史,表现率真、善良的人性和藏地家族的兴衰传奇;《落日时分》以汉族青年的视角来观察康巴地区的方方面面,边地人的纯真感染了成长在现代文明中的失意者。相较于这两部作品,《命定》的独特性在于引入了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大背景,以两位康巴藏区青年“逃离”自己的故乡,投身行伍参加抗战军队为主线,表现了边缘世界中的个体如何被一步步卷入历史的洪流。贡布的敢爱敢恨,为了面子不惜杀人,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执着;土尔吉的犯戒出走,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好奇与向往。二者恰好表现了变革时代边地地区对现代文明的暧昧态度,“中国现代性的历程展现出却是一种悖论式的画面。一方面在追求着现代性(自觉或不自觉),一方面自始至终、或明或暗地隐含着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抗。简言之,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追求与反抗并存”。贡布与土尔吉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种隐喻,是憧憬与审视并存的藏地现代化进程。
一、 边缘历史的自我表述
飞地,是人文地理学中的词汇,意指不毗邻却属于其行政管辖范围。一般来说,处于边缘地带的飞地具有政府控制能力弱,行政管理成本高,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文化杂合交融性强等特点。康巴藏区因地理位置相对闭塞等因素,较晚被纳入现代文明的进程之中,这也意味着对藏地的描述大多来自于外来者,其自身的历史是被压抑与遮蔽着的。
萨义德认为,欧洲的文化生成和管理着“东方”。萨义德引用了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认知霸权,“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及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方”之中同样存在着“内部东方主义”的思维路向,具体而言,这里指的是以儒释道文明为主的汉文化圈对边地少数民族的表述。这也使得边地的历史成了主流历史之外的边缘历史,如何使这种边缘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作家的责任所在。
藏区作为特殊的文化空间,以其神秘、诗意的气质吸引着世人。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中的藏区书写成了热门的题材,优秀作品亦是不少。“井喷”似的藏地描写自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最突出的便是为了迎合读者的猎奇化阅读心理,在小说中着力于展现藏区不同于现代文明世界的“异域情调”,“正是基于此,很多作家‘西藏书写’的挖掘取向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差不多都框定在一个双方默契的定势和共识之中——对西藏进行奇观化展示,专注于炫耀‘异域风情’”。而达真所创作的《命定》突破之处就在于,没有执着于为藏地披上神秘、朦胧的外衣,而是呈现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康巴地区。一如同为西藏作家的阿来和评论家陈晓明所言,“面对千人一面的都市经验的审美疲劳,面对新鲜的、未知的、甚至带有猎奇心态和视角进入藏地的人,达真的小说,像是一种真诚的邀请,一个大胆的手势,用小说的巨大空间呈现一个被误读的神秘西藏”。
《命定》表现被遮蔽的藏地历史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以小人物进入大历史,见证康巴地区被纳入现代文明,具有隐喻色彩。《命定》刻画了两位性格鲜明的主人公,贡布和土尔吉。小说上、下部分别名为“故乡”和“异乡”,故事的主线是两位主角逃离“故乡”(原生态文化),一步步进入直至融入“异乡”(现代文明)。土尔吉自幼被送入佛门出家。在寺庙中,土尔吉遇到了长征途中负伤而阴差阳错来到这里的刘大爷。在与刘大爷的交往中,土尔吉知道了日本鬼子、国军和“红色汉人”的存在。这里,刘大爷充当了不自觉的传播现代文明的先行者。而后,随着土尔吉因犯“淫戒”而远走他乡,一点点见识到了藏地之外的文明,他展现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憧憬。在为驼峰航线修筑备用机场的过程中,土尔吉真正接触到了现代科技,他对机械与混凝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主动接触修建机场的测量队,为后者在了解当地民俗文化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被测量队的人称为“土博士”。“同测量队的汉人接触中他学会了许多,明白了许多奇迹是这些整天同书和地图打交道的人制造出来的,他们像呼风唤雨的大喇嘛。”加入抗战军队之后,土尔吉见识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家乡的械斗,又或是史诗传说中的战争与这枪林弹雨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在成为战地医疗兵的过程中土尔吉也获得了对生命的终极感悟。土尔吉的经历可以看作是现代性滞后的边地,由隔阂到接触,再到融入、反思,最终超越现代文明的一种隐喻。
另一方面,《命定》在尊重文化的基础之上,在“二元对等”的思维框架下对汉、藏两种文化进行了再审视。文学作品以自身的文化力量显示自身,感染读者,然而尊重文化是前提,而非目的。汉族作家所创作的以西藏为题材的小说,往往出现超出“尊重”而“依附”藏地文化的现象,与之相对的也就产生了使之与中原汉地的文化、现实产生一种“对抗”。吴炫教授的否定主义美学中,提出了文学应该是对文化的一种穿越,“在‘尊重文化’的思维下,所有中西方的文化都只是材料,作家只能以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作为自己的价值依托,用各种‘既定材料’来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命定》正是体现了这样的“穿越”,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二元对等”思维。小说中描写了一场在两位汉人官员(刘团长,宋县长)见证下的藏民群体斗殴。因一件小事儿突然爆发的流血事件让刘团长大惑不解,“内地的群殴事件几乎都与‘吃’这个字有关,与生活所迫息息相关,而今日之事与‘吃和生活所迫’相距十万八千里,竟然与争面子、争口气紧密相连,为了争面子,连命都不要地大打出手”。康巴男儿的血性自然也让读者大受感染,啧啧称赞。然而作者也并未一味推崇这种为了面子而不顾一切的行为,借另一位汉人旁观者宋县长之口道出了导致其部落间争斗不断的深层原因,“表面上这种无闪电的雷声好像骤然炸开,其实它透出草原民族某种长期形成的心理,这个心理因素是因草而积淀的”。当犯了大戒的土尔吉被家人接回家中,全家人冒着被连累的风险,依然对土尔吉加倍地关爱(当地文化中不能容忍犯戒的僧人)。这也表现了爱可以超越文化的束缚。对贯穿小说始终的“卡颇热”(指为了面子而争口气)一词,作者也有一种审视的目光,“‘卡颇热’这句话在某件事情上一旦从嘴里说出来之后,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就无法控制了,它也许会给当事人、家庭、部落带来好处,甚至带来荣誉,反之也许会带来不利,甚至是灭顶的灾难”。对文化不单单停留在表现的一面,而是多一层审视与追问,这正是文学作品超越性的表现。
二、填补抗战文学图谱
作家何顿在抗战题材小说《黄埔四期》的创作谈中写道:“抗日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打了14年,正面交锋8年,可是中国没有一部值得称道的抗战小说立足于世界二战小说之林。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缺失,让中国作家蒙羞。”“抗战小说无经典”似乎成为了带有普遍性的否定性结论。关于战争小说的评价标准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抗战这一重要创作资源在被不断地发掘,表现抗战的作品也愈发成熟。作家们逐渐破除了公式化、脸谱化、概念化,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抗战文学作品。《命定》也是其中之一,其优点和突破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塑造了尊重生命的当代英雄形象。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英雄开始“走下神坛”,英雄神话的崇高感大为减弱,英雄人物由“神”回归到“人”。出现了很多以“小人物”为主角的抗战作品,如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温故1942》,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甚至出现了一批“反英雄”的英雄人物,如尤凤伟《生命通道》中的“汉奸”苏原医生,高建群《大顺店》中的被迫充当日本军妓的少女“大顺店”,以及莫言笔下的土匪形象。相较于“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英雄,这些边缘化的“英雄”形象不得不说是作家刻意为之。《命定》塑造英雄形象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战争中尊重生命的当代英雄。
主角土尔吉加入抗战军队之后一直苦恼一个问题,出于他的佛门信仰不能杀害生命。战场之上,土尔吉无论如何都扣不下扳机。想要抗日报国又不愿杀害敌人,这使得土尔吉面临两难的境地。所幸,机缘巧合他成了一名战地医疗兵。枪林弹雨的战场之上,土尔吉不要命似地飞奔,一上午拯救了十一个受伤的战友。小说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土尔吉在战场上为濒死的日军超度。重伤的日本军官想要有尊严的死去,面对奄奄一息的暴徒,土尔吉突然明白人在心灵深处一定掩藏着善,而兽性则是外力强加的。土尔吉愿意在吟诵中为这位杀人者洗净罪恶。最后,土尔吉接过手枪帮助这位饱受痛苦,随时可能毙命的日本军人提前结束了生命。而这,也是身为喇嘛的土尔吉第一次杀人。让人想起电影《血战钢锯岭》中那位坚定信仰,不愿拿起武器的基督徒道斯。战火纷飞的战场中,军医道斯不顾一切地救起了70多名战友,甚至救下了几位日本人(敌军)。“上帝,让我再救一个吧!”是道斯的内心独白。土尔吉和道斯,他们都是富有超越性,尊重生命的当代英雄。
其次,基于反战立场的战争批判。陈晓明教授指出当代抗战文学中存在将敌人矮化、魔鬼化的倾向,人间的战争成了人与恶魔的交锋。在正义的名义下,举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就可以了,由此也就带来了战争描写的情绪化,以及反思性的匮乏。“失去了对立面的现实性和具体性的文学表现,同时也导致了自我认同一方的空洞化,神勇的历史主体只是一味地按照意识形态的观念去构造,文学创作的主体并没有真正给予其以血肉之躯和活的心理情感和性格。”《命定》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这种既有的模式,实现的方法是以个人经验进入大历史。土尔吉在故乡之时,便在口耳相传中了解到日本的侵略,也理所当然的把日本人想象成从地狱而来的魔鬼。随着土尔吉真正来到了战场,便逐渐破除了那种敌人嗜血成性、不可理喻的认知。直到战场之上为濒死的敌人超度,土尔吉领悟到慈悲为怀的爱和友善是生命的最高境界,这是超越民族国家的。
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反战立场。达真不惜笔墨地描写战争的血腥与残酷,“战争告诉他,在人的肉体与钢铁的较量中,人的肉体显得是如此脆弱,像摆放在桌上的瓷花瓶,像阳光下的积雪、风中的云朵那样脆弱,那样悲壮”。战争太过残酷,战火与硝烟中生命是那么脆弱。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明确的反战立场。小说最后一节,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土尔吉六十年来一直在为阵亡的战友们守灵。远去的爆炸声和惨叫声如同梦魇般缠绕着土尔吉,六十年来他一直苦思冥想,一直在追问“战争到底给人类留下了什么?是胜者的快乐还是败者的伤痛?”最终土尔吉得出了结论,“必须对战争彻底说不!战争就是罪恶!战争是人类永恒的耻辱!”这也是作者对于战争本身的批判。
最后,不容遗忘的藏人远征军历史。《命定》是首部描写中国藏族军人直面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且描写到此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涉及的远征军入缅作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重创日军,在缅甸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世界反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达真为了写作《命定》去了众多少数民族抗战纪念馆,河北献县抗日英雄马本斋纪念馆,呼和浩特蒙古人民抗日纪念馆,云南腾冲抗日烈士陵园国殇园,朝鲜族抗日领导人朱德海纪念碑,考察了海南黎族的抗战史。这又一次提示我们少数民族抗战无疑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命定》是一次对抗战文学图谱的填补。
小说最后,土尔吉六十年来都没有离开缅甸东北的小镇巴默——这个埋葬着众多阵亡战友的地方。随着年华老去,这位身在异国他乡的老兵似乎要随着那段历史被一同遗忘。好在,作者留下了希望。土尔吉终于收到了中国远征军老兵协会的通知,得知中国新政府要为远征军老兵颁发纪念章。得知新政府承认远征军是抗日救国的,老人老泪纵横。值得庆幸的是,如今我们对于抗战的历史有了更加客观的表述,入缅远征军的地位与作用也得到了肯定。小说结尾处,土尔吉望着满天红云,对着“乱造坟”吹奏起了《老兵们,睡得安稳吗?》。
三、“命定”与小说内因果的逻辑必然性
“命中注定”一词指认为一切遭遇都是命运预先决定,人力无法挽回。达真的小说以“命定”为题,似乎在强调小说中的命运因果。小说中的情节因果关系自然不同于生活,因为其中有作家权力的存在。笔者认为,《命定》中人物命运看似是神秘因素所造成的宿命,实则是小说内因果逻辑推演下的必然结果。
作家阎连科提出了小说中“外真实”、“内真实”、“内因果”几个概念。外真实指人的行为与事物的真实;内真实指人的灵魂与意识的真实;内因果指故事情节不依赖外在世界的条件,而是靠内在精神世界来推动矛盾发展。由内因果推动的小说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内因果中的内真实如同控制故事运行的发动机,左右着小说情节走向如预定的飞机航线图;另一个是内因果必然带有一种预言性和神秘性。
好的小说是人物自己在行动,作家只是给作品中的人物提供条件与历史空间。《命定》中,首次踏上战场面对敌人的土尔吉,回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在受伤的刘大爷那里第一次知道日本鬼子的存在;逃难的路上听到家园沦丧的东北男人唱《松花江上》;在打西修筑抗日机场;亲眼目睹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最终报名参军。这些偶然的事件让土尔吉似乎变成了刘大爷的化身,在不知不觉间延续着他的事业。土尔吉不禁感叹道:“这一连串的事似乎是命中注定了的。”不过,通过考察土尔吉的人物性格便可发现,推进人物行动的并不完全是好友贡布和抗战的大背景,而是其自身对爱和善的虔诚。土尔吉对佛法的追求与其犯淫戒甚至和情人私奔其实并不冲突,这是一种爱的本能。人物的灵魂乃是人物变化、言行的唯一根源。内真实便是小说故事的推进器。在内因果合理逻辑的推演下,小说便获得了真实。《命定》中宿命与真实的统一即是源于此。
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说过,他一辈子都在听别人转述非洲,现在需要听听非洲人自己的声音。文学中的藏地书写,存在着一个被神秘、悬疑、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建构出的西藏。藏族作家达真所创作的《命定》是藏地历史与文化的自我表述,这不是来自好奇的打量或盲目的崇拜,它还原了一个“被遮蔽的西藏”。此外,小说中还有对藏族军人抗战和入缅作战这些边缘历史的书写,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将这些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也有了特殊的意义。贯穿小说始终的反战立场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读者要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雷鸣,中共党员,湖南衡东人,1972年5月出生。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北省作家协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山东师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研究。

聂章军,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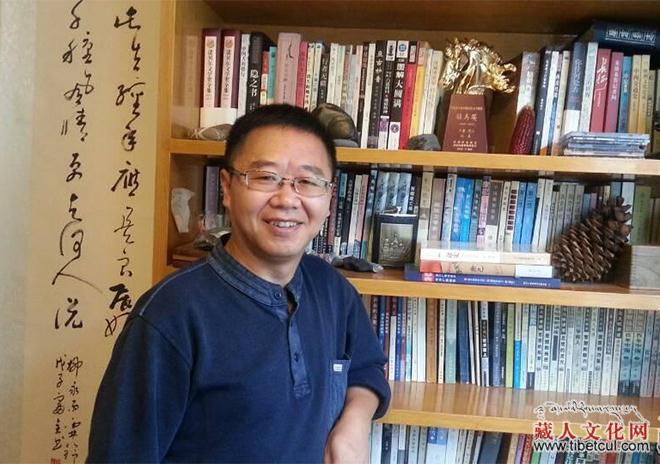
达真,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康巴》《命定》。其中,《康巴》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根据《康巴》改编的大型广播剧获第十二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并翻译成英文出版;《命定》获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 “2012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