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族当代作家中,达真一直致力于探求民族精神文化最好的讲述方法,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康巴》堪称一部地方志的精神标本,在宏阔驳杂的历史场景中,书写了多民族聚居地“康巴”多种文化的交汇与冲突,并在爱的信仰下最终走向融合。《命定》坚持从人性、爱出发的写作立场,对历史战争和个体命运赋予民族色彩的阐释。
作为世界第二次大战的主要受害国和战胜国,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综观建国以来反映抗战历史的小说,有一个发展嬗变的轨迹。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一批红色经典作品,如《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等,主要突出中国民众和共产党在抗战中艰苦卓绝的事迹,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性解放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抗战题材的小说开始注重挖掘正史遮蔽缝隙中的民间史,野史和稗史,出现了诸如莫言的《红高粱》等带有新历史意味的写作,小说从民间立场出发,塑造了草莽英雄人物形象,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意蕴。近年来,作家更为重视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给予肯定。同时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中,讲述全民抗战的历史。抗战题材的作品屡见不鲜,但以少数民族为主人公正面讲述其亲历前线为场景的作品却鲜有为之,因此《命定》的文学史意义尤为重要。它使我们再一次深刻理解全民抗战的含义,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离不开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奋战,同时塑造了深具民族特性的藏族英雄形象土尔吉和贡布,再现了鲜活的历史记忆,为抗日战争题材书写下浓重的一笔。
但不能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简单地界定《命定》,它与惯常的抗日题材小说有显著的不同,具有丰富的民族意味。首先,小说两个主人公土尔吉和贡布加入抗日队伍不是出于明确的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和理念,而是有很多偶然因素和机缘巧合,甚至是不情愿或者走投无路情况下命运的挟裹。都是被追杀从故乡出逃,为寻一条生路而远离加入滇西反攻部队,僧侣出身的土尔吉甚至难以认同自己从一个不杀生的喇嘛转变为刀戈相向的战士。贡布是为了能在战场上立功获得奖金和荣誉,以赔付杀人的命价好日后返乡。其次,小说对两个人战场上英勇行为的描述,虽然土尔吉和贡布是被日本人的残暴和战友惨烈的牺牲激起了杀敌的勇气,但参杂一些神秘色彩。比如土尔吉冒着敌人的炮火不顾危险冲上去救助受伤的战友邱炳国的情景:“三宝护佑,胸口上绑着的经书护佑,三宝护佑,胸口上绑着的经书护佑……、”在土尔吉的反复念诵中,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到了土尔吉面前就拐弯了。小说对战争胜利原因的探讨也颇为寻味。毋庸置疑,滇西战场的胜利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但义与不义既中国自卫反击的正义之战与日本侵略者的不义行为,早已注定了战争的胜负。这种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正如佛教中的善恶两方,由此对战争胜利根源的思索赋予因果、宿命论的宗教思想。由此深化了“命定”的文学意蕴,小说《命定》超出了惯常的叙事模式和阅读经验,给予读者新鲜的审美感受。
小说对两个主人公的设置颇具匠心,土尔吉和贡布的僧俗身份集中体现了藏地两种不同的生活和文化。《命定》通过讲述个体人生命运,展示了康巴藏地的民族文化和精神特质。
土尔吉的寺院生活是很多小喇嘛生活的写照。懵懂之年被视出家当喇嘛为至高荣誉的父母送进寺院,强行割断了家庭的温暖和世俗世界的乐趣。但谨严的教规禁锢不了小喇嘛的好奇心,土尔吉像孩童一样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探究、尝试的欲望。九年的寺院生活,土尔吉和师傅达杰彭措结成如同父子般的感情,这也是藏地寺庙师徒关系的常态。土尔吉因犯了教规禁忌而被驱逐出寺院的遭遇,表明宗教对俗世快乐的放逐和对人性的约束,而土尔吉被规约的人生体现了藏地的宗教信仰崇拜。
小说从人性的立场探讨土尔吉违背教规的行为。土尔吉为何会犯此大戒?小说讲述了一些诱因。比如偶然的机缘他无意中看了汉族僧人净缘抄写的仓央嘉措情诗,使他对男女之情心生好奇和向往;他在绘画中对与女性身体紧密相关的题材的关注和擅长等,但深层的原因与他幼年失去母爱抚慰下对异性温情日积月累的思恋不无关系。小说对土尔吉违背教规生发的源自生命本能对异性的爱慕从他自幼的情感缺失寻找原因,因此对主人公的遭遇给予人性化的关注,“遗憾的是母性的柔情在土尔吉九岁那年便提前退出了,因此,阿妈的声音、体态、柔顺、温暖、神态等这些与女性相关的气息,对于因过早出家的土尔吉而言显得弥足珍贵,像一粒生命力强劲的种子扎根在心里,只要有适宜的土壤便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由土尔吉个体命运轨迹进而引发一些思考。藏区有很多少年像土尔吉一样孩童时期被送进寺庙,从一开始只是烧水、打杂的小僧侣到每日念经、礼佛的喇嘛,寺庙生活引领他们离佛祖越来越近,他们怀着无上的荣耀和诚挚的信仰一心向佛。这也是一群鲜活的生命,然而他们却必须用意念自觉地摒弃七情六欲的诱惑,用神性逼退身上的魔性、欲念,最终修得成佛。但从人性的观点来看,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像土尔吉一样的藏族孩子却从小被剥夺了自主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力。是否应该在他们有一定的人生经历之后,听凭内心的意愿去选择是皈依佛祖还是另外的生活?从另一方面来说,此时的皈依可能是更深刻的参悟和信念的坚定,而不仅仅是遵循流于传统的仪轨。
豪放重情的贡布是典型的康巴汉子,他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阐释着康巴藏地的风俗文化和精神气质。抢婚、为尊严和面子而战、为公平正义和荣誉而杀人,在贡布身上凝聚着康巴汉子的精气:敢爱敢恨、英勇善战、豪放不羁、率性而为,这正是格萨尔人文精神在康巴这块土地洒下的种子。《格萨尔》英雄史诗所彰显的就是人性,其核心价值是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任何民族的神话,总与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相贯通,史诗与民族精神一同深植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而后生发开去,化为形形色色的精神表象。原始的力度感,古朴的道义感,自尊自强、勇敢无畏的品格,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超越一切的圣洁和庄严,专情和敬仰悲壮牺牲的献身精神,激发了全民的热情和崇拜,民族英雄因此而获得了全民族的意义……”。
小说从人文精神传统的视角而不是站在道德律令的立场评判贡布的言行,同时也挖掘了康巴文化精神之源。贡布的形象与藏族民众不杀生、善的信仰从根本上来说又是相违背的,但在贡布身上看不到他杀人后的自责,反而成为这块土地令人钦佩的英雄。从贡布的抢婚来看,是为了追求爱和美,而当地的抢婚风俗也佐证了“康定情歌”中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贡布的形象是对土尔吉为代表的僧侣生活的一种平衡和补充,深刻阐释着康巴大地涌动着的鲜活生命力和对荣誉、自由、爱和美的张扬。
土尔吉和贡布的出行轨迹从故乡到异地,从藏文化浓郁的部落草原到多民族多文化的交汇地,既是空间的变换,同时也是开阔视野、文化交流的过程。在故乡的土尔吉和贡布的命运深受藏地约定俗成思维观念的影响,所以土尔吉被称为“扎洛”陷入亲人离众人唾弃的境地,而正是因为尊严、面子和好强的个性,使贡布欠下了命债,陷入困境不期而遇的两个人结伴出逃。在色甲果采金场和然打西机场耳闻目睹抗日宣讲团和亲历庆祝飞机试飞时,来自不同国度和民族的风情习俗和文化仪式使土尔吉大开眼界,而且被整齐有力的标语口号和悲怆激昂的合唱所感染,不知不觉投身其中。异乡新鲜的所见所闻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滞后闭塞的故乡草原那一小方天地相比,异乡正发生风云激荡的变动。在与美国军官和汉族军民相处的日子,土尔吉和贡布渐渐了解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心理,土尔吉学会了汉话,一切新奇的事物激发了他强烈的探求欲望,而贡布的勇猛好战赢得大家的叹服。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族群进行着文化的冲突、碰撞和交汇,在抗日的民族大义的洪流中趋向融合。正是经历这样的历程,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土尔吉和贡布才能站在一个更开阔的视角去看待一己的坎坷命运并理性审视民族传统文化的痼疾,因此出走的过程也促进了土尔吉和贡布精神的成长,因此,《命定》也可看作是一部成长叙事小说。
由于作家民族身份、文化立场的不同,藏地题材的作品在叙事视角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非藏族作家笔下的藏地更多地具有文学想象的色彩,作品往往传达的是“他者”对藏地的观望;藏族作家写本土的作品则普遍书写藏地一隅的人和事,局限于一己的悲欢和人事的评论,大多是单一身份视角叙事。当然也有一些藏族作家的创作如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主人公为走出藏地的现代藏人,但又呈现出“失根”状态在物欲横流中挣扎、彷徨。《命定》的主人公植根于藏地深厚的文化土壤,从故乡到异乡的途中逐渐跳出狭隘的观念和一己悲欢,在多种民族多样文化的交汇熏陶下提升自己。而且作者不是站在藏族或者汉族等其他民族单一的视角立场去看,而是互看,以文化平等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优劣的姿态描述他者,保证了叙述立场的相对客观,体现了达真探求的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和解的主题。正如小说中濒临死亡的佛教徒日本少佐,他不懂藏族却能听懂土尔吉念诵的经文,在战场上他们是各为其主对阵的双方,但共同的宗教文化信仰使他们达成心灵的共鸣。临死前他也坚信土尔吉会超度他尽快摆脱痛苦,心底的“善”使他们心灵共通。“土尔吉怀着一颗悲悯的心帮助这位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敌人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这是土尔吉参加滇西反击战以来第一次杀掉敌人。”土尔吉用共宗教共通的善和爱完成了对日本少佐的精神征服,这超越国界、民族、敌我的大爱也使土尔吉获得心灵的解脱。
刘再复认为,“文学需要向内心世界挺进,需要表现灵魂的深”,“文学更多地应当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小说《命定》有两条主要线索,明的一条线索以土尔吉、贡布从故乡逃到异乡——参加滇西反击战——贡布为国捐躯,土尔吉为战友守墓。还有一条线索讲述了土尔吉心灵证悟、灵魂思辨的心路历程。小说有两种叙述声音,一个是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另一种是土尔吉自我灵魂的对话、辩驳、冲突,正是后一种声音体现了小说挺进了灵魂书写的维度。
童年时期土尔吉被家人送进绒布寺当喇嘛,意味着与俗世生活的隔绝和对人性七情六欲的了却。但情窦初开的年龄却犯了黄教的禁忌与贡觉措偷情,事发之后被寺院惩戒驱逐出寺院。起初土尔吉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寺院决定要处罚他时还有得过且过的想法,只要能在寺庙待下去受罚就受罚。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名誉以及给师傅和亲人带来的影响和伤害,而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因为他的过错年迈的师傅达杰彭措跟着受辱被体罚,连家人也不敢在公众面前表现对他的关爱,只有情人贡觉措不顾一切、不离不弃地跟随他。与贡觉措相比,他显得懦弱而没有担当,以不能给予爱人更好的生活为理由而抛弃她悄悄逃走,其实他把自己的困境怪罪在贡觉措头上,对她心生怨恨甚而认为她是他的累赘和心魔,甚至一度升起裹卷钱财杀人的恶意歹心。如果说他违背教规犯下的禁忌是心魔压倒了对神佛的敬仰,体现了僧俗两种心性的冲突,而此时的意念则是人、兽、神三性的较量。在出逃途中,扎洛的称号似是土尔吉头上的疮疤,羞于被别人提起和知晓,因抛下贡觉措内心也时时悔恨、自责,同时他也感到委屈、愤懑。一方面他认同黄教的禁欲教规,认为自己犯下了不齿的罪行;但同时内心有另一种声音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至少不应该被逐出寺院,是一些心生嫉恨的人落井下石。这两种声音正如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理解:“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是否加入滇西大反击的队伍问题上,土尔吉也经历着思想的挣扎。作为曾经的喇嘛,他一贯奉行佛教不杀生的信条,但战争肯定是有杀戮的,所以他曾试图逃避选择留在藏地。在你死我亡的战场上,土尔吉关键时刻依然没能突破内心的障碍,眼睁睁看着战友在枪林弹雨中倒下、贡布受袭而迟迟打不响手中的枪。而他内心却经受着巨大的煎熬、折磨和无法辩驳的压抑和委屈。他终于选择当了医疗救助员,既可以为抗战奉献又不违背不杀生信条的适合岗位并表现突出。因出色的表现,土尔吉得到大家的认可并获得路小慧的青睐,使他逐渐走出自卑、自怜变得自信而充满憧憬,在超度完贡布的亡灵和帮助日本少佐结束他罪恶的灵魂后,土尔吉最终获得了心灵的了悟和解脱:佛教的善是超越一切形式的大爱,只要是无私无畏的利他精神都是澄明的。
土尔吉的精神历程正如佛教徒的苦修,一切的果都是前世种下的因,好多的机缘巧合、偶然因素推动着个人命运的走向,经历的所有磨难、痛苦和煎熬都是为了最后的证悟,到达对生命的终极感悟。小说把握住土尔吉微妙的心理波澜,细腻呈现了一个在僧俗两念、人兽神三性中心灵不断辩驳的过程,倾听小人物内心的声音,显示了小说灵魂探索的深度。
《命定》指向丰富的阐释空间,藏族民众命定会与各族人民站在统一的阵线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相互尊重理解的基础上终会走向融合,正义定会征服邪恶,而个体命运与民族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而这些“命定”都是由超越一己的“大爱”促成的。贡布东躲西藏也不能摆脱仇人追杀的“债”,在为国捐躯的民族大义面前化解了;正是这种超越部落、民族、国界的大爱,土尔吉和贡布才能融入抗战的行列,也是不禁锢于任何形式的大爱,才使土尔吉最终获得解脱和证悟,由此,《命定》实践了对个体命运与历史战争的另一种讲述。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七辑

赵丽,女,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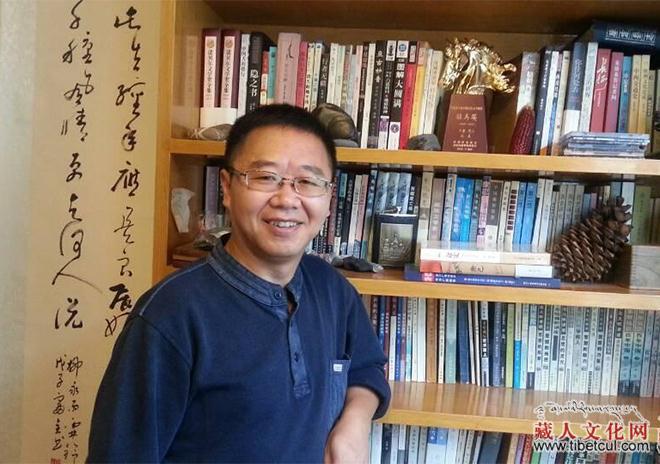
达真,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康巴》《命定》。其中,《康巴》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骏马奖”,根据《康巴》改编的大型广播剧获第十二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并翻译成英文出版;《命定》获2012年度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并入选 “2012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