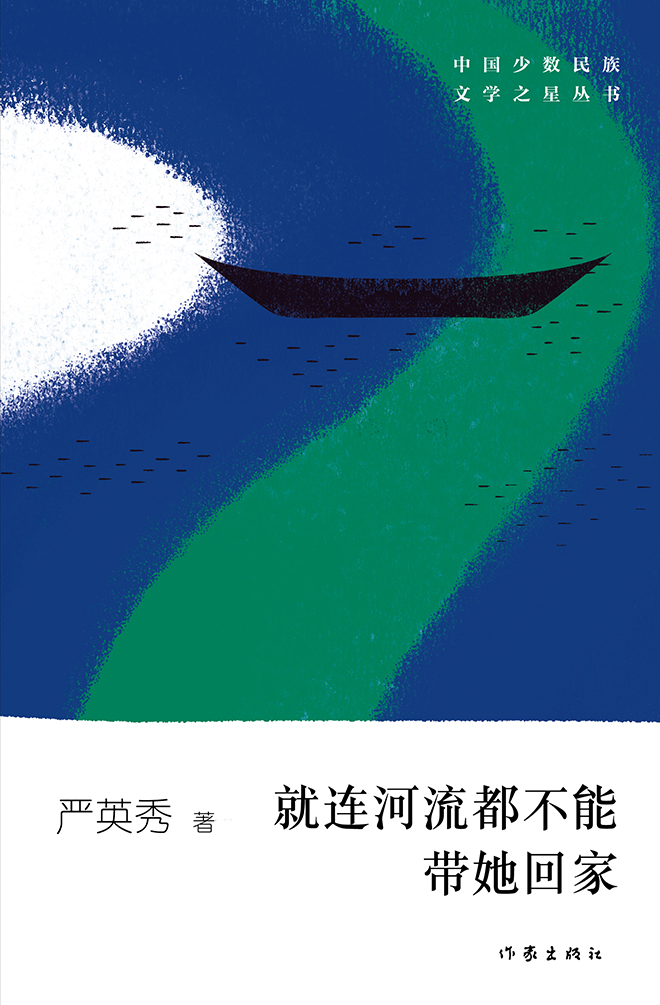
创作谈 | 严英秀:就算时间带走了所有的岸
我从不曾预料到2018年在我生命中的特殊性。一本书的即将问世,一个人的遽然离世。这看上去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而且,根本不具备等量齐观性。但在2018年,它们接踵而至,缠杂交错,横亘在我的今天。并且漫延不绝,正在构成更长的将来。
一本书,就是这本《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我已经有五部书了,都是小说集。很久以来,我想有一部散文集。我一次次地想象那些散文结集出版的样子,它的颜色,芳香,它敝帚自珍的重量。但人们已习惯了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所以,在2018年,当我以散文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那简直是一个意外。却原来,念念不忘,真有回响。
然而,得知这意义非凡的喜讯是在母亲的病床边。我的母亲,一个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藏族妇女,她不曾留下陪我吟诗涂鸦的亲子记忆,但当我拿起笔,她始终是我所有文字中那个最强大的存在。尤其,在散文这种极自我的文体里。暮年时分,她常常摩挲着我的小说集,双眼闪亮。事实上,她并不知道书里写着什么,单是女儿写了书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她无限欣慰。她是那么骄傲于自己的女儿成了“写书的人”。我曾告诉她,这些书是别人的故事,将来我会出一本书,那本书里有她。
就是这样。知道我可以出这本“有她的书”之后十四天,母亲走了。然后,在她出殡的第二天,我赴京参加了散文集的改稿会。再然后,在她七七祭奠的第二天,因着这本散文集我随中国作协采访团去了南海三沙市永兴岛。天涯海角,心神迢遥,今夕何夕。我以为我已饱经沧桑,我以为我已被生活掳掠太多,可是,当比辽阔更辽阔的大海涌向我的眼睛,当比激荡更激荡的大风吹起我的头发,当比孤独更孤独的风景靠近我的足迹,我突然于身心深处感到了一双无处不在的抚慰之手。那样的手,那样的温热,此生已然别过,为何会在某一刻悄然相逢?
大海,无边无际,消释一切,包容所有。大海让一个刚刚痛失母亲的人,失而复得了唯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感到的大欢喜,大善意和大委屈。海岸线上,万道霞光,一轮崭新的日出。生命的登场有着那般磅礴的欢喜,如同它谢幕时庄严的静穆。我仿佛第一次真正懂得了关于自然万物的那些素朴真理,谛听到了天籁交响。我是那么真实地触摸到了自己。我已失去了世间最珍贵的,我还要遭遇更多的失去,但我正在路上,我必将不断地被馈赠,被壮大,被丰盈。
很大风。风从海上来,吹起了无穷大无穷远的蔚蓝。海蓝到剔透如镜,蓝到深不见底,仿佛全世界的蓝都集中在这里,仿佛这无边无际的海域也盛不下如许多的蓝,眼看着这蓝冲溢到了天边,眼看着这蓝侵占了全部的天空,海天浑然一色,海天蓝到让我无语哭泣。无与伦比的2018年,所有的岁月之殇,终于在南中国一碧万顷的长风中,哭出了海也似的泪。
我知道在这样一篇创作谈里,抛开创作话题回述如此私人的生活境遇,是不适宜的。我一己的执念,我的偏狭之笔,没有沉淀和提炼,缺乏结晶和升华,尚未掘进到人类公共情感和经验的幽深,尚未抵达文学性的高度。但关于这本书,我最想说的就是这些。仅仅是在去年,我还在《致母亲》中咏叹:“走进榆叶梅的花海,我猝不及防跌进了修辞的包围中——它多么像你的一生。那么多的春天,那么多的捧出。”而此刻,又一个春天呼啦啦全开了,我却被一枚钉子钉住了心和口。
如此,也必须重新启程。走下去,写下去。是的,不能被述说的生活,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依然是无法想象的。写散文,还是小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如此美丽如此伤痛的人世,我怎么可以停止歌唱和哭泣。我怎么可以说:我一无所有,我两手空空。
而这本《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之于我,是永远的,唯一的。时间带走了所有的岸,那个曾经的港湾已彻底湮灭,但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我,在这本书里,在文字的救赎中归于和母亲十指紧握,永不分手。这浩荡的悲喜人生,这纷纭而至的命运,从此我不再轻言放手。

评论 | 郑函:严英秀的至真至勇
读严英秀的这本《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并不轻松。文字绵密缱绻,意识流淌跳跃,仿佛在一片密林中追寻着一只野鹿,不容半点分神。不仅如此,阅读渐进,忽然产生巨大的惶恐:我怎么能如此深入地闯进了她的内心。严英秀的自我如此强大,这本散文集分为“我所栖身的生活”和“我所经历的阅读”两部分,勇敢地以我观物、抒己之怀,在这个追求“取悦”和“目的”的年代,这本任性的“自白书”越显弥足可爱。
严英秀的写作驱动力是内向的,看到一树繁花的波澜、一场倒春寒时与女儿的较量、一个小城、一幅小画,都可以成为思绪生长的锚点,她以丰富细腻的内心作壤,任由这些枝桠繁茂。在严英秀的字里行间,甚至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在思绪浩瀚中捕获那些闪念,如何将它们细细品择,又如何将它们流淌到指尖。她写作的目的同样也是内向的,母亲离世的悲痛、创作面对的困惑和质疑,心思敏感如她,必然需要一个出口才不至于被自己击溃,写作此时变成了自我抚慰、阐释与和解, “唯有写出来,记下来,我才能走过我自己”。正是这样勇敢、真我的赤诚相见,使她将这些一己的独特感受变得共通,使她的思想和观点超越自我书写,成为对生活结晶的描摹。严英秀将这本书献给她的母亲,母亲过世恰与她入选的这次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开展系列活动的时间重叠。当时因为这项工作我也多与她见面、联络,在读到记录那一段时间的《天之大》时,才明白面色憔悴、强颜欢笑背后一颗正在恸哭的心。母亲和女儿是严英秀“所栖身的生活”的主题,她在想起女儿时就会想起母亲,在面对母亲时又不禁念起女儿,“这样生生不息的交错,是多么令人伤感又使人振奋的生命的奥秘啊,一个人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一条路的尽头总会生出另一条路,四季轮回更替从无死灭,万事万物都在既定的轨迹上行走”。她试图理解的,不是女儿或者母亲,是女儿给了她为人母的体验,她又用母亲去照映自己的未来,二者交叠在一起,归根结底探索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生。
一个真诚、忠实于自己的写作者必然是勇敢的,不仅在于勇于将自己的苦痛和思考剖开展现给世人,更在于写自己想写而不去满足他人的期待。在严英秀的文字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读书的人、一个爱花的人……而最为人所瞩目的“西部”和“藏族”两个标签却要排到十几名之后。批评家对她的质疑在所难免,在《在西部写作中》,严英秀直言不讳:写,是一种迎合;不写,才是坚守。“当西部本身已面目模糊,渐行渐远时,我们的文学该如何的西部?我们是表现这古老的西部大地和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变异和生长,在持守和嬗变中再创造出真正的反映母族大地的现代诉求的新的西部传统,还是永远地开掘取之不尽的西部资源,让自己的文字成为类似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旅游中那种满足了东部人的优越感和猎奇欲的民俗表演”。
我认同她,也敬佩她。作为“甘肃八骏”、“藏族作家”,人们认为在这个框架下获得了荣誉与关注,就理应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所以她的辩驳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一种推脱责任和数典忘祖。但是一个真实生活在这个环境和文化中的人,如实地反映生活与自我,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回避,让土地与民族所赋予的精神自然流淌,“就算不以地域生活为显性的主题元素,也都会毋庸置疑地留下自己植根故土的明显胎记”。这何尝不是对当代藏族、当代西部的直面和表现,这样的真实交给时间去审视可能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