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江河源”读书推出的《果洛三人行》,就是长期生活在果洛地区的藏族诗人木雅·多杰坚措、居·沙日才、班玛南杰的作品合集。此书是三位诗人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上提议并最终出版的,一经面世,即在青海文学界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它不仅见证了果洛作家的团结与友谊,更传达了三位诗人在辽阔的玛域草原奋力攀爬、并肩而行,与更多的文学同道一起传播诗心、诗情、诗意的勤奋和执着。本期专版,除选发三位诗人的诗作外,还特意推出我省评论家马钧为《果洛三人行》所写的序言。序言对三位诗人的诗作作了精当的点评,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三位诗人的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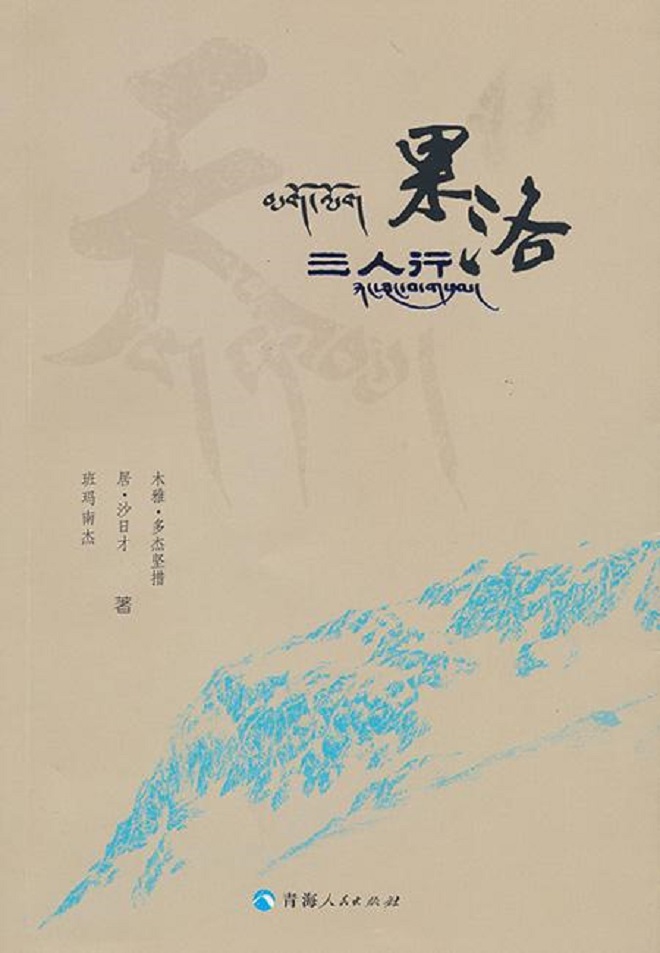
——序《果洛三人行》
与一直占据文学—地理资源优势的发达省份相比,青海文学一直处在文学的外围和边缘地带,从最初一代作家不无悲壮的突围,到今天青海当代文学的存在方式,都宿命般地延续着一种“南征北战”“远距离投篮”式的文学证明方式。其艰苦卓绝的写作拼搏过程,没有比昌耀孤拔的创作经历和最后迟来的荣耀,更能恰切地象征整个青海文学的命运的。
时至今日,青海的诗人在诗歌圣殿的红地毯上走过的身影仍旧显得有些形只影单。而作为在青海文学中占据强大能量的藏族诗人,除了他们在藏区享有的荣耀以外,他们在汉语诗歌界的价值和影响力,还没有被诗歌界充分地认知和评估。
藏族诗歌一直以来都延续着地缘诗歌美学的传统,覆盖藏区的藏族文化和宗教是使这一传统得到不断延续的最大内驱力。促使这一传统不断赓继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藏族诗人一般都以类似留鸟的方式,长期居住在某个藏族聚居区,那里的地理空间既是他们的生息之地,也是他们的寄魂之地,这种生存与精神的双重空间,成为他们写作的“无尽藏”。这也就是说,藏族诗歌虽然受到汉语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影响,但它首先具有一种诗歌的自生力,它以一种“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式的自在方式存在着。
《果洛三人行》这本诗集,就向世人展示了地方诗歌视域,在今天全球化、城市化、娱乐化、消费化的背景下的特异形象。仿佛是文化语境置换后的藏地“桃园三结义”,诗集中为首的多杰坚措和位居其二的沙日才,都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果洛本土诗人;班玛南杰殿后,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与前两位果洛本土诗人稍有区别的是,他的第一故乡是海南藏族自治州,他是16岁随父母去了果洛,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
于坚在十多年前为《藏族当代诗人诗选》写下的序言里,对藏族当代诗歌有一个诗学判断:“神性,这是一个旧世界的词。这些诗歌中的美学精神不是什么‘日日新’的现代性,它是对一个充满神性的日常世界的旧有诗意的证实。”于坚这个判断,用在这部诗集上,仍然具有一部分效用。三位诗人所开拓出的新的疆界,新的意象美学,是他所不能预见和预先研判的。
于坚的这句“充满神性的日常世界的旧有诗意的证实”,从发生学上,应当来源于藏族文化和藏族宗教。藏族属于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佛教文化是他们共有的文化基因。在这本诗集中,读者只需稍稍关注一下三位诗人不约而同出现的高频词就可见一斑:“众神”“轮回”“转山”“金刚杵”“央金玛”“前生”“诵经”“掘藏大师”“天葬”“右旋海螺”“嘛呢堆”“玛卿岗日”“格萨尔”“九眼天珠”“祭坛”“唐卡”“大法会”“涅槃”……这一通过词语所折射出的精神维度或心灵内景,毫无疑问是汉族诗歌当中所不具备的。这些在汉语诗歌中显得极其异样、生涩、神秘、骇厉、原始的精神意象,可以被视作藏族诗歌最为直观的语言成色。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单凭一些民族、宗教的习用语来彰显地域-民族特色显得有些标签化和表浅化,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更深层的心理体验、思维方式来观察藏地诗歌独有的品质。
被批评家们一直忽视的一个情况是:藏族诗人要么是生长在以藏语为母语的环境中,要么是生长在汉语环境中。以藏语为第一语言的藏族诗人,同时又能掌握汉语,他所书写的汉语诗歌便会自然而然地将藏族文化中的语汇乃至藏族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心理流程,投射到诗歌的文本当中,这种与汉语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诗歌判然有别的藏族诗歌,是其存在的最大价值。
多杰坚措的诗歌,以一种沉稳内敛的激情,偏于内观的体验,书写着短小精悍的诗篇。他朴素、真挚而又意蕴绵绵诗歌,确实再次证实了“一个充满神性的日常世界的旧有诗意”,又透露出一种超然的静谧感。这种静谧感既能指示物理空间的寂静无声,又能指示一个人内心的安宁状态,一个不被外部世界的扰攘所困的、拥有宁静之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精神能量。
《封存一瓣雪花的记忆》
小满时节。独自
站在夕阳的背后
封存一瓣雪花对雷声的
记忆。而雪
依旧沉默地下着
春雷也任性地保持沉默
此诗的核心词语都是“静默”,诗人不动声色地赋予客观物象以灵性的拟人化摹写,既是藏族人万物有灵这一古老思维的诗性转化,又在其“静默”体验的背后,积聚着强韧的内心能量和强烈的情感。诗人“以静制动”的诗歌美学,镇定地应对“喧嚣世界”的定力,是藏族诗歌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文化个性和诗学品质之一。
多杰坚措的诗歌里还拥有一种崇高、肃穆的时空感,用他惯用的语汇来替换,应该称作“苍茫感”。“一朵野花安静。摇曳着∕草原苍茫的味道,亲吻死亡。”(《只言片语》)将渺小到一朵安静的野花,置放到旷荡无垠的草原,这意象是多么简朴啊,但意象的空间又是何等的辽广。多杰坚措更为特别的一点,是把“苍茫感”延伸到宇宙意识的层面,继而将诗境提升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少有人书写的壮美之境、虚空之境:
“来不及捕捉,便在视线的尽头消失∕而我,却还在时间的速度之外沉醉”(《蹄音中消失的马》)
“晚风如雪,在∕月光的背后悄然飘落”(《晚风,在月光的背后悄然飘落》)
“众神缄默不语。天在天上”(《走过一个季节》)
“宇宙之外,月亮之上∕心跳 成为另一个世界的旋律∥谁的叹息,在一首诗里∕点燃 银河”(《失眠》)
“马蹄踏响远山的回音∕雪山突兀,在想象之外沧桑千年”(《笛声中有百灵鸟在飞》)
“心,在轮回的激流中无声地∕淹没。而一声法螺响在云天之外”(《一声法螺响在云天之外》)
沙日才则是一位激情四溢的诗人,他的诗歌长于漫无节制的抒写,诗篇以长诗居多,恣肆汪洋的情感,粗率豪放的想象力,裹挟着一股凌厉的诗风,他的《天葬》《藏獒》《冬虫夏草》等诗作,便是例证。在这本诗集里,最能代表他个人诗情才华的诗作,当属《从今天起,我只做一个奇石收藏家》。石头这个简单的自然意象,在他的笔下,完全变成了极其魔幻又极其真实的意识幕布。这首诗让人们看到了藏族诗歌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巨大的包容性和现代精神品质,它不但善于发现旧有世界的神性与诗意,他们还努力克服着文化时差和心理时差带给藏族诗歌的某些滞后性,并锐意攫取着古今杂糅的复杂体验。
三人中年龄最小的班玛南杰,在地理视域的抒写上相对比前二人淡化,他更倾向于诗人心理空间和心理现实的体验和表达,同时他又喜欢将叙事、对话的功能,与诗性的抒情结合在一起。多地写作的经历使他善于处理多种题材,无论是成长的经历,青春时期的懵懂与伤感,相恋时的思念,都被他自由而多变的笔触娓娓道来。既有柔婉的声腔,更有直探事物本相的犀利。有着翻译经历的他,在遣词造句上更是极力追求用语的精炼、诗意的别致,在思想勘探的深度上也屡屡透出令人意外的锋芒。
他的《下乡散记》,以极为纪实的手法,撷取行旅途中的一个个日常瞬间,编织出行旅者在途中的见闻、对话,童年记忆、诗人自己的日记等不同类型的话语片段。诗歌文本毫无挂碍的自如跨界,既体现出现代诗歌不受传统诗歌教条束缚的巨大突破力,也透示出诗人自由不羁的心性。他的《纹忆录》(题目完全是作者生造的一个词汇,但细细体味,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妙处),是一首以诗体抒写的成长录,诗性的语言在重现往日时光的同时,完成了一个诗人局部人生的速写画像。
有着藏族母语思维方式的诗人,在使用汉语写作时,往往会对汉语语汇、词性、语序乃至诗行的排列,进行一番别出心裁的移植、调整和改换,制造出两种语言磨合下崭新的思维,锻造出一种新的语言程序,语法规则。
多杰尖措的《只把根埋进土地深处》:“在低处,一棵草∕无论落雪还是雨飘”采用宾语前置,使得诗句的意脉曲折有致。《碎裂的骨骼》:“尘世喧嚣,碎裂的骨骼∕飘落成一地白雪皑皑”“白雪皑皑”原本是个形容霜雪的成语,在这里诗人已将其名词化。
沙日才的《白唇鹿》:“而我的 焦虑与不安∕又恰恰是 你也像∕褪色的雪山”其中“你也像”一句,出现得多么突兀啊,但它又像是极其微妙地捕捉到了潜意识里的一个迅捷的跳转,一个思维里突然冒出的意念。《黑帐篷》(一):“三十八条牛皮绳鹰爪似橛子∕纵横交错”从字面上阅读,“三十八条牛皮绳鹰爪似橛子”一句好像在理解时有点硌,如果不出现“鹰爪”一词,语义便是极其顺畅的,但是它的出现既显示了诗人思维深层结构的原貌,也强化了橛子更具生命化的牢固性,还有一点就是就是使地域风物的色调更为鲜明和谐。他还喜欢拆解固定词组:《白唇鹿》:“只是 不再是白唇鹿∕或不再是你自己∕留给世界的∕只是唇亡齿寒∕或鹿死谁手?”将“白唇鹿”这一专有名词拆解为“唇亡齿寒”“鹿死谁手”两个成语,意在强化生物链环的相互关联与依存,强化对白唇鹿存亡的忧患意识。《色达》:“色达 绛红色的信仰∕僧尼 低矮木格窗口 一声叹息∕熄灭了酥油灯∕色即是空 达便是终”“色达”本是表示地名的一个固定词组,诗人把它拆解后,便在原有的固定之意中分别释放出两个新增的意思:一则摘取《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的一句佛经,一则“达便是终”。在《狼毒花》一诗里,诗人干脆将草原上一种有毒的植物“狼毒花”进行拆解:“我是狼 狼行千里∕我是毒 以毒攻毒∕我是花 花好月圆”诗人采用这种词语拆解法的动机,至少是不满足于原有词语意义的固化、贫乏和单一,这也可被看成诗人在词语不拘礼法的狂欢节上,多么顽皮嬉闹的一面。在我记忆中,昌耀在《一天》一诗里把“资本论”拆解为:“有人碰杯,痛感导师把资本判归西方,∕惟将‘论’的部分留在东土。”这是词语拆解法发挥解蔽功能极为经典的一个例子。
班玛南杰的《呐喊·桑烟》(组诗),利用藏族谚语,构成精简有力的诗句:“犄角再弯也扎不进自己的脑袋∕洪流再汹也淹不了自己的浪花”。
三位诗人多数情况下,都能以简洁朴素的文字,表达意味隽永的意境。
请看班玛南杰的《一夜冬》:
多想啊……多想
雪前还乡,与你
围炉坐等春日
在每一次寒流袭来之际
请看沙日才《黑帐篷》(二)
坠落草原的
一颗美人痣
怀春少女
野牦牛正在
分娩 金秋十月的牧场
两首诗用的意象都是日常意象,但它们一个以沉吟的句调刻写怀恋者温纯的情思,一个以巧妙的比喻,写出家园妩媚诱人、生机盎然的草原情调。
班玛南杰还有一首《无题》:
人走了,又回来了。东山
屹立在童年,城镇背靠的土丘
真正成熟的,应是荒芜
随风的。除了白昼,一无所知
此刻,天蓝,云白,草木抽芽
我和一块藏毯,半碗茯茶就此病倒
几乎压缩到极致的短句,加上蒙太奇般的意象剪辑,加上有意的语句断裂和大跨度的语义跳跃,使这首看上去极其简单的诗歌,理解起来多了曲折、迂回甚至晦涩的阐释空间。
《果洛三人行》,在直面现实这一点上,也显示出三位诗人与时俱进的审美观照。像多杰坚措的《移民》,就直接反映了藏族人生活状态的改变和牧人无以调适的心态:“望着城市的面孔∕丢失了纵马驰骋的洒脱心情∥行走城市的夹缝 有些茫然∕你似乎也忘记了最初的呼吸方式”班玛南杰的《归途》《消失:因为黑暗的缘故》等诗,沙日才的《冬虫夏草》等诗,都对形形色色的丑恶和怪诞,扭曲的人性世界做了颇具深度的抒写。
集子中的有些诗作,在语句的推敲上尚欠一些功夫,有些篇章因缺乏用心的剪裁,使有些原本极具张力的诗行,牵连受损,表达效果大打折扣。在长诗的驾驭上,还应考虑到诗歌结构的缜密度,内在逻辑,情感收放在审美观照中的理性约束。
最后想说的是,三人成众,这三位诗人也部分地彰显出藏地边缘诗群的某些风貌。他们自在着,自信而安静地发力、发声。边缘诗群如何赢得自身的荣耀而活着,班玛南杰的《呐喊·声音》(组诗),无意中给出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和启示:
一个人的声音是多么的微弱
似乎周遭任何响声都可以淹没这样的发声
可你并不间断
这让一切声音都遗憾为瞬间
你却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