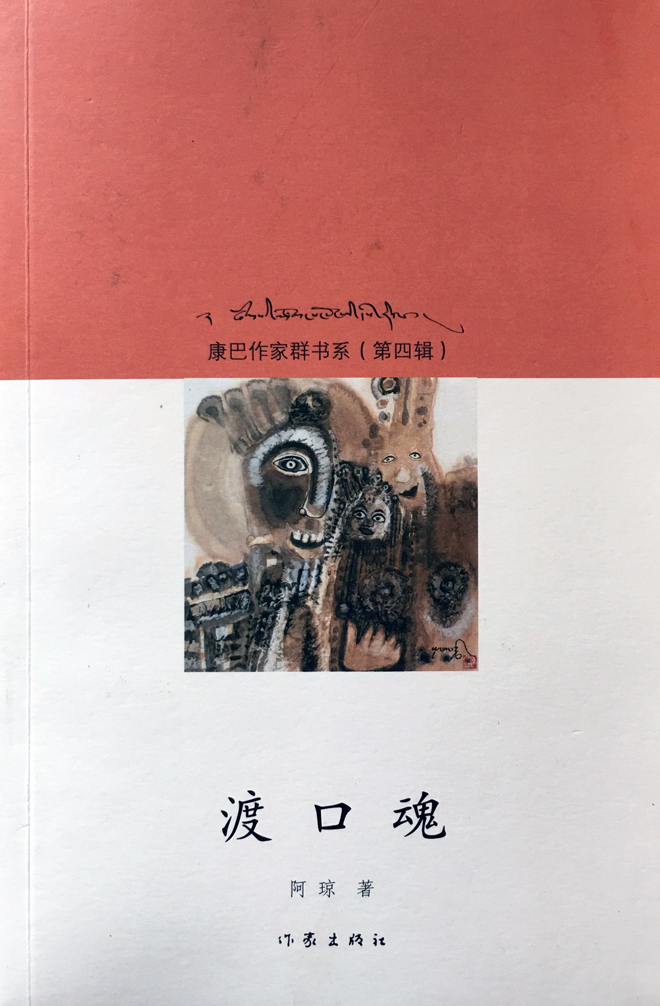
地方志与“家风”传承
——阿琼小说《渡口魂》的现实意义
杨凤银
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是因为小说会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将一个民族的历史以断代史的方式活现成一定地域或家族历史的撰述。人对一个地域的感知首先从风土人情和景物风貌开始,而风土人情和景物风貌又往往承载了一个地方的精神和魂魄,——阿琼的小说《渡口魂》兼具了上述诸种要素。
直门达渡口、通天河、直本家族、唐蕃古道,单从一个文本的构成质素考察,《渡口魂》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宏阔的格局,形成一个迷人的局,布满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的表征密码。
当然,复活一个地方的历史和记忆还得需要文学的手段,即找到一个故事讲述的切口,剥开沉寂的时间迷雾,让风云变幻的时代露出真相,让一段埋没的往事重回当前;找到一种精神得以传承的承载实体,让讲述的故事能够带领每一个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地域特色的劳动场面和一个渡口的日常,是一个机巧的处理。鹰在高空游弋逡巡,风雨到来,——一个忙碌摆渡的场面,让一个家族的隐秘往事就此拉开大幕。写劳动场面看不出什么秘密,或曰一个场面可能并无什么秘密可言,但细究:直门达渡口刚开始的这个摆渡场面,因一场预料之中的大雨没有显出慌乱来,相反,是一种忙碌而秩序井然。小说真正的魅力和对文本价值的潜在价值追求,沉潜在了一个普通的忙碌场面里,对直本家族精神的表达和领会不需要摆脱生活本身而突然出现,像通天河的水“不舍昼夜”地流淌,才沉淀出直门达渡口的“魂”,才能显出直本家族的精神来,并成为直本家族一直的坚守。在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里,融入对“家风”的细致书写,让历史事件显出人情的味道,是阿琼小说《渡口魂》耐读的一个原因。
渡口,可能会因为社会的发展最终被废弃,家族的命运也会随时代风云变幻而浮沉,但以渡口为标志和荣耀的渡口之魂会融汇进渡口人的血液里,以渡口人的精神面貌出现在直本家族的记忆里,这是沉淀出来的种族记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藏地的一个存在。“渡口的人民心胸宽阔像大海,不管什么人,来到渡口就是客人,渡口能渡所有来来往往的客。”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传承在每一代人的意识深处,渡口人的心灵就让一种光辉笼罩,在面对渡口的历史时,这样的“渡口魂”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世间的真善美、假丑恶来。这是一个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所具备的“责任”,在对历史记忆的追述和复活过程中还原出人类情感世界中最可贵的占位来,将一个渡口在时代风云中的变迁所凝结成的精神内核析出,再让一个家族出场,以鲜活生动的家族日常将一种精神勾兑得血肉丰满,所有的事件和人物都在诺布的视域里次第上演,历史记忆复活的方式有了一个恰切的通道。
一个儿童的眼睛,很澄澈,很单纯,诺布在对世间世相的观看和评判也很澄澈单纯。根嘎作为一个仆人,追随主人进出的样子,“恭恭敬敬侧着身弯着腰,很像跟在他身后的那条大黄狗”,这样的人物评价和影响符合一个直本家族小少爷的“实情”,也符合一个渡口的“历史事实”。通过一个澄澈单纯的眼睛走进一个纷扰的历史现场,巧妙地开展故事的讲述,复活一个历史家族的隐秘历史,既为文本找到了一个恰切的入口,也很微妙地撤出了历史的“线头”,通天河奔流不息,渡口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遭废弃,但渡口魂会延续下来,储存在渡口人的记忆力,融汇进血液当中,成为“唐蕃古道”的一种精神传承。诺布形象的塑造很特别,没有一个世俗眼光里的锐利,或具备一种超凡的预见能力,而是一个普通的“直本少爷”,直门达渡口的人物和事件,都会很正常地被“看出”,不存在一个“他者”的比照以显示其独特性,而又能很真切地扯出直门达渡口历史的细致来。
直门达渡口历史和直本家族的隐秘往事,是小说《渡口魂》讲述的故事,这种将“人”与“事业”必然联系的手段面相上看不出什么关乎艺术的秘密手段,但细究起来,就能很自然地发现:灵魂存于肉身,现于“事业”。人的精神品质和对一种家族精神的信仰需要在对待事业的态度中验证出来,如此简单的事与理的关联逻辑,让渡口发生的事件具备讲述的必要,灵魂有了落实的载体,“黏附在皮船上的生存之道”通过“通天河上的摆渡”这一几代人的事务被传承了下来,直本家族的历史也在对渡口事务的处理上有了被讲述的必要。这种故事架构自然而不失机巧。
对话是一种古老的讲故事的方式和手段。一个家族的历史和家族的精神,若要被细致而精彩地得以呈现,牵扯到历史,又能关涉到当下和将来,直本老爷和孙子诺布这一人物关系的设置很有艺术。家族历史的讲述,让爷爷承担故事的内容,让“对话”成为故事出场的方式,精妙而贴切,语言又是人物形象丰满的最好手段。爷爷与孙子这一对人物关系的设置把过去和当下、将来,把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复杂而纷繁的故事层面置于了一个方便呈现的档口,并且能在任何一个场合都能有故事进展的可能,让事件从不同的内涵方面自然流出:在家庭琐事方面也能让故事展开丰富的一面。家族精神的一个源头:祖先罗本雍仲,这样一个不能出现在故事现场的历史人物,却能被“对话”引入到故事讲述的当场。对家族精神的信仰也从这样的“讲故事”得到肯定、赞扬和传承,诺布的成长也是在爷爷的故事中被家族的精神熏陶、浸染。家风的形成和传承让后来者有了一种天伦之乐般温馨的存在语境。也使现代时尚语境和物质消费潮流下的行为日常,即在“唐蕃古道”这一历史文化场域中,具备一种蘸满历史血脉的厚重感。
线性讲述与立体建构的搭建手段,让直门达渡口历史和直本家族的故事融合迂回。这是《渡口魂》能够具备历史讲述类小说厚重品质的前提。先在的是少爷诺布的成长史,在一个成长者的眼中,渡口的发展变化与周围人事的变迁,就是个人生命内容的更新和不断丰盈的过程。从日常摆渡到历史大事件在直门达渡口的在场,通过一个成长少年的澄澈的眼睛观出,然后形成一个家族未来的灵魂格局,成就一个未来渡口掌门人的价值观,同时将家庭内部的属于“情”的这一要素自然而巧妙地融汇到少爷生命的河流中。历史的现场与家庭伦理的内容一起充实一个少年的生命,事件和成长都能以一个必然的标准和方向发展,从待人接物到对“人”的辨认、社会潮流的把握,被佛教叙事场这个语境引向“善”。
浓郁的藏域风情和鲜艳的佛教文化氛围,让小说《渡口魂》有一种迷人的魅力。不是强烈的宗教气氛平添了的一份,也不是对一个雪域高原的“旅游手册”式的简单介绍强化的一种文本的特质,而是对藏民族,一个具备“宽厚”“仁爱之心”的藏民族日常生活的精彩书写,才使得小说故事与人物日常有了文化普及与交流、追求民族和谐团结的文化追求。房屋居室的陈设、家庭日常的安排,以及对待万物和人事的平常态度,心灵世界对自然的敬畏,精美地转换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细微表达,丰富而平实,日常而高尚。
以诺布继父为例。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处理,表面上看来很“粗暴”,——影响式的描写和“逻辑在先”般的人物定性,但这“简单粗暴”种融入的是对善恶和好坏的原初态度,是一个民族对“人”的最根本的认可标准,也符合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大家庭的历史事实,这种真实的力量恰好源于对这个人物角色的“粗暴”处理和叙述。小说中对直本家族的表述是以罗本雍仲作为家族之神展开的,讲述直本家族的历史是以回顾往事的形式切入到过去和一种家族精神的深处的,这种展开和深入的方式又是后代受到祖先的庇护的心理认可结构渲染开的,这种结构的重叠让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有了一种撼动心灵的力量,同时渗透着对自然规律和人事戒律的敬畏,一种恰切的层次融合继而形成流淌在事件之中的信仰使得地域文化和家族精神有了出场的意义。小说人物的设置与人物功能的考量,《渡口魂》做了世俗化和日常化处理,满足了家族故事的讲述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展示,巧妙而不露拙处。
在将家族精神和地域文化精神融入到家长里短的讲述中之外,时代大事件对直门达渡口的辐射,也是《渡口魂》丰富层次的一个呈现,从军阀混战、抗战等时代大事件都如“渡客”般从通天河上来往过。大事件的处理,在家族故事的讲述中是一个不好处理的要素,要么别的文本已经有过精彩地呈现,要么没有实际鲜活的样子可以承载,生硬地切入时代大事件的讲述可能会弄巧成拙。直门达渡口直接地参与过抗战物资的“摆渡”,但渡口这个“舞台”限制了场景的自由切换,所以直门达渡口一直是小说故事展开的“中心舞台”。怎么才能让时代里会沉淀为历史的内容自然地存在于文本中,又不失其该有的分量,作者以一场庆祝抗战胜利的联欢活动的形式让其盛大出场,——精彩而有力!这一安排化解了家庭叙事在时代氛围下大事件切入而不落于窠臼的难题。
切入民族之间交流往来的内容,从小说阅读的原初感觉体验,是作者的一个无意识或曰自然的书写,因为通天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直门达渡口本身的功能确定了“交流”的存在。雪域高原与内地的来往交流都经由通天河而通达彼此的目的地,通天河上的直门达渡口自然就成了民族交流融合之地,各族人民、不同信仰之间的人彼此间宽容、仁慈,成就了直门达渡口的繁荣昌盛,在抗战关键时刻“打破摆渡规矩”的反常事情,也是一个关于民族和大义的“壮举”!——《渡口魂》在切入到民族话题的书写时,除了对藏民族宗教日常修为的细致书写之外,一个高屋建瓴的处理出彩之处就是将日常宗教行为关涉为一个中国人该有的坚守下表达了出来,这样,日常的宗教概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个体的基本修为,而这样向善的日常凝聚成的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此梳理而来,《渡口魂》书写的是一个偏安西域的通天河上的一个家族的故事,承载的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分量,直本家族的“信仰”和坚守不单是掌管一个渡口的一个名叫直本的家族的“心灵史”,直本家族的隐秘往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雪域高原的生长史。这种对地域文化精神的挖掘,是一种“责任”性质的“记忆”,文化与精神通过这样的“记忆”才有传承下去的可能。而这正说明了小说《渡口魂》的现实意义,透过“直本家族”的故事,逼近了曾经的真实和一个民族的记忆,且通过自己的文字魔法,将故事与真实之间不可捉摸的模糊的缝隙呈现了出来,最终让“历史”得以再现。回到这样强烈的历史现场,每个读者的感觉一定是迷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