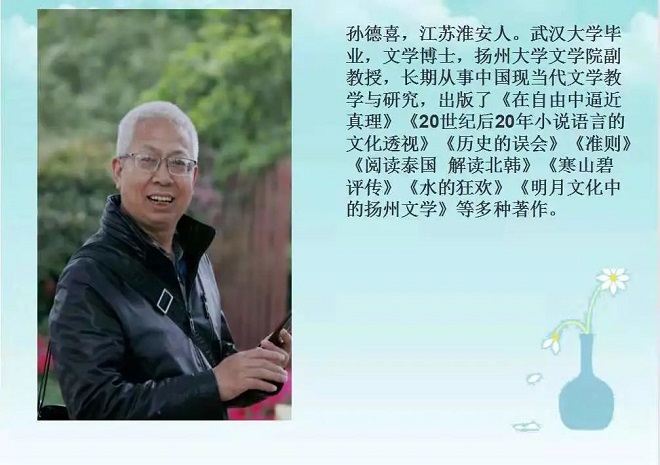“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这是阿来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云中记》第一句叙述。这句简单的叙述意味深长。此时的阿巴,作为一个祭师从山下往山上攀爬,去看望四年前那场大地震中遇难的云中村的人们。这是生者对死者的安抚和慰藉,也是生者与死者之间隐隐存在着的一种联系。因而阿巴的“攀爬”不仅是在山道上,而且还在生与死之间。阅读了阿来的这部小说,我觉得整个小说所叙述的就是阿巴的这一“攀爬”,而且围绕着他的这一“攀爬”,所展示的非常丰富的问题:活人与死人的关系、宗教与世俗的关系、苯教与佛教的关系以及出走与回归的关系。这些关系都由具体的事物上升到哲学的境界,进而对于人的存在提出了终极性的追问。
一、活着与死亡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一场特大地震。《云中记》中的瓦约乡云中村就位于地震震中地区。这场地震给云中村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村中的房屋也有很大的损毁,而且地震造成了巨大的地缝,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山体滑坡的地质隐患。因而,地震之后,政府在救治了云中村的幸存者之后,将他们搬迁到了移民村,于是云中村所在的地方便变成了废墟。但是,过了4年,阿巴不顾众人及其外甥仁钦的劝阻,坚持独自牵着两匹马回到已经成为废墟的云中村。阿巴认定自己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身份,他要肩起祭师的职责。祭师是当地原始宗教的神职人员,其职责一方面祭祀山神,“侍奉神灵”;另一方面“抚慰鬼魂”。
地震虽然过去了4年,但是在阿巴心目中,那些死去的云中村人的鬼魂仍在。他常常想:“那云中村活人都走光了,留下了那些亡魂,没人安慰,没有施食怎么办?没有人作法,他们被恶鬼欺负怎么办?”“死了的人也要人照顾啊。”因此,他要回到云中村去履行祭师的职责。阿巴不止一次对人说,活人由政府安置和照顾,死人由他来安抚。阿巴的人死鬼魂在的观念,是云中村人自古流传至今的信念。而这一信念来自于原始宗教。对此观念,有学者作过这样的描述:“如果一个人死了,人们还是相信,他和活着时一样依然有感觉能力,他的死只是简单地妨碍他同活人以一种认知得到的方式交流沟通,他的灵魂完全是有意识,依然具有人的全部渴望和欲求。”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仰,云中村那些遇难的人虽然在4年前那场地震中殒命,但是他们的鬼魂还在,仍然在村子里徘徊,游荡。这些鬼魂既然是人死后所变,那么还保存着活人的某些需求,需要吃食,需要精神安慰,但是又由于是鬼魂而不同于活人,因而不能相互照顾,互相安慰,更不能生产吃的东西,这就需要祭师来照顾。
不过,在云中村人信念中,鬼魂到了一定时期也会消失的。到了那时,就不需要活人来祭奠了,理由是鬼魂如果不消失,世界就会挤满了鬼魂,因此一些鬼魂必须消失,至于到底过多长时间消失,则没有人追问。其实,鬼魂究竟在多长时间后消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死后仍然会以鬼魂的形式存在。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照顾鬼魂是对死者的追思和悼念;第二,体现了对死者的一种终极关怀。
阿巴出身于祭师之家,而这个家庭给他的则是民间宗教的熏陶,这就使他相信,人死后,其灵魂仍然还在游荡,还需要照顾和安慰,但是他毕竟生活在新中国。自从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人们接受的基本上是唯物主义教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死亡主要是肉体的死亡,随着肉体的死亡,人的意识也将随之消失,所以,人死了不会变成鬼神,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所谓鬼神都是无稽之谈,是封建迷信。阿巴接受过学校教育,这就使他对鬼魂存在与否充满疑惑,甚至感到矛盾。他穿着法衣,戴着法帽,手摇法铃,敲着法鼓,在云中村的废墟中转悠,希望能遇见鬼魂,但是他一直没有遇到,即使他给鬼魂抛撒食物,也没有见到。然而,他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是祭师,就得履行职责,因而即使没有遇到鬼魂,也没有放弃。其实,鬼魂是不存在的,但是刚刚死去的人,与活着的人都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突然逝去,活着人一时从感情上不能接受,他们生前的种种生活情景还浮现在人们眼前,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另一方面,死者的突然离世,对生者的思想、感情、生活与工作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活着的人总会以各种方式追悼死者,缅怀死者。仁钦的母亲在地震中遇难了,阿巴在呼唤她时见到鸢尾花开了,便将鸢尾视为她的亡灵,仁钦后来将那株鸢尾带在身边,让死去的母亲与自己永远在一起。
阿巴在地震4年之后,不顾众人劝阻毅然回到云中村,当然不是简单地悼念和追思死者,而是对云中村的原始式的宗教信仰的传承,他以云中村传统文化特有的方式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阿巴照顾云中村的那些孤魂野鬼,实际上也是给活着的人的一种宽慰。让活人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与思念,放下沉重的悲痛,以便轻松地投入新的生活。
二、宗教与世俗
云中村的存在是和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小说对此作了这样的叙述:
一千多年前,一个生气勃勃的部落来到这里,部落首领对众子民说,我要带着你们停留在这里了,我要让我的子民不再四处漂泊。这些话,都是包含在山神颂词里的。云中村山神就是村后那座戴着冰雪帽子的山。山神就是当年率领部落来到此地的头领。他的名字叫作阿吾塔毗。
和许多藏民一样,云中村的村民一直自认为是雪山山神的子民,而且他们将自然神和祖先神话融合为一体,因而他们觉得自己的存在受到了阿吾塔毗的荫庇,所以也一直敬拜。然而,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现代文明的传入,云中村也和许多原生态文化的地域一样,不再是世外桃源,正在由原始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过渡。在云中村这里,虽然仍然保持着某些原始宗教信仰,但世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进而形成了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并存。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宗教与世俗并存,但是绝大多数地方的宗教都已经过改革而成为现代宗教,其意义在于给人以终极关怀,原始性的鬼魅大都已祛除。而云中村的宗教却仍然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原始特性,只是随着现代文明的传入,云中村的世俗化越来越突出。于是,宗教与世俗既并存,又隔阂,相互之间时常纠结着,但是由于宗教被纳入到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加以保护,所以宗教与世俗没有发生冲突。然而宗教与世俗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两种话语,而且这两种话语不时产生碰撞、交汇和对话。
阿巴与世俗语言的隔阂最初显现在他不明白自己拿到政府给他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经济补贴。他觉得自己祭祀自己村子的山神,是一个祭师的职责,与政府无关,可是政府还要给自己钱。有人认为他是“云中村人说的死脑筋”。阿巴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后来将政府给的钱送给了到远处上学的孩子们,因为这些孩子在阿巴看来都是“山神爷爷”的子孙。对于阿巴的举动,有个干部想利用这件事做宣传,要求阿巴说“感谢领导关心”之类的世俗之语。阿巴宁可保持沉默,也不将自己的语言世俗化。后来,他对外甥仁钦说:“没有山神,政府不会给我钱。给了我就是山神的钱,娃娃们都是阿吾塔毗的子孙。”更令阿巴黯然神伤的是,村里那些已经世俗化的人都说:“唉,阿巴你要是不提山神,就成了典型,到处演讲去了,能去好多地方!”外甥仁钦虽然也能够理解舅舅,但他身为干部,也只能以干部的身份对他说:“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外甥的话很得体,他的话也是出于世俗考虑,因为支持地震灾区难民的全国各地的人绝大多数也都是世俗之人。在地震发生前,当地一位副县长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要在云中村搞成旅游目的地,居然要求将云中村约定俗成的两个节日时间固定下来。而云中村的节日原本具有宗教意义,现在为了世俗的旅游和经济发展,搞起了所谓的“移风易俗”。民间的节日一旦被改变,其原有的宗教意义就可能被淘空,只剩下表演的形式。副县长要求云中村“改变观念”,出发点当然是为改善云中村的经济条件着想,但是越来越远离原始宗教。这种宗教与世俗的隔阂造成了彼此的阻隔,令阿巴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
令阿巴更伤感的是云中村的年轻人对于传统的信仰已经非常淡漠。云中村生长着花楸树,老辈人间曾经流传着熊因食用花楸树的浆果而醉倒的故事。阿巴虽然没有见过熊吃花楸树浆果而醉倒的事,但是他对这一传说深信不疑,然而,到年轻人那里居然不爱听,而且还“说这是胡说八道。”虽然阿巴与这些年轻人之间发生冲突,但是他与年轻人已经渐行渐远了。这使阿巴不断向内心退却。他只能在心里向山神倾诉,于是他爬到山上的神坛前,“仰望着雪山,责问过山神阿吾塔毗,怎么忍心把云中村从他的怀抱中推开。”他这是以责问的方式诉说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地震发生后,军方派来了救援直升飞机,“从来没有见过直升机的云中村人没有人认为是山神显灵了。连阿巴这个专门侍奉山神的人也没有觉得这是山神显灵了。”
生活在20—21世纪的阿巴不仅目睹到年轻人越来越远离祖宗传下来的宗教信仰,而且自己也常常陷入困惑当中。阿巴在与地质调查队的专家们相处中,听到专家们说了一些新名词,便联想到他曾经担任过发电员,他不由产生了疑惑,感到十分茫然:“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说不出全部世界了,我们云中村的语言怎么说不出新出现的事物了。”“他们好像说着自己的语言,其实已经不全是自己的语言。”这不仅仅是语言交流的障碍问题,更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意味着旧的时代的逝去,当科学渐渐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宗教也就很容易为世俗所取代。阿巴日益预感到:世俗化悄悄地侵蚀着云中村的原始宗教,使其产生崩塌的迹象,就像地震过后的裂隙,在不断地扩大,迟早都会滑落。
最终,云中村还是不可避免地滑落了。阿巴强烈地预感到这一天的到来。他觉得自己始终属于云中村,如果云中村不存在,那么作为祭师的他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选择了与云中村共存亡,最终随云中村而去。阿巴随云中村的消逝,也正是阿来以另一种方式为原始宗教的消失所唱的挽歌。
三、苯教与佛教
云中村人所信的是苯教。苯教是西藏地区最古老的宗教,现在虽然不如佛教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苯教与佛教产生过冲突,但是也能够和平共处。云中村人虽然信奉苯教,但是并不排斥佛教,而且佛教也没有歧视佛教。两者教义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一定程度上的沟通与联系。阿巴同云中村世世代代的人一样,一直信奉苯教。不过,由于阿巴是半路出家的“祭师”,对于苯教的鬼魂的认识还不准确与深刻,于是他到邻村的一位老祭师那里去请教。但是,阿巴所提的问题让老祭师生气了,老祭师将他当作佛教徒了。阿巴所问的是鬼魂是不是一直都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佛教与苯教的分水岭。在佛教看来,人死后灵魂是一直存在的,是要轮回转世的;而苯教则认为:“人死后,鬼会存在一段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先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但这些鬼会惊讶于自己的身体怎么变得如此轻盈,他们飘来飘去,又高兴又惶惑。习惯了沉重的皮身么!再后来,鬼就会明白自己已经死了,脱离了那个肉身了。慢慢地,他们就会被光化掉,被空气里的种种气味腐蚀掉,变成泥土。”祭师在向阿巴解释时显得非常肯定:“一种很细很细的灰白的泥土,也可以化成磷火,化成风。总而言之,一旦化作了这些东西,一个鬼就消失了。”苯教与佛教虽然对于人在死后的灵魂问题的认识不同,但是都在讨论人的存在的终极性问题,既关注人的死亡,又关注人的灵魂。而灵魂的存在又是与生密切联系的,不管灵魂是转世还是消失,在这两个宗教中都得到了关照,实际上也是对死者的一种深切的怀念,也可以说是死者活在生者的心中,于是死者的精神在生者这里得到了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藏人的信仰包含着虽死犹生的意义,人在死亡以后,并没有离开活着的人,是以另一种形态存在,即使死人的灵魂“被光化掉,被空气里的种种气味腐蚀掉,变成泥土”,但是仍然存在,并且就在活人的身边。
四、离开与回归
到现代社会,人的流动越来越频繁,而且流动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偏远的地区,人们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到外地去,也可能有外人来到这地方。当然,如果纯粹地自然地发展,那将是十分缓慢的。云中村最初确实迎来了水电站工程技术员,也开始有一些青年因读书或工作而外出离开。真正使云中村大规模迁离的正是2008年的那场汶川大地震。这次地震不仅摧毁了云中村的房屋院落围墙,而且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更为严重的是地震留下了一道大地裂缝,使云中村不再适宜居住,变得十分危险。于是政府对云中村这次地震的幸存者作了妥善安置,将重伤员送到大城市治疗,其他活着村民都被迁到了移民村。最先回归云中村的当然是阿巴,他的回归是作为祭师要祭奠亡魂,进而与云中村融为一体,不再离开。跟随阿巴回归云中村的还有他的外甥仁钦和云丹。仁钦回到村里来,最初是为了劝说阿巴离开云中村这个危险的区域,后来不仅看望了死去的母亲,将母亲幻化成的花朵带在身边,并且理解了舅舅的行为,于是在云中村的废墟上与舅舅道别,独自离开了这里,继续他的职务工作。仁钦虽然离开了云中村,但是他在与舅舅的对话和舅舅的祈祷与祝颂声中实现了精神上的回归。
云丹是阿巴的朋友。当他得知阿巴要回到云中村时,他表示理解,想通过低价售给阿巴两匹马以便给阿巴提供帮助。在马匹生意做好后,他们俩还在山上坐下相互“告诉”(将自己与对方分别以来所经历和了解的事情告诉对方)。阿巴回到云中村之后,云丹在云中村消失之前也回来了。他是送因地震而被截肢的央金回到云中村的。这一次的回归,云丹是从语言“切口”开始的,他从阿巴那里恢复了对于云中村独有语言的记忆。后来,云丹多次到山上来看望阿巴。就在云中村大限即将到来之时,云丹与阿巴作了一次煮茶长谈。他们这次所谈的主要是鬼魂看见的世界是不是我活着的人看到的一样。这个话题谈论的是生人与死人的区别,涉及到生前与死后的问题,其实质是原始宗教信仰的问题,是云中村的精神存在的问题。他们的谈论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这种谈话意义很大。从云丹来说,则是精神上的回归;对于阿巴而言,则是他最终选择与云中村一道消失的根源:他要通过自己的死亡去解开鬼魂所看到的世界之谜。
《云中记》还叙述了央金和中祥巴返回云中村之事。央金是云中村的姑娘,在汶川大地震中不幸失去了一条腿,于是被送到外地治疗,并且在安上假肢后学习舞蹈。就在阿巴回到云中村以后,央金也回来了。不过,她的这次回来最初是她所在的演出公司安排的。而演出公司的安排是想通过现场拍摄来煽情以扩大该公司的影响,目的显然是为了经济利益。但是,央金在演出过程中在阿巴的开路引导下,渐渐地脱离了公司的安排,真正实现了精神的回归。她在云中村的废墟上跳了舞。她所跳的舞虽然不是云中村的土风舞,但是她跳出了自己的“愤怒、惊恐”和“绝望的挣扎”,跳出了她的生命意志和回乡的复杂情感。同时,她还“梦呓一样”地告诉死去的父母与弟弟:自己回来了,并表示自己要回家了。当她回到曾经的家时,她控制不住内心的感伤进而晕倒。后来她由晕倒转而平静地睡着了。就在央金沉睡之际,阿巴做起了法事,告诉央金的三位死去的亲人,她回来了,阿巴的“告诉”并不仅仅是慰藉死者,更是改变了央金回归的意义:由被人安排的商业性的表演转变为“看”死者。经过沉睡之后,央金像是变了一个人,“安安静静,一声不吭”,尤其是她的眼睛“很安静”。她的这种状况表明她已达到精神上的回归,她的灵魂得到了云中村的安妥。后来,央金虽然还是离开了云中村,但是她的精神还是与云中村永远联系着,同时也是生者与死者灵魂的融合。
中祥巴是老祥巴的二儿子。老祥巴生了三个儿子,他们一家在云中村声誉不好,从老祥巴到他的三个儿子都不讨村里人喜欢。他们作为云中村的异类而存在,所以他的三个儿子也就分别叫“大祥巴”“中祥巴”和“小祥巴”。后来,祥巴的几个儿子外出闯荡,混出了模样,便回到了云中村盖起了高大房屋。地震发生后,祥巴的儿子们也都离开了云中村。过了4年,中祥巴又回到了云中村,盖了全村最气派的房子以炫耀。不过,后来遇到了地震,云中村成为地质灾害危险区,中祥巴不得不与村里人一样离开云中村。不过,后来中祥巴再次回到了云中村。中祥巴这次是坐热气球回来的。但他既不是缅怀死去的云中村人,也不是追忆云中村的历史,而是为他的热气球旅游开发作准备的。他的行为表面是一种回归,实际上他是在将云中村视为旅游资源来开发,还具有化苦难为消费的意味,是对死去人们的大不敬,甚至是亵渎。阿巴并不知道中祥巴回来的目的,只是觉得回来的方式有些古怪,但是他转念一想:“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来,都说明他们没有忘记云中村”。这么一想,阿巴“感到很欣慰了。”好在祥巴受到了仁钦的批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阿巴则将中祥巴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祥巴家的那些死人”,在死者与活人建立了联系。
五、死去与永存
阿巴最终还是选择随云中村一道逝去。地震过后,云中村便成为地质灾害区。地震留下了裂缝在渐渐的扩大,云中村便面临着崩塌和坠落的危险。一灵之后,没有离开,而是留了下来。他在与外甥仁钦作了长谈,取得了对旦发生崩塌和坠落,云中村将不复存在。阿巴对此是很清楚的。他重回云中村,在安慰了亡魂,送走好朋友云丹之后,静等着大限来临。在与外甥仁钦的交谈中,阿巴谈了他的生死观:他将和云中村一道坠落,“不是死,是消失。进而世界一起消失。”阿巴对于生死的这种看法表明,人是不会死亡的,只是“消失”,也就是说活着的人不会再看到他,而死去的他将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而且,阿巴还认为,自己是和云中村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云中村的“消失”,他也将“消失”,所以他的死实际上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只是人们不再看到而已,因而他告诉仁钦,不必感到悲伤,于是他要仁钦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穿上他的祭师法衣,用他的法器为他送行。于是,仁钦为其举行了送行仪式。在送行仪式上,仁钦按照阿巴的提示给他呼告:“祖宗阿吾塔毗,保护神阿吾塔毗,收下你子孙的魂灵吧!”“给他指回去的路!”“给他指光明的路!”“让他看见你的灵光!”“飞升了!”“光芒啊!”在外甥的呼告声中,阿巴脸上“没有一丝悲伤的迹象”,而且“在闪闪发光”。此时的仁钦“心里似乎也不再只是充满悲伤,自有一种庄严感在心中升起。”从这个仪式来看,在即将逝去的云中村这里,死亡便是将魂灵交给了祖宗或者保护神,是回到祖宗那里去,因而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回归,那么生命得到了永存,所以仪式充满了庄严。其中既有对生命的敬畏,也有对死亡的深刻认识。
阿来虽然是藏族作家,而且一直书写藏区藏人和藏事,但是他“对宗教有着非常强烈的质疑”。尽管这并不代表阿来反对宗教,然而他还是与宗教来开了一定的距离。在《云中记》中,阿来所书写的云中村当然不可避免地涉及苯教和佛教,但是他并没有沉浸在宗教当中,也没有要将读者带入宗教世界,他的书写目的是在探讨人的生与死的问题,在宗教的外壳下包蕴着的是哲学的意义。而且,这还和原始文化关系密切,随着现代文明的浸入,原生态的文化也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乃至消逝。对此,阿来看得很清楚:“消逝的一切终将消逝,个体的生命如此,个人生命聚集起来的族群如此,由族群而产生的文化传统也是如此,……”云中村最终还是消逝了,随其消逝的还有阿巴与云中村的原生态文化。然而,几乎就在云中村与阿巴逝去的同时,就在仁钦对舅舅逝去表现出理解的同时,仁钦的女友提出了结婚,而结婚则是意味着新的生命即将诞生,这大概就是阿来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他对生与死的认识,从而也暗示着阿巴“攀爬”于生与死之间的意义。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