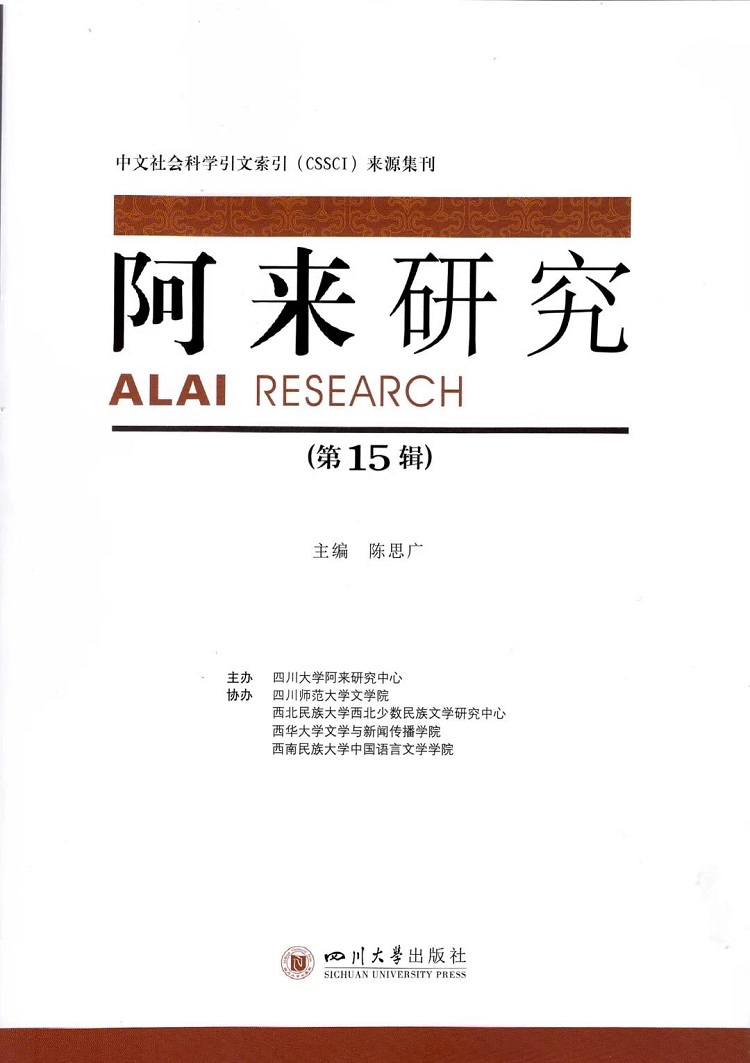
民族的、地方的历史具有永恒的文学魅力,历史叙事是现代藏地汉语小说的重要题材。青海藏族女作家梅卓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等,均是民族历史题材。《太阳部落》讲述的是伊扎部落、沃赛部落与当地县府势力的恩怨;《月亮营地》主要讲述月亮营地、章代部落等与马家兵团的抗争;《神授•魔岭记》讲述的则是格萨尔王后裔东查仓部落神授艺人阿旺罗罗的成长史和格萨尔史诗藏民族记忆的传承。与其他藏族作家一样,梅卓的历史叙事并没有规避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重要事件、重要场面和重要人物,但明显不同的是,她在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更加注重抒情表达,在历史叙事的主线中时常缀串地方景观、民族文化、人物心理、民间歌谣等,用富于诗性特质的语言呈现细节化的片段,有着显著的抒情特征。从早期创作到当下实践,梅卓形成了一以贯之的美学风格,于热烈奔放之中诗意流淌,可称为民族历史叙事文学中的“诗化小说”,这为现代小说进行历史叙事提供了别样的路径。
一、从田园到香巴拉:诗化的地理景观
梅卓长篇小说的诗意抒情气质首先表现为她在进行历史叙事的同时,不惜笔墨细致勾画藏地独特的地理景观。对自然山川风物的描写渲染,对特定地理空间的关注与强调,几乎出现在小说的每一个章节中,其中不少章节直接以地方命名,如“青稞地”“亚塞仓城堡”“酒馆”等。天空、太阳、草原、山峦、森林、雪域、河流、湖泊等自然景观,以及这些地理空间中的人与自然的融合、部落成员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民族历史的宏大场域中开阔舒展,摇曳生姿。
一是作为藏民族丰饶宁静的田园。在《太阳部落》中,作者以桑丹卓玛的视角描写了伊扎这个地方的地理景观,桑丹卓玛应千户夫人耶喜的召唤,走向亚塞仓城堡,一路所见的是“一派丰腴而甜美的秋之原野”,亚塞仓城堡 “四周是层层叠叠的白杨,整齐、挺拔,在风中翻动阳光的树叶发出神秘而森严的低语”,接着写了城堡的布局,四个大院、高高的角楼、开阔的院子、楼前的花草、门楣上的雕花,等等。傍晚时分,洛桑达吉结束劳作回家,“夕阳栖在山巅,亚浪仓沉浸在桔红色的夕照之中。几处炊烟,召唤着各自的家人”,夕阳的余晖刚好洒在西厢房。小说又详细描写了平民尕金的院子,依然是一片妩媚、丰饶的景象,尽管对于洛桑达吉来说这里并非他理想中的家。《月亮营地》的开篇,作者并不急于展开故事,而是大手笔地展示“月亮营地”这一地理空间:艳阳高照。炫目的太阳使大地更加容易进入黑夜。沉浸在黑夜里的山山水水在月亮的清辉中格外宁静、安详,这一方自由的集散地因此被称作月亮营地,人们还以月亮的名字命名了这里的山和水:达日神山和达措神湖。达日神山屹立在北方,山巅终年白雪皑皑,山下的松树和杨树已经绿了,雄鹰在群山之间自由地飞翔。达措神湖紧紧依傍在神山东侧,湖面已经冰消雪融,碧蓝深沉的湖水清波荡漾,仿佛是镶嵌在大草原上的一颗碧玉宝珠……春天的气息从达日神山的南麓开始弥漫。山脚原先光秃的杨树枝重新发芽、变绿,松树则退去白雪素装,绽露苍苍翠色。山下已是一片蓊碧,而山腰的草坡也开始召唤牧人和羊群了。再过一个月,牧人们就得带着家当、帐篷,赶上羊群转场,把家庭搬到深山里去,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季。
月亮营地这一理想的田园,有太阳普照,有月光沐浴,有神山圣水的滋养与护佑,雄鹰翱翔,草木青葱,牧人和羊群散落其间,如诗如画。在《神授•魔岭记》中,也有对东查仓夏季牧场的细致描写:“远远望去,一座嶙峋巍峨的石山下,大片牧场正呈现出夏天旺盛的生命力,绿油油的牧草绵延到天边,各种野花点缀其间,吐露着淡淡的芬芳。白色的羊群犹如蓝天上投影下来的一团团白云,柔和地飘荡在青草之间,而黑色的牦牛群则像一座座钢铁战士,守候着青草的家园。”成长中的阿旺罗罗一路所见风光旖旎,在史诗的演唱中展现了雪域之邦的山水立体图。作者打破现实、历史与神话的界限,让阿旺罗罗通过神奇的魔戒看到格萨尔王妃阿达拉姆生机勃勃的千年鹿城:“高墙上的鹿角倒影投射下来,阳光下的草地碧绿青翠,铺排在城堡四周,清风拂来,天地间一派静谧。放眼望去,成群结队的白唇鹿游走在城堡之外广袤的草场上,它们有的悠闲自在地啃食着青草,有的神态安详地回望着他。远处,是一群黑色的野牦牛,长可及地的披毛在阳光中熠熠生辉。”千年鹿城表达着丰富的过往世界,那是一个壮丽时代的富饶的家园图景。可见,梅卓的这些地理景观描写,展现出浓郁的田园牧歌色彩。
二是作为理想精神的桃花源或香巴拉。梅卓在小说中塑造了多处能够容纳人们爱情与自由的伊甸园。比如《太阳部落》中桑丹卓玛与洛桑达吉的幽会之地,玛冬玛河流环绕,玛冬玛湖水碧绿,长长的密林、隐蔽的山洞、绵绵的雨、弯弯的红月亮……作者用一系列唯美的自然意象进行渲染,显得情意绵绵。幽会之后,“两人看到了那一面碧莹莹的湖水。玛冬玛湖,清粼粼的玛冬玛,波光柔柔的玛冬玛,情意撩人的玛冬玛”。在这里,玛冬玛湖和密林中的山洞就是美丽爱情的伊甸园,那是一个传说中的世界。在《月亮营地》中,月亮营地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集散地,营地上的“快乐酒馆”是自由的象征,是青年男女聚会之所,斗士格斗之所,也是浪漫爱情的发生之地,阿•格旺与尼罗、茜达与陌生人(云丹嘉措)之间的相遇相爱都在此发生。《太阳部落》中对衮哇塘这一地理空间的塑造更具有理想桃花源或香巴拉的色彩。“衮哇塘,在黄昏到来之际,显得非常宁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村落,沿山坡而下,每一户人家的庄廓都结实而美观,与别的村落有所不同的是,衮哇塘的外围是一垛围起整个村落的高墙,就仿佛衮哇塘本身就是一座庄廓,那里面包含着周密和谐的、完整不可分的内在意义。”在外人眼中,衮哇塘是土匪窝,其实那是一个类似梁山泊的地方,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世界,那里的人们热情友好,到处传说着“孜孜森杰”的英雄故事。
三是富于宗教色彩的灵魂净土。在藏地文学文化中,地理景观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神山圣水,有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常常意味着对人的拯救、对灵魂的洗礼。《太阳部落》中的玛冬玛山成为香萨的密修之地,人们修峨堡、煨桑烟,祭祀阿妈君日神山。雪玛被千户次子才扎强暴之后,那发出缥缈的流水声的贡尕河就意味着拯救:“雪玛浸入光洁的水中沐浴……到河里洗得干干净净,她不是和从前一样干净么?”在此,贡尕河之于雪玛,充分显示了河流的“救赎”意义。《月亮营地》中也有达日神山和达措圣湖,小说开篇就详细描写了祭祀达日神山的盛会。《神授•魔岭记》中的珠姆泉是格萨尔王妃森姜珠姆的寄魂泉,阿尼玛卿是格萨尔王的寄魂山。小说从多个视角展示了阿尼玛卿神山的壮丽景观,比如阿旺罗罗在金雕上俯视阿尼玛卿神山千年冰川起伏跌宕,冰隙裂缝深不可测;从圆光镜中看到阿尼玛卿神山雪峰闪耀,牧草丰美,是格萨尔英雄的诞生之地。此外,还有圣湖措琼诺日依则,周边有三百六十个名叫昂唯雪当的小湖泊,春秋时节,天鹅会在这里舞蹈,人们还有祭祀圣湖的仪式。阿旺罗罗借助神杖,看到圣湖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闸宝大师引导阿旺罗罗以圣湖为镜,面对圣湖观想,天人合一,观大千世界,最终从自然中获得灵感,以圣湖为镜,修得心圆光,完成了他圆光—自圆光—心圆光的修习,这是他成为神授艺人至关重要的一步。
梅卓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独特的藏地山水地理景观,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对读者来说都具有民族地域风情的诱惑与震撼,有别于其他地方作家的风景书写,从小说的艺术效果来说,明显放缓了历史叙事的节奏,增添了小说文本的诗意抒情之美。
二、英雄与浪游者:诗化的人物形象
梅卓在长篇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对英雄和浪游者形象的着力塑造充分体现了她历史叙事中的诗意抒情气质。
一是英雄的失落与诞生、爱恨与孤独。《太阳部落》《月亮营地》中首先叙述的就是老一代英雄的落幕。《太阳部落》中的伊扎部落老千户及其夫人正面临死亡,老千户回想着年轻时的美好往事,他抱着妻子冰凉的身体,慢慢松开紧紧攥了一生的双手,面色灰暗,把那枚从18岁就戴着的代代相传的太阳石戒指摘下来,却没有等到继承者嘉措的到来,“千户举着那枚象征着无上权利的太阳石戒指,一个人醒在这漫长、炎热而枯燥无味的中午”。一代英雄凋零,太阳石戒指的神秘光芒正在黯淡,预示着伊扎部落将有劫难。《月亮营地》中的阿•格旺出场时已经五十多岁,他看到儿子甲桑在祭山盛会口剑穿刺比赛中获得第一,也在回想自己的年轻岁月,他曾经也像甲桑一样英勇健美,是他“带领众人创建了这座像月亮一般美丽的营地。在这里,他辉煌过;他拥有所有的权利;他是这营地的无冕之王”。但他当年离开了所钟情的尼罗,入赘营地最富有的阿家,又续娶年轻漂亮的寡妇娜波,他在一夜之间忽然觉得自己老了,老得再也不能目睹穿刺口剑的仪式,只能全神贯注地辨认青年们吆喝声中甲桑那长长的、充满动感的呐喊声。
伴随着老英雄的落幕,年轻一代英雄迅速成长,横空出世。甲桑从16岁开始就在口剑穿刺比赛中年年夺冠,又在与纨绔子弟阿•文布巴的胆量比赛中赢得稀有的猎枪,并一枪击毙如同英雄一样光彩夺目、高傲孤独的雪豹,成为月亮营地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拥有镇子上最好的快马和最好的猎犬。但他却因与阿•吉的恋爱受阻而失落,怨恨阿•格旺,成为孤独的行者,被人们称作“狼人”。后来又因错杀同父异母的妹妹阿•玛姜而忏悔,把自己放逐到营地之外镌刻玛尼石以赎罪,“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他似乎打算就这么度过一辈子,平静地、跟别人和营地毫不相干地度过余生”,像孤狼一样活着。当甲桑得知章代·乔是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那猎人的感觉全部苏醒,“胯下的骏马犹如张开了无形但却有力的翅膀,秋天成熟的草场在蹄下仿佛绿色的浮云般一掠而过”。他重新焕发英雄的风姿,冲进重围解救章代•乔,再一次成为部落的英雄。“他是这群英雄中的英雄,是雄鹰之王,是月亮营地的斗士,是笑傲沙场的胜利之旗”⑮,甲桑历尽沧桑之后,看到了生存的意义。后来因遭到敌人的伏击,他为解救被俘的妇女和孩子,主动暴露自己,要求交换人质,身陷敌营壮烈战死。甲桑死了,少年章代•乔又加入未来的战斗,新的英雄正在成长。此外,《神授•魔岭记》主要就是演唱格萨尔王的英雄事迹,其中的英雄崇拜就无需赘述了。
二是浪游者与拯救者形象。《太阳部落》里的嘉措就是一个出走者。他本是伊扎部落千户夫妇的独生子,是千户爵位的继承者,但他从8岁开始就疯狂地喜欢骑马,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包括权力、财产和女人。当父亲老千户即将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冬季牧场骑马,“十七岁的少年只懂得骑马游戏的快乐,当他转过他欢乐的面庞,忽然发现属于他的一切都变了模样”,表兄索白通过贿赂省府官员而受封千户爵位,太阳石戒指到了索白手上,嘉措失去了一切,土地、城堡和家园。一无所有的嘉措在索白大办婚礼的喧噪声中走出千户城堡。小说反复写到嘉措从千户城堡出走的姿态,“两袖清风”“潇洒”,决绝而自由,开始了他新一轮孤独、痛苦的漫游。桑丹卓玛的父亲收留了憔悴的少年嘉措,并把漂亮的女儿许给他。但嘉措并不属于这里的家庭,他常常独自出门,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桑丹卓玛并不懂得丈夫嘉措的内心世界,嘉措注定会继续出走。在晴朗的天气,嘉措吹着口哨,牵着白马雪狮,带着护身盒,走出桑丹卓玛的家,离开了伊扎。从此嘉措就更加成为影踪漂浮的浪游者,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何处,他时常出现在女儿香萨的深切怀念中,出现在桑丹卓玛偶尔想起的时刻。其实,嘉措去了一个叫“衮哇塘”的地方,在那里重建起属于自己的江湖世界,他突然带队抢劫在伊扎部落为非作歹的士兵的枪支弹药,呼啸而去,后来又抢劫了县府军马。他其实很爱妻子桑丹卓玛,“在异乡异地、在梦中、在心里都曾经无数次地呼唤”妻子的爱称“桑丹”,也曾突然回到家让妻子跟他一起到衮哇塘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桑丹卓玛因有身孕而拒绝前往。小说对嘉措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从侧面完成的,从不同人物的视角刻画嘉措。在女儿香萨的心目中,父亲嘉措高大英俊,慓悍异常,是独一无二的父亲,偶尔听到有关父亲的壮举和善行,把劫掠的财物分给衮哇塘的穷人;在妻子桑丹卓玛的眼中,那是一个行踪漂浮、无法把握的嘉措;在衮哇塘,人人传说的嘉措是神一样的存在,“衮哇塘,因为有了‘汉子嘉措’,就成为穷人向往的天堂,因为有了‘孜孜森杰’,那里就成了富人谈虎色变的地狱……一提起孜孜森杰,简直无人不晓,无人不知,在妇女们的眼中,他是春天的绿荫,而在男子们的眼中,他则是升上天空的旗帜”。当小说写到衮哇塘的时候,又讲述了嘉措当年出走的潇洒姿态,嘉措的抉择非同一般,面对失去的一切,他不是争夺,不是复仇,而是决绝而潇洒地离去。他的屡次出走,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梦想,他要在另一个地方重建属于自己的江湖。他做到了, 他成了衮哇塘的英雄,江湖中到处有着他的传说。到了小说的末尾,嘉措又作为部落的希望、拯救者而存在,伊扎部落和沃赛部落在县府严总兵的攻击下被洗劫,阿琼带着太阳石戒指寻找父亲嘉措。“这枚黯淡了多年的太阳石戒指,忽然慢慢地放射出逼人的光芒,它与阿琼胸前的风马一样,周围散发着灼热的火焰,那仿佛指着一个方向,火焰的方向指向远方。”那就是衮哇塘的方向。小说这一节的标题就叫“寻找香巴拉”,作为整篇小说的结局,象征意味明显,衮哇塘是公平、自由之所在,是有别于伊扎的一个理想的境地。
此外,《月亮营地》中的章代公子云丹嘉措也是一个浪游者。云丹嘉措是章代头人的次子,因有哥哥桑科协助父亲管理部落事务,他在年少时云游各地,四海为家,整日流连于舞池酒海,对父亲和哥哥的境况一无所知,对部落的危机也毫无感觉。直到父亲病逝,哥哥在战斗中被俘客死异乡,敌军压境,整个部落危在旦夕,所有的责任和义务都来到云丹嘉措的眼前,他成了唯一能挽救章代的人,他迅速崛起,成立自卫组织,到月亮营地寻求帮助,成为部落的拯救者。
在诸多历史小说中,英雄人物一般不会缺席,但大多数作品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主要注重的是其建功立业的丰功伟绩,注重的是“史”的建构和开疆拓土的格局,而少了他们作为“人”的烟火气息和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梅卓历史小说中的传奇英雄与浪游者形象有着侠骨柔情,他们既是部落的开拓者、守护者,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有着丰富饱满的爱恨情仇、失落孤独、潇洒浪漫,在历史严肃、冷峻、残酷的外壳下,增添了诗意的温润与柔软。当然,这与藏地游牧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浪漫气质密切相关。
三、青春与爱情的创伤:诗化的悲剧氛围
梅卓的长篇历史小说对故事情节的把握有独到之处,她并不急于讲述故事,也不刻意制造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在叙事的同时,荡开一笔,让情绪铺展,形成张弛有度的节奏,这是一种诗意的蔓延。她讲述的部落历史变迁过程,交织着密集纠缠的爱情,其中人物多数是少男少女;她以优美的笔调写出了他们青春的快乐与感伤,写出了他们爱情不幸的创伤经历,有着浓烈的悲剧意识。
在《太阳部落》中,青年男女爱情的纠葛十分绵密,几乎每个人物都坠入了难以挣脱的情网,显得深情绵邈。桑丹卓玛与洛桑达吉幽会,在雨中,在隐秘山洞激情缠绵,“洞外,是缠绵的雨,是雨的私语,是抒情歌曲最后那声悠悠的拖音”,“她是怎样出现的?婀娜的身上系着飘逸的紫红腰带,长长的辫子,哀伤的面孔,倔强美丽的眼睛,青春的芳唇,她出现在明明的月光中,还是婆娑的风里”,小说对他们的幽会有着大篇幅抒情性描写。离别使得洛桑达吉在桑丹卓玛的心中变得更加完美无缺,具有某种超出常人的理想气质,成为一种精神。当他们久别重逢,因为误听桑吉卓玛与索白相好的传言,洛桑达吉赌气离开。洛桑达吉病逝之后,桑丹卓玛把对方送给她的镯子碾成粉末,随风撒进秋天的玛冬玛河。这一段爱情,就是一首缠绵悱恻、动人心魄的诗篇。
桑丹卓玛的女儿香萨与阿莽青梅竹马,阿莽是香萨的崇拜者,他一直保存着香萨的头发。后来阿莽被送进衮巴寺做了小沙弥,重逢时,他们已经长成少男少女,身着袈裟的阿莽想把自己心爱的白马送给香萨,香萨羞答答地走开了,阿莽痴痴相望,怅然若失,“一直看着香萨走远,他望着她的背影,那纤细的、散发着灿烂阳光的背影,此时此刻,是那么让他留恋,他留恋她的芬芳气息,还有她那轻烟似的脚步”。在朦胧情感的驱使下,阿莽向父亲索白提出不可思议的还俗的请求,竟然获得了许可。但香萨的好友雪玛被才扎强暴,香萨误以为是阿莽干的。阿莽前去求亲被拒,香萨摔碎瓷瓶的声音扎在阿莽的心里,无辜、失落、绝望的少年阿莽骑着白马雪狮奔走在雨中,奔上山岗,跃下悬崖而死。后来,香萨来到阿莽的坟前,割下一把头发和一截小指埋在泥土里,以此陪伴阿莽,然后进山密修。这里明显有着汪曾祺《受戒》的味道,但其中的悲剧氛围更加浓烈。
雪玛与夏仲益西也是青梅竹马的玩伴,他们时常在蓝天、白云、阳光下嬉戏,夏仲益西对雪玛十分倾慕。他在山坡上吹着鹰骨笛,曲子名叫迎新娘,雪玛唱着歌。他们手拉着手,并排躺在夜空下,讲着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但夏仲益西的母亲要他娶丹增才巴老爷的千金,雪玛又遭遇才扎强暴,夏仲益西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家。最后,雪玛疯了,“她那张姣好的脸上早已沾满了一层层的污垢,嘴里那两排曾经非常美丽的牙齿,现在遗失得干干净净,她就那样张着黑洞洞的嘴巴,朝着喇嘛们无声地笑着”。她把老喇嘛当作英俊青年夏仲益西,千娇百媚地唱着被当作禁忌的拉伊情歌。这又有着《红楼梦》宝黛爱情的影子了。
此外,还有索白对桑丹卓玛的情意,她是他渴望一生的女人;完德扎西与妻子措毛最后的缠绵;千户夫人耶喜曾经被埋葬的爱情,她把对理想情郎的爱意投射到仆人完德扎西身上,完德扎西死后,耶喜落水可以看作一次未完成的殉情;阿琼与沃赛头人嘎嘎在赛马会上一见钟情,但因为部落之间的恩怨,母亲桑丹卓玛拒绝了嘎嘎的求婚,甚至出现了抢婚情节等。可见《太阳部落》中的爱情悲剧十分密集,它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爱情之书。
《月亮营地》也交织着爱情悲剧。阿•格旺与尼罗的爱情就是典型。阿•格旺入赘阿府,成为月亮营地的首富,痴情的尼罗就像祥林嫂一样悔恨埋怨自己命不好,不能给他一个姓氏和一个大院。她不愿意原谅他,但他们又相互牵挂。尼罗心中的阿•格旺永远年轻,骑着白马像一阵旋风,她死后的灵魂寄托到阿•格旺家的白尾牦牛身上;阿·格旺时常在梦中回想他们曾经的岁月,他待在牛棚里与白尾牦牛对话,反复倾诉、忏悔,啃食手指,甚至不顾世俗的眼光,请喇嘛为尼罗诵经。他们的爱情悲剧从青春演绎到白头,让人叹惋。
甲桑与阿•吉相互钟情,阿•吉是阿•格旺的继女,尼罗曾经去向阿•格旺替甲桑求婚被拒,阿•吉被远嫁给有权有势的章代部落头人的大少爷,做了章代夫人,“甲桑从此不再关心自己的婚事,一头扎进营地之外的荒山野林,把所有的兴趣转移到打猎中去”,成了最优秀的猎人。由于章代部落面临危机,离别十年的阿•吉又回到月亮营地。甲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报之以冷漠,但他又时常深夜无眠。当阿•吉再次前来请求甲桑营救儿子乔的时候,“漫长的噩梦,经过时光淘洗的痛苦,就像一颗在夜里带着闪亮尾巴的星星,倏忽滑过甲桑的头顶”。甲桑营救乔凯旋,阿•吉在帐篷守候,彼此钟情彼此等待的年轻人紧紧相拥,爱情愈来愈美,愈来愈真。但好景不长,最后甲桑战死沙场。一段穿越时光的爱恋,被卷在部落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
在这条主线之中,作者还穿插了阿•玛姜与甲桑的情感纠葛。阿•玛姜是阿•吉的妹妹,因为甲桑从阿府牵走白尾牦牛,又被一群蒙面人围困,他误以为是阿•格旺在耍花招,对阿•格旺仇恨到了极点,狂怒地冲进阿府,与阿•格旺对峙,甲桑的腰刀击中了扑上前来保护父亲的阿•玛姜,这时,阿•格旺道出实情。原来阿•玛姜与甲桑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俩并不知情,并且阿•玛姜正在暗恋着甲桑,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死在心上人的刀下。这一段插入的情节,增加了不可避免的伦理悲剧,既有中国传统小说悲剧模式的痕迹,也有西方文学中的悲剧之美,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青春与爱情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梅卓在历史叙事中融入众多青春男女的爱情纠缠,以大幅描写营造悲剧氛围,强化了作品的诗化美学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长时段的遮蔽与压抑,作家们纷纷聚焦作为“人”的恋爱与情欲,一时涌现出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低俗、粗糙的宣泄,而同时代的梅卓用纯净的语言、优美的意象,谱写了一曲曲青春与爱情的悲歌,即便是对情欲的描写也是浪漫唯美的,如同绸缎般丝滑而富有光泽。
余论
梅卓长篇小说的诗化风格除了表现在上述地理景观、人物形象、悲剧氛围等层面之外,还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对葬礼、婚礼、祭祀等民族文化习俗的呈现,对辫套、唐卡、圆光镜等民族特色器物的展示,索白、章子文、守塔者等人物内心的独白抒情,对情歌、民歌、史诗等歌谣段落的穿插引用,以及众多穿越现实、梦境、历史、神话的如梦似幻的片段描绘,不一而足。总的来说,梅卓擅于运用“越轨的笔致”,通过景观、人物、悲剧等元素,在历史叙事中诗意抒情,使作品在回肠荡气中散发着诗性气质,大气而隽永。
梅卓长篇小说的这种美学风格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地方性。富有特色的“地方”是作家作品风格形成的土壤,梅卓是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青藏高原是她文学的故乡。文学常常得“江山之助”,青海本身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梅卓书写的自然原型,小说中的“伊扎”“月亮营地”“东查仓”等地理空间均有着她原乡的影子,天空、草原、山峦、湖泊是构成这些地理空间的重要元素,这里是英雄的诞生地,也是骑士的疆场,因此就有了浪漫、自由、奔放的人物及其精神。二是民族性。藏民族特色文化是梅卓长篇小说生成的重要基因,这使得其作品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风景画”之外,呈现出具有浓郁西部色彩的“风俗画”“风情画”,以及宗教的神性色彩,比如天葬、祭祀、赛马会等。西部游牧民族的流动性也使得“流寓色彩”成为西部文学的一个 重要美学特征,梅卓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三是女性。女性的细腻、温柔、纯真,使得梅卓的长篇历史小说呈现出诸多异于男性作家的历史小说的特质。由女性特质延伸而来的孩童视角也是一大特点,比如《太阳部落》中,以童年香萨的眼光看待成人世界,看待父亲嘉措,看待母亲与情人的约会;《月亮营地》中着力刻画章代•乔的各种怪异言行及其与甲桑的相处等;《神授•魔岭记》是作者献给爱女的童书,主人公阿旺罗罗13岁,他有一个神通广大的保护神兼同伴的角色扎拉。孩童的叙述视角无疑增加小说文本的诗化色彩。四是与梅卓多种文体的尝试密切相关。除小说之外,梅卓还写有大量的散文诗和散文,出版有《梅卓散文诗选》等,其中不少篇目的风格与小说中的描写类似,这就形成了小说、诗歌、散文之间的文体渗透。一个作家的风格是在不断的选择、锤炼与融合中形成的。
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诗化小说,大多数是一种宁静的牧歌情调,如废名的《桥》、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等。相较而言,梅卓的长篇历史小说既走出了女性作家容易流入的纤弱,也走出了男性作家常有的刚硬,是婉约与豪放的圆融,大气磅礴而又缠绵悱恻,形成了在宏大历史叙事中诗意抒情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女性作家驾驭历史题材的独特性,也为现代以来的诗化小说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蒋林欣,女,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当代文坛》特约编辑,四川李劼人研究学会会员,四川省写作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在《社会科学研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江西社会科学》等CISSCI来源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国家报刊发表文艺评论多篇。主持教育部课题2项,省厅级课题4项,参与课题5项。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