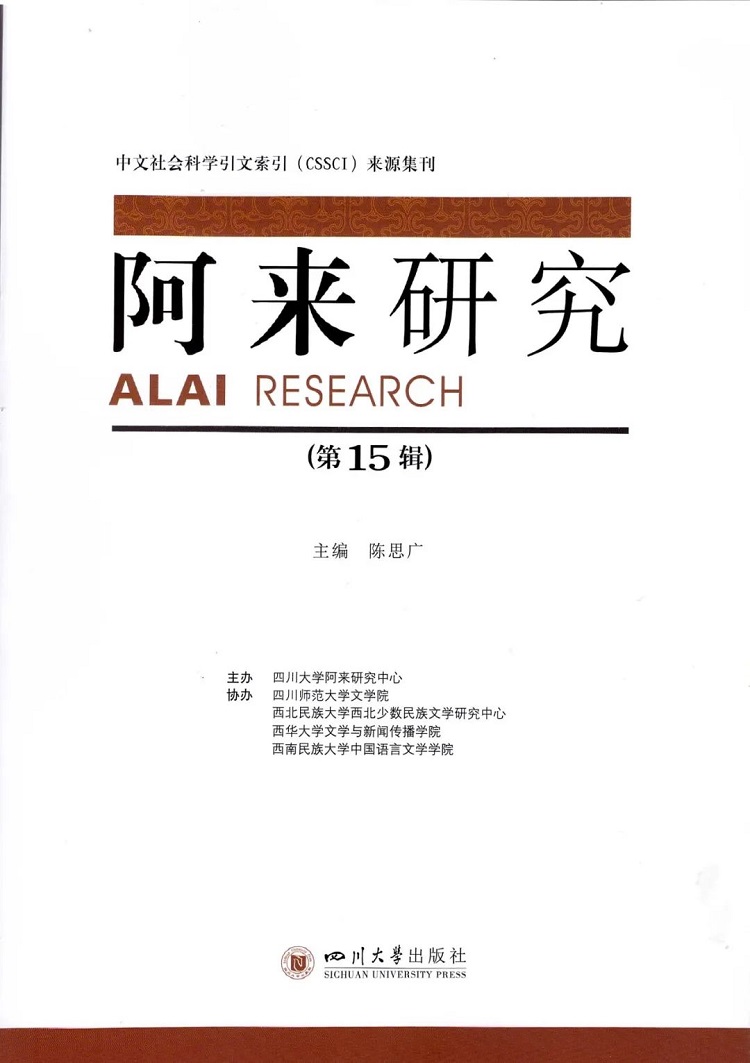
在梅卓的创作生涯中,文学评论并非她的关注点和重点工作。作为当代文坛的一位优秀作家,梅卓在小说、散文、诗歌方面都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作品。然而,从一个苛刻的,甚至也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角度来看,梅卓没有专门的文学评论计划,也没有较为完整的评论文章。对一个作家提出评论写作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不过,梅卓却有一些随笔、访谈等“断片式批评”,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意义独特。梅卓的这些简短的、自由的“断片式批评”实践,为理解梅卓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角度。同时,梅卓“断片式评论”所提出的诗学观点,呈现出了她直击现代诗学核心的思考,为当代诗学的建构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生长点。
一、断片式批评
关于梅卓的创作,可以说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评论。但是,相比较而言,关于梅卓的“断片式批评”的研究还并未起步。当然,与大多数作家一样,评论确实不是梅卓个人生命历程和创作的重心。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对于“断片式批评”这一较为特别的评论模式的研究,也还几乎没有展开。因此,对梅卓的“断片式批评”做一个较为深入的思考,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学活动中,存在着较为丰富的“断片式批评”的实践和文本,虽然这一独特的批评实践并未在研究界得到较多的关注和重视。具体而言,在当代各类文学活动与实践,如会议、讲座、访谈、感言、致辞、随笔、推荐语等之中,作家都会即兴或者有所准备地发表一些对作家、作品的简短评论,我统一称之为当代文学的“断片式批评”。此外,诗人在一些文章中对作家作品的点评,也可列入这一范畴。当代文学中的这类“断片式批评”是一种有着当代特色和诗学意义的批评样式,应该引起注意。从发生学来看,大多数“断片式批评”具有即兴的特点,这就使得这种评论比规范式评论更为鲜活,更有个性,也更为真诚。从形式和内容看,“断片式批评”短小、精练,且避开了相关复杂历史背景和理论的干扰,直接与作家、作品、观念“硬碰硬”,可以说成为一种较为有效,而且也可以直达“文心”的评论实践。所以从当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来说,“断片式批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文学评论方式。当然,在文学批评史上,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有着独具特色的“评点传统”,出现了一批出色的“评点批评家”,形成了一批重要的“评点批评文本”。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文体一一“笔记”,形成了一批“笔记体批评”。当下的“断片式批评”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评点传统”和“笔记体批评”的继承。这些批评模式,都极为强调批评主体的直觉,突出文本的审美特征。但同时,与中国古代传统评点、笔记的感性表达相比,这些“断片式批评”又有着新的发展,即不仅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性思维,也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另外,当下作家的“断片式批评”尽管很丰富,但最终形成文字的也仅为一小部分。所以,对“断片式批评”展开进一步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梅卓可以说是当代文坛中有着丰富“断片式批评”实践的代表。据现有的相关材料,梅卓的“断片式批评”不少。梅卓的多重身份就让她有了“断片式批评”实践的各种机会,也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断片式批评”的文本。实际上,梅卓的这些“断片式批评”从内容来看是非常丰富的,也并非都指向当代诗学,但“诗学”却是梅卓的这些“断片式评论”的一个重要向度,而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在当代诗学建构之路上的独特思考。如2011年《青海湖》创刊第500期时,在访谈中,梅卓就谈到了《青海湖》的历史意义,即“成为青海历史留影、青海社会写真、青海文化样本、青海精神张扬、着力塑造文学青海的期刊”①,这一 “断片式批评”实际上包含了梅卓对文学与地域深刻关系的理解和认识。2014年在青海湖诗歌节的采访中,梅卓又谈到了她对诗歌与传统、诗歌与社会的关系的思考:“首先文字具有社会性,记录和传递着民族文化和知识,诗人运用文字中最美好、最精粹的部分延续着宝贵的文化传统;同时每位诗人都是社会人,无法回避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诗歌与社会、诗歌与时代、诗歌与生活都息息相关,每一位优秀的诗人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言人,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良知和尊严,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类精神世界的高度。”②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梅卓诗学建构的努力。在2016年首届华语诗歌春节联欢晚会(青海分会场)上,梅卓致辞说:“把诗歌当作春晚的主角,这是首创,是诗歌走向人民,走向生活的良好开端。因为我们一 直相信,生活需要诗歌,诗歌需要人民③在这里,她又重申了诗歌与生命、诗歌与 人民的关系这一命题。同年,在昌耀80周年诞辰专题学术研讨会上,梅卓更为明确地 呈现出了自己的诗学观念:“以昌耀先生生前已然抵达的诗歌创作巅峰状态来推断,如 果他活到现在,他完全有可能又创作出了许多兼具现代意识、青海地域特质、个人气质 禀赋的精品力作。”④此外,梅卓还有不少的“断片式批评”文本,如在2019年青海湖 国际诗歌节暨国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召开期间,在《“既要埋头写文章,还要抬头看世界”——访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卓》的采访中,她说道:“我曾经游历过门源仙米、珠固、苏吉滩等藏族群众聚居的地方,这里的风光美不胜收,群众热情善良,民族文化深厚,作为一名游历者,我深受感动;作为一名藏族人,我心生敬仰;作为一名回乡游子,我深感自豪。为此,我创作了一些诗歌作品一吐我内心对家乡的情感。”⑤梅卓在自己的文学大厦的建构中,注入了汩汩流淌的乡愁。总之,我们看到,在当代“断片式批评”方面,梅卓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诗学观点,“断片式批评”可以说是梅卓文学创作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行动诗人
梅卓“断片式批评”在当代诗学的建构中有着独特的关注点和话语方式,也有着鲜明的个性。其中,“行动诗人”的这一概念对重新审视梅卓文学创作的特色和意义,有着重要的价值。
当代诗学所谓“行动诗人”这一概念,梅卓首先在《诗与自然的距离》中提到,“在我看来,诗人有两类,一类是文字诗人,一类是行动诗人”⑥。此后,她又在“2011中国宜春•明月山第二届国际华文作家写作营”的“断片式批评”中进一步呈现。在以“地域文化自然文学”为主题的文学论坛上,梅卓再次提到了“文字诗人”和“行动诗人”两个概念。她说:“青海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得世人对青海这片土地有了深刻的认识,使得青海各个作家群彰显了自身独特的一面,将地域特征与时代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青海,在最接近自然的地方,诗人有两类,一类是文字诗人,一类是行动诗人。”⑦梅卓并没有对“文字诗人”和“行动诗人”做较为明确的界定和区分。不过我们看到,她的诗歌观念更为关注的是“行动诗人”。梅卓对“行动诗人”这一诗学观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在青藏高原,行动的诗人随处可见:格萨尔艺人带着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吟诵在高远的山冈,曼陀铃琴手弹着世界上最美的情歌吟唱在低回的河谷,他们代表着藏族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中的民间精华,相对疏离于文本形式。”⑧据此,我认为梅卓的“行动诗人”这一观念之中有这样的四个关键点:格萨尔艺人、吟诵在高原的山冈(或低回的河谷)、民间精华、相对疏离于文本形式。围绕这四个关键点,我们看到,梅卓文学观念中的一个核心就是“文本(或者说文字)”与“行动”的轻重问题。毫无疑问,对“行动”的关注、实践和建构,是梅卓诗学或者说文学实践的重要基点。
梅卓看重的就是“行动”,她就是一个“行动诗人”。在梅卓的生命历程中,就曾有着漫长的行动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路上”的作家,一位“行动诗人”。她曾自述说:
这次游历是从2005年10月份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翌年夏天,先是走远处,回来休整后又走近地,基本走遍了所有藏区。这个计划曾是我向往多年的,最终得以实施后,有种不枉此生的感觉。这之前也长期游走,但许多地方还是头一次走到。藏区从地理上说,她的高峻和博大举世罕有,从文化上说,她的厚重和积淀也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的风俗民情展示出别具一格的魅力,就像在观望一架多棱镜,令人目不暇接。游历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毕竟能让人产生巨大的创作激情。⑨
此时我们看到,“行走”几乎可以说构成了梅卓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创作的重要源头。在相关的文章中,梅卓也多次回顾了自己的“行动”:“我们开始设计路线,在反反复复的意见整合中,最终决定从西宁出发,经甘南、阿坝、甘孜、迪庆、林芝、山南、日喀则、阿里、拉萨、那曲,然后回到青海。” “为时近四个月。行程三万多公里,基本走遍安多、康巴、卫藏、阿里的大部分地区……”⑩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行动”的偏爱与执着,梅卓还在自己的创作中构建出了一系列的“行动文本”,如《藏地芬芳》《走马安多》。同样,她的小说如《神授•魔岭记》,也可以说是一个“在路上”的“行动文本”。正如有学者的评论:“‘在路上'的阿旺罗罗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神奇异事和生死考验,如同《西游记》里唐僧的取经之路,‘九九八十一难'的跋涉、体验,重在‘过程'和领悟。” ⑪由于有着“行动”或者“在路上”的独特诉求,梅卓的创作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行动文本”,这也是当代文学实践的一种极为有意义的探索。
与此同时,梅卓将“文字诗人”与“行动诗人”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对当代诗学中“文字诗人”的一个重要补充和推进。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语境中,“文字诗人”无疑是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诗学路径。此时,诗人特别强调“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也就如西川所说,“在修辞方面达到一种透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在面对生活时采取一种既投入又远离的独立姿态” ⑫。进而,我看到在当代诗学写作中,一个落脚点就指向了修辞,一种质地复杂的艺术技巧,而这也构成了欧阳江河所说的知识分子“专业的和边缘人的身份”,或者说一种具体的“文字身份”。正如王家新所言,“90年代诗人的写作从不同层面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而且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在诗歌中用复杂技巧表现现代人的真切处境、他们对文化现实的积极回应和介入……”⑬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成为一种“文字诗人”。在当代诗歌写作中,“互文性”便是“文字诗人”诗歌写作的重要表现。这里所言的“互文性”,除了指在诗歌中灌注古代诗歌或者西方诗歌的精神与血液以外,更强调一种语言资源,即对古代诗歌语言、西方诗歌语言的借鉴。孙文波提到,“在一个民族文化由统一的意识形态干预左右的现实境遇中,所谓的地方习俗、话语习惯,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将‘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胶合为不可分离的‘文化共在'的牵制,并由此发生‘此在'变异,从而形成‘现实的语言'与‘语言的现实’。”⑭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90年代诗歌的诗意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大型的语言突进,“或许更接近于诗歌的本来要求——它迫使诗人从刻意于形式的经营转向对词语本身的关注”⑮。张柠也认为,“朦胧诗后,许多诗人都走了……剩下来的……大多数都早早地进入了词语沙龙……与词语沙龙相对应的'词语集中营”⑯。90年代的诗歌论争和诗歌创作可以说就是在“词语”这个层面上展开的。诗人们纷纷开始打磨自己的语言座驾,并实现一种语言自我,成就了一批一批的“文字诗人”。那么,面对宏大的启蒙、救亡、革命、民族、历史、社会等命题,当代诗歌如何轻装上阵,从词语开始完成自己的语言使命?如何从语言中构建出自己的诗学体系?从语言出发,诗歌又如何与启蒙、救亡、革命、民族、历史、社会等厚重命题深度兼容呢?“行动诗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可以说,在“行动”的基础上,才可进一步完成“文字”的诗歌使命,才能让诗歌的诗 性超越“文字”,进入澄明的个体精神与历史经验之中,释放出想象与自由的火花。
在“行动文本”基础之上,梅卓的“在路上”探求就不仅仅只是“行走在路上”,而更上升为一种生命存在的精神方式。我们看到,梅卓的“行动”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地,那就是“神山圣地”。正如有学者评论说:“梅卓的小说创作是在向世人阐释其内心深处对青藏高原、对故土安多、对藏族崇尚的神山圣地的一次次流连忘返。这一点,梅卓曾有过自我表述,她谈到自己寻找文学灵感的方式,就是无数次地游走于青藏高原,这一过程给予她很多感动,并由此唤起了沉淀已久的激情。”⑰我们看到,正是在“神山圣地”的引领之下,诗人才有了孜孜以求的“行动”,才有了发动自己文学事业的动力。因此可以说,梅卓所指的“行动诗人”具体就是“行走在朝圣之路上的诗人”。“神”构成了梅卓“行动”的最为重要的维度:“我们常常遇到险境,这时我总是紧闭眼睛,快速地念诵莲花生大师咒语,敦请大师帮助我们脱离险境,恳求左肩的虎神、右肩的豹神、头顶的山神赐予力量和勇气。”⑱换言之,在梅卓看来,没有“神”的降临,就没有生命的“行动”,正是“神”让“行动”有了扎实的基础。进而,在梅卓的创作中,“行走在朝圣之路上的诗人”让我们看到了那种有着“朝圣”诉求的“神灵降临的抒情和叙事”。在梅卓的作品中,神灵无处不在。如在《神授•魔岭记》中,她就写道:“牧人家庭中男主人每天一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煨起桑烟祭祀众多的神灵,桑料里混合着柏枝和青裸、炒面、酥油,点燃后桑烟的香气很快就会弥漫在草原的上 空,接着爷爷向四方吹起白色海螺,这支海螺由祖辈传下来,亘古以来招引着众多神灵:早餐备好,请众神降临。” ⑲可以说,“请众神降临”成为梅卓“行动”的终极目 的,由此,梅卓“行动诗人”的思考有了鲜明的“神性诗学”维度。
也是在“请众神降临”的文学事业之中,梅卓的作品营造出了浓浓的“宗教氛围”, 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神性诗学”。对此,几位学者都展开了相关的论述,如:“梅卓小 说不仅直接以宗教为题材,而且充分表现了人物的命运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同时,在她的其他文学样式如诗歌、散文作品中亦不难看出潜在的宗教文学符号。” ⑳这也成为梅卓文学创作的印记:“梅卓的小说中奇异、梦幻般的氛围缘自藏民族浓厚的宗教文化熏染下形成的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意识。藏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他们的信仰虔诚而独特,他们相信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未知的神灵世界。” ㉑总之我们看到,在梅卓的“断片式批评”中,她所提出的“行动诗人”,特别是“行走在朝圣之路上的诗人”的观念,构成了非常充实的“神性诗学”,成为梅卓文学创作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三、神性诗学
梅卓的“行动诗人”之思,为当代诗学建构提出了一个较为重要的诗学概念,这进一步深化了当代诗学中“神性诗学”的理论建构,为当代诗学的进一步突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神性诗学”或者说“宗教诗学”,在当代诗歌的诗学建构中并不鲜见,陈仲义《高蹈宗教情怀的灵魂学一一神性诗学》就有专门的理论建构。㉒问题在于,当代诗歌的“神性诗学”本身就是一个既迫切又十分复杂的工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梅卓的“行动诗人”之思就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方面,梅卓的“神性诗学”本身就建立在“请众神降临”的基座上,这是当代诗歌“神性诗学”所难以具有的底色。我们已经看到,梅卓从生活到创作,都有着丰富的宗教基础,体现出宏大的“神性之思”,这是我们当下诗学建构中所缺少的基本起点。梅卓的“神性诗学”本身所具有的坚实的“众神”基础,让她在宗教、神性、灵魂、自由之间悠然地掘进,锻造出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学空间。耿占春就谈到了梅卓创作中行动、神性、文学、“救助”的天然的一体化特色和独特的诗学魅力:
梅卓以血液中流淌着的亲缘性,在时间和性别上的两极,用经文般的语言、用顶礼的仪式的语言写下了《佛心之旅》。对诗人来说,米拉日巴尊者、藏王松赞干布和伟大的歌者仓央嘉措,他们的一生既是一部行动的情史,又是藏族历史上最有情的章节。在米拉日巴的家乡芒域贡塘,追述了尊者苦修的一生。诗人祈求:“但请以你的悯悲心,摄受我吧。”
关于年轻的六世达赖喇嘛有许多传奇,一说在解往北京途经青海湖时被拉藏汗所杀,一说他在青海湖决然遁去,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和蒙古,一说仓央嘉措去了五台山,在那里闭关坐静……梅卓写道:“于是,我的王,你年年漂浮于达旺的田野上,漂浮于麦穗饱满的光泽间,漂浮于高原之外的远方他乡。”“你漂浮到……我伸出手,感觉到你陷落时的永恒之痛楚。”这是失之毫厘的时刻和救援。对梅卓来说,救助之手仍然来自仓央嘉措。㉓
而梅卓的这种努力和实践,也为学术界所熟悉:“如她错落有致地运用了活佛转世、巫师、梦魇、灵魂游走、梦境、心灵感应等藏民族原始文化和宗教文化中极富神秘性的文化符号,轻松自如地突破了奇异虚幻的神灵世界与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完成了神秘和现实的自由转换。” ㉔换言之,与当代诗歌中的“神性诗学”建构相比,由于梅卓本身就“行走在朝圣的路上”,其创作就是“请众神降临”,这使得她在当代“神性诗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本真意义。
另一方面,梅卓又是一个有着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的现代作家,在“神性诗学”建构以及文学创作中,她又时时站立在“神性诗学”的另一面,不断反思超越或重建“神性诗学”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尼采震耳欲聋的一声“上帝死了”,道出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也展示出“神性诗学”的困境。他的这一声呼喊,让在现代理性时代科技文明之下生存的人突然发现,人的信仰、价值已经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特别是在“上帝死了”之后,由于哲学中形而上学价值体系的崩溃,神性世界轰然倒塌,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无神的世界”,一个没有神性的世界。客观世界、物质世界、抽象的精神均势附着在神性光环上,“上帝一死”,这些体系就轰然倒塌。正如艾略特长诗《荒原》所展示的一样,在“上帝死了”之后,西方文化面临着巨大灾难。诸神退却之时,即是生命干涸、大地枯萎之时!没有了神性,大地就没有了灵性,成为荒芜的世界;没有了神,万物就只处于用具的地位,成为枯竭的事物;最重要的是,没有神性价值,人的心灵枯干、空虚……没有了终极意义。尽管中国“神性诗学”没有这样强烈的真实语境和困境,但我们已经深深地进入了现代性高歌猛进的浪潮之中,彻彻底底地成为一个现代人。于是,我们的当代诗学也面临着对现代性的质询,也翘望着“神性诗学”在“上帝死了”之后以新的方式降临!
梅卓“行动诗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对“上帝死了”之后“神性诗学”的建构有着启示意义。具体而言,梅卓创作中“神性诗学”的“行动”,一边是“行走在朝圣的路上”,享受着“众神降临”赐予的丰赡;另一边是“行走在现代的路上”,直面和思考的现代困境。在论述梅卓作品的文章中,“现代”,成为理解她诗学观念以及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小说创作中,梅卓时刻把对民族文化品格的探索和考量融入其中。如对人的灵魂和内心情感的追问,对宗教信仰和藏族文化的延续思考,现代人如何超越精神困惑,感知生命的真正价值和人生的意义等,都是梅卓小说表达的重要内容,也是梅卓对自身民族历史和族裔文化认知的独特之处。” ㉕这里所提到的“现代人如何超越精神困惑”,正是梅卓“行动诗人”所要面对和超越的问题。另外,还有学者谈到“现代都市爱情的宗教拯救”:“她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把女性的爱情梦想和理性认识,安置在六道轮回的宗教背景中加以审视,从而令人心痛地映现出爱的决绝、爱的无奈、爱的残酷、爱的盲目、爱的纯粹,以及爱的宽容。在轮回的命运中,爱情的永恒悲剧性得以充分显现,具有一种撼动人心的美感冲击力,这无疑是对落入窠臼、日趋疲软的现代都市爱情的宗教拯救。” ㉖梅卓的“神性诗学”,“行走在现代的路上”,面对“现代人如何超越精神困惑” “现代都市爱情的宗教拯救”等现代困境,也就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上帝已死”的现代情绪,从而与现代人生有着更为直接的碰撞,这使得她的“神性诗学”建构更有着普遍的意义。进而,面对“神性诗学”如何“行走在现代的路上”的难题,梅卓在她的“断片式批评”中提出“敬畏”,凸显出了一个重要的拯救向度。梅卓讲道:“实质上,行动诗人往往更贴近自然,或许他们的标志,就是与大自然融为了一体,大自然赋予藏族人的信仰模式,就是敬畏。” ㉗如何面对现代困境,弥补“上帝死了”之后裂开的“神性诗学”天幕?“敬畏”无疑是一条重要的丝线。在“敬畏”之心下,梅卓呈现了一种新的生命之境,“仓央加措仁波切预言了自己的灵魂将远赴理塘,转生下世后,还会回到拉萨。他用优美的诗句、精妙的比喻展示了活佛转世的全部机关:肉体的死亡只是暂时的,它是再生的一个必然过程,灵魂就像一只洁白的鸟儿,它飞去,还会飞回来,而得道者们就有足够的能力使灵魂自由飞翔” ㉘。超越肉体的偶然性进入“灵魂自由的必然性”,也让她“行走在现代的路上”的“神性诗学”有了可能。
总之,我们看到,“断片式批评”是梅卓文学活动与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断片式批评”中提出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行动诗人”这一概念。由于有着“行动”或者“在路上”的不断实践,梅卓的创作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行动文本”,这些文本彰显了梅卓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对于重新审视梅卓文学创作的特色和意义有着重要的价值。梅卓是同时“行走在朝圣路上”和“行走在现代路上”的“行动诗人”,这让我们看到,现代“神性诗学”不仅需要享受“众神降临”赐予的丰赡,还应积极地面对和思考现代困境。由此,梅卓的“敬畏”之思融合了 “朝圣”与“现代”,呈现出当代诗歌“神性诗学”建构的一条推进路径,彰显了当代“神性诗学”建构的新的可能。
注释:
①王丽一:《执著的坚守——访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卓》,《青海日报》2011年4月22日。
②葛文荣:《诗歌,成为八月青海关键词》,《西宁晚报》2013年8月8日。
③王十梅、李芸焯:《2016首届华语诗歌春晚青海分会场开幕》,《西海都市报》2016年1月31日。
④雪归:《共筑海内外诗歌精神高地》,《海东时报》2016年10月12日。
⑤范文举:《“既要埋头写文章,还要抬头看世界"——访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卓》,《祁连山报》2019年8 月8日。
⑥梅卓:《诗与自然的距离》,《民族文学》2007年第11期。
⑦黄维:《宜春华文作家写作营把脉地域文化抗拒文学同质》,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 _ 2011 _ 11 _ 04/0421496 _ 0. shtml.
⑧黄维:《宜春华文作家写作营把脉地域文化抗拒文学同质》,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 detail _ 2011 _ 11 _ 04/0421496 _ 0. shtml.
⑨郭建强:《藏族女作家梅卓:依托浑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叙事》,《西海都市报》2007年12月27日。
⑩梅卓:《和那亚一起旅行》,《西藏人文地理》2007年第2期。
⑪杨霞:《集体记忆与个人话语的诗性书写——评梅卓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青海湖》2020年第10 期。
⑫西川:《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71页。
⑬陈均:《90年代部分诗学词语梳理》,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0年版,第396页。
⑭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 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⑮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5页。
⑯张柠:《<0档案>词语集中营》,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页。
⑰贺仲明、李伟:《民族身分的自觉与地域诗性的探寻——梅卓小说论》,《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⑱梅卓:《和那亚一起旅行》,《西藏人文地理》2007年第2期。
⑲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⑳耿筱青:《追寻“如月离云"的意境——梅卓文学创作中的宗教因素》,《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 期。
㉑胡芳:《〈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梅卓小说之民族文化寻根》,《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㉒陈仲义:《高蹈宗教情怀的灵魂学——神性诗学》,《山东文学》1997年第8期。
㉓耿占春:《藏族诗人如是说——当代藏族诗歌及其诗学主题》,《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㉔胡芳:《〈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梅卓小说之民族文化寻根》,《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㉕贺仲明、李伟:《民族身分的自觉与地域诗性的探寻——梅卓小说论》,《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㉖张懿红:《梅卓:民族立场与民族想象》,《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㉗梅卓:《诗与自然的距离》,《民族文学》2007年第11期。
㉘梅卓:《理塘:洁白的仙鹤永在飞翔》,《福建文学》2006年第3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王学东(1979—),诗人、教授、博士,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当代诗歌、蜀学、民国文学。 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四川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校园文艺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理事,成都市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主任。《蜀学》副主编,《李冰研究辑刊》副主编。著有诗学专著《“第三代诗”论稿》《文革“地下诗歌”研究》,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星星>诗刊与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重点项目《20世纪四川新诗史等多项课题。出版诗集《现代诗歌机器》。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