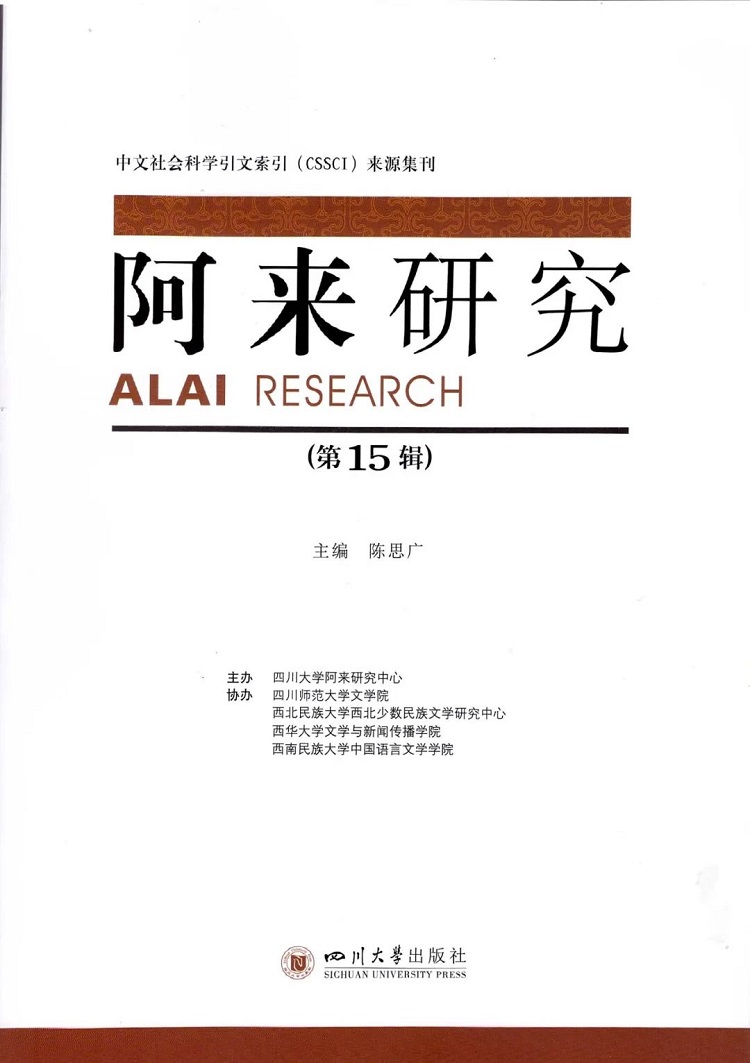
一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曾将文学视为“移位”的神话,文学不过是神话的康续。他在考察欧洲文学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出文学发展的规律, 指出文学以五种形态循环发展。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神话到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再到文艺复兴的悲剧、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直至近百年来的讽刺文学,五种文学样态沿着圆形的轨迹周而复始。可以说,从神到英雄再到讽刺文学中的“反英雄”,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失去远古神性的文学再现,最终导致的是无法协调的荒诞,这是现代性引发的悲剧。现代社会的危机就在于诗意生活的丧失,当现代技术打造的工具理性凌驾于所有传统的价值之上,技术秩序便决定性地重构了世界秩序。正因为如此,从维科到海德格尔都在努力打造重返“诗意的栖居”的拯救方案。文学是现实的镜像,自21世纪以来,现实似乎呼应了弗莱的“文学循环论”,重返神话的诗意栖居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从《哈利•波特》到《魔戒》,21世纪的文学无不在善恶、正义、爱情、背叛等传统神话谱系中搭建审视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即使是像《黑客帝国》这样的科幻电影,也在抽象时空的维度打造了超现实的空间,以宗教精神绘制了末日救赎的终极画面。“有评论把《黑客帝国》和《圣经》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结构进行对比,认为其救赎思想来自基督教末日预言,而尼奥不过是耶稣的翻版。”①
2005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发起了“重述神话”项目,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出版社参与了这项活动,组织各自国家的文学家投入了 “重述神话”的文学创作。在我国,苏童、李锐、叶兆言、阿来等作家接受了项目邀请。然而,或许是受到“命题作文”模式的影响,“重述神话”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苏童的《碧奴》是“孟姜女哭长城”的现代诠释,苏童想用孟姜女的眼泪解决“一个巨大的人的困境”②,但宏大的人性思考让“神话主体最终似乎成了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形象”③。阿来的《格萨尔王》同样从现代视角切入,去审视这部民族史诗。“阿来说,他之所以要写这部小说,就是想要打破西藏所谓的神秘感,让人们从更平实的生活入手,从更严肃的历史入手来了解藏族人,而不是过于依赖如今流行的那些过于符号化的系统。”④但正因为这样的初衷,把我们的目光更多地从神话世界带入现实世界,导致文本出现想象力贫乏、神话色彩不足的问题。我认 为,“重述神话”在中国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困境,但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之所以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传统文化对理性异乎寻常的重视,以及由此所积淀的“集体无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即使像阿来这样的藏族作家,因为从小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之间流浪”,所以,他的创作便更多的是哲学和理性的思考。
相比之下,藏族作家梅卓的《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则呈现出浓郁的神话意味。文本以谪诡奇幻的色调打破了梦幻、虚幻和现实之间的壁垒,营造了一个爱与恨、善良与残暴、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懦弱等双构形态的神话世界。小说以 13岁少年阿旺罗罗向神授艺人蜕变的成长之旅为主要情节,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交汇杂糅在一起,让阿旺罗罗在神话传说与现实世界之间自由腾挪。这个奇异的世界充盈着光怪陆离的景观。兰顿大师可以划开阿旺罗罗的肚皮,将格萨尔史诗《魔岭大战》篇“那一大摞书装进阿旺罗罗的肚子里”,随后用“手掌一抹”,“肚皮竟然完好如初,连一条缝都没有”。⑤凝聚着几代大师修炼功力的香气具有无限能量, 只要“闻到一次,就可以十几天不吃饭”⑥。还有“翅膀展开足有两米长”⑦、能够载人飞行的金雕,会说话的乌鸦,以及各种奇异的法宝:圆光镜、森伦剑、松耳石奶桶、姜喝贝嘎神杖、九股如意能断神剑、丹露丸、阿达拉姆魔戒、龙畜之乳,还有宝石镶嵌、 黄金铸造、被冰雹包裹了十年的格萨尔王宝座……显然,这个无比奇幻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梅卓的卓越想象力。我们看到,即使是现实中的自然界也发生着幻妙的颠倒和位移:
起初湖中稀疏的水草摇曳生姿,越往湖底,就越茂密起来,一株株古老的大树从湖底伸展向上,铺排的枝叶就像卓玛本宗的柏树宫殿,繁盛而壮丽,在幽静的深处是连绵起伏的山冈,岩石与岩石之间,有逡巡的雪豹、棕熊和猞猁,山腰上游荡着岩羊、白唇鹿和马鹿,山脚下有红狐和狼群渐行渐远,香獐出现在森林间,雪鸡群在草丛里忽隐忽现,而山鹰和金雕扶摇直上,在静水之中划开一道道波浪,留下白色的翅影......⑧
这些奇幻景观让《神授•魔岭记》堪称东方的《魔戒》。繁复、瑰丽、恢宏是神话特有的色彩,托尔金在谈到神话时指出,作家所营造的神话世界“包含着除了精灵和仙女,除了矮人、巫师、怪兽、巨人或龙以外的很多东西,它包含着大海、太阳、月亮和天空,它包含着大地,以及大地上一切存在的东西;树和鸟,水和石头,酒和面包,当然还有我们——凡人”⑨。显然,在托尔金看来,神话便是一个“第二世界”,在那里, 可能发生任何奇迹,但这些奇迹又在情理之中。这样一个奇异世界是神话故事所必须具备的首要元素。从这一点来看,《神授•魔岭记》的确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神话的世界。阿旺罗罗向格萨尔王神授艺人成长的道路是主线,格萨尔王征战魔王路赞和路赞在“末法时代”复活试图统治世界是两条辅线,由此,神、人、魔所处的世界相互交织并置, 将过去、现在、未来拉扯到同一空间中,构筑了奇幻的景观。
但是,梅卓笔下的神话世界又与《魔戒》有着本质差别。《魔戒》中开辟的“第二 世界”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种族、文字和历史,是一个纯粹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尽管有着很强的象征意蕴,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折射,但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世界”。梅卓笔下的神话世界不同,它更多地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神话世界的根基生发在现实世界的文化框架下,从而呈现着藏民族特有的思想情感、生活体验、价值观念。文本对藏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习俗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呈现。从香雄文、玛尔文等藏族最古老的文字,到神奇的圆光术、占卜、祈福、禳灾、转山等 藏族民俗,乃至“提并古”“提海捷”等藏族孩子的游戏;还有“唐卡,神帽,精耙, 转山,煨桑,桑烟,供奉,祈祷,功德,加持,扎定;藏原羚,黄岩羊,八宝图,雪莲花,白唇鹿;夏窝子,酥油灯,护身符,圆光镜,药佛泉,寄魂山……无数具有民族、 地域和宗教特色的物事就像繁星点点,闪烁在青藏高原的苍穹中”⑩。当然,这些地方性知识的生动呈现,并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消费心理,而是要让读者深入到藏族日常生活的画卷中,去深度了解藏族文化。
贯穿于文本始终的是藏族文化中的“万物有灵”思想。实际上,“万物有灵”并非藏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人类学家泰勒和列维•布留尔都指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万物有灵”,在人类祖先的眼中,日月山河、花草树木都与人一样具有灵魂。灵魂是“万物有灵”论的核心。泰勒说:“灵魂是不可捉摸的虚幻的人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虚无得像蒸汽、薄雾或阴影;它是那赋予个体以生气的生命和思想之源……它能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⑪由于诸多历史文化的因素,许多藏族同胞依然保持着这种纯净而原始的思维方式。在《神授•魔岭记》中,梅卓借格萨尔说唱艺人嘎玛威色之口,表达了对灵魂不朽与力量的敬畏。“格萨尔史诗中的关键点也是灵魂的问题,灵魂在何处安放,是许多重要人物的生命保 证。”⑫在文本中,那些逝去的亡灵都有自己的寄魂之物。阿尼玛卿山之所以圣洁, 是因为它是格萨尔王的寄魂山,凝结着宇宙至尊力量的金焰魂石便沉睡在阿尼玛卿山中。阿旺罗罗的修行从转神山开始,当他一次次叩长头,让自己的身体与大自然完全贴合时,他凡俗的肉体开始在自然的灵性中汲取养料,最终完成了生命的蜕变。这是一种真正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同阿旺罗罗与他的保护神扎拉,实际上便是一种人神同体的共存关系。
“万物有灵”不仅是藏族人的思维认知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文本开篇就写道:“现在是末法时代,人类的寿命都太短暂,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领会天神的意思,只顾拼命地毁坏山川河流的纯洁”⑬;“山里的虫草都挖光啦,外乡人一大批一大批地来,带着小铲子,拉家带口,就像乌云一般。山坡上的草皮都翻了个遍,虫草也不长了,蘑菇也不长了”⑭。还有那些不顾性命的登山者,目的在于“要征服自然”。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对立的生态观以及贪婪的人性导致自然严重破坏,“所以格萨尔大王的故事才需要不断地传承下去”⑮,以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家园。格萨尔王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保护众生的使命,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将保护乐土的使命交给了神授艺人,只要当艺人唱起格萨尔史诗时,他的保护罩就能起作用,“只要艺人在,光罩就在,山河大地的原生样貌就在,人与动物,自然与生灵的最初平衡就在”⑯。我想,这正是格萨尔史诗在当下的意义。这部恢宏的史诗不只是一块“活化石”,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涵和面对未来的希望。可以说,梅卓的神话叙事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藏民族认知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本中飞行女康珠玛骑着金雕飞翔在蓝天的图景,便是对人与自然自洽关系的最好诠释。
二
《神授•魔岭记》以少年阿旺罗罗历尽艰辛成长为神授艺人为叙事主线,因此,也可以看作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成长小说。神授艺人是藏族神秘而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在神授前目不识丁,但一夜之间便可以在梦中学会说唱,或在一场大病之后就神奇地掌握了说唱技巧。这种“灵异现象”已经引起了生命科学家的关注。这些神授艺人的说唱技艺和神秘记忆到底是如何获得的,的确耐人寻味。因此,怎样刻画这样一个神授艺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难题,过于神秘化或过于现实化都难以真正诠释好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神授经历。可以说,梅卓的叙述非常巧妙,她无意于揭示这一文化现象的秘密,而是通过民间文学中的“行走”母题,着重书写阿旺罗罗在“行走”中的修炼与成长,将此与格萨尔王降妖除魔的英雄使命做一种精神同构,由此,让我们在“编年体”之外的神话世界里去触摸藏民族文化的历史印记。文本的开篇,梅卓就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充满了贪婪、欲望,乱象丛生的“末法时代”画卷。贪婪的欲望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和世界秩序的混乱,甚至在格萨尔王金刚法舞的表演仪式中发生枪击事件。于是,阿旺罗罗这样看似卑微弱小的小人物,却最终背负起了重大的使命。他的成长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无数次在神话中演绎的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故事,还有一次次在超验的维度中开始的精神远征。
阿旺罗罗的“行走”始于黑魔王路赞化作野耗牛破坏姻亲联盟仪式。野耗牛撞伤了神授老艺人嘎玛威色,毁坏了法宝圆光镜。“圆光镜是格萨尔艺人传唱的重要法器,只有圆光镜在,艺人才能传承格萨尔利国利民的精神,史诗空间才能扩大保护光环。”⑰ 为了修复圆光镜,阿旺罗罗开始了他的艰难险程。尽管这是一次拯救圆光镜的旅途,但是阿旺罗罗的“行走”更多的是在彰显一种自我牺牲的奉献。在桑巩卡,他答应帮助身患重病的老奶奶去截取森林深处白唇鹿的鹿茸;他将兰顿大师给他的弥足珍贵的奇妙香气慷慨地赠予素不相识的转山人;面对被冰雹包裹的格萨尔王金座,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扑上去,代替朋友用自己身体的热量去融化冰块;为了解救保护藏羚羊的老奶奶,他 “顾不得多想”就冲了下去,结果被非法猎杀藏羚羊的歹徒打伤;他冒着生命危险搭救掉进冰缝里的登山队员;为了挽救被魔王诅咒的闸宝大师,他独自勇闯魔王的千年城 堡,取回了 “写有闸宝大师名讳和咒符的密咒”⑱;他深入湖底,杀死毒蛇,救出母亲, 取回了解救父亲的“解药”。可以说,阿旺罗罗的“行走”是在不断奉献和施舍中完成的修行与自我超越。正如他为了给自己亲爱的守护神扎拉聚魂,三天三夜西西弗斯般不停地搭建不断自行消失的白塔,最终明白了 “修塔的过程才是救人救己的过程”,“每块石头都要带着虔诚的信仰和加持力”,⑲于是,“他将这块石头举上额头,念诵六字真言,平和的气息传达给每一块石头,吉祥的话语低声诵出,像唱着温婉的歌谣,黑夜笼罩大地,黑夜也像一团火焰,照亮了他的心房。他在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中,第四次顺利完成了石塔的全部工程”⑳。正是这样的行走、修炼、悟道使得阿旺罗罗最终成为神授艺人。我们知道,佛教文化将施舍视为一种高尚的美德,菩萨以身布施的故事成为佛教文化中最富生命气息的光彩亮点。“割肉啖鹰” “以身饲虎”讲述的都是佛陀救护一切众生的大悲行愿,呈现出“头目脑髓皆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获得善报的重要业因,也是大乘菩萨道的重要修持内容。由此看来,品行的修炼显然是成为神授艺人的必要条件。
当然,仅仅基于外部的修炼还是不够的,真正的神授艺人还需要强大的内部“基因”。我们看到,阿旺罗罗最初对格萨尔王史诗的系统性接受来自兰顿大师的强行灌注:
兰顿大师用长长的指甲在阿旺罗罗的腹部上上下下比画了一阵,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划开了他的肚皮!
他把阿旺罗罗的内脏一扔,就扔得远得看不见了。阿旺罗罗简直要死了, 他觉得自己除了疯狂大叫,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他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疯狂大 叫上,声音简直震耳欲聋,可是兰顿大师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他此时正在专心致志地把那一大摞书装进阿旺罗罗的肚子里。㉑
这段书写极具魔幻色彩,似乎是要解开神授艺人的超能力之谜。但是,装进阿旺罗罗肚子里的《魔岭大战》,只能帮助他熟稔宏大史诗的内容,却无法让他真正理解格萨尔王的精神内涵,也就是说,“神授”绝非从外而内的灌输或学习,而是一如柏拉图所说的“灵魂的回忆”,是主体自觉的内心生发。所以,尽管阿旺罗罗的“行走”始自保护和修复圆光镜,但最终圆光镜为了阻止被魔王利用,“自断光芒” “自爆身相” “镜像全失”。圆光镜的自我牺牲,令阿旺罗罗更加自觉地承担起了格萨尔王说唱艺人的使命。当他的双眼被魔王毒瞎后,他感悟到“魔王夺走我的眼珠,但并不能夺走我的‘看见',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只有灵魂感悟到的,才要用心把握”㉒。于是,他努力修习圆光术,“从他圆光,到自圆光,再到心圆光,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历程。阿旺罗罗从最初只能借助大师观看圆光镜,发展到能够自己观看圆光镜,到后来失去视力,没有圆光镜的情况下,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以圣湖为镜,修得心圆光,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从此以后,阿旺罗罗可以借助任何可以反光的物质,就可以打开通往遥远岭国的神秘道路,任意撷取格萨尔史诗中《魔岭大战》篇章的任何部分”㉓。显然,阿旺罗罗修炼心圆光是一个将史诗全然内化的过程,正像嘎玛威色老艺人所说:“它(圆光镜) 也仅仅是法器,是身外之物,成为艺人更重要的是自身的能量。”㉔
佛教一直强调顿悟,追求向心求悟的真谛。《坛经》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顿悟是瞬间的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征兆的从天而降。顿悟之前常常会有一段时间的反复尝试与挫败,只有在不断修炼的基础上,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慧根才能在倏忽间生发出来。我认为,梅卓正是在此意义上道出了神授艺人的秘密, 即只有外修内悟,才能真正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打通现实与史诗的壁垒,进入史诗中,获得格萨尔王内在的精神真谛。由此,神授艺人的成长在保持其传奇色彩的同时, 又有了扎根现实的意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
可以说,《神授•魔岭记》是“重述神话”的一次有益尝试。梅卓立足于当下的社会语境,融入史诗神话中的素材、人物、故事、结构,让古老的格萨尔史诗得以“复活”。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梅卓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建构她的神话世界。其实,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80 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国作家,诸如莫言、余华、苏童、阿城、扎西达娃、马原、残雪、孙甘露等,或多或少都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西藏新小说异军突起。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马原的《拉萨河女神》首开魔幻现实主义西藏叙事, 由此使得西藏的汉文小说有了自己的特色,摆脱了对内地的模仿,一度成为中国小说最具原创力的亮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藏新小说存在着无法规避的局限性。其中,从神奇走向猎奇的趋势,使得西藏新小说在80年代后期走向了奇观化和怪异化的困境。而且,“外部人”的视角也很难从魔幻书写中挖掘藏民族的文化之根,即使像 西达娃这样的作家,对藏民族的“文化现象既陌生又亲切,既萌发融入其中的热望,又有着难以企及的距离感”㉕,而这种距离感无疑屏蔽掉了藏文化腹地的诸多丰富、复杂的内涵。
与西藏新小说不同,梅卓更多地接纳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民间性,并成功地将藏族文化融入其中。俄罗斯学者梅列金斯基曾指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大量民间元素的运用:“《百年孤独》这一史诗般的鸿篇巨作,理应称之为‘神话小说'(从《芬尼根的苏醒》及《约瑟及其弟兄们》的意义说来)。加・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一著作中极广泛地仰赖于拉丁美洲的民间创作,而对其借用则堪随心所欲:辅之以古希腊罗马情节和《圣经》情节、历史传说中的细节、祖国哥伦比亚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史实,并不乏种种怪诞的、带有幽默意味的变异及作者异常丰富的虚构,一一诸如此类虚构有时则是对生活和民族历史之任意的神话化。”㉖可见,以民间史诗、神话、民族历史素材建构文本的主体内容,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这样的素材,在《神授•魔岭记》中可谓俯拾是。
而梅卓在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还采用了民间史诗的叙事模式,这就有别于魔幻现实主义追求陌生化、夸张、变形乃至荒诞的先锋性,形成了别有一番滋味的原汁原味的“藏式魔幻”神话。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奈特在对荷马史诗《奥德赛》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史诗叙事在本质上是“动词的表达和扩展”,㉗世界上众多的史诗叙事基本都有“出发-回归”的模式:英雄出发一英雄征战一英雄落难(或死亡)一英雄归来(复活)。梅卓在《神授•魔岭记》中就采用了这样的叙事模式。文本开篇叙写黑魔王袭击姻亲联盟仪式,破坏了圆光镜,于是,阿旺罗罗“出发”,去找闸宝大师修复圆光镜。一路上,与英雄征战一样,阿旺罗罗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圆光镜不断地被修复,又不断地被损坏;与魔王的数次对决;尘世间的各种纷乱厮杀。可以说,阿旺罗罗的行走像是无休止的“极限挑战”,他屡次伤痕累累,命悬一线,在与魔王的一次战斗中,还被魔王的毒蛇毒瞎了双眼。阿旺罗罗也曾陷入无尽的痛苦:“我什么都做不好,现在已经成了废人,我看不见,甚至感觉也没办法呼吸……我愿我从来 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㉘是闸宝大师和亲人们帮助他度过了失明的黑暗时光,令阿 旺罗罗悟出,眼睛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只有用心灵之眼才能看到被万物 遮蔽的真相,最终修炼成为神授艺人,与家人团聚。由此,整个叙事完成了 “出发一征战一落难一回归”的全过程。
不仅如此,文本中格萨尔王征战魔王的辅线也保留了史诗中的“出发一回归”模式,与阿旺罗罗的行走主线形成了结构上的呼应。这条辅线基本上是用格萨尔史诗中的魔岭大战建构起来的:雄狮大王降临人间,汇集岭国各部落来到阿尼玛卿祭祀山神,前往查姆寺修炼;梅萨被魔王路赞掳走;格萨尔王征讨路赞;魔女阿达拉姆归降格萨尔王;格萨尔王杀死路赞,征服了魔国,将路赞的尸体压在黑塔下。可以说,梅卓在小说文本中完整讲述了格萨尔史诗中魔岭大战的全部内容。文本中,阿旺罗罗的成长与格萨尔王的除魔在一实一虚两个相互交织的空间中展开,由此,就构建了一种镜像关系。这种镜像,并非仅仅囿于文本的叙事层面,也存在于精神层面。格萨尔史诗中,格萨尔王作为大梵天王之子,莲花生大师的化身,“自诞生之日开始,就开始为民除害,造福百姓”㉙;“这位雄狮大王自从登上王位,就领导着岭国发展得欣欣向荣。但对于格萨尔来说,他是负有使命的天神之子,他的责任不仅体现在岭国的富强上,还要征服天下的妖魔,让所有的百姓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㉚。格萨尔王的这种精神在阿旺罗罗身上得以传承与再现。我们看到,文本最精彩动人的环节不是阿旺罗罗修成正果,实现人生理想,而是“在路上”的过程,是一个弱小的少年听从召唤,不断成长、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着格萨尔王的精神和意志,最终让阿旺罗罗蜕变成一个英雄,带来了守护人间和平、为同胞造福的奇幻力量。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神授•魔岭记》叙事结构的精妙,梅卓将文本的叙事结构与精神结构做了相应的叠套,呈现出现实世界与神 话世界的交汇甚至叠加的样态,从而建构起神授艺人阿旺罗罗与格萨尔史诗的精神同构。
荣格曾说,每一个神话意象中都“凝聚着一些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渗透着我们祖先历史中大致按照同样的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的残留物。它就像心理中一条深深的河床,起先生活之水在其中流淌得既宽且浅,突然间涨起成为一股巨流”㉛。梅卓通过一个神授艺人的成长历程,将藏民族的宗教文化、神话思维与审美意+识渗透到文本叙事中,再现了原汁原味的格萨尔王史诗,借助神话的转化功能,让我们摆脱工具理性束缚,去反观现实,以更为平等、平和、平衡的心理状态,去追求诗意的精神高度。正如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所指出的,神话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 “在个体保持健康、活力和心灵和谐的状态下,一步步地引导他走完一个可以预见的、 有益人生的完整历程”㉜。这何尝不是《神授•魔岭记》提供给我们的一种重新审视历史,解读人性的视角呢?在现实中,我们与阿旺罗罗一样,“在路上”不断地成长。
注释:
①陈晓明:《视听文明时代的到来——新的美学与感知世界的新方式》,《文艺研究》2015年第6期。
②苏童:《我为什么写〈碧奴〉?》,《潇湘晨报》2006年7月22日。
③朱崇科、李淑云:《失败的“故事新编”——评苏童的〈碧奴〉》,《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④梁海:《神话重述在历史的终点——论阿来的〈格萨尔王〉》,《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
⑤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⑥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
⑦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1页。
⑧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4页。
⑨J.R.R.Tolkien, Tree and Leaf. Boston: Houghton M^iflin Company, 1965, p9。
⑩《〈神授•魔岭记〉:一部藏族精神文化的认证和授权之作》,《青海日报》2019年12月27日。
⑪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
⑫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2页。
⑬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⑭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1页。
⑮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⑯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55页。
⑰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8页。
⑱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33页。
⑲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页。
⑳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页。
㉑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7-78页。
㉒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2页。
㉓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22页。
㉔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4页。
㉕李佳俊:《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浅析新时期藏族作家不同群体的审美个性》,《中国藏学》2006年 第1期。
㉖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93-395页。
㉗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㉘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5页。
㉙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6页。
㉚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页。
㉛C.G.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叶舒宪编选,《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 公司2011年版,第96页。
㉜约瑟夫•坎贝尔:《指引生命的神话:永续生存的力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梁海,女,博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出版《小说的建筑》《天道酬技》《阿来文学年谱》等多部学术专著,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等发表文学评论百余篇。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第十四届、十五届大连市社会科学进步奖等。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