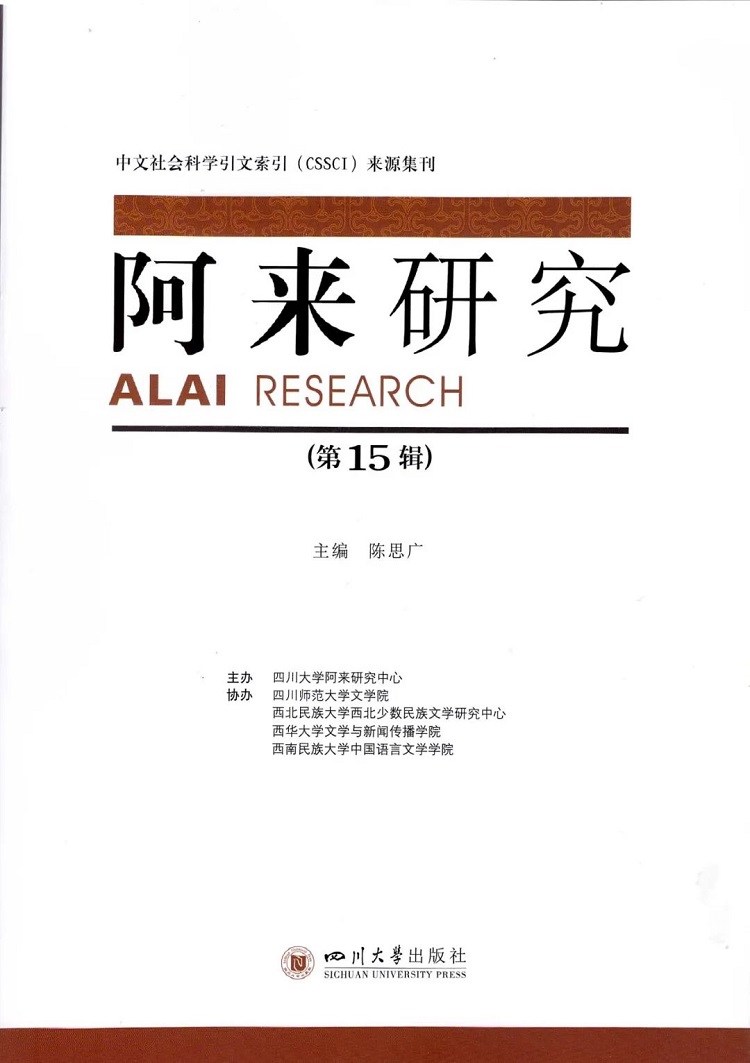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关系,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直就是近现代以来文化路径探索中的核心命题,国人也在一代代的探索中积累教训与经验。林毓生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著作名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①,在新世纪的今天,国民经济已经极大发展、文化竞争日益突出的时候,中国要走得远,走得更有活力,文化引领与探路功能就更为紧迫,这是深层次的探索,也是创造性的探索。创造性与创新性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老”在于这一直以来是人类发展的老使命,“新”在它的新语境、新经验。正是在此意义上,梅卓《神授•魔岭记》带来充分的启示。
一、有魂之根
“末法时代” 一样是个老话题,作为一个警世预言,它发挥着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末法时代”所述种种犹如生活现实的阴面,从辩证角度说,总是会降临的,或者说它早已存在于生活中的某处。对于“末法时代”人们并非束手无策,因为智慧之书已经告诉我们应对之策,佛法、信仰、英雄、使命都藏于史诗之中,应对之策就在于佛法一般的信仰和英雄一般的使命作为。伟大传统发出对现实的召唤,纷繁人事都将在这召唤中对号入座,人正在对自我寻找、对使命领悟中建立自己的伟业。《神授•魔岭记》首先让人感受到的就是其充沛的元气,旺盛的生命力、丰富奇诡的想象力如同滔滔江水,一浪叠一浪。这既表现为丰满又层次分明的人物形象,也表现为繁杂宏大而又有条不紊的结构布局和情节发展,而支撑这些高难度技术层面操作的,是扎实的底气和自信,是主题的宏大、深厚。阿旺罗罗的成长和对真善美的坚定追求,众人对正义终将战胜邪魔的信念,来自格萨尔大王精神激励的骄傲和自信,这些要素奠定了全篇睥睨天下、吞吐古今的文化自信。这种信仰是高贵、纯净的,对于我们时代的叙事群落来说,这种气质令人激动,它背后有历史智慧做支撑,因而它更是自信、勇敢、坚定的。
当视正义信仰为理所当然时,《神授•魔岭记》特出于时代的纯净气息却在提醒我们,近年来文学中浊气、虚气泛滥的严峻现实。“文化溃败时代” “告别革命” “躲避崇高” “不谈爱情”,文坛一片靡靡之音和虚幻缥缈之像,“活着”成了了不起的思想,“我就是一个小市民”成了自我认同,庸俗混世哲学成了流行观念,犬儒与虚无成了风尚。这不是所谓“末法时代”的表征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②,“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③,这不是可怕的堕落,不是信仰的“末法时代”吗?这些浊气与虚气的泛滥在于无魂、无文化、无信仰,脱离了文化传统赋予的胸襟;在于无根、无依恃,脱离了生活与人民这个力量之源;在于无心、无趣,一味投机,屈从于低级趣味。梅卓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文化自信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恰如灵魂与气质之于一个人。文化自信奠定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不可少的骨气和底气。这自信源自于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持久、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创新能力。” ④自重者,人恒重之;自轻者,人恒轻之。没有信仰和灵魂的人如何能赢得尊严?国人需要找到自己的力量依恃之源;占领了战略高点,就有了信心和底气,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神授•魔岭记》的底气何在,锐气何来?就在于文化传统这个魂,就来自人民与现实生活这个根,所以就富有勇气与信心,谱写出一曲黄钟大吕的正气歌。
没有骨气和操守的、庸俗的软骨头是自己都要厌弃的对象,又怎么可能成为人民的偶像?在精神软骨症浪潮中,《神授•魔岭记》告诉我们,如何英雄地去死,如何向死而生,如何为民族文化壮骨!为有牺牲多壮志,求法的成就令人憧憬和渴望,可阿旺罗罗的牺牲却更令人动容,他瞎眼后到处摸索的惨状令人痛苦,可他对于失败的自责、悲哀和绝望更让人痛彻心扉,这种悲剧的崇高感支撑着民族精神的脊梁。英雄之殉乃为国殉,英雄的复活重生更是激动人心,这是民族气运的重生复活,是民族意志的重生复活。有魂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根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文化史、民族史、党史、军史,都是历史,皈依和再出发的核心在于深入领悟其魂其骨,用于实践、继承和担当,融入传统并还创造性地成长、发展。骨气与底气的源头关键是“我信”,这个过程需要一股憨勇,而这股憨勇正是以清晰的判断和信念为支撑,这种信念就是对真善美的信仰和对民族文化之根的坚守。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数千年磨砺而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这种融合本身就是历史智慧的体现,是经过长期摸索、合作而最终积淀出的历史智慧,是大胸襟、厚历史的产物。这种多元文化和谐相处、融会互补的大胸襟、大智慧,只有居于历史的极高点才能体会。在世界仍不太平,西方文化霸权和民族主义横行的当今时代,这种文化融合的智慧和自信所带来的底气就会推动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坚定信念。于历史看,藏文化正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也发挥着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作用,而藏文化本身也经历了苯、佛之争与融合。在今天,藏族文学所坚守的信仰恰恰是医治物欲横行、信仰沦丧之疾的醒世良药。次仁罗布《放生羊》《祭语风中》、阿来《云中记》、万玛才旦《静静的嘛呢石》《撞死了一只羊》等已经鲜明展示出这一难得的高尚品质,梅卓《神授•魔岭记》坚守的格萨尔信仰再次强化了这一高尚品质的卓越贡献。文化自信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历史智慧、文化积累所支撑,是历史风霜千磨万击后的选择,多民族构成的多元文化正是强大内生活力的根本之一。在这条文化自信的路上,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自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自信,小主人公阿旺罗罗就有着这样的文化自信,历经万难,却从不丢失信仰,求索之路也绝不停滞,终得正果,成就伟业。
有了豪气干云的灵魂,小说叙事的万千气象就纷至沓来,井然有序。魔王得逞于一时,却不能让人民惊慌失措,这份心灵宁静、信仰坚执何来?有了这个“古”,人民面对错综复杂甚至是艰难繁乱的“今”,也一样可以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信心,这种战略定力既来自辨妖识魔的火眼金睛、圆光之镜,也将是降妖伏魔的能力。阿旺罗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雄狮大王的加持,有阿达拉姆诸神的加持,有闸宝大师、兰顿大师等修行者的引领,也有爷爷、父母等血缘亲人的呵护,还有同龄少年的陪伴和共同成长。换言之,阿旺罗罗们有传统文化之神的加持,有人民和大地的加持,有自信心的加持。这信心岂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岂是狂妄和虚幻?相反恰恰,是自有源头活水来。英雄的成长和担当不是凭空编造,其坚忍执着的成长过程和战斗意志令人惊喜和叹服,这是自然而又激动人心的庄严成长。最终,新一代通过成长而融入传统,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阿旺罗罗们是英雄事迹的继承者,更是英雄精神和伟大文化的创造者。
保护神扎拉这个小精灵式的角色,也是有根的。的确已存在不少类似的前身,比如《魔戒》中的怪物咕噜姆,阿旺罗罗的成长也的确像是霍比特人的成长,也的确有灰袍甘道夫等巫师神灵的帮助引领,也一样有与《哈利•波特》类似的儿童群像和想象情节,但《神授•魔岭记》更站在人类文化的峰尖,兼收并蓄,创造性吸收和转化,完成人类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建构。人类面临的使命是一样的,人类向善向美的心灵是相通的,人类的美好情感是相通的,这就是对话和沟通的基础,是达成理解和共识的桥梁,因而是真善美的终极信念之所在。
或许有人不服气——它,“抄” 了那么多!是的,这部作品,或许我们应该说梅卓只是半个作者,另一半是民族文化经典格萨尔史诗。不,甚至应该说还不够半个,还有《魔戒》《哈利•波特》,还有保护藏羚羊等现实生活材料,还有藏地人文、地理的丰富资料——哦,“抄”得挺多,甚至还可以算上《西游记》,这一算下来,梅卓怕是算三分之一个作者也够呛。可事实上,这就是创作,这就是创造,在这里,丰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伟大的文学传统、复杂的现实生活进入了一个大缸发酵,酝酿出芬芳的新酒,就如有人所说,不是歌德写出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写出了歌德。伟大的传统借一个叫梅卓的女子来开口说话,她也是一个神授艺人,她开口讲的正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正是时代生活的呼唤之音,也是大地深处传出的雄壮进行曲,她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轻轻一跃,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与人类文化意义上的一次创新与创造。她浸淫经典, 正是在得其真义的基础上方敢于大胆取舍化用,敢于创新创造。面对宏大的传统,《神授•魔岭记》不是机械重复和照搬,没将格萨尔王写得更老更旧,而是写活、写实、写灵了。作者以对英雄和传统的召唤来寄寓忧世、入世之心,来解决现实问题,古为今用。阿旺罗罗既是老传统的一部分,也是新传统的一部分,他开创了新的神话,创造了新的奇迹。作者不是“食古不化” “食洋不化”,而是传承、转化、创造、发展,将想象力和创造力灌注于扎实的文化血脉之中,灌注于现实生活土壤之中,实现了标志性的新腾飞。
二、救世之行
在梅卓《神授•魔岭记》这里,格萨尔不是一个简单搬用的符号标签,也不是一个奇幻游戏式的消费对象,而是融入文化血液,既熔铸为内在宁静的灵魂,也创造性地焕发出经世致用的批判活力。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时代和人民,梅卓深深服膺现实土壤和人民信念:“文学的篇章虽有个人书写,却注定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事业。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⑤《神授•魔岭记》的创作顿悟就在于“思索史诗中魔王及其代表事物在当下的影响时……猛然醒悟”:
所谓“魔障”,并非只存在于史诗中,也并非必然要有牛头马面的形象, 当下现实生活里依然存在,比如那些在可可西里对着藏羚羊的枪口,而用生命去担当的杰桑•索南达杰们则是人中豪杰、天之骄子,这样的人堪称当代英 雄。导致“山川失衡、水旱不调”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就是“众生心性 尽染”,因此生态、生命、生存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与“绿水青山”的生态 环境保护思想、正能量精神的弘扬是高度契合的,文学也应该观照到这样的身 边现实,挖掘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先进理念,更好地服务于当下。⑥
梅卓引入佛教的“末法时代”观念,其鲜明的现实批判性为“老话”注入了 “新酒”。
小说引入现实生活的严峻危机,屠杀藏羚羊、盗挖虫草,破坏草原生态,暴躁的丹底,还有沦为魔王宿主的“内奸”拉达巴桑,这些小说细节都是现实生活的投影。“末法时代”来临的标志并非只是莲花生大师预言的“铁鸟升空,铁马走路”这些外在符号,更重要的是内在人心的变化。梅卓借神灵之眼来透视时代乱象,直指“末法时代”之根一一“雪山消融,圣水枯竭,两岸失去滋养,动物失去家园,人类强烈的欲望蒙蔽了智慧,贪婪、嗔恨、痴惑、傲慢,导致各种冲突,扰乱了宇宙秩序,破坏了自然法则,人们失去上天的护佑,使得魔鬼出世成为可能,妖魔鬼怪全都伺机而动,可以想见,魔王路赞也正是在这种种条件下才可以转世再来的呀!” ⑦作品创造出的新神魔之战并非凭空杜撰,相反是立足于生活逻辑的扎实基础,这样,外在情节与内在灵魂才是相互支撑、彼此需求的,外在的繁复与内在的深沉才能彼此催化、层层递进。魔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的力量之源,因此,与魔的战斗才是艰难的、必要的,对魔的胜利也才是意义重大的。对魔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批判和拯救功能的最终实现,由此,对新“神”诞生的讴歌才真正具有了雄壮宏伟的史诗品格。在史诗基础上创造新的史诗,这就是了不起的继承与创造性的超越!金猴奋起千钧棒,只缘妖魔又重生。英雄的成长,首先来自生活的召唤。传统文化是灵魂之根,而现实生活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沛流量,“末法时代”魔王转世还魂这一独特的背景设定创造性地表达了新的生活真实,小说以强大的消化能力将“末法时代”的种种乱象纳入正法叙述之中并战而胜之,这就是正法的胜利、信心的回归,也是批判力和拯救力的增长。
源于生活的底气不只带来将纷繁世相纳入文化传统之中的化繁为简,更带来了艺术创造的胆气。在民间传说中,神授艺人尽管确有传唱史诗的神奇能力,但无论是神授的过程,还是传唱艺人的能力都是比较边缘化的,并非生活的核心。《神授•魔岭记》事实上大胆改变了民间传唱艺人的功能,将阿旺罗罗由现实生活中史诗传播这一相对单一的功能升级为抗魔救世,使其成为英雄格萨尔的新一代传人。由此,《神授•魔岭记》就升级为一部格萨尔精神传承记,一部民族精神文化掘藏记,也是一部少年英雄成长记。阿旺罗罗不仅是传统的传唱艺人,还承担起了救世英雄的责任,成为与转世还魂的魔王路赞搏斗的新英雄,这实际上就是“末法时代”下的格萨尔王。阿旺罗罗的功能获得过程由传说中偶然的天启神授变为小说中艰辛的奋斗求索,被动接受改造变为主动追求,其过程是成长逻辑在支撑。这里的神授,实乃人授;而人授,又实乃人求。在故事模式上,作品近乎《西游记》的取经考验,有魔拦,有神助,善恶搏斗的复杂历程就是修心修性的过程,最终证得圆满正果。小说还创造性地借助“加持”,将格萨尔王的英雄形象和品质转移到阿旺罗罗身上,形成功能和形象的叠加效应,使阿旺罗罗成为新一代的格萨尔式英雄,直接同现实中、神话中的各式妖魔搏斗。因此,这并非一个偶然的神授故事,而是一个必然的英雄成长的故事,生活需要英雄,时势需要英雄,最终时势造就英雄。正是立足于强大的生活逻辑,新的神魔交战、英雄降世才不再是野语村言, 而成为一个呼唤英雄、造就英雄的壮美故事。
三、积学炼艺之路
传统文化赋予的信仰之魂,现实生活灌注的新生活力解放了创造力,除了这些根本的精神支柱,《神授•魔岭记》还在艺术上表现出极其成熟的魅力。高贵的灵魂,丰厚敏锐的生活,成熟高明的艺术,使得《神授•魔岭记》可以跻身中国当代文学一流作品之列。
《神授•魔岭记》以伟大的想象力构筑出宏大神奇的人神魔世界,为神授艺人的求法过程设计出丰富的层次,从剖腹填藏的大师之授到圆光艺人自修,而圆光镜也从神奇展现到破损、修复、碎裂,最终又合一,与此同时圆光艺人也经历了他圆光、自圆光、 心圆光三重境界之锤炼。这些如同九九八十一难般繁复的情节设置跌宕起伏、变幻莫测,始终蕴含着迷人的奇幻吸引力。
魔王路赞有九个头,会不断复活,它不死的根源在于寄魂之术,而寄魂物需要特殊的武器才能消灭。魔王分别借红铜角野牛、阿达拉姆魔戒、人间宿主、本尊现世等方式还魂出世,其行踪难测,法力日盛,让人胆战心惊。魔王甚至还有三头魔采雏、五头魔相宛等帮凶。王妃梅萨、王妹阿达拉姆,乃至沦落为魔王宿主的父亲拉达巴桑也各有迥异的遭际和个性特征,构筑出敌营之中战斗的复杂性,因此战斗故事毫不枯燥,其丰富性令人手不释卷。
在人的世界,阿旺罗罗的童趣童真,保护神扎拉人性化的机灵活泼,均个性鲜明,谐趣常在。其他各色配角,如老艺人嘎玛威色,修行者闸宝大师、兰顿大师,爷爷绛秋昂杰、祖母康珠玛、父亲多杰丹坚,同龄小伙伴仁倩卓玛、拉姆卓玛、布群昂加、丹底,这些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组成宏大的群像,让全篇始终洋溢着浓浓的温馨与爱意。历史与命运承担者的使命、责任与勇气,纯净坚执的信仰,人性、神性的交融,让小说感人至深。
连接人神魔三界的还有那些层出不穷的神奇之器,如金雕之翅、龙畜之乳、圆光之镜、白海螺、护身符、青蛙脚印、白唇鹿、红宝石、阿达拉姆魔戒、九股如意能断神剑、金焰魂石、阿尼玛卿神山,乃至白塔、神箭、桑烟,这些繁复而又神奇的意象组建起的是整个“宇宙”。
《神授•魔岭记》不只以超凡的想象力构建神魔奇幻世界,更是从俗世人间自然升华到神灵领域。人为神授,人与魔斗,人与人亲,人也与恶人战斗,层次繁复却又分明,人界与神界的转换毫无阻滞,从伏地而卧的安静腾空而起,到盘旋入云的轻灵,自然顺畅。格萨尔史诗颂词唱段的信手拈来,新艺人传奇生活的自由穿插,新旧化合一体,相得益彰,既有古树新枝,又有磅礴气势、深邃情感,全篇宏大的建构中始终贯穿着深邃的慈悲与爱意。连接全篇的内在纽带,是伟大的想象力、伟大的情感、伟大的主题。因此,对《神授•魔岭记》的思考要超越技术层面,进入艺术灵魂层面,去体会其沉静的气度和坚韧的信心,史诗一般优美的词句,文化的自信与执着的信念。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神授•魔岭记》背后掩映着梅卓的成长之路,对此的探究, 于梅卓个人、于作家群体,都是有意义的。梅卓写有堪称“藏地史三记”的《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让梅卓初获声名的《太阳部落》已经展露出宏大历史构架的言说野心,历史、女性、情感、性、婚姻,这些纷繁的情节匆匆如流,历史叙述的建构欲望与匆忙节奏同样突出,却也是作品气韵不够协调的根源。《月亮营地》是一大步超越,其细节与仪式的描述远远超越《太阳部落》,精微描写和宏大气度的融合标志着作者的成熟。作品具有心灵的平静与叙述的雍容,三个部落由纷争到外敌威胁下的联合,宏大沉重的历史在清爽的叙事气息中次第展开,有条不紊,娓娓道来,对民族文化的表现与反思附着其上,作品既有骨肉,又有灵魂。
英雄叙事中人物饱满,丰富细腻。男人里甲桑孤傲执拗、冷漠强悍;阿•格旺倔强偏执;酒鬼少爷阿•文布巴鲁莽好斗;章代•云丹嘉措风流潇洒,在部落沦落下锤炼得能屈能伸;还有天葬师麦尔贡的尴尬,章代•乔的少年英气,他们都是小说最具魅力的形象。女人中尼罗、女药人、阿•吉、茜达、阿•玛姜个性突出,内涵饱满。甲桑、茜达、夏布三兄妹也个性分明,相映成趣。重新找回故事和人物正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进化轨迹,从《太阳部落》到《月亮营地》,这种进化痕迹也是明显的。《月亮营地》的超越还在于魔幻的必要性、深刻性。鬼魂、梦魇、魔法是生活逻辑的自然生长, 毫不生硬,成为情节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还在表达自由、思想穿透力上获得升华效应。阿•玛姜在死后对甲桑的回魂访问就是合乎逻辑的魔幻,因为情坚意长,故而火葬时一整天也点不燃火,却在回魂完成后的瞬间燃烧,回魂时戴上的甲桑的银戒指在火化之后闪现于灰烬中,虚幻与真实的界限恍惚难辨;尼罗虽死犹生,寄魂于牛,如同活人一样参与人世间的情感纠葛;还有章代•乔随身携带早亡妹妹章代•吉的胫骨,阿•格旺啃咬见骨的食指,部落集体失忆的现实与隐喻,这些都是植根于扎实深沉的生活逻辑、情感逻辑而绽放的神奇的现实之花。《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一脉相承,层层超越,堪称梅卓的“藏地史三记”。
除《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之外,梅卓还有不少的中短篇小说, 其中同样隐藏有她成长的密码。相比于历史叙事明显的魔幻化技法运用,当代生活题材作品更多依靠生活本身的巨大内在跳跃幅度而形成情节张力,因而此类作品倒更多直接展示时间、空间、人物关系等的巨大变化。如《蛋白质女孩和渥伦斯基》中夏姆、琼果、木米三人的婚恋关系。在这三个大学同学间,琼果因为木米的“渥伦斯基这个流氓”课堂言论而分手,工作之后再聚首,琼果与密友夏姆一起去做人流,才知夏姆与木米即将结婚。《秘密花蔓》中一向被轻视的女画家卓玛为救表面风光的师兄、丈夫而卖掉耗费20年心血的巨幅唐卡,最后才发现一直被丈夫欺瞒。《唐卡》中考古三人组里的桑杰才让坚守纯粹的学术操守,而导师张教授与师兄多杰本却在明里暗里引诱、逼迫他倒卖古唐卡。这些生活的跳跃本身已够魔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倒是老老实实以现实主义直接呈现即可。而长篇小说往往追求细节的真实和传神,故而要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便出现了魔幻等手法上的变化,这种魔幻手法的引入同时实现了文学和文化精神上的神奇化。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在现实的跳跃和手法的跳跃间有取舍,梅卓的小说才是好读的,而非晦涩难懂的。
此外,梅卓一直致力于从现实叙事中获得领悟。生活虽然琐碎,人物虽然繁杂,情节虽然五花八门,但在篇末总会有一种独特的领悟升腾而起,让一切琐碎瞬间归位,成为有机整体,得到寓言性的升华。如《魔咒》,一个看似庸碌俗世中万千爱情故事的叙事下面,是对生活哲理的领悟,全篇入咒一解咒一悟咒,得到诗性构建的升华质变。故事就是道场,不同的人生阅历也是道场,寺院缭绕的香烟、悠长的诵经声、神山圣湖,这些只是作为表象的符码,真正的修炼其实在于俗世人间的繁杂万象。
除了小说,梅卓还有大量的游记散文,放到梅卓成长的整体之中,这些游记散文也变得别有意味。《吉祥玉树》《藏地芬芳》《走马安多》,还要加上《人在高处》中的一半篇幅,这百万字以上的“行走”之作,坦率地讲,恐怕对外界来说文史价值是有限的,无论是地理知识还是人文历史掌故,毕竟很多都具有“抄书”的性质。可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文字反而构成一种现象,让人想要探究,是什么在支撑她的书写热情,支撑她不厌其烦的甚至未免有些单调之嫌的罗列与述说?
梅卓自述:“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内心世界不可分割,但我却更久、更深地沉溺于外部。游走的积累和经验在我是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使它们纯粹,成为一篇篇文章。” “游走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感动。”⑧看来,谜底不言而喻,这是独特的“一个人的行走”,在别人看来单调和浮泛的行走表述恰恰是“一个人的修炼”。就如鲁迅拓古碑一样,别人以为毫无意义,可于他自己,却恰恰是灵魂的深邃探索,没有拓古碑的乏味, 没有“铁屋子”里苦闷和绝望的堆积,就没有《长明灯》里的呐喊,没有“抉心自食, 欲知本味” ⑨,更没有《狂人日记》的爆发。承认梅卓百万言游记文史价值的不足,恰恰打开了另一扇门,那就是进入她《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神授•魔岭记》小说创作的法门。“因为游走,我逐渐摆脱文风中的个人感伤和自艾自怜。好在数年后的今天, 游走对我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使我懂得温暖不仅来自于内心,更多地来自于乡亲故土兆示着的智慧、良知与尊严。” ⑩这样的写作恰就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写在心灵深处, 写到历史的深处。这样的写作是化身为民族、历史、文化代言者的叙述,是面对民族、 历史、文化的写作,这就是“藏地史三记”宏阔境界的源头。游记不免单调枯燥,可 “藏地史三记”却摇身一变,鲜活、深邃、灵动。这真是面壁十年图破壁,一朝破壁天下惊。梅卓的行走并非学者的贡献,而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的灵魂感悟和知识进食,“游走本身并没有意味着结果,结果是紧紧掩藏在心底的、经过时间淘洗、接受历史考验,并在思维的沉淀之中渐渐升起的激情的迸发” ⑪。游走是材料,心灵是窖缸,写出的是陈年佳酿;游走是笔记的积累,是资料库,是“藏地史三记”的底本。那些读来单 调乏味的游走方志,梅卓却甘之如饴,似乎浑然不觉其笨拙,正见其心静,其意诚,其行笃。不积畦步无以至千里,“以山的名义”“以水的名义” “以人的名义” “以天的名义” “以地的名义” “以美的名义” “以爱的名义”,《吉祥玉树》这七章,已经可见这种全方位的积累。没有百万言游记散文入地千里的根系,哪能支撑“藏地史三记”入云万丈的腾空翱翔。
从文体实验来说,《人在高处》将小说与人文地理、史实组接,告诉我们这块土地上屠杀造成的惊恐与苦难远比小说虚构的更加残暴,更加魔幻,这块土地上的后人所担负的历史记忆又是何等的沉重与丰富。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历史的幸存者,也都是历史的承担者,感受着佛法的慈悲,也体悟着生老病死和爱恨情仇的轮回。小说中有以前写就的各式片段,人文地理与历史是有资料可查的,《吉祥玉树》里也已收入,也就是说材料是现成的,小说写作实际是一种电影后期制作式的剪辑,却并非图书市场里投机取巧的拼凑,而是给我们新的震撼和启示。尽管难说有多成功,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从游记到小说、从《人在高处》到《神授•魔岭记》之间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与质变。
作家梅卓感悟大地,融入伟大文化传统和高贵的灵魂之中,身体力行,创造出伟大的超越之作。《神授•魔岭记》之所以可以跻身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流作品之列,除了其本身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创造性转化之路是扎实和富有示范性、启示性的,它有力地回答了我们的胆气从哪里来,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的创造性如何练就的问题。
注释:
①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北岛:《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③北岛:《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④梅卓:《坚定文化自信 繁荣青海文艺》,《青海日报》2017年12月15日。
⑤梅卓:《青海文学:丰收的时节已经到来》,《青海日报》2009年9月25日。
⑥梅卓:《“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之于我》,《青海日报》2020年10月23日。
⑦梅卓:《神授•魔岭记》,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77页。
⑧梅卓:《游走在青藏高原(代后记)》,《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⑨鲁迅:《墓碣文》,《鲁讯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⑩梅卓:《游走在青藏高原(代后记)》,《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⑪梅卓:《游走在青藏高原(代后记)》,《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白浩,男,1973年9月生。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