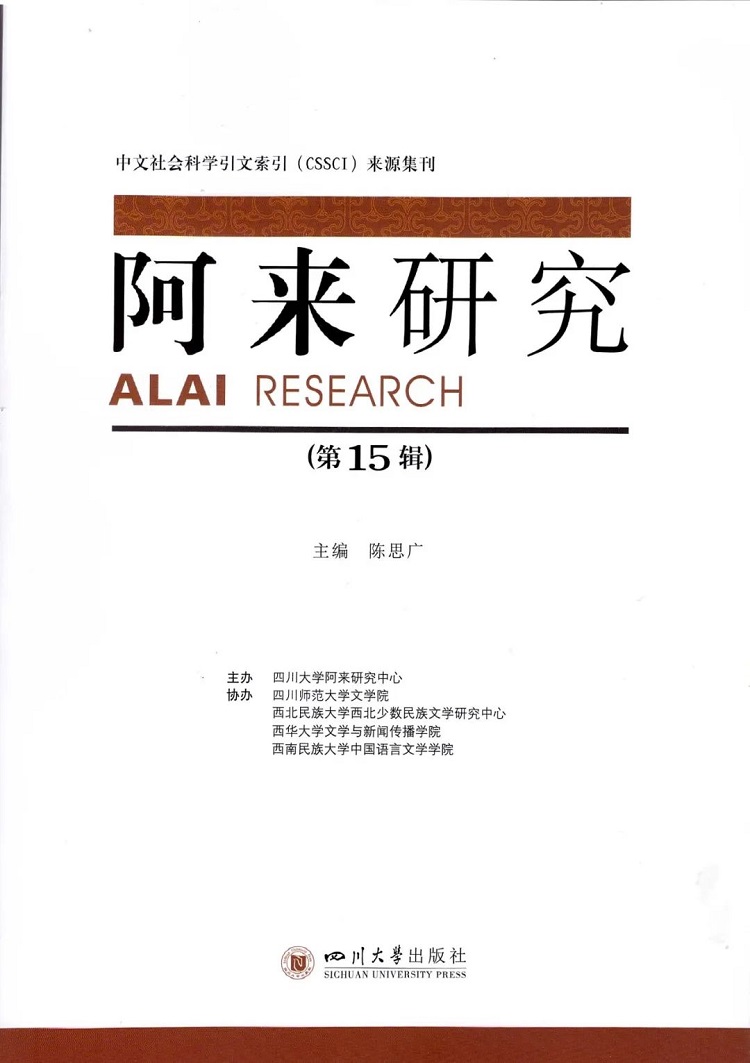
梅卓出生在位于汉藏边界的安多地区,从小便以藏族身份接受汉文化教育,多用汉语进行创作,是用汉语创作的藏族女作家。面对藏族文化发展困境、西藏文学沉寂期,梅卓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也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梅卓多重身份的优势为其进入藏族文化空间提供了更多便利和可能,她擅长将藏族文化置于藏族历史长河中去描摹,极力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融入宏大历史叙事语境,以此来观照历史和现实,力图阐释民族文化中的痼疾,重塑历史,重铸民族品格和民族灵魂。梅卓将民族文化注入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第一次尝试是《太阳部落》,但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还比较稚嫩,随后出现的《月亮营地》则显得更加成熟,它“自觉探索民族出路,描绘出一幅睡狮觉醒,民族振兴的光明前景”①。这两部小说都以马步芳家族侵略统治时期的历史为背景,书写藏族部落的变迁,涵盖了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多年中,在反动政府的多重压迫下,部落从最初的麻木、自相残杀到逐渐觉醒、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历史进程,回荡着藏族部落历史行进的足音。②但是,两部小说都没有在历史场景上进行过多的着墨,而是把焦点投射到几个部落的生活百态,将民族历史掩藏在文化书写中,反映出对民族发展的新诉求。相较于《太阳部落》,《月亮营地》在潇洒飘逸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深沉老道,后者比前者更有分量,更能体现梅卓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价值。
一、历史语境下的藏族文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西藏文学》为阵地,西藏新小说发端。梅卓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初稿刊载于《西藏文学》1994年第4期,随后几年,又发表了同类型长篇小说《月亮营地》。她倾心倾力书写藏族人的生活和历史、命运和精神,从藏族的历史传统中汲取有益的心理文化资源,构筑民族文化认同,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去挖掘民族的集体记忆。
独特多元的地域文化作为底色贯穿《月亮营地》始终,充分展现了丰富浓厚的藏族 文化,包括民族信仰(宗教)、历史文化、风情习俗、生活方式、认知观念等,如万物 复苏后仙境般的神山和圣湖,错落有致的藏式建筑,壮观神圣的祭山盛会,神秘奇幻的 丧葬仪式,有神奇法力的巫师,敢爱敢恨的儿女情长,分离但不灭的灵肉,等等,都是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藏地自然景观、人文风貌。而梅卓所选取的有益现代社会发展的民族文化资源主要有“万物有灵”民族信仰和敢于战斗的民族精神。其中,民族信仰是包括梅卓在内的新时期藏族作家在创作时都会采借的民族文化元素,秉持民族信仰的行为活动在《月亮营地》里大量出现:
甲桑说着跨上马背,沙利跳起来,毛孔粗大的黑色鼻子挨了一下主人的靴 子,似乎嗅到了方向,便主动朝前跑去。那匹马毫不迟疑地跟上去,步履稳笃地跑起来。③
这段内容描写甲桑的伴侣——马和狗(沙利)与甲桑心灵相通、默契十足的相处方式。动物似乎可以与人交流,是藏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信仰的体现,是藏民们最初看待世界的思维模式,是这个民族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能摆脱的文化根源,深深影响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雪山、湖水、草原、骏马、耗牛、雪豹等民族文化物象表达对生灵的崇敬和赞美,展现了藏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万物有灵”的观念使藏民有了心灵寄托,有了灵魂归属,有了以群体的力量去战胜苦难的信念。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藏族人民永远保持坦然乐观的态度,对生活充满希望,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
当“万物有灵”赋予人时,便出现了许多超乎现实的成分,同样富含浓郁的藏文化特色。比如女药人拥有感知现在、预知未来的能力,知道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又能在睡梦中得到珍宝,制造迷香帮助女人挽回情人,她脱离部落的正常生活,如同神灵一样存在;又如尼罗这般普通的人死后灵魂与肉体分离,寄魂于耗牛,与尚在人世的亲人对话;再如月亮营地这个部落集体失忆,遗忘了所有人的名字等奇异现象,充满了魔幻神秘的色彩。梅卓延续了藏族传统的原始思维模式,将藏族社会普遍存在的神鬼元素融入小说文本的历史语境,不仅使小说审美意蕴浓厚,更是加深了人物心理刻画、形象塑造,推动了情节发展,为月亮营地的觉醒和保卫提供了神秘力量。但也正是对梅卓的这种过于魔幻的描写,有人提出质疑:这样的作品是否缺乏历史逻辑性?在面对这种质疑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在藏族的文化系统里,极富地方色彩的神与佛是无处不在的,它们内化在藏族人民的心灵深处,融化于藏族人民的生活样态之中,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方式。因此在藏族人民那里,不需要明确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他们深信不疑的“虚幻”必然会由作家反映在文学世界里。④
以藏族身份进行汉语写作的扎西达娃和阿来同样如此,他们的作品也免不了“魔幻”书写”,如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和阿来的《尘埃落定》《灵魂之舞》等。需要说明的是,三者的魔幻书写各有特色。阿来的小说注重描述传统体制崩溃、信仰瓦解的过程,以冷静的姿态观望民族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逐渐消逝的必然趋势,面对藏族不切实际的信仰成分,阿来是秉持批判的态度的,因此他的小说的魔幻色彩并没有扎西达娃和梅卓那样奇异、浓厚,而是呈现出了似真似幻、似实似虚的特色。与此相比,扎西达娃的魔幻书写充满神性的意味,他的小说在于重构历史,建立对人间净土 “香巴拉”的信仰,力图在藏族文化和魔幻现实主义之间寻找契合点。扎西达娃书写的是西藏化的魔幻,其中虽然也有现代文明与民族信仰的冲突,但更多是对已内化至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信仰的坚定守护,将其作为小说人物的精神寄托。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魔幻书写中,没有人比扎西达娃更能运用藏 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在这个层面上,梅卓与扎西达娃的魔幻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都 “不是故弄玄虚,不是对拉美的亦步亦趋,魔幻只是西藏的魔幻,有时代感,更有凝重的永恒感”⑤。但梅卓的魔幻书写呈现出更多的现代性思考,存在鲜明的女性意识,小说中种种魔幻事件几乎都是围绕女性产生的。和阿来相比,除了女性意识的呈现,梅卓的魔幻书写对民族文化的肯定成分更多。因此,我们不需要把关注点投射在作品是否过于虚幻,而更应该关注作家是否能对魔幻的东西信手拈来,将其天衣无缝地织补进现实情景,表现传统的人生。毫无疑问,梅卓是具有这种创作自觉的,这是梅卓独有的写作特质,不应当从别的文化语境中将它剥离。
除了 “万物有灵”民族信仰之外,对天葬、火葬、玛尼石、占卜、祭祀、打猎、美食美酒、民歌等风情习俗,梅卓也多有着墨。她总是多姿态地展示藏族民众的生活方式与认知观念,力图还原最真实的藏民族历史文化。
现在是一比十三,没有比这个比例更糟的。……“留下你们的狼皮吧!” 甲桑大喝一声,从半蹲的姿态中一挺而起,长刀挥舞开去,冲锋陷阵的两只狼 已被截断了前肢……夏布惊叹地查看着远远近近躺倒的狼只。⑥
藏民是天生的好猎手,甲桑在面对13头狼时英勇搏斗,毫不畏惧,血脉深处的自然野性未曾泯灭,这是梅卓对绝对力量的崇拜与肯定,显示出甲桑带领三个部落英勇反抗侵略者的典型英雄气质。而被称为狼人的甲桑,其孤傲独立的性格暗示了个人-民族觉醒的艰难历程,表明拯救民族危亡需要个人觉醒向民族觉醒的过渡。
可以说,民族信仰和民族生活方式参与且融入了梅卓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展示了藏族的历史。藏民族普遍存在和遵从的文化习俗作为一种历史的延续,代代传承,并融入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梅卓正是从藏民的生活出发,将藏族历史作为长篇小说历史叙事的一种表现形式,显示了藏族历史的多重维度。
二、对藏族历史的反思与超越
新时期以来,藏族作家的历史叙事越来越具有自己的主体精神的投射,他们都执着地弘扬民族文化,细致入微地描写西藏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融入对民族信仰的领 悟、对民族未来发展的感知。梅卓的小说创作并非局限于对藏族历史文化的陈述,流于 外部展示,而是利用历史叙事的技巧深入剖析并反思民族历史文化,表现出对重塑民族 历史、重铸民族品格和民族灵魂,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愿望。
梅卓小说通过再现藏族部落历史的兴衰,回顾藏族的生存和发展,多面性展示了藏族文化传统,维护具有地域特色的藏族文化,张扬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和勇猛果断、豪放热情、率直忠诚的民族品质,是对藏族文化强烈的自信心和认同感的表现。但是,对藏族文化存在的负面成分,梅卓有着清醒的认识、理性的思考,这使她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启蒙色彩,与同时期的藏族女作家央珍的《无性别的神》对藏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彰显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一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感性和敏锐的洞察力表达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个体生命、族群命运的体悟,自觉地探索民族出路,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认知。央珍的小说指出藏民曾信奉的寺庙也并非人间净土,而能真正带领人民走向新生的是现实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⑦,这是央珍探索出的民族发展的新出路。梅卓对传统信仰并不像央珍那样失望,她相信某些信仰仍然是民族探寻新出路的途径,阻碍民族前进的痼疾是可以通过重新审视民族文化而被剔除、取代的。如果说《太阳部落》对人的复杂性的书写还只是初露头角的话,那么《月亮营地》对人性的剖示就更为充分。甲桑误杀妹妹阿•玛姜后,脱离了部落生活,住在营地之外的玛尼石堆旁,刻玛尼石七七四十九天以忏悔,但同时他也在逃避现实,在民族危难之际只考虑个人情绪, 麻木而又固执地坚持己见。甲桑独战狼群的英雄精神被消解,而与甲桑类似的青年却沉 迷醉生梦死的堕落生活,头人懦弱无能、不听劝告,他们都对外界不闻不问,章代部落 的灭亡也丝毫不能让他们感知到近在咫尺的民族危机,“什么章代不章代的,跟我的狼 皮有什么关系。”⑧——这一切,几乎浇灭了部落生存的希望。本应引领民族前进、维 系藏民生活的神被消解,甲桑们在酒精和儿女情长中丧失了英雄品质,展现出复杂的人性。当男性不能解救民族于水火时,梅卓便把希望寄托于女性。阿•吉以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在神山祭祀仪式上就已暗示部落的命运,她亲历马家军团的残暴,深知他们的野心,对营地将要面临的危机有超乎寻常的敏感,以民族大义和博大胸怀唤醒了拯救民族的英雄一一甲桑。梅卓对历史英雄的叙事表现出她对民族的回眸和审视,即使对不堪回首的、血腥惨烈的记忆有着无法填补的缺憾和无能为力的悲痛,也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历史的回望中坚定地将批判的笔触指向民族内部,去分析藏族部落的群体形象,看到 藏民族危机的本质所在——缺乏民族文化认同感,并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失忆症唤醒民族同胞:铭记历史,坚定信仰。
另外,在反思的过程中,梅卓化悲痛为力量,带着希望探寻族群命运,以一种超越性的眼光思考个体与群体、个人意志与民族意识如何取得平衡的问题。当群体处于一种 溃散的状态时,个体能否超越群体凌驾于历史之上?梅卓赋予阿•吉化度冥顽不灵的男性英雄的能力,使她成为圣杰化、女性化的民族话语代言人。⑨也就是说,作为女性的、个人的阿•吉并不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全部力量,只有把“孤独无助的个体生命汇入浩浩荡荡的群体生命”,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民族洪流”⑩。阿•吉的民族大义只有结合民族群体才得以实现,独行的雪豹被甲桑射杀正有此隐喻,这也是梅卓渴望重塑民族历史,构筑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原因。同时,女性的启蒙能力没有成为主宰族群命运的绝对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梅卓鲜明的女性意识没有走向极端。如果过于强调宏大叙事和主旋律书写,那么文学所展示的内容只会空泛。即当个人意志被民族意识取代,发出宏大无我的呼唤,也会走向另一种极端。由个体意志逐渐转化为群体意识,再上升到民族意识,正是这样一种渐变,才更加表现出民族文化心理。梅卓以甲桑为代表,探索了个人意志向民族意识转向的路径。甲桑独战狼群大获全胜,但在面对部落面临唇亡齿寒的危机时,却麻木固执,沉浸在个人感伤和困顿中无法自拔:十年前对心爱的姑娘远嫁他乡耿耿于怀,十年后最爱他的母亲的突然离世对他造成二次打击,在与阿•格旺的争执中误杀亲妹妹阿•玛姜后他终于崩溃。此时民族危难仿佛已不足以与自身伤痛相提并论。甲桑虽然神勇过人,最具号召力,但对爱情、亲情、生命的迷惘导致他不能感知民族危机。直到阿•吉告诉甲桑乔是他们的孩子时,甲桑才打开心结,唤醒了身上原始野性的生命力。“他为了乔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他更愿意自己是战士”⑪,成功解救乔后,甲桑完成了本我向超我的飞跃,他意识到了死亡与生存的问题,加深了对生存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热爱:“他使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意义和蕴涵” “看到了生的延续是多么可贵”“他看到了自己的再生!那个流转着他青春的血液的小小身体,乔,他的儿子”⑫——与其说是甲桑,不如说是梅卓自己体悟了生命的意义。更进一步说,梅卓看到了个体意志的有限性,深入刻画甲桑冲破自我狭隘的个人情感去认识死亡的历程,表明只有融入群体、上升到民族层面的存在才能永恒。梅卓在小说最后描述三个部落终于联合为一体奔向战场,甲桑为解救族群而牺牲,马家军团溃败逃亡,乔即将成为带领民族走向新生的英雄,正说明了上升到民族层面的生存意义已经传达给广大藏族民众。
因此,梅卓对个人、群体、个人意志、民族意识的思考意在表明个人的启蒙意识、 领导力量对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当个人结合群体,个人意志转换为民族意识时, 叙事便有了意义的生成和升华。
三、审美追求及价值取向
《月亮营地》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承担着在当下的时间维度中寻找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的使命,显示了藏族文学创作的巨大潜力和独特魅力,有着不俗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梅卓的小说有着自身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文学自身就是一种审美方式……它证明着、显示着人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创造能力。”⑬梅卓是藏族作家,但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这样特殊的身份赋予了她进入文学空间的多重可能性。除了可以渗透汉民族精神摇篮、情感世界之外,还能因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新的审美眼光,洞观本民族的历史,产生新的发现和体验。表现在创作里,首先是梅卓采借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小说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审美价值。尤其是新奇、独特的魔幻书写,对不同的读者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效果。本民族的读者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特别是对“万物有灵”的传统信仰极为熟悉,因此魔幻书写能够激发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情怀,有益于重铸民族品格和民族灵魂。藏族之外的读者则会有陌生的审美体验,从而形成一定的审美距离。但随着审美经验的不断增加,他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作者达到内心共鸣,形成更为宏阔的文学理解,以肯定其中的文化认同,能够看到它们在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其次,梅卓秉持重塑民族文化认同这一观念进行创作,其作品离不开民族性,且时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梅卓更能贴近现实去思考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她在题材、内容上都选取与本民族相关的文化元素,并对它们进行提炼加工,揭示民族发展历史中存在的痼疾,探寻民族通往希望之地的路径,达到审美上的艺术性和民族性的互融,为历史叙事增添了创作活力和文学养分。随着民族文化认同的逐渐细化,梅卓对个体生命和民族生存做出辩证思考,让我们看到了民族信仰缺失的根源。回望历史的刀光剑影,族群对死亡与生存的关系的误解往往造成信仰的缺失,特别在生或死的两难抉择中总是陷入困顿,表现为族群的沉沦和迷茫,对现实的疏离,看不到危险来临,偶尔会有那么几个人说“让他出击,他会把这群外来人打他个落花流水”⑭的玩笑话,这样一种个体意志和生命力的委顿何尝不是一种民族困境。基于这种困境,梅卓凸显出重塑民族自信的重要性,秉持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希望,坚定重塑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信念,探索出一条由个体启蒙到群体团结,由个体意志苏醒到民族品格重铸的道路。随着创作的不断发展,梅卓超越民族自然风俗的表层书写,开拓出具有审美特征与价值取向的艺术世界。可以说,她将民族文化熔铸在历史叙事中,延续和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文化血脉和精神信仰,为藏族文学受众范围的扩大及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藏族文学和中国文学成为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提供了多种可能,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繁衍。
在现实层面,梅卓的藏地书写也表现出了深远的启迪意义。一方面,梅卓作为藏族女作家的代表,其创作有益地补充了当代文坛以男性为中心、以汉族为主流的现象所导致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缺失,使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得到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藏族文坛一直以男性创作话语为中心,这与时代背景、藏族社会生活有关系,女性处于边缘与失语的状态,就连央珍这样接受过汉文化教育的作家也在作品《无性别的神》中透露出对女性有机会接受教育的震撼,更不用说其他女性。梅卓的创作无疑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拨,有力地改变了藏族文坛长期处于男强女弱的局面,也将会 鼓励更多的女性去进行创作,使藏族文学大放异彩。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梅卓的女性 意识不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她以女性作家身份创作,代表女性发声,并不是在指斥男性 权力,而意在说明文学应多元化发展,藏族文坛多些创作话语,多些不同声音,这应是 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较好途径。
另一方面,梅卓文学创作拓展了学术研究价值,“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多样化的存在 方式为研究文学的规律提供了较为鲜活的材料和极大的阐释空间”⑮。以《月亮营地》为例,梅卓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民族色彩,她的思维方式、创作方法、文本形 式、语言表达等与汉族作家的作品有较大的差别,因而对理解、进而把握藏族文学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梅卓小说中的藏族地域特色、历史叙事、民族文化认同等都可成为绝好的研究话题,她把存在于民族内部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元素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给学者们提供了多样的考察方式。虽然梅卓不是书写藏族文化的第一人,但她的藏地书写因感性的认知和理性的思辨而有不同于其他藏族作家作品的特点。可以说,藏族作家梅卓的作品为丰富文学研究开拓了一条通道。
结语
从梅卓的长篇历史叙事作品《月亮营地》可以看出,她的创作既有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复归,又有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理性思辨,她在回望藏族历史中描摹藏族民众的生活图景,重塑民族文化认同,倾注了自己炽热的情感和冷静的价值判断,展示了藏民族的文化性格,剖析了他们的生存观,以其独特的视野客观地评判阻碍民族发展的痼疾,即狭隘的民族历史观和民族心理,显示出文学自觉意识和博大的文化胸怀。
注释:
①张懿红:《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②胡芳:《〈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梅卓小说之民族文化寻根》,《青海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③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④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
⑤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⑥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7页。
⑦耿予方:《央珍、梅卓和她们的长篇小说》,《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⑧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⑨王冰冰、白薇:《一个故事的3种说法:民族/历史叙事的弥合与分裂——藏族女作家梅卓小说论》,《西北 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⑩张懿红:《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⑪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⑫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 — 259页。
⑬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⑭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⑮张永刚、李雨君:《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研究》,《学术探索》2020年第7期。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科研,涉及“中国现当代重要文学现象”“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中国西部文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多有转载。出版著作、主编教材1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等项目多项,获教育部及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多项。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