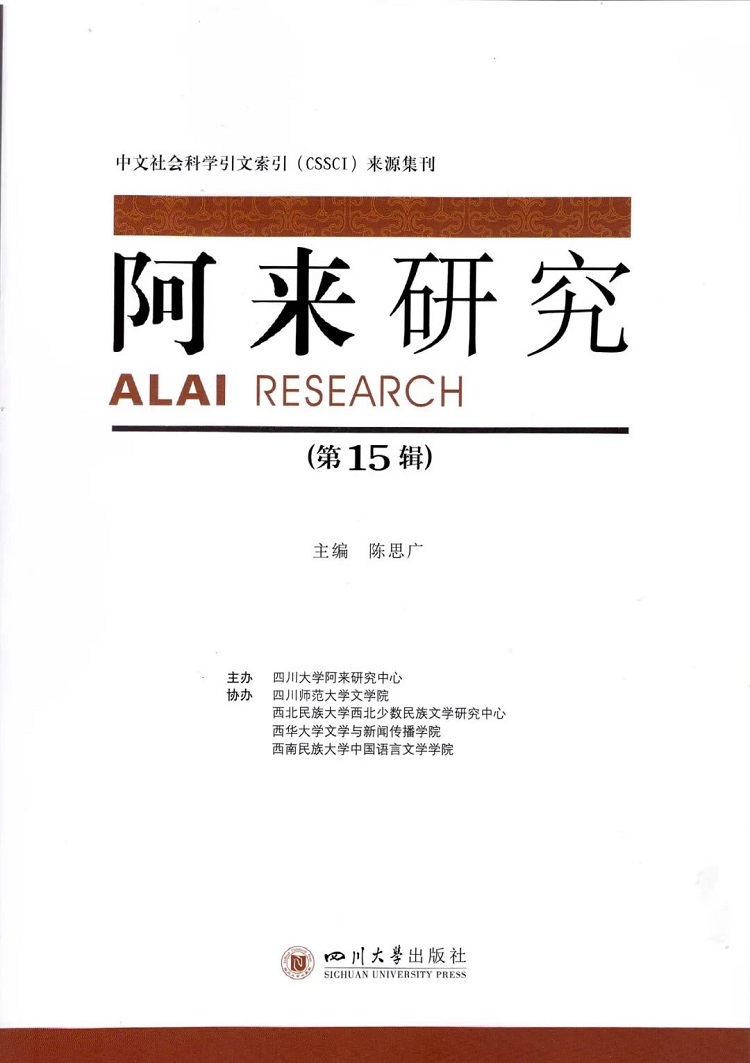
少数民族作家如何表现本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一位作家该如何鲜明地表现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特征,却又同时能规避刻意制造“民族性”所造成的生硬和片面。藏族女作家梅卓的散文创作通过“行走”的言说方式表现日常生活,为读者呈现藏民族文化的现状,用充满温情和信仰的笔描绘来自民间的力量。
一、民族立场与原始主义:梅卓的言说姿态
承认并激活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力因素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也因此融多民族文化于一体,并长期保持着各族文化的特色。多元复合的状态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生长的可能性,因为中华文化内部的主流因素与少数民族、异质文化等边缘成分碰撞,就有利于打破僵化的一元文化现状,从而使当代文化获得新的生机。同时,还避免了当代文化可能面对的窘境:要么被西方话语强行阐释,要么落入所谓国粹的旧圈。因此,让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借鉴与互补,并形成相互参照的价值体系,是顺应当下潮流发展的文化建构目标与追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现代文学的言说总是遵循着一套西方的话语体系, 它强调西方文化和思想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和浸染,这种方式显示出用欧洲中心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态度。因此中国文学陷入一种无法被“正名”的状态,存在着“基本概念的混乱”1。加之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市场化、殖民化与工业化皆在不遗余力地推广西方现代文明的经验,作家们竟也将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一种解放的话语与文学范式,而忽略保持个性的重要性。“许多中国作家将西方现代主义等同为现代性的符号和解除中国传统文化合法性的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受虐性的自制行为……在中国现代主义者的写作中,缺乏一种对西方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语境的自觉反思2当西方文化的版图逐渐扩张,受到影响的其实不仅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立性,还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城市化的进程渗透了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让人身不由己地卷入一体化的进程。从文化转型和更替来看,环境相对封闭地区的民族追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逐渐舍弃自己民族独特性的过程,而若要坚守自己文化的个性则又会与外来文化绝缘。所以本土化和全球化拉锯式的牵扯便给少数民族作家带来阐释的焦虑以及可供挖掘的土壤。
健全的文化应在多元共生、自由竞争的环境中生长,因而民间的、边缘的、原始的文化形态在当代更应作为一种独特的力量来参与文学的建构。对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而 言,他们需以外来思想作为手段,挖掘沉睡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记忆,拒绝遗忘,唯有 这样,才能将本民族厚重的文化资源激活,并让其以全新的面貌打破被边缘的格局,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建构的重要部分。梅卓正是这样努力尝试的一位作者。
当下对梅卓的研究多是从其小说入手的,目光也较多地集中在其小说所呈现出的民族性特征以及民族性想象之上,或是从梅卓的叙事技巧、女性立场、语言风格来对其作品进行言说。“她对藏文化的再现,有自己独特的想象路径,即:其一是在生死爱欲中反思历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集体主体性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其二是通过话语转换,使藏文化传统融入城市写作、女性写作,在拯救失落的现代爱情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爱情的悲剧性。此外,梅卓小说渲染藏文化的神奇魅力,富有象征意象,语言典丽流畅。”3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梅卓小说提供了途径,却并不能作为一面镜子来映现梅卓其他的文学创作,例如散文。
散文在梅卓的文学创作整体中具有独特的魅力。梅卓在小说创作中多用文体实验的笔法对藏族部落史进行艺术重构,比如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用小说建构藏民族生活的常见仪式、事物。在《麝香之爱》中,梅卓则一改对边缘生活的书写,转而反映藏族人进入都市后生活、心理的种种变化。而在《神授•魔岭记》中,梅卓更是通过魔幻主义的创作手法,以神魔、精灵、穿越等题材,展现藏文化的瑰丽与丰富。综上所论,梅卓的小说创作呈现出题材选择的自觉,她更多在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中展示藏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通过人物命运的遭际暗示对藏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的隐忧。但在其散文创作中,梅卓却有意地避开小说中挥之不去的严肃与沉重,而以“行走”的方式对藏民族文化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呈现。
从《人在高处》《藏地芬芳》到《走马安多》,这些散文集共同组成梅卓的“行走”系列的散文。在这些散文集中,梅卓的自觉言说较之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更为自信的状态,她展现了宗教、建筑、风俗、生死、婚嫁、灵童、骏马、饮食、歌词等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常见事象。这种自信源自作家强烈的族群认同感,也因为作者终于不依靠现代 的手法和技巧乃至某种立场,终于能在淘洗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开始以沉潜的目光来审视周围的人与事,并以悲悯的目光来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在经历了地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行走之后,梅卓化身为她笔下人群中的一员,观察着身边的人与事, 并用充满温情的笔触展示他们精神的富足。
梅卓散文的这种书写方式可以用原始主义进行阐释。原始主义是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的,他从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等方面阐释原始文化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它能作为探求进步、克服阻碍的方式,对整个文明产生影响。譬如泰勒提到宗教仪式的特点是拥有“惊人的永恒不变性……保留着远在历史范围之前的漫长时期中的那种形式和意义”4,所以这些仪式能超越时间的限制在前人与后人之间产生一系列奇妙的联系,最终实现泰勒所说的“万物有灵但同时,泰勒也意识到,“当向人之无形的奉为神的灵魂祈祷的时候,则这祈祷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们之间日常交际的进一步发展……祈祷既是理性的行为,也是实际的行为”5。所以祈祷等宗教行为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更成为梅卓笔下藏民族寄托情感的途径。有研究者尝试对原始主义进行定义,其认为其主要有三层含义,“分别是人性的原始主义、文化的原始主义和文学的原始主义”6。在这种阐释之下,原始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人类的情感而存在的,是人对所经历过的生命历程的价值评判,既包括对先民的追思,又含有对个体生命中童年时期的怀念。梅卓在散文中所呈现出的对藏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的追思,实际就饱含着原始主义的情感。她透过人文现象,去挖掘行为与习惯之下的人性因素;她通过追怀过去,试图寻找藏民族信仰的生命价值。所以梅卓的散文中充满着原始主义的情感,这种情感却又如人的爱憎、欲求一般,以常态化的形式出现,它的价值在于人对过往生命的再次审视。其次,原始主义是一种尚古的文化思潮,以原始和自然的文化状态作为当下文化价值评判的标准,要求文明呈现返璞归 真的效果。细读梅卓的散文可以发现其中有以藏民族文化心态来审视当代文明发展的特点。再次,原始主义还呈现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倾向,它把原始文化生态与现代文明进行对比,同时艺术上借鉴原始神话等超现实主义手法,这一点更多地体现在梅卓的小说创作如《神授•魔岭记》之中。
在梅卓的散文中,对藏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对都市及现代人的质疑,对藏族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的赞美与对现代文明的反讽,同时构筑起她原始主义创作理念中互补的两面。她的笔下,藏族少数民族地区原始性的民风民俗成了通往神性永恒的所在,对宗教、建筑、风俗、生死、婚嫁、灵童、骏马、饮食、歌词等藏族日常生活的书写,都幻化为牧歌般的诗意描绘。而原始主义的创作立场也更多反映出梅卓的创作和言说姿态。
二、宗教与习俗:梅卓散文的藏族风情
原始主义文学批评在具体的实践中常常借助原型批评和文学母题出现。弗洛伊德因 揭示人的精神结构而闻名于世,他认为人的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部分: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无意识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中更深的层次,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真实和本质的部分。荣格拓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还有非个体层面,自远古的祖先时期到当下存在一种代代相传的经验,并且这种经验会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记忆模式,简称“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使得某一族群的作家对某种原型或原始意象产生特殊的关注,这种历史中重复的生命痕迹构成了他们创作的深层动因。在梅卓的散文中,原始主义倾向的着力点便呈现在宗教与习俗这两个原始母题上,宗教沟通了肉身与灵魂,习俗串联起日常生活,类似于弗洛伊德所指涉的死本能与生本能。宗教与习俗交织在梅卓的“行走”系列散文中,带有深刻的原始意识,而以“行走”的方式来重新审视民族历史,则又显现出一种自觉的寻根意识。
在梅卓散文中,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有对寺庙、僧侣、佛教、信仰相关人和事的言 说。在《藏地芬芳》之中,梅卓其实已经借人物之口述说了 “行走”的意义,即“为后 人留下一份民间文化的调查卷宗”7,因为有感于优良传统的消失,这“表现在人们的 心理素质以及外在的生存环境上,包括服饰、建筑、民间和宗教文化的传承”8,所以 试图通过“行走”来展示藏民族的生活现状。梅卓认为,藏文化在当代大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宗教精神,同时藏文化得以完整保存也是靠寺院传承,青藏高原的每一座寺院本质上都是一座繁荣的博物馆,其中的人文景观无疑是精华所在。在对宗教的介绍中,梅卓一面向读者介绍雪域地理风情,一面又对藏族四大支系的异与同进行梳理。寺院、活佛、朝圣、密修、轮回都生动地呈现在她的文字中,展现了一个普通人变成佛的过程,又通过展现佛的行动和信仰而把他还原成人。譬如在写到拉卜楞寺的时候,梅卓称这座寺庙为拉让(活佛宫殿),它背依飞凤山,面临大夏河,把曾经政教合一的至高权威描绘在庄严的金顶上,整体建筑鳞次栉比,蔚为壮观。但梅卓并未止步于对寺院神圣的描绘,而是笔锋一转,继续描写与拉卜楞寺密切相关的僧侣俄旺宗哲。梅卓从他出生面带笑容的不凡写起,一直写到1709年主持建设拉卜楞寺并使之成为东北藏的宗教、文化中心,俄旺宗哲一生的传奇与经历便与这座寺庙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而其肉身灵塔 至今供养在寺中,留给后人无限的敬仰。
与宗教、寺庙相联系的,还有梅卓对寺中建筑、陈设和日常活动的书写。拉卜楞寺的主要建筑有大经堂、狮子吼佛殿、贡唐宝塔、大金瓦殿、灵塔殿等,教育体系为六大学院,最盛时可供四千僧侣学习,是享誉青藏高原的高等学府。而近三百年的历史,亦让拉卜楞寺成为一座琳琅满目、包罗万象的博物馆,大到高15米的弥勒佛像,小到盈寸的木雕,贵重如公元8世纪传下的佛祖像,更有红珊瑚树、纯金藏塔、珍珠宝塔、象牙法衣、玉石佛像等奇珍异宝。宗教的神圣、僧侣的传奇、寺庙的雄伟、陈设的丰富 信仰的虔诚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梅卓对宗教文化的书写,这也是她以文化传承者的身份所做出的自觉言说。
但藏民族的虔诚信仰并不仅仅体现在拜佛与诵经之中,他们生活的细节里更是充满了对神的尊崇,这种情结让他们在面对群山、河流时,心中的神圣感都会油然而生。梅卓写到玛曲的人们煨桑(一种宗教祭祀仪式,点燃柏枝、青裸,以供养神灵)时要呼唤神山们的名字。每一座神山都拥有自己的名字,也拥有不同的法力,例如诺日敖巴神山主司医药,山下有药水泉,能治胃病和胆囊病;华木喝尔是牧神,牧人拜他,羊的数量可以增加。除拜神之外,郎木寺的僧人们还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三举办晒佛节,他们拿出珍藏的巨幅织锦唐卡佛像,挂在山坡上,供信徒们瞻仰,吸引成千上万的朝拜者。梅卓对藏民族宗教的自信言说有其特殊意义。藏族民众向来重视精神生活,强调佛教教义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对藏民族而言,精神的追求远远高于对物质的渴望。藏民族聚居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生产力水平也并不高超,但他们仍努力创造灿烂的精神文化,这与整个民族对宗教的虔诚信仰是分不开的。
除宗教外,梅卓散文还充溢着对习俗的刻画,习俗主要是以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在其散文中的。梅卓的“行走”系列散文重在以平视的目光、体验的姿态去感受藏民族的日常生活,在其行走的过程中,读者能感受到祖先、语言、宗教和民俗带来的多方位的文化体验。梅卓原生的族群认同感带给她一种富有天分的审视视角,使她能够细腻地表现这种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这种体悟是有别于他者视角的,对于梅卓而言,这种远离尘嚣之美就是一种生活,藏族文化就是她的生活方式本身。习俗的魅力在梅卓《藏地芬芳》《走马安多》等散文集中首先体现在藏族服饰的精巧上。譬如《若尔盖到川主寺》 一文中,梅卓写到曼格智格的僧靴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一双深红色的靴子,崭新的靴面上没有一丝折纹,式样仍是传统的,敦实的靴底,圆厚的靴面,直筒的靴腰,靴尖微微卷起,走起路来没有声响。我看着满心欢喜,这么大冷的天,这双靴子看上去非常暖和。”9除此之外,僧人们还会佩戴象牙念珠和马鞍戒指,虔诚地向神佛祈祷。梅卓笔下的藏族妇女衣饰也很考究。老太太们的头饰较为特别,一块头巾顶在头上,长辫子及续辫盘在头巾上用来固定,头巾有红色、暗红色和红黑格子相间几种。而年轻妇女的头饰则更为讲究,镶着琥珀和珊瑚,胸前挂着象牙念珠,围裙干干净净的。梅卓展示出的藏族人民的服饰穿越时间的长河,未受外界潮流的影响,始终保持着传统风格,或许在他们心中,外物皆为形役,唯有流传下来的历史和信仰,才是最珍贵的认知和记忆。
从生到死是人的宿命,梅卓在散文中亦展现出藏民族对生与死的态度。对于生,他们没有过多欲望诉求,“主妇依然像从前的所有日子一样,把第一勺酸奶敬奉给灶神和天地,感谢大自然无私的赐予,对于藏人来说,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由来已久的世界观”10。而对于死,藏人似乎也别有一番超然之态。梅卓在《孝的安多方式》中记录 她参与一位老人松更节的见闻。松更是在老人去世前儿女为他们举办的礼敬佛法、布施 大众的大规模善事活动。老人们年过五十,权力交付儿女后,就算是人生大事基本完成,“生”的责任全部尽到,开始为身后事打算,平时除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之外,主要以诵经祈祷度日。在松更节上,主人极尽招待之能,伴随着僧侣们抑扬顿挫的诵经声, 客人们尽享美食,欢声笑语。在这种氛围里,索南才让老人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他轻松地谈到死亡,认为经过了松更节,对于死亡便再也没有顾虑,将来也不会误入歧途, 因为孩子们已经为他修好了来世的路,他辛苦的一生已经有了最好的报答。在梅卓的笔下,藏族人对生与死都呈现出一种达观的姿态,他们或许会为失去亲人而痛苦,但他们更多是把这种痛苦当成此生的历练,痛苦让他们更倾心于宗教的神圣。
在刻画藏民族习俗的过程中,梅卓还引入了对婚礼和丧仪的描写。例如婚礼第一步一定要请僧人诵经,择定结婚吉日和送亲迎亲的良辰,迎亲人数不限,但只能去单数,不能去双数,空额是为新娘留的,以示欢迎新娘从此正式成为新郎家的成员。对于丧葬,梅卓也写到了一些禁忌,比如家里或村里人死后忌谈笑、歌舞,服丧49天内忌洗头、沐浴、饮酒、盛装,平时忌提死者名字,等等。而贯穿梅卓散文的,则是以平缓细腻的笔触叙写的藏族人日常生活点滴,其中有他们的饮食习惯,有他们饲养的骏马,有灵童的发现,有青年男女的舞蹈和歌声,亦有节日时的祭祀与欢乐。
对于梅卓散文中的表现内容而言,她自觉言说的姿态很难只用心怀藏地、挂念故土等词来总结,而更像是一种宿命般的选择。梅卓从小对藏族的生活方式耳濡目染,随着她的成长,这种故土情结已在她心里生根发芽。所以梅卓自创作以来就始终关注着这片大地,这是一种来自血脉内部的选择,更是藏文化本身所包含的强大生命力。从小说到散文,对藏文化的言说在梅卓的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在《太阳部落》《月亮营地》 等小说中,梅卓是带着发掘藏文化特色的眼光去进行书写的,她也借此构筑了自己的小说中的部落特征和游牧生活,因此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小说这一文体的局限使梅卓更多地去关注藏民族人性层面的价值,试图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希冀和诉求,这就部分地脱离了客观的描绘。而在《藏地芬芳》《走马安多》等散文中,梅卓则真正把自己沉潜下来,去体悟、感受、呈现周遭的世界,显示出她创作心态的成熟。
三、“行走”与“万物有灵”:梅卓散文的言说立场与方式
论及梅卓散文的言说方式与艺术技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行走”的方式和“万物有灵”的视角。
梅卓曾在《走马安多》的后记中写道:“我至今不明晰游走的意义在于什么。但我喜欢这样的游走。多年前我开始文学创作,也开始了这种漫无目的的游走。无疑,文学创作与作家的内心世界不可分割,但我却更久、更深地沉溺于外部。游走的积累和经验在我是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使它们纯粹,成为一篇篇文章。”11对于梅卓而言,行走并不意味着要征服自然,而更多在于感动。她通过行走流连于青藏高原宏伟的寺庙、青翠苍茫的草原、曲径通幽的静修之地中,也享受着与世无争的和谐。更让她感动的是,“行走”能够让她真实地体察当代藏族人的生存现状,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如生死、嫁娶、歌舞、朝拜等,感受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值得注意的是梅卓在行走和书写中表达出的文化相对观。梅卓游历藏族地区,对影响藏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进行了探究,她按照藏民族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观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思考,肯定其价值,但并不表现出民族的自我中心意识,显示出客观与审慎的姿态。
在梅卓的散文中,藏文化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与都市文化带来的物欲满足是不同的。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漠,作为个体的人感到无比的孤独。而藏文化却始终保持着古老文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受其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源于藏民族的佛教传统,这种坚定的信仰在当今这个变动的时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要想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独立性,在当代多元化的时代中也绝非易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卓同其他民族作家一样坚守着知识分子写作的立场,建构着她的藏文化世界,同时又有意识地选择言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民族文化,既为保存独立的民族文化而努力,也为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了力量,这就体现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责任意识。
除了言说立场之外,梅卓散文的艺术特点还体现在其言说方式上。梅卓倾心原始的藏文化传统,是受了原始主义的影响。而当原始主义进入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浮出水面:怎样将藏民族原始生活的内容上升到艺术的层次?爱德华•泰勒将关于精灵的学说称作“万物有灵观”12,原始人通过为自然物创造浪漫神话来实现人性与神性的统一。梅卓在散文中首先是有意识地对地名与人名做特殊化的处理,即采用藏语音译,如用“阿咪东索”代替牛心山,用“宗姆玛釉玛”代替卓尔山,用“青唐”代替西宁,等等。这种处理能让读者穿越现实回到遥远的过去,在尘封的历史中徜徉,享受时空穿梭带来的陌生感和神圣感。其次,梅卓散文中还细致地描绘了藏民族由于受 “万物有灵观”的影响而为神山、湖泊所创造的美丽神话。譬如“卓尔山属于丹霞地貌, 由红色砂岩、砾岩组成,在太阳的照耀下,它呈现出鲜艳的丹红色,藏语称为‘宗姆玛釉玛',意为红颜王后,赞美她色若沃丹、灿如红霞的美貌。相传宗姆玛釉玛原是龙王的公主,与阿咪东索是情深意重的情侣,由于违反龙、神两界不能相恋的天条,被惩罚化作了石山,但她与阿咪东索坚守爱情誓言,千百年来默默相守,今天我们看到的仍然 是他们不离不弃的身影”13。在这一段记录中,冰冷的地名被添加上了拟人化的名字, 这就为现实的场域平添一份生命力和活力感。梅卓在此用神话的形式,为本民族文化又 赋予了厚重的历史外衣,显示出她对民族传统的充分理解和化用。
注释:
1.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正名"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版,第17页。
3.张懿红:《梅卓小说的民族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4.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97页。
5.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页。
6.方克强:《原始主义与文学批评》,《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7.梅卓:《藏地芬芳》,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
8.梅卓:《藏地芬芳》,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3页。
9.梅卓:《藏地芬芳》,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10.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1.梅卓:《月亮营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4页。
13.梅卓:《走马安多》,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高晓瑞,女,四川自贡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文化研究。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