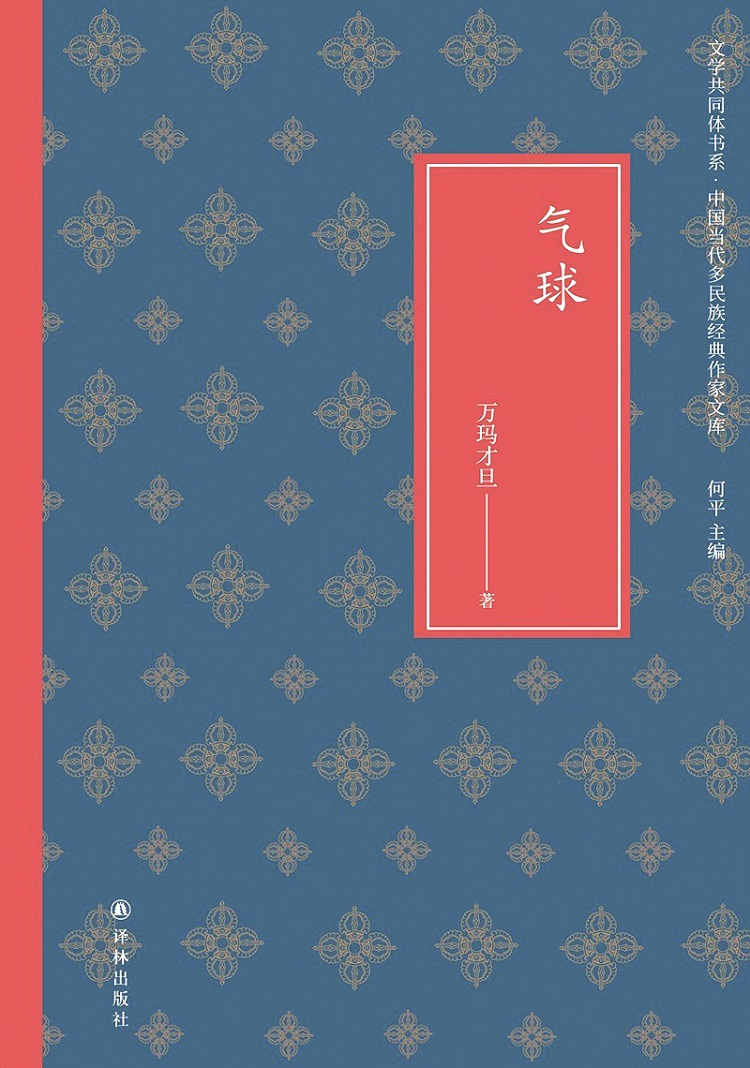
дёҮзҺӣжүҚж—ҰжӣҙеӨҡдёәе…¬дј—жүҖзҶҹзҹҘзҡ„пјҢжҳҜз”өеҪұеҜјжј”иҝҷдёӘиә«д»ҪгҖӮд»–зј–еҜјзҡ„гҖҠйқҷйқҷзҡ„еҳӣе‘ўзҹігҖӢгҖҠиҖҒзӢ—гҖӢгҖҠеЎ”жҙӣгҖӢгҖҠж’һжӯ»дәҶдёҖеҸӘзҫҠгҖӢгҖҠж°”зҗғгҖӢзӯүз”өеҪұжӣҫеңЁеҗ„еӨ§йҷўзәҝзғӯжҳ 并иҺ·иҝҮеҗ„з§ҚеӣҪеҶ…еӣҪйҷ…еҘ–йЎ№гҖӮ然иҖҢпјҢиҝҷдәӣе……ж»Ўжө“йғҒзҡ„и—Ҹең°йЈҺжғ…е’Ңж–Үиүәж°”жҒҜзҡ„з”өеҪұпјҢеӨ§йғҪж”№зј–иҮӘдёҮзҺӣжүҚж—Ұжң¬дәә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пјҢд»–еңЁж–ҮеӯҰдёҠзҡ„иө·зӮ№иҰҒжҜ”з”өеҪұж—©еҫ—еӨҡгҖӮиҝ‘е№ҙжқҘпјҢдҪңдёәе°ҸиҜҙ家з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ҠжқҘи¶Ҡиў«иҜ»иҖ…дәІиҝ‘е’Ңи®ӨеҗҢгҖӮд»–еҜ№и—Ҹең°ж•…д№ЎеӯңеӯңдёҚеҖҰең°жҢ–жҺҳе‘ҲзҺ°дёҺзҺ°д»Ји§Ӯз…§пјҢд»–еңЁз”өеҪұдёҺе°ҸиҜҙдёӨдёӘйўҶеҹҹйҮҢзҡ„еҸҢж –е№¶иҝӣдёҺзӣёдә’жҲҗе…ЁпјҢйғҪи®©жҲ‘们зңӢеҲ°ең°еҹҹеҶҷдҪңдёҺи·Ёз•ҢиһҚеҗҲзҡ„еӨҡз§ҚйЈҺиІҢдёҺж–°зҡ„еҸҜиғҪ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пјҡвҖңжҲ‘жёҙжңӣд»ҘиҮӘе·ұзҡ„ж–№ејҸи®Іиҝ°ж•…д№Ўзҡ„ж•…дәӢпјҢдёҖдёӘжӣҙзңҹе®һзҡ„иў«йЈҺеҲ®иҝҮзҡ„ж•…д№ЎвҖқпјҢиҝҷеҸҜи§ҶдҪңд»–зҡ„еҶҷдҪңиҮӘзҷҪгҖӮжңүйЈҺд»Һи—Ҹең°еҲ®иҝҮпјҢйӮЈжҳҜйқ’и—Ҹй«ҳеҺҹдёҠз©әеҫҗеҫҗеҗ№жӢӮзҡ„зҺ°д»Јд№ӢйЈҺпјҢж’¬еҠЁзқҖжҲ‘们еҜ№дәҺжң¬еңҹдёҺеӨ–жқҘгҖҒдј з»ҹдёҺзҺ°д»ЈгҖҒиҫ№ең°дёҺж—ҸзҫӨзҡ„жғҜжҖ§жҖқз»ҙе’Ңеӣәжңүи®ӨзҹҘпјҢд№ҹз»ҷиҝҷзүҮеңҹең°дёҠзҡ„дәә们еёҰжқҘеҶІеҮ»дёҺеӣ°жғ‘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ҘиһҚеҗҲдәҶзҺ°д»Ји§ҶйҮҺзҡ„жң¬еңҹеҢ–еҶ…йғЁи§Ҷи§’пјҢжҸҸиҝ°и—Ҹж°‘з”ҹжҙ»зҡ„ж—ҘеёёдёҺеҸҳеҢ–пјҢе°ҠйҮҚдёӘдҪ“зҡ„зңҹе®һж„ҹеҸ—дёҺдҪ“йӘҢпјҢ并иҜ•еӣҫеңЁиҝҷз§ҚдёӘдҪ“еҢ–д№ҰеҶҷдёӯеҺ»дҝқз•ҷдёҖдёӘж—ҸзҫӨзҡ„зү№иүІдёҺж–ҮеҢ–пјҢе‘ҲзҺ°е…·жңүи¶…и¶ҠжҖ§зҡ„зІҫзҘһеҠӣйҮҸе’ҢдәәжҖ§дәәжғ…д№ӢзҫҺ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еҸҷдәӢз®ҖзәҰгҖҒзӯӢйӘЁжҜ•зҺ°пјҢж“…й•ҝжҠҪеҸ–ж—ҘеёёдәӢзү©иҝӣиЎҢж„Ҹд№үйҮҚз»„пјҢдҪңдёәдәәзү©ж•…дәӢзҡ„еҸ‘еҠЁжңәгҖӮеӨ§йҮҸзҡ„зӢ¬еҸҘжҲҗж®өпјҢеҸ°иҜҚиҲ¬зҡ„дәәзү©еҜ№иҜқпјҢиҝ‘д№ҺзҷҪжҸҸзҡ„еҠЁдҪңе·Ёз»ҶпјҢй«ҳжҪ®еӨ„зҡ„жҲӣ然иҖҢжӯўпјҢд»ҘеҸҠз”өеҪұиҲ¬зҡ„еңәйқўж„ҹе’Ңй•ңеӨҙж„ҹпјҢйғҪи®©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еҜҢжңүеҜҶеәҰе’Ңеј еҠӣгҖӮжңүеҚЎдҪӣе°ҸиҜҙжһҒз®Җдё»д№үзҡ„еҪұеӯҗпјҢжңүи—Ҹең°й«ҳеҺҹиӢҚеҮүзЎ¬зҳҰзҡ„зңҹе®һи§Ӯж„ҹпјҢжҲ–д№ҹз¬ҰеҗҲи—Ҹж—Ҹдәәзҡ„еҸЈеӨҙиЎЁиҫҫж–№ејҸе’Ңж°‘й—ҙеҸҷдәӢдј з»ҹгҖӮвҖңйқ’зЁһй…’вҖқеҺҹжң¬жҳҜи—Ҹең°еңҹдә§пјҢеҸҜжҳҜеӣ дёәе•ҶдёҡеҢ…иЈ…иў«еҲ’еҲҶдёәеҗ„з§Қзӯүж¬ЎпјҢжҳӮиҙөзҡ„йқ’зЁһй…’жүҚжҲҗдёәгҖҠзҢңзҢңжҲ‘еңЁжғід»Җд№ҲгҖӢйҮҢзҡ„еҸҷдәӢеҠ©жҺЁеҷЁпјҢжүӯиҪ¬дәҶжҙӣи—Ҹ家被дәәиҝҪеҖәгҖҒ家еҫ’еӣӣеЈҒзҡ„еҮ„жғ¶еұҖйқўпјҢд№ҹж”№еҸҳдәҶйҮ‘й’ұйӯ”еҠӣеёҰжқҘзҡ„дәәйҷ…жқғеҠӣе…ізі»гҖӮеӣ дёәжҙӣи—Ҹе–қзҡ„йқ’зЁһй…’д»·ж ји¶…д№Һжқ‘дәәжғіиұЎпјҢеҜ“зӨәзқҖж¬ еҖәдәәз”ұз©·еӣ°жҪҰеҖ’еҲ°иЎЈй”Ұиҝҳд№ЎгҖҒйҮҚе»әдёӘдәәиҚЈиҖҖзҡ„иә«д»ҪиҪ¬еҸҳпјҢд№ҹи®©еӨ§дјҷз”ұиҝҪеҖәзҡ„еҰӮж„ҝд»ҘеҒҝеҲ°еҜ№еӨ–йқўдё–з•Ңе’ҢиҚЈеҚҺеҜҢиҙөзҡ„еҗ‘еҫҖгҖӮеңЁе°ҸиҜҙгҖҠж°ҙжһңзЎ¬зі–гҖӢдёӯпјҢвҖңж°ҙжһңзЎ¬зі–вҖқдёҚд»…жҳҜжҖҖж—§д№Ӣзү©пјҢиҝҳжҳҜжҙ»дҪӣеҜ№еҘіеӯ©зҡ„иө дёҺгҖӮиҝҷи®©еҘіеӯ©жӯӨеҗҺзҡ„з”ҹжҙ»ж—ўе……ж»ЎиӢҰйҡҫпјҢеҸҲз»“дёӢдҪӣзјҳпјҡеӨ§е„ҝеӯҗиҜ»д№ҰеҺ»дәҶеӨ–ең°пјҢе°Ҹе„ҝеӯҗиў«жҢҮи®Өдёәжҙ»дҪӣиҪ¬дё–пјҢдёӨдёӘе„ҝеӯҗйғҪдёҚиғҪз•ҷеңЁиә«иҫ№пјҢжңҖеҗҺеҸӘиғҪз—…йҮҚж—¶жүҚдёҖ家еӣўиҒҡпјҢ并еңЁж°ҙжһңзЎ¬зі–зҡ„йҮҚжё©дёӯе“Ғе°қз”ҹжҙ»дёҺе‘Ҫиҝҗзҡ„зҷҫиҲ¬ж»Ӣе‘ігҖӮгҖҠеЎ”жҙӣгҖӢйҮҢзҡ„зү§зҫҠйқ’е№ҙз•ҷзқҖвҖңе°Ҹиҫ«еӯҗвҖқжң¬жҳҜдёәдәҶеўһеҠ дёӘжҖ§дёҺеӨ–иІҢиҫЁиҜҶеәҰпјҢ并йҡҗеҗ«дёҖз§ҚеҜ№еҘіжҖ§жғ…ж„ҹзҡ„жңҹеҫ…пјҢеҚҙеңЁиҝӣеҹҺз…§зӣёеҠһиә«д»ҪиҜҒ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иў«дәәеүӘеҺ»е°Ҹиҫ«еӯҗгҖҒйӘ—иө°еҚ–зҫҠй’ұпјҢдёҚдҪҶжіҜзҒӯдәҶдёӘжҖ§пјҢиҝҳиҝ·еӨұдәҶиҮӘжҲ‘пјҢйҷ·е…ҘзҺ°д»ЈзӨҫдјҡзҡ„ж—Ӣж¶ЎгҖӮ
еңЁеҸҷдәӢжҠҖжңҜдёҠ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ү№еҲ«ж“…й•ҝеҸҚжһ„еҶІзӘҒпјҢиҝӣиЎҢеҗ„з§ҚеҘҮеҰҷзҡ„е«ҒжҺҘе’Ңж··еҗҲгҖӮеңЁжңҖеә”иҜҘеҸ‘з”ҹеҶІзӘҒзҡ„ж—¶еҲ»иў«д»–жё©е’ҢеӨ„зҗҶжҲ–дёҖ笔еёҰиҝҮпјҢеңЁд№ з„үдёҚеҜҹзҡ„ж—Ҙеёёз”ҹжҙ»дёӯжҢ–еҮәеҶ…еҝғзҡ„жғҠйӣ·жҲ–ж•…дәӢзҡ„зҝ»иҪ¬гҖӮиҝҷиғҢеҗҺжңүең°еҹҹзҡ„еҢәеҲ«гҖҒж–ҮеҢ–зҡ„е·®ејӮгҖҒи§Ӯеҝөзҡ„зў°ж’һпјҢд№ҹжңүеӨҚжқӮзҡ„дәәжҖ§жғ…ж„ҹпјҢжӣҙдёҺдёҮзҺӣжүҚж—ҰејҖйҳ”еӨҡе…ғзҡ„жҖқз»ҙи§ҶйҮҺжңүе…ігҖӮдҪңдёәдёҖдҪҚд»Һи—Ҹең°иө°еҮәжқҘеҸҲдёҚж–ӯеӣһжңӣгҖҒж·ұж·ұзң·жҒӢзҡ„дәә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дҪҚжҺҘеҸ—дәҶзҺ°д»Јж–ҮжҳҺжҙ—зӨјеҜ№ж•…д№ЎжңүдәҶжӣҙеӨҡи®ӨиҜҶзҗҶи§Је’ҢзІҫзҘһе»әжһ„зҡ„дәә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Ҝ№иҝҷдәӣйҒ—еӯҳгҖҒе·®ејӮгҖҒзҹӣзӣҫдәҶ然дәҺеҝғеҸҲдёҚе…ҚиёҢиәҮгҖӮеҶІзӘҒзҡ„еҸҚжһ„ж¶үеҸҠдёӨжҖ§гҖҒд»Јйҷ…гҖҒеҗҢд»Јдәәд№Ӣй—ҙпјҢиҝҳж¶үеҸҠдј з»ҹдёҺзҺ°д»ЈгҖҒдё–дҝ—дёҺзҘһжҖ§пјҢжҳҜзҺ°д»ЈеҢ–иҝӣзЁӢдёӯи—Ҹең°дәәж°‘еҝ…然иҰҒйҒӯйҖўзҡ„зҺ°е®һеҸҳеҢ–гҖҒеҶ…еҝғз–јз—ӣд»ҘеҸҠзІҫзҘһеӣ°жғ‘гҖӮзҲұжғ…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йҮҢдёҚеҶҚжҳҜзӢ¬еҚ жҺ’д»–зҡ„пјҢиҖҢеҸҳеҫ—еҚҡеӨ§ж…ҲжӮІгҖӮгҖҠж°ҙжһңзЎ¬зі–гҖӢйҮҢжғ…ж•Ңзӣёи§Ғзҡ„дёӨдёӘеҘідәәз«ҹ然没еҸ‘з”ҹд»Җд№ҲеҶІзӘҒпјҢиҖҢзӯүеүІйәҰзҡ„з”·дәәеӣһжқҘиҮӘе·ұеҶіе®ҡпјҢеҪјжӯӨйҡҗеҝҚзҡ„жғ…ж„ҹдёӯе……ж»Ўз—ӣиӢҰдёҺжӮІжӮҜпјӣгҖҠзү№йӮҖжј”е‘ҳгҖӢйҮҢиҖҒдәәзҡ„第дёҖдёӘиҖҒе©Ҷеӣ дёәз”ҹз—…зӢ¬иҮӘеңЁеҺҝеҹҺдҪҸзқҖпјҢ并且иҜҙжңҚиҖҒ家зҡ„дёҖдёӘе№ҙиҪ»е§‘еЁҳе«Ғз»ҷдәҶиҖҒдәәгҖӮгҖҠж°”зҗғгҖӢе’ҢгҖҠж°ҙжһңзЎ¬зі–гҖӢйғҪе…іеҲҮеҘіжҖ§зҡ„иҮӘиә«еӨ„еўғгҖӮеҪ“е·Із»Ҹз”ҹдёӢдёүдёӘеӯ©еӯҗгҖҒз”ҹжҙ»еӣ°йҡҫзҡ„еҘідәәж„ҸеӨ–жҖҖеӯ•е№¶иў«и®Өе®ҡдёәдәІдәәиҪ¬дё–пјҢвҖңз”ҹдёҚз”ҹвҖқжҲҗдёәж‘ҶеңЁеҘ№йқўеүҚзҡ„е·ЁеӨ§йҡҫйўҳгҖӮеҪ“еҘідәәеӣ дёәдёҲеӨ«ж—©йҖқгҖҒдёҖзӣҙжғіз•ҷдёӘе„ҝеӯҗеңЁиә«иҫ№пјҢжІЎжғіеҲ°еӨ§е„ҝеӯҗжҳҜиҜ»д№Ұзҡ„еӨ©жүҚгҖҒе°Ҹе„ҝеӯҗиў«жҢҮи®Өдёәжҙ»дҪӣиҪ¬дё–пјҢвҖңз•ҷдёҚз•ҷвҖқжҲҗдёәеҘ№еҶ…еҝғеӯӨиӢҰеҸҲж— д»ҺйҖүжӢ©зҡ„з–‘йҡҫ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ҙеӣ жһңиҪ®еӣһжҳҜи®ӨиҜҶи—Ҹең°жңҖйҮҚиҰҒзҡ„ж„ҸиұЎпјҢ并дёәе…¶жіЁе…ҘзҺ°д»Ји§ҶйҮҺгҖӮжүҖд»ҘеҪ“дәҶжҙ»дҪӣзҡ„еӯ©еӯҗд№ҹжңүеӨ©зңҹиғҶе°Ҹзҡ„дёҖйқўе’ҢеҜ№жҜҚзҲұзҡ„жёҙжұӮпјҢиҖҢиҪ¬дё–жҙ»дҪӣзҡ„е“Ҙе“ҘжҲ–еҗҢеӯҰд№ҹдјҡеҜ№е…¶дә§з”ҹеҸҲзҶҹжӮүеҸҲеҲ«жүӯгҖҒеҸҲдәІиҝ‘еҸҲ敬з•Ҹзҡ„еӨҚжқӮж„ҹеҸ—гҖӮиҝҷдәӣеұӮеұӮеҶІзӘҒпјҢжҳ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е…іжіЁж•…д№Ўзҡ„еӣ°жғ‘е’Ңз–јз—ӣпјҢд№ҹжҳҜе…іеҲҮдәәд№Ӣдёәдәәзҡ„з”ҹеӯҳд№ӢиӢҰдёҺзІҫзҘһеӣ°еўғ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иҜҙжӣҙеҪ°жҳҫеҮәе…·жңүи¶…и¶ҠжҖ§зҡ„дәәжҖ§дәәжғ…д№ӢзҫҺгҖӮи¶…и¶ҠиҮӘжҲ‘и¶…и¶Ҡдё–дҝ—и¶…и¶ҠзҰҒеҝҢпјҢжү“йҖҡз”ҹдёҺжӯ»гҖҒеӨ©дёҺең°гҖҒеҮЎдҝ—дёҺзҘһеңЈгҖӮ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йҮҢзҡ„еҲ»зҹіиҖҒдәәеҸ—дәәд№Ӣжүҳз»Ҳдәәд№ӢдәӢпјҢеҚідҫҝжӯ»еҗҺд№ҹиҰҒеңЁжңҲе…үдёӢеҲ»е®ҢжңӘз«ҹзҡ„е…ӯеӯ—зңҹиЁҖжүҚеҺ»еҫҖз”ҹ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Җҹе–қй…’гҖҒжўҰеўғи®©дәәзү©йҳҙйҳіеҜ№иҜқгҖҒз”ҹжӯ»зӣёйҖҡпјҢж—ўжҳҜеҜ№жүҳд»ҳзҡ„дәӨд»ЈпјҢд№ҹжҳҜз§Ҝеҫ·иЎҢе–„еҪ°жҳҫеӨ§зҲұгҖӮгҖҠе…«еҸӘзҫҠгҖӢйҮҢдёӨдёӘиҜӯиЁҖж–ҮеҢ–дёҚйҖҡгҖҒж №жң¬ж— жі•дәӨжөҒзҡ„йҷҢз”ҹдәәпјҢжҳҜдәәжҖ§дәәжғ…让他们и¶ҠиҝҮеӣҪж—ҸдёҺиЎЁиҫҫзҡ„и—©зҜұпјҢеҝғж„ҸзӣёйҖҡең°жҠұеӨҙз—ӣе“ӯгҖӮгҖҠзү№йӮҖжј”е‘ҳгҖӢйҮҢзҡ„иҖҒдәәжү“з ҙзҰҒеҝҢеҺ»еҪ“зҫӨдј—жј”е‘ҳдёәзҺ°е®һи§ЈйҡҫпјҢжҳҜеҜ№дҝЎд»°зҡ„и¶…и¶Ҡе’ҢдәәжҖ§зҡ„еҚҮеҚҺгҖӮгҖҠж°ҙжһңзЎ¬зі–гҖӢйҮҢзҡ„еҘідәәи®©йәҰе®ўи·ҹзқҖжқҘжүҫд»–зҡ„иҖҒе©Ҷеӯ©еӯҗеӣһ家пјҢзӢ¬иҮӘжҠҡе…»е°Ҹе„ҝеӯҗпјҢеҸҜжҳҜеҗҺжқҘзҡ„жҜҸдёҖе№ҙйәҰе®ўеӨ«еҰҮйғҪи·‘жқҘеё®еҘідәәеүІйәҰеӯҗпјҢйәҰе®ўжӯ»еҗҺд»–еҰ»еӯҗеҸҲеёҰзқҖдёӨдёӘеҘіе„ҝжқҘеё®еҝҷгҖӮиҝҷж ·дёҖз§Қе…·жңүи¶…и¶ҠжҖ§зҡ„жғ…д№үжҺҘеҠӣе’Ңз”ҹе‘Ҫе’Ңи§ЈпјҢй—ӘзғҒзқҖдәәжҖ§дәәжғ…зҡ„жё©жҡ–зҫҺеҘҪ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ҘзӢ¬еұһдәҺиҮӘе·ұзҡ„ж–№ејҸпјҢд»ҺеҶ…йғЁжү“йҖҡдәҶи—Ҹең°ж•…д№ЎдёҺзҺ°д»Јдё–з•Ңд№Ӣй—ҙзҡ„йҖҡйҒ“пјҢжҸӯзӨәзҺ°д»Је®Ўи§ҶдёӢзҡ„и—Ҹең°еҜҶз ҒдёҺз”ҹжҙ»еӣҫжҷҜпјҢ并具жңүжҳҺжҳҫзҡ„еҸҢж –йЈҺж јгҖӮиҝҷйҮҢзҡ„еҸҢж –пјҢдёҚд»…жҢҮд»–еңЁз”өеҪұдёҺе°ҸиҜҙдёҠзҡ„еҸҢйҮҚе»әж ‘пјҢеңЁзІҫиӢұдёҺеӨ§дј—гҖҒдёҘиӮғдёҺйҖҡдҝ—дёҠзҡ„еҸҢеҗ‘еҠӘеҠӣпјҢиҝҳжҢҮд»–еңЁж—¶д»ЈиҜӯеўғдёӢеҜ№ең°еҹҹж—ҸзҫӨиҜӯиЁҖж–ҮеҢ–зҡ„ж•Ҹж„ҹдёҺиҮӘи§үпјҢеңЁеҶ…е®№йЈҺж јдёҠе…·иұЎдёҺжҠҪиұЎгҖҒзҺ°е®һдёҺи¶…жӢ”зҡ„з»“еҗҲпјҢиҝҳжңүжң¬еңҹдёҺеӨ–жқҘзҡ„зў°ж’һпјҢдј з»ҹдёҺзҺ°д»Јзҡ„ж‘Үж‘ҶпјҢзү©иҙЁдёҺзІҫзҘһд№Ӣй—ҙзҡ„еҪјжӯӨзӣёдҫқеҸҲзӣёдә’жҠөзүҫгҖӮжӯЈжҳҜиҝҷдәӣйҳ”еӨ§дё°еҜҢзҡ„еҸҢж –е…ғзҙ 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иә«дёҠиҮӘз”ұеҲҮжҚўдёҺеӨҡйҮҚиһҚеҗҲпјҢжүҚеёҰжқҘеҘҮеҰҷзҡ„еҢ–еӯҰеҸҚеә”дёҺзҫҺеӯҰж•ҲжһңпјҢи®©д»–зҡ„и—Ҹең°ж•…дәӢеҘҮејӮзңҹе®һгҖҒж–°йІңејӮиҙЁпјҢеҲ«е…·дёҖж јеҸҲеҸ‘дәәж·ұжҖқгҖӮз”ұжӯӨжғіеҲ°и—Ҹж—ҸдҪң家зҡ„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пјҢйҷӨдәҶ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ҢиҝҳжңүйҳҝжқҘгҖҒжүҺиҘҝиҫҫеЁғгҖҒж¬Ўд»ҒзҪ—еёғгҖҒеӨ®зҸҚгҖҒжұҹжҙӢжүҚи®©зӯүдёҚж–ӯж¶ҢзҺ°зҡ„дјҳз§ҖдҪң家гҖӮдёәд»Җд№Ҳи—Ҹж—ҸдҪң家зҡ„жұүиҜӯеҶҷдҪңеңЁж•ҙдёӘе°‘ж•°ж°‘ж—ҸеҲӣдҪңдёӯеҚ“然иҖҢз«ӢпјҢдёәд»Җд№Ҳи—Ҹж—ҸдҪң家зҡ„дҪңе“ҒжҜ”дёҖдәӣжұүж—ҸдҪң家жӣҙдёәеҮәиүІжӣҙжңүиҙЁж„ҹе’ҢеҶІеҮ»еҠӣпјҹ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йҘ¶жңүж„Ҹе‘ігҖҒеҖјеҫ—ж·ұжҖқзҡ„иҜқйўҳгҖӮйҷӨдәҶи—Ҹең°з”ҹжҙ»гҖҒеҶҷдҪңйўҳжқҗзҡ„зӢ¬ејӮжҖ§пјҢеӣ дёәжңүдәҶжң¬ж°‘ж—ҸиҜӯиЁҖж–ҮеҢ–жүҳеә•пјҢи—Ҹж—ҸдҪң家еҜ№жұүиҜӯзҡ„ж•Ҹж„ҹгҖҒжҖқз»ҙж–№ејҸзҡ„дёҚеҗҢгҖҒиҜӯиЁҖиЎЁиҝ°зҡ„иҪ¬еҢ–пјҢеҜ№д»–иҖ…дәӢзү©зҡ„зӢ¬зү№ж„ҹеҸ—е’ҢзҗҶи§ЈпјҢйғҪеҸҜиғҪжҲҗдёә他们ж–ҮеӯҰзҡ„е®қи—ҸпјҢдёәе…¶еҶҷдҪңеҠ©еҠӣгҖӮд»ҘжӯӨдёәйүҙпјҢеҜ№з…§зҡ„жҳҜжұүж—ҸдҪң家иҮӘиә«еҶҷдҪңдёҠйқўдёҙзҡ„еҗ„з§ҚжғҜжҖ§е’Ңз–ІжІ“гҖӮиҝӣиҖҢиЁҖд№ӢпјҢеңЁиҝҷдёӘдё–з•ҢдёҖдҪ“еҢ–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еҰӮдҪ•дҝқжҢҒеҜ№иҮӘиә«иҜӯиЁҖе’Ңз”ҹжҙ»д№ғиҮіж°‘ж—Ҹж–ҮеҢ–зҡ„ж•Ҹж„ҹжҖ§пјҢж—ўиғҪдҝқз•ҷзү№иүІеўһеҠ иҫЁиҜҶеәҰпјҢеҸҲиғҪеңЁжӣҙеӨ§зҡ„иҢғеӣҙеҶ…иў«и®ӨеҸҜе’ҢжҺҘеҸ—пјҢжҳҜжҜҸдёҖдҪҚи®Іиҝ°иҖ…йғҪеҸҜиғҪйҒӯеҸ—зҡ„еўғйҒҮе’ҢжҢ‘жҲҳгҖӮ
еҺҹеҲҠдәҺгҖҠж–ҮиүәжҠҘгҖӢ2022е№ҙ7жңҲ8ж—Ҙ

еҗҙдҪізҮ•пјҢеҘіпјҢ1981е№ҙ10жңҲз”ҹпјҢйҮҚеәҶе·«жәӘдәәпјҢж–ҮеӯҰзЎ•еЈ«пјҢгҖҠй•ҝжұҹж–ҮиүәгҖӢеүҜдё»зј–пјҢйІҒиҝ…ж–ҮеӯҰйҷўз¬¬26еұҠдёӯйқ’е№ҙдҪң家й«ҳз ”зҸӯеӯҰе‘ҳгҖӮеңЁгҖҠеҪ“д»ЈдҪңе®¶з ”з©¶гҖӢгҖҠжү¬еӯҗжұҹиҜ„и®әгҖӢгҖҠеҢ—дә¬ж–ҮеӯҰгҖӢгҖҠй•ҝжұҹж–ҮиүәиҜ„и®әгҖӢгҖҠж–ҮиүәжҠҘгҖӢгҖҠж№–еҢ—ж—ҘжҠҘгҖӢзӯүжҠҘеҲҠеҸ‘иЎЁж–ҮеӯҰиҜ„и®әиӢҘе№ІпјҢеҮәзүҲжңүиҜ„и®әйӣҶгҖҠдёҚдёҖж ·зҡ„зғҹзҒ«гҖӢ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Ңз”өеҪұеҜјжј”пјҢзј–еү§пјҢдҪң家пјҢж–ҮеӯҰзҝ»иҜ‘иҖ…гҖӮд»Ҙз”өеҪұе’Ңе°ҸиҜҙеҲӣдҪңдёәдё»гҖӮд»Һ1991е№ҙејҖе§ӢеҸ‘иЎЁе°ҸиҜҙпјҢе·ІеҮәзүҲгҖҠиҜұжғ‘гҖӢгҖҠеҹҺеёӮз”ҹжҙ»гҖӢ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гҖҠд№ҢйҮ‘зҡ„зүҷйҪҝгҖӢзӯүеӨҡйғЁи—ҸгҖҒжұүж–Үе°ҸиҜҙйӣҶпјҢиў«зҝ»иҜ‘жҲҗеӨҡз§Қж–Үеӯ—еңЁжө·еӨ–еҮәзүҲпјҢиҺ·еҫ—вҖңжһ—ж–ӨжҫңзҹӯзҜҮе°ҸиҜҙеҘ–вҖқвҖңйқ’жө·ж–ҮеӯҰеҘ–вҖқвҖңиҠұеҹҺж–ҮеӯҰеҘ–вҖқвҖңеҚҺиҜӯж–ҮеӯҰдј еӘ’еӨ§еҘ–В·е№ҙеәҰе°ҸиҜҙ家вҖқзӯүеӨҡз§Қж–ҮеӯҰеҘ–йЎ№гҖӮд»Һ2002е№ҙејҖе§Ӣз”өеҪұзј–еҜје·ҘдҪңпјҢдё»иҰҒз”өеҪұдҪңе“ҒжңүгҖҠйқҷйқҷзҡ„еҳӣе‘ўзҹігҖӢгҖҠеҜ»жүҫжҷәзҫҺжӣҙзҷ»гҖӢгҖҠиҖҒзӢ—гҖӢгҖҠеЎ”жҙӣгҖӢгҖҠж’һжӯ»дәҶдёҖеҸӘзҫҠгҖӢгҖҠж°”зҗғгҖӢзӯүпјҢиҚЈиҺ·ж„ҸеӨ§еҲ©еЁҒе°јж–ҜеӣҪйҷ…з”өеҪұиҠӮжңҖдҪіеү§жң¬еҘ–гҖҒзҫҺеӣҪеёғйІҒе…Ӣжһ—еӣҪйҷ…з”өеҪұиҠӮжңҖдҪіеҪұзүҮеҘ–гҖҒеҸ°ж№ҫйҮ‘马еҘ–жңҖдҪіж”№зј–еү§жң¬еҘ–гҖҒдёӯеӣҪз”өеҪұйҮ‘йёЎеҘ–жңҖдҪіеҪұзүҮеҘ–гҖҒеҚҺиҜӯз”өеҪұдј еӘ’еӨ§еҘ–жңҖдҪіеҜјжј”еҘ–зӯүеҮ еҚҒйЎ№еӣҪеҶ…еӨ–з”өеҪұеӨ§еҘ–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