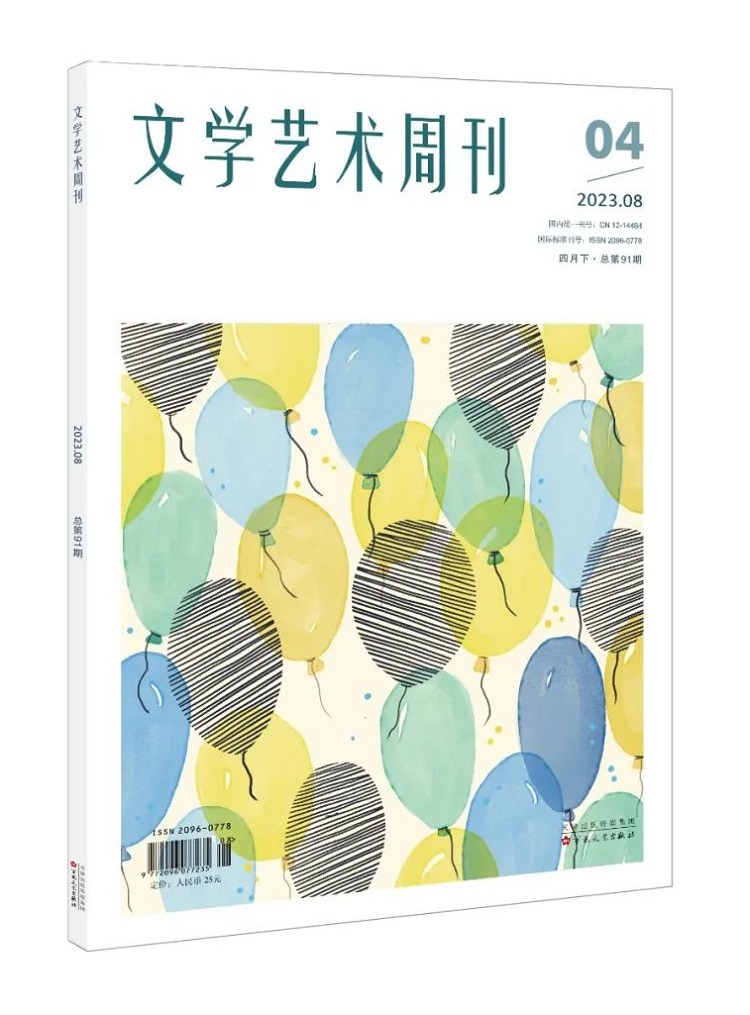
李学辉常说他写小说慢,但我却觉得他快得超出了一般预期。当我的脑海中还缭绕着上一部长篇小说《国家坐骑》带来的强烈震撼时,他已拿出了又一部奇崛独特的文本《塞上曲》。这个偏守在河西一隅的“乡下人”,有一片叫“巴子营”的园子,他常年躬耕劳作在那里,春华秋实,径自欢喜着。当然,他不是田园居士,他在凉州城里有一个职位,开会,编刊,研讨,时时为一方文学水土培土浇灌,奔走,忧虑。他确乎是一个忙人。那么,这些长篇大作,以及不间断出现的短篇佳构,到底是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呢?
李学辉,一个勤勉有加又心无旁骛的写作者。认识他的人在赞许这一点的同时,也钦慕文学给了他应得的回报,就像那片园子,总有好看又好吃的收成。12年前的《末代紧皮手》,以绝无仅有的“紧皮”这一古老的西北乡俗,书写了特定历史环境下动荡浮沉的人物命运,表现了当代乡村历史及其实践进程的复杂性和艰难性,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展示了厚重而独特的凉州文化。作品问世后,从读者到评论界,大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唤醒了人们潜隐的文化乡愁,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耕时代的最后一曲挽歌”。
应该说,作为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末代紧皮手》赢得的好评和声名是罕见的——但它当得起。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开启了人的独特生存空间的高妙之作。作为小说同行,别的不说,单是那遣词造句就很让我着迷。瘦硬,冷冽,精准,是极富个人标识度的语言风格。我以为从题材到叙事,《末代紧皮手》都是“极致”的了。我以为,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后,李学辉会缓口气,“日常”一点,“写实”一点。我没有想到,与我的“以为”恰恰相反,时隔几年,更惊世骇俗的《国家坐骑》诞生了。
2018年出版的《国家坐骑》,因着作者的信任,我或许是最早从草稿看起的几个人之一。我一直想为这部作品写点什么,但整整四年过去了,虽也曾写过一些零星的所谓评语导言,却始终产生不了一篇完整的文字。这四年,窗外的世界发生了太多的改变,我自己的生活也覆水难收地变故着。我一直茫然,惶然,久久地沉陷于疼痛中。我知道李学辉有在何时何地都能摊开一张纸写小说的定力,而自己却浮躁得连一篇读书心得都一拖再拖,以至于此刻,眼前,忙不迭地又面对了他新出炉的《塞上曲》。
我该为这些小说说些什么呢?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它们是如此地远离我熟悉的生活,也远离我一贯的阅读视野。我得承认,在读《国家坐骑》之前,我对书中所展示的凉州大地上的这段另类“民间史”一无所知。甚至,读了开头近十节的内容,看到各路马户出场,各色人等如马政司的官员们、庙祝、相马师等陆续推进情节,我都是满心疑惑,没有明白过来故事里的这些人要做什么。一直到“一个粉嘟嘟的婴儿展现在面前”,一直到木匠打出了“一张能立起来的娃儿床”,圉人宣布:“这是他的命,要做龙驹,吃义马粮,他就得像马一样,从娘胎里爬出来,一生都得站着睡觉。”我才恍然大悟!这一悟,只觉头皮“嗖”地一下直发麻,原来,所谓“龙驹”就是凡间为人母者孕育的人身肉胎!原来,一个婴孩因为“这是规矩,这是他的命”,便生下来就成“国家的马”了。
或可说,古今中外的悲剧文本中,这样奇绝的故事也是极少有的吧?虽说家国叙事向来是文学正统,但《国家坐骑》还是氤氲着一种江湖遗响的况味。“万物可变,旗、纛、马,此三者,国之命脉,不可变。”国有兵才稳,兵有马才胜,“龙驹一出,天下大兴。”一个孩子,就这样在凉州民众的家国想象中,被锻造成了一匹“国家之马”。但世易时移,“国家之马”在,“国家”却不在了。这最后一个“龙驹”的悲歌,简直冷冽奇拔如长空裂帛。尽管已有《末代紧皮手》带来的独异感受在前,我依然吃惊于平日温厚的李学辉在小说中迸发的这样一种不管不顾的“浪漫”精神,这样剑走偏锋的英雄主义。他太大塞长河、西风烈马了,但掩卷长思,我却不得不承认,他的魔幻是如此贴近现实,他的怪异却也是对过往时间的重新打量。通过“义马”这一符号,他挖掘了底层民众内心坚固的国家信念,对他们的祭献精神做了令人扼腕长叹的讴歌。同时,在对末代“义马”诞生、成长、死亡的全过程书写中,李学辉表现出了对晚清衰亡史的透彻认知,对于国家与民众命运、庙堂和民间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精到把握。他出入于现实和传奇之间,以冷峻奇崛的语言记述了一个绝世题材故事,呈现了一部诗意飞扬又遒劲有力的文本,为自汉唐以来文学长廊中瑰丽不绝的凉州画卷,新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义马”,这个刷新了今古奇观之道的文学形象,这匹只能驰骋在凉州大地上的义马,在“他”的身上,李学辉成功地写出了了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之间的转化,实现了“象征”和“现实”的水乳交融。毋庸置疑,义马形象体现的道义力量是具有震撼灵魂的警世作用的。不仅是义马,还有围绕在义马身边的一群西北边地面貌各异的人物,他们以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以人的勇气、智慧和担当,共同构建了当代文学中的殉道者形象。而这其中,最让人隐痛不忍的就是义马的娘。这个十月怀胎、千辛万苦生产后亲手把孩子祭献出去的母亲,从头到尾她的心泡在泪水中却从来不敢大声哭一场。她不追求“生龙驹才能光宗耀祖”,不稀罕做“马神娘娘”,她满心指望的不过是“像正常人一样,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然而,她生活在笃信“有其忠勇之人,有其铁骑之勇,国家有望。洋人的子弹,能快过龙驹吗?”的愚忠人群中,她只能接受、服从命中注定的一切。
最后,为了反抗马家军阀对义马的凌辱,她英勇地死去了。那“迎着刀冲了过去”的身影,像闪电般震颤了我的心。世间为人母者,都会感受到她的感受,其实她也许早在等待身死这一刻,因为她早已死于心碎。一个迷茫的妇人,一个绝望的母亲,然而,谁能说这个悲怆的牺牲者不是一个英雄?
可是,李学辉为什么要马不停蹄地写这样创伤性的地方掌故呢!这个夏天,读到“凉州三部曲”之收官之作《塞上曲》时,我不可抑制地发出这样的感慨。我自忖虽为一介女子,注定的“第二性”,却向来并不“风花雪月”,情归之处偏偏是属于另一个性别的“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大飘零,和“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慷慨悲歌。唐诗三百首,字字珠玑,但最让我意乱情迷的每每都是“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类感觉的诗句。但即便如此,李学辉的小说还是太“难看”了。这些骇人听闻的人和事,奇则奇矣,壮则壮矣,但到底太生僻了些,太“伤人”了些。难道凉州叙事必得这样孤绝到底、残酷到底吗?
李学辉自己是知道这点的,在《塞上曲》里,他借林则徐之口对自己的小说三部曲所写内容做了总结,也算是聊解读者疑惑:“奇哉!我来之途,遇人便问俚俗僻事。这些,史书上根本看不到。传闻凉州一有紧皮手,二有义马,今日又亲见斑蝥,总觉不可理喻又不得其解。说荒诞吧,其势可存;说愚昧吧,其怪自在。若说一种精神吧,倒也能说得过去。”
没错,这当然是一种精神。但钦敬精神之余,悲哀也是彻骨的啊!《国家坐骑》里,韩骧夫妻生子为“义马”,以图为国驰骋。虽则悲痛,终有荣耀。而在《塞上曲》的时空里,穆家幺儿落地便遭生母遗弃,成长过程中受尽世人欺凌。生而为“斑蝥”,孤独落魄如朔风不绝,曾经的荣光和壮怀激烈却已是无声的回响了。
何为斑蝥?等着做炮弹的人也。人炮弹,炮弹人,这是又一个鲜为人知的凉州秘史。第一次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战败。主战派林则徐被贬新疆伊犁。曾留学德国的南方火器局火炮技师萨镇淮,因与同僚们观念不同,也被排挤到北方边地的凉州火药局。在这里,人们研发炮弹的秘诀是“硫磺硝石柳条灰,加上斑蝥震天威。”
斑蝥由朝廷专定的炮户中的男丁承担。一旦成为斑蝥,便被朝廷所供养,吃喝均由火药局供给,实则由全城的商户和居民承担。斑蝥死前,便送入专设的斑蝥房。待尸体腐烂生蛆化为飞蛾,由役工清扫出飞蛾灰,在制作炮弹时,与硫磺、硝石和柳条灰混和调制。据说加了斑蝥灰的炮弹,爆炸时威力无比。
斑蝥者,不仅仅是死后躯体化灰成为炮弹配料,关键是,活着时就要接受各种“练炮胆”的训练,裸身上被一遍遍刷清漆,每天服用硝石、硫磺、柳条灰,以致皮肤皴裂,面色土黄。他被下到虎穴,“一直活在黑暗中”。若不堪疲累惊吓在里面睡着了,就有人踩虎穴,放毒焰,逼他醒来。如此严酷的种种过程,令外来者萨镇淮不忍卒看,他感慨说:“这太不人道”,但“军匠不懂,问萨镇淮啥叫人道。”在所有凉州人的眼里,“当兵打仗,种田交粮,做了斑蝥作炮弹,天经地义的事。”
这是1845年的中国,“天朝帝国至今,就像一棵大树,内有囊虫蚀其根本,外有洋人肆意遭践,还有更多人在冷眼旁观,这样一种局面,战何能胜,国何能固。”但在遥远的边地西凉,有一群人,他们不顾国运颓然,他们不懂炮弹的威力取决于火药配制的精度和比例,与人身并无相干,他们只是坚信着“看护好火药局,看护好斑蝥,就等于为朝廷看护住了点希望。”
还能再说什么呢,这些怪异得让人难以置信又现实得让人欲哭无泪的人和事!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古凉州的殉道和祭献烛照不了那些深不见底的黑暗,无力让被列强的坚船利炮震慑吓退了的民族精神还魂,重生。历史车轮,奔腾而来,寂然而去。但我们从这些卑微如草芥的黎民身上看到愚昧的同时,也看到了力量,生生不息的民间大地上,“地火在地下运行”。只要“人气”聚拢不散,枯树会发新芽。一骑义马尘,荡涤人心世态,飞扬家国情怀;一曲斑蝥歌,唱尽风云际会,氤氲爱恨情仇。历史烟尘虽浩邈远逝,激扬诗意依旧绵延不绝。没有一种付出,一种牺牲,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时间湮灭。
还能再说什么呢,这一条道走到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学辉!这个生于凉州、长在凉州、半辈子用文字写凉州的黑脸汉子,他就像一个执着的大地守夜人,一个在大雪纷飞时走遍山川河流的行吟诗人,我相信他一定是聆听到了那片土地最深处的秘密。紧皮手,义马,斑蝥,这一个个立于天地之间的孤绝形象,这一部部遒劲厚重的小说文本,使“凉州”这个苍劲如铁的文化地标,呈现出越来越雄奇悲壮、越来越辉煌多情的面貌。从此,我似乎不该再期望他的“平和”,他的“现实主义”,因为,植根于广袤而浑厚的凉州大地,深掘如此古老而独特的凉州文化,惊世骇俗或许是他命定的选择,而不可救药的英雄主义,是他对故乡最大的反哺与供养?
一遍遍重读中完成这篇小文时,时光已到寒露十月。极目遥望西北以西的凉州古城,我知道巴子营的那个园子,走过了姹紫嫣红的季节,正在收获一个盛大的秋天。
原刊于《文学艺术周刊》2023年第8期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出版《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狂流》《走出巴颜喀拉》《照亮你的灵魂》等。获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大学教授,现居兰州。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出版《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狂流》《走出巴颜喀拉》《照亮你的灵魂》等。获国内多种小说、评论奖项。大学教授,现居兰州。

李学辉,笔名补丁,甘肃武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第二十八届高研(深造)班学员,甘肃小说八骏之一。现供职于武威市文联。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钟山》《北京文学》《飞天》《朔方》《芳草》等刊物,被《小说月报》选载和参加全国名家小说巡展、入选各种选本。出版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和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李学辉的小说》、随笔小品集《弹指拈花》等,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梁斌小说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