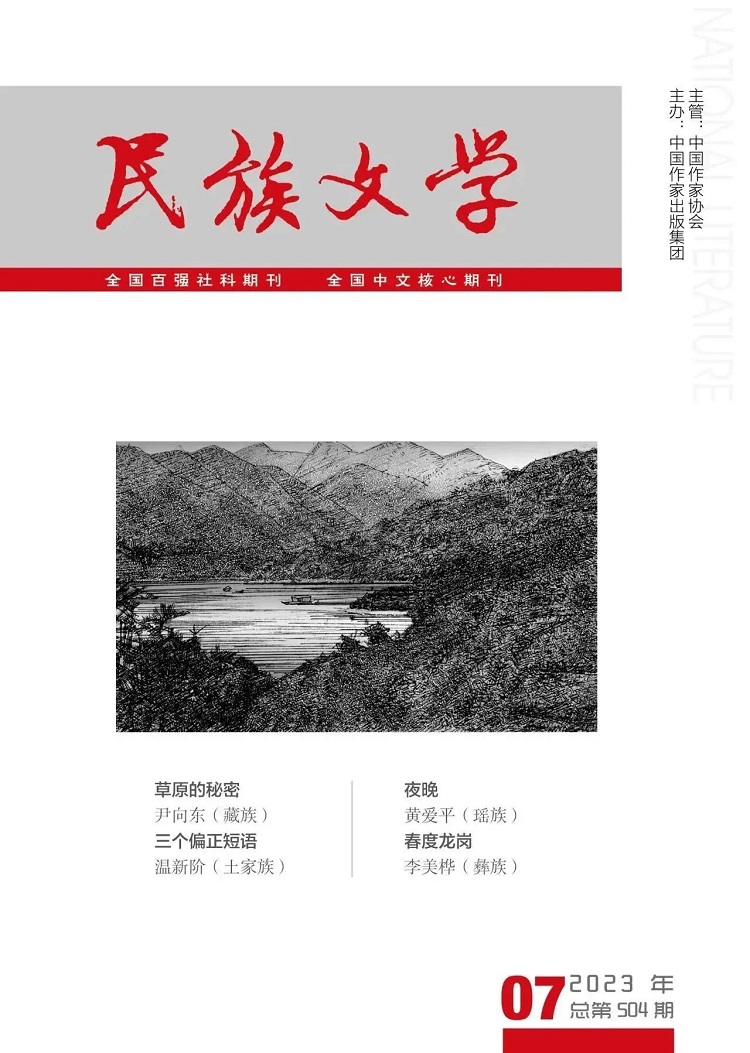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指出并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总书记站在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高度,发表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重要讲话,为全球文明建设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了我国的大国担当与风范,也为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增添了强大信心与动力。
“生命共同体”包括“生命”与“共同体”两个基本范畴。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阈内,个人的自由与发展皆依赖于共同体,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存在共同利益的个人在共同的规则约束下形成的群体。“生命共同体”作为“共同体”的具体发展,指的是由具有生命特征的物体所构成的联结体,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属于生态伦理学范畴。人从自然界进化而来,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人类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及适应自然,遵循自然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生命共同体”概念引申至文学范畴,与之关系密切的是围绕人与自然主题的文学,典型的有自然文学、环境文学与生态文学。冯小军提出的“生态文学相较于自然文学和环境文学的最大优势是生命共同体意识”①,点出了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写作与三者尤其是与生态文学之间的联系。
少数民族一直以来被认为在生态写作上具备先天的优势,这主要源于他们地理与文化等因素受自然的影响较大,丰硕的创作成果皆证明少数民族作家在生态写作上实至名归。近些年来,少数民族作家以自身的民族话语在生态领域占据一席之位,出现了叶广芩、阿来、李传锋、郭雪波、满都麦、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生态文学作家。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具有浓厚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自然贯穿于他们的生存需求、精神追求以及终极意义上。首先,基于生存所需,人类在生存需求上与自然联结为生命共同体。其次,藏族作家追求民族文化信仰下的生命平等,传达人类应敬畏自然万物、敬畏生命的信念。最后,藏族作家在文本实践中阐释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终极意义,即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藏族文学语境中的自然形象及伦理认知
文学语境是一种动态性共识,它在文学的经验、传统、知识以及批评理论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中的自然文学语境折射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在对自然的文学表达上,藏族作家在文本中阐释了人与自然多样的生存联系,具体表现为自然在文学语境中的多面形象。
(一)藏族文学语境中的自然形象
无论是常年冰雪覆盖的雪域高原、蜿蜒纵横的湖泊河流,还是蓝天下牛马漫步的草地等自然景象,藏族作家皆能以最柔情的文笔将其描绘出来,他们的书写出发点是对自然的感激之情。作为游牧民族,藏族人民逐水草而居,草原是他们生活的住所。诗人旺秀才旦歌唱道“哦,无边的大草原/这是纯洁,未遭玷污的绿色世界/这是牛羊遍地、水草丰盛的爱情家园”。在王小忠的《家园》中“热烈的风从草原吹来,被思念包围的家园呀,此刻我只想要深处的安宁”。这是诗人对于民族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的深情礼赞。梅卓的《野血烈焰》书写了千万如热嘎老人的牧民们,日常生活资源都是从牦牛身上得来的,牦牛为他们带来温暖与健康,带给他们战胜疾病与寒冷的力量。阿来的《蘑菇圈》中,在饥荒的岁月里蘑菇支撑起阿妈斯炯一家的生活,村里许多人也能喝上一碗香甜的蘑菇汤。在藏族文学中,自然是“家园”,以哺育者的形象存在,满足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各项需求。
然而伴随着现代化潮流的涌入,藏族人民对于自然的认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仅仅是基本生存层面上的需求来源,而是能换来财富与权势的“宝贝”。藏族所世居的青藏高原有着许多珍稀的自然资源,许多动植物价值不菲。在外界的需求与观念的变化下,青藏高原上的自然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掠夺。藏族作家将这种掠夺具体化,以珍稀动物以及药材作为基点,最为典型的是阿来的“山珍三部”,分别以虫草、松茸与岷江柏作为书写线索。在《三只虫草》中,虫草能换来一切物质所需,能满足桑吉的所有愿望,给表哥买手套、给姐姐买李宁T恤、给老师买飘柔洗发水,也能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上级从而获得官运的升迁;在《蘑菇圈》中,蘑菇成为高价的珍品遭到疯狂采摘;在《河上柏影》中,岷江柏作为珍稀木材最终也被伐无剩,种种行径皆因人类对金钱与权势的追赶,自然也以摇钱树与权势敲门砖的形象出现在藏族作家文本中。
在人对自然的掠夺下,人类与自然关系发生恶化,自然以受害者与报复者的形象存在于藏族作家的文本中,自然既可以像母亲般孕育天地万物,也有着毁灭一切给人类生存带来巨大打击的能力。久美多杰的散文集《故乡和远方》频频关注着故乡的自然生态,《在宗果河滩怀念森林》中他回忆了自己儿时所在的宗果,那时的宗果,水草丰茂,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多年后,美丽的故乡却频频爆发泥石流、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现代社会上,有些人经常埋怨说大自然正在消灭我们。我在想: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一种生命或物体,是我们欺负了大自然,所以遭到它的报复。”阿来的《机村》系列中,原始自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变得面目全非。机村原本是一座美丽古老的自然村落,后来却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将机村人一次次置于危险的境地。在人类认为掠夺自然是获得财富的捷径时,大片的原始森林、珍贵稀有的树木被大规模砍伐,人类“先祖”猴子被大规模枪杀。随之,自然的文学语境便成了“受过伤的报复者”,以自己的报复方式宣泄自身的不满,便出现了《荒芜》中,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摧毁了土地与庄稼,机村人甚至被逼迫离开生活了千百年的故土,去寻找古歌中的旧万国。
(二)对自然的伦理认知
藏族作家作品中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是民族生存经验下的产物。在《神授·魔岭记》中,梅卓借药士大叔道出“自然界是非常神奇的,与人类、动物、植物的生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人体,随着日月星辰的流转,天地四时的运行,人体的五脏、气脉以及血液的循环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我们药士一定要按照一定的时机、物候、节令来取用药材,才是尊重自然恩赐之道”这一道理。在《野血烈焰》中,梅卓又写道:“对于牧人来说,生存于天地之上的所有生物都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尊重自然法则、顺应天意,是他们保护家园生态环境健康循环的本能观念。”因此面对狼群对家牛的袭击,牧人们虽痛恨但不会对其赶尽杀绝。藏族人民相信人与自然是统一体,自始至终都信守着珍爱自然的承诺。因此在藏族作家的文本中,常涌现着作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呼声。
拥塔拉姆的散文集《守望故乡》以导游的形式,亲近万物进入自然,向人们介绍了故乡炉霍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化身为万物中的一员身临其中,“谁知昨夜落下春雪,大地被覆盖了一层白沙……喜鹊在雪枝上的阳光里欢歌笑舞,与它们打过目光的招呼,从白杨下跑向湖边……要不是天鹅和水鸟们的自在游动,真以为自己是画中的人。”在自然大地的怀抱中,拥塔拉姆与自然成为一体,将自己带入如画的风景,自然景物在她的笔下生机勃勃,充满着强盛的生命力。“我们站在山上注视草原,白色下面几处墨绿的暗圈依稀可见,黑色的牛毛帐篷和牛马星星点点分布在草原上……”可爱的自然风光随着作者的视角不断移动,从山下到山顶,往下俯瞰,美丽的宗塔草原被群山围绕,地面好似摇篮。草原中的牧民帐篷与牛儿马儿自在地散步吃草,俨然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丽画面。梅卓《野血烈焰》中的牧民在季节更替中不断地转移草场去放牧,这种轮牧方式一方面能让牛羊拥有充足的饲料,另一方面又能减轻草场受到的危害,有利于草场植被的恢复。每年在风雪下搬迁的牧民、动物与自然三者合一融为一体,彰显着藏族人民对于自然之道的理性认知。生于一方水土,老人在野血交配成功、家庭逐渐富裕、孩子们生活有了更好保障之日,仍坚守传统,怀着一颗对自然的感恩之心,将一碗牛奶淋入哺育他们的楚玛尔河,回报这条养育他们以及牦牛的河流。阿来《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与蘑菇之间有着超越种族的情谊。阿妈斯炯自从发现蘑菇圈后,便把蘑菇当成自己的孩子照料,在干旱的年景里,不辞辛苦地提着水桶往返于泉水边,为它们浇水,并为蘑菇盖上树叶与苔藓,让它们免受干旱与人为破坏。在采摘蘑菇的时候,阿妈斯炯双腿呈半跪姿势,心怀感恩地将它们摘下,并且放着大朵的蘑菇不采留给鸟儿吃。人与自然的和谐姿态激荡着藏族作家的思绪,人与自然在和谐中共鸣起舞,勾勒出生命共同体的蓝图。
二、藏族文化传统中的生命平等追求
万物有灵作为藏族传统的文化思维,在作家的创作下通过文本上升到艺术层面,从而实现了对自然神性与生命高度的阐释。作为一种原始思维,万物有灵的核心思想在于人们要对自然万物心存敬畏之心,用诗性智慧感受世间万物,以达到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境界。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在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时,不仅仅是通过文学语境呈现人与自然生存层面的共同体关系,同时也是基于自然万物在藏族的观念认知中有着神性与灵性的性质,是有情众生之一。通过书写自然万物的神性,藏族文学传达了人类应敬畏自然界一切生命、热爱一切生命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一)万物有灵:守护自然的神性
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蕴含着浓厚的“万物有灵”民族信仰,折射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观念。在藏族作家的文本中,神山圣湖崇拜以及图腾崇拜都传递着藏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神山圣湖保护着一方水土。在阿来《空山》中,圣湖色嫫措保护着一方的水土祥和。尽管色嫫措无人见过,但他们却坚信那里有着一对金野鸭,它们是机村人世代信奉的保护神,是它们带来生命与温暖。在江洋才让《康巴方式》中,藏族人不敢在神山上随意挖掘,害怕伤害神山上的禽兽鱼虫。南卡婆婆不允许人们随意带走山上的石头。此外,山上的一切都属于山神,人们从山上得到的一切都是山神的赋予,如在阿来《三只虫草》中,虫草被村民认为是山神神圣的礼物。而牦牛作为藏族的图腾,是藏族人民的精神与形象代表,在梅卓的《野血烈焰》中,藏族人民像牦牛一样有着坚韧且尊贵的烈性与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自然的神性思维,还存在于作家对自然界生物的灵性书写中。在雍措的散文集《凹村》中,橘树会因为另一半的死亡充满痛苦,不再结果。牛会自知生命尽头自行走丢,在幽静的流水沟等待死亡。老黄牛与黑耕牛有属于它们的爱情。狗会像人一样进行思考,存在嫉妒心理,进行人类才有的结婚生子。“没爹没娘”的野生核桃树在被全家刀砍斧凿时它依然活着,砍过的伤口,像嘴巴一样张着,四季不衰。此外,藏族作家笔下的万物有灵还体现在动物有着与人类同样的情绪互通能力。达真的《命定》中,贡布视爱马“雪上飞”为“恋人”与“兄弟”,他剪下马的鬃毛请活佛为其开光诵经。“当贡布从襁褓里掏出一根哈达戴在马脖子上的时候……不可思议的神降出现了,笼罩拉雅雪峰的云雾朝四处散开,一束阳光穿越云层照亮刀剑一样的雪峰,直插雾霭散去的碧空蓝天,像是在聆听早已丢失的人与动物在远古时代以来开创的交流本初。”人畜和睦的赞歌,在达真的笔下真切动人。“雪上飞”学着人的模样跪下前蹄与贡布“人马互跪”更是将人与动物互相尊重、动物的有情灵性演绎得淋漓尽致。次仁罗布《放生羊》通过书写一个老人与一只羊的故事,展示了人与动物互相救赎的过程。老人因为亡妻的托梦痛苦不已,希望早日帮助亡妻从地狱的煎熬中挣脱出来。在与即将被宰杀的绵羊相遇后,仿佛熟识已久的莫名亲切感让他买下羊并让其成为放生羊。放生羊寄托了老人对亡妻的思念与记忆,老人的精神得到了解脱与救赎,也和羊建立了跨越生物种族的情感。
(二)敬畏生命:追寻生命的平等
藏族人民对于自然的尊重,很大程度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从而衍生出了对生命平等的认知。自然万物同人类一样,皆是有情、有灵的生命存在,对生命应抱以敬畏之心。基于自然万物都具有灵性,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藏族作家兼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让我们感触到这种信念力量的强大。电影改编自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与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影片故事中司机金巴不小心撞死了一只羊,惆怅过后将其放到副驾座上送去给喇嘛做超度的仪式并送去天葬。为羊超度,赎罪洗脱才能换来司机内心的安宁,这也正源于藏族根深蒂固的万物有灵尊重生命的观念。
意西泽仁《一支无字的歌》中书写了牧区人与狗建立的深厚情谊,牧区的老人会像吻孩儿一样吻哈巴狗儿的嘴巴。在心爱的狗遭遇不测后,格芭阿婆伤心欲绝,为狗唱起了亲人逝世才会唱的悲歌。在多吉卓嘎的《西藏生死恋》中,一头名为喀果的熊在未与主人公公扎结怨时,“它就在那片山谷里,公扎捡牛粪、找狐狸、放羊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它……没有交往,却像老朋友般熟悉”,互不干扰、和睦相处。即使在喀果犯下人命后,公扎在为措姆报仇时,几次都有机会将它打死,却因为这只熊要么是怀孕,要么是带着熊崽等情况,一次次地丧失了报仇的好机遇。在公扎的内心深处,生命超越仇恨,他不忍夺去熊崽诞生以及母熊当母亲的机会,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与珍视。藏族作家的笔下,山水皆有情,万物皆有灵。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不仅是彼此生存层面的利益联系,在精神层面更被赋予了强大的情感联系。
三、“集体无意识”下的自然归属感
一直以来,人类对于哲学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到哪里去?”从不放弃寻找答案。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②藏族文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在本质上与之相呼应,即“人为自然之子,从自然而来,到自然中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可以分为有意识与无意识,两者是相对而言的,意识具有自我拥有的精神功能,可感知与接收外来信息;无意识则作为人类结构中的更深层次,通常情况下是不能为人本身所察觉得到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后被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解释为人类远古祖先传下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记忆模式,即“集体无意识”。人类进化至今,若说现代人在精神上对自然的敬畏是受“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属于有意识,那么藏族作家对于自然的回归渴望,则是本能性,源于人类对于自然的需求感与归属感,属于集体无意识。
(一)人类的精神危机
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经历了各种科学技术的革命,生活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一次次的飞跃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疏远。当鸟语花香的原野、枝繁叶茂的丛林、纵横交错的湖泊被一座座高楼大厦代替之时,自然终结了它与人类的共存空间。在人类漫长的现代化进程里,人类习惯将自身放于中心,无节制地从自然索取资源。然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并没有使得人类的精神世界同步丰盈起来,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人类不知不觉与自然渐行渐远。
与通过划分势力范围将自然资源占为己有的发展方式不同,过去生于草原的藏族牧民与自然极为亲近。他们以草地为床,与万物为伴,不会画地据为己有,而是带着帐篷行至一方暂住一时。在他们的观念里,草原从不是任何人的私有物品,而是属于自然万物,自然给予他们足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如今,尽管藏族由于地理原因,所处的区域受现代工业化的影响较为缓慢,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受着外界的冲击,生活方式与观念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精神世界也像自然生态一般史无前例地遭受破坏、失去平衡,精神的萎靡与异化由此而生。深究其因,这实则也体现了人的精神状态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新世纪以来的藏族文学中,藏族人民在现代工业化影响下的精神异化主要表现为生命信仰的崩塌。藏族诗人阿顿·华多太自20世纪90年代便意识到自然生态的危机,2008年诗集《忧郁的雪》道尽了工业化与现代化下自然界的生存困境与诗人的精神困境。《睡熟的蚯蚓》中,工业化使得蚯蚓遭受着酸雨的折磨,“只为一阵直直渗入他头颅的酸雨/他痛恨人类的文明/铸造了浓浓黑烟”。梅卓的《神授·魔岭记》中阿旺罗罗目睹美丽矫健的藏羚羊遭受匪盗血腥的屠杀,小羊羔因为喝下被猎人下过毒的泉水而无法生还。盗猎者在枪杀藏羚羊时,使得老奶奶也中枪。阿来《空山》中猎人达戈为了一己私欲,对猴群痛下杀手。这都发生在生命信仰坍塌的年代,人类在追求利益时,伤害着自然也将自然推离我们的世界。
(二)自然的生命救赎
正如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开篇所言:“在物欲浩荡、时光碎裂、神性坍塌的时代,青藏的辞典是阳光、雪花、青草,是泥土、甘露、花香,是草原、河流和山峰,也是道路、心性和觉悟。”③在这人类频犯错误的年代,青藏高原上的自然可以是“道路、心性、觉悟”。世间一切事物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类的实践活动若过多地干涉其中,便会导致被干涉的客体朝着不健康不平衡的方向发展。生命从本质上而言来源于自然,植根于自然。藏族作家的文本中,许多主人公进入都市之后受到身心磨难,这种煎熬感不仅仅源自都市生活方式带来的困顿,也是源于内心对于都市的排斥。最终他们选择回归故土,在大自然中疗伤。如梅卓《麝香之爱》中,许多离开故土进入都市的青年人,都在都市中迷失自我,有的最终选择回归故乡,回归自然。再如白玛娜珍《拉萨红尘》中,女主人公雅玛在都市里跌跌撞撞,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爱情与归宿。而她的好友朗萨与恋人莞尔玛相约奔赴自然,在生养他们的大自然里与蓝天为伴,在清澈的河流边呼吸清新的空气,在美丽广阔的草原中与羊群为友,彼此的心灵在大自然中融为一体,烦躁的精神与骚动的灵魂找到了平静的归宿。
在藏族作家的文本中,自然对人类的生命救赎一方面体现为人逃离都市回归自然,寻回生命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体现为自然对人心灵的治愈。大自然的一切都是真诚、恬静与古朴的,树木、河流与动物等具有的粗糙感及原始感,对人的心灵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也能安抚不安的灵魂,治愈内心的创伤。在诗人花盛的《草地上》中,云朵可以填充生活的盲区,“低垂的云朵蕴含着细碎的雪粒,一遍遍填充着生活的盲区”;草地可以宽慰亲人的离世之痛,让他重拾生活的期盼与希望,“在这片草地上,这是我必经的事情——以此温暖心中或枯黄、或残缺、或冰凉的花瓣,以此宽慰亲人的离世和空空的家园,以此给自己重新画出心中斑驳的远方”;最终诗人发出“当我们以草叶的方式重新活过,高原的风将使我们一同抵达远方最亲的人,它替你我铺开了生活的路,也替你我传唱着源自信念的力量”的感叹。在白玛娜珍的散文集《西藏的月光·爱欲如虹》中,主人公与朋友因为在生活中遭遇不顺心的事,在挫折面前选择远离喧嚣的都市,五一期间去往岗日托噶山朝拜,在大自然的包围中,心中的阴霾被一洗而净。神圣的雪岭、空旷的山野、繁盛的树木以及欢歌的鸟儿,都让她们的心灵变得轻松自在,灵魂似乎得到了洗礼,自然的怀抱让她们找到了慰藉。对于藏族作家而言,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自然是人的生命归宿。正如鸟儿有巢、兔子有窝,人类若无法从视觉上看见自然、从触觉上感知自然,那终将处于无根游离的状态。
结 语
综合观之,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对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的阐释,在基础层面,藏族作家将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带入文学语境进行阐释,从而传达了人与自然应有的相处之道;在精神层面,藏族作家表现出在万物有灵的民族信仰中,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由此衍生出了对生命平等的认知,强调自然不仅仅与人类联结为生存层面的生命共同体,在精神层面亦是如此;最后,藏族作家在文本中从哲学意义上分析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人来自自然,归于自然,集中表现为不管何时何地,自然对于人类而言有着精神拯救、心灵治愈的功能,是人类的最终归宿。
此外,藏族作家虽在文本中常常突出现代工业化背景下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这也是生态写作常见的叙事结构,但并不意味着藏族作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故步自封与一味排斥。藏族作家对于人与自然尖锐矛盾关系的披露,目的绝非为了凸显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为了力证人与自然两者统一,这种统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命运缠绕于一体而无法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人类作为“大地母亲最强有力且不可思议的孩子”④,应与自然母亲同生同长,同时跳出自我中心主义的格局,以“自然之子”肩挑重任,善待养育自然母亲。自然以历史的、运动的规律朝着未来发展,是历史的一部分,人类在该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当下提倡的恢复自然最为原始美丽的状态,像解放人类一样地解放自然,也并非是对现代化的否定以及鼓吹回到前工业技术时代,而是呼吁以目前能掌握的技术以及文明成果,去调和解决人与自然不断升级的矛盾与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世纪以来藏族作家对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的理想传达。
注释:
①冯小军:《生态文学创作,要厘清哪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生态文明》,2021年第4期,第77-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0页。
③格绒追美:《青藏辞典》,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④[英]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7期

郑佳丽,女,广东揭阳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3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多民族作家文学研究。评论文章见于《青海湖》、青海作家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