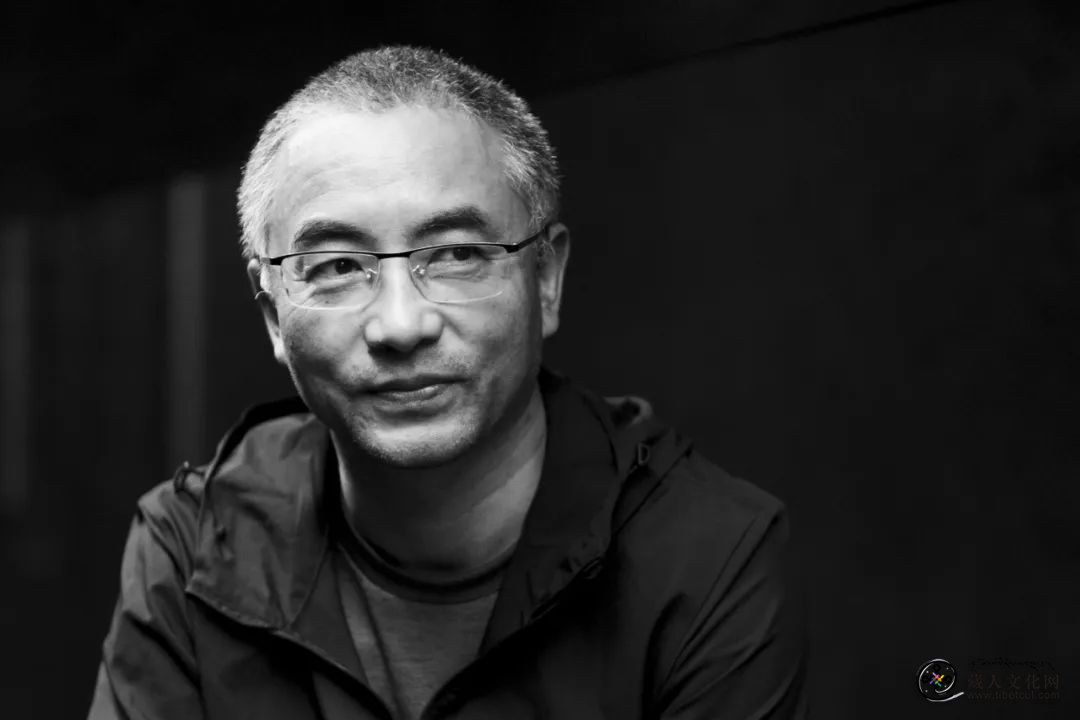
2023е№ҙ5жңҲ8ж—ҘеҮҢжҷЁпјҢи—Ҹж—ҸдҪң家гҖҒеҜјжј”гҖҒзј–еү§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ңЁиҘҝи—Ҹеӣ еҝғи„Ҹз—…зӘҒеҸ‘еҺ»дё–пјҢз»Ҳе№ҙ54еІҒгҖӮеҷ©иҖ—дј жқҘпјҢд»ӨдәәйңҮжғҠгҖҒжӮІжҒёдёҚе·ІгҖӮ
дёҮзҺӣжүҚж—ҰжҳҜдёҖдҪҚжқ°еҮәзҡ„еҜјжј”пјҢд№ҹжҳҜдёҖдҪҚеҮәиүІзҡ„е°ҸиҜҙ家гҖӮд»–еЁҙзҶҹең°иҝҗз”ЁзҺ°д»Јдё»д№үзҡ„еҸҷдәӢжҠҖе·§пјҢжҚ•жҚүгҖҒж’·еҸ–еҸҠж·¬зӮјеҪ“дёӢи—Ҹең°зү§ж°‘зҡ„ж—Ҙеёёз”ҹжҙ»пјҢиҫ…д№Ӣд»ҘиүәжңҜзҡ„еҚҮеҚҺе’Ңе®ЎзҫҺзҡ„иҪ¬еҢ–пјҢи¶…и¶ҠдәҶдј з»ҹзҡ„еҜ№дәҺж°‘ж—Ҹж–ҮеӯҰзҡ„еҲ»жқҝеҚ°иұЎпјҢжӣҙж·ұеҲ»ең°еҮёжҳҫеҮәдәҶдәәзҡ„еӨҡйҮҚз”ҹеӯҳж ·жҖҒгҖӮеңЁзҹӯзҜҮе°ҸиҜҙдёӯпјҢдҪң家з«Ӣи¶ідәҺдёӘдәәиЎЁиҫҫзҡ„еҹәзӮ№пјҢдәҺи—Ҹж—Ҹж•…дәӢзҡ„д№ҰеҶҷдёӯеҮёжҳҫгҖҒеј жү¬жҷ®йҒҚдәәжҖ§зҡ„ж·ұеұӮи•ҙж¶өпјҢиЎЁиҫҫеҮәд»–еҜ№дәҺж°‘ж—ҸдҪң家ж ҮзӯҫејҸеҲҶзұ»зҡ„вҖңеҺ»иә«д»ҪеҢ–вҖқиҜүжұӮгҖӮж—©жңҹ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ҫҝе·Із»ҸејҖеҗҜдәҶиҝҷжқЎдёӘдҪ“еҸҚжҖқдёҺеҪ“д»Јж„ҸиҜҶзҡ„иһҚеҗҲд№Ӣи·ҜгҖӮеңЁиҝҷйҮҢпјҢжҲ‘们еҸҜд»ҘзңӢеҲ°еҶҷдҪңжҠҖе·§зҡ„еӨҡж ·еҢ–еҖҹз”ЁгҖҒжғ…иҠӮеҸҷиҝ°зҡ„зҷҪжҸҸејҸе‘ҲзҺ°гҖҒеҸҷдәӢи§Ҷи§’зҡ„ж‘„еғҸејҸжҚ•жҚүзӯүе…·дҪ“иЎЁеҫҒгҖӮиҝӣдёҖжӯҘиҖҢиЁҖпјҢи—Ҹең°зҡ„еӨ–йғЁзҺҜеўғгҖҒдҪң家зҡ„жҲҗй•ҝз»ҸйӘҢдёҺеҲӣдҪңдё»дҪ“зҡ„иҮӘи§үзӯүиҙЁзҙ пјҢжӣҙжҳ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зӯүж–°дёҖд»Ји—Ҹж—ҸдҪң家еңЁеҲӣдҪңдёӯеӨ§йҮҸиҝҗз”ЁзҺ°д»ЈжүӢжі•зҡ„ж·ұеұӮеҺҹеӣ гҖӮд№ҹжӯЈеӣ жӯӨ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ҘйІңжҳҺзҡ„зҺ°д»Јдё»д№үд№ҰеҶҷеҪўејҸеҮёжҳҫдәҶж°‘ж—ҸејӮиҙЁиғҢжҷҜдёӢжҷ®йҒҚдәәжҖ§зҡ„еӨҡз»ҙгҖҒдё°еҜҢдёҺж·ұеҲ»гҖӮд»–дёҚеҶҚжү§зқҖдәҺеҜ№е®—ж•ҷдҝЎд»°еҸҠж°‘ж—ҸеҺҶеҸІдј еҘҮзҡ„зҘһеҢ–еҶҷдҪңпјҢиҖҢжӣҙеӨҡжҺўзҙўеҮәдёҖз§ҚеҹәдәҺдёӘдәәиЎЁиҫҫзҡ„еҜ№дәҺж—ҸзҫӨеҺҶеҸІи„үз»ңдёҺеҪ“дёӢйҒӯйҷ…зҡ„зҺ°е®һд№ҰеҶҷпјҢжүҖжҺўи®Ёзҡ„дё»йўҳж—ўз«Ӣи¶ідәҺжң¬ж°‘ж—Ҹзҡ„з”ҹеӯҳеңәеҹҹпјҢеҸҲиғҪеӨҹи·іеҮәд»ҘеҫҖзҡ„еҚ•зәҝи§Ҷи§’пјҢд»ҘзҺ°д»ЈжҖ§зҡ„зӣ®е…үдёҺд№ҰеҶҷжҠҖе·§йҮҚж–°еҜ№дј з»ҹдҝЎд»°дёҺеӨ–жқҘж–ҮжҳҺзҡ„дә’еҠЁдёҺзі…еҗҲиҝӣиЎҢж•ҙдҪ“и§Ӯз…§пјҢд»ҺиҖҢдҪ“зҺ°еҮәдәҶзҺ°д»Јдё»д№үеҸҷдәӢзҡ„еӨҡе…ғд№ҰеҶҷж–№ејҸгҖӮ
дёҖгҖҒвҖңеҗ‘еҶ…иҪ¬вҖқзҡ„еҸҷдәӢпј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ҲӣдҪңзҡ„зҺ°д»ЈжүӢжі•иЎЁеҫҒ
еҸ—ж—¶д»ЈзҺҜеўғеҸҳиҝҒеҸҠдёӘдәәжҲҗй•ҝз»ҸйӘҢзҡ„еҪұе“ҚпјҢд»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дёәд»ЈиЎЁзҡ„ж–°дёҖд»Ји—Ҹж—ҸдҪң家善дәҺеҖҹйүҙиҘҝж–№зҺ°д»Је°ҸиҜҙжүӢжі•пјҢиҝҷеёёеёёдҪ“зҺ°еңЁд»–们зҡ„дёӯзҹӯзҜҮе°ҸиҜҙеҸҠиҜ—жӯҢзҡ„еҶҷдҪңдёӯгҖӮйҖҡиҝҮеҜ№ж–Үжң¬з»“жһ„зҡ„з»ҸиҗҘдёҺз»ҶзЈЁ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ҰеҶҷдәҶи—Ҹж—Ҹдәәж°‘дәҺж—¶д»ЈеӨ§жҪ®иЈ№жҢҹдёӢеә”еҜ№иҮӘ然дёҺдё–з•Ңзҡ„зү№ж®Ҡе§ҝжҖҒгҖӮд»Ҙ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әд»ЈиЎЁпјҢдҪң家еҖҹеҠ©иҘҝж–№жҠҖе·§гҖҒжұүиҜӯиЎЁиҫҫи®Іиҝ°и—Ҹж—Ҹж•…дәӢпјҢеңЁжҖ»дҪ“жҠҠжҸЎи—Ҹең°еҪ“дёӢз”ҹеӯҳж ·жҖҒзҡ„еҗҢж—¶пјҢд№ҹиҝӣдёҖжӯҘдё°еҜҢдәҶдё–з•Ңж–ҮеҢ–еӨҡе…ғе…ұжһ„зҡ„з№ҒиҚЈеұҖйқўгҖӮз”ұжӯӨ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Ңе…¶д»–и—Ҹж—ҸдҪң家зҡ„зҺ°д»ЈжҖ§д№ҰеҶҷе…ұеҗҢжһ„жҲҗдәҶе…ЁзҗғеҢ–иғҢжҷҜдёӢи—Ҹж—Ҹж–ҮеӯҰеҲӣдҪңе’ҢиҖҢдёҚеҗҢзҡ„зІҫзҘһж°”иҙЁгҖӮе…·дҪ“иҖҢиЁҖ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ҲӣдҪңзҡ„зҺ°д»ЈжүӢжі•дё»иҰҒдҪ“зҺ°еңЁдёӨдёӘз»ҙеәҰгҖӮ
(дёҖ)еҖҹйүҙзҺ°д»Је°ҸиҜҙзҡ„еӨҡж ·еҢ–жҠҖе·§пјҢиҝӣдёҖжӯҘеҮёжҳҫдәәзҡ„еӨҡйҮҚз”ҹеӯҳж ·жҖҒ
зҺ°д»Јдё»д№үж–ҮеӯҰжҖқжҪ®еңЁ20дё–зәӘ80е№ҙд»Јдёӯжңҹзҡ„еҶ…ең°ж–ҮеқӣдёҖеәҰжҺҖиө·жіўжҫңгҖӮе…Ҳй”Ӣжҙҫзҡ„ж–ҮеҢ–жҖқжҪ®дёҺдј з»ҹзҡ„е®—ж•ҷдҝЎд»°й—ҙзҡ„дәӨз»ҮдёҺдјҡйҖҡпјҢд№ҹд»Ө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ҲӣдҪңе°ҸиҜҙжүҫеҲ°дәҶжңҖеҲқзҡ„зҒөж„ҹгҖӮжӯЈеҰӮд»–еңЁиҮӘиҝ°дёӯжҸҗеҸҠжӣҫеҖҹйүҙжӢүзҫҺзҡ„йӯ”е№»зҺ°е®һдё»д№үеҶҷдҪңпјҢвҖңи—Ҹж—Ҹзҡ„зҘһиҜқж•…дәӢзү№еҲ«еӨҡпјҢи°ұзі»еҫҲе№ҝпјҢеҫҲеӨҡеҸІд№ҰйғҪжңүйӯ”е№»е…ғзҙ пјҢжҲ‘зҡ„е°ҸиҜҙдёӯжңүиҝҷдәӣеҶ…е®№пјҢд№ҹжҳҜеҜ№и—Ҹж—Ҹдј з»ҹж–ҮеӯҰзҡ„继жүҝеҗ§вҖқв‘ гҖӮеҖјеҫ—жіЁж„Ҹзҡ„жҳҜ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并дёҚеӣҝдәҺжҹҗдёҖзү№е®ҡзҡ„еҶҷдҪңиҢғејҸпјҢиҖҢжҳҜйҖҡиҝҮе№ҝжіӣеӯҰд№ еҗ„зұ»зҺ°д»Је°ҸиҜҙзҡ„еҲӣдҪңжҠҖе·§пјҢе°ҪеҸҜиғҪдё°еҜҢең°жһ„е»әеӨҡе…ғеҢ–зҡ„ж–Үжң¬гҖӮиҝҷе…¶дёӯпјҢд»–е°Өе…¶зғӯиЎ·дәҺеңЁж–Үжң¬дёӯзҪ®е…Ҙи¶…зҺ°е®һдё»д№үзҡ„е…ғзҙ пјҢжҜ”еҰӮиұЎеҫҒгҖҒиҚ’иҜһгҖҒйҷҢз”ҹгҖҒйӯ”е№»гҖҒжҡ—зӨәгҖҒйҡҗе–»зӯүжүӢжі•гҖӮиҝҷдёҚд»…дёәеҚ•зәҜзҡ„ж—ҘеёёеҸҷдәӢеўһж·»дәҶдёҖеҲҶзҘһз§ҳзҡ„иүІеҪ©пјҢиҝҳз”ұжӯӨиҝӣдёҖжӯҘжҢҮеҗ‘дәҶжӣҙдёәж·ұйӮғзҡ„е“ІеӯҰжҖқиҖғгҖӮжӯЈжҳҜеӣ дёәеүҘзҰ»дәҶеҚ•дёҖзҡ„зЁӢејҸеҢ–еӨ–еЈіпјҢ他笔дёӢзҡ„дәәзү©дёҺж•…дәӢж— з–‘жҳҫеҫ—жӣҙеҠ йІңжҙ»дёҺзғӯзғҲгҖӮ
зәөи§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пјҢиҝҷж ·зҡ„зү№жҖ§ж— з–‘иў«жңүж„ҸиҜҶең°еҮёжҳҫгҖӮеңЁе°ҸиҜҙгҖҠи„‘жө·дёӯзҡ„дёӨдёӘдәәгҖӢдёӯпјҢдҪңиҖ…еҖҹйҳҝеҰҲеҶ·жҺӘиҝҷж ·дёҖдёӘвҖңйқһжӯЈеёёвҖқзҡ„иҖҒдәәеҪўиұЎпјҢд»ҘиҚ’иҜһзҡ„д№ҰеҶҷеҪўејҸпјҢеҸ‘жҺҳеҮәзү№е®ҡдәәзү©еҜ№дәҺзҺ°е®һзҺҜеўғдёӯз”ҹе‘ҪдҪ“йӘҢзҡ„зӢ¬зү№иЎЁиҫҫгҖӮжӯӨеӨ–пјҢдҪңиҖ…иҝҳе–„дәҺеҖҹйүҙеҝғзҗҶеӯҰеҸҠеҜ“иЁҖејҸгҖҒеӨҚи°ғејҸгҖҒиұЎеҫҒејҸгҖҒйҡҗе–»ејҸеҸҷдәӢзӯүеӨҡж ·еҢ–еҶҷдҪңжҠҖе·§гҖӮиӯ¬еҰӮе°ҸиҜҙгҖҠжӯ»дәЎзҡ„йўңиүІгҖӢе°ұи®Іиҝ°дәҶе°јзҺӣеңЁйқўеҜ№иҫҫеЁғе’ҢеҚ“зҺӣж—¶еҝғзҒөзҡ„еҶ…зңҒгҖҒжҢЈжүҺдёҺеҸҚеӨҚпјҢ并д»Ҙе°јзҺӣзңӢеҲ°вҖңжӯ»дәЎзҡ„йўңиүІвҖқйҡҗе–»дәҶжҪңи—ҸдәҺе°јзҺӣеҶ…еҝғзҡ„еӨҡйҮҚдәәж јгҖӮеңЁ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ӯпјҢдҪң家е°ҶзҺ°е®һзҡ„зү©зҗҶж—¶й—ҙдёҺдё»дәәе…¬зҡ„еҝғзҗҶж—¶й—ҙ并зҪ®пјҢйҖҡиҝҮжҙӣжЎ‘еңЁжўҰеўғдёӯдёҺе·Іж•…еҲ»зҹіиҖҒдәәзҡ„еҜ№иҜқпјҢеӨ§еӨ§еўһејәдәҶиҝҷдёҖдәӢ件зҡ„зңҹе®һзЁӢеәҰпјҢжҡ—зӨәдәҶдҪң家еҜ№дәҺдҪӣж•ҷзІҫзҘһзҡ„зҡҲдҫқдёҺз¬ғдҝЎгҖӮгҖҠд№ҢйҮ‘зҡ„зүҷйҪҝгҖӢдёӯпјҢдҪң家йҖҡиҝҮвҖңжҲ‘вҖқдёҺжҙ»дҪӣеҗҢеӯҰд№ҢйҮ‘зҡ„зүҷйҪҝж— ж„ҸдёӯдёҖеҗҢиў«дҫӣеҘүеңЁдҪӣеЎ”дёӯеҸ—дәәиҶңжӢңдёҖдәӢпјҢе°Ҷж—ҘеёёдёҺзҘһжҖ§з»“еҗҲпјҢжҠҳе°„дәҶеҪ“дёӢи—Ҹең°зӨҫдјҡдё–дҝ—жҖ§дёҺе®—ж•ҷжҖ§зі…еҗҲзҡ„дёҖйқўпјҢиҜ»жқҘд»ӨдәәдёҚзҰҒиҺһе°”гҖӮ
е°ҸиҜҙгҖҠеҚҲеҗҺгҖӢзҡ„жһ„жҖқдәҰ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дҪңиҖ…еңЁз®Җз»ғиҪ»зӣҲзҡ„笔и°ғдёӯе‘ҲзҺ°еҮәжңүиҠӮеҲ¶зҡ„йӯ”е№»иүІеҪ©пјҢеұ•зӨәдәҶдёҖдёӘе°‘е№ҙеңЁе№Ҫдјҡжғ…дәәж—¶й”ҷжҠҠзҷҪеӨ©еҪ“дҪңеӨңжҷҡиҖҢз•ҘжҳҫиҚ’иҜһзҡ„е–ңеү§еңәжҷҜгҖӮд»–е·§еҰҷең°жү“д№ұдәҶжғҜеёёзҡ„ж—¶й—ҙйЎәеәҸпјҢеұ•зҺ°дәҶе°‘е№ҙжҳӮжң¬иҝҪжұӮзҲұжғ…зҡ„зӮҪзғҲдёҺзғӯжғ…гҖӮиҷҪ然и°ңеә•еңЁж•…дәӢзҡ„жңҖеҗҺжүҚиў«жҸӯејҖпјҢдҪҶжҳҜеҰӮжһңеҶҚж¬Ўз»ҶиҜ»ж–Үжң¬дҫҝдёҚйҡҫеҸ‘зҺ°пјҢдҪңиҖ…еҜ№е°‘е№ҙжҳӮжң¬дёҖи·Ҝиө°жқҘжүҖеӨ„зҺҜеўғзҡ„е‘ҲзҺ°ж–№ејҸжңүж„ҸиҜҶең°иҝӣиЎҢдәҶжЁЎзіҠеҢ–зҡ„еӨ„зҗҶгҖӮж— и®әжҳҜеҲәзңјзҡ„вҖңжңҲе…үвҖқгҖҒеңҹи·ҜдёҠзҡ„иӣҮгҖҒд№–е·§зҡ„еӨ§й»„зӢ—гҖҒеҸјиҖҒйј зҡ„й»‘зҢ«зӯүиҮӘ然зҺҜеўғгҖҒз”ҹзү©пјҢиҝҳжҳҜйӮ»жқ‘е°‘е№ҙиҙҫе·ҙгҖҒзўҫзЈЁзҡ„е°ҸеҜЎеҰҮе‘ЁжҺӘгҖҒиҜөз»Ҹзҡ„дёңе·ҙеӨ§еҸ”гҖҒеҚ“зҺӣзҡ„家дәәзӯүдәәзү©еҸҠе…¶жҙ»еҠЁзҺҜеўғпјҢж— дёҚе…·жңүејәзғҲзҡ„жҡ—зӨәж„Ҹе‘іпјҢиҝҷдҫҝдҪҝеҫ—з»“еұҖзҡ„зңҹзӣёж—ўеҮәдәәж„Ҹж–ҷеҚҙеҸҲеҗҲд№Һжғ…зҗҶ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Ҷдәәзү©жҙ»еҠЁиҢғеӣҙзҪ®дәҺдёҖз§ҚиҺ«еҗҚзҡ„еӣ°жғ‘д№Ӣдёӯд»Ҙи§ЈйҮҠзӘҒиҪ¬зҡ„з»“еұҖпјҢиҝҷиЎЁзҺ°дәҶдҪңиҖ…еңЁеӨ„зҗҶж–Үжң¬ж—¶жүҖе…·жңүзҡ„жҳҺзЎ®зҡ„зҗҶи®әж„ҸиҜҶгҖӮ
жҜӢеәёзҪ®з–‘пјҢзҺ°д»Јдё»д№үж–ҮеӯҰзҡ„дёҖеӨ§зү№иүІдҫҝжҳҜејәи°ғиЎЁзҺ°дҪң家еҲӣдҪңзҡ„дё»и§Ӯеӣ зҙ пјҢ他们йҖҡиҝҮеҜ№ж–Үжң¬еҪўејҸзҡ„дёҚж–ӯеҠ е·ҘгҖҒз»ҶзЈЁпјҢеҜ№иҮӘжҲ‘ж„Ҹд№үиҝӣиЎҢеҸҚеӨҚжҺўеҜ»е’ҢиҝҪй—®пјҢеӣ иҖҢеҪўжҲҗдәҶж–ҮеӯҰеҸҷдәӢзҡ„вҖңеҗ‘еҶ…иҪ¬вҖқеҖҫеҗ‘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ҲӣдҪңдҫҝ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д»–еңЁдёӘдәәзҡ„еҲӣдҪңе®һи·өдёӯеҚҒеҲҶиҮӘи§үең°жіЁйҮҚеҜ№дәҺдёӘдҪ“з»ҸйӘҢзҡ„е‘ҲзҺ°пјҡвҖңеҮәеҸ‘зӮ№йҮҚиҰҒзҡ„жҳҜдёӘдәәзҡ„иЎЁиҫҫпјҢжҳҜе»әз«ӢеңЁиҝҷдёӘж°‘ж—ҸгҖҒиҝҷдёӘең°еҹҹдёҠзҡ„гҖӮдҪ иӮҜе®ҡжҳҜе…ҲжңүдёҖдёӘжғіжі•гҖҒж•…дәӢпјҢжҳҜдёҺиҝҷзүҮеңҹең°жңүе…іиҒ”зҡ„вҖҰвҖҰжҲ‘并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иЎЁзҺ°ең°еҹҹзҡ„зү№иүІвҖқв‘ЎгҖӮиҝҷж ·зҡ„еҲӣдҪңзҗҶеҝөеңЁе…¶е°ҸиҜҙгҖҠеЎ”жҙӣгҖӢдёӯжңүе®Ңж•ҙзҡ„еұ•зӨәгҖӮеӯӨе„ҝеЎ”жҙӣжңүи¶…еёёзҡ„и®°еҝҶеҠӣпјҢд»Ҙзү§зҫҠдёәз”ҹпјҢеҸҲд»Ҙе…¶зӢ¬е…·зү№иүІзҡ„е°Ҹиҫ«еӯҗиҖҢиў«жқ‘йҮҢдәәеҶ еҗҚвҖңе°Ҹиҫ«еӯҗвҖқпјҢзңҹе®һзҡ„姓еҗҚеҚҙиў«дәәйҒ—еҝҳгҖӮдёҺжүҖй•ҝдәӨи°ҲиҝҮзЁӢдёӯеЎ”жҙӣеӨ§ж®өиғҢиҜөгҖҠдёәдәәж°‘жңҚеҠЎгҖӢдёҺгҖҠжҜӣдё»еёӯиҜӯеҪ•гҖӢпјҢиҝҷж ·зҡ„жғ…иҠӮи®ҫзҪ®е®һеҲҷеңЁжҡ—жҢҮдё»дәәе…¬з»ҸеҺҶзқҖеӣҪ家主жөҒж–ҮеҢ–д»·еҖјеҸ–еҗ‘дёҺи—Ҹж—Ҹжң¬еңҹе®—ж•ҷдҝЎд»°еҸҢйҮҚеЎ‘йҖ зҡ„иҝҮзЁӢгҖӮжӯЈжҳҜиҝҷж ·дёҖдёӘжҲҗй•ҝдәҺдј з»ҹи—Ҹең°жқ‘иҗҪпјҢжҺҘеҸ—зқҖеҸҢйҮҚд»·еҖјеЎ‘йҖ зҡ„еЎ”жҙӣпјҢд»ҘиҝӣеҹҺжӢҚз…§иҝҷдёҖдәӢ件дёәеҘ‘жңәпјҢз”ұеӨ–еңЁзҺҜеўғзҡ„йҒҪеҸҳжҝҖеҸ‘иө·жҪңи—Ҹзҡ„ж¬ІжңӣпјҢд»ҺиҖҢйҒӯйҒҮдәҶд»·еҖјеҚұжңәпјҢжңҖз»Ҳд»–еҒ·еҚ–дәҶеҲ«дәәзҡ„зҫҠ并被зҗҶеҸ‘еә—еҘіеӯ©жүҖж¬әйӘ—гҖӮжӯӨеӨ–пјҢдҪңдёәвҖңиў«йҒ—еҝҳиҖ…вҖқзҡ„еЎ”жҙӣпјҢеңЁиҮӘжҲ‘еӯҳеңЁдёҺд»–иҖ…е®Ўи§Ҷзҡ„е·®ејӮд№Ӣй—ҙпјҢе…¶иә«д»ҪеҜ»жүҫдёҺд»·еҖји®ӨеҗҢзҡ„иҝҮзЁӢд№ҹиҙҜз©ҝдәҺж•ҙдёӘж•…дәӢд№ӢдёӯгҖӮжңҖз»ҲпјҢжүҖй•ҝиҰҒжұӮеүӘеҺ»иҫ«еӯҗзҡ„еЎ”жҙӣйҮҚж–°жӢҚз…§пјҢйҡҗе–»дәҶе…¶дёӘдҪ“иә«д»ҪдёҺд»·еҖји®ӨеҗҢеңЁз»ҸеҺҶдёҺеӨ–з•Ңзҡ„дёҖзі»еҲ—зў°ж’һеҗҺд»ҚжңӘжҳҺжң—гҖӮдҪңиҖ…жүҖзқҖйҮҚе…іжіЁзҡ„пјҢжӯЈжҳҜеӨ„дәҺдј з»ҹз”ҹжҙ»еҪўжҖҒдёӢзҡ„и—Ҹж—Ҹдәәж°‘еңЁйқўеҜ№зҺ°д»Јд»·еҖјж—¶жүҖйҒӯйҒҮзҡ„еҝғжҖҒеҶІеҮ»пјҢд»ҘеҸҠиҝҷдёҖеҶІеҮ»иғҢеҗҺжүҖи•ҙеҗ«зҡ„еҜ№дәәжң¬иҙЁз”ҹеӯҳж ·жҖҒзҡ„е“ІеӯҰжҖқиҖғгҖӮ
(дәҢ)е°ҶзҺ„еҰҷзҡ„е®—ж•ҷзІҫзҘһдёҺе…ұйҖҡзҡ„жҷ®йҒҚдәәжҖ§йҡҗи—ҸдәҺиҝ‘д№ҺзҷҪжҸҸзҡ„жғ…иҠӮеҸҷиҝ°
зәөи§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иҜёеӨҡе°ҸиҜҙгҖҒеҪұи§ҶдҪңе“ҒпјҢжһҒз®Җдё»д№үзҡ„йЈҺж јеҸҜи°“жҳҜд»–йІңжҳҺзҡ„дёӘдәәеҢ–ж ҮзӯҫгҖӮж— и®әжҳҜ笔墨з®ҖзңҒзҡ„ж–Үеӯ—иЎЁиҝ°пјҢиҝҳжҳҜд»ҘеҪўдј зҘһзҡ„дәәзү©еҲ»з”»пјҢд»ҺдёӯйғҪиғҪзңӢеҮәдҪң家平淡еӨ©зңҹзҡ„ж•ҙдҪ“йЈҺж ј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ңЁе°ҸиҜҙдёӯйӮЈдәӣзңӢдјјз®ҖзңҒзҡ„еҸҷиҝ°дёҺжғ…иҠӮиғҢеҗҺпјҢеҫҖеҫҖи•ҙеҗ«зқҖеӨҚжқӮдё”ж·ұеҲ»зҡ„жҖқиҖғпјҢиҝҷжҳҜдҪң家еҜ№дәҺйҡҗи—ҸеңЁж•…дәӢеҶ…йғЁзҡ„еј еҠӣиҝӣиЎҢејәеҢ–еҗҺзҡ„ж•ҲжһңгҖӮж–Үжң¬зҡ„иЎЁеұӮеҸҷиҝ°жүҖйҡҗеҗ«зҡ„ж·ұж„ҸпјҢдҪҝеҫ—дёҮзҺӣжүҚж—Ұ笔дёӢзҡ„ж•…дәӢжҲ–з”ҹи¶ЈзӣҺ然пјҢжҲ–иҖҗдәәеҜ»е‘іпјҢжҲ–еӨұиҗҪжҖ…жғҳпјҢжҜҸдёҖзҜҮйғҪжёІжҹ“зқҖдёҚеҗҢзҡ„жғ…з»ӘдёҺиүІеҪ©пјҢеӣ жӯӨе…·еӨҮеӨҡи§’еәҰж·ұе…Ҙи§ЈиҜ»зҡ„еҸҜиғҪжҖ§гҖӮ
е°ҸиҜҙгҖҠе…«еҸӘзҫҠгҖӢдҫҝжҳҜиҝҷж ·дёҖзҜҮжҸӯзӨәдәәзұ»е…ұйҖҡжғ…ж„ҹзҡ„дҪідҪңгҖӮдҪң家жңүж„ҸзӘҒз ҙдј з»ҹзҡ„жұүи—Ҹе…ізі»ејҸеҸҷдәӢжЁЎејҸпјҢе°ҶвҖңд»–иҖ…вҖқзҡ„иә«д»ҪиөӢдәҲдёҖдёӘдёҺз”ІжҙӣиҜӯиЁҖдёҚйҖҡзҡ„еӨ–еӣҪдәәпјҢд»ҺиҖҢеңЁжӣҙе№ҝжіӣзҡ„ж„Ҹд№үдёҠеҮёжҳҫдәҶеӯҳеңЁдәҺдәәзұ»жғ…ж„ҹдёӯзҡ„е…ұйҖҡжҖ§гҖӮж•…дәӢжғ…иҠӮжң¬иә«еҚҒеҲҶз®ҖеҚ•пјҡз”Іжҙӣеӣ иў«зӢје’¬жӯ»зҡ„е…«еҸӘзҫҠиҖҢдјӨеҝғиҗҪжіӘпјҢиҝҷзүөеҠЁзқҖеӨ–еӣҪдәәд№ҹйҷ·е…ҘдәҶеӣ вҖң9В·11вҖқдәӢ件иҖҢеӨұеҺ»е®¶дәәзҡ„е·ЁеӨ§жӮІз—ӣд№ӢдёӯгҖӮеҪ“дёӨдәәжҠұеңЁдёҖиө·е®Јжі„еҪјжӯӨзҡ„жғ…ж„ҹгҖҒеҜ»жұӮж…°и—үж—¶пјҢең°еҹҹж–ҮеҢ–гҖҒе®—ж•ҷдҝЎд»°еҸҠиҜӯиЁҖиЎҢдёәзҡ„е·ЁеӨ§е·®ејӮеңЁиҝҷдёҖеҲ»дҫҝе·Із»Ҹиў«дәәзұ»е…ұеҗҢзҡ„жӮІдјӨдҪ“йӘҢжүҖжЁЎзіҠгҖҒж·ЎеҢ–гҖӮдҪң家жғіиҰҒеҪ°жҳҫзҡ„дҫҝжҳҜпјҢжүҖжңүдёҚеҗҢз§Қж—ҸгҖҒдёҚеҗҢиӮӨиүІзҡ„дәә们еҜ№дәҺе№ёзҰҸдёҺе’Ңе№із”ҹжҙ»зҡ„е…ұеҗҢиҝҪжұӮгҖӮ
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ҪңдёәдҪң家早жңҹзҡ„е°ҸиҜҙдҪңе“ҒпјҢеҖҹеҠ©е°‘и®ёйӯ”е№»зҺ°е®һдё»д№үиүІеҪ©пјҢи®Іиҝ°дәҶй…’й¬јжҙӣжЎ‘еӣ дёҖеқ—еҳӣе‘ўзҹідёҺеҲ»зҹіиҖҒдәәгҖҒжқ‘йҮҢдәәгҖҒжҙ»дҪӣеұ•ејҖзҡ„дёҖж®өиҪ»е–ңеү§гҖӮвҖңеҳӣе‘ўзҹівҖқиҝҷдёҖйқһиҜӯиЁҖз¬ҰеҸ·еңЁиҝҷйҮҢе…·жңүдёӨж–№йқўеҠҹиғҪпјҡдҪңдёәж„Ҹд№үзҡ„иҪҪдҪ“пјҢе®ғдёҖж–№йқўе°ҶдҪӣж•ҷзІҫзҘһеӨ–еңЁең°е‘ҲзҺ°дәҺи—Ҹең°ж°‘дј—зҡ„ж—Ҙеёёз»ҸйӘҢд№ӢдёӯпјҢеҸҰдёҖж–№йқўд№ҹеҖҹеҠ©дёәдәәжүҖж„ҹзҹҘзҡ„е®ўи§ӮеҪўејҸе°Ҷе…·дҪ“зҡ„дёӘдәәдёҺжҠҪиұЎзҡ„ж•ҷд№үзӣёиҒ”з»“гҖӮдәҺдҪң家иҖҢиЁҖпјҢйҖҸиҝҮз®ҖеҚ•зҡ„жғ…иҠӮпјҢд»–жӣҙеҠ жіЁйҮҚзҡ„жҳҜеҳӣе‘ўзҹіиұЎеҫҒдәҶеҪ“дёӢи—Ҹең°зӨҫдјҡзҡ„еҶ…йғЁз»“жһ„зҡ„иҪ¬еҸҳпјҡвҖңи—ҸеҢәзҡ„зҠ¶еҶөдёҺеҳӣе‘ўзҹіжңүеҫҲеӨҡзӣёдјјзҡ„ең°ж–№пјҢиЎЁйқўдёҠзңӢиө·жқҘдјјд№ҺжІЎжңүд»Җд№ҲеӨӘеӨ§зҡ„еҸҳеҢ–пјҢдҪҶеҶ…йҮҢеҚҙдёҖзӣҙеңЁеҸ‘з”ҹзқҖдёҖдәӣеҸҳеҢ–гҖӮвҖқв‘ў
еңЁеҪ“д»Је°ҸиҜҙдёӯпјҢи—Ҹең°зү§ж°‘еёёд»ҘзҺ°д»ЈеҢ–зӨҫдјҡиҝӣзЁӢдёӯзҡ„иҫ№зјҳдәәеҪўиұЎеҮәзҺ°пјҢиҖҢдҪңдёәиҫ№зјҳдәәдёӯзҡ„ејұеҠҝзҫӨдҪ“пјҢи—Ҹең°еҘіжҖ§зҡ„еӨҡйҮҚиҫ№зјҳеҢ–зҡ„зү№ж®Ҡиә«д»Ҫе°Өдёәд»ӨдәәжіЁзӣ®гҖӮеңЁеҪ“д»Ји—Ҹж—ҸеҘіжҖ§зҡ„ж„ҹжғ…жӮІе–ңеү§дёӯ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ж јеӨ–е–„дәҺеұ•зҺ°ж—Ҙеёёз”ҹжҙ»дёӯзҡ„еҘіжҖ§з”ҹеӯҳд№Ӣз»ҙгҖӮеңЁгҖҠ第д№қдёӘз”·дәәгҖӢдёӯпјҢйӣҚжҺӘзҡ„з”ҹжҙ»иҪЁиҝ№дҫҝ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йқўеҜ№зңҹеҝғд»Ҙеҫ…зҡ„з”·дәәпјҢеҘ№еқҰзҷҪең°и®Іиҝ°дәҶиҮӘе·ұзҡ„ж„ҹжғ…з»ҸеҺҶгҖӮдҪңдёә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зҡ„дёҲеӨ«жүҖиЎЁзҺ°еҮәзҡ„е®Ҫе®№дёҺзҗҶжҷәд»ӨеҘ№ж„ҹеҠЁпјҢ然иҖҢд»Һд»–еұЎж¬ЎвҖңжҲ‘们е°ұиҰҒејҖе§ӢдёҖз§Қж–°зҡ„з”ҹжҙ»дәҶ!вҖқзҡ„зӢ¬зҷҪдёӯпјҢеҚҙйҡҗйҡҗиЎЁйңІд»–ж— жі•д»Һеҝғеә•зңҹжӯЈеҜ№йӣҚжҺӘзҡ„иҝҮеҫҖйҮҠжҖҖпјҢй…’зІҫжӣҙдёҖж¬Ўж¬ЎеҠ еү§дәҶдёӨдәәзҡ„зІҫзҘһйҡ”йҳӮгҖӮеңЁиҝӣиЎҢдәҶеӨҡж¬Ўжғ…ж„ҹдёҺиӮүдҪ“зҡ„жҢЈжүҺгҖҒеҚҡејҲд»ҘеҗҺпјҢйӣҚжҺӘжңҖз»ҲиҺ·еҫ—дәҶдё»дҪ“ж„ҸиҜҶзҡ„жё…йҶ’гҖӮж–Үжң«дҪңиҖ…д»ҘйӣҚжҺӘзҡ„вҖңеЁңжӢүејҸеҮәиө°вҖқдҪңдёәйҡҗеҗ«з»“еұҖпјҢеұ•зҺ°дәҶеҘіжҖ§еҜ№дәҺдёӨжҖ§й—ҙзәҜзІ№гҖҒе№ізӯүзҲұжғ…зҡ„дҝЎеҝөиҝҪжұӮгҖӮдәҺйҒ“еҫ·гҖҒ家еәӯгҖҒзӨҫдјҡзӯүеӨҡйҮҚеҺӢжҠ‘д№ӢдёӢиЎЁзҺ°еҮәзҡ„еҶіж–ӯдёӯпјҢжҲ‘们дёҚйҡҫж„ҹеҸ—еҲ°и—Ҹең°еҘіжҖ§з”ҹе‘ҪеҠӣйҮҸзҡ„ж—әзӣӣдёҺиҮӘз”ұж„Ҹеҝ—зҡ„иӢҸйҶ’гҖӮ
з»јдёҠпјҢд»Һж–Үжң¬жң¬иә«еҮәеҸ‘еҸҜд»ҘзңӢеҲ°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ҮӯеҖҹиҮӘиә«зҡ„ж–ҮеӯҰи§ҶйҮҺпјҢеңЁдё–дҝ—еҢ–з”ҹжҙ»еңәеҹҹдёӯд»Ҙи—Ҹең°е®—ж•ҷеә•и•ҙдёҺж°‘ж—Ҹж„Ҹеҝ—дёәиғҢжҷҜеҮёжҳҫжҷ®йҒҚдәәжҖ§зҡ„ж·ұеұӮеҶ…и•ҙпјҢдәҺеӨҡе…ғж–ҮеҢ–е…ұжһ„зҡ„еҪ“дёӢиҝҺжқҘдәҶдёҖе№…зҺ°е®һдё»д№үзІҫзҘһеӨҚеҪ’зҡ„ж–ҮеӯҰеӣҫжҷҜгҖӮйӮЈд№ҲеҪ“д»Һж–Үжң¬з§»зӣ®иҮідҪң家жң¬иә«ж—¶пјҢиҖҗдәәеҜ»е‘ізҡ„й—®йўҳжҳҜпјҢдҝғжҲҗдҪң家еңЁеҲӣдҪңйЈҺж јж–№йқўзҡ„иҪ¬еҗ‘зҡ„еҘ‘жңәдёҺеҠЁеҠӣеҸҲд»ҺдҪ•иҖҢжқҘ?
дәҢгҖҒеӨҡе…ғиә«д»Ҫзҡ„е»әжһ„дёҺзЎ®з«Ӣпј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Ҡе…¶зҺ°д»Јдё»д№үд№ҰеҶҷйЈҺж ј
еҸ—ж—¶д»ЈзҺҜеўғеҸ‘еұ•дёҺдёӘдәәйҖүжӢ©з©әй—ҙжӢ“е®Ҫзҡ„еҪұе“ҚпјҢж–°дёҖд»Ји—Ҹең°дҪң家еҫҖеҫҖжңүзқҖеҚҒеҲҶдё°еҜҢзҡ„е·ҘдҪңз»ҸеҺҶгҖӮиӯ¬еҰӮж¬Ўд»ҒзҪ—еёғе…ҲеҗҺдәҺжҠҘзӨҫдёҺжқӮеҝ—зӨҫиҙҹиҙЈзј–иҫ‘е·ҘдҪңпјҢйҫҷд»Ғйқ’дҪңдёәи®°иҖ…дёҺеҲ¶зүҮдәәжӣҫеҸӮдёҺеӨҡйғЁеҸҚжҳ и—Ҹең°з”ҹжҖҒдҝқжҠӨзҡ„зәӘеҪ•зүҮзҡ„жӢҚж‘„е·ҘдҪңпјҢзҘҒзҝ иҠұеңЁй©¬и№„и—Ҹж—Ҹ乡马蹄еӯҰж Ўд»Һж•ҷдёүеҚҒдҪҷиҪҪвҖҰвҖҰдёҚеҗҢзҡ„иҒҢдёҡдҪ“йӘҢдҪҝи—Ҹж—ҸдҪң家еҜ№еңЁйҖүжӢ©з”ҹжҙ»зҡ„жҲӘйқўгҖҒеҲҮе…Ҙж•…дәӢзҡ„и§Ҷи§’гҖҒеұ•ејҖеҸҷдәӢзҡ„ж–№ејҸзӯүеұӮйқўиғҪеӨҹжӣҙеӨҡз»ҙеәҰең°жӢ“еұ•иҜқиҜӯиЁҖиҜҙзҡ„з©әй—ҙгҖӮд»ҺдҪң家иҮӘиә«зҡ„жҲҗй•ҝз»ҸйӘҢжқҘзңӢпјҢж–°дёҖд»ЈдҪң家зҡ„ж–ҮеҢ–еӯҰе…»еҶіе®ҡдәҶе…¶еҲӣдҪңеҝғжҖҒзҡ„иҮӘдҝЎдёҺд»Һе®№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зӯүж–°дёҖд»Ји—Ҹж—ҸдҪң家жҷ®йҒҚе…·жңүй«ҳдёӯгҖҒжң¬з§‘з”ҡиҮізЎ•еЈ«д»ҘдёҠеӯҰеҺҶпјҢеҜ№иҘҝж–№зҺ°д»Јж–ҮиүәзҗҶи®әзҡ„иҮӘи§үз§ҜзҙҜеҸҠи—Ҹең°дј з»ҹе®—ж•ҷж–ҮеҢ–еҪ“дёӢе‘Ҫиҝҗзҡ„е®Ўж…ҺжҖқиҖғпјҢдҪҝеҫ—他们зҡ„ж–ҮеӯҰеҲӣйҖ жҷ®йҒҚе‘ҲзҺ°еҮәдёҖз§ҚжӣҙеҠ жҲҗзҶҹе®ўи§Ӯзҡ„йқўиІҢгҖӮеңЁдј з»ҹеҸҷдәӢжҠҖжі•зҡ„еҹәзЎҖд№ӢдёҠпјҢж–°дёҖд»Ји—Ҹж—ҸдҪң家жӣҙеҠ жңүж„ҸиҜҶең°жіЁйҮҚжҺўзҙўдҪңе“ҒиүәжңҜеҪўејҸзҡ„еӨҡж ·жҖ§пјҢе…·дҪ“дҪ“зҺ°дёәеҜ№дёӯеӨ–еӨ§йҮҸзҡ„ж—ўжңүж–ҮеӯҰжҲҗжһңзҡ„еҖҹйүҙдёҺеҗёж”¶гҖӮ
д»Ҙи—Ҹж—ҸдҪң家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ҮӘиә«зҡ„жҲҗй•ҝз»ҸеҺҶдёәдҫӢгҖӮ1969е№ҙеҮәз”ҹзҡ„д»–жӣҫеңЁдёӯдё“жҜ•дёҡеҗҺд»ҺдәӢж•ҷеёҲе·ҘдҪңпјҢиҖҢеҗҺе°ұиҜ»дәҺиҘҝеҢ—ж°‘ж—ҸеӨ§еӯҰзҡ„и—ҸиҜӯиЁҖж–ҮеӯҰдё“дёҡгҖҒи—Ҹжұүж–Үзҝ»иҜ‘дё“дёҡпјҢ并дәҺ2002е№ҙиөҙеҢ—дә¬з”өеҪұеӯҰйҷўиҝӣиЎҢеҜјжј”дё“дёҡзҡ„ж·ұйҖ еӯҰд№ гҖӮй•ҝжңҹзҡ„и·ЁеӯҰ科еӯҰд№ з»ҸеҺҶпјҢд»Ө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ҷж ·дёҖдҪҚйӣҶдҪң家гҖҒзҝ»иҜ‘家гҖҒеҜјжј”еӨҡйҮҚиә«д»ҪдәҺдёҖдҪ“зҡ„и—Ҹж—Ҹйқ’е№ҙпјҢз”«дёҖзҷ»дёҠж–ҮеқӣдҫҝеҪ°жҳҫеҮәејҖйҳ”зҡ„еҲӣдҪңи§ҶйҮҺд»ҘеҸҠж·ұеҺҡзҡ„зҗҶи®әеҠҹеә•гҖӮд»–жӣҫеңЁи®ҝи°ҲдёӯжҳҺзЎ®жҸҗеҲ°ж–ҮеӯҰдҪң家дёҺз”өеҪұеҜјжј”еҸҢйҮҚиә«д»Ҫзҡ„зӣёдә’дҪңз”ЁеҜ№иҮӘиә«еҸ‘еұ•зҡ„вҖңеҪұе“ҚеҫҲеӨ§пјҢеҢ…жӢ¬еҜ№дәӢжғ…зҡ„и®ӨиҜҶпјҢеҜ№еҸҷдәӢзҡ„её®еҠ©зӯүвҖқпјҢиҝҳжңүвҖңж–ҮеӯҰеҲӣдҪңеҜ№еҶҷеү§жң¬жңүеҫҲеӨ§её®еҠ©пјҢжңүжғіжі•еҸҜд»ҘиЎҢиҜёдәҺж–Үеӯ—пјҢдёҚдјҡиҜҙеҶҷдёҚеҮәжқҘеү§жң¬вҖқгҖӮв‘Је…·дҪ“иҮі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пјҢйҡҸеӨ„еҸҜи§ҒеҜјжј”иҝҷдёҖиә«д»ҪеҜ№е…¶е°ҸиҜҙеҲӣдҪңиҝҮзЁӢзҡ„е…ЁйқўеҪұе“ҚпјҢе°Өе…¶жҳҜе…¶еҜ№з”өеҪұжӢҚж‘„жүӢжі•зҡ„еҖҹйүҙпјҢжһ„жҲҗдәҶиҮӘ然平淡гҖҒеҶ…и¶Ӣе№Ҫиҝңзҡ„зӢ¬зү№ж–ҮйЈҺгҖӮ
еә”еҪ“жҢҮеҮәпјҢвҖңеҸҷдәӢи§Ҷи§’вҖқиҝҷдёҖжңҜиҜӯжң¬иә«дҫҝжҳҜдёҖдёӘеёҰжңүе…үеӯҰе’Ңж‘„еҪұжҠҖе·§ж„Ҹе‘ізҡ„еҸҷдәӢеӯҰжҰӮеҝөгҖӮж‘„еғҸејҸеҸҷдәӢи§Ҷи§’еҚіжҳҜд»Ҙ第дёүдәәз§°иҝӣиЎҢеҶҷдҪңгҖӮеҸҷиҝ°иҖ…д»ҝдҪӣдёҖеҸ°е®ўи§Ӯзҡ„ж‘„еғҸжңәпјҢе®Ңе…ЁеӨ„дәҺжүҖеҸҷиҝ°зҡ„з”»йқўд№ӢеӨ–гҖӮдҪңиҖ…жңүж„ҸиҜҶең°жӢүејҖдәҶиҮӘе·ұдёҺж•…дәӢд№Ӣй—ҙзҡ„и·қзҰ»пјҢжҠӣејғдәҶеҜ№дәҺ笔дёӢдәәзү©еұ…й«ҳдёҙдёӢзҡ„йҒ“еҫ·е®ЎеҲӨпјҢеҸӘжҳҜеҝ е®һең°и®°еҪ•жүҖжҚ•жҚүеҲ°зҡ„дәәзү©еҜ№иҜқеҸҠиЎЁжғ…пјҢиҖҢдәәзү©зҡ„еҝғзҗҶжҙ»еҠЁеҸҠйҡҗеҗ«зҡ„ж•…дәӢдё»йўҳеҲҷйңҖиҜ»иҖ…йҖҸиҝҮиЎЁйқўеҪұеғҸжңҖеӨ§йҷҗеәҰең°еҒҡиҮӘиЎҢзҗҶи§ЈгҖӮеңЁ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ӯпјҢдҪң家е°ұж—¶еёёйҮҮз”Ёж‘„еғҸејҸеҸҷдәӢи§Ҷи§’иҝӣиЎҢд№ҰеҶҷпјҢдҪҝиҜ»иҖ…ж„ҹеҲ°еҰӮеҗҢи§ӮеҪұиҲ¬зҡ„йҳ…иҜ»дҪ“йӘҢгҖӮе…ідәҺиҝҷдёҖзӮ№пјҢдҪң家жӣҫз»ҸжҸҗеҲ°иҮӘе·ұеңЁжӢҚж‘„з”өеҪұж—¶еҜ№дәҺи®Іиҝ°ж–№ејҸзҡ„йҖүжӢ©пјҡвҖңиҝҷж ·еҒҡжҳҜдёәдәҶжӣҙеҘҪең°иҝҳеҺҹеңәжҷҜвҖҰвҖҰеӣ дёәи®Іиҝ°зҡ„ж„ҹи§үжҳҜеҫҲеҘҪзҡ„пјҢжҜ”жӢҚеҮәжқҘзҡ„ж„ҹи§үжӣҙеҘҪгҖӮвҖқв‘Ө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иҝҷж ·зҡ„еҶҷдҪңжүӢжі•жҳҜеҸ—еҲ°дәҶдҪң家жң¬дәәз”өеҪұйЈҺж јзҡ„еҪұе“ҚпјҢеҗҢж—¶д№ҹдҪҝеҫ—иҜ»иҖ…ж„ҹеҲ°йҳ…иҜ»еҰӮеҗҢи§ӮеҪұпјҢд»ҺиҖҢдёәжҺҘеҸ—дё»дҪ“зҡ„йҳҗйҮҠжҸҗдҫӣдәҶжӣҙеӨ§еҸҜиғҪзҡ„иЁҖиҜҙз©әй—ҙгҖӮ
д»ҘзҹӯзҜҮе°ҸиҜҙгҖҠдёҖеқ—зәўеёғгҖӢдёәдҫӢгҖӮдҪң家专门йҮҮз”ЁдәҶеӣәе®ҡеҶ…иҒҡз„ҰеһӢи§Ҷи§’иҝӣиЎҢеҸҷдәӢпјҢд»Өж•ҙдёӘдәӢ件жІҝдё»дәәе…¬д№ҢйҮ‘зҡ„иЎҢеҠЁеҸҠж„ҸиҜҶеұ•ејҖгҖӮдҪң家жңүж„Ҹж‘’ејғжҲҗе№ҙдәәеӣәжңүзҡ„жҖқз»ҙжғҜжҖ§пјҢиҖҢжҳҜеҖҹз”Ёи—Ҹж—Ҹе„ҝз«Ҙд№ҢйҮ‘зҡ„зңјзқӣи§ӮеҜҹиә«иҫ№зҡ„жғ…еўғпјҢж„ҹзҹҘе‘ЁйҒӯзҡ„дәӢзү©гҖӮе„ҝз«Ҙеёёеёёе°ҡдёҚе…·еӨҮйҖҶеҗ‘жҲ–жҠҪиұЎжҖқиҖғзҡ„иғҪеҠӣпјҢеңЁзҗҶи§ЈжҲҗдәәзҡ„дё–з•ҢжҲ–иҖ…е°қиҜ•и§ЈеҶій—®йўҳж—¶пјҢ他们еҫҖеҫҖдјҡеҮӯеҖҹиҮӘиә«д»…жңүзҡ„е…·дҪ“з»ҸйӘҢиҝӣиЎҢеҚ•еҗ‘еәҰзҡ„жҖқиҖғгҖӮеӣ жӯӨе°ҸеӯҰз”ҹд№ҢйҮ‘дјҡдёәдәҶеҶҷеҮәдёҖзҜҮдҪңж–ҮпјҢзӣҙи§Ӯең°жғіеҲ°з”ЁжӢүжҺӘзҡ„зәўйўҶе·ҫи’ҷдҪҸеҸҢзңјпјҢд»ҘжӯӨжқҘзңҹеҲҮең°дҪ“йӘҢзӣІдәәз”ҹжҙ»зҡ„дёҖеӨ©пјҡ
д№ҢйҮ‘зңӢзқҖжӢүжҺӘи„–еӯҗдёҠзҡ„зәўйўҶе·ҫиҜҙпјҡвҖңдҪ еҸҜд»ҘжҠҠдҪ зҡ„зәўйўҶе·ҫеҖҹжҲ‘дёҖеӨ©еҗ—?жҲ‘иҰҒз”Ё е®ғи’ҷдҪҸжҲ‘зҡ„еҸҢзңјгҖӮвҖқ
жӢүжҺӘжӣҙжҳҜиҜ§ејӮең°жңӣзқҖд№ҢйҮ‘пјҢиҜҙпјҡвҖңеҸҜд»ҘеҖҹз»ҷдҪ вҖ”вҖ”еҸҜжҳҜдҪ дјҡд»Җд№Ҳд№ҹзңӢдёҚи§Ғзҡ„пјҢ иҝҷж ·зҡ„дёҖеӨ©дјҡеҫҲжј«й•ҝзҡ„гҖӮвҖқв‘Ҙ
иҝҷж ·зҡ„вҖңеҲӣдёҫвҖқеңЁжҲҗдәәзңӢжқҘж— з–‘жҳҜе№јзЁҡзҡ„пјҢдәҺеӯ©з«ҘиҖҢиЁҖеҚҙжҳҜеҗҲжғ…еҗҲзҗҶгҖӮдҪң家дёҚеҺҢе…¶зғҰең°е°Ҷе°ҸеӯҰз”ҹд№ҢйҮ‘з”ЁзәўйўҶе·ҫи’ҷдёҠиҮӘе·ұзҡ„зңјзқӣжқҘж„ҹеҸ—дё–з•Ңзҡ„еҚҠеӨ©зҡ„з»ҸеҺҶз»Ҷз»ҶйҒ“жқҘпјҢж•ҙж®өж•…дәӢз”ұд№ҢйҮ‘дёҖи·Ҝзҡ„жүҖи§ҒгҖҒжүҖй—»гҖҒжүҖиЁҖдёІиҒ”иө·жқҘпјҢж¶үеҸҠзҫҠжң¬гҖҒеӨ®жҺӘгҖҒж—ҰеӨҡзӯүдәәд№Ӣй—ҙзҡ„еҜ№иҜқгҖҒ иөҢзәҰгҖҒиЎЁзҷҪеҸҠдәүжү§гҖӮд»ҺеҸҷдәӢж•ҲжһңжқҘзңӢпјҢдёҖж–№йқўпјҢдҪң家йҖҡиҝҮеҜ№еҚ•дёҖж•…дәӢж—¶еҲ»зҡ„еҚ•дёҖиҜқиҜӯе‘ҲзҺ°пјҢйҒҝе…ҚдәҶиҮӘиә«дё»и§Ӯж„ҸеӣҫеҜ№дәҺж•…дәӢзҡ„е№Іжү°пјҢдҝқиҜҒдәҶеҸҷдәӢзҡ„е®ўи§ӮпјҢеҪ°жҳҫдәҶж•ҙзҜҮдҪңе“Ғзҡ„з«Ҙзңҹз«Ҙи¶Јпјӣ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иҝҷж ·зҡ„иҒҡз„ҰжүӢжі•д»Өе°ҸиҜҙжүҖе‘ҲзҺ°зҡ„з”ҹжҙ»дёҺжҲҗдәәзҡ„ж—Ҙеёёз»ҸйӘҢд№Ӣй—ҙдә§з”ҹдәҶеҫҲеӨ§зҡ„е·®ејӮпјҢеӣ иҖҢ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ҚйҷҢз”ҹеҢ–зҡ„ж•ҲжһңгҖӮ
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ж‘„еғҸејҸеҸҷдәӢи§Ҷи§’зҡ„иҝҗз”Ёд»Өж–Үжң¬е®һзҺ°е®ўи§Ӯе‘ҲзҺ°пјҢдҪҶиҝҷ并дёҚж„Ҹе‘ізқҖдҪңиҖ…еңЁе®һйҷ…еҲӣдҪңдёӯжІЎжңүиЎЁзҺ°еҮәд»»дҪ•дё»и§Ӯе§ҝжҖҒгҖӮе…¶е®һ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жӣҫеңЁи®ҝи°ҲдёӯжҢҮеҮәпјҡвҖңжғіиҰҒж·ЎеҢ–жҺүиғҢжҷҜзҡ„дёңиҘҝвҖҰвҖҰжҠҠиҘҝи—ҸиЎЁйқўжҖ§зҡ„з¬ҰеҸ·жӢҝжҺүпјҢжҠҠдәәзҡ„зҠ¶жҖҒеҮёжҳҫеҮәжқҘгҖӮеёҢжңӣйҖҡиҝҮиҝҷдёӘдәәзү©пјҢи§Ӯдј—иғҪеӨҹдҪ“дјҡеҲ°иҮӘиә«зҡ„еӨ„еўғпјҢиҝҷдёӘжҳҜжңҖйҮҚиҰҒзҡ„гҖӮвҖқв‘ҰеҸҜи§ҒпјҢеҜ№еҪ“дёӢи—Ҹең°еҮЎдҝ—з”ҹжҙ»дёӯжүҖйҡҗзҺ°зҡ„е®—ж•ҷзІҫзҘһдёҺеӨҚжқӮдәәжҖ§зҡ„еҸҢйҮҚиҖғйҮҸдёҺе®Ўи§ҶпјҢжүҚжҳҜдҪңиҖ…й•ҝжңҹд»ҘжқҘиҮӘи§үзҡ„иүәжңҜиҝҪжұӮгҖӮеӣ жӯӨпјҢеңЁиҜёеӨҡзңӢдјје№іж·Ўе®ўи§Ӯзҡ„жҸҸеҶҷд№Ӣдёӯ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ҫҖеҫҖеҮӯеҖҹжғ…иҠӮзҡ„зӘҒиҪ¬жҲ–иұЎеҫҒгҖҒйҡҗе–»зӯүд№ҰеҶҷжҠҖе·§жөҒйңІеҮәиҮӘе·ұзҡ„д»·еҖји§ӮеҝөпјҢдҪҝеҫ—е°ҸиҜҙж–Үжң¬е…·жңүжӣҙеӨ§зҡ„йҳҗйҮҠз©әй—ҙгҖӮ
иӯ¬еҰӮеңЁе°ҸиҜҙгҖҠйҷҢз”ҹдәәгҖӢзҡ„еҸҷдәӢдёӯпјҢдҪң家еҖҹвҖңеҜ»жүҫвҖқиҝҷдёҖжҜҚйўҳиҝӣдёҖжӯҘж·ұеҢ–дёҺжӢ“еұ•дҪңе“Ғзҡ„иұЎеҫҒз©әй—ҙгҖӮе®ғеӣҙз»•зқҖдёҖдёӘеӨ–жқҘиҖ…й—Ҝе…Ҙжқ‘йҮҢеҜ»жүҫеҸ«еҚ“зҺӣзҡ„еҘідәәиҝҷдёҖдәӢ件еұ•ејҖпјҢеҗ«и“„ең°йҡҗе–»з”ҡиҮіиұЎеҫҒзқҖзҺ°д»ЈдәәзҒөйӯӮзҡ„еӨұиҗҪдёҺеҪ·еҫЁгҖӮвҖңдәҢеҚҒдёҖдёӘеҚ“зҺӣвҖқпјҢеңЁдҪӣж•ҷж•ҷд№үдёӯд»ЈиЎЁзқҖеҘізҘһеәҰжҜҚпјҢдҪңдёәдё–й—ҙдёүж®Ҡиғңд№ӢзҘһзҡ„дёҖе‘ҳпјҢеҘ№д»¬д»ҘжҺ’йҷӨдј—з”ҹжӮІиӢҰдёәдәӢдёҡгҖӮдҝЎдј—жҷ®йҒҚи®ӨдёәпјҢеҸӘиҰҒдёҚж–ӯең°еҝөиҜөеәҰжҜҚзҘҲзҘ·ж–ҮпјҢе°ұдёҖе®ҡдјҡеҫ—еҲ°еәҰжҜҚзҡ„еҠ жҢҒпјҢд»ҺиҖҢдҝқжҢҒдёӘдҪ“зҡ„иә«еҝғе®үд№җгҖӮз”ұжӯӨеҸҜи§ҒпјҢиҝҷдёӘж»ЎжҳҜвҖңз–ІеҖҰе’Ңе“ҖдјӨвҖқ⑧зҡ„йҷҢз”ҹдәәжҳҜдёәеҜ»жұӮиҮӘеәҰиҖҢжқҘ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д»–еҚҙдёәдәҶе·®йҒЈжқ‘ж°‘еҜ»жұӮеҚ“зҺӣиҖҢе°ҶйҮ‘й’ұдёҺдҝЎд»°зӣёеҜ№зӯүпјҢеёҢжңӣз”ЁдёҖеј еј зҷҫе…ғеӨ§й’һжҚўеҫ—зҒөйӯӮзҡ„еҪ’е®ҝпјҢиҝҷд№ҹжҡ—зӨәдәҶд»–е®һеҲҷ并дёҚиғҪиҺ·еҫ—жқҘиҮӘеәҰжҜҚзҡ„ж…°и—үгҖӮжһң然пјҢд»–жңҖз»Ҳд№ҹжІЎжңүеҮ‘йҪҗдәҢеҚҒдёҖдёӘеҚ“зҺӣпјҢеҸӘиғҪеёҰзқҖ并дёҚжҳҜд»–иҰҒеҜ»жүҫзҡ„зҒөйӯӮеҪ’е®ҝзҡ„й”Җе”®е‘ҳеҚ“зҺӣй»Ҝ然ең°зҰ»ејҖдәҶгҖӮ然иҖҢпјҢе°ұеңЁдёҖж®өж•…дәӢзңӢдјје·ІжӢүдёҠ帷幕зҡ„ж—¶еҖҷпјҢи„ёдёҠжҙӢжәўзқҖе№ёзҰҸе–ңжӮҰзҡ„жқ‘й•ҝеҮәеңәдәҶпјҢд»–еҗ‘дј—дәәе®Је‘ҠдәҶеӯҷеҘіеҚ“зҺӣзҡ„иҜһз”ҹпјҢж•…дәӢеңЁиҝҷйҮҢжҲӣ然иҖҢжӯўгҖӮиҮіжӯӨпјҢдҪң家йҖҡиҝҮе·§еҰҷзҡ„жғ…иҠӮеҸҚиҪ¬пјҢеҖҹе©ҙе„ҝж–°з”ҹзҡ„еҠӣйҮҸйҡҗе–»дәҶеҜ№еҪ“дёӢдҪӣж•ҷдҝЎд»°еҸҜиғҪжҖ§зҡ„ж®·еҲҮжңҹеҫ…гҖӮ
д»ҺдёҮзҺӣжүҚж—Ұжң¬дәәзҡ„еҲӣдҪңз»ҸеҺҶдёӯ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жӯЈжҳҜз”ұдәҺеӨ–йғЁзҺҜеўғгҖҒе®—ж•ҷдҝЎд»°еЎ‘йҖ дёӢзҡ„ж°‘ж—ҸеҝғзҗҶпјҢеҠ д№Ӣж–°дёҖд»Ји—Ҹж—ҸдҪң家еӨҡйҮҚзӨҫдјҡиә«д»Ҫзҡ„зӣёдә’еҖҹйҮҚпјҢ他们зҡ„еҶҷдҪңжүҚеңЁе…·жңүжө“йғҒзҡ„ж°‘ж—Ҹзү№иүІзҡ„еҗҢж—¶еҸҲжү“дёҠдәҶйІңжҳҺзҡ„дёӘдәәйЈҺж јзғҷеҚ°пјҢд»ҺиҖҢжңүж•Ҳең°жӢ“еұ•дәҶеҪ“дёӢи—Ҹж—Ҹж–ҮеӯҰзҡ„иЁҖиҜҙз©әй—ҙгҖӮ
дёүгҖҒж°‘ж—Ҹеә•иүІдёҺдё–з•Ңи§ҶйҮҺпј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дёҺ21 дё–зәӘи—Ҹж—ҸеҶҷдҪңзҡ„еҶ…ж ё
вҖңж–ҮеӯҰдҪңдёәиҜёж°‘ж—Ҹй—ҙзІҫзҘһж–ҮеҢ–жҺҘи§Ұдёӯе°Өе…¶жҳ“ж„ҹзҡ„йғЁеҲҶпјҢеёёеёёдјҡеңЁдёҚеҗҢж°‘ж—Ҹзҡ„иҝҮд»ҺдёӯпјҢж„ҹжҹ“жҲ–жҺҘз§ҚдёҠеҜ№ж–№зҡ„еҹәеӣ вҖқв‘Ё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ӯзҡ„дёҖдј—ж–Үжң¬еҚіжҳҜеҰӮжӯӨгҖӮ第дёүдәәз§°зҡ„еҸҷдәӢж–№ејҸдҪҝдәәзү©зҡ„еҪўиұЎеЎ‘йҖ е…ҚдәҺз©әжіӣиӮӨжө…пјҢиҝ‘д№ҺзҷҪжҸҸзҡ„иҜ—ж„ҸеҶҷдҪңеҸҲйҒҝе…ҚдәҶж•…дәӢзҡ„еҶ—й•ҝд№Ҹе‘іпјҢиҘҝж–№зҺ°д»ЈиүәжңҜжҠҖе·§зҡ„зәҜзҶҹдҪҝеҫ—ж•ҙзҜҮе°ҸиҜҙе®Ңж•ҙж·ұеҲ»ең°еұ•зӨәдәҶи—Ҹж—Ҹдәәж°‘зі…еҗҲдәҶдё–дҝ—дёҺзҘһеңЈгҖҒзҪӘжҒ¶дёҺж•‘иөҺзҡ„зӢ¬зү№з”ҹе‘ҪдҪ“йӘҢпјҢд»Өе…¶е°ҸиҜҙжӢҘжңүзӢ¬зү№дё”жҢҒд№…зҡ„иүәжңҜйӯ…еҠӣгҖӮйӮЈд№ҲпјҢжҳҜд»Җд№ҲжҲҗе°ұдәҶ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ғҪеӨҹиҮӘи§үең°иҝҗз”Ёеҗ„зұ»зҺ°д»ЈжүӢжі•дәҺе…¶е°ҸиҜҙеҲӣдҪңзҡ„еҗ„дёӘеұӮйқў?еңЁиҝҷдёӘз»ҙеәҰдёҠ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ҲӣдҪңеҸҲдёҺе…¶д»–и—Ҹж—ҸдҪң家еҪўжҲҗдәҶдҪ•з§ҚеҶҷдҪңйЈҺж јж–№йқўзҡ„еҢәеҲ«пјҢе…¶е…ұеҗҢзҡ„зІҫзҘһеҶ…ж ёеҸҲжҳҜд»Җд№Ҳ?
( дёҖ ) е’ҢиҖҢдёҚеҗҢзҡ„д№ҰеҶҷзү№иүІ
д»ҺдҪң家жҲҗй•ҝзҡ„еӨ–йғЁзҺҜеўғиҖҢиЁҖпјҢжҜӢеәёи®іиЁҖпјҢз”ұдәҺеҸ—ең°зҗҶз©әй—ҙдёҺеҺҶеҸІжёҠжәҗзҡ„еҪұе“ҚпјҢи—Ҹең°дёҚеҗҢеҢәеҹҹзҡ„дҪң家еңЁеҶҷдҪңдёӯеҫҖеҫҖе‘ҲзҺ°еҮәеҗ„ејӮзҡ„е§ҝжҖҒгҖӮиҝ‘е№ҙжқҘпјҢеңЁи—Ҹж—Ҹзҡ„ж–ҮеӯҰеҲӣдҪңйўҶеҹҹпјҢдёүеӨ§и—Ҹж—Ҹең°еҢәзҡ„дҪң家дҪңе“ҒејҖе§Ӣд»ҺеҸҷдәӢжЁЎејҸгҖҒдёӯеҝғиҰҒж—ЁгҖҒиҜӯиЁҖйЈҺж јзӯүеӨҡж–№йқўе‘ҲзҺ°еҮәеҮёжҳҫеҗ„иҮӘеҢәеҹҹзү№иүІзҡ„е’ҢиҖҢдёҚеҗҢзҡ„д№ҰеҶҷи¶ӢеҠҝ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Ҝ№дәҺзҺ°д»Је°ҸиҜҙжүӢжі•зҡ„еӨҡж ·еҢ–еҖҹз”ЁпјҢжӯЈжҳҜеҹәдәҺе®үеӨҡең°еҢәзҺҜеўғжүҖеҪўжҲҗзҡ„йЈҺж јгҖӮ
ж №жҚ®дёҚеҗҢзҡ„ең°еҹҹзҺҜеўғдёҺеҺҶеҸІжәҜжәҗпјҢдј з»ҹж„Ҹд№үдёҠзҡ„и—Ҹж—Ҹең°еҢәеҸҲиў«еҲ’еҲҶеҚ«и—ҸгҖҒе®үеӨҡгҖҒеә·е·ҙдёүеӨ§еҢәеҹҹгҖӮдҪҚдәҺйқ’и—Ҹй«ҳеҺҹдёңеҢ—йғЁзҡ„е®үеӨҡпјҢиҮӘеҸӨд»ҘжқҘеҸ—и—ҸгҖҒеӣһгҖҒи’ҷгҖҒжұүзӯүеӨҡж°‘ж—Ҹж–ҮеҢ–дәӨжөҒзў°ж’һзҡ„жөёжҹ“гҖӮдҪңдёәеӨҡе…ғж°‘ж—ҸгҖҒе®—ж•ҷж–ҮеҢ–并еӯҳзҡ„дәӨиһҚең°еёҰпјҢз»ҸиҝҮеҺҶеҸІзҡ„й•ҝжңҹжј”еҸҳпјҢе…¶еҶ…йғЁж°‘ж—ҸзІҫзҘһеҸҠдҝЎд»°зҡ„еӨҡж ·жҖ§зү№зӮ№иҫғд№Ӣе…¶д»–еҢәеҹҹжӣҙеҠ жҳҺжҳҫпјҢйҳҝжқҘгҖҒдёҮзҺӣжүҚж—Ұзӯүи®ёеӨҡжҲҗзҶҹзҡ„е®үеӨҡеҸҢиҜӯдҪң家зҡ„еҲӣдҪңдҫҝжҳҜеҰӮжӯӨгҖӮдҪң家йҫҷд»Ғйқ’д№ҹжӣҫеңЁи®ҝи°ҲдёӯжҢҮеҮәпјҢе®үеӨҡең°еҢәжҳҜвҖңдёӯеҺҹжұүж–ҮеҢ–е’Ңи—Ҹж–ҮеҢ–зҡ„зў°ж’һеҢәпјҢеӣ жӯӨпјҢе®ғд№ҹжӢ…иө·дәҶдёӨз§Қж–ҮеҢ–й—ҙзҡ„дҪҝиҖ…зҡ„и§’иүІвҖҰвҖҰжҲ‘жҳҜеңЁиҝҷж ·дёҖз§ҚиғҢжҷҜдёӢжҲҗй•ҝиө·жқҘзҡ„еҶҷдҪңиҖ…пјҢеҸҢиҜӯеҶҷдҪңпјҢе°ұжҲҗдәҶдёҖз§ҚиҮӘ然иҖҢ然зҡ„дәӢвҖқв‘©гҖӮд»ҺзҹӯзҜҮ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ӯпјҢдёҚйҡҫзңӢеҮәдҪң家еҜ№еҪ“дёӢи—Ҹең°еҮЎдҝ—з”ҹжҙ»дёӯжүҖйҡҗзҺ°зҡ„е®—ж•ҷзІҫзҘһдёҺеӨҚжқӮдәәжҖ§зҡ„еҸҢйҮҚиҖғйҮҸдёҺе®Ўи§ҶпјҢиҝҷжӯЈжҳҜеҸ—дәҶе…¶й•ҝжңҹд»ҘжқҘиҮӘи§үзҡ„иүәжңҜиҝҪжұӮд»ҘеҸҠе®үеӨҡең°еҢәж–ҮеҢ–иғҢжҷҜеЎ‘йҖ зҡ„еҸҢйҮҚеҪұе“ҚгҖӮ
з»јдёҠпјҢжӯЈеҰӮжқЁд№үжүҖиЁҖпјҢиҫ№ең°зҡ„вҖңж–ҮжҳҺеёҰжңүеҺҹе§ӢжҖ§пјҢеёҰжңүжөҒеҠЁжҖ§пјҢеёҰжңүеҗёж”¶еӨ–жқҘзҡ„ејҖж”ҫжҖ§вҖқпјҢи—Ҹең°дҪң家еӨҡз»ҙеәҰеҲҮе…ҘеӨҚжқӮзҡ„и—Ҹж—Ҹж–ҮеҢ–е®—ж•ҷдј з»ҹжүҖиҝӣиЎҢзҡ„д№ҰеҶҷжҳҜе’ҢиҖҢдёҚеҗҢзҡ„пјҢиҖҢиҝҷд№ҹвҖңе°ұжҳҜеӨҚеҗҲеһӢзҡ„ж–ҮеҢ–з»“жһ„гҖҒеҠҹиғҪжүҖеёҰжқҘзҡ„ж–ҮеҢ–еҠЁеҠӣеӯҰзҡ„е‘ҪйўҳвҖқгҖӮв‘ӘдёҚеҗҢең°еҹҹзҡ„з”ҹжҖҒзҺҜеўғгҖҒеҢәеҹҹж–ҮеҢ–еҠ дёҠе…ұеҗҢзҡ„и—Ҹдј дҪӣж•ҷдҝЎд»°пјҢжһ„жҲҗдәҶдёҚеҗҢи—Ҹж—ҸдҪң家зҫӨзӢ¬зү№зҡ„з”ҹе‘ҪдҪ“йӘҢдёҺиә«д»Ҫи®ӨеҗҢгҖӮдёҮзҺӣжүҚж—ҰдҫҝжҳҜеңЁиҝҷж ·е’ҢиҖҢдёҚеҗҢзҡ„зҺҜеўғдёӢжҲҗй•ҝиө·жқҘзҡ„дёҖдҪҚеёҰжңүйІңжҳҺзҡ„еҲӣдҪңйЈҺж јзҡ„и—Ҹж—ҸдҪң家гҖӮ
(дәҢ)иҮӘ然дәәжҖ§е®ЎзҫҺеҢ–дёҺи¶…и¶Ҡиҫ№з•Ң
зәөи§Ӯдј—еӨҡзҡ„и—Ҹж—ҸдҪң家дҪңе“ҒпјҢж— и®әжҳҜе°Ғе»әж—¶жңҹд№ҰеҶҷеӨҡж°‘ж—ҸеҶІзӘҒгҖҒзў°ж’һзҡ„еҺҶеҸІиҝӣзЁӢпјҢиҝҳжҳҜи§Јж”ҫеҗҺд№ҰеҶҷи—Ҹжұүж°‘ж—Ҹзҡ„дәӨжөҒдёҺиһҚеҗҲпјҢд»ҘеҸҠ20дё–зәӘ80е№ҙд»Јзҡ„зҘһжҖ§еҶҷдҪңпјҢд№ғиҮіж”№йқ©ејҖж”ҫд»ҘжқҘе…ЁзҗғеҢ–иғҢжҷҜдёӢи—Ҹж—Ҹе®—ж•ҷж–ҮеҢ–дёҺеӨ–жқҘж–ҮеҢ–зҡ„еҜ№иҜқпјҢи—Ҹж—ҸдҪң家ж„ҲжқҘж„ҲжҳҫжҖ§ең°е‘ҲзҺ°еҮәиҮӘи§үзҡ„ж–ҮеӯҰиҝҪжұӮгҖӮ21дё–зәӘд»ҘжқҘ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зӯүж–°дёҖд»Ји—Ҹж—ҸдҪң家жӣҙжҳҜиҮӘи§үең°е°ҶиҮӘжҲ‘жҖқиҖғе‘ҲзҺ°дәҺдҪңе“Ғд№ӢдёӯпјҢиҝҗз”Ёеҗ„зұ»зҺ°д»ЈеҲӣдҪңжүӢжі•жңүж„ҸиҜҶең°з»ҸиҗҘж–Үжң¬пјҢдҪ“зҺ°еҮәзҺ°д»ЈжҖ§и§ҶйҮҺзҡ„жӢ“еұ•дёҺжҖқжғіе§ҝжҖҒзҡ„зӢ¬з«ӢгҖӮ
д»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дёәд»ЈиЎЁзҡ„ж–°дёҖд»Ји—Ҹж—ҸдҪң家еҜ№иҮӘ然дәәжҖ§зҡ„е®ЎзҫҺеҢ–д№ҰеҶҷпјҢдҪ“зҺ°дәҶжӣҙй«ҳеұӮж¬Ўзҡ„ж–ҮеӯҰиҮӘи§үгҖӮиҝҷдёҚеҗҢдәҺе®ҸеӨ§еҸҷдәӢдёӯеҜ№ж°‘ж—Ҹзү№жҖ§зҡ„еҺӢжҠ‘пјҢд№ҹдёҚеҗҢдәҺйғЁеҲҶдҪң家еҜ№е°‘ж•°ж°‘ж—ҸдәәжҖ§зҡ„зҘһз§ҳеҢ–пјҢиҖҢжҳҜйҖҡиҝҮжҷ®йҖҡдәәзҡ„еҮЎдҝ—з”ҹжҙ»пјҢе®ЎзҫҺең°еұ•зҺ°жё—йҖҸдәҺе…¶дёӯзҡ„ж°‘ж—Ҹж–ҮеҢ–еҝғзҗҶгҖӮеӣ жӯӨпјҢгҖҠеЎ”жҙӣгҖӢдёӯйҒӯйҒҮйҒ“еҫ·еҚұжңәзҡ„зү§зҫҠдәәеЎ”жҙӣпјҢгҖҠжӯ»дәЎзҡ„йўңиүІгҖӢдёӯеҜ№дёҚиғҪиҮӘзҗҶзҡ„ејҹејҹзҲұжҒЁдәӨз»Үзҡ„е°јзҺӣпјҢ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дёӯе—ңй…’еҚҙе–„иүҜиҷ”иҜҡзҡ„жҙӣжЎ‘гҖҒзө®еҸЁеҸҲжё©еҗһйҮҚжғ…зҡ„еҲ»зҹіиҖҒдәәпјҢзӯүзӯүпјҢд»ҘзҘһжҖ§зҡ„и§Ҷи§’иҖҢиЁҖпјҢеӨ§йғҪдёҚжҳҜзәҜдёҖдёҚжқӮжҲ–е®ҢзҫҺж— зјәпјҢ他们зҡ„з”ҹжҙ»д№ҹ并йқһж—¶ж—¶е……ж»ЎжҲҸеү§еј еҠӣпјҢдҪҶ他们жҒ°жҒ°е°ҪеҸҜиғҪе®Ңж•ҙең°е‘ҲзҺ°еҮәдәҶи—Ҹж—Ҹдәәж°‘еңЁе®—ж•ҷдёҺдё–дҝ—з”ҹжҙ»дёӯзҡ„еӨҡж ·йқўиІҢгҖӮиҝҷз§ҚеҸҚзҘһеңЈеҢ–гҖҒеҘҮи§ӮеҢ–еҶҷдҪңзҡ„еҠӘеҠӣпјҢеңЁе…¶еҗҺгҖҠд№ҢйҮ‘зҡ„зүҷйҪҝгҖӢгҖҠж•…дәӢеҸӘи®ІдәҶдёҖеҚҠгҖӢзӯүе°ҸиҜҙйӣҶдёӯиҝӣдёҖжӯҘеҫ—еҲ°е»¶дјёпјҢеҮәзҺ°дәҶгҖҠж°”зҗғгҖӢдёӯеҫҳеҫҠдәҺдҝЎд»°дёҺиҮӘжҲ‘й—ҙзҡ„еҚ“еҳҺгҖҒгҖҠзҢңзҢңжҲ‘еңЁжғід»Җд№ҲгҖӢдёӯжҡҙеҜҢеҗҺж»Ўи…№жҲҫж°”ең°иҰҒжұӮвҖңйҡҸдҫҝжқҖдёҖдёӘе°ұиЎҢвҖқв‘«зҡ„жҙӣи—ҸгҖҒгҖҠж°ҙжһңзЎ¬зі–гҖӢдёӯйҘұеҗ«иӢҰйҡҫдёҺжҲҗе°ұзҡ„жҜҚдәІзӯүпјҢжӣҙеӨҡе…·жңүиҫғејәзңҹе®һжҖ§гҖҒзҺ°е®һжҖ§гҖҒеҸҚжҖқжҖ§зҡ„еҮЎдҝ—дәәзү©еҪўиұЎгҖӮ
з»“еҗҲиҝҷдёҖеҲӣдҪңзү№иүІеҸҜд»ҘзңӢеҮәпјҢд»ҘдёҮзҺӣжүҚж—Ұдёәд»ЈиЎЁзҡ„еҪ“дёӢи—Ҹж—ҸдҪң家笔дёӢзҡ„дәәзү©пјҢдёҖж–№йқўе…·жңүж·ұеҸ—дј з»ҹжөёжҹ“зҡ„иў«еҠЁдҫқйҷ„еһӢдәәж јпјҢ他们йЎәеә”иҮӘ然дёҺзҘһзҡ„ж—Ёж„ҸпјҢд»ҘеҺҡйҮҚзҡ„жӮІжӮҜжғ…жҖҖпјҢжҺҘиҝ‘еҺҹе§Ӣең°з”ҹеӯҳзқҖпјӣеҸҰдёҖж–№йқўпјҢдјҙйҡҸзқҖзҺ°д»ЈеҢ–з”ҹжҙ»ж–№ејҸзҡ„йҖҗжёҗжҷ®еҸҠпјҢи—Ҹж—Ҹж°‘дј—зҡ„дё–дҝ—з”ҹжҙ»еҸ‘з”ҹдәҶиҫғеӨ§зҡ„ж”№еҸҳпјҢзӣёеә”зҡ„пјҢж–°зҡ„д»·еҖји§Ӯеҝөз”ұжӯӨејҖе§Ӣз”ҹеҸ‘пјҢ并еңЁжҜҸдёӘдәәзҡ„з»ҸйӘҢдё–з•ҢдёӯеҹӢдёӢдәҶиҪ¬жҠҳзҡ„дјҸ笔гҖӮиҝҷж ·зҡ„дәәзү©еҪўиұЎйҡҫд»Ҙз”ЁзҺ°д»ЈзҗҶжҖ§/е®—ж•ҷдј з»ҹзҡ„дәҢе…ғеҜ№з«Ӣзҡ„иҜқиҜӯиҜ„д»·зі»з»ҹиҝӣиЎҢиҜ„еҲӨпјҢеҚҙжҳҜеҪ“дёӢи—Ҹж—Ҹж°‘дј—жңҖдёәеӨҚжқӮдё”зңҹе®һзҡ„еҶҷз…§гҖӮдј—еӨҡдәәзү©еҪўиұЎжүҖжҳ з…§еҮәзҡ„жҷ®йҒҚдәәжҖ§зҡ„еӨҡз»ҙдёҺе…ұйҖҡпјҢжӣҙжҳҜе‘јеә”дәҶдё–з•Ңж–ҮеӯҰзҡ„дё»жөҒиҜқиҜӯеҪўејҸпјҢиҝҷжҳҜеҪ“дёӢи—Ҹең°ж–ҮеӯҰжңҖзӘҒеҮәзҡ„иҙЎзҢ®д№ӢдёҖгҖӮеҸҜйў„и§Ғзҡ„жҳҜпјҢжңӘжқҘи—Ҹж—Ҹж–ҮеӯҰзҡ„еҸ‘еұ•и¶ӢеҠҝеҝ…е®ҡжҳҜе…је…·жң¬еңҹж„ҸиҜҶдёҺдё–з•Ңзңје…үпјҢйӣҶж°‘ж—ҸдҪҝе‘ҪгҖҒе®—ж•ҷдҝЎд»°дёҺ家еӣҪжғ…жҖҖдәҺдёҖдҪ“пјҢйҖҸиҝҮеҜ№жң¬ж°‘ж—Ҹз”ҹеӯҳж ·жҖҒзҡ„и§Ӯз…§пјҢз”Ёж–ҮеӯҰд№ҰеҶҷеЎ‘йҖ е…ёеһӢдәәзү©пјҢиҝӣиҖҢеҮёжҳҫеҮәи¶…и¶Ҡиҫ№з•Ңзҡ„е…ұеҗҢзҡ„дәәзұ»жғ…ж„ҹдёҺж„ҸиҜҶгҖӮ
з»“ иҜӯ
жҖ»д№ӢпјҢеңЁдё»жөҒж–ҮеӯҰиҝӣдёҖжӯҘж„ҹеҸ¬дёҺдҪң家з«ӢеңәиҮӘи§үжү¬ејғзҡ„еҸҢйҮҚ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йҖҡиҝҮеҜ№зҺ°д»ЈеҢ–иғҢжҷҜдёӢи—Ҹж—Ҹзү§ж°‘еҮЎдҝ—дәәз”ҹжҲ–еӣ°жғ‘жҲ–еӯӨзӢ¬зҡ„иҜ—ж„Ҹеұ•зҺ°пјҢеҮёжҳҫдәҶж°‘ж—ҸејӮиҙЁиғҢжҷҜдёӢжҷ®йҒҚдәәжҖ§зҡ„еӨҡз»ҙгҖҒдё°еҜҢдёҺж·ұеҲ»гҖӮд»–зҡ„е°ҸиҜҙйӣҶ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еӣ дј з»ҹдёҺзҺ°д»ЈгҖҒе°Ғй—ӯдёҺеҸ‘иҫҫгҖҒдәәжҖ§дёҺзҘһжҖ§гҖҒиҮӘжҲ‘дёҺд»–иҖ…д№Ӣй—ҙзҡ„дә’еҠЁдёҺж‘©ж“ҰиҖҢ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жһҒеҜҢи§ЈиҜ»жҖ§зҡ„иЁҖиҜҙз©әй—ҙгҖӮжңҖдёәйҮҚиҰҒзҡ„жҳҜпјҢеңЁеӨҡе…ғж–ҮеҢ–иҝӣдёҖжӯҘйў‘з№Ғж·ұе…Ҙдә’еҠЁзҡ„еҪ“дёӢпјҢеңЁеҗ„ж°‘ж—ҸгҖҒеӣҪ家平зӯүеҜ№иҜқдёҺдәӨжөҒзҡ„иҜӯеўғдёӯпјҢеҰӮдҪ•иғҪеӨҹж—ўеҖҹеҠ©е…ЁзҗғеҢ–иҜқиҜӯжӢ“еұ•ж–ҮеӯҰиЎЁзҺ°зҡ„еңәеҹҹпјҢеҸҲз«Ӣи¶іжң¬еңҹзҡ„ж–ҮеҢ–дј з»ҹдҝқжҢҒиҮӘиә«ејӮиҙЁеұһжҖ§пјҢйҖҡиҝҮж–ҮеӯҰдҪңе“Ғж·ұеҲ»иЎЁзҺ°еҮәжң¬еңҹж–ҮеҢ–зҡ„зІҫзҘһеҶ…ж ёпјҢд»ҺиҖҢдҪҝеҲӣдҪңе…·жңүжҷ®йҒҚзҡ„дё–з•Ңж„Ҹд№үгҖӮдәҺжӯӨпјҢдёҮзҺӣжүҚж—Ұе·Із»ҸеңЁж–ҮеӯҰдёҺз”өеҪұзҡ„еҸҢеЈ°йҒ“дёӯејҖеҗҜдәҶеҸҜиҙөзҡ„жҺўзҙўе®һйӘҢгҖӮдҪҶжҳҜж јеӨ–д»Өдәәе”Ҹеҳҳзҡ„жҳҜпјҢвҖңж•…дәӢеҸӘи®ІдәҶдёҖеҚҠвҖқпјҢи—Ҹж—Ҹж–ҮеӯҰдёҺз”өеҪұзҡ„еј•и·Ҝдәә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ҳжңүеӨӘеӨҡзҡ„зҒөж„ҹдёҺи®ЎеҲ’жІЎжңүд»ҳиҜёе®һзҺ°пјҢе°ұд»Өдәәз—ӣеҝғең°жәҳ然иҖҢйҖқгҖӮж–Ҝдәәе·ІеҺ»пјҢе№ҪжҖқй•ҝеӯҳпјҢеңЁдёҮзҺӣжүҚж—Ұзҡ„еҸ‘жҺҳдёҺйј“еҠұдёӢжҲҗй•ҝиө·жқҘзҡ„вҖңи—Ҹең°ж–°жөӘжҪ®вҖқдҪң家们д»Қ然任йҮҚйҒ“иҝңпјҢжңӘжқҘзҡ„и—Ҹең°ж•…дәӢд№ҹе°Ҷз”ұ他们жүҝжҺҘгҖҒжј”иҝ°дёҺдёҚж–ӯеҸ‘жү¬гҖӮи—Ҹж—Ҹж–ҮеӯҰдёҺз”өеҪұеҸІе°Ҷж°ёиҝңй“ӯи®°иҝҷдҪҚжқ°еҮәзҡ„еҲӣдҪңиҖ…вҖ”вҖ”дёҮзҺӣжүҚж—Ұ!
жіЁйҮҠ
в‘ 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дёҒжқЁпјҡгҖ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еҶҷе°ҸиҜҙжҳҜжҜ”жӢҚз”өеҪұжӣҙзәҜзІ№зҡ„еҲӣдҪңгҖӢпјҢгҖҠдёӯеҚҺиҜ»д№ҰжҠҘгҖӢ2022е№ҙ6жңҲ15ж—ҘгҖӮ
в‘Ў 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жңұй№Ҹжқ°пјҡгҖҠж–ӯиЈӮзҡ„ж°‘ж—ҸжҖ§вҖ”вҖ”и—Ҹж—ҸеҜјжј”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и°ҲгҖӢпјҢгҖҠз”өеҪұж–°дҪңгҖӢ2016е№ҙ第3жңҹгҖӮ
в‘ў 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и®ёйҮ‘жҷ¶пјҡгҖҠдёҮзҺӣжүҚж—ҰеҜјжј”и®ҝи°ҲгҖӢпјҢгҖҠжҲҸеү§дёҺеҪұи§ҶиҜ„и®әгҖӢ2015е№ҙ第5жңҹгҖӮ
в‘Ј 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жңұй№Ҹжқ°пјҡгҖҠж–ӯиЈӮзҡ„ж°‘ж—ҸжҖ§вҖ”вҖ”и—Ҹж—ҸеҜјжј”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и°ҲгҖӢпјҢгҖҠз”өеҪұж–°дҪңгҖӢ2016е№ҙ第3жңҹгҖӮв‘Ө 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жңұй№Ҹжқ°пјҡгҖҠж–ӯиЈӮзҡ„ж°‘ж—ҸжҖ§вҖ”вҖ”и—Ҹж—ҸеҜјжј”дёҮзҺӣжүҚж—Ұи®ҝи°ҲгҖӢпјҢгҖҠз”өеҪұж–°дҪңгҖӢ2016е№ҙ第3жңҹгҖӮв‘Ҙ 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пјҢдёӯеӣҪж°‘ж—Ҹж‘„еҪұиүәжңҜеҮәзүҲзӨҫ2014е№ҙзүҲпјҢ第102-103йЎөгҖӮ
в‘Ұ дёҮзҺӣжүҚж—ҰгҖҒйҮҺеҗӣпјҡгҖҠдё“и®ҝ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еңЁиҝҷдёӘзӨҫдјҡпјҢжү’дёӢзҡҮеёқзҡ„ж–°иЎЈжӣҙйҮҚиҰҒгҖӢпјҢгҖҠз”өеҪұдё–з•ҢгҖӢ2016е№ҙ第12жңҹгҖӮ
⑧ 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гҖҠеҳӣе‘ўзҹіпјҢйқҷйқҷең°ж•ІгҖӢпјҢдёӯеӣҪж°‘ж—Ҹж‘„еҪұиүәжңҜеҮәзүҲзӨҫ2014е№ҙзүҲпјҢ第35йЎөгҖӮ
в‘Ё е…ізәӘж–°пјҡгҖҠеҲӣе»ә并确з«ӢдёӯеҚҺеӨҡж°‘ж—Ҹж–ҮеӯҰеҸІи§ӮгҖӢпјҢгҖҠж°‘ж—Ҹж–ҮеӯҰз ”з©¶гҖӢ2007е№ҙ第2жңҹгҖӮ
в‘© йӮҰеҗүжў…жңөгҖҒйҫҷд»Ғйқ’пјҡгҖҠжҲ‘пјҢеңЁйқ’жө·еҶҷдҪңвҖ”вҖ”йҫҷд»Ғйқ’и®ҝи°ҲгҖӢпјҢйҷҲжҖқе№ҝдё»зј–пјҢгҖҠйҳҝжқҘз ”з©¶гҖӢ(第6иҫ‘)пјҢеӣӣе·қеӨ§еӯҰ еҮәзүҲзӨҫ2017е№ҙзүҲпјҢ第176-177йЎөгҖӮ
в‘Ә жқЁд№үгҖҒйӮөе®Ғе®ҒпјҡгҖҠвҖңйҮҚз»ҳдёӯеӣҪж–ҮеӯҰең°еӣҫвҖқвҖ”вҖ”жқЁд№үе…Ҳз”ҹеӯҰжңҜи®ҝи°ҲгҖӢпјҢйӮөе®Ғе®ҒпјҢгҖҠзҺ°д»Јж–ҮеӯҰпјҡеӯҰ科еҺҶеҸІдёҺжңӘжқҘиө° еҗ‘гҖӢпјҢз”ҳиӮғж•ҷиӮІеҮәзүҲзӨҫ2013е№ҙзүҲпјҢ第11йЎөгҖӮ
в‘« дёҮзҺӣжүҚж—ҰпјҡгҖҠж•…дәӢеҸӘи®ІдәҶдёҖеҚҠгҖӢпјҢдёӯдҝЎеҮәзүҲйӣҶеӣў2022е№ҙзүҲпјҢ第239йЎөгҖӮ

йӯҸж¬ЈжҖЎпјҢз”ҳиӮғзҷҪ银дәәпјҢйҷ•иҘҝеёҲиҢғеӨ§еӯҰж–ҮеӯҰйҷўеҚҡеЈ«з ”з©¶з”ҹгҖ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