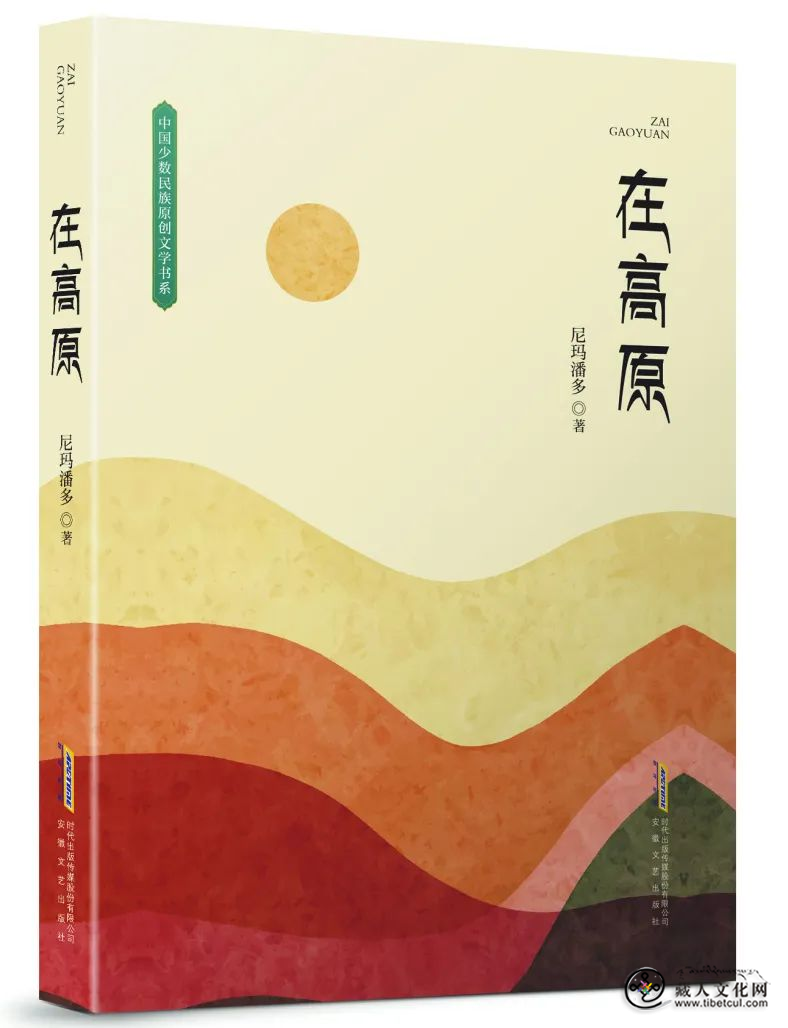
《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12 在当代藏族女性作家中,尼玛潘多的创作具有很大的辨识度。她往往从女性个体生命处境出发,以遒劲绵密的现实主义文笔,深入描摹西藏城乡社会生活,展现西藏现代化进程中普通人的生命遭际,意图“剥去西藏的神秘与玄奥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实生活展现跨越民族界限的、人类共通的真实情感”[1],在21世纪以来的藏地叙事“还原化”书写中,显现了独特的价值。2022年底出版的长篇小说《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延续了尼玛潘多以往小说创作的风格并进行了新的拓展。作品由个人史进入家族史,从现实生活描摹向纵深历史探寻,通过父辈与子辈、城市与乡村、藏地与汉地等多维视角展现了西藏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并有意识地将西藏城乡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相联系,拓展了藏地叙事的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作品富涵的精神气质以及对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描写成为中国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历史书写 谢有顺教授在其《小说是活着的历史》一文中谈到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土地情结和历史情结,认为中国的小说传统始终脱不了历史这一大传统,小说不和历史发生对话,就很难获得持久的影响力。[2]尼玛潘多的创作扎根大地,从一开始就试图以宏阔的视角展现西藏的历史变迁以及个体在时代变化中的心路历程,有意识地建构起她对西藏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思考。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紫青稞》(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将鲜被关注的西藏农村变革纳入艺术视野,通过乡村儿女的命运转折,呈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的现代化变革之路。而在长篇新作《在高原》中,尼玛潘多显现出她向历史纵深处的开掘,作品以一家四代人的经历,呈现出西藏近百年的社会发展图景,凸显了作家对个体、族群命运的探寻和对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思考。 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呈现百年历史,展现对个体与民族国家精神血脉的探寻,这很能考验作家在处理大的历史事件上的艺术魄力。尼玛潘多的《在高原》在对历史书写的架构和处理中是有侧重的。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历史波谲云诡,尼玛潘多主要运用回溯和追忆的手法,在家族溯源中呈现其历史之风貌。如对家族第一代扎西次仁(张天禄)经历的描写,展现了晚清的政治局势。“20世纪初,拉萨发生乱情,清朝驻藏官兵在动乱中遭到驱逐。在驻藏大臣衙门任低等文官秘书的张天禄,虽不舍拉萨,也只能随众前往印度,取道印度回家。”[3]历史作为粗略的线条,如草蛇灰线一样隐藏在文本中,作者关注的更多是对历史语境下个体生存的描摹和对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勾勒。在对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书写中,作者则以大量的篇幅详尽地描写了“文革大革命”时期的知青生活,通过朗杰多吉的回忆和追溯,细致地呈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社会的状况,并在个人的遭遇史中让逝去的历史得以鲜活再现。 “知青文学”的热潮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王安忆、韩少功、史铁生、梁晓声、叶辛等一批知青作家对知青生活进行了回溯和反思,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整体或局部以知青为叙述对象的作品亦有不少。尼玛潘多的历史书写不同于很多描写知青题材的作品,或者高举理想主义旗帜对那段经历进行浪漫化的书写,或者写肉体和精神的创痛,而是将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物还原于逐渐被淡忘的静默的历史画面之中,以娓娓叙说的方式通过他们的遭际展现了那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作者挖掘历史中的人事,通过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全景的呈现,在日常生活的铺排之中展现了个体灵魂的受难和他们坚韧的生存景观。对普通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命运的关注,不仅意味着西藏历史书写空间的开拓,而且将对“文革”的反思带到了历史的本真现场,从而进行了多元的辩证思考。 《在高原》中,“文革”到来后,还俗回家的朗杰多吉的姑姑索朗开始变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祖传的茹玛大院里也住进了其他住户,生活日渐逼仄和压抑。学校里的政治运动使朗杰多吉感觉生活一天天正朝着低处滑去,一种坠落感让人丧气。1970年3月20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号召下,19岁朗杰多吉和一群初中学生,以及小学毕业后就赋闲在家,连中学的门都没有进去过的十来岁的少男少女,要汇入农村插队的时代浪潮之中。学校的操场上聚满了插队的学生及送行的亲友:“广播里传来校长的声音,话别的人太多,没几个人听广播,朗杰多吉记住了偶尔飘来的几句话:‘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要做新时代的农民……’”[4]朗杰多吉当晚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1970年3月20日,我们从学校统一出发奔赴各县。出发前,学校的操场上挤满了送行的人,有学生家长和亲戚,也有那些因为身体和家庭原因不用下乡的同学,他们都带来了酒和酥油茶,见人就要敬上一碗,好像我们是即将上战场的人,命运难以预料的感觉。”[5]作者平静地写着,没有任何渲染,但文字背后却有一种难掩的苍凉。犹如食指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所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6]诗人以其透彻心扉的诗句楔入时代,真实地记录了一代知青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隔着历史的尘烟,尼玛潘多冷静地叙述了雪域大地上的这场历史变革。“如果说真有命运安排的话,我跟随姑姑到东孜,然后执意要下乡在塔玛当知青,是不是对命运的反抗?”[7]那个站在学校操场顶着三月寒风的19岁青年,其实并不清楚前方的路况,他只是不得已做出了那个历史境遇下与万千知识青年相同的选择,被历史裹挟,然而又带着期望,到塔金县塔玛公社插队。朗杰多吉背负着自身的理想,也担负着塔金人民对于知识青年的期待。他勤恳、隐忍、虔诚,在陌生的塔玛公社用行动践行奉献,在打土坯、修沟渠、寻找失踪牧民桑多的过程中,都表现了坚毅、勇猛、敢于担当的精神,脚踏实地赢得了村民的尊重和信任。然而贫瘠而艰苦的生活,时时涌动的孤独和无人理解的窒息之感使他在苦难的岁月中暗自伤悲。初到塔玛公社,在“三打一反”运动中,朗杰多吉就因为砍了一棵小树做铁锹把子而受到了批判,在一次次大会上做检讨,这使他感受到了羞辱。作者虽然没有过多地去渲染插队生活的苦难,没有对这场历史运动进行臧否,然而,在作品中,通过对同去插队的学生的低落心情,以及在插队后期大家想方设法离开乡村的描写,对这场历史运动进行了真切的反思。 作品通过朗杰多吉的经历,真实地刻画了发生在雪域高原上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者的用意显然是多方面的,既有沉浸在文字后的反思,又有在苦难中寻找生命之光的努力,她以纵深的历史感叠加有意味的叙事形式,着意凸显的是生命的韧性、道德情感的淳朴与人性的良善,这使其笔下的叙事有了人性光芒与精神辉耀。乡村虽然荒僻、贫穷、落后,但乡村人的善良和淳朴,特别是乡村姑娘的温柔多情、善解人意,使不少知青在苦难的境地中得到灵魂安宁。作品中梅朵曲珍以自己的细致体贴和纯洁深沉的爱使朗杰多吉感受到了无边的温暖,两人之间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尼玛潘多挖掘人性的良善和美好,她所呈现的历史图景中,虽也有如会计、副队长等自私算计、暗怀心思之人,但在展现这些人物时,对其更多的是理解之同情。尼玛潘多写苦难,但在苦难生活里却辉映着人性之光芒。 在此前的西藏书写中,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白玛娜珍的小说都曾涉及“文革”,但知青书写在藏族文学史上是缺失的。尼玛潘多的创作关注普通人的命运遭际,将雪域高原上的知青生活引入我们的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玛潘多的《在高原》构建了藏地“文革”叙事的新图景,拓展了藏族文学历史书写的领域。
二、家族记忆 21世纪以来历史叙事的题材丰富多样,而家族历史题材的创作往往将视角落在时代大历史和个体人物的成长上,通过家族的变迁和个体人物的迁徙流转来展现历史的发展进程,由此在历史和个人的双重记忆中完成了对灵魂的审视和对社会的探查。尼玛潘多表示:“在写作完长篇小说《紫青稞》后,我一直有个愿望:写出一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作品。随着时间的延绵,随着周遭各色人物的不断走入与走出,完整地呈现出时间与环境对人生的影响和转变。”[8]《在高原》通过对家族四代人经历的描摹,展现了西藏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在这其中,既有清朝末年朗杰多吉的爷爷扎西次仁的曲折经历,又有朗杰多吉的父亲旦增去噶伦堡经商的惊险传奇,还有朗杰多吉的知青经历,以及朗杰多吉的女儿白玛措吉在新的时代变革中的心路历程。尼玛潘多以家族叙事的方式贯穿起了对西藏近百年历史的思考,她将知识化的历史处理成与个体经验、家族变迁相关的历史,从而使历史的书写显得鲜活而生动,并因为对日喀则一带民情风俗的描绘,使整部作品蕴含丰厚的民俗文化特质,承载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地域经验,显现了饱满、深邃而旷达的历史审视与审美探求。 作品从朗杰多吉的爷爷扎西次仁即张天禄开始写起。张天禄老家在四川雅安,幼时双亲早逝,历经磨难,机缘巧合跟随商队进入西藏,做了驻藏大臣衙门的低等文官,后数年在西藏生活,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盼望与其他进藏的同僚一样,娶一个本地女子幸福度过一生。但在动乱的形势下,他不得已只能随众准备前往印度,取道印度回内地老家。在边境小镇夏斯玛,他遇到在拉萨交情深厚的朋友喀苏家的大公子索朗次仁,索朗次仁恳切地挽留他:“你在老家也无牵挂,一切从头再来,还不如留在这里,这天终归是变不了的,最多阴雨绵绵几天。”[9]在索朗次仁的帮助和提携下,张天禄假扮藏族人,起藏名扎西次仁,跟随商队来到东孜,被索朗次仁安排在商店当伙计,他勤劳苦干、聪明机巧,深得商店老板果果扎西的信任和厚待。扎西次仁最后在东孜娶亲安家,顺风顺水地单独做起了生意,攒下了一笔家产,买下了茹玛大院。扎西次仁为人豪爽,“日子过顺了也想着别人,无论是普尺的娘家人,还是同乡会的,或者邻里们,对他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在同乡会携家带眷相聚的中秋节,大家推举他任同乡会的副大爷,辅助果果。作为一个外来人,这样的认可,让他热泪盈眶”[10]。儿子旦增学识出众,很快在东孜的宗府谋到了差事,深得东孜宗本的赏识,成为家族的希望。旦增年轻气盛,为了不被人看轻受欺负,要振兴家业,不畏艰险到噶伦堡经商。但旦增最后却和父亲决裂,离开东孜来到拉萨经商。作者在文中设置了悬念,父子决裂的原因扑朔迷离——到底是因为与酒娘女儿的婚事,还是因为旦增赌博败光了家产,抑或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作品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但作品通过探寻原因,显现了家族溯源的努力,同时通过家族探寻,呈现了广阔的民间生活场景。 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展开,在交叠的叙事中展现家族的历史,还原历史场景,使家族人物形象一点点丰满起来。旦增的儿子朗杰多吉被过继给姑姑索朗,他来到东孜,又在时代浪潮中到塔金县塔玛公社插队,后来在塔金安家。朗杰多吉的女儿白玛措吉大学毕业回到塔金,经过努力调到拉萨,但在拉萨却感受到难以融入的心灵之痛。作品通过对历史语境中普通人物经历的描写,展现了在大的时代变革中个体的命运遭际,在家族叙事中呈现了鲜活的个人记忆。 值得关注的是,作品在家族叙事中还凸显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尼玛潘多认为,在“褪去了民族特色这层外衣之后,大家都是寻常的普通人,情感都是共通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11]。虽着墨不多,但作品书写历史发展脉络中的藏汉一体,彼此交融的生活图景显得温馨又美好。扎西次仁对西藏的深情和恋恋不舍,索朗次仁对扎西次仁的欣赏与帮助,藏族姑娘普尺对扎西次仁的爱慕与温情,果果扎西与扎西次仁之间的融洽体贴,都展现了历史进程中藏汉交融、和谐生活的图景。笔触到了当代,对白玛措吉在内地求学,及工作后与卓玛、李启梅、夏荷之间友情的渲染描摹,全景式地展现了民间日常生活的和谐,也勾勒出了民族融合、家国同构的历史脉络,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品格。此外,作品中,扎西次仁跟随索朗次仁从边境小镇夏斯玛到东孜的旅程,旦增去噶伦堡经商的惊险之旅,帕里一带的商行和酒馆,以及扎西次仁在东孜的生活、塔金的地域风貌等,尼玛潘多对烟火世情的种种描写展现了普通人的生存体验,其写作兼具审视和包容的姿态,呈现了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风俗景观。
三、精神探求 尼玛潘多的创作关注个体在时代转折过程中灵魂与精神的探求,在家族叙事中不仅展现了民间传统伦理和现代经验之间的冲突,更凸显了个人在时代语境中的精神跋涉。 朗杰多吉因父亲的决定而从拉萨来到东孜,又随时代浪潮插队来到塔金乡下,虽然为了爱情在塔金安家,但内心深处始终弥漫着对拉萨的深深的眷念。作品写朗杰多吉刚结婚那阵喜欢喝酒,他的酒量小,用不了多久就会喝醉,然后乘着醉意背诵《忆拉萨》,并边哭边说自己没处说话。犹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所阐明的,孤独是人类存在的本质,隐忍是面对生活的态度,终其一生,朗杰多吉内心隐幽的向往仍然是拉萨,却永远难以走出塔金,回到自己的断脐之地。作品写朗杰多吉固执地保持着拉萨人的身份特征,永远一口优雅的拉萨口音成为他的标志。为了让女儿白玛措吉也说得一口好听的拉萨话,“他宁愿毁掉慈父形象,爱唠叨、爱发怒。和小伙伴在一起,白玛措吉觉得用塔金话更自在,回到家里,照顾到父亲感受,语言系统切换到拉萨频道,但总会不小心冒出一两句塔金土话,遭到怒目而视或者一声呵斥是常事。那时的她常常纳闷,身在塔金,为什么非要说拉萨话?”[12]其实这里面寄托着朗杰多吉无奈的憧憬,他已不能返回故乡,而唯一能做的,是期望他的返城愿望能在女儿这里实现。他叮嘱女儿一定要学习好表现好,想方设法去拉萨,千万不要回塔金。然而,白玛措吉大学毕业时由于就业政策,不得已只能回到塔金。白玛措吉原本对于留不留在拉萨没有太多的执念,但塔金县城的破落与人际关系的逼仄使她倍感压抑。更重要的是塔金的人固守着传统观念,因为随便一句“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白玛措吉就受到各种风言风语。而在日常工作中,但凡想锐意而为,做出一点小小的变动,都会引起很多阻挠和质疑。身陷塔金,白玛措吉感受到的是困顿和不被理解的孤独。 尼玛潘多的创作糅合着真实的生命体验,显现着她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和对现代化进程中西藏城乡生活的深度思考。西藏和内地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紫青稞》中,她写出了乡村儿女走向城市的艰难,作品通过桑吉之口道出:“城市再大,也没有一处墙根会让你歇息;城市再富,也没有一碗清茶供你解渴;城市再美,也没有一样美丽为你存在”。[13]而《在高原》不仅书写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还写出了普通城镇和大城市的差距。对于塔玛乡的人来说,塔金是个难以跻身的城市,所以当朗杰多吉被调到县城广播站时,梅朵曲珍感受到了横亘在两人间的巨大鸿沟。但对于从拉萨来到塔金的朗杰多吉来说,塔金偏僻落后,是他在内心一直想要离开的地方。朗杰多吉的女儿白玛措吉从小就由父亲灌输走出小县城的梦想,在内地大城市接受大学教育,按父亲的愿望是毕业要去拉萨,但现实是她不得不回到塔金。白玛措吉在小县城的受困及她后来到拉萨之后的精神郁结,一方面呈现了小县城的保守与按部就班,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年轻一代的精神追求与困惑。在两代人的精神追求中,拉萨与塔金之间该如何选择成为朗杰多吉和白玛措吉心中横亘的问题,最终走出塔金去往拉萨成为他们共同的愿望。失去的永远在追忆,在翻腾的人生之海中,朗杰多吉因为时代原因,不得不留在塔金,于是永远做着走出塔金的梦。而白玛措吉承载着父辈的期望,最终走出塔金,来到拉萨,但内心深处却始终弥漫着难以融入的疏离之感。 尼玛潘多在谈到其长篇小说《紫青稞》时说:“我只是想讲一个故事,一个普通藏族人家的故事,一个和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生活、生存问题的故事。”[14]《在高原》同样展现了尼玛潘多对普通世俗人生和个体精神的关怀。朗杰多吉的个体困境在于时代浪潮裹挟下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无奈。而白玛措吉的困境在于生命之庸常,在于青春激情的理想和现实的格格不入。作品对白玛措吉的个体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大学时,她暗恋嘎玛丹增,却告白未果;在塔金工作后,喜欢上下乡的音乐老师,互生情愫,但音乐老师最终离开塔金;与青梅竹马的多扎相处日久后产生好感而结合,但由于思想观念不同,最后感情破裂;多年后她被初恋情人嘎玛丹增调到拉萨工作,本以为可以再续前缘,却得知嘎玛丹增已有妻子。 两代人的人生之路是不同的,然而又都有着难以逾越的生命困境,由此传达着作家对于人生中诸多哲学命题的态度与思考。在凡俗的尘世,如何摆脱生命的困境,寻觅安顿灵魂之地,显然是尼玛潘多创作的一个着力点。虽然尼玛潘多写苦难,但她的作品背后往往渗透着一种生命的阔达和韧性。在作品的开头,面对难熬的塔金的风季,梅朵曲珍坦然若素,她说,“春天的风,是塔金的产前痛,塔金将生下一个美丽的夏天”。[15]这传达着一种豁达的人生观,并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作者试图用高远深厚的人性关怀去化解生命的苦难,从而实现灵魂的救赎和精神的安顿。作品中的梅朵曲珍心地善良、敢爱敢恨、热情豁达,她纯洁真挚的爱让朗杰多吉在苦难岁月中感受到温情。作品中的多扎宽厚老实、心地善良,他对生活的简单追求以及对学生的真切关怀使得他在素朴的生活中显现出人性的光辉。盛产风雪的塔金是寒冷的,但因为有人性的光芒,寒风也能化作细雨,从此高地不再寒冷。尼玛潘多用朴拙的文笔呈现了她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普通人生存境地的关注,渗透在文字中的对个体生命的理解之同情及对人性之光的探寻,使人感受到了值得珍重的人间温情。 从创作伊始尼玛潘多就显现出了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抱负:“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让人们在神秘之外,看到一处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16]她的作品探查被宏阔的历史书写忽略的普通小人物的悲欢和追求,关注时代变动中个体的灵魂境遇,将一个个没入历史尘烟中的人物生动地呈现出来,从而展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西藏。学者阎浩岗在论及次仁罗布的创作时指出:“作家写出的作品既是个人思想情感的结晶,又不可避免地处于文本的互文网络之中。按布鲁姆的说法,后起作家均面临‘影响的焦虑’,他们都试图与前面的作家对话,写出不一样的东西。”[17]他认为扎西达娃、阿来和次仁罗布,分别代表了藏地书写的三种不同类型,即造魅、祛魅和既不有意造魅又不致力祛魅。作为一名“70后”的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小说创作始于21世纪初期,面对已有的文学经验,尼玛潘多既有承继,又有新的审美判断和追求,她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西藏,也就是一个充满烟火世俗意味的真实的西藏。比之阿来以如椽之笔呈现他对川西藏地的祛魅书写,尼玛潘多则以女性的细腻和深入历史的洞察力呈现了鲜活的西藏,拓展了西藏的文学书写领域。她深入描摹西藏城乡社会生活,关注大的时代动向,又以女性的细腻、柔韧展现着对脚下土地的思考,传达着对逝去时光的追问和对个体精神困境的关怀。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紫青稞》书写改革开放的浪潮在西藏农村引起的变化,通过乡村儿女的奋斗之路展现了西藏现代化的进程,传达出对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风貌。“对个体与民族国家精神血脉的探寻与书写,以及对照亮历史的人性之光的探寻,无疑是中国‘70后’作家寻找自我历史根脉、确立自我审美历史根基、书写‘当代中国故事’所蕴含的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更显示出这一代作家审美既具地域化特征又走向历史化、民族化的文化自觉意识。”[18]新作《在高原》的视野则更为开阔,兼顾乡村、县镇和城市三种地理空间,并将藏地和汉地、现在和过去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普通小人物的命运遭际映现了西藏近百年的历史,在家族叙事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图景,展现了新时代西藏书写的文化自觉,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内涵、民间意蕴和人性光芒,彰显了新时代西藏作家中国书写的独特面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藏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究”(20AW02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刘峥、尼玛潘多:《紫青稞是一种精神》,《西藏商报》2010年3月13日。 [2]谢有顺:《小说是活着的历史》,《小说评论》2012年第2期。 [3]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09页。 [4]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 [5]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页。 [6]食指:《相信未来:食指诗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7]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54页。 [8]尼玛潘多:《创作谈》,《民族文学》2022年第8期。 [9]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10页。 [10]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24页。 [11]赵丽:《为沉默的农村女性发声——尼玛潘多访谈录》,王军君主编,《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6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2页。 [12]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版,第7-8页。 [13]尼玛潘多:《紫青稞》,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14]刘峥:《尼玛潘多:紫青稞是一种精神》,《西藏商报》2010年3月13日。 [15]尼玛潘多:《在高原》,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16]尼玛潘多:《用文字构建一个新世界》,王军君主编,《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17]阎浩岗:《综合与超越的艺术追求——次仁罗布〈祭语风中〉读解》,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页。 [18]张丽军:《当代中国故事的书写与审美主体的确立——中国“70后”作家长篇小说新论》,《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学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等。主持 “当代藏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尼玛潘多,女, 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日报高级记者, 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第二十八届高研(深造)班学员。作品散见于《长篇小说选刊》《中国作家》《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民族文学》《青年文学》《西藏文学》等刊物。出版有长篇小说《在高原》《紫青稞》,中短篇小说集《透进病房的阳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文、哈萨克文等;荣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六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民族文学2012年度小说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