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美多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人,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少语系藏语言文学专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青海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作品收入《新中国建立60周年青海文学作品选·藏文卷》《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藏族卷)》等多部文集和大中学校藏语文教材教辅。出版有诗歌集《一个步行者的梦语》(藏汉双语)和散文集《极地的雪》(藏文)、《久美多杰散文集》(汉文)以及翻译作品集多部。曾获青海章恰尔文学奖·新人新作奖、青海藏语文学野牦牛奖·翻译奖、甘肃达赛尔文学奖·散文奖、青海省第七届文学艺术奖及天津孙犁散文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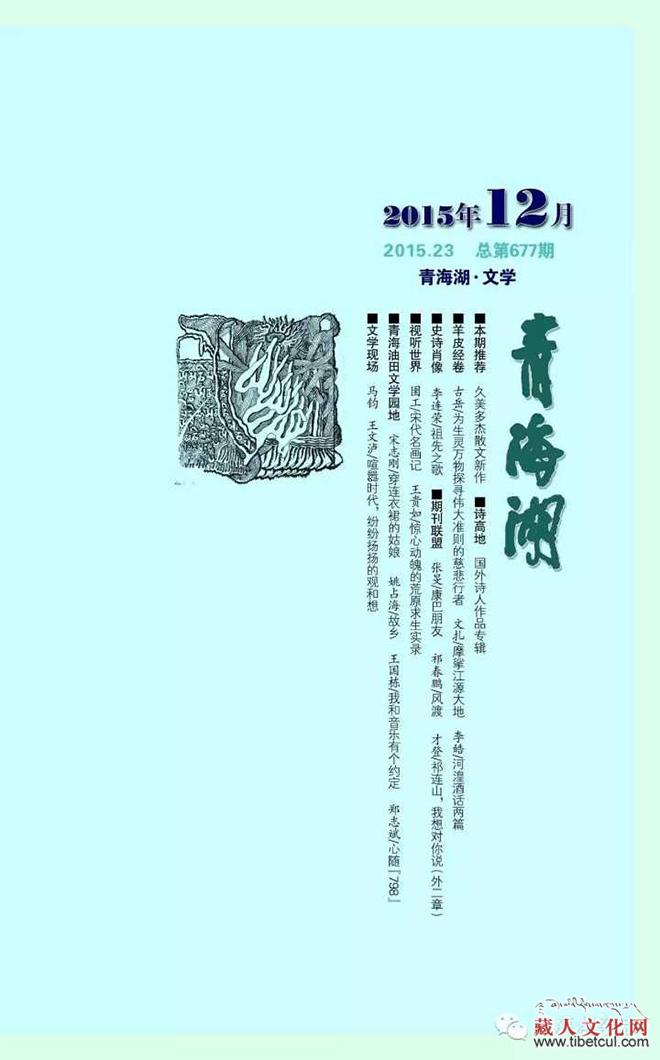
我不是从小喜欢写作的那种人,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只不过是一个在九月份踏进校园的人。因此,总认为秋天是我离开家的季节。尽管小学在本村,中学在县城,离家其实不远,但是九月无法改变地成为我在异乡思念故土和亲人的时间。
每年的九月,故乡满怀收获的喜悦,我在自己的远方能听见村人们长长舒气的声音。
那年九月,我刚进大学校门。一名学长很认真地对我说:通过我的观察,你现在的样子很土,但过不了多久,肯定会变成一个时尚而超前的人。
那年九月,我大四了。同学们半开玩笑地说:看你又瘦又苍白,简直就是一个刚从浙江来的木匠。
那年九月,我来到了石乃亥——青海湖西岸一个牧业乡。在两年多时间里,先后担任乡政府驻村干部、扫盲干事、乡机关藏语文教师和乡党委秘书。从事文秘工作后发现,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依靠和精神寄托的藏语言文字,居然成了可有可无的知识和工具。由于在日常工作中很少能够使用,平时又没有机会接触所学专业,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藏语文水平在下降,汉语文应用能力却有了一定的提高。在惶惑中,为了不荒废专业,我利用空闲时间坚持母语写作,给《日月山》《青海藏文报》《西藏日报》《青海群众艺术》《岗尖梅朵》《章恰尔》《西藏文艺》等报刊投稿,还经常换笔名,不让自己认识的报刊编辑知道我是谁。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目前的单位,尽管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但有时候被一些领导和同事认为“不务正业”“用外语写作”;我坚持搞文学翻译,一度被很多朋友认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自己却没有任何成果”。后来,我坚持双语写作,也得到过个别领导和不少朋友和读者的认可与鼓励。我的一只脚就这样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我的文字,最初是想让它们伫立在圣湖之畔歌唱,想让它们仰卧在草丛中看云。然而,它们却蹲坐在故乡的山冈和异地的沃野上,胡思乱想,自言自语。我希望散文记录我的脚步,诗歌掩盖我的脆弱,它们却含情脉脉地观望我一直没敢做的那些事情。在纸上乱写时看不见心仪的那个人,心仪的人出现时文字就会离开,它可能希望我像一棵树独自发呆。
我至今仍在为自己熟知母语而感到荣幸,从来没有因为不懂外文而感到羞愧。我的文字,首先是献给母语读者,然后就是关注藏族文学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和不懂本族语文的同胞。
每次写完几句艰涩难懂或过于直白的文字后,我开始思考读者怎样理解的问题。后来发现自己的诗可以写自己,但不能始终只表现自己;自己的散文应该记录别人,但也不可把自己完全排除在外。我还发现当我们把作品吊在气球上放飞,它从此不再是你一个人的。
一个作家,如果认为写作是痛苦的事情。那么,他应该立即放弃,否则就有心理变态的嫌疑——明知是痛苦还自找痛苦,就好比拿刀子戳自己的屁股,这是一种自残行为。我们想得比别人多那么一点,我们甚至比别人多一个信仰,所以我们比别人更清醒或更糊涂一些。但是,我觉得写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只要真诚实在,不求名、不争功、不图利,我的写作过程中就不会有痛苦。
我羡慕那些蓄长发、披白衣的密宗修行者,深山、旷野、密林、村舍……闭关静思,云游四方,以道歌抒发心中的夏天,用夏天享受干净的阳光,让阳光感化众生的心灵。即使把眼睛忘在家里,也能看到比蓝更蓝的天空。我希望自己能写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尊重写作,努力让作品对得起读者。
当创作者数量大增,超过了阅读者的数量,或者说阅读者急剧减少,低于创作者的数量时,就离只有自己读自己作品的时代不远了。一旦,只有作者本人是自己的读者时,我们就轻松、舒服多了——只要在脑子里构思一下就可以,没有必要浪费时间——潜心创作,低头修改,用怀疑的眼光定稿,然后投给报刊,等印出来独自一人从头到尾细读三遍。
假如我学过绘画艺术,假如让我去画画,我会选择美的主题,去描绘丑陋的东西。没有缺陷的美,不必用笔去玷污和践踏。
登到高处呼喊时,文字在身后沉睡;当文字花白的胡须飘动时,还有谁会在现场?没有生活基础和现实经验的文学作品现在越来越多了,我自己也写过不少。聪明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内容是真实的,哪些话语是虚假的。
我认为,当天空被音乐爱抚,白云却一动不动时,她的腹中已经怀上了文字。
艰难的匍匐,只为得到神灵的眷顾。与其这样,不如骑马走游天涯,用雨水和风沙洗涤内心,播撒一些慈爱的种子,智慧女神央金玛肯定会守候在你的枕边。
假如有一天,我们无缘和明天的太阳握手,需要留下的是人品还是文品呢?
当人们记不清把自己的爱给了谁,把反复无常的喜怒哀乐全扔出门外时,我愿提着用散文和诗歌编织的袋子,做一个拾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