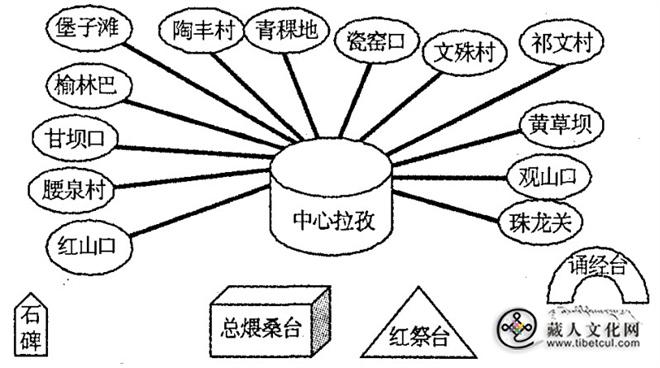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写在张子选最新诗集《人间有我用坏的时光》出版之际
在当代诗歌版图中,张子选以四十年藏地行吟为底色创作的“藏地诗篇”,如同一股来自雪域的清流,既打破了传统地域书写的局限,又为当代诗歌的精神维度拓展了新的空间。他的作品不仅在读者中引发广泛共鸣,更以独特的美学范式、题材选择与精神内核,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多维度的深远影响,成为连接地域文化与普遍人性、传统诗学与现代表达的重要参考文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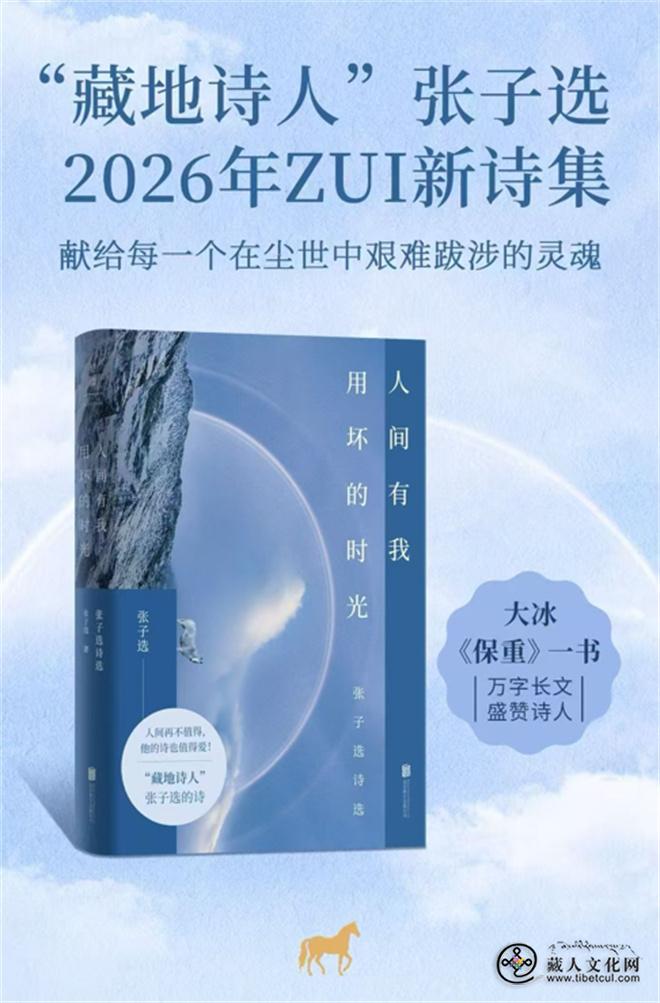
地域书写的革新:解构“藏地神秘”,重建真实的地域诗学
长期以来,藏地在文学创作中常被符号化、神秘化,成为“远方”“神性”的抽象载体。此类书写既偏离了地域的真实面貌,也消解了其文化深度。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则率先打破这一桎梏,以“去神秘化”的自觉,重建了藏地书写的真实维度,为当代地域诗歌创作提供了全新范式。
在其前著《藏地诗篇》序中言及,张子选明确提出“当我们提及西藏时,首先应去神秘化”,这一主张贯穿其创作始终。在《哭》中,他写下“多年来我放牧诵经,睹物思人/而扎西在宴客,卓玛在摇铃/正当青海湖抱住青海/西藏抱住喜马拉雅/我手掌上正驰过一头秋天的/丧失一切的精壮牡鹿”,诗中没有刻意渲染的神性光环,而是将藏地的自然景观(青海湖、喜马拉雅)与普通人的日常(宴客、摇铃)、个体的情感(睹物思人)融为一体。这种书写让藏地摆脱了“异域奇观”的标签,回归为“可感的生活场域”——既有天地的壮阔,也有人间的烟火;既有信仰的庄重,也有生命的脆弱。正如诗评家阿苏越尔在《一百辆汽车,也比不上一匹马》中评价的,张子选的藏地书写“是崭新层级的‘看山是山’,消除了预设的神秘,藏地才袒露出无比鲜活的力量”。
这种“去神秘化”的地域书写,对当代诗歌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为其他地域题材的创作者提供了启示——地域书写不应停留在表面的意象堆砌(如草原、雪山、经幡的简单叠加),而应深入地域的文化肌理与生活细节,挖掘其中的人性共通性。例如,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的诗歌创作中,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借鉴这种“日常化地域书写”,将牧场劳作、市集喧闹、家庭琐碎融入诗中,让地域特色与生命体验自然交融;另一方面,它矫正了读者对“远方”的浪漫化想象,推动当代诗歌从“猎奇式书写”转向“沉浸式体验”,使地域不再是诗人宣泄个人情怀的工具,而是与诗人平等对话的“精神伙伴”。
此外,张子选对藏地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意象体系。他笔下的 “腰”意象便是典型代表——在《春天记事》中,“春好酷似小蛮腰/鲜花的腰,青草的腰/甚至于一脉粼粼逝水之腰”,将“腰”赋予自然景物,既展现了藏地春天的柔美律动,又暗合藏族文化中“腰”通过腰带、腰裙象征身份与情感的文化内涵。此种将地域文化符号与自然、情感相融合的手法,让传统意象获得了现代生命力,也为当代诗人如何“活化地域文化”提供了范例——不再是生硬地植入文化名词,而是让文化基因自然融入诗意表达。
自然书写的突破:从“风景投射”到“生命共生”
当代诗歌的自然书写常面临两种困境:要么陷入“纯客观描摹”的刻板,要么沦为“自我情感投射”的附庸,难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精神对话。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则以“生命共生”的视角,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当代自然书写开辟了新路径。
在他的诗中,自然不是被动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类平等的“生命主体”——鹰、马、羊、草、雪山,都拥有自己的意志与情感,与人共同构成藏地的生命网络。《若尔盖湿地》中,“路朝北走,水往南聚/而偌大的天空/喜欢沉浸于花湖,潋滟地裸泳/上午,束苇溯溪/下午,游禽打鱼/偶见有鹰悬停,执着于迎风送云”,这里的天空、束苇、游禽、鹰,都不是静态的景物,而是充满“生命律动”的存在:天空“裸泳”显其自在,鹰“执着”见其性情。诗人没有将自己的情感强加于自然,而是以“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记录人与自然的“互动瞬间”——正如《苍天在上》中,安多红马“忽闪着一双长睫美目/与人类之一,面面相觑”,如此这般跨越物种的对视,消解了人与自然的界限,展现出“物我两忘”的高古境界。
此种“生命共生”的自然观,无疑对当代诗歌的自然书写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它推动诗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不再将自然视为“人类情感的载体”,而是尊重自然的“自主性”。例如,王家新在《在西昌邛海湖畔听到鸟鸣》中,将鸟鸣视为“比诗歌研讨会更重要的存在”,黑陶在《请求朝霞》中“用第一缕火温暖逝去的父亲,用第一道光唤醒沉睡的家乡”,类似诗句都能看到张子选“自然有灵”观念的影子——自然不再是“被歌颂的对象”,而是“参与人类生命的伙伴”;另一方面,它为自然书写提供了“细节化”的表达路径。张子选善于捕捉自然中微小的“生命细节”:《年楚河上游》中“小马探足蹚水,行至今生”,《无人区》中“一只红尾沙蜥,仍在坚持自己/业已承传六千五百万年的/涉险与进化”,这些细节让自然不再是抽象的“宏大概念”,而是可触可感的“生命个体”。类似写法影响了后续诗人对自然的观察方式——从关注“壮阔景观”转向捕捉“微观生命”,让自然书写更具温度与真实感。
值得注意的是,张子选的自然书写始终蕴含着“悲悯情怀”。《藏北入冬帖》中,“少数未被及早劝归山穴/乖乖蜷身冬眠的大小棕熊/如若踏冰寻鱼不得,或将登门造访/那曲县油恰乡嘎登寺/意在觅食,捎带听经”,诗人没有将棕熊的困境浪漫化,而是以平实的笔触写出生命的挣扎,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生灵的理解与心疼。这类“悲悯式自然书写”,矫正了当代诗歌中“猎奇式自然描写”的弊端,让自然书写不再是“炫耀对自然的占有”,而是“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且已成为当代自然诗歌的重要精神特质之一。
情感与哲思的融合:为当代诗歌注入“轻而不浮”的精神质地
当代诗歌的情感书写常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过于“私人化”而晦涩难懂,要么过于“大众化”而流于浅白;哲思表达则常因“概念化”而显得生硬。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则以“轻而不浮”的笔触,实现了情感与哲思的完美融合,为当代诗歌的精神传达提供了平衡范式。
他的情感书写兼具“私人温度”与“公共共鸣”。《在人间》中,“你承诺过的月亮/还是没有出现/而我无眠,或者/我只是衣单天寒地/替你多爱了一夜人间”,诗句源于个人的情感失落(“月亮未出现”),却没有局限于私人的哀怨,而是将失落升华为对人间的 “额外温柔”——“替你多爱一夜人间”,这一情感的升华,让个人体验转化为普遍的人性善意,每个经历过遗憾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共鸣。又如《供花・说渡》中,童僧递来的白月季“天上人间,竟真没个人堪寄/就将它供于佛前如何”,个人的孤独与对信仰的敬畏交织,情感既细腻又开阔,避免了私人情感的狭隘。此种“从私人到公共”的情感转化,为当代诗人如何“处理私人情感”提供了启示——私人情感不应是封闭的“内心独白”,而应是连接他人的“精神纽带”,通过对私人体验的提炼,抵达人类共通的情感内核。
在哲思表达上,张子选摒弃了“说教式”的议论,而是将哲思融入“场景与细节”之中,实现了“哲思的诗化”。《悯生帖》中,“虫草下山/大鱼登岸/绕道秋天/与君一见/筷子共碗/相顾无言/眼含人间/泪流满面”,没有一句直接谈论“生命意义”,却通过虫草、大鱼的相遇、筷子共碗的沉默,道出了生命中“相遇的珍贵”与“无言的悲悯”,哲思如流水般自然融入诗意,不留痕迹。又如《与时间有关》中,“几匹黄叶满地霜。爱人,是你吗?心似寒秋独自凉。佛啊,你在吗?”将对爱人的思念与对信仰的叩问并置,在孤独的场景中暗含对“生命存在”的思考,这种“以场景代哲思”的写法,避免了当代诗歌哲思表达的“概念化”弊端,让哲思既有深度,又有温度。
此类“情感与哲思融合”的特质,为当代诗歌注入了独特的“精神质地”——轻而不浮,深而不重。正如有文章评价其诗歌“轻盈、瑰丽,极富韵律美,意境苍茫深远;悲悯中蕴藏深情,荒凉中透着微光”。这一质地既区别于朦胧诗的“沉重哲思”,也不同于口语诗的“轻浅直白”,为当代诗歌提供了“平衡的精神选项”。许多年轻诗人开始借鉴这种“轻哲思”的写法,如在处理“时光流逝”“生命孤独”等主题时,不再依赖抽象议论,而是通过自然场景、日常细节传递哲思,以期能让诗歌既“好读”又“耐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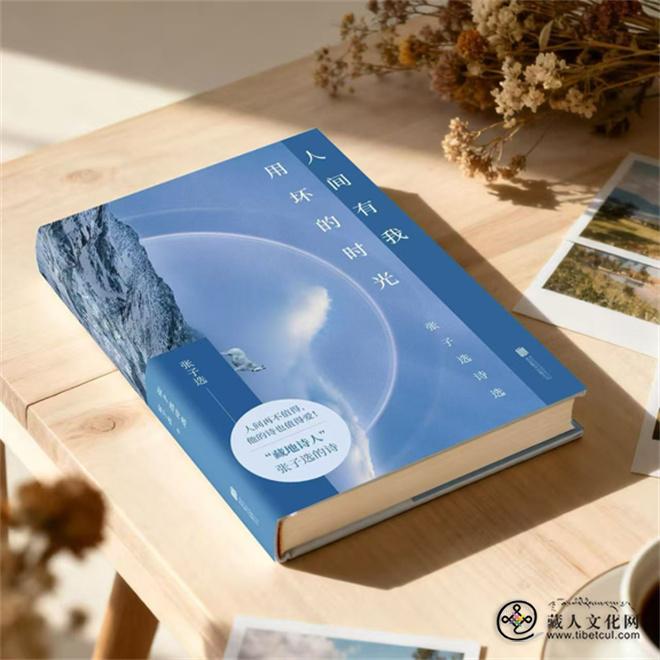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激活古典诗学,丰富当代诗歌语言
作为深谙古典文学的诗人,张子选善于从中国古典诗学中汲取养分,并将其与现代语言、藏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对话”的独特语言风格,从而为当代诗歌的语言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对古典诗学的借鉴,首先体现在“意象的传承与转化”上。《请月照人》中,“近来什么事情都能令我伤心/光是看见弦月东升/就感觉有什么在心底下沉/并发出很大的扑通一声”,“月亮”是古典诗歌中“思乡、怀人”的经典意象,张子选却赋予其现代情感——月亮不再是“引发乡愁的符号”,而是触发个体“内心震动”的媒介,古典意象与现代情感的结合,让“月亮”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又如《六滴雨》中,“第三滴雨,随风入井/像藏刀归鞘,闺女入梦”,“雨入井”的意象脱胎于古典诗歌的“雨打芭蕉”“雨入寒窗”,但诗人以“藏刀归鞘”“闺女入梦”的现代比喻,让古典意象焕发出藏地特色与现代气息,实现了“古典意象的在地化与现代化”。
其次,在语言形式上,他融合了古典诗词的“韵律美”与现代诗歌的“自由性”。他的“藏地诗篇”多采用短句,节奏明快,却暗含古典诗词的“平仄与对仗”——《甘南骑行》中“骑马向南,不时北看/好久没见,有点想念/生灵盈野,菩萨投闲/桥之彼端,新雪下山”,前两句“向南”与“北看”、“没见”与“想念”形成隐性对仗,后两句“生灵盈野”与“菩萨投闲”、“桥之彼端”与“新雪下山”句式对称,读来朗朗上口,兼具古典诗词的韵律与现代诗歌的灵动。此种“韵律自由”的语言风格,矫正了当代诗歌要么“过于追求格律而僵化”、要么“完全放弃韵律而散乱”的弊端,为当代诗歌语言提供了“兼顾韵律与自由”的范例。
此外,他对“民间语言”的吸收,也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语言生态。张子选善于从西北与藏地民间歌谣、日常对话中提炼诗意,如《大意如此》中“妹妹生得好/落花的身材流水的腰/妹妹长得妙/裁两声鸟叫做胸罩”,语言直白鲜活,带有民间歌谣的“俏皮与质朴”;《他们说》中“他们说,藏区旅游,你不能随便踹狗/你所嫌弃的狗,没准是你前世的舅舅”,则直接引用民间俗语,让诗歌充满生活气息。诸如此类“民间语言的诗化”,打破了当代诗歌“精英化”的语言壁垒,让诗歌更贴近普通读者,也推动更多诗人关注“民间语言中的诗意”,为当代诗歌语言注入了更多“在地性”与“烟火气”。
创作姿态的启示:“行吟者”身份与“真诚写作”的坚守
在当代诗歌“多元化”却也“碎片化”的语境中,张子选四十年如一日的“藏地行吟” 与“真诚写作”,为当代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姿态启示——诗歌不应是“书房里的文字游戏”,而应是“生命与土地的对话”;诗人不应是“闭门造车的精英”,而应是“扎根生活的行者”。
他的“行吟者”身份,不仅是地理上的“行走”,更是精神上的“扎根”。从1983年在甘肃阿克塞县中学任教,到此后四十年游走于藏区各地,张子选的诗歌不是“想象中的藏地”,而是“亲历的生命体验”——《病中,记起最后的驮盐队伍远去》中,他记录下“最后一支驮盐队伍的最后一次远行”,既是对藏地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也是对“消失的生命场景”的珍视;《转场途中,报友人书》中,“跟着罗布一行人吆牛赶羊,搬家转场/春天下过的大雪,到了冬天,为把/山地沟谷重新填满,照例又得猛下几番”,细腻的转场细节,若非亲历者,绝难写出。这种“扎根生活的写作”,让他的诗歌拥有了“不可复制的真实性”,也提醒当代诗人:真正的诗歌创作,需要“深入生活的勇气”与“长期观察的耐心”,而非“凭空想象的灵感”。
更重要的是,他的“真诚写作”坚守,在“诗歌娱乐化”“语言游戏化”的当代语境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张子选的“藏地诗篇”从不追求“晦涩的技巧”或“标新立异的观念”,而是以“平实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情感与思考”——《抱歉帖》中,“抱歉,这路走着走着,便渐入了秋天/抱歉,这马骑着骑着,就错过了永远”,语言简单直白,却道尽了人生的怅憾与无奈;《也好》中,“雪仍在山顶真好/水还在湖面真好/大地上的一石一鸟/似乎都还未曾被放乱/草绿今世真好/花忆前身真好”,没有复杂的意象,却以“真好”的复沓咏叹,表达出对生活的珍惜与热爱。这种“真诚”,让他的诗歌跨越了地域、年龄、文化的界限,被柳岩、大鹏、刘欢等演员朗诵,在B站、“为你读诗”等平台广泛传播,成为“大众与诗歌对话的桥梁”。
张子选的“藏地诗篇”之所以能引发普遍共鸣,核心便在于“真诚”——对藏地的真诚热爱,对生命的真诚尊重,对情感的真诚表达。此种“真诚写作”的姿态,也影响了一批年轻诗人。他们开始摒弃“为技巧而技巧”的创作误区,转向“以情感为核心”的真实表达,关注身边的小事、普通人的命运、生活的细节,让诗歌重新成为“连接人与人”的精神纽带。
从地域书写到精神重构:作为“精神坐标”的“藏地诗篇”写作
张子选的“藏地诗篇”对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地域书写”的范畴,成为一个“多维度的精神坐标”:在地域书写上,他解构了神秘化的地域想象,重建了真实的地域诗学;在自然书写上,他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生”,突破了传统自然描写的局限;在情感与哲思上,他融合了私人体验与公共共鸣,注入了“轻而不浮”的精神质地;在语言上,他激活了古典诗学,吸收了民间语言,丰富了当代诗歌的表达;在创作姿态上,他以“行吟者”的身份与“真诚写作”的坚守,为当代诗人提供了重要示范。
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张子选的“藏地诗篇”不仅是“藏地的深情告白”,更是“对人间的温柔慰藉”。他让当代诗歌看到:地域可以是“真实的生活场域”,自然可以是“平等的生命伙伴”,情感可以是“连接他人的纽带”,语言可以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写作可以是“生命与土地的共鸣”。正如大冰在推荐语中所说:“人间再不值得,他的诗也值得爱!”
综上所述,张子选“藏地诗篇”从地域书写到精神重构形成的影响,或许不会立刻改变当代诗歌的整体格局,却会如藏地的雪水般,慢慢渗透到当代诗歌的肌理之中,滋养出更具温度、更有深度、更贴近生命本质的诗歌作品。
张子选,诗人、编剧。著有《执命向西》《藏地诗篇》等诗文集。中央电视台《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第三季、《中国成语大会》第二季首席编剧,腾讯视频、黑龙江卫视《见字如面》第一至第五季总编剧。独立电影长片《老虎的斑纹》主演之一。其最新诗集《人间有我用坏的时光》,于2026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