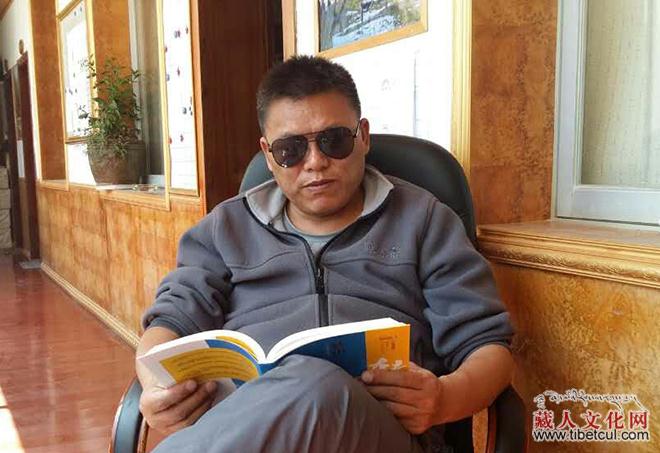
و‰ژè¥؟ه°¼çژ›ï¼Œ1970ه¹´ن»£ه‡؛ç”ںن؛ژè—ڈن¸œ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ن¸‹ï¼Œوœ‰è¯—وŒه’Œو•£و–‡ن½œه“پهڈ‘è،¨ï¼Œو‹چو‘„ç؛ھه½•ç‰‡ï¼Œه’Œوœ‹هڈ‹هˆ›هٹهڈŒè¯و°‘هˆٹم€ٹه›ه½’م€‹و‚ه؟—م€‚
ç”ںه‘½é‡Œçڑ„é›ھه±±
——è—ڈهژ†وœ¨ç¾ٹه¹´è½¬ه±±و‰‹è®°
2015ه¹´10وœˆن¸و—¬ï¼Œوœو‹œé›ھه±±çڑ„è„ڑو¥ه¼€ه§‹هگ¯ç¨‹م€‚ه‡؛هڈ‘ن¹‹ه‰چ,ه¤©ç©؛و±‡èپڑèµ·هژڑهژڑçڑ„ن؛‘ه±‚,ه¤œé‡Œهگ¬هˆ°é›¨و°´و³¼و´’ن¸‹و¥çڑ„ه£°ه“چ,وˆ‘هœ¨ه؟ƒé‡Œوڑ—ه–œï¼Œè؟™ن¸چوک¯ه¤©é™چç”ک霖ن¹ˆï¼پهگ‰ç¥¥ه•ٹï¼په¤©ن؛®èµ·ه؛ٹ,ن½†è§پ雨éœپن؛‘و•£م€‚è؟™هœ°و–¹هˆڑه¥½ه¤¹هœ¨ه±±è„ڑ,看ن¸چهˆ°ه±±é،¶ï¼Œو²،و³•çœ‹هˆ°هچ،瓦و ¼هچڑ群ه³°ï¼Œوˆ‘ن¾؟هڈŒو‰‹هگˆهچپوœç€é›ھه±±و–¹هگ‘祈祷ï¼ڑ
هگ‘ن¸ٹه¸ˆé،¶ç¤¼ï¼پ
هœ¨è™¹ه…‰ن؛¤وژ¥çڑ„هœ°ç•Œï¼Œ
هچ—و–¹ه¯ں瓦绒و²³è°·ï¼Œ
و–¹ن¾؟ه’Œو™؛و…§çڑ„و•™و³•ن¹‹ه؛§ن¸ٹ,
雄è¸ç»’èµهچ،瓦و ¼هچڑم€‚
ه±±ن½“ه¦‚ç«–ç«‹çڑ„é•؟çں›ï¼Œ
ه±±ه°–ن¼¼ç™½è‰²çڑ„ه¤ڑçژ›ï¼ˆé¢هˆ¶ن¾›ه“پ),
色ه½©ه¦‚ه¼ وŒ‚çڑ„白绸م€‚
وˆ‘هگ‘ن½ 祈祷,请و‚²و‚¯ï¼پ
……
وˆ‘çڑ„ه®¶ه°±هœ¨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ن¸‹
ه½“هˆ«ن؛؛问起,و‰ژè¥؟,ن½ ه®¶هœ¨ه“ھ里ï¼ںوˆ‘ن¼ڑو¯«ن¸چçٹ¹è±«هœ°ه‘ٹ诉ن»–,وˆ‘çڑ„ه®¶ه°±هœ¨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ن¸‹م€‚وˆ‘و‰€è¯´çڑ„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ه°±وک¯çژ°هœ¨هœ°ه›¾ه’Œن¹¦ç±چن¸و‰€وŒ‡çڑ„و¢…里é›ھه±±ï¼Œن»–و¨ھن؛کن؛ژو€’ه±±ه±±è„‰ن¸و®µï¼Œوک¯ن¸€ç»„ه³°ç¾¤م€‚ه…¶ه®و¢…里é›ھه±±وک¯هœ°هگچ误用,هœ¨هچ،瓦و ¼هچڑه±±ç³»ن¸ï¼Œç،®وœ‰ن¸€ه؛§ç§°ن½œ“و¢…里”çڑ„ه±±ï¼ˆن½†ن¸چوک¯ه±±ه³°ï¼‰ï¼Œو„ڈو€ن¸؛“èچ¯ه±±”,ه› ه±±ن¸ٹç››ن؛§ه†¬è™«ه¤ڈèچ‰م€پè´و¯چم€پèƒ،黄è؟ç‰هگچè´µé«که±±èچ¯وگ而ه¾—هگچم€‚ه°†هچ،瓦و ¼هچڑ误称ن¸؛و¢…里é›ھه±±ه§‹ن؛ژ解و”¾هˆوœںç»کهˆ¶çڑ„هœ°ه›¾م€‚1986ه¹´ن¸و—¥èپ”هگˆç™»ه±±éکںو²؟用و¤é”™è¯¯هœ°هگچ,ن»¥è‡³ç”±ن؛ژ1991ه¹´ه±±éڑ¾ن؛‹ن»¶é€ وˆگçڑ„ه¼؛ه¤§ه½±ه“چ,و¢…里é›ھه±±ن»£و›؟ن؛†هچ،瓦و ¼هچڑم€‚هچ،瓦و ¼هچڑهœ¨è—ڈè¯è¯ه¢ƒé‡Œçڑ„و„ڈو€وک¯“و²³è°·هœ°ه¸¦çڑ„白色é›ھه±±”م€‚ن»–وœ‰ن¸¤ن¸ھهگچ称ï¼ڑç»’èµهچ،瓦و ¼هچڑه’Œن¹ƒé’¦هچ،瓦و ¼هچڑم€‚ه‰چ者وک¯è‹¯و•™و—¶وœںçڑ„هگچ称,èµوک¯هڈ¤è€پçڑ„ç¥çپµï¼ŒوŒ‡ç…ç¥ï¼Œç…ç¥وœ‰ه…«ç§چ,ن¹ں说وœ‰هچپن¸€ç§چن¹‹ه¤ڑ,ه…·وœ‰ç›¸ه½“ه‡¶çŒ›çڑ„هٹ›é‡ڈم€‚هچ،瓦و ¼هچڑه°±وک¯هœ¨è—ڈهœ°èµ«èµ«وœ‰هگچçڑ„èµç¥é›ھه±±م€‚ن¹ƒé’¦هچ،瓦و ¼هچڑ,هچ³ه¤§هœ£هœ°هچ،瓦و ¼هچڑم€‚ن½›و•™ن¼ ه…¥è—ڈهœ°ن¹‹هگژ,ه¯¹è‹¯و•™è؟›è،Œن؛†ن؟ç•™و€§و”¹é€ ,هژںو¥ن¸€ن؛›è‘—هگچçڑ„ç¥ه±±ç»ڈè؟‡ن½›و•™هٹ وŒپن¹‹هگژوˆگن¸؛ن½›و•™çڑ„éپ“هœ؛,هƒڈهچ،瓦و ¼هچڑه°±وˆگن¸؛è—ڈن¼ ن½›و•™è‘—هگچوœ¬ه°ٹ(è—ڈن¼ ن½›و•™ه¯†ه®—ن؟®è،Œè؟‡ç¨‹ن¸è§‚ن؟®çڑ„ن½›ï¼‰ن¹‹ن¸€èƒœن¹گ金هˆڑçڑ„هˆ¹هœں,é‡چè¦پçڑ„ن؟®è،Œهœ£هœ°م€‚
وˆ‘وœ‰و—¶ه€™ن¹ںن¼ڑه‘ٹ诉و¥ن؛؛,è؟™ه؛§é›ھه±±وک¯وˆ‘çڑ„ه‘½و ¹هگé›ھه±±ï¼Œوˆ‘وک¯ن»–çڑ„ه‘½و ¹هگه„؟هگم€‚è؟™هڈ¥è¯ن¸ژه…¶è¯´هگ‘ن»–说وکژوˆ‘ه’Œ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ن¹‹é—´çڑ„ه…³ç³»ï¼Œه…¶ه®وک¯هœ¨ه‘ٹ诉è‡ھه·±ï¼Œ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ن¸چن»…ن»…وک¯وˆ‘ه‡؛ç”ںçڑ„هœ°و–¹ï¼Œو›´وک¯ن»¤è‡ھه·±çڑ„ç”ںه‘½èژ·ه¾—و„ڈن¹‰çڑ„و— ن¸ژن¼¦و¯”çڑ„هœ؛هںںم€‚
é›ھه±±é™©ه³»è€Œه¯’ه†·ï¼Œè¢«è§†ن½œç”ںه‘½çڑ„ç¦پهŒ؛,而هœ¨وˆ‘ن»¬çڑ„ç”ںه‘½é‡Œï¼Œن¸ژé›ھه±±ç»“ç¼ک,ه°¤ه…¶وک¯èƒ½ه¤ںه‡؛ç”ںهœ¨ه¦‚و¤é‡چè¦پçڑ„ç¥ه±±هœ£هœ°ï¼Œوک¯ن¸؛èژ«ه¤§çڑ„ç¦ڈوٹ¥م€‚
هœ¨è—ڈهœ°ï¼Œç¥ه±±ن¹ںوœ‰ه±ç›¸ï¼Œن½چن؛ژو»‡è—ڈن؛¤ç•Œه¤„çڑ„و¾œو²§و±ںه’Œو€’و±ںçڑ„هˆ†و°´ه²و€’ه±±ه±±è„‰ن¸و®µçڑ„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ه°±ه±ç¾ٹم€‚2015ه¹´وک¯è—ڈهژ†وœ¨ç¾ٹه¹´ï¼Œهœ¨م€ٹهچ،瓦و ¼هچڑهœ£هœ°ه؟—م€‹ن¸وڈگهˆ°ï¼Œهœ¨è؟™ه؛§ه±±çڑ„وœ¬ه‘½ه¹´ï¼Œ“ن؛ژهچ°ه؛¦م€پو±‰هœ°م€په°¼و³ٹه°”م€پ里هںں(وŒ‡ن»ٹو–°ç–†ن؛ژç”°م€په’Œç”°ن¸€ه¸¦ï¼‰م€پهŒ—و–¹é¦™ه·´و‹‰ن»¥هڈٹه†ˆه؛•و–¯ه±±ï¼ˆهچ³ه†ˆن»پو³¢é½گ)ن¸؛首و‰€وœ‰ه؛·è—ڈçڑ„ن¸€ç™¾ن؛Œهچپه…«ه¤„ه¤§هœ£هœ°ه’Œن¸€هچƒé›¶ن؛Œهچپن؛Œه¤„ه°ڈهœ£هœ°çڑ„ه®ˆوٹ¤ç¥و‚‰çڑ†ن؛ژè؟™ن¸€ه¹´ه†…é™چن¸´ن؛ژهچ،瓦و ¼هچڑهœ£هœ°ه†…而ه®‰ن½ڈم€‚ن¸؛و¤ن؛؛ن»¬éƒ½هپڑ礼و‹œم€په·،礼ه’Œو•¬ن؟،,ن¸¾è،Œن¼ڑن¾›م€پ点燃ن¾›çپ¯م€پç«–وڈ’é‡ٹè؟¦ç‰ںه°¼و——ه¹،ه’Œن؟®و¶و،¥و¢پ,致و•¬و„ڈن¾›ه…»ه’Œن؟®ن¹ م€‚و€»ن¹‹ï¼Œهڈھè¦پن؟®è،Œï¼Œه‡€ه–„çٹ¹ه¦‚هڈکوˆگهچپن¸‡م€‚”هچ،瓦و ¼هچڑوک¯è—ڈهœ°è‘—هگچçڑ„ه¤§ç¥ه±±م€په¤§هœ£هœ°ï¼Œه…·وœ‰و®ٹ胜çڑ„هٹ وŒپهٹ›ï¼Œèƒ½ن½؟ن؛؛هœ¨è½®ه›ن¹‹ن¸ç¦»è‹¦ه¾—ن¹گ,ه› و¤وœو‹œهچ،瓦و ¼هچڑé›ھه±±وک¯è—ڈو°‘至ه…³é‡چè¦پçڑ„ه؟ƒو„؟ن¹‹ن¸€ï¼Œه°¤ه…¶هœ¨ç¾ٹه¹´وœو‹œهچ،瓦و ¼هچڑ,و›´وک¯ن¸€ن»¶و— و¯”èچ£ه¹¸çڑ„ن؛‹وƒ…م€‚وˆ‘ن¹ںهڈ‘و„؟هœ¨وœ¨ç¾ٹه¹´وœو‹œهچ،瓦و ¼هچڑم€‚
ن»ٹه¹´ï¼Œه› ن¸؛ن¹ںوœ‰ه…¬هٹ،ن¹‹éœ€ï¼Œوˆ‘هœ¨وœو‹œé›ھه±±هœ£هœ°çڑ„هگŒو—¶ï¼Œè؟کهœ¨هچ•ن½چçڑ„组织ن¸‹ï¼Œن¸ژهگŒن؛‹ن»¬ه¼€ه±•è½¬ه±±è·¯ن¸ٹçڑ„çژ¯ه¢ƒو¸…و´پو´»هٹ¨م€‚ç”±ن؛ژè—ڈهŒ؛ه…¬è·¯ن؛¤é€ڑه’Œç»ڈوµژو،ن»¶çڑ„و”¹ه–„,ن»ژهگ„هœ°ه‰چو¥وœو‹œهچ،瓦و ¼هچڑçڑ„香ه®¢ن¸ژه¾€ه¹´ç›¸و¯”وˆگه€چه¢ه¤ڑ,و²؟途都وœ‰ن؛؛ه¼€è®¾é£ںه®؟点ه’Œه°ڈهچ–é“؛,由و¤ن¹ںه‡؛çژ°ن؛†هƒهœ¾و³›و»¥çڑ„é—®é¢کم€‚
ن¸€و”¯é”™è؟‡ن؛†“هڈ–é’¥هŒ™”هڈˆه؟½ç•¥ن؛†وœو‹œهœ£è؟¹çڑ„转ه±±éکںن¼چ
è؟‡ن؛†و¾œو²§و±ںن¸ٹçڑ„éک³وœو،¥ï¼ˆè€پو،¥وک¯ه؛§é“پç´¢و،¥ï¼Œçژ°هœ¨ن؟®ن؛†و–°و،¥ï¼Œو‰€وœ‰çڑ„转ه±±è€…都è¦پهœ¨و¤è؟‡و±ں,走ن¸ٹ转ه±±çڑ„ه°ڈ路),转ه±±çڑ„éکںن¼چه¼€ه§‹ن¸ٹه±±م€‚وŒ‰ç…§è½¬ه±±çڑ„ن¼ ç»ںè·¯ç؛؟,وˆ‘ن»¬ه؛”该ه…ˆهˆ°و”¯ن؟،ه،کهڈ–ه¾—ه¼€هگ¯“ه¤–转ه®«é—¨”çڑ„é’¥هŒ™م€‚هچ،瓦و ¼هچڑ转ه±±ç؛؟è·¯وœ‰ن¸¤و،,هچ³ه†…转ه’Œه¤–转,ن¹ںهڈ«ه¤§è½¬ه’Œه°ڈ转——ه¤–转ن¸؛ه›´ç»•و•´ه؛§é›ھه±±ç»•هŒن¸€هœˆï¼Œé€”ç»ڈن؛‘هچ—ه¾·é’¦م€پè¥؟è—ڈه¯ںéڑ…هژ؟ه’Œه·¦è´،هژ؟,ç؛¦250ه…¬é‡Œï¼›ه°ڈ转هˆ™هœ¨هچ،瓦و ¼هچڑçڑ„و£é¢çڑ„ه¾·é’¦هژ؟ه¢ƒه†…转ن¸€هœˆï¼Œç؛¦120ه…¬é‡Œم€‚
ن¸ژوˆ‘ن»¬هگŒهژ»çڑ„هŒ—ن؛¬ن؛؛è€پé’ںن¸€ه¼€ه§‹ه°±وٹ›ه‡؛ن»¤ن؛؛ه؛”وژ¥ن¸چوڑ‡çڑ„é—®é¢کم€‚وˆ‘ه‘ٹ诉ن»–,è؟™ه؛§é›ھه±±هœ¨è—ڈو°‘ه؟ƒن¸وک¯ن¸€ه؛§و— و¯”辉煌çڑ„ه®«و®؟——看ç€ن»–ç–‘وƒ‘çڑ„眼ç¥ï¼Œوˆ‘说,è؟™ه؛§ه®«و®؟وŒ‰ç…§ه†…ه¤–ن¸¤ن¸ھه®«é—¨وœ‰ن¸¤ن¸ھه…¥هڈ£ï¼Œçژ°هœ¨وˆ‘ن»¬è؟›ه…¥çڑ„وک¯ه¤–é—¨çڑ„ه…¥هڈ£م€‚
ن¹ں许وک¯وˆ‘çڑ„è¯و°”وœ‰ن؛›ن¸چه®¹ç½®ç–‘هگ§ï¼Œè€پé’ںهˆڑè¦په¼ ه¼€çڑ„هک´هڈˆن¸چوƒ…و„؟هœ°هگˆن¸ٹن؛†م€‚ه› ن¸؛ن»ژو¾œو²§و±ںه¤§و،¥è¾¹هˆ°هچٹه±±è…°ç¬¬ن¸€ن¸ھه±±هڈ£è؟™و®µè·¯ç¨‹وˆ‘ن»¬è¢«ه®‰وژ’ن¹ک车é€ڑè؟‡ï¼Œو‰€ن»¥وٹٹ“هڈ–é’¥هŒ™”è؟™ن¸ھçژ¯èٹ‚ç»™هڈ–و¶ˆن؛†ï¼Œè؟™ن»¶ن؛‹ç،®ه®ن»¤وˆ‘وœ‰ن؛›ن¸چو‚¦ï¼Œه› ن¸؛“هڈ–é’¥هŒ™”相ه½“ن؛ژ转ه±±è€…هگ‘ç¥ه±±هڈ©é—¨çڑ„ن»ھه¼ڈ,ن¼ ç»ںن¸ٹهڈھوœ‰هڈ–ن؛†é’¥هŒ™ï¼Œè½¬ه±±و‰چه…·ه¤‡ن؛†هگˆو³•و€§م€‚ن½†ه› ن¸؛è¦په¤§éکںن؛؛马هچڈè°ƒè،Œè؟›ï¼Œن؛ژوک¯هڈھه¥½è°ƒو•´è‡ھه·±çڑ„ه؟ƒو€پم€‚
è€پé’ںوƒ³è·ںéڑڈهœ¨وˆ‘è؛«è¾¹ï¼Œن½†ن»–çڑ„وڈگé—®ه¤ھه¤ڑ,而وˆ‘هœ¨è½¬ه±±و—¶هڈˆن¸چه¤ھوƒ³è¯´è¯ï¼Œè؟™ه°±éڑ¾ن¸؛ن»–ن؛†م€‚وˆ‘çں¥éپ“ن»–و¥ن¸€è¶ںن¹ںن¸چه®¹وک“,ن¹ںçں¥éپ“ن»–وƒ³ه¤ڑن؛†è§£ن¸€ن؛›هچ،瓦و ¼هچڑçڑ„ن؟،وپ¯م€‚ه…¶ه®è€پé’ںوک¯ن¸ھهڈ¯çˆ±çڑ„è€پç”·ن؛؛,وœ‰ç‚¹èƒ–çڑ„ن¸ç‰è؛«وگ,هچ—ç“œن¼¼çڑ„脑袋ن¸‹é¢çڑ„脸虽然ه†چو™®é€ڑن¸چè؟‡ï¼Œè®©ن؛؛看ن؛†ه؟ƒé‡Œèژ«هگچهœ°è¸ڈه®م€‚ه°±ه‡è؟™ن¸€ç‚¹ï¼Œوˆ‘ن¸چه†چ讨هژŒه’Œن»–说è¯ن؛†م€‚وˆ‘è؟™ن؛؛èµ°è·¯و€§هگو€¥ï¼Œن½†è€پé’ں让وˆ‘ه؟ƒç”کوƒ…و„؟هœ°و”¾و…¢ن؛†و¥هگم€‚è€پé’ںن¸€è·¯ن¸ٹé—®è؟™é—®é‚£ï¼Œهڈˆو— ن¼‘و¢هœ°هپœن¸‹و¥çœ‹è·¯è¾¹çڑ„èٹ±èٹ±èچ‰èچ‰م€‚çœںوک¯ن»€ن¹ˆن¹ںن¸چو”¾è؟‡م€‚
وˆ‘ن»¬è·¯ن¸ٹن¸چو–éپ‡è§پ逆هگ‘而è،Œçڑ„苯و•™ه¾’,هœ¨و”€è°ˆن¸ه¾—çں¥ï¼Œن»–ن»¬éƒ½و¥è‡ھè¥؟è—ڈوکŒéƒ½çڑ„ن¸پé’هژ؟ه’Œو´›éڑ†هژ؟ن»¥هڈٹé‚£و›²çڑ„ه·´é’هژ؟م€‚è€پé’ںهڈˆé—®è‹¯و•™ه¾’ن¸؛ن»€ن¹ˆè¦په€’ç€è½¬م€‚وˆ‘ه‘ٹ诉ن»–,苯و•™è®¤ن¸؛ه®‡ه®™ه¤©ن½“وک¯é€†و—¶é’ˆو—‹è½¬çڑ„,苯و•™çڑ„“هچچ”符هڈ·ه°±è،¨ç¤؛ن؛†è؟™ç‚¹ï¼Œé€†هگ‘转ه±±ه°±وک¯ن¸€ç§چن¸ژè‡ھ然هگˆن¸€çڑ„è،Œن¸؛م€‚苯و•™وک¯è—ڈهœ°هڈ¤è€پçڑ„ه®—و•™ï¼Œه´‡ن؟،ن¸‡ç‰©وœ‰çپµï¼Œه®ƒوœ‰ه®Œو•´çڑ„çں¥è¯†ç³»ç»ںه’Œç›¸ه½“ه®Œه–„çڑ„ن»ھ轨م€‚ç¥ه±±çڑ„èµ·و؛گه°±هœ¨é‚£é‡Œم€‚هœ¨è‹¯و•™ن¹‹ه‰چ,ه±±وک¯ç¥–ه…ˆçڑ„è±،ه¾پ,由ن؛ژçپµé‚ن¸چçپ观ه؟µï¼Œè—ڈن؛؛认ن¸؛é›ھه±±وک¯ç¥–ه…ˆçڑ„هŒ–è؛«ï¼Œèچ«ه؛‡ç€هگژن»£ه®‰ه؛·ه’Œه¹¸ç¦ڈم€‚ن½›و•™é‡Œو²،وœ‰ç¥çپµه¦è¯´ï¼Œهڈھوک¯هœ¨و–‡هŒ–و”¹é€ è؟‡ç¨‹ن¸é‡‡هڈ–ن؛†وٹکن¸çڑ„هٹو³•ï¼Œه› و¤ه‡؛çژ°ن؛†è؟™ç§چه®—و•™و¶µهŒ–وƒ…ه†µم€‚وˆ‘讲ن؛†ن¸€ه †ï¼Œè€پé’ںè„‘هگ被ه¼„وˆگن؛†وµ†ç³ٹم€‚
转ه±±ن¹‹è·¯ن¸ٹç¥è؟¹ه¯†ه¸ƒï¼Œهœ¨2003ه¹´è½¬ه±±و—¶ï¼Œو±‰هœ°و¥çڑ„وœ‹هڈ‹ن»¬ن؛؛و‰‹ن¸€وœ¬م€ٹé›ھه±±هœ£هœ°هچ،瓦و ¼هچڑم€‹ï¼Œن¸€وœ¬و£ç»ڈهœ°وŒ‰ç…§ن¹¦ن¸ٹçڑ„وŒ‡ç¤؛,ه¯¹ç¥è؟¹و— ن¸€éپ—و¼ڈهœ°è؟›è،Œوœو‹œï¼Œن»¤وˆ‘è؟™ن¸ھه½»ه¤´ه½»ه°¾çڑ„è—ڈن؛؛و„ںهٹ¨ه¾—ن¸€ه،Œç³ٹو¶‚م€‚转ه±±ن¹‹è·¯وœ¬وک¯è½¬ç»ڈن¹‹è·¯ï¼Œوک¯ن¸€و،苦ن؟®ن¹‹è·¯ï¼Œè®©ن؛؛هœ¨ه؛¸ه¸¸çڑ„ç”ںو´»ن¸è؟›ه…¥ç¥هœ£ç©؛间,èژ·ه¾—解脱çڑ„و·±هˆ»هگ¯هڈ‘م€‚ç»ڈه…¸é‡Œè¯´ï¼ڑوœو‹œو²؟途ç¥è؟¹ï¼Œهڈ¯ن½؟ن؛؛ه†…ه؟ƒé‡Œç”ںèµ·è™”و•¬ن¹‹ه؟ƒï¼Œن½؟è™”و•¬ن¹‹ه؟ƒèژ·ه¾—ه¢è؟›م€‚وˆ‘ن»¬è؟™و¬،هڈھé،¾ç€èµ°è·¯ï¼Œهچ´ه؟½ç•¥ن؛†وœو‹œï¼Œه؟ƒن¸ن¸چه…چو„§و‚”م€‚
هˆ°è¾¾ه½“و™ڑèگ¥هœ°ï¼Œن½†è§په±±è°·é‡Œçڑ„èچ‰ç”¸ن¸ٹè“色ç‚ٹçƒںو°¤و°²وˆگن¸€ç‰‡ï¼Œه¤§وœ‰ن¸–ه¤–ه¹»ه¢ƒن¹‹و„ںم€‚هگƒè؟‡é¥ï¼Œوœ¬وƒ³ه¥½ه¥½è؛؛ن¸‹و¥ç،觉,هڈ¯هپڈهپڈ被è€پé’ںç¼ ن½ڈ,è¦پç»™ن»–讲و¸…و¥ڑç¥ه±±è؟™ن¸ھهگچه ‚م€‚ç¢چن؛ژè€پé’ںوک¯ن¸ھو†¨و€پهڈ¯وژ¬ن¹‹ن؛؛,ن¾؟ن¸چه¥½و„ڈو€و‹‚ن؛؛ن¹‹و„ڈم€‚ç¥ه±±وک¯è—ڈو—ڈç¥çپµن؟،ن»°çڑ„ن¸€ç§چé‡چè¦په½¢ه¼ڈ,ن¸”وœ‰ç›¸ه½“é‡چè¦پçڑ„هœ°ن½چم€‚هœ¨è‹¯و•™çڑ„ه®‡ه®™è§‚ه؟µن¹‹ن¸ï¼Œوٹٹن¸–ç•Œهˆ†ن¸؛ن¸‰ç•Œï¼Œهچ³ه¤©ç•Œم€په¹´ç•Œه’Œé¾™ç•Œï¼Œه¤©ç•Œه±…ن؛ژوœ€ن¸ٹ,龙界ه±…ن؛ژهœ°ن¸‹ï¼Œه¹´ç•Œه¤„ن؛ژن¸é—´م€‚ه±±ç¥ه°±وک¯ه¹´ç•Œçڑ„ن¸»ن؛؛,ن»–وک¯ه¹´ç•Œن¸€هˆ‡ç¥çپµçڑ„ç»ں领者,ه› و¤è¢«ç§°ن¸؛“و—¥è¾¾”م€‚وˆ‘ه€ںé¢کهڈ‘وŒ¥ï¼Œهœ¨çژ°ن»£çڑ„و–‡وکژ社ن¼ڑ里,ن؛؛ه°±وک¯è‡ھ然çڑ„ن¸»ن؛؛,相ه¯¹ن؛ژç¥ه±±è؟™ç§چ观ه؟µï¼Œوک¯ن¸چوک¯وٹٹن؛؛ه’Œè‡ھ然çڑ„ه…³ç³»وœ¬وœ«ه€’ç½®ن؛†م€‚è€پé’ںéه¸¸ه–„ن؛ژه›ç”é—®é¢ک,ن»–çڑ„ç”و،ˆوک¯ï¼Œهœ¨ن¼ںه¤§çڑ„è‡ھ然é¢ه‰چن؛؛ç®—ن¸ھن»€ن¹ˆï¼ںن»€ن¹ˆéƒ½ن¸چوک¯م€‚说هڈ¥ه®è¯ï¼Œè؟™و ·ه›ç”ن¼¼ن¹ژه¤ھو•·è،چ,ن½†وˆ‘ن¸چ能质疑è€پé’ںçڑ„ه¦è¯ڑم€‚è؟™ن¸€ه¤©ï¼Œن»–هƒڈن¸ھه©هگن¼¼çڑ„هڈˆé—®هڈˆçœ‹ï¼Œوک¯ن¸ھوœ‰ه؟ƒن؛؛ه“ھم€‚ن»–وک¯ن¸چوک¯و€€ç€è™”و•¬çڑ„ه®—و•™وœو‹œه؟ƒçگ†ï¼Œه¹¶ن¸چé‡چè¦پ,ن»–ه؟ƒçگ†ه’Œè؛«ن½“çٹ¶و€پçڑ„ن؛²ه’Œé€ڑèچو‰چوک¯وœ€ن¸؛é‡چè¦پçڑ„م€‚ن½†وک¯ه‘ٹ诉ن»–ن¸€ن؛›è—ڈو—ڈçڑ„ن¼ ç»ںو–‡هŒ–ه’Œçں¥è¯†ï¼Œه؛”该وک¯وˆ‘ه¯¹ه¾…è؟™ن½چو–°è®¤è¯†çڑ„وœ‹هڈ‹ه؛”وœ‰çڑ„و€په؛¦ï¼Œن½•ه†µهœ¨ه¼‚هںںو–‡هŒ–çژ¯ه¢ƒن¹‹ن¸çڑ„è€پé’ںهƒڈن¸ھه—·ه—·ه¾…ه“؛çڑ„ه©هگم€‚وˆ‘ه‘ٹ诉ن»–,è—ڈن؛؛转ه±±ï¼Œن¸€و–¹é¢وک¯ç¥ˆç¦ڈ,ن¸€و–¹é¢وک¯ن؟®è،Œم€‚هڈ¯وک¯è€پé’ںçڑ„è„‘هگè؟کو²،ه¼„و¸…و¥ڑç¥ه±±وک¯و€ژن¹ˆه›ن؛‹م€‚ç¥ه±±ه°±وک¯وœ‰ç¥çپµوژŒوژ§çڑ„ه±±ï¼Œè؟™ن¸ھوژŒوژ§è€…ه°±وک¯ه±±ç¥ï¼Œهœ¨è—ڈهŒ؛,و‰€وœ‰çڑ„ه±±éƒ½وک¯ç¥ه±±ï¼Œه±±ç¥çڑ„هœ°ن½چن¹ںهƒڈن؛؛类社ن¼ڑن¸€و ·وœ‰ه؛ڈهˆ—,وœ‰ن¸–ç•Œç؛§م€پ部èگ½ç؛§وˆ–هœ°هŒ؛ç؛§م€پو‘èگ½ç؛§م€په®¶و—ڈç؛§çڑ„ه±±ç¥ï¼Œن»–ن»¬وœ‰ç€ه®Œو•´çڑ„结و„ن½“ç³»م€‚هƒڈهچ،瓦و ¼هچڑوک¯ن¸–ç•Œç؛§çڑ„ç¥ه±±ï¼Œç»ڈه…¸é‡Œè¯´ï¼Œن»–è؟کوک¯ن¸–ç•Œç¥ه±±çڑ„و€»ن¸»م€‚è؟™ن¸ھه±±ç¥è؟کهˆ†ن¸–é—´ç¥ه’Œè¶…ن¸–é—´ç¥م€‚ن¸–é—´ç¥وک¯ن½ژç؛§ç¥çپµï¼Œهڈھç®،物质ن¸–界,说é€ڑن؟—ن¸€ç‚¹ه°±وک¯هڈھç®،ه†·وڑ–饥饱,而超ن¸–é—´ç¥هˆ™ç®،هˆ°ن؛†ن؛؛çڑ„ç²¾ç¥ن¸–界,ه°±وک¯وœ‰ç›ٹن؛ژن؛؛çڑ„解脱ن؛‹ن¸ڑ,ن»–ه› ن¸؛ه…·وœ‰ن½›و€§è€Œوˆگن¸؛وٹ¤و³•م€‚هچ،瓦و ¼هچڑو—¢وک¯هœ°ن½چه¾ˆé«کçڑ„ç¥ه±±ï¼Œهڈˆه› ن¸؛è؟™ن¸ھç¥ه±±çڑ„ه±±ç¥ه…·وœ‰ن½›و€§ï¼Œهœ¨ن½›و•™ن¼ ه…¥è—ڈهœ°ن¹‹هگژ,وˆگن¸؛胜ن¹گ金هˆڑهˆ¹هœںçڑ„ن؟وٹ¤ç¥م€‚
ه› ن¸؛第ن؛Œه¤©è؟کè¦پç؟»è¶ٹوµ·و‹”4300ç±³çڑ„ه¤ڑه…‹و‹‰ههڈ£ï¼Œن¸چ能ه¤ھو™ڑ,هڈھ能粗略هœ°è®²م€‚ن¹ںن¸چçں¥éپ“è€پé’ںè„‘هگوœ‰و²،وœ‰ن؛‘ه¼€é›¾و•£م€‚è€پé’ںن¹ںهگˆن¸ٹè®°ن؛†ه¯†ه¯†é؛»é؛»çڑ„وœ¬هگ,è€پè€په®ه®هœ°ç،觉هژ»ن؛†م€‚
وœ‰ن؛؛وŒ‚ن؛†و”€ç»³ن»¥و–¹ن¾؟ن؛؛ن»¬é€ڑè؟‡ï¼Œè؟™ن¹ˆهپڑهˆ°ه؛•وک¯و£ç،®è؟کوک¯ç”¨ه؟ƒè؟‡é‡چï¼ں
ه¤ڑه…‹و‹‰ه› ن¸؛وµ·و‹”é«ک,ن¸”ه±±هٹ؟é™،ه³è€Œه‡؛هگچم€‚ç«™هœ¨ههڈ£ï¼Œه¯’é£ژه¼؛هٹ²ï¼Œه‡ و¬²وٹٹن؛؛ه†»هƒµم€‚وˆ‘é،¾ن¸چن¸ٹ脑部ç¼؛و°§é€ وˆگçڑ„ن¸چ适,赶紧و‰¾هœ°و–¹وŒ‚ن؛†ç»ڈه¹،م€‚è؟کو²،وٹٹن¸€ه¤´و‹´ه¥½ï¼Œه¼؛é£ژن¾؟وٹٹç»ڈه¹،هگ§ه•¦ه•¦ه±±و‰¯ن؛†èµ·و¥م€‚ه±±هڈ£ن¸¤ن¾§ï¼Œé•؟ه¯؟ن؛”ه§ٹه¦¹ه’Œهچپن؛Œن¸¹çژ›ه¥³ç¥ï¼ˆç¥çپµهگچ称)ه¹»هŒ–而وˆگçڑ„ه±±ه³°وٹ«ç€çڑ‘çڑ‘白é›ھهœ¨ç؛¯و¾ˆçڑ„è™ڑç©؛ن¹‹ن¸ه¤؛ن؛؛眼目م€‚وˆ‘هœ¨ه±±هڈ£è¯µه؟µه…ه—çœں言,ه¹¶ه°†وŒپ诵هٹںه¾·ه›هگ‘(و—¢وٹٹهٹںه¾·é¦ˆèµ ن¸ژه›هگ‘ه¯¹è±،,ن¹ںوٹٹè‡ھه·±çڑ„هٹںه¾·هکه¯„هœ¨ه›هگ‘ه¯¹è±،那里م€‚è؟™é‡Œو‰€è¯´çڑ„هٹںه¾·وک¯وŒ‡و¶ˆé™¤وپ¶ن¸ڑçڑ„ه–„ه¾·م€‚)给هœ¨è½¬ç”ںن¹‹è·¯ن¸ٹçڑ„و¯چن؛²م€‚و¤و—¶ï¼Œوˆ‘و„ں觉و¯چن؛²ن¹ںهگهœ¨è؛«و—پ诵ç»ڈم€‚ه½“èµ·è؛«و—¶ï¼Œه››ه‘¨و™¯ç‰©و¶ˆه¤±و®†ه°½ï¼Œن¸€ç‰‡ç©؛茫م€‚وˆ‘çں¥éپ“,و³ھو°´ه·²ç»ڈو·¹و³¨ن؛†هڈŒçœ¼م€‚
ه¤ڑه…‹و‹‰è؟™و®µè·¯ç¨‹هœ¨è½¬ه±±è·¯é€”ن¸هڈ«هپڑ“ç”ںو»ç•Œه،”,ه°±وک¯ه·²ç»ڈه¾€ç”ںçڑ„ن؛؛ن»¬هœ¨è؟™é‡Œç‰ه¾…ç€è‡ھه·±çڑ„ن؛²ن؛؛م€‚وˆ‘وœ¬و¥وک¯è¦پوٹٹè؟™ن»¶ن؛‹è®²ç»™è€پé’ں,ن½†وƒ³èµ·ن¸ٹو¬،و°´ç¾ٹه¹´è½¬ه±±çڑ„و—¶ه€™ï¼Œé©¬éھ…说,ن»–و¢¦è§پهœ¨ه±±هڈ£ç¥ˆç¥·çڑ„ن¸€ن½چè€پن؛؛هڈکوˆگن؛†ن¸€هŒ¹ç™½é©¬ï¼Œوˆ‘ه°±و”¾ه¼ƒن؛†è؟™ن¸ھو‰“ç®—م€‚
ن¸‹ه±±çڑ„è·¯وک¯و§½و²ںن¸108éپ“وٹک转م€‚è؟™و®µن¸‹ه،è·¯هœ¨11وœˆè‡³و¥ه¹´4وœˆن¼ڑ被ه†°é›ھه°په†»ï¼Œن¸‹ه،هڈھ能هگهœ°و»‘è،Œï¼Œه› و¤ç»ڈه¸¸هڈ‘ç”ںو‘”و»و‘”ن¼¤ن¹‹ن؛‹ï¼Œن½†وœهœ£è€…ن¹‰و— هڈچé،¾هœ°ه‰چè،Œï¼Œن»ژن¸چ视ن½œç•ڈ途而退缩م€‚
çژ°هœ¨وœ‰ه؟ƒن؛؛ن»ژه±±هڈ£وŒ‚ن؛†و”€ç»³ن»¥و–¹ن¾؟ن؛؛ن»¬é€ڑè؟‡م€‚وˆ‘ه؟ƒé‡Œه¾ˆéڑ¾è¯´و¸…و¥ڑ,è؟™ن¹ˆهپڑهˆ°ه؛•وک¯ه¯¹è؟کوک¯ç”¨ه؟ƒè؟‡é‡چم€‚ه› ن¸؛وˆ‘觉ه¾—,وœهœ£وœ¬è؛«ه°±وک¯هœ¨و— ه¸¸ه°کن¸–ن¸ه¯¹ç”ںه‘½çڑ„و„ںو‚ں,è؟™ç§چو„ںو‚ںه؛”该هœ¨é™©ç»ن¹‹ن¸ç”ںهڈ‘ه‡؛و¥م€‚è‡ھهڈ¤ن»¥و¥ï¼Œوœهœ£è€…ه°±وک¯è؟™ن¹ˆèµ°è؟‡و¥çڑ„,و›´ن½•ه†µه½“و—¶çڑ„ç©؟ç€و،ن»¶وک¯ه¤ڑن¹ˆçڑ„简هچ•م€‚
èµ°هˆ°ه±±è„ڑ,وœ‰ه†…هœ°و¥çڑ„转ه±±ه®¢ه–œه½¢ن؛ژ色هœ°ه‘¼هڈ«ç€هڈ‘و³„وŒ‘وˆکçڑ„胜هˆ©ï¼Œن»–ن»¬و‰¾ه¯»هگˆé€‚çڑ„ن½چç½®و‘†و”¾ه§؟هٹ؟و‹چ照留ه؟µم€‚è€پé’ںه€’وک¯و¤و—¶ه¾ˆو²‰ç€ï¼Œè„¸ن¸ٹو²،وœ‰و´‹و؛¢ه–œè‰²م€‚ن»–ه—“éں³وœ‰ç‚¹هڈ‘ه¹²هœ°è¯´ï¼ڑ“وˆ‘هˆڑو‰چهگ¬è—ڈو°‘说è؟™و®µè·¯ن¸ٹو»è؟‡ن¸چه°‘ن؛؛,وک¯è؟™و ·ن¹ˆï¼ں”
وˆ‘è¦پو€ژن¹ˆè·ںن»–说ه‘¢ï¼ںè؟™و®µè·¯وک¯و»è؟‡ن؛؛,ن½†ن¸چçں¥هˆ°ه؛•و»è؟‡ه¤ڑه°‘ن؛؛ï¼ںهœ¨è؟™é‡Œو»هژ»çڑ„,ن؛؛ن»¬ن»ژو¥و²،وœ‰ه½“هپڑو»ن؛ژéه‘½ï¼Œç”ڑ至ه½“هپڑن¸€ن»¶ه€¼ه¾—èچ£è€€çڑ„ن؛‹وƒ…م€‚ن½ ن¸چè§پن¸ٹن؛†ه…«ن¹هچپه²پçڑ„耄耋è€پن؛؛ن¹ںو¥è½¬ه±±ن¹ˆï¼Œهˆڑهˆڑè؟کوœ‰ن¸€ن½چ106ه²پçڑ„هڈ¤ç¨€è€پن؛؛ن¹ںهœ¨ه™هگçڑ„وگ€و‰¶ن¸‹èµ°è؟‡هژ»ن؛†م€‚è¯è؟کو²،说ه®Œï¼Œو—پè¾¹ن¸€ن½چو¥è‡ھé’وµ·çژ‰و ‘ه·çڑ„ن¸ه¹´وœهœ£è€…用و±‰è¯وڈ’è¯è؟›و¥è¯´ï¼ڑ“وˆ‘هˆڑو‰چهگ¬ن؛†ن½ ن»¬çڑ„说è¯ï¼Œوˆ‘爷爷ن¹ںوک¯هœ¨وœو‹œè·¯ن¸ٹهژ»ن¸–çڑ„,ن»–هژ»ن¸–çڑ„و—¶ه€™وک¯76ه²پم€‚وˆ‘و¯ڈه¹´éƒ½و¥è½¬ن¸€و¬،,çژ°هœ¨ه·²ç»ڈ转ن؛†36هœˆم€‚”说ه®Œه¾„è‡ھèµ°ن؛†م€‚وژ‰ه¤´هگ‘و¥و—¶çڑ„و–¹هگ‘وœ›هژ»ï¼Œه±±è·¯و›²و›²وٹکوٹک,وœهœ£çڑ„ن؛؛وµپهƒڈن¸²ç؛؟ن¸ٹçڑ„çڈ هگن¸€èˆ¬وژ¥è؟ن¸چو–م€‚
و¥è‡ھهںژه¸‚çڑ„ه·¥ن¸ڑن؛§ه“پ,هڈکوˆگن؛†è½¬ه±±è·¯ن¸ٹè¶ٹ积è¶ٹه¤ڑçڑ„هƒهœ¾م€‚
è€پé’ںه¯¹ن¸€è·¯ن¸ٹو³›و»¥çڑ„هƒهœ¾è€؟è€؟ن؛ژو€€م€‚هœ¨ه®؟èگ¥هœ°ï¼Œن»–ه¼‚ه¸¸و؟€هٹ¨هœ°è·ںوˆ‘讨è®؛èµ·و²؟途çڑ„هƒهœ¾é—®é¢کم€‚ه…¶ه®è½¬ه±±è·¯ن¸ٹè¶ٹو¥è¶ٹه¤ڑçڑ„ن¸¢ه¼ƒç‰©ن¹ںوک¯ç¼ 绕هœ¨وˆ‘ه؟ƒن¸çڑ„ن¸€ن¸ھ结م€‚
ن؛§ç”ںè؟™ن¹ˆه¤ڑهƒهœ¾çڑ„هژںه› وک¯çژ°هœ¨çڑ„ن؛؛ن»¬ه¯¹ç‰©è´¨çڑ„ه€ڑé‡چè¶ٹو¥è¶ٹه¤§ï¼Œé™¤ن؛†éƒ¨هˆ†è؟œéپ“而و¥çڑ„وœهœ£è€…è؟کو²،وœ‰و”¹وژ‰هگƒç³Œç²‘ه’Œç‰›è‚‰ه¹²çڑ„ن¹ وƒ¯ï¼Œو›´ه¤ڑو¥è‡ھه†œهŒ؛çڑ„ن؛؛ن»¬هˆ™è؛«ن¸ٹه¸¦é’±è€Œو¥ï¼Œه› ن¸؛و²؟途都وœ‰ç®€وک“é£ںه®؟点م€په°ڈهچ–é“؛,هڈ¯ن»¥ن¹°çں؟و³‰و°´م€پ饮و–™م€په•¤é…’م€پ白酒ç‰هگ„ه¼ڈ饮ه“پ,é¥؟ن؛†هڈ¯ن»¥ن¹°و–¹ن¾؟é¢م€پ零é£ںو¥ه……饥م€‚è؟™ن؛›هŒ…装袋م€پ饮و–™ç“¶ه’Œوک“و‹‰ç½گهœ¨ن؛«ç”¨è؟‡ن¹‹هگژه°±وˆگن؛†ن»¤ن؛؛触目وƒٹه؟ƒçڑ„هƒهœ¾م€‚وˆ‘çڑ„ن¸€ن½چهœ¨ç”µè§†هھ’ن½“ه·¥ن½œçڑ„وœ‹هڈ‹هœ¨وˆ‘ن»¬ه‡؛هڈ‘ن¹‹ه‰چ转ه±±ه›و¥ï¼Œç›¸وœ؛ه’Œو‰‹وœ؛ه›¾ه؛“里ه°±è£…ن؛†و»،و»،ه½“ه½“çڑ„هƒهœ¾ه›¾ç‰‡م€‚وˆ‘و‰€هœ¨çڑ„هچ•ن½چن¹ں被ه½¢هٹ؟ن¸¥ه³»çڑ„هƒهœ¾é—®é¢ک焦ه¤´çƒ‚é¢م€‚
وˆ‘让è€پé’ںه…ˆهˆ«و؟€هٹ¨ï¼Œوˆ‘ه‘ٹ诉ن»–,è؟™ن؛›و¥è‡ھهںژه¸‚çڑ„ه·¥ن¸ڑن؛§ه“پ,هœ¨هںژه¸‚ن؛؛çڑ„眼ن¸وک¯هƒهœ¾ï¼Œه¹¶ه¯¹ه®ƒن»¬çڑ„و±،وں“ه’Œهچ±ه®³و€§çڑ„认识ه·²ç»ڈ相ه½“وˆگç†ں,هڈ¯وک¯ه¯¹ن؛ژè¾¹è؟œهœ°هŒ؛çڑ„è—ڈو°‘,ه®ƒن»¬è؟کهڈھوک¯و–°ç”ںن؛‹ç‰©ï¼Œو–°é²œو„ںè؟œه¤§ن؛ژه¯¹و±،وں“ه’Œهچ±ه®³و€§çڑ„و·±هˆ»è®¤è¯†م€‚و¤ه¤–,è—ڈو—ڈن؛؛è؟کوœ‰ن¸€ن¸ھو ¹و·±è’‚ه›؛çڑ„观ه؟µï¼Œè®¤ن¸؛ç¥ه±±هœ£هœ°ه…·وœ‰و®ٹ胜çڑ„هٹ وŒپهٹ›ï¼Œن¸€هˆ‡وœ‰ه®³çڑ„ن¸œè¥؟都能被ç¥ه±±ç¥ه¼‚çڑ„هٹ›é‡ڈ解ه†³وژ‰م€‚
و‰€ن»¥ï¼Œه¯¹هƒهœ¾çڑ„ç®،çگ†ه’Œوژ§هˆ¶è¦پن»ژو؛گه¤´ن¸ٹن¸‹و‰‹م€‚وˆ‘ه§‹ç»ˆè®¤ن¸؛,و‰€è°“çڑ„çژ¯ن؟ه…‰é وٹ€وœ¯ه°ڑن¸چ能达هˆ°وœ€هœ†و»،çڑ„结وœï¼Œه› ن¸؛وٹ€وœ¯ن»…ن»…هڈھوک¯و‰‹و®µï¼Œن؛؛ه؟ƒه’Œè،Œن¸؛و–¹ه¼ڈçڑ„و”¹هڈکو‰چوک¯وœ€é‡چè¦پçڑ„,ه› و¤ï¼Œè½¬ه±±è·¯ن¸ٹهƒهœ¾é—®é¢کçڑ„解ه†³ن¸چوک¯و²،وœ‰هٹو³•çڑ„,ه› ن¸؛è—ڈو°‘çڑ„هڈچو€èƒ½هٹ›ه’Œè،Œن¸؛çں«و£èƒ½هٹ›è؟کوک¯و¯”较ه¼؛çڑ„م€‚ه…³é”®وک¯و–¹و³•ï¼Œوˆ‘هœ¨ه؟ƒن¸ه¯¹è‡ھه·±è¯´ï¼Œن¹ںه¯¹è€پé’ں说م€‚ه…¶ه®è€پé’ںن¹ں看هˆ°ï¼Œه¾ˆه¤ڑوœهœ£è€…看هˆ°وœ‰ن؛؛هœ¨و¸…وچ،هƒهœ¾ï¼Œو»،و€€و•¬و„ڈهœ°éپ“谢,و‰‹ه؟ƒوœن¸ٹهœ°è¯´ï¼ڑه›¾هگ‰ه¥‡(谢谢)ï¼پوœ‰çڑ„ن¹ںé،؛و‰‹وچ،起路边çڑ„هƒهœ¾م€‚
ç؟Œو—¥و—©و™¨ï¼Œè€پé’ںè¯é‡چه؟ƒé•؟هœ°ه¯¹وˆ‘说ï¼ڑن½ 用è—ڈè¯ه‘ٹ诉è—ڈو°‘,وٹٹè‡ھه·±çڑ„هƒهœ¾è‡ھه·±ه¸¦èµ°م€‚وˆ‘è·ںن»–ه¼€çژ©ç¬‘ï¼ڑن¹ں许ن½ و‰€è®¤ن¸؛çڑ„هƒهœ¾ï¼Œن»–è؟که½“ه®è´ه‘¢م€‚ه°±هƒڈ牛ç²ھ,ن½ ن»¬è®¤ن¸؛وک¯هƒهœ¾ï¼Œهڈ¯è—ڈو°‘هچ´وٹٹه®ƒه½“燃و–™ه‘¢ï¼Œç‰›ن¸چهƒڈن؛؛è§په•¥هگƒه•¥ï¼Œه®ƒو‹‰ه‡؛و¥çڑ„ن¸œè¥؟ه¹²ه‡€ç€ه‘¢م€‚è€پé’ں脸色هڈکه¾—ن¸چو‚¦ï¼ڑن½ ن»ٹه¤©و€ژن¹ˆه•¦ï¼ں牛ç²ھ能è·ںهƒهœ¾و¯”هگ—ï¼ںهœ¨è€پé’ںé¼»ه°–ن¸ٹè؟کو²،وœ‰و¸—ه‡؛و±—çڈ ن¹‹ه‰چ,وˆ‘赶ه؟™و”¾ç¼“è¯و°”,说ï¼ڑè·ںن½ ه¼€çژ©ç¬‘ه‘¢ï¼پ许وک¯وˆ‘وٹٹè€پé’ں认ن¸؛ه¾ˆن¸¥é‡چçڑ„هƒهœ¾é—®é¢که½“وˆگن؛†éڑڈو„ڈçڑ„çژ©ç¬‘è¯ï¼Œوگه¾—è€پé’ںو‹‚袖而هژ»م€‚è€پé’ںçڑ„çœںè¯ڑ,让وˆ‘ه†…ه؟ƒو³›èµ·ن¸€éکµéڑ¾è¨€çڑ„é…¸و¥ڑï¼ڑهœ¨هƒهœ¾ه¤„çگ†و–¹ه¼ڈن¸ٹ,由ن؛ژç¼؛ن¹ڈهƒهœ¾و¸…è؟گç»ڈ费,هœ¨ه½“هœ°وœ‰ن؛؛وڈگè®®ه،«هں‹وˆ–者ç„ڑ烧,وˆ‘هڑوŒپ直言ن¸چ讳هœ°وڈگه‡؛هڈچه¯¹و„ڈè§پ,ه› ن¸؛ه،«هں‹çڑ„结وœوک¯é›ھه±±è¢«هƒهœ¾ه……و–¥ï¼Œé›ھه±±وک¯ç؛¯ه‡€ن¹‹هœ°ï¼Œن½•ه†µç¥ه±±هœ£هœ°ن¸چ能هڈ—هˆ°ن»»ن½•çژ·و±،م€‚ç„ڑ烧ن¹ںن¸چه¦¥ï¼Œن؛؛ن»¬و¯ڈه¤©éƒ½هœ¨ç…¨و،‘ç¥ç¥€ï¼Œو،‘çƒںن»ژه±±è„ڑهچ‡هگ‘ه±±é،¶ï¼Œهœ¨ç¥ه±±ن¸ٹç„ڑ烧هƒهœ¾ï¼Œه²‚ن¸چوک¯وœ‰è؟ن؛ژه¯¹é›ھه±±çڑ„و•¬ه¥‰م€‚وˆ‘觉ه¾—,ه،«هں‹ه’Œç„ڑ烧هœ¨ç¥ه±±è؟™و ·çڑ„هŒ؛هںں里وک¯ن¸€ç§چ简هچ•è€Œç²—وڑ´çڑ„ن¸¾هٹ¨م€‚هœ¨è‡ھ然هœ£ه¢ƒن¸çڑ„çژ¯ن؟è،Œهٹ¨ه؟…é،»ه……هˆ†ه°ٹé‡چن¼ ç»ںو–‡هŒ–,هچƒن¸‡ن¸چ能è؟·ن؟،وٹ€وœ¯و‰‹و®µم€‚ه› و¤ï¼Œه¦¥ه–„çڑ„هٹو³•ه؛”该وک¯ç”±و”؟ه؛œه‡؛هڈ°ç›¸ه…³و³•è§„,ه†چè¾…ن»¥ه®—و•™ç•Œçڑ„ه€،ه¯¼ï¼ˆè؟™و–¹é¢çڑ„ن½œç”¨ه¾ˆé‡چè¦پ),ه¯¹و؛گه¤´è؟›è،Œن¸¥و ¼وژ§هˆ¶م€‚
ه¼€è½¦è½¬ه±±ن¸چن»…و¶ˆه¼±ن؛†è‹¦éڑ¾ï¼Œن¹ںè؟œç¦»ن؛†éپچه¸ƒن؛ژو¥éپ“ن¸ٹçڑ„ç¥è؟¹
وˆ‘ن¸€ç›´ç—´è؟·ن؛ژ“ç« وپ°éƒژ”è؟™ن¸ھè·¯هگچم€‚ç« وپ°هœ¨è—ڈè¯é‡Œوک¯ç”ک霖م€پç”ک露çڑ„و„ڈو€م€‚è؟™و®µè·¯ن¸€ç›´ن¼¸ه±•هœ¨èŒ‚ه¯†çڑ„و£®و—ن¸م€‚è؟™و—¶èٹ‚,é«که±±و¨م€پو،¦و ‘م€پèٹ±و¥¸م€پن؛”角و«م€پèگ½هڈ¶و¾ن؛¤ç»‡èµ·ç»ڑ烂çڑ„金黄ه’Œç؛¢è‰²ï¼Œçٹ¹ه¦‚ن»™ه¥³ه¾®é†؛ن¸çڑ„و¢¦ه¢ƒم€‚çœںن¸چو„§وک¯م€ٹهچ،瓦و ¼هچڑهœ£هœ°ه؟—م€‹ن¸و‰€وڈڈè؟°ï¼ڑè؟™é‡Œçڑ„و ‘وœ¨éƒ½وک¯ن½›èڈ©èگ¨çڑ„ه¹،ه¹¢م€‚
وœهœ£è€…ن¼ڑهœ¨è؟™و®µè·¯ن¸ٹç چن¼گ竹هگهپڑو‹„و£چم€‚è؟™ç«¹و£چن¸چن»…ن»…وک¯èµ°è·¯و—¶çڑ„ه€ںهٹ›ن¹‹ç”¨ï¼Œه®ƒè؟کèپڑ集起“ه¤®”م€‚“ه¤®”وک¯è—ڈو–‡هŒ–ن¸éه¸¸é‡چè¦پçڑ„观ه؟µï¼ŒوŒ‡çڑ„وک¯ç¦ڈو°”م€پç¦ڈè؟گم€پç¦ڈ祉,ه±…ن؛ژن؛؛è؛«هˆ™è؟گهٹ؟畅达,èپڑن؛ژو‘ه؛„هˆ™و‘ه؛„ç¹پèچ£وکŒç››م€‚هœ¨è—ڈهœ°و°‘é—´وœ‰éڑ†é‡چçڑ„祈ç¦ڈه’Œè؟ژç¦ڈن»ھه¼ڈم€‚è—ڈو—ڈو°‘间认ن¸؛,ç¥ه±±وک¯“ه¤®”çڑ„ه®ه؛“,ن½†è؟™ن¸ھه®ه؛“ه¹¶ن¸چوک¯ن¸‡و— ن¸€ه¤±çڑ„,ه®ه؛“çڑ„ه®‰ه…¨هڈ–ه†³ن؛ژن؛؛çڑ„è،Œن¸؛م€‚ه¦‚وœن؛؛ه¯¹ه¾…è‡ھ然界è´ھه¾—و— هژŒï¼Œه°±ن¼ڑç ´هڈن؛†ه®ه؛“,致ن½؟“ه¤®”و¶ˆه‡ڈن¸§ه¤±م€‚“ه¤®”ه°‘ن؛†و²،وœ‰ن؛†ï¼Œهˆ™ن؛؛ن¼ڑè،°è´¥ï¼Œه®¶ه؛è´¥èگ½ï¼Œو‘ه؛„و²،و³•ه®‰ه±…م€‚
هœ¨è·¯è¾¹ï¼Œن¸€ن½چو¥è‡ھè¥؟è—ڈçڑ„è€پن؛؛و£هœ¨ه¾€ه¸ƒè¢‹é‡Œè£…è؟›هœ£هœںم€‚è€پن؛؛说,ن»–ن»¬و‘ه؛„éپهڈ—ن؛†و—±çپ¾ï¼Œè™½ç„¶وœ‰و”؟ه؛œه®و–½و•‘çپ¾ï¼Œن½†è€پن؛؛ه؟ƒé‡Œن¸چه®‰ï¼Œن»–肯ه®ڑهœ°è®¤ن¸؛è؟™وک¯“ه¤®”ن¸§ه¤±ن؛†م€‚è€پن؛؛وٹ¬çœ¼çœ‹ن؛†çœ‹è؟œه¤„色ه½©و–‘و–“çڑ„é«که±±ï¼Œو„ںو…¨هœ°è¯´ï¼ڑè؟™é‡Œه±±ن¸ٹçڑ„و£®و—é•؟ه¾—è؟™ن¹ˆه¥½ï¼Œوµپو°´è؟™ن¹ˆو¸…و¾ˆï¼Œوک¯è؟™é‡Œçڑ„“èپڑ”ه…»ه¾—ه¥½ه•ٹم€‚è€پن؛؛说çڑ„“èپڑ”,وک¯وŒ‡ç²¾ç²¹م€پç²¾و°”,وˆ–者هڈ¯هپڑèگ¥ه…»م€په…»هˆ†çگ†è§£ï¼Œوک¯ن½؟ن¸‡ç‰©ç¹پèچ£çڑ„è†ڈè„‚م€‚“èپڑ”çڑ„ه¥½هڈه†³ه®ڑن؛†ه±±م€پو°´م€پهœںهœ°ه’Œن¸‡ç‰©çڑ„ه“پè´¨م€‚ه¦‚وœه±±ه¤±هژ»ن؛†“èپڑ”,èچ‰وœ¨و¯و»ن¸چé•؟,é£ç¦½èµ°ه…½ç»è؟¹ï¼›و°´ه¤±هژ»“èپڑ”,ن¾؟ن¼ڑه¹²و¶¸و–وµپï¼›هœںهœ°ه¤±هژ»ن؛†“èپڑ”,هˆ™ن¸‡ç‰©ن¸چç”ں,陷ه…¥و»ه¯‚م€‚“èپڑ”ه¾—هˆ°ه…»وٹ¤ï¼Œهˆ™é’ه±±ç¹پ茂م€پç»؟و°´é•؟وµپ,ن¸‡ç‰©ç”ںوœ؛ç›ژ然,而ن¸”ن¼ڑèپڑ集起ه¼؛ç››çڑ„“ه¤®”م€‚è€پن؛؛说,“èپڑ”ه’Œ“ه¤®”ن؟وٹ¤ه…»è‚²ه¥½ن؛†ï¼Œن؛؛ه°±هڈ¯ن»¥èژ·ه¾—ه®‰ه±…ن¹گن¸ڑçڑ„ه¥½ç¦ڈو°”م€‚
èµ°هˆ°و€’و±ں边,وˆ‘و‰چçں¥éپ“ه¦‚ن»ٹ转ه±±هڈ‘ç”ںçڑ„هڈکهŒ–م€‚眼ه‰چçڑ„è؟™و،ه…¬è·¯ه°±وک¯هچ—وژ¥ن؛‘هچ—و€’و±ںه·è´،ه±±هژ؟م€پهŒ—è؟è¥؟è—ڈو—èٹه¸‚ه¯ںéڑ…هژ؟çڑ„ه¯ں瓦龙ن¹،çڑ„ه¦‚ن»ٹه£°هگچé¹ٹèµ·çڑ„“ن¸™ه¯ںه¯ں”ç؛؟è·¯م€‚ه…¬è·¯ن¸ٹ车و¥è½¦ه¾€é»„ه°که¼¥و¼«م€‚看车牌هڈ·ï¼Œهں؛وœ¬éƒ½وک¯ن؛‘هچ—è؟ھه؛†م€پè¥؟è—ڈوکŒéƒ½م€پé’وµ·çژ‰و ‘çڑ„车م€‚ن؛؛ن»¬ه·²ç»ڈه¼€ه§‹ن¹ک车转ه±±ن؛†م€‚è؟™ن¸چه…چ让وˆ‘و„ںهˆ°è®¶ه¼‚ï¼پ虽然هœ¨و¥و—¶çڑ„è·¯ن¸ٹن¹ں看هˆ°و‘©و‰ک车هœ¨è½½ن؛؛,ن½†و²،وƒ³هˆ°ï¼Œè½¬ه±±çڑ„车وژ’وˆگن؛†ن¸چè§په¤´ه°¾çڑ„é•؟é¾™م€‚وˆ‘هœ¨é¦™و ¼é‡Œو‹‰çڑ„ن¸€ن½چوœ‹هڈ‹ن¹ںه¼€ç€è¶ٹé‡ژ车هœ¨è½¬ه±±م€‚ن»–وٹٹ车هپœن¸‹و¥ï¼Œو‘‡ن¸‹çژ»ç’ƒçھ—,ن»ژ车çھ—里竖起هڈ³و‰‹ه¤§و‹‡وŒ‡ï¼Œç”¨ن¸€ç§چه¾ˆèµو‰¬çڑ„هڈ£و°”ه¯¹وˆ‘说ï¼ڑه—¨ï¼Œن¸چé”™ه‘€ï¼Œه‡†ه¤‡ه…¨ç¨‹ه¾’و¥ï¼ںوˆ‘被ه°ک雾ه‘›ه¾—و²،و³•è¯´è¯ï¼Œن¾؟وœن»–وŒ¥و‰‹è®©ن»–赶紧走م€‚
ه…¶ه®ن»ژه¹´هˆه¼€ه§‹هگ¬هˆ°وœ‰ن؛؛ه¼€è½¦ه¤–转,ه› ن¸؛é،؛ç€ه…¬è·¯èµ°ï¼Œوٹٹç؛؟è·¯ه¾€ه¤–و‰©ه¤§ن؛†ï¼Œهڈ¯وک¯و²،وœ‰وƒ³هˆ°وœهœ£è½¦éکںه¦‚و¤ه£®è§‚م€‚ه¯¹ن؛ژن¹ک车转ه±±ï¼Œوˆ‘ه؟ƒé‡Œçœںوœ‰وٹµهˆ¶م€‚وˆ‘ن¹ںé—®è؟‡ه–‡هک›وœ‹هڈ‹ï¼Œن¹ک车转ه±±هٹںه¾·ه¦‚ن½•ï¼ںن»–说,ن¸»è¦پهœ¨ن؛ژهڈ‘ه؟ƒم€‚ن»–è؟که›ç”ن؛†وˆ‘çڑ„ن¸€ن¸ھé—®é¢کم€‚çژ°هœ¨وˆ‘ن»¬و‰€è®¤ن¸؛çڑ„ه¤–转ç؛؟路,ه…¶ه®هœ¨هڈ¤è€پçڑ„转ه±±ç؛؟è·¯و¥è¯´وک¯ن¸è½¬ç؛؟路,çœںو£çڑ„ه¤–转ن»ژن؛‘هچ—è؟ھه؛†ه·çڑ„ç»´è¥؟هژ؟白وµژو±›ن¹،ç؟»è¶ٹ碧èگ½é›ھه±±ï¼Œن»ژو€’و±ںه·è´،ه±±هژ؟走,“ن¸™ه¯ںه¯ں”ن¾؟وک¯هڈ¤è€پçڑ„转ه±±è·¯م€‚و£هœ¨ن؟®ه»؛ن¸çڑ„ه¾·é’¦è‡³è´،ه±±ه…¬è·¯ه› ن¸؛ه،Œو–¹è€Œن¸چ能é€ڑè،Œï¼Œهگ¦هˆ™ï¼Œهڈ¯ن»¥وƒ³è§پ车轮و»ڑو»ڑçڑ„هœ؛é¢ن؛†م€‚“ه½“然,”ن»–说,“用è„ڑ走路转ه±±هٹںه¾·è‚¯ه®ڑه¤§ن؛ژهگ车م€‚”
ه–‡هک›çڑ„è¯ه§”ه©‰ن¸چè؟‡ï¼Œن½†وˆ‘认ن¸؛转ه±±وœهœ£هژںوœ¬وک¯ن¸€ç§چ苦ن؟®و–¹ه¼ڈ,هœ¨è‰°é™©çڑ„è‡ھ然çژ¯ه¢ƒé‡Œç£¨ç ؛è؛«ن½“,é€ڑè؟‡è؛«ن½“çڑ„و„ںهڈ—ه”¤é†’ه†…ه؟ƒçڑ„هڈ‘è§پ——ن¸¥é…·çڑ„è‡ھ然çژ¯ه¢ƒه²‚ن¸چوک¯ç”ںه‘½هکهœ¨çٹ¶و€پçڑ„è±،ه¾پن¹ˆï¼ںن¹ں许و—¶é—´م€پç»ڈهژ†م€پè؛«ن½“çڑ„هژںه› ن½؟è؟™ن؛›ن؛؛ن¸چه¾—ن¸چ采هڈ–è؟™و ·çڑ„و–¹ه¼ڈ,هڈ¯وک¯ï¼Œè؟™ن¹ںه¤ھن¸ژو—¶ن؟±è؟›ن؛†م€‚ه¼€è½¦è½¬ه±±و”¹هڈکن؛†è½¬ه±±è·¯ç؛؟,ن¹ںè؟œç¦»ن؛†éپچه¸ƒن؛ژو¥éپ“ن¸ٹçڑ„ç¥è؟¹م€‚
و— è®؛و¥è‡ھه“ھ里م€پن½•ç§چهٹ¨ه› ,ه‡،وک¯è½¬ه±±ه®¢éƒ½ن¼ڑèژ·ه¾—转ه±±هٹںه¾·
و— è®؛ه†…转è؟کوک¯ه¤–转,转ه±±çڑ„éکںن¼چن¸وœ‰ن؛†و±‰ن؛؛م€پç؛³è¥؟ن؛؛م€‚هœ¨è—ڈن؛؛ن¸ï¼Œو›´وœ‰è¥؟è—ڈو‹‰èگ¨م€پéک؟里ه’Œوœ¬ن¸چه±ن؛ژهچ،瓦و ¼هچڑن؟،ن»°هœˆçڑ„ن؛؛ن»¬م€‚وˆ‘وƒ³ï¼Œè؟™ن¸چن»…ن»…وک¯ن؛¤é€ڑن¾؟هˆ©ï¼Œç»ڈوµژو،ن»¶و”¹ه–„çڑ„هژںه› م€‚
هœ¨è½¬ه±±çڑ„起点ن¸ٹ,ن¸€ن½چو¥è‡ھè¥؟è—ڈو³¢ه¯†هژ؟çڑ„è€پن؛؛è؛«و— هˆ†و–‡هœ°ن¸€è·¯هŒ–ç¼ک而و¥ï¼Œè½¬ه®Œه±±ن»–è؟که‡†ه¤‡هژ»و‹‰èگ¨وœو‹œم€‚هœ¨ه¯ں瓦龙ن¹،و‰ژ那镇ن¸ٹ,ه½“وˆ‘ن»¬ن»ژو£هœ¨و–½ه·¥ن¸çڑ„è،—éپ“ن¸ٹç»ڈè؟‡ï¼Œو¥و¥ه¾€ه¾€çڑ„è،Œن؛؛هگ‘ه‡ è؟‘蓬ه¤´ه¢é¢çڑ„è€پé’ںوٹ•و¥وƒٹه¥‡çڑ„ç›®ه…‰م€‚ن¸€ن¸ھن¹ںهœ¨è½¬ه±±çڑ„ه¾·é’¦ه°ڈè€پن¹،é—®وˆ‘,è؟™ن¸ھو±‰ن؛؛(وŒ‡è€پé’ں)ن»ژه“ھ里و¥ï¼ںوˆ‘ه‘ٹ诉ن»–è€پé’ںو¥è‡ھهŒ—ن؛¬ï¼Œن¸€è·¯ه¾’و¥è؟‡و¥çڑ„,è„ڑه؛•ه·²ç»ڈه®Œه…¨ç£¨çƒ‚ن؛†ï¼Œè،€ç³ٹن¹Œو‹‰çڑ„م€‚ه°ڈé’ه¹´هƒڈوک¯è‚¯ه®ڑهœ°ه†²è€پé’ں点ن؛†ç‚¹ه¤´م€‚è€پé’ںن¸چçں¥éپ“وˆ‘ن»¬ن¹‹é—´هœ¨è¯´ن»€ن¹ˆï¼Œن»ژè،£وœچèچ·هŒ…里و‘¸ه‡؛50ه…ƒو‹؟ç»™ه°ڈé’ه¹´ï¼Œه°ڈé’ه¹´ه©‰و‹’م€‚è€پé’ں让وˆ‘ç»™ه°ڈé’ه¹´è¯´éپ“说éپ“,请ن»–و”¶ن¸‹م€‚ه°ڈé’ه¹´è¯´ï¼Œوˆ‘è؛«ن¸ٹوœ‰é’±ï¼Œè°¢è°¢ه¥½و„ڈم€‚وˆ‘说,ن»–وƒ³è·ںن½ ن¹°ç‚¹è½¬ه±±çڑ„هٹںه¾·م€‚ه°ڈé’ه¹´ن¸چ解م€‚وˆ‘说,ن»–وک¯çœںه؟ƒçڑ„,ن»–و²،وœ‰è§‰ه¾—ن½ ç¼؛é’±ه‘€م€‚ه°ڈé’ه¹´ن¸چ解,说ï¼ڑè؟™و±‰ن؛؛ه¥½ه¥‡و€ھم€‚ه°ڈé’ه¹´و²،وœ‰وژ¥هڈ—è€پé’ںçڑ„ه¸ƒو–½ï¼Œè؟™è®©è€پé’ںوœ‰ن؛›ه°´ه°¬م€‚هگژو¥ï¼Œè€پé’ںçڑ„è؟™50ه…ƒè¢«è¥؟è—ڈç±»ن¹Œه¥‡çڑ„ن¸€ن½چè€پن؛؛و”¶ن¸‹ن؛†م€‚è€پن؛؛وٹٹé’±و”¥هœ¨و¾و ‘çڑ®ن¼¼çڑ„و‰‹ن¸ï¼Œهڈ£ن¸ن¸چو–هœ°هڈˆو„ںè°¢هڈˆç¥ç¦ڈم€‚وˆ‘ه¯¹è€پé’ں说ï¼ڑè€پن؛؛ه®¶وٹٹن»–转ه±±çڑ„هٹںه¾·هˆ†ç»™ن½ ن¸€هچٹه•¦م€‚è€پé’ںهڈˆçœ¨ه·´ه…¶هچ•çœ¼çڑ®م€‚
هœ¨وœهœ£è·¯ن¸ٹ,وٹ‘وˆ–وک¯ن؛؛ن¸–çڑ„ç”ںو´»ن¸ï¼Œن¸€ن¸ھو–½èˆچ者هگŒو—¶ن¹ںوک¯ن¸€ن¸ھهڈ—و–½è€…م€‚ه°±هƒڈè€پé’ںه’Œè؟™ن½چè€پن؛؛,è€پé’ںçڑ„ه–„è،Œه¾—هˆ°ن؛†ç¥ç¦ڈ,è؟™وک¯ن¸€ç§چو®ٹ胜çڑ„ه›وٹ¥ï¼Œè؟™ç§چه›وٹ¥ه؟…ه°†ن½œç”¨ن؛ژè€پé’ںçڑ„ç¦ڈوٹ¥م€‚هœ¨é£ژé›ھè؟·و¼«çڑ„说و‹‰ههڈ£ï¼Œé‚£ن¸ھه©‰و‹’è€پé’ںو–½èˆچçڑ„ه°ڈé’ه¹´é¬¼ن½؟ç¥ه·®هœ°çھœهˆ°وˆ‘é¢ه‰چ,ه¯¹وˆ‘说ï¼ڑ请ه‘ٹ诉ن½ çڑ„و±‰ن؛؛وœ‹هڈ‹ï¼Œه°±è¯´ن»–çڑ„ه؟ƒو„ڈوˆ‘领ن؛†ï¼Œوˆ‘ن¸؛ن»–祈ç¦ڈم€‚
هœ¨è½¬ه±±è·¯ن¸ٹ,ه¤¹و‚ç€è¶ٹو¥è¶ٹه¤ڑçڑ„و±‰ن؛؛م€پè€په¤–,ن»–ن»¬وœ‰çڑ„و€€ç€ه®—و•™وƒ…و€€ï¼Œوœ‰çڑ„被è،Œèµ°çڑ„ه†²هٹ¨ن½؟然,وœ‰çڑ„ه‡؛ن؛ژه¥½ه¥‡ï¼Œن½†و— è®؛ن½•ç§چهٹ¨ه› ,هœ¨و،‘هگ‰çڑ„眼ن¸ن¹ںوک¯è½¬ه±±ه®¢ï¼Œن¸€و ·هœ°èژ·ه¾—ن؛†è½¬ه±±هٹںه¾·م€‚هœ¨ن»–看و¥ï¼Œه¤–ن؛؛çڑ„هٹ ه…¥ï¼Œن»¤ن»–و›´è§‰ه¾—وœهœ£ن¹‹è·¯çڑ„ç¥هœ£م€‚ن¸€è·¯ن¸ٹ,ن»–ç»™وˆ‘讲ن؛†ه¾ˆه¤ڑه¤–و¥è½¬ه±±ن؛؛çڑ„و•…ن؛‹م€‚و،‘هگ‰وک¯ن¸€هگچه½“هœ°هگ‘ه¯¼ï¼Œن»–ه¸¦ن؛؛转ه±±ه·²ç»ڈ100ه¤ڑو¬،,虽然وœ‰ن؛›ن؛؛ه¼€ه§‹çڑ„و—¶ه€™و„ڈو°”é£ژهڈ‘,هڈ¯وک¯èµ°ç€èµ°ç€ه°±çں«وƒ…ن¹‹و°”وڑ´éœ²و— 疑,وœ‰çڑ„è؛«هœ¨èچ’ه±±é‡ژه²è؟که¯¹هگƒن½ڈو€¨ه£°è½½éپ“,éڑ¾ن»¥ن¼؛ه€™ï¼Œن½†ن»–用ن¸€هڈ¥è¯و€»ç»“ن؛†ه¯¹è؟™ن؛›ن»–و‰€ه¸¦è؟‡çڑ„ن؛؛ن»¬çڑ„هچ°è±،“ن»–ن»¬éƒ½وک¯ه–„良çڑ„ن؛؛م€‚”
هچ،瓦و ¼هچڑ转ç»ڈéپ“ه»¶ن¼¸هœ¨ه´‡ه±±ه³»ه²ن¹‹é—´ï¼Œن¸€è·¯è¦پç؟»è¶ٹ6ه؛§é«که±±ï¼Œه…¶ن¸ه››ه؛§وµ·و‹”超è؟‡4000米,ç؛؟路起ن¼ڈçٹ¹ه¦‚و³¢ه³°وµھ谷,ن¸€è·¯ç©؟è؟‡é«که¯’م€پç‚ژçƒم€پ险ه¢ƒï¼Œو²؟途و™¯è‡´è؟هŒ–و— ç©·م€‚
هœ¨è¥؟è—ڈéک؟ن¸™و‘,وœهœ£çڑ„香ه®¢ه’Œه½“هœ°و‘و°‘è·³ن؛†é€ڑه®µه¼¦هگèˆم€‚هœ¨ه¼¦هگçڑ„ن¼´ه¥ڈن¸‹ï¼ŒوŒه£°ه›èچ،هœ¨ه±±è°·é‡Œï¼ڑ
ن¸ٹ部é›ھه±±ن¹‹ه·…,
ç¦ڈè؟گو±‡èپڑن¹‹ه¤„م€‚
ن¸‹éƒ¨هگ‰ç¥¥و‘ه؛„,
ç¦ڈ祉و±‡èپڑن¹‹ه¤„م€‚
هگ‰ç¥¥و‘ه؛„里é¢ï¼Œ
ن؟®ه»؛金هگ般çڑ„ه°ڈه¯؛,
请ن½ هڈ©و‹œè½¬ç»ڈ,请ن½ ن¾›é¦™ن¾›و°´م€‚
ه¤–转ه¤–转,ه¤–ه›´è½¬ç»ڈ祈و„؟و¶ˆé™¤ç½ھéڑœï¼Œ
ه†…转ه†…转,ه†…ه›´è½¬ç»ڈ祈و„؟ه…چ除هٹ«éڑ¾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