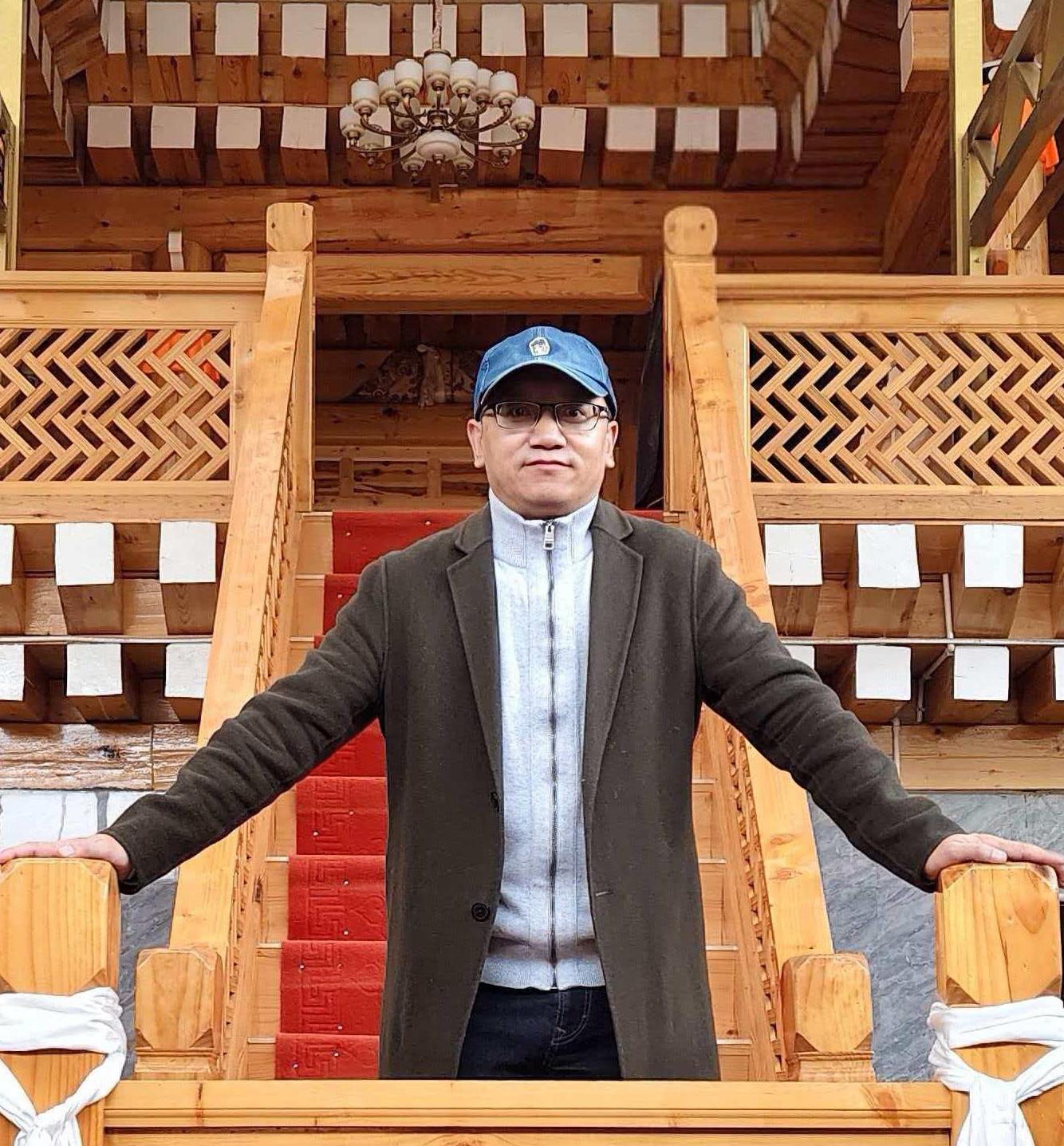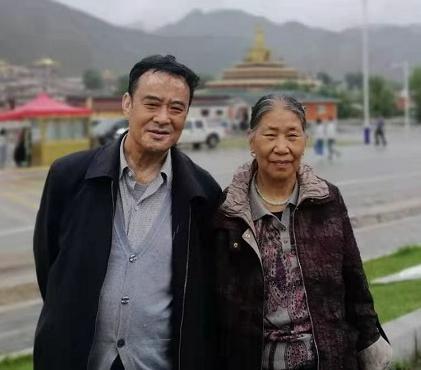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坐在甘肃夏河县拉卜楞镇的一家小店里,喝着滚烫的酥油茶,掰开一个拉卜楞面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往事。午后的阳光照在从窗口铺过来的那片影子上,细碎的尘埃在光柱里漂浮游离,稍远些的墙壁上雕刻着的传统图案“和睦四瑞”若隐若现。
偶尔从二楼临街的窗口望去,逐渐宽阔起来的街道上,来自各地的游客熙熙攘攘。彼时,当地的旅游业刚刚兴起。
那次是专程去参加好友仁青的婚礼。他是一位优秀的歌手,嗓音嘹亮,相貌俊朗,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我们相识于黄河岸边那座大学校园里,最初是师生,后来成了兄弟。那时,我就曾品尝过他从家里带来的拉卜楞面包。
这种名为“拉卜楞面包”的食品,还有一个更通用的名字——“焪锅”,是甘肃、青海一带比较常见的一种传统面食。拉卜楞面包的做法异于其他地方,自然有别具一格的风味。
首先是发酵麦面,然后加入纯碱中和,并掺入牛奶或酥油增加酥软度,通常不再添加其他原料。将揉好的面团置于高十公分、直径二十公分左右的筒状铁盒内,盖上盒盖,埋进火塘的热灰中,慢慢烘烤至熟透。由于烘烤的时间比较短,成品外焦里嫩、松软可口,切片享用时,浓郁的麦香扑鼻而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制作器皿的改进,现今的烘焙大多在电烤箱内完成,埋入锅灶或火炕内热灰中烘烤的方式已不多见了。
拉卜楞面包既管饱扛饿,还可中和胃酸,老少咸宜,更能长期储存。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它是长途旅行者的理想干粮。一些讲究的主妇,还会在发酵好的面团里揉进一些香豆,使口感更加丰富。在我的老家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香豆”也被称作“苦豆”,不知何故,大概有甘苦相依的寓意吧。
据当地朋友介绍,拉卜楞面包最早由青海热贡一带迁居夏河的人们带来,深得当地群众的喜爱。但现今,拉卜楞面包仅在夏河县境内才能买到,即便相邻的合作市也难觅其踪。
此后多年,每每路过夏河地界,我总要捎上几个拉卜楞面包和两桶牦牛酸奶,带回旅居三十余年的临水城市,以此慰藉远离故土的味蕾和乡愁。有次,为了那一口心心念念的拉卜楞面包,我舍弃走高速路的便捷,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依毛梁,顺着昔日的县道一路向下,来到合作市和夏河县交界处的小镇——王格尔塘。王格尔塘,藏语意为“亲王扎帐的平滩”。相传这里是拉卜楞寺筹建者察罕丹津迎娶南佳卓玛时,扎建帐篷、宴请宾客的地方。站在三岔路口,我不禁遐想:三百年前的那场盛大婚宴上,是否也曾摆上这金黄酥脆的拉卜楞面包?
进入王格尔塘镇街口,想在那家熟悉的面食店里买几个刚出炉的拉卜楞面包。店门却紧闭,挂着一把带钥匙的链锁。拨通店主留在大门上的电话号码,里面传出不急不缓的声音:“面包在桌子上,一个5元;酸奶在冰箱里,一桶38元。都是今早刚做的。你自己扫微信付款就行。走的时候,帮我把锁子挂上。”我依言而行,出门的时候,一位身着藏装的大哥也自行从货架上拿了一些面包,扫码支付后骑着摩托车离去。这份朴素的信任与自在,多么抚慰人心。
正要离开王格尔塘,作家朋友龙仁青打来了电话,邀我叙旧。我说,我在甘南的王格尔塘,这里有种非常好吃的拉卜楞面包,据说就来自你的家乡青海。挂断电话时,车后座上的拉卜楞面包,静静地散发着麦香。
掉头驶入夏河高速,四野绿意盎然。曲奥乡一带的桃花,在车窗外开得热烈。经过土门关时,远处的白塔静谧伫立山脚——那是通往青藏高原的古老关口,也是游子告别甘南的最后一瞥。
青藏高原的又一个夏天来了。三江一河环绕着的甘南草原,正伸开热情的臂膀,欢迎八方的宾客。

刚杰·索木东,藏族,又名来鑫华,甘肃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有大量诗歌、散文、评论、小说,作品入选百余个总结性选本,译成多种文字。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