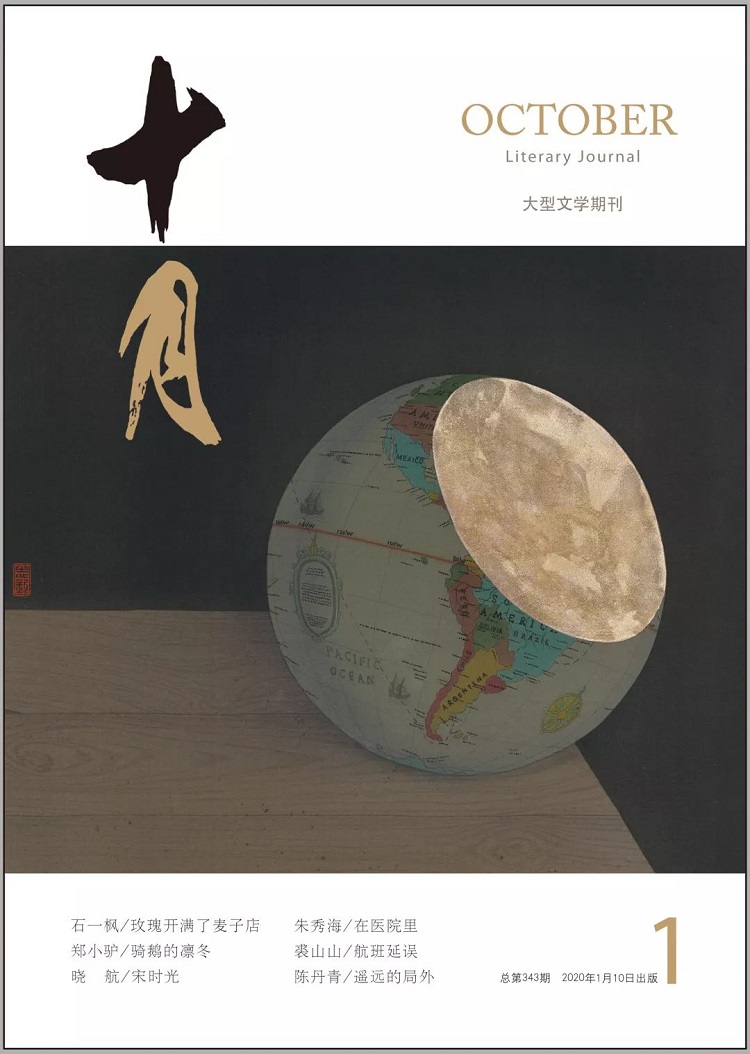
高原奔涌
金沙江是从迪庆州德钦县进入云南境内的。它来到这里,似乎是为了一个约会,怒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的吉热拍格出发,澜沧江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杂多县吉富山出发,它们沿着青藏高原一路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便被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雪山阻隔,各自寻找可以突围的路径,在震耳欲聋的涛声里彼此呼应着,艰难前行。在滇西北这片大山的阵营里,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玉龙雪山、哈巴雪山,如一群操戈披甲的武士,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展开了一场山与水之间的战争。在这里,澜沧江与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为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的最短直线距离不到19公里,浪花与岩石、涛声与森林,形成了亘古不息的较量。这便是滇西北地区“三江并流”的天地奇观,2003年7月“三江并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天地之间的聚会终将散去。金沙江从此将一路向东,挥别怒江和澜沧江,出云南,入四川、湖北,直至太平洋。然而,就在它挥别之前,依然对滇西北这片土地恋恋不舍。在这里,梅里雪山、白马雪山的阻挡,让金沙江成为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在金沙江两岸,藏族、纳西族人生活在这里,一条被人们称为茶马古道的小路,也沿着金沙江边一次次试探,终于在这个叫奔子栏的地方,渡过江去。其实,茶马古道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滇西的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大理这一片被群山环抱而又气候湿润的大地上,数千年以来一直生长着茂密的茶树,云南盛产的茶叶,被马帮驮着,沿着崇山峻岭之间曲折的山路,走出大山,经过滇西重镇大理,途经丽江,向着雪域高原西藏,以及更加遥远的尼泊尔、印度,在马帮的铃声里一路远去。马帮所到之处,当他们行走,便是一路风雨一路民歌。当他们停下来时便在岁月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驿站。茶马古道一路延伸,云南的江河便用奔腾的浪花来挽留。茶马古道一路向北,便遭遇了迎面而来的金沙江。奔子栏便是茶马古道与金沙江拥抱之后留下的一个古老的驿站。奔子栏在藏语里是“美丽的沙坝”的意思,金沙江沿着山势,在这里流成了一个美丽的“U”形,从这儿往西北行即可进入西藏,逆江北上,即是四川的德荣、巴塘;沿金沙江而下,就是维西、大理;往东南走,则是香格里拉县及丽江。千百年来,远途跋涉而来的马帮,在赶马人的歌声里来到江边的小镇上,一群又一群马匹暂时卸下茶叶、银器、丝绸等货物,在这里稍作休息。在这里,马匹在夜色里吃着草料,赶马人枕着金沙江的涛声收藏了一个短暂的浅梦。第二天,他们收拾好装好货物和简单的行李,在飞来寺僧侣们的诵经声里继续往来于江上,消失在群山巨大的阴影里,只留下一路的赶马调。
金沙江一路南下,在丽江的石鼓小镇转了一个弯,从此向东流去。这里,便被人们称为长江第一湾。“江流到此成逆转,奔入中原壮大观”,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转弯:从这里,金沙江与怒江、澜沧江分道扬镳,一路东去,从此成为长江的一部分。长江在中国南方一路流淌,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南方文明。在这个小镇上,金沙江水变得稍微缓慢了一些,给小镇留下了一片浅滩、柳林和大片的庄稼地。星罗棋布的村舍点缀在田野里,被桃花映衬着,被油菜花包围着,全然是一幅江南水粉画。金沙江在石鼓小镇稍作停留以后,便掉头向东,向着玉龙雪山与哈巴雪山的夹缝里挤进去。两座高耸的雪山,南岸的玉龙雪山海拔5596米,临峡一侧山体陡峭,几乎是绝壁,无路可寻;北岸的哈巴雪山海拔5386米,两座雪山从山顶到江底的垂直高差达到3700多米,形成了幽深、狭窄的峡谷,只给金沙江留下数百十米的宽度,最窄的一处,两岸之间只有30米,中间有一块巨石岿然不动,传说中,老虎可以借助这块巨石,跳过江去。因此,这一段金沙江,便被称之为虎跳峡。在这里,金沙江里满眼都是坚硬的礁石、坚硬的崖壁、坚硬的岩石,它们似乎早已结成了钢铁一样的阵地,把金沙江这个陌生的闯入者阻挡回去。山与水的战争,就这样展开了。面对这样的拒绝,金沙江在这里变成了狂躁的、愤怒的、勇猛的野兽,汹涌澎湃的江水用尽了它所有的力量,把这些礁石和两岸的悬崖拍击着、撕扯着。与此同时,两座高山布下了石头的营垒,石头从两岸挤压,让江水无路远退,石头迎面阻挡,让江水浊浪滔天。在这里,高山紧缩形成的狭小空间里,江水冲击岩石产生的轰鸣声,掩盖了一切声响。心跳的声音、呼吸的声音,脚步的声音,这些是距离我们每一个人最近的声音,然而,虎跳峡的洪流让它们在瞬间消失了,置身于震耳欲聋的水声里,我们只有倾听,别无选择。过了虎跳石,金沙江的落差更加明显,在随处可见的乱石滩中,峡谷内出现了7处10米多高的跌坎,江水在瞬间跌坠,浪花四溅,水雾迷蒙,涛声如雷。山与水之间的战争,在这里让每一个人领略了什么叫真正的惊心动魄。
金沙江流出了虎跳峡,山势渐低,群山环绕,在它们的中间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盆地,人们在这些盆地里生活、劳作、相爱、老去。金沙江继续流淌前行,两岸又是高耸的、炎热的群山。这些连绵不断的群山里,居住着彝族、傈僳族、傣族等古老的民族。在那些山林里、山谷中、山坡上,他们种植、放牧、狩猎,他们居守、迁徙、回归。在漫长的岁月里,太多的路被他们用一个又一个脚印踏出来,再年复一年地被生长的鲜花和野草覆盖。但是,无论岁月再漫长,他们的内心里同样也留下了太多的东西,比如毕摩经书、太阳历、火把节、创世纪、左脚舞以及隐藏在群山里的崖画。更远的时光,是更加幽暗的,当金沙江流淌到一个叫元谋的地方的时候,那一片如今盛产蔬菜和水果的土地,早在一百七八十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放眼整个中国乃至亚洲,被我们称为“元谋人”的远古智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曾经是我们人类最早的故乡。金沙江到了水富县,便是它在云南省境内的最后一个驿站了。在这里,云南人、四川人往来穿梭,在风雨岁月里行走了千百年。在这里,金沙江的流淌,不再是涛声冷寂地拍打着两岸山崖的景象。金沙江下游的巧家县有一个充满了诗意的地方叫白鹤滩。金沙江在这个诗意的地方成为一汪碧水,映照着高远的天空,映照着连绵起伏的乌蒙山。一座现代化的水泥大坝拔地而起,一座水电站将会让金沙江成为水电能源的重要基地。其实,在云南,在金沙江上,也绝不仅仅只有白鹤滩水电站。从金沙江进入云南以后,它就携带着滚滚江水从滇西北高原上一路奔涌而下,狭窄的水道,高悬的落差,让每一个湾滩都成了建设水电站的绝佳地带。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盛与发展,金沙江上游先后规划和建设了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等“一库八级”电站,下游还有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白鹤滩等4座世界级水电站。金沙江,既是云南的母亲河,同时也可是称之为电力之江。
作为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是金沙江上的第一个码头。轮船的出现,让金沙江在水富的浪花具备了特别的意义。在汽笛声里,云南人顺流而下,经过宜宾、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正在用敞开的胸怀来拥抱。云南通往世界的路,从水富开始,就变得畅通起来。世界从水富开始,亲切地注视云南,倾听云南。
涛声里的金戈铁马
滇西北其实是一个不平静的地方。在许多人眼里,因为山重水复,这里往往会被当成一片人迹罕至的烟瘴之地,只有虎狼蛇蟒出没其中,而无笙舞弦歌隐约其间。是的,当人们把回顾的目光投向中原和江南,在黄河与长江的两岸,数千年以来,战争频繁,硝烟弥漫,刀来剑往,一个王朝被推翻,另一个王朝又粉墨登场,在旌旗与诏诰的掩蔽下,多少人成为英雄,多少人成为败寇,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筑起了另一些人的名垂青史。而在滇西北的金沙江边,似乎一直都是那些涛声,那些群山和田畴。但是,这仅仅是一些陌生人对一个陌生地域的陌生判断。事实上,这里从来都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几个相对固定的政治势力之间,演绎着你争我夺的征战与杀伐。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在匈奴横亘在河套以西阻断西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的情况下,中原地区似乎已经失去了西向的通道。但是,在西域,张骞在大夏国看到了从中国四川地区传出去的蜀布、邛竹杖。张骞因此判断,中国南方还有一条通往印度、波斯的路。于是,为了打通这条从南方通往西域的路,汉武帝便派军南下,然后向着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进发。大汉王朝的势力抵达了云南,再没有西去,却拥有了一片新的领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设置越嶲郡,该郡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大部分,乐山市和雅安市的西南部,攀枝花市,云南省丽江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一部分。金沙江边的这一方土地,便成了越嶲郡的一部分,被纳入了西汉帝国的版图。作为一个又一个王朝的边疆,金沙江的两岸,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有着刀光剑影时隐时现。
战争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在金沙江边,向北,是庞大的中央王朝,向南,则是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部落。地方与中央,驯服与对抗,如同潮水此消彼长。在诸葛亮写下的那篇著名的《出师表》里,他曾经写下“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话。这里所说的“泸”,就是金沙江。在那个战火四起的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了稳定蜀国的大后方,率领大军,分别从现在的四川西昌、宜宾,贵州毕节兵分三路,征讨云南地方少数民族势力。大军所向之处,金沙江首当其冲成为天堑,横亘在军队的进与退之间。一时之间,被金沙江环绕的云南北部战火四起,虽有彩云南现,密林遮掩,却无法挡住刀光剑影投射在云南大地上的印迹。在云南,诸葛亮麾下的蜀军手握刀枪剑戟,孟获的勇士身披藤甲重铠,展开了地方与中央的较量。将近2000年过去了,谁也无法看见当年的战争经历了怎样的冲锋与败退。但是,通过发黄的史籍,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几次战役之后,“七擒孟获”成为一个歌颂战神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美谈。金沙水拍,云崖耸峙,两岸众多以“诸葛”二字外加一些寨、坪、坡等山地特征的地名,滞留在了距离金沙江边不远的山水之间,见证了那场战争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之后的依稀记忆。
战争是让一个地方得以繁荣稳定的特殊方式。金沙江在云南北部的存在,似乎又是一把开启群山之门的钥匙。在那个漫长的冷兵器时代,谁控制了金沙江边的那些渡口、驿站和关隘,谁就有了向着更加深远的地方渗透的优势。在滇西北,在长江第一湾石鼓,金沙江更是印证了这个规律。从隋唐时期开始,云南地方先后兴起了南诏、大理两个雄踞一方的政权。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北方雪域高原的吐蕃政权和东方不断更替的中原王朝。三者各自虎视眈眈,只要有一方力量减弱,便有另外二者结成联盟兵戎相见。这里的土地,见证了铁蹄、箭镞、刀剑的撞击与厮杀,见证了伤口、鲜血、死亡的呈现与隐没。在王朝更替的时候,这里成为疆场,承载两支军队的攻与守。也正是这样的特殊环境,各方政治势力彼此都不能以压倒性的优势取代对方,便只能借助金沙江边的本土势力彼此制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纳西族人充分发挥了战略要地的特性,既在几个强大政权的夹缝里寻找自身的利益,更在左右逢源的战略中得到了锻炼,历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因此而成为滇西北重要的地方势力,并且在兼容并蓄中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纳西族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居住在金沙江边的纳西族,与洱海之滨的白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而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纳西族甚至是木氏土司,却又对从雪域高原流传下来的藏传佛教无限景仰。同时以“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的忠诚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承担起了为国家镇守边疆的重任。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样的格局也曾经一度被打破。来自遥远的天边的某一支军队,一旦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历史便会被改写。
由唐至宋,金沙江边相当大一片区域曾经长期作为南诏、大理政权的北方边界。无论是“唐标铁柱”的对抗,还是“宋挥玉斧”的冷静,金沙江流域及其南方的土地,始终在南诏、大理的事实管辖范围内。这时候,在石鼓这个号称长江第一湾的地方,吐蕃的势力与南诏、大理的势力在这片被金沙江涛声拍打着的土地上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这种情形,直到元朝时期才被改变。南宋的时候,蒙古人在北方草原兴起,并且逐渐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族。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军事奴隶制的蒙古汗国,展开了它作为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横扫亚欧大陆的征战与杀伐。1234年,蒙古灭金国之后,消灭南宋入主中原之事就被提到了日程上来。蒙古贵族采取先征服西南诸番,而后南北夹攻南宋的战略。为此,他们必须事先征服大理。 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直指云南。中路由忽必烈亲自率领,南下过大渡河,西向金沙江,进入丽江东部,再南攻大理。这一年9月,忽必烈率军到达金沙江西岸,命令将士杀死牛羊,塞其肛门,“令革囊以济”,做渡江之用。他们在石鼓镇一带长达数十里的江面上,分别从石鼓、奉科、巨甸等地渡江后入丽江。这就是昆明大观楼长联里“元跨革囊”典故在大地上的真实所在。在大军压境的时候,丽江纳西族首领麦良显示了面对大势所趋时的智慧,选择了投降。金沙江的天堑并没有跟以往一样作为天然屏障,为了一个地方政权的苟延残喘而拼死挣扎,金沙江的滩涂也没有用血流成河的所谓悲壮去抵抗一支强大的铁骑和一个帝国的统一大业。麦良的开门迎降,加速了大理国的覆灭。元军渡过金沙江后一路所向披靡,大败大理守军,最后得以从云南一路东去,抄了南宋王朝的后路,直至把南宋的最后一个小皇帝逼到大海边,由老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自尽。
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的那场世所罕见的万里长征,再次把古老而宁静的石鼓小镇揽入改天换地的历史旋涡中。1936年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率领的二、六军团,紧跟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经历了国民党军队一路的“追剿”之后,这支红军从云南东北部艰难前行到了滇西北。一路上,他们一次次试图渡过金沙江,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沿着金沙江逆流而上,沿途寻找渡江的机会。终于,他们兵分两路,分别从大理和丽江抵达石鼓这个兵家必争之地,4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这里渡江北上抗日,石鼓镇因此成了中国著名的红色渡口。
忽必烈革囊渡江不仅仅是在石鼓古镇。在丽江北面,金沙江如同一条巨蟒钻进了群山,一路上形成了悬崖峭壁与深谷激流的映照与反衬。江水的阻隔、群山的屏障,使得这里的地势异常险峻,一个城堡或者一个关隘,往往可以扼守数十里的疆域。宝山石头城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浪花四溅、峭壁四布的金沙江边,宝山石头城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从远处看,整座城都建在一块独立的蘑菇状的巨大岩石上,它的四壁非常陡峭,即使是猿猴也难以攀爬上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里的居民因地就势,在巨石的四周加筑了一圈五尺高的石墙,使石城更易防御和掩护,整个宝山石头城只有前后两道门可以出入,关上城门就成了万无一失的安全岛。早在唐朝的时候,纳西族的先民们从北方迁徙到这里,开始了他们在丽江这片宁静的土地上的生活。他们不畏艰险,运用当地现成的石头,修筑石级梯田,从峡谷深处层层修筑,直达距河谷两三千米的高坡。在石头城里,民居群落全部随岩就势,有的柱磉桌凳等均用天然岩石稍加修琢而成,有的凿厨中巨石为灶,有的把庭院中的巨石凿成水缸,有的甚至将房中巨石修凿成石床,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中路军经四川过大渡河挥师南下,分别在金沙江的“木古渡”和“宝山”乘羊皮革囊和筏子横渡,从宝山渡过来的元军就驻扎在宝山石头城。在元代的时候,云南设立了中书省,这里便设立了宝山州府。到了清代,宝山州撤销了,这里便由州不断地降格,最后成了一个自然村。如今,石头的屋子盛满了他们所有的日子,石头围着的庄稼,支撑着他们的饱暖;石头的床,使他们的梦想,在滇西北的深夜里,向着天堂展开。
玉壁金川纳西人
20世纪8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提出过“藏彝走廊”的概念。这个著名的人类学理论指出: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流经的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印度北部,是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怒、独龙、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佤、布朗、德昂、苗、瑶等数十个民族数千年以来繁衍生息和迁徙流动的一条大通道。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雪山、冰川、高原、盆地、河谷、森林、湖泊、江河遍布其中,并且纵跨寒带、温带、热带等几种气候,形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纷繁复杂的条件,造就了这一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民族多元化,因此,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认为:藏彝走廊地区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少有的生物资源的基因库,更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库。自从有人类活动以来,藏彝走廊地区一直是各民族南来北往的大通道,他们沿着江河的流向,顺着山脉的走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时而风起云涌,时而风轻云淡,不断流动、融合、变化,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民族生态群落。
金沙江边的丽江古城,便是藏彝走廊上的纳西族在遥远的岁月里建起来的一座流溢着古老而灿烂的民族文化神韵的高原城市。
伴随着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的金沙江的涛声,纳西族的祖先们逐水而来,最后在滇西北金沙江流域停下了继续前行的脚步,终于在这片川滇藏交界处的高原上栖息繁衍。如今的纳西族,分布在金沙江流域的云南丽江、迪庆、大理和四川盐源、木里以及西藏的芒康、察隅这一片广阔的区域里。纳西族与雪山、密林、滩涂、草地、山谷融为一体,以丽江为中心聚集区,向着四方扩散。虽然时光早已老去,他们的来时路已经成为一个个陌生的地理名词,但是,在纳西族古老的《神路图》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在那段漫长而遥远的岁月里,正是那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名,珍珠一样穿起了纳西族曾经从他们的发祥地由北向南千里跋涉的身影。时到如今,在丽江,在金沙江边的那些古朴的纳西族村寨里,某个老人离开人世的时候,纳西族的东巴祭师往往会念起指路经,让逝者的灵魂在祭师的指引下,沿着祖先们当年一路迁徙的路,回到那个早已模糊了的起始地。
金沙江在丽江转了一个弯,折身东去,却把纳西族留在这片土地上。金沙江离开之前,在这里留下了太多让纳西族世代珍惜的东西。
玉龙雪山是纳西人的神山。纳西族的先辈们一路迁徙来到这里,便守着这座高达5596米、地球上纬度最低的雪山,与它魂梦相依,再也没有离开过。在纳西族的《创世纪》里,纳西人的始祖崇忍利恩先后娶了两位天女为妻,美丽的竖眼天女生下了动物生灵,贤惠的横眼天女生下了人类三兄弟。从此,人与自然便在玉龙雪山的怀抱里相亲相爱。相爱的人们,当他们幸福安康时,就把风调雨顺的祈祷献给玉龙雪山上的神灵。当他们爱情受挫时,便相约到雪山脚下的蓝月谷、云杉坪,穿上最美的衣服,带上最好的食物,唱着情歌,无忧无虑地过上几天倾情相爱的日子,然后彼此殉情,不带一点遗憾地死去。
纳西族在金沙江流域生活的数千年时光里,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东巴教。从事这种宗教祭祀活动的人,被称为东巴,他们所使用的经书,被称为东巴经。在金沙江流域的群山里,纳西族村寨散布在江边、林间、山谷、坡地。相对于中原和江南地区,这里的生活是平静的、安详的。在东巴的诵经声里,在东巴经卷上,一种原始宗教出现了。每一片土地上都有神灵生活着,每一种生灵都具备了神性,每一个山头都居住着神。数以万计的东巴经书,被纳西村寨里的东巴们世代相传,形成了浩如烟海的经书世界。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东巴们所珍藏的东巴经书,究竟有多少,谁也没有统计过。直到1999年,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所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遍及世界各地的东巴经书的海洋才向世人展露出冰山一角。如今,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各地,便发现,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瑞士等国家的图书馆里也珍藏着成千上万的东巴经书。与此同时,在金沙江流域的纳西族村寨,还有多少东巴经书,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精准的答案。就是这样,纳西族把金沙江流域当成了他们在大地的图书馆,用年复一年的现实生活去创造一个民族的历史,收藏一个民族的文化。于是,在东巴经里,我们看到了纳西族对于天文、气象、时令、历法、地理、历史、风土、动物、植物、疾病、医药、金属、武器、农业、畜牧、狩猎、手工业、服饰、饮食起居、家庭形态、婚姻制度、宗教信仰,乃至绘画、音乐、舞蹈、杂剧等多么庞杂、多么丰富、多么深刻的想象、叙述、见解和判断。东巴教就是纳西族的灵魂里的金沙江,而那些用树皮制成的每一本东巴经书,每一个象形文字,都是被时光的尘沙隐藏着的人类智慧的金子。
数千年前,纳西族的祖先们渡过金沙江,在玉龙雪山脚下放缓了脚步,他们围绕着雪山,在一个个水丰草茂的地方放牧、耕耘、打猎、放鹰、收获。于是,他们在距离雪山很近的地方,建起了一个个村落。随着村落渐渐在纳西人一代又一代的居守中渐渐变得庞大,街道、店铺、客舍都出现了。纳西人在雪山的注视下最初建成的城郭叫白沙。后来,纳西人像一群玉龙雪山的孩子,在雪山的注视下慢慢地向着丽江盆地的南方迁移,在一个叫束河的地方建起了他们新的城郭。这时候,茶马古道已经兴起,从南方远道而来的马帮在这里停下来,休整、饮食、交易、浅睡,然后离去。束河的石板路一天天被到来或者离去的马蹄踩得越来越光滑,束河也就成了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驿站。纳西族的商人们随着马帮远去,中国西藏、缅甸、尼泊尔、印度,都留下了从束河出发的纳西族商队的身影。沿着茶马古道,纳西族渐渐地成了一个经商民族,当白沙和束河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另一个城郭又产生了,那就是现在的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是纳西民族在滇西北地域性政治格局中不断壮大起来的产物。在古城里,纳西族木氏土司建起了属于自己权力象征的府邸。在被徐霞客形容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里,历代木氏土司一边在古城里与往来的客商做生意,一边平衡南诏、大理与吐蕃的南北冲突,一边接受中央王朝的诏令征讨各方,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控制领域,形成了一个涵盖滇川藏交界地区的地方势力版图。当然,纳西民族在金沙江边上千年的繁衍与发展,绝不仅仅是放牧、狩猎、经商、杀伐,除创造了象形文字和东巴经,纳西族还形成了自己在诗词歌赋里的精神世界。最初的,最遥远的,最闪耀的,是谁?历史告诉我们,纳西族的文人是一代又一代木氏土司,其中木泰、木公、木高、木青、木增、木靖6人成就最为卓著,被后人尊称为木氏六公。《明史·土司传》里说:“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在木氏土司的激励下,生活在丽江古城里的纳西族民众里产生了一群文人,他们读书、写诗、画画,丽江古城因此也就有了“大砚”的别称。是的,丽江古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除了红尘里的世俗生活,还特别注重对生活品位和生活情趣的追求。最纯净的雪山之水,流进丽江古城里,在纳西族用800年的时光厮守的古城穿街过巷——清澈的水缓缓地流过,阳光下闪烁的波光,收藏了岸上飘飞的柳絮,收藏了马帮载着货物匆匆而过的身影,收藏了坐在低矮的店铺屋檐下恬淡的眼神,收藏了纳西族东巴祭司低回的诵经声。暮色渐浓的时候,丽江古城里水声渐淡,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小城,炊烟四起,歌声远溢,千年如一的安详,又呈现在了纳西族人梦境里。这样的生活,他们从遥远的岁月里一直延续着。
这种宁静的生活也曾经被打断过。1996年2月3日,一场罕见的大地震降临在丽江古城,试图冲断丽江古城从远古向着未来流淌的血脉。但是,纳西族作为“大江大河吸干后不解渴者的后代,三袋炒面一口吞下不呛的后代,三根腿骨一口咬断牙不碎者的后代”,不仅很快地在废墟上建设了一个新的古城,还在1997年12月将丽江古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6月,“三江并流”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同年9月,纳西族东巴古籍被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如今,在丽江古城的生活,许多人用一个特别美好的词来加以形容:柔软时光。如今的丽江古城,每一天都用它的从容与恬淡,敞开怀抱去接纳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客。在滇西北的阳光里,丽江古城总是很温暖的,就像那些古城僻静的街道上缓慢地行走着的纳西老人们沉静的目光。阳光从古城曲曲折折的流水里反射到低矮的木质房屋的门面上,让那些鲜嫩的花朵,显露出高原地带特有的醇厚与纯朴。人们在迷宫一样的街道上慢慢地走着,那些陌生的面孔,闪动的目光里满是新奇的神色。窄窄的街道上,老人们夹杂在众多的行人起起落落的脚步声里,那背影呈现出来的拙朴的民族服装,充满了神话色彩的披星戴月的羊皮褂,藏青色的布帽子以及长长的飘带,吸引了关注的目光。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游人,泡吧、晒太阳、发呆,把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光和生命,托付给了丽江古城,迟迟不愿离去。终于,在无数次回首中离开了,马上又掐算着日子,在飞机、火车上,向着丽江古城飞奔而来。丽江,又用它的柔软时光,给每一个人呈上一份梦里梦外的安详与宁静,茶一样清淡,阳光一样温暖。
远去的彝汉同辉
金沙江在中国西南地区流淌,从横断山区到乌蒙山区,它的众多支流仿佛叶脉,深入幽深的群山里,形成了一个形同榕树叶片一样的广阔区域。它横跨滇川黔三省,每一座极不起眼的山里,村寨星星点点散布其间,寨边苦荞地四面铺开,寨外马樱花怒放。这条古老的金沙江及其支流从西向东,弯弯曲曲地流淌着。而在这个流域的群山里,一个个古老的民族如同山间的繁花,在幽暗的时光里生生不息,其中,是具生命力的,便是与金沙江同样古老的民族:彝族。
金沙江从丽江继续流淌前行,两岸又是高耸的、炎热的金沙江河谷地区。生活在金沙江两岸的彝族人,用他们古老的历史见证了金沙江千年不息的流淌。彝族人就居住在金沙江边的群山里,凡是苦荞地铺开的山坡,都有彝族人在耕种、歌唱。凡是马樱花怒放的林间,都有彝族人的舞蹈、祈祷。传说中彝族人共同的老祖宗叫阿普笃慕,他的后代从洛尼山走向四面八方:老大慕雅枯和老二慕雅切率领武部落和乍部落向云南的西部、南部和中部发展;老三慕雅热和老四慕雅卧率领糯部落和恒部落沿着金沙江流域进发,逐渐到达现在的大、小凉山和四川南部;老五慕克克率领布部落在云南的东部、东北部,以及贵州的兴义、毕节一带发展;老六慕齐齐率领默部落则到广西的隆林一带发展——这便是彝族六祖分家的传说。六部在各地生根发芽,繁衍成今天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传说是遥远的,而稍微近一点的,便是彝族人建立的一个王国——南诏国。在距离金沙江不远的巍山县,曾经是彝族首领皮罗阁于公元738年建立的南诏国的都城。南诏国作为云南大地上崛起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它的势力重心主要集中在金沙江流域。这个国家凝聚了金沙江流域彝族各部落的力量,向四面八方宣示了一种政治力量的存在。随后,于公元937年在洱海水滨建立的大理国,同样是以金沙江流域作为它的政治力量的核心区域,彝族作为这个区域举足轻重的本土民族,为大理国数百年的存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使得大理国成为与唐、宋两大王朝并存的政权,曾经辉煌一时。
云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经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但这种状态从明朝的“洪武调卫”开始,改变了:从明朝开始,云南成了汉民族占大多数的地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平定内地以后,先后五次遣使到元朝最后一块根据地云南,试图招降元梁王匝剌瓦尔密,均告失败。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等人率军平定云南,明军出四川、过贵州、进云南,沿着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的路线,历时近一年半时间,云南梁王政权和大理段氏政权被初步平定。
为了加强云南边疆稳定,朱元璋从洪武十五年(1392年)开始在昆明建云南左卫,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在金沙江边的永胜县设立澜沧卫,先后设置军事卫所40余个。平定云南的数十万明朝驻军以军事屯垦的方式,在东起贵州威宁,西南至腾冲,南抵越南屯守,营寨遍布云南各地关津要隘。与此同时,作为明王朝驻守云南的最高首领,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为配合军屯的巩固与发展,在云南境内全力实施民屯制度,先后从江南地区迁移地主富户、旺族大姓、贫民罪犯等四五百万汉族民众,以民屯的形式,远赴云南,在遍及全省的各卫所附近,屯边垦殖。仅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就有湖南、江西、湖北等地人民200余万迁入云南。3年后,又从南京迁移30余万人开发云南。随着大量屯边民众一起进入云南的,还有一些商人,他们是因为云南丰富的盐矿资源而被招募随军抵达的。这些盐商进而在内地招募佃户,以商屯的形式在云南黑井、大姚、安宁、云龙等地冶盐、垦植,一方面补充了云南驻军的军费,另一方面也为内地提供了大量的盐源。在云南,在金沙江边,开始大量地出现了汉语,汉服,汉族的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边疆稳定之后,这些遍布云南各地的汉族军民,把他们崇尚文化、知书识礼的古老传统也带到了云南这片繁花似锦的沃土之上。在元朝以前,只有靠近各路、府、州、县的白族和少部分彝族上层人士才不同程度地吸收汉文化。但是,从明朝开始,朱元璋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发出榜文,要求云南各地都与中原内地一样设置官方学校,优选本地有名望学识的文化人担任学官,大力培育地方读书人。永乐年间,云南各地普遍设立社学,各民族可以通过科举制度,到内地做官。洪武年间到云南屯边戍守的汉族军民的后代,从此又凭借着他们的聪明才智,进入内地,宦游四方,一个书香云南开始形成了。从此之后,金沙江的浪花,开始呈现诗词歌赋的韵味。
波光洗涤过的远途
作为云南境内极为重要的一道自然屏障,金沙江对于许多往来于云南与内地的人来说,具有双重意义——祖国内地进入云南主要有三个入口,一是从贵州经胜境关进入滇东曲靖抵达昆明;一是从四川宜宾经滇东北五尺道进入昭通抵达昆明;一是从滇西北的攀(攀枝花)西(西昌)大裂谷经永胜到大理。后二者都必须渡过金沙江。千百年来,很多人从金沙江上经过,有的人到了云南就停止了,有的人则继续前行,或者沿红河而下,从蒙自出境到越南;或者由大理经保山腾冲出境到缅甸,或者由丽江迪庆进藏区到印度。金沙江,总是万里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涛声远去的时候,人们身后从此就是关山重重,异乡漫漫。
从丽江往东、往南,沿着金沙江的流向,盆地越来越多,人烟也随之而越来越稠密。人类在大地上的行走,因为江水的阻隔,必然会有桥出现。在金沙江上,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向着丽江走来,在一个叫梓里的地方,被迎而横亘的金沙江挡住了。清朝光绪二年(1876年),贵州提督蒋宗汉私人捐资10万银圆开始在这里建桥,历时5年以后,桥建成了。于是,在这里,金沙江上有了一座桥:梓里桥。这是金沙江顺流而下的路上第一座古老的铁链桥。18根手工锻制的大铁链横跨在92米宽的江面上,悬系两岸,往来的人们,从此不用再悬挂在藤索上经历穿云破雾的危险,也不用再置身于渡船中经历惊涛骇浪的颠簸,更不用再身系羊皮革囊只身涉水而经历命悬一线的恐惧。从古至今,人们从成都、重庆、宜宾跋涉重重远山近水而来,在这里踏上桥头,他们的双脚平稳地踩在平整的桥板上,沐浴着江风,从从容容地走过江去,然后一步步走向中国丽江、大理、西藏,缅甸,印度。这座桥,因此而成就了它“万里长江第一桥”的古称,不是因为最宽,也不是因为最长,更不是因为最现代化,而是因为它最早解决了人们最迫切的难题。
从梓里铁链桥由南往北顺流而下,金沙江在一个叫太极的村庄正式向着东方流去。太极这个地名,是因为金沙江在这里转弯,江水与四周的群山之间形成了一个彼此环抱的回环,酷似一个由山与水构成的太极图,山坡为阳,水湾为阴,互为依托。在这里,人们借着舟楫之便往来于江上。金沙江再往下流淌三四十公里,与一条南北走向的峡谷形成了“十”字交叉,便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渡口。由滇西北的攀(攀枝花)西(西昌)大裂谷经永胜渡金沙江到大理。从永胜县境内的金沙江边渡过江去,大理古国便隔江相望了。自古以来,人们或负担,或骑乘,或驱车,在江边停下来,一叶小木船,载着三五个人,在江水里行进。到了对岸,下船,上路,离开。江涛里,两岸都是在炎热的江风里疯狂地生长着的水稻。稻田里隐隐可见的小路,引导着一些人南来北往,出去,或者回来。因为古渡口就在江边,人们排开了太多的繁华与喧嚣,给它取了一个朴素的名字:金江古渡。它很早以前就存在着,当人们渐行渐远,也许有过回望,也许是沉默不语。伤感或者喜悦,转瞬之间就消失了,只有一川江水,曾经目睹过,听见过。这个金江古渡,我们如果从北方把视线投向南方,这里便只是一个遥远得难以抵达的僻壤幽渡,谁也不会想象出它太多的价值和意义来。但是如果从南往北,这里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在金沙江的南岸,便是大理古国的腹心地带,到大理古国的都城仅仅有100公里左右的路程。金沙江这道天堑便成为大理古国与历代中原王朝暗中博弈的“边关”重地。金沙江边军情的风吹草动,在都会让洱海边王城里锦衣玉食的那个人寝食难安。直到后来,元朝铁骑统一云南,把这片彩云之南的土地纳入中央版图,使云南成为大元帝国的一个省,至此,金沙江在这里的渡口,真正成为中央王朝内流河上的小点,它的河床不再是疆界,它的涛声也不再是号角。往来于金江渡口的人们,往往是为了他们各自生命里的奔波与忙碌。曾经的明朝状元杨慎在北京因为“议大礼”的事件触怒当朝皇帝,被流放云南,便在这里往返于江上,流连于云南山水间,发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慨叹。如今,历史的尘烟早已散去,金沙江两岸已经成为世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只有距离金江古渡口不远的佛教圣地鸡足山上的佛像,年复一年地见证着人们在红尘俗世里从不停止的奔忙。
金沙江一直往东流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从一片幽暗的群山往视野开阔的地方一路奔涌。在云南的东北部,乌蒙山成为一道关隘,如同沉重的大门,把云南屏蔽起来。金沙江在乌蒙山区的流淌,更是让那些进出云南的人面临难以想象的艰险。再艰难,也会有路翻山越岭、渡江涉滩而来。大秦帝国初步实现了全国大一统,一条狭窄的道路便从乌蒙山外面向着云南境内延伸进来。这条道路,以石板、石块、石门等方式,在云南的大地上弯弯曲曲地前行,一路上的山梁、村庄、田野、丛林,都被这条路穿起来,如同时光里的珍珠,虽然一次次更换名称,但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条路,与秦帝国“车同轨”的革命同步,始终保持着五尺的宽度,云南人都称之为“五尺道”。在乌蒙山里,金沙江与五尺道展开了一场岁月之战。金沙江借助乌蒙山的峰峦叠嶂阻拦再阻拦,五尺道借助人的脚步突破再突破。这条路支撑着那些脚步,在风霜与星月的陪伴下,进入云南之后便向着四面八方延伸。那些秦人、汉人、唐人、宋人,草鞋布衣,骡马舟车,千百年来步步向前。金沙江出了云南,便一路远去,向着遥远的东方,以长江的名义抵达大海。那些消消涨涨的浪花,还会记住群山之中的云南吗?
原刊于《十月》2020年1期

陈洪金,云南永胜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十月》《散文》《散文选刊》《新华文摘》《大家》《山花》《天涯》等,出版《陈洪金文集》(5卷)等20部。曾获得新浪网“万卷杯”全国原创文学大奖赛“最佳抒情散文奖”、台湾首届“喜菡”散文奖、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散文奖等奖项,有作品入选大学教材,中学教辅读物、高考模拟试卷。现供职于云南省丽江市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