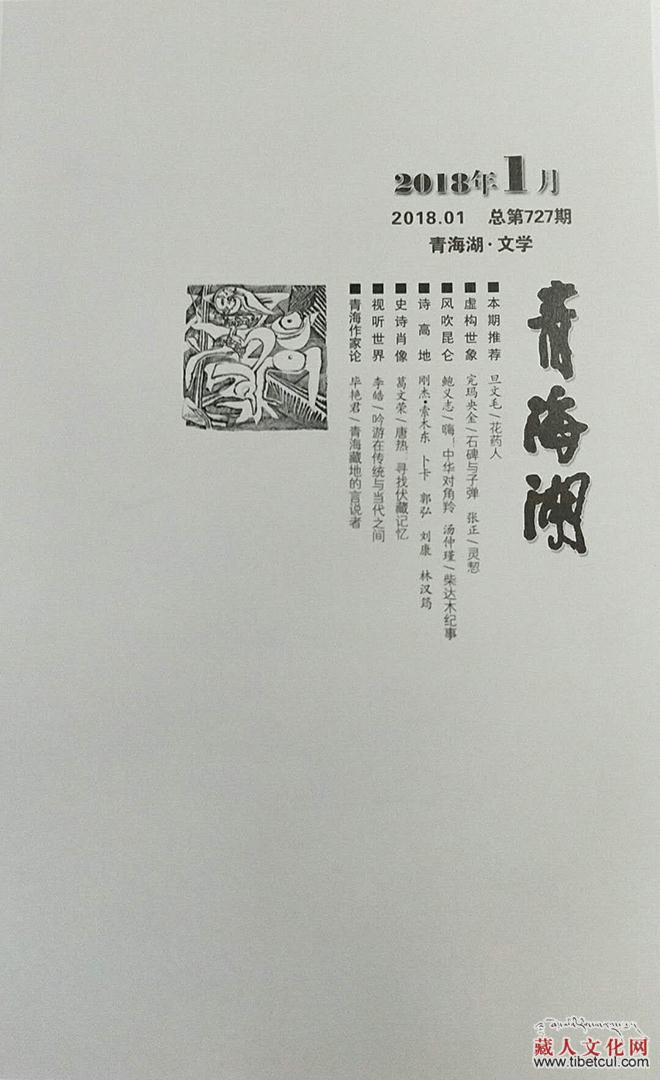
У║ФтГљт║ЋСИІтЈЉтЄ║уџёСИђСИфтЊЇС║«тБ░жЪ│№╝їТііТѕЉТЃіжєњС║єсђѓТѕЉуЮЂт╝ђую╝уЮЏ№╝їС╗┐СйЏТў»ж╗јТўј№╝їС╣ЪтЈ»УЃйТў»тѓЇТЎџ№╝їТђ╗С╣І№╝їтЁЅу║┐тЙ«т╝▒№╝їС╗јУњЎуЮђТ╣ќУЊЮУЅ▓уфЌтИўуџёуј╗уњЃуфЌСИіТіЋУ┐ЄТЮЦсђѓТеАу│іСИГ№╝їТюЅтЄаСИфС║║уџёжЮбтГћтюеую╝тЅЇТЎЃтіе№╝їТў»тЄаСИфтЦ│С║║№╝їТЇ«У»┤Тў»ТѕЉуџёжў┐тЕєсђЂтцќжў┐тЕєсђЂТ»ЇС║▓сђѓтЦ╣С╗гСИђжйљугЉС║є№╝їС║ЅуЮђУ»┤№╝џтеЃжєњС║є№╝їт┐ФТЮЦуюІ№╝їтеЃжєњС║є№╝Ђ
ТѕЉтЄ║ућЪтѕџтѕџтЇЂтцЕТѓБС║єТќ░ућЪтё┐Уѓ║уѓј№╝їСйЈУ┐Џтї╗жЎб№╝їу╗ЈУ┐ЄТ▓АуЎйтцЕТ▓Аж╗ЉтцюуџёУЙЊТХ▓№╝їТўетцЕСИітЇѕтЄ║жЎбтЏъС║єт«ХсђѓТѕЉтЙѕу┤»№╝їтЙѕуЃдУ║Ђ№╝їУ║║тюеТИЕТџќтјџт«ъуџёТБЅУбФжЄї№╝їжЌГСИіую╝уЮЏ№╝їСИђуЏ┤уЮАтѕ░уј░тюесђѓТѕЉуџёуѕИуѕИтцфт╣┤Уй╗С║є№╝їТЅЇ20т▓Ђ№╝їС╗ђС╣ѕжЃйСИЇТЄѓ№╝їТ▓АСИфт«Ѕуе│уџёТЌХтђЎ№╝їТЋ┤тцЕСИЇуЮђт«Х№╝їУ┐ўТЌХСИЇТЌХтЂџуѓ╣У«Ежў┐тЕєтњїТ»ЇС║▓у▓ЙуЦътЈЌтѕ║Т┐ђуџёС║ІсђѓТѕЉуџётЄ║ућЪС╣Ъу╗іСИЇСйЈС╗ќуџёУёџ№╝їУ┐ЎСИЇ№╝їтЇЂтцџтцЕтЅЇУ┐ЏС║єТІўуЋЎТЅђ№╝їтѕ░уј░тюеУ┐ўТ▓АтЄ║ТЮЦсђѓтї╗жЎбжЄї№╝їТѕЉТў╝тцютЋ╝тЊГ№╝їтЙѕтцџТЌХтђЎТў»тюетЉ╝тќіуѕИуѕИ№╝їСйєТ▓АС║║ТўјуЎйсђѓТ»ЇС║▓жЌ«тцДтцФ№╝їтцДтцФТЃ│жЃйТ▓АТЃ│У»┤№╝џу╝║жњЎсђѓУЎйУ»┤УЄ│С╗іТѕЉУиЪуѕХС║▓Т▓АТЅЊУ┐ЄуЁДжЮб№╝їтюеТ»ЇС║▓УѓџтГљжЄїТ▓ЅТ▓Ѕуџёж╗ЉТџЌСИГ№╝їтЄГу╗єтЙ«ТЋЈжћљуџёТёЪУДЅ№╝їТѕЉти▓у╗ЈжЮътИИуєЪТѓЅС╗ќС║єсђѓТѕЉтѕџтЄ║ућЪжѓБС╝џтё┐№╝їУбФтїЁУБ╣тюеуѕХС║▓уџёСИђС╗ХТЌДУАгУАФжЄї№╝їуѕХС║▓уџёТ░ћТЂ»ТхИжђЈС║єТѕЉуџётЉ╝тљИсђѓТѕЉжџЙтЈЌтЙЌУдЂтЉй№╝їтЈЉуЮђжФўуЃД№╝їтў┤тћЄУхиС║єуџ«№╝їтц┤С╣Ъуќ╝тЙЌтјЅт«│№╝їТѕЉТИ┤ТюЏуѕХС║▓уџётцДТЅІТІЅТІЅТѕЉуџёт░ЈТЅІ№╝їС╝ажђњу╗ЎТѕЉућитГљТ▒ЅуІгТюЅуџётіЏжЄЈсђѓ
ТѕЉуџёжў┐тЕєсђЂТ»ЇС║▓ТъЂТюЅт┐ЇУђљС╣Іт┐Ѓ№╝їСйЈжЎбТюЪжЌ┤тЦ╣С╗гтў┤жЄїТЋ░УљйуЮђуѕИуѕИ№╝їуЎйтцЕТЎџСИіУй«ТхЂТі▒ТѕЉтюетю░СИіУйгТѓасђѓ
ТѕЉт░йТюђтцДуџётіфтіЏ№╝їуЮЂт╝ђУ┐ўтцётюет╝▒УДєжўХТ«хуџёую╝уЮЏуюІТѕЉуџёжў┐тЕєсђЂтцќжў┐тЕєтњїТ»ЇС║▓сђѓТѕЉуџётцќжў┐тЕєую╝уЮЏжЄїТ│фтЁЅжЌфжЌфуџё№╝їУѓ»т«џтЈѕТў»тюеС╝цт┐ЃжџЙУ┐ЄС║єсђѓтЦ╣жџЙУ┐ЄуџёТў»Т»ЇС║▓ућЪТѕЉТЌХ№╝їТѕЉуџёуѕИуѕИСИЇтюеую╝тЅЇСИЇУ»┤№╝їУ┐ўтюеТІўуЋЎТЅђ№╝їСИЇуЪЦжЂЊС╗ђС╣ѕТЌХтђЎТЅЇУЃйтЄ║ТЮЦсђѓтцќжў┐тЕєућеУ░еТЁјтЈѕТђеТЂеУХ│УХ│уџёую╝тЁЅуюІуюІжў┐тЕє№╝їТЃ│У»┤С╗ђС╣ѕтЈѕТі┐у┤ДС║єтў┤сђѓтцќжў┐тЕєТЏ┤тіат┐Ѓуќ╝Т»ЇС║▓ућЪтГЕтГљС╗ЦТЮЦтЇЂтцџтцЕтЙЌСИЇтѕ░С╝ЉТЂ»№╝їуЎйтцЕТЎџСИіТђђжЄїТі▒уЮђтЋ╝тЊГуџёТѕЉсђѓт┐Ѓуќ╝ТѕЉтѕџТЮЦС║║СИќТ▓АтЄатцЕСЙ┐УдЂжЂГтЈЌуќЙуЌЁуџёуЌЏУІд№╝їТїежњѕТЅј№╝їт░ЮУЇ»уџёУІдтЉ│сђѓтћЅ№╝їУ░ЂтЈѕУ«ЕС║║С║║жЃйУ«▓СИѕС║║жЌетЅЇтЦ│тЕ┐теЃтцДтЉб№╝їтЈѕУЃйт»╣тЦ│тЕ┐У»┤тЈЦС╗ђС╣ѕ№╝ЪтЦ│тЕ┐СИіжЌе№╝їуЏўУЁ┐тЮљтюеуѓЋСИітќЮУїХ№╝їСИјУђЂУЙѕС║║ТЅ»жЌ▓У»Ю№╝їСИѕТ»ЇтеўУдЂтюетјеТѕ┐жЄїуЁ«УЁіУѓЅтїЁТЅЂжБЪ№╝їтєЇТііубЪтГљубЌСИђСИђуФ»СИіуѓЋТАї№╝їтЮљтюеСИђТЌЂ№╝їугЉтљЪтљЪтю░уюІС╗ќтцДтЈБтљЃтќЮсђѓую╝СИІТЮЦтѕ░С║▓т«ХжЌеСИі№╝їтцќжў┐тЕєуЪЦжЂЊУЄфти▒тЈфУЃйу«ЌСйюСИђжЌеС║▓Тѕџ№╝їСИЇтЈ»тцџУ»Г№╝їтЊфжЄїТЋбТїЉтЅћ№╝Ђтцќжў┐тЕєТў»УАїС╣АжЄїуџёУДёуЪЕ№╝їтюеТюѕтГљтЇЂтцЕСИіТЮЦТјбТюЏТ»ЇС║▓тњїТѕЉуџёсђѓ
ТѕЉуџёую╝уЎйтЈЉУЊЮ№╝їтї╗ућЪтЈѕУ»┤ТѕЉТѓБТюЅУ┤ФУАђсђѓТѕЉТ»ЇС║▓ућЪТѕЉуџёТЌХтђЎт░▒ТѓБТюЅСИЦжЄЇуџёу╝║жЊЂТђДУ┤ФУАђсђѓжў┐тЕєтњїтцќжў┐тЕєУ»┤№╝џтѕџућЪуџётеЃтеЃт░▒Тў»У┐ЎТаи№╝їжЋ┐жЋ┐т░▒тЦйС║єсђѓжў┐тЕєС╗гжџЙт«╣тцќС║║У»┤тГЎтГљуџёСИђСИЂуѓ╣тё┐СИЇТў»№╝їуЅ╣тѕФТў»жњѕт»╣тѕџтѕџтЄ║ућЪСЙ┐СйЈС║єтї╗жЎбуџёТѕЉсђѓтЦ╣С╗гт┐ЃСИГтЁЁТ╗Ауќ╝уѕ▒тњїтќюТѓд№╝їт┐ЇСйЈСИЇТ╗А№╝їТІ┐ую╝уџ«у┐╗у┐╗тї╗ућЪсђѓтї╗ућЪжА┐С║єжА┐№╝їУ┐ўТў»тЮџТїЂУ»┤№╝џтиЕУєютЈЉУЊЮ№╝їТюЅуѓ╣У┤ФУАђсђѓтЄ║жЎбтљјтцДС║║УдЂуЅ╣тѕФТ│еТёЈУљЦтЁ╗№╝їтцџтљЃу║бТъБсђЂуїфУѓЮсђЂУЈаУЈюсђѓтцДС║║тЦХТ░┤тЦйС║Џ№╝їтГЕтГљуџёУ║ФСйЊС╣ЪУЃйтЙЌтѕ░Тћ╣тќёсђѓжў┐тЕєС╗гУ┐ъУ┐ъУ»┤№╝џТў»№╝їТў»№╝їтЦй№╝їтЦйсђѓтаєУхиСИђУёИуџёугЉ№╝їТіітї╗ућЪжђЂС║єтЄ║тј╗сђѓ
ТѕЉуЮАС║єтЦйжЋ┐ТЌХжЌ┤№╝їТбджЄїУДЂтѕ░С║єУ«ИтцџС║║№╝їу╗ЈтјєС║єУ«ИтцџС║І№╝їтЇіуЮАтЇіжєњуџёуіХТђЂСИГ№╝їСИЇу╗ЈТёЈжЌ┤№╝їтљгжў┐тЕєУ»┤тЄ║ућЪтЇЂтцџтцЕуџёТѕЉУ┐ўтцётюетЅЇСИќжЄї№╝їТѕЉжЌГуЮђую╝уЮЏ№╝їСИђугЉ№╝їСИђжбд№╝їуџєТў»тюеУиЪтЅЇСИќжЄїуџёт«ХС║║ТЅЊС║цжЂЊ№╝їТюЅС║єжФўтЁ┤ТѕќСИЇжФўтЁ┤уџёС║ІТЃЁсђѓ
уџёуА«Тў»У┐ЎТаи№╝їТѕЉтюетЅЇСИќТў»СИђСИфУбФуД░СИ║жФўт╣▓уџётю░Тќ╣уггСИЅтЈиС║║уЅЕсђѓтЇЂСИЃтЁФт▓ЂТЌХУбФС║║ТіЊти«тј╗у╗ЎжЋЄтјІС║єтцДТђ╗у«АуџёУДБТћЙтєЏждќжЋ┐жђЂС┐АсђѓУДБТћЙтєЏтюеТђ╗у«Ат║южѓИ№╝їСИђСИфС║║тюетцДжЌеСИіуФЎт▓Ќ№╝їтЈдТюЅтЇЂтЄаСИфС║║ТѕќтЮљТѕќуФЎтюетцДжЌетЈБтЄаТБхуЎйТЮеТаЉСИІ№╝їТЊдТъф№╝їжЌ▓УЂісђѓУ┐ўТюЅтЄаСИфС║║ТІ┐ТюЏУ┐южЋютљЉУ┐ютцёУДѓТюЏсђѓуФЎт▓ЌуџёУиЪТѕЉСИђУѕгтцДуџёт░ЈС╝ЎТііТѕЉтИдУ┐ЏжЎбтГљ№╝їУ┐јжЮбСИцт▒ѓтюЪТЦ╝№╝їт║Ћт▒ѓтЄатц┤ж╗ЉуЅЏтюетљЃт╣▓УЇЅ№╝їТѕЉС╗гСИіС║єуфёуфёуџёТюеТЦ╝Тб»№╝їТЮЦтѕ░ждќжЋ┐УиЪтЅЇсђѓждќжЋ┐ТјЦУ┐ЄС┐АуюІС║єуюІ№╝їжЮътИИжФўтЁ┤тю░ТІЇС║єТІЇТѕЉуџёУѓЕУєђ№╝їтЊѕтЊѕугЉуЮђУ»┤№╝џт░ЈС╝ЎтГљ№╝їУ░бУ░бСйа№╝ЂСйатИдТЮЦС║єтЦйТХѕТЂ»№╝ЂТѕЉС╗гжЕгСИіт░▒ТюЅтљјТЈ┤С║єсђѓжѓБТў»СИфуДІтљјуџёТИЁТЎе№╝їжБјТа╝тцќтЄЅ№╝їТѕЉуЉЪуЉЪтЈЉТіќ№╝їждќжЋ┐У»┤№╝џтѕ░тјеТѕ┐тќЮубЌуЅЏтЦХтљДсђѓУ»┤уЮђУ«ЕУ║ФУЙ╣уџёжђџУ«»тЉўТІ┐у╗ЎТѕЉСИђтЈфубЌсђѓТѕЉуџёУѓџтГљТГБтюетњЋтЎютЎютЈФ№╝їТІ┐уЮђубЌУиЪжђџУ«»тЉўтѕ░С║єтјеТѕ┐сђѓ
Т▓АУ┐ЏжЌе№╝їСЙ┐жЌ╗тѕ░уЅЏтЦХућюТ╗ІТ╗ІуџёждЎтЉ│№╝їТѕЉтњйтЈБтћЙТ▓Ф№╝їУђЂУ┐юуюІУДЂтюЪуЂХСИіСИђтЈфт░ЈжЊЂжћЁжЄїуЅЏтЦХТх«УхитјџтјџуџёуЎйТ▓Ф№╝їт┐ФУдЂТ║бтЄ║жћЁТ▓┐№╝їуѓіС║ІтЉўТІ┐тЄ║СИцтЈфжИАУЏІТЅЊУ┐ЏжћЁжЄїсђѓТѕЉУђљт┐ЃуГЅтЙЁ№╝їуюІуЮђуѓіС║ІтЉўуџёУёИУЅ▓№╝їС╗ќтў┤УДњтЙ«тИдугЉТёЈТЌХТѕЉТўјуЎйжѓБТў»ТќГт«џжИАУЏІуЅЏтЦХуЁ«уєЪС║є№╝їтЈ»С╗ЦуЏЏС║єсђѓТѕЉСИђТііТІ┐УхиуЂХтЈ░СИіуџёжЊЂтІ║№╝їСИђСИІтГљС╝ИУ┐ЏжћЁжЄї№╝їТњЄУхиСИцСИфУЏІуЎйтїЁУБ╣уЮђ№╝їжђЈтЄ║Тџќж╗ёУЅ▓уџётЈ»уѕ▒уџёжИАУЏІтђњУ┐ЏубЌжЄї№╝їтЈѕУѕђС║єС║ЏуЅЏтЦХсђѓуѓіС║ІтЉўтњїжђџУ«»тЉўСИђУхиСИіТЮЦтѕХТГб№╝їС╗ќС╗гУ»┤№╝џжѓБТў»ждќжЋ┐уџё№╝їждќжЋ┐ТўетцЕтѕ░С╗ітцЕТ▓АтљЃСИђтЈБжЦГтЉб……У»ЮТ▓АУ»┤т«їждќжЋ┐ТІ┐убЌУ┐ЏТЮЦС║є№╝їТѕЉТђћТђћуюІуЮђС╗ќсђѓждќжЋ┐уѕйТюЌСИђугЉ№╝їтцДтБ░У»┤жЂЊ№╝џт░ЈС╝ЎтГљтЙѕТю║уЂхтўЏ№╝ЂУдЂСИЇУдЂТЮЦТѕЉУ┐ЎжЄїтЂџС║І№╝ЪУ»єСИЇУ»єтГЌ№╝ЪТѕЉ14т▓ЂУ┐ЏуџётГдтаѓ№╝їтЁЁтЁХжЄЈС╣Ът░▒Тў»уј░тюет░ЈтГдС║їСИЅт╣┤у║ДуџёТ░┤т╣│№╝їТѕЉУ»┤№╝џТѕЉС╝џтєЎУЄфти▒уџётљЇтГЌ№╝їу╗ЎТЮЉтГљжЄїуџёС║║УфітєЎУ┐ЄтЇќтю░тЇќТѕ┐уџётЦЉу║дсђѓжѓБт░▒УХ│тцЪС║є№╝ЂждќжЋ┐У»┤№╝їТїЦТїЦТЅІ№╝џтј╗жбєтЦЌУАБТюЇтљДсђѓуц║ТёЈжђџУ«»тЉўтИдТѕЉтЄ║тј╗сђѓ
ТѕЉуЕ┐СИітєЏУБЁ№╝їС╗ЁС╗ЁтЄаСИфТюѕ№╝їждќжЋ┐жѓБжўЪС║║жЕгТњцУх░С║є№╝їТѕЉуЋЎтюетю░Тќ╣сђѓжЃежўЪУйгСИџтѕ░тю░Тќ╣уџёС║║№╝їт░▒Тў»тЈЌжЄЇуће№╝їС║ћт╣┤тљј№╝їТѕЉућ▒СИђСИфжђџУ«»тЉўтЇЄС╗╗жбєт»╝№╝їтЁѕу«АтЄаСИфТЮЉ№╝їтљју«АСИђСИфтј┐№╝їтєЇтљјТЮЦтѕ░тиъСИіу«АтЄаСИфтј┐уџётиЦСйюС║єсђѓТѕЉтюетЂџтю░Тќ╣жђџУ«»тЉўуџёТЌХтђЎтіатЁЦС║єТ░ЉтЁх№╝їТъфТ│ЋтЄє№╝їТЅЊжЮХТгАТгАТѕљу╗ЕтљЇтѕЌуггСИђ№╝їСИіу║ДтЦќС║єТѕЉСИђТЮєт░ЈтЈБтЙёТГЦТъфсђѓТѕЉжЮътИИуЈЇТЃю№╝їтИИтИИТііт«ЃТЊдтЙЌжЌфжЌфтЈЉС║«сђѓ
ТюЅС║єТъф№╝їт░▒ТЃ│тЂџуѓ╣С║ІТЃЁтЄ║ТЮЦсђѓСИђТгАСИІС╣А№╝їТѕЉтИдСИіС║єУЄфти▒уџёТГЦТъфсђѓС╣АСИІж║дућ░жЄїжЄјжИАТЅЉТБ▒ТБ▒С╣▒жБъ№╝їУйдтѕ░СИђСИфт▒▒тЮА№╝їтљЉСИІуюІтј╗СИђТюЏТЌажЎЁуџёт║ёуе╝№╝їт▒▒тЮАСИіуЂїТюеу░Єу░Є№╝їТАдТаЉжЮњтєѕт»єт»єт«ът«ъ№╝їуЪ│тц┤жЂЇтИЃсђѓУ┐ЎжЄїТюЅТюђтЦйуџёТјЕТіц№╝їТў»жџЙТїЉуџёТЅЊуїјуј»тбЃ№╝їТѕЉСИцТЅІуЌњуЌњ№╝їСИІС║єУйд№╝їУ«ЕУиЪжџЈуџёС║║тЙЁтюеУйджЄї№╝їтЙёУЄфУх░У┐ЏТаЉТъЌсђѓ
ТѕЉуюІУДЂтЦйтЄатЈфжЄјжИАжБъУхиУљйСИІ№╝їУХ┤СИІТЮЦ№╝їТІ┐тЦйТъф№╝їТЉєТГБтД┐ті┐ТћЙС║єСИђТъфсђѓТъфТ▓АтЊЇ№╝їТў»тГљт╝╣тЇАС║єтБ│сђѓТѕЉТІ┐УхиТъфтЅЇтљјуюІуюІ№╝їУДЂУ║ФТЌЂТюЅСИђтЮЌуЪ│тц┤№╝їт░єТъфТЅўСИЇУй╗СИЇжЄЇтю░тюеуЪ│тц┤СИіуБЋС║єСИђСИІсђѓ“уа░”уџёСИђтБ░№╝їТ▓АТЮЦтЈітЈЇт║ћ№╝їтГљт╝╣СИЇтЂЈСИЇтђџт░ёУ┐ЏТѕЉуџёУЃИУєЏсђѓтГљт╝╣тюеТѕЉуџёУ║ФСйЊжЄїтц▒уе│у┐╗Т╗џ№╝їУ┐ЁжђЪжђаТѕљС║єтцДжЮбуД»тѕЏС╝ц№╝їт░йу«АУйдСИіуџёС║║уггСИђТЌХжЌ┤УиЉтѕ░ТѕЉУиЪтЅЇ№╝їТігУхиТѕЉтАъУ┐ЏУйджЄї№╝їтЈИТю║С╗ЦТюђт┐ФуџёжђЪт║дт╝ђУйдУхХУи»№╝їТ▓Атѕ░тї╗жЎб№╝їТѕЉСЙ┐Т▓АТюЅТ░ћТЂ»С║єсђѓ
ТѕЉТў»ТЅЊуїјТъфУх░уЂФуд╗СИќуџё№╝їС║Іт«ъУбФжџљуъњСИІТЮЦсђѓТѕЉуџёТъфТў»СИіу║ДтЦќтЊЂ№╝їТѕЉтЈѕТў»тј╗СИІС╣А№╝їУ┐ЎТаи№╝їтЏатЁгтЏау┤атЇатѕ░уЎЙтѕєС╣ІС╣ЮтЇЂС╗ЦСИі№╝їтЇЋСйЇу╗ЎТѕЉт╝ђС║єУ┐йТѓ╝С╝џ№╝їТѕЉуџёт«ХС║║тЙЌтѕ░С║єтЙѕтЦйуџётЙЁжЂЄтњїт«Ѕуй«№╝їС╗ќС╗гтЁежЃйТћЙСИІТЅІжЄїуџёС║ІтЏът«Х№╝їСИЃСИЃтЏЏтЇЂС╣ЮтцЕуЄЃуЂ»СИЇуЂГ№╝їУ»итЃДС║║У»ху╗ЈСИЇТќГ№╝їСИ║ТѕЉУХЁт║дсђѓСИЇтЄ║тЄаСИфТюѕ№╝їТѕЉУйгСИќС║єсђѓТѕЉТў»тЏаТЅІжЄїТюЅТъф№╝їтЈѕТюЅтЄ║жЌетИдУйдуџёСЙ┐тѕЕ№╝їТЋ┤ТЌЦтљЃуЕ┐СИЇТёЂ№╝їТг▓ТюЏСИЏућЪ№╝їУЄфти▒ујЕТъфУх░уЂФУђїТГ╗уџё№╝їтЇЂтѕєТЄіТѓћ№╝їтЈфТЃ│УйгСИќтѕ░СИђТѕит╣│тИИуЎЙтДЊт«Х№╝їтІцті│у«ђтЇЋтю░У┐ЄТЌЦтГљ№╝їТѕЉтдѓТё┐УйгСИќтѕ░С║єуј░тюеУ┐ЎСИфТюгтѕєТИЕТџќуџётєюТ░Љт«Хт║ГжЄїсђѓТѕЉт«Ѕт┐Ѓтю░уГЅтЙЁУ»ъућЪсђѓ
тЅЇСИђТ«хТЌХжЌ┤№╝їжѓБУ┐ўТў»тюеТ»ЇС║▓УѓџтГљжЄїуџёТЌХтђЎ№╝їтЏЏтЉежЮЎТЌатБ░ТЂ»№╝їТѕЉУДЅтЙЌтЇЂтѕєТєІжЌи№╝їтц┤УёЉтЇ┤тЈўтЙЌУХіТЮЦУХіТИЁТЎ░№╝їжЂЦУ┐ютцё№╝їТѕЉуюІУДЂТѕЉжѓБт╣┤Уй╗уџёуѕИуѕИ№╝їУ║ФУЃїСИђСИфу▒╗С╝╝С║јжЃежўЪтиЦтЁхТјбтю░жЏиућеуџёТјбТхІС╗фуџёСИюУЦ┐№╝їтюеТ┤«Т▓│тЇЌт▓ИСИђуЅЄТ╗ЕТХѓтю░СИіСИЊт┐ЃУЄ┤т┐Ќтю░ТјбТхІсђѓС╗ќуџёУёќтГљжЃйСИЇС╝џу╝ЕСИђСИІ№╝їт░йу«АжБјтЙѕтцД№╝їТ▓ЎтюЪт┐ФУдЂт░єС╗ќтЪІТ▓АсђѓУ┐ЎтЮЌт«│С║єТќЉуДЃУѕгуџёТѕѕтБЂ№╝їтљгУ»┤тЙѕТЌЕуџёТЌХтђЎжЂЌт╝ЃуЮђСИЇт░ЉжЎХтЎежњ▒тИЂС╗ђС╣ѕуџё№╝їС║║С╗гУюѓТІЦУђїУЄ│№╝їТїќтюЪУ▒єУѕгт»єт»єтѕеТїќсђѓТюЅС║║Тїќтѕ░С║єтЄаС╗Х№╝їТюЅС║║СИђС╗ХС╣ЪТ▓АТїќтѕ░сђѓуѕИуѕИУх░С║єСИфТЇитЙё№╝їС╗јжў┐тЕєуџёТъЋтц┤жЄїтЂитЄ║т«ХжЄїт╝ђт░ЈтЇќжЃеУхџтѕ░уџёжњ▒№╝їС╣░С║єСИфуј░С╗БтїќуџёТю║тЎе№╝їТЃ│СИђСИІтГљТїќтЄ║тѕФС║║Т▓АТїќтѕ░уџёуеђтЦЄтЈцУЉБ№╝їСИђСИІтГљтЇќтѕ░тцДжњ▒сђѓуѕИуѕИСйЮтЂ╗уЮђУ║ФтГљСИђТГЦСИЇжЂЌ№╝їТЮЦТЮЦтЏътЏъТјбТхІС║єтЦйтЄажЂЇ№╝їу╗ѕС║ј№╝їТю║тЎеТ╗┤Т╗┤тЈФтЊЇ№╝їуѕИуѕИСИђТііТЅћТјЅТјбТхІС╗ф№╝їС╝ИтЄ║тЈ│Уёџ№╝їС╗ЦтидУёџСИ║Тћ»уѓ╣№╝їУ║ФСйЊТЋЈТЇитю░УйгСИЅуЎЙтЁГтЇЂт║дућ╗С║єСИфтюєтюѕ№╝їТјЦуЮђ№╝їжБът┐Фтю░УиЉтѕ░тю░УЙ╣ТІ┐тЏъжЊЂжћеТїќУхиТЮЦсђѓуѕИуѕИТїќС║єтЦйжЋ┐ТЌХжЌ┤№╝їтцЕжЃйж╗ЉС║є№╝їТЅЇтЏътѕ░т«Хсђѓ
уѕИуѕИУЃїтЏъТЮЦтЇітЮЌуЪ│убЉ№╝їтЈБУбІжЄїУ┐ўУБЁТюЅтЄаТъџжћѕУ┐╣ТќЉТќЉуџёжњ▒тИЂсђѓ
ТХѕТЂ»С╝атЙЌжБът┐Ф№╝їСИђжА┐жЦГуџёТЌХжЌ┤№╝їТЮЉжЄїУђЂУђЂт░Јт░ЈсђЂућиућитЦ│тЦ│жЃйТЮЦтѕ░ТѕЉт«ХжЎбтГљС║єсђѓС╗ќС╗гСИЇуљєС╝џТѕЉС╝ИТІ│ТњЉУЃ│Уєі№╝їТЈљтЄ║ТіЌУ««№╝ѕтЁХт«ъС╗ќС╗гуюІСИЇтѕ░ТѕЉ№╝їтЈфТў»УІдС║єТ»ЇС║▓№╝їтЦ╣СИђжўхжўхУЁ╣уќ╝№╝їтюеуѓЋСИіуѕгУхиТЮЦтЈѕтЇДСИІ№╝Ѕ№╝їтљхтљхтџитџи№╝їтЄ║тЄ║У┐ЏУ┐Џ№╝їт«їтЁежАЙтЈіСИЇтѕ░ТѕЉС╝џт»╣У┐ЎуфЂуёХтЈЉућЪтЈўТЋЁуџёуј»тбЃС║ДућЪТЂљТЃДсђѓТѕЉтљгтѕ░СИђСИфТ┤фжњЪУѕгтЌАтЌАСйютЊЇуџётБ░жЪ│№╝їжѓБТў»ТѕЉуѕИуѕИуџётцДС╝»№╝їТѕЉУ»ЦтЈФтцДжў┐уѕисђѓ№╝ѕжА║СЙ┐У»┤СИђСИІ№╝їТѕЉжў┐уѕи42т▓ЂСИіТГ╗С║јСИјт▒▒УЃїжЮбТЮЉт║ёуџёСИђтю║УЇЅтю░Тб░ТќЌсђѓжЊЂуаѓт╝╣ТііС╗ќуџёУёИТЅЊТѕљС║єуГЏтГљт║ЋсђѓУЄфжѓБС╗Цтљј№╝їжЄЇУдЂт«ХС║І№╝їжЃйУдЂућ▒ТѕЉтцДжў┐уѕитЄ║жЮб№╝ЅтцДжў┐уѕиУ»┤№╝џУ┐ЎТў»ТЃ│тйЊт╣┤уџёубЉ№╝їт░ЈТЌХтђЎС╗јт«ХжЄїУђЂС║║жѓБжЄїтљгУ»┤У┐Є№╝їСИђС║ЏС║║т«ХСИјтЈдСИђС║ЏС║║т«ХсђЂСИђСИфТЮЉтГљСИјтЈдСИђСИфТЮЉтГљТюЅуЋїубЉ№╝їУАЎжЌежЄїС╣ЪТюЅУ«░С║ІУ«░тіЪуџёуЪ│убЉсђѓТ▓│Т╗ЕжѓБжЄїТЌЕТЌХтђЎТў»УѓЦуЙјуџёућ░тю░№╝їтИИтИИтЈЉућЪС║Ѕтю░ТЅЊТќЌ№╝їУ┐ЎСИіжЮбтГЌтцџтЙЌтЙѕ№╝їтЈ»УЃйУ«░уЮђтЋЦС║ІТЃЁтЉб№╝їТў»уеђуйЋУ┤Д№╝їУ«Етј┐СИіТќЄуЅЕждєуџёС║║ТЮЦуюІуюІсђѓТўјтё┐т░ЋС┐Ютѕ░тј┐СИітЈФС║║тј╗сђѓт░ЋС┐ЮТў»ТѕЉуѕИуѕИуџётЦХтљЇ№╝їжў┐тЕєТ»ЇС║▓С╗гУ░ѕтѕ░уѕИуѕИТЌХжЃйУ┐ЎТаиуД░тЉ╝сђѓТѕЉТ»ЇС║▓УѓџтГљтЙѕтцДС║є№╝їТђђтГЋтЦ│С║║ТЎџжЌ┤тЄ║жЌеС║јС║║С║јти▒жЃйСИЇтљЅтѕЕ№╝їУЁ╣уЌЏжЌ┤жџЎ№╝їТѕЉТ»ЇС║▓С╗јуѓЋСИіуѕгУхиТЮЦ№╝їУХ┤тюеуфЌТѕиСИітљЉтцќуюІсђѓТѕЉС╣ЪтЙѕуЮђТђЦ№╝їТЅГтіеУ║ФСйЊТЃ│ТЅЙСИфТќ╣тљЉуюІСИфуЕХуФЪ№╝їТЌатЦѕТђјТаитіфтіЏтЏЏтЉежЃйТў»Т╝єж╗ЉСИђуЅЄ№╝їТ▓АТюЅСИђТўЪтЁЅС║«№╝їТѕЉТћЙт╝ЃтіфтіЏ№╝їтљ»тіеТёЪУДЅу│╗у╗Ъу╗єу╗єТёЪтЈЌсђѓТѕЉуюІУДЂС║єуфЌтцќТюЅтЄаТћ»ТЅІућхуГњСИђжЌфСИђжЌфуџё№╝їУЃќУЃќуўдуўдсђЂжФўжФўуЪ«уЪ«уџёС║║тй▒тюеуфЌтИўСИіТЎЃтіе№╝їугЉтБ░сђЂтЋДтЈ╣тБ░СИЇТќГсђѓТ»ЇС║▓у╗ЈтЈЌСИЇСйЈТѕЉуџёТіўУЁЙ№╝їу┤»тЙЌтЮљтЏъуѓЋСИісђѓ
у╗ѕС║ј№╝їуфЌтцќт«ЅжЮЎСИІТЮЦ№╝їС║║С╗гтљёУЄфтЏът«ХС║є№╝їуѕИуѕИУх░С║єУ┐ЏТЮЦсђѓ
уѕИуѕИтЄЉтѕ░Т»ЇС║▓УиЪтЅЇ№╝їТііТЅІТћЙтѕ░Т»ЇС║▓уџёУѓџтГљСИіУ»┤№╝џтё┐тГљ№╝їтњ▒С╗гт░▒УдЂтЈЉтцДУ┤бС║є№╝їСйат░▒УдЂТюЅСИф“тюЪУ▒ф”уѕИуѕИС║єсђѓтѕФС║║жЃйУ«▓“тюЪУ▒ф”Тў»ТђјС╣ѕтюЪУ▒фуџё№╝їтњ▒С╣ЪтюЪУ▒фСИђтЏъсђѓУ»┤тЙЌжФўтЁ┤№╝їуѕИуѕИт░єУђ│ТюхУ┤┤тѕ░Т»ЇС║▓уџёУѓџтГљСИітЉйС╗цТѕЉ№╝џтЈФуѕИуѕИ№╝ЂуѕИуѕИу╗ЎСйаС╣░Тъф№╝їС╣░тѕђ№╝ЂТ»ЇС║▓ТЅЉтЊДСИђтБ░угЉС║є№╝џТў»у▓ЙТў»ТђфтЋі№╝Ъуј░тюет░▒тЈФуѕИуѕИсђѓС╣░тЋЦСИЇтЦй№╝їтЂЈС╣░Тъфтѕђуџё№╝їт░Јт┐Ѓжў┐тдѕтљгУДЂсђѓуѕИуѕИУ»┤№╝џућиС║║т«Хуѕ▒Тъфуѕ▒тѕђТў»тцЕТђД№╝їтѕФуџёУ┐ўСИЇуѕ▒тЉбсђѓТ»ЇС║▓тѕџУдЂт╝ђтЈБ№╝їуѕИуѕИСИЇуљєС╝џ№╝їу╗Ду╗Гт»╣ТѕЉУ»┤№╝џтѕФС║║У»┤уѕИуѕИТў»тѓ╗тГљ№╝їтЂиС║єт«ХжЄїуџёжњ▒№╝їС╣░С║єУђЇТііТѕЈуџёТю║тЎе№╝їТјбСИЇтѕ░т«Ю№╝їУ┐ЎСИІтахСйЈС╗ќС╗гуџётў┤С║єтљД№╝ЪуѕИуѕИТїќтѕ░уџёжѓБСИфуЪ│тц┤уќЎуўЕтђ╝жњ▒уЮђтЉб№╝їТў»СИфтЈцУЉБсђѓтњ▒ТіітЈцУЉБтЇќС║є№╝їТііТѕ┐тГљуЏќТѕљСИЅт▒ѓТЦ╝№╝їт║ЋжЮбт╝ђт░ЈтЇќжЃе№╝їС║їт▒ѓтЂџСИфтцДт«бтјЁ№╝їС╣░СИіжФўу║ДТ▓ЎтЈЉ№╝їт«бС║║ТЮЦС║єтќЮУїХсђЂУ░ЮжЌ▓С╝а№╝їуѕИуѕИуџёС╝┤тё┐ТЮЦС║єтќЮжЁњсђѓСИЅт▒ѓт░▒СйЈС║║№╝їт«Ѕт«ЅжЮЎжЮЎсђЂТЋъТЋъС║«С║«уџёсђѓ
ТѕЉУ┐иу│ітЙЌСИЇУАї№╝їуЮАУ┐Єтј╗С║є№╝їТбджЄїУДЂтѕ░С║єуѕИуѕИУ»┤уџёСИЅт▒ѓТЦ╝Тѕ┐№╝їуЎйтбЎ№╝їт«йтцДуџёуј╗уњЃуфЌ№╝їу▓Ѕу║бУЅ▓уфЌтИў№╝їТў»тЁеТЮЉТюђТ╝ѓС║«уџёсђѓ
Т»ЇС║▓тњїуѕИуѕИУй╗тБ░У»┤У»ЮсђѓС╗ќС╗гС┐Ет░▒Тў»жѓБТаи№╝їтЇЋуІгтюеСИђУхиуџёТЌХтђЎУ»┤У»ЮУиЪУџітГљтЈФС╝╝уџё№╝їтюетю║уџёуггС║їСИфС║║С╝ЉТЃ│тљгтѕ░сђѓС╗ќС┐ЕСИђСИфуѓ╣тц┤№╝їСИђСИфу╗ЎТи╗УїХжђњуЃЪ№╝їС║цТхЂУ┐ЏУАїтЙЌТюЅТ╗ІТюЅтЉ│№╝їтЙѕжА║уЋЁсђѓСИЇжА║уЋЁуџёТЌХтђЎС╣ЪТў»ТюЅуџё№╝їТ»ЇС║▓тИїТюЏуѕИуѕИт«Ѕт┐Ѓтюет«ХжЄїт«ѕт░ЈтЇќжЃе№╝їуѕИуѕИт░▒Тў»тЃЈт▒Ђую╝жЄїтц╣С║єТа╣уЃДуЂФТБЇ№╝їтЮљСИЇСйЈ№╝їУђЂтЙђтцќУиЉсђѓуѕИуѕИУ»┤№╝џжѓБтЇЂтЮЌтЁФтЮЌуџё№╝їтЋЦТЌХтђЎТЅЇУЃйТїБтѕ░тцДжњ▒сђѓТ»ЇС║▓У»┤№╝џт«Ѕт«Ѕуе│уе│т╝ђжЊ║тГљ№╝їС╣░УїХС╣░жєІуџёжњ▒ТюЅт░▒ТѕљС║є№╝їтЙђтљјТћњС║єжњ▒№╝їтњ▒т╝ђтцДСИђС║Џ№╝їУ┐ЏС║ЏжФўТАБУ┤ДсђѓуѕИуѕИУ»┤№╝џжѓБтЙЌуГЅтѕ░уї┤т╣┤жЕгТюѕсђѓуѕИуѕИтљјТЮЦТъюуюЪт╣▓С║єСИђС╗ХжИАуїФуї┤ТђДтГљтћгС║║уџёС║І№╝їУ┐ЎТў»тљјУ»Ю№╝їТѕЉтљјжЮбС╝џУ«▓тѕ░сђѓ
уггС║їтцЕ№╝їуѕИуѕИтљЃт«їТЌЕжЦГтј╗тј┐СИітЈФС║║С║єсђѓТ»ЇС║▓УАБУЦЪТЅБтГљт«їтЁеТЅЊт╝ђ№╝їжю▓тЄ║тюєтюєуџёУѓџтГљ№╝їТќюжЮатюеУбФтъЏСИіуЮАуЮђС║єсђѓтЁ┤У«ИтЦ╣УиЪуѕИуѕИУ«▓ТѓёТѓёУ»ЮСИђтцюТ▓Атљѕую╝№╝їУ┐ЎС╝џтё┐тЏ░тЮЈС║єсђѓжЎбжЄїжЄЇжЄЇуџёУёџТГЦУИЈтЊЇС║є№╝їТѕЉтљгтѕ░жў┐тЕєжЌ«№╝џТЌЕжЦГтќЮУ┐ЄС║є№╝ЪТў»тцДжў┐уѕиуџётБ░жЪ│тюеуГћ№╝џтќЮУ┐ЄС║єсђѓТѕЉУдЂтЄ║ућЪуџёУ┐Ўтю░Тќ╣у«АтљЃСИЅжА┐жЦГуД░“тќЮ”№╝їУДЂжЮбтЋЦжЃйСИЇУ»┤№╝їСИђСИфжЌ«№╝џтќЮС║є№╝ЪСИђСИфуГћ№╝џтќЮС║єсђѓу«ЌТў»УАїТЃ»СЙІТЅЊС║єТІЏтЉ╝№╝їС╣ЪуЪЦжЂЊт»╣Тќ╣Тў»тљЃУ┐ЄжЦГС║єсђѓтцДжў┐уѕиУ»┤№╝џТѕЉТІ┐С║єС║ЏжбюТќЎсђѓт░ЋС┐ЮТїќуџёубЉСИіжЮбуџётГЌТеАу│ітЙЌтЙѕ№╝їтј┐СИіуџёУАїт«ХТЮЦС║єуюІСИЇТИЁТЦџ№╝їТѕЉТЈЈСИђСИІсђѓТѕЉуЪЦжЂЊУ┐Ўтю░Тќ╣уџёжбюТќЎТў»ућет▒▒СИіу║бУЅ│УЅ│уџёт▒▒СИ╣Уі▒тЂџуџёсђѓт▒▒СИ╣Уі▒т╝ђтЙЌу║бжЂЇт▒▒тЮАуџёТЌХтђЎ№╝їтЦ│С║║С╗гу╗ЊС╝┤СИіт▒▒№╝їжЄЄТ╗АУЃїу»╝№╝їтЏът«ХтђњтюетцДУІФтЇЋСИіТћЙтѕ░тцфжў│т║ЋСИІТЎњ№╝їтЙЁт╣▓жђЈ№╝їтюеуЪ│УЄ╝жЄїТЇБТѕљу╗єТюФ№╝їтЂџУі▒тЇиждњтц┤уџёТЌХтђЎтЇитюежЮбжЄїТѕќуѓ╣тюежАХуФ»№╝їУњИтЄ║ТЮЦтЙѕТў»тќют║єУ»▒С║║сђѓтцДжў┐уѕитљЕтњљжў┐тЕє№╝џТІ┐С║ЏТ░┤ТЮЦ№╝їТііубЉСИіжЮбуџёТ│ЦтюЪТ┤ЌТјЅсђѓжў┐тЕєтЎћтЎћуџёУёџТГЦтБ░С╗јтјеТѕ┐тЊЇтѕ░жЎбтГљСИГ№╝їТЃ│т┐ЁТў»ТІ┐Т░┤тњїТі╣тИЃтј╗С║єсђѓСИђС╝џтё┐№╝їтцДжў┐уѕиУ»┤№╝џУ┐ўУдЂТЎЙСИђС╝џтё┐№╝їТ░┤т╣▓С║єТЅЇУЃйТЈЈсђѓТјЦСИІТЮЦ№╝їТ▓АТюЅтБ░жЪ│С║єсђѓ
у║дУјФСИГтЇѕжЦГуџёТЌХтђЎ№╝їжЎбтГљжЄїтљхтџиУхиТЮЦсђѓС║║тЙѕтцџ№╝їСИђСИфт╣┤Уй╗ућиС║║уџётБ░жЪ│У»┤№╝џТѕЉуюІуюІсђѓтЙѕт┐Ф№╝їС╗ќтЈФжЂЊ№╝џУ┐ЎТў»тЋЦтЈцубЉтЋі?У┐ЎС╣ѕт╣▓тЄђ№╝їтГЌУ┐╣У┐ЎС╣ѕТќ░ж▓юсђѓтцДжў┐уѕиУ»┤№╝џТѕЉтѕџТ┤ЌС║єСИђСИІ№╝їТіітГЌТЈЈС║єСИђСИІ№╝їТђЋСйаС╗гуюІСИЇТИЁТЦџсђѓуА«т«ъТў»тЈцубЉ№╝їТўетцЕСИІтЇѕС╗јТ▓│Т╗ЕУЙ╣ТїќтЄ║ТЮЦуџёсђѓУ┐ўТў»жѓБСИфућиС║║уџётБ░жЪ│№╝їУ»┤№╝џСйаТЈЈт«Ѓт╣▓тЋЦтЉб№╝ЂСИђТЈЈт░▒тЮЈС║ІС║є№╝їТў»тЈцУЉБС╣ЪСИЇу«ЌтЈцУЉБС║єсђѓтЈцт░▒Тў»ТЌД№╝їтјЪТЮЦтЋЦТаитГљт░▒С┐ЮуЋЎтЋЦТаитГљ№╝їтђ╝С╗ит░▒тђ╝тюет«ЃтјЪТЮЦУЄфУ║ФуџёТаитГљСИісђѓтцДжў┐уѕи“тЋі”С║єСИђтБ░№╝їтєЇТ▓АС║єСИІТќЄсђѓжѓБСИфућиС║║ТјЦуЮђУ»┤№╝џСйауа┤тЮЈС║єТќЄуЅЕуџётјЪуюЪТђДсђѓТЈЈ№╝їт░▒Тў»СИђуДЇуа┤тЮЈУАїСИ║сђѓтцДжў┐уѕитЈѕ“тЌе”С║єСИђтБ░№╝їТѕЉС╝░ТЉИС╗ќТў»СИђТІЇтцДУЁ┐Ті▒тц┤тЮљтюетю░СИіС║єсђѓ
жЎбтГљжЄїтєЇТЌаС║║У»┤У»Ю№╝їуфЂуёХ№╝їтљгУДЂуѕИуѕИтцДтЈФСИђтБ░№╝џтцДтцД№╝ѕУ┐Ўтю░Тќ╣у«АтцДС╝»тЈФтцДтцД№╝Ѕ№╝ЂСйатњІУ┐ЎС╣ѕТЅІжЌ▓тЉб№╝ЪТѕЉУ┤╣С║єС╣ЮуЅЏС║їУЎјС╣ІтіЏТЅЇТїќтѕ░У┐ЎС╣ѕСИђСИфубЉ№╝їУ┐ўтЈФСйау╗Ўуа┤тЮЈТјЅС║є№╝ЂтцДжў┐уѕиућ│УЙЕжЂЊ№╝џТѕЉтЦйт┐ЃтЦйТёЈТЃ│т╝ёт╣▓тЄђуюІтЙЌТИЁТЦџСИђуѓ╣тё┐№╝їтњІт░▒Тў»уа┤тЮЈС║є№╝Ъжў┐тЕєт┐ЎтќЮжЂЊ№╝џСйаУ┐ЎтеЃтеЃтњІУ»┤У»ЮтЉб№╝ЪУиЪтцДтцДУ┐ЎС╣ѕУ«▓тљЌ№╝ЪСйатєЇтј╗ТїќСИђСИфСИЇт░▒ТѕљС║є№╝ЪуѕИуѕИУ»┤№╝џСйатйЊТў»Т▓│Т╗ЕжЄїТІЙуЪ│тц┤тЉб№╝ЪТїќУ┐ЎСИфубЉТЉћтЮЈС║єТѕЉуџёС╗фтЎе№╝їТѕЉтєЇТІ┐тЋЦтј╗ТїќтЉб№╝Ъжў┐тЕєУ»┤№╝џТђфСйаУЄфти▒УабСИЇУ»┤№╝ЂтјЪТЮЦ№╝їуѕИуѕИтюетљгтѕ░С╗фтЎеТ╗┤Т╗┤тЈФуџёТЌХтђЎСИђТ┐ђтіе№╝їТііС╗фтЎежџЈТЅІтљЉтю░СИіСИђТЅћ№╝їтј╗ТІ┐жЊЂжће№╝їТІ┐ТЮЦжЊЂжћеуюІУДЂС╗фтЎеУбФТЉћТќГС║єУЁ┐№╝їубјТѕљСИцТѕфсђѓуѕИуѕИТїќтѕ░С║єуЪ│убЉ№╝їжФўтЁ┤тЙЌСИЇУАї№╝їт»╣УЄфти▒У»┤№╝џТќГС║єт░▒ТќГС║є№╝їтєЇС╣░Тќ░уџё№╝їуј░тюеС╣ЪСИЇжюђУдЂС║єсђѓ
тј┐СИіТЮЦуџёС║║тљЃС║єжў┐тЕєуФ»тј╗уџёжЮбТЮАУх░С║єсђѓуѕИуѕИУ║║тюеуѓЋСИі№╝їСИђСИІСИђСИІТњЋТЅ»ТъЋтиЙ№╝їућЪућЪТііТъЋтиЙТњЋТѕљС║єубјуЅЄсђѓТ»ЇС║▓тѕџУ»┤С║єСИђтЈЦ№╝џСйаТњЋТъЋтиЙт╣▓тЋЦ№╝ЪУ┐ўтЙЌУі▒жњ▒С╣░сђѓуѕИуѕИт░▒тљ╝С║єСИђтЈЦ№╝џжњ▒№╝Ђжњ▒№╝ЂСйат░▒уЪЦжЂЊтЄаТ»ЏтЄатЮЌуџёжњ▒№╝ЂТ»ЇС║▓СйјтБ░тЈѕУиЪСИіСИђтЈЦ№╝џТ▓АТюЅТїБтцДжњ▒уџётЉй№╝їт░▒т«Ѕт┐Ѓт«ѕжЊ║тГљсђѓуѕИуѕИУ»┤№╝џСйаТюЅт«їТ▓Ат«ї№╝ЪуФІУ║ФтЄ║С║єТѕ┐жЌесђѓ
ТѕЉУюиТЏ▓тюеТ»ЇС║▓уџёУѓџтГљжЄї№╝їжЎцС║єУЄфти▒уџёт┐ЃУи│№╝їУ┐ўтљгУДЂтЈдСИђжбЌт┐ЃУёЈтюет╝║ТюЅтіЏтю░Уи│тіе№╝їУи│тіеуџётљїТЌХТЋБтЈЉуЮђСИђуДЇТ░ћтЉ│№╝їТў»ТхЊуЃѕуџёТ▒ЌтЉ│тњїуЃЪтЉ│№╝їжѓБТў»уѕИуѕИуџё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Т░ћтЉ│ТѕЉт░єтюетїЁУБ╣ТѕЉуџёС╗ќуџёТЌДУАгУАФСИі№╝їтј╗уєЪТѓЅ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т┐ЃУёЈУАђТХ▓т┐ФжђЪТхЂтіе№╝їт┐Ёт«џТў»тюеТђЮУ░ІуЮђС╗ђС╣ѕсђѓСИђС╝џтё┐№╝їуѕИуѕИуџёт┐ЃУёЈтЈЉтЄ║С║«тЁЅ№╝їтЈўтЙЌТИЁТЙѕжђЈТўјУхиТЮЦсђѓТѕЉуЪЦжЂЊуѕИуѕИтЈѕУдЂУЃїуЮђжў┐тЕєтњїТ»ЇС║▓№╝їтЄ║тј╗т╣▓тЋЦС║ІтЉбсђѓТѕЉУ«▓СИЇтЄ║У»Ю№╝їТђЦтЙЌтЈфУИбТ»ЇС║▓уџёУѓџтГљсђѓТѕЉтљгУДЂТ»ЇС║▓уќ╝тЙЌтЊјтљєтЊјтљєтЈФтћц№╝їжў┐тЕєУиЉУ┐ЏТ»ЇС║▓уџёТѕ┐жЌ┤№╝їУ»┤№╝џТђЋТў»УдЂућЪС║єсђѓТѕЉуі»С║єСИЇтцДСИЇт░ЈуџёСИђСИфжћЎУ»»№╝їтѕџтѕџТёЈУ»єтѕ░№╝їСЙ┐уФІтЇ│т«ЅжЮЎСИІТЮЦсђѓТ»ЇС║▓тњїжў┐тЕєС╣Ът«ЅжЮЎСИІТЮЦС║єсђѓу«ЌУхиТЮЦС╣ЪУ┐ўТюЅСИђСИфтцџТюѕтЉб№╝їУ┐ўТ▓Атѕ░ТЌХжЌ┤№╝їУ┐ўТў»жў┐тЕєуџётБ░жЪ│сђѓСИЇуќ╝С║єСйаУ║║СИђС╝џтё┐№╝їуќ╝уџёУ»ЮСйатќіТѕЉсђѓжў┐тЕєтЎћтЎћтЄ║тј╗С║єсђѓ
уѕИуѕИТюЅСИфујЕС╝┤тё┐№╝їжџћСИЅти«С║ћТЮЦт«ХжЄїсђѓУ┐ЎтЄатцЕ№╝їС╗ќТЮЦтЙЌтІц№╝їС╣ЪуЅ╣тѕФТЌЕС║Џ№╝їжў┐тЕєтѕџтѕџУхит║і№╝їтј╗тђњт░┐ТАХ№╝їС╗ќт░▒Тјет╝ђтцДжЌеУ┐ЏТЮЦС║єсђѓуѕИуѕИтљгУДЂжЎбтГљжЄїтцџС║єСИђСИфС║║уџёУёџТГЦ№╝їтЙѕт┐ФУхит║і№╝їуЕ┐УАБУ┐јтЄ║тј╗сђѓС┐ЕС║║тюеТфљСИІтЈйтЈйтњЋтњЋСИђжўх№╝їуѕИуѕИУ┐ЏтјеТѕ┐ТЈГт╝ђуг╝т▒Ѕ№╝їТІ┐СИцСИфУ┤┤жЦ╝тГљТЈБУ┐ЏТђђжЄї№╝їТђЦтїєтїєтЄ║жЌеС║єсђѓжѓБТ«хТЌХжЌ┤№╝їуѕИуѕИтЏът«ХтЙѕТЎџ№╝їТюЅТЌХтИдТЮЦСИђтЈфжЄјжИА№╝їТюЅТЌХтИдТЮЦСИђтЈфжЄјтЁћ№╝їтцДт«ХтљЃТЎџжЦГ№╝їжЄјтЉ│уџёждЎТ░ћжБўТ╗АТѕ┐жЌ┤№╝їТѕЉтЈфУЃйУюиу╝ЕтюеТ»ЇС║▓УѓџтГљжЄї№╝їтљгУДЂС╗ќС╗гТњЋтњгжЄјжИАУЁ┐тњїжЄјтЁћУЁ┐№╝їУ┐ъУ┐ъУ»┤№╝џждЎ!ждЎ№╝ЂтљИТ║юСИђтБ░№╝їжў┐тЕєтќЮС║єСИђтЈБУѓЅТ▒ц№╝їтњ│С║єСИцтБ░№╝їтЈ»УЃйТў»уЃФуЮђС║є№╝їТХЕуЮђтЌЊжЪ│т»╣уѕИуѕИУ»┤№╝џСйаУ«▓У┐ЎС║ЏТў»СйауџёС╝┤тё┐жђЂуџёТѕЉт░▒тйЊТѕљТў»СйауџёС╝┤тё┐жђЂуџё№╝їС╗ЦтљјСйатѕФтєЇУдЂС║єсђѓтЈѕТў»СИцтБ░тњ│тЌйсђѓСйатЇЃСИЄСИЇУдЂтіеТъфтЋі№╝ЂТЈљтѕ░Тъф№╝їТѕЉтЁеУ║ФжЃйУдЂтЈЉТіќ№╝їжў┐тЕєтЈѕУ»┤сђѓжў┐тЕєуџёУ»ЮТГБТў»Т»ЇС║▓УѓџтГљжЄїуџёТѕЉТїБТЅјуЮђТЃ│У»┤тЈѕТЌаТ│ЋУ»┤тЄ║уџёУ»Ю——ТъфтцџтЇ▒жЎЕтЋі№╝ЂТѕЉт░▒Тў»тюеТъфСИіСИДтЉйуџё№╝їУ┐ўТюЅТѕЉуѕиуѕисђѓтєЇТюЅСИђСИфТюѕТѕЉт░▒УдЂжЎЇућЪС║є№╝їтѕ░ТЌХтђЎТѕЉтЙЌУ«ЕуѕИуѕИтцДтцДуџёТЅІТЇДуЮђТѕЉсђѓуѕИуѕИтцДтцДуџёТЅІТў»СИђтЮЌТИЕтјџуџётюЪтю░№╝їТѕЉтЙЌУљйтюежѓБтЮЌтю░СИіТѕљжЋ┐сђѓ
ТЎџСИі№╝їт░▒ТѕЉС╗гС╗е№╝ѕУЎйуёХтюеУѓџтГљжЄї№╝їТѕЉС╣Ъу«ЌСИђСИф№╝Ѕ№╝їтљгУДЂуѕИуѕИт»╣Т»ЇС║▓У»┤№╝џу╗ЎСйаТЅЊжЄјжИАтј╗С║єсђѓжЄјжИАУљЦтЁ╗тЦйсђѓТ»ЇС║▓У»┤№╝џТѕЉСИЇтљЃжЄјжИАуЁДТаитЦйтЦйуџё№╝ЂСйатцџтЙЁтюет«ХжЄї№╝їтИ«жў┐тдѕуюІжЊ║тГљТЅЇТў»сђѓуѕИуѕИУ»┤№╝џтЕєтеўС╗гтц┤тЈЉжЋ┐УДЂУ»єуЪГ№╝їт«ѕСИфт░ЋжЊ║тГљ№╝їт«ѕтѕ░УђЂС╣Ът░▒жѓБС╣ѕтЄаСИфжњ▒сђѓуЮА№╝їуЮА№╝їтЏ░ТГ╗С║є№╝ЂуѕИуѕИСИЇтєЇУ»┤С╗ђС╣ѕ№╝їтњїУАБтђњСИІуЮАС║єсђѓ
ТѕЉуџёую╝тЅЇ№╝ѕУЎйуёХжЌГуЮђую╝№╝їСЙЮуёХуюІтЙЌтѕ░№╝ЅуфЂуёХУЁЙУхиС║єтЏбтЏбС║ЉуЃЪ№╝їуЏ┤жЊ║т▒Ћтѕ░тю░т╣│у║┐СИісђѓТѕЉуюІУДЂСИђУЙєУГдУйдуД╗тіеУђїТЮЦ№╝їућ▒СИђСИфт░Јж╗Љуѓ╣тЈўТѕљУГдуЂ»жЌфуЃЂуџёжЊЂтЂџуџёт║ъуёХТђфуЅЕсђѓУ┐ЎСИфТЃЁТЎ»тѕ║Т┐ђуЮђТѕЉ№╝їС╗цТѕЉСИЇУЃйт«Ѕуе│сђѓУ┐ЎТў»СИфтЄХтЁє№╝їТѕЉУІдС║јТЌаТ│ЋтЉіУ»Ѕжў┐тЕєтњїТ»ЇС║▓сђЂуѕИуѕИ№╝їТђЦтЙЌтидтє▓СИђСИІ№╝їтЈ│ТњъСИђСИІ№╝їТ»ЇС║▓тЈѕуЌЏУІдтю░Уюиу╝ЕУхиУ║ФтГљ№╝їТѕЉСИЇТЋбтіеС║єсђѓСИђтцЕТЎїтЇѕ№╝їжѓБУЙєУГдУйду╗ѕС║јТ┤╗ућЪућЪтю░С╗јУ┐ъТјЦтцЕУЙ╣уџёж╗ётюЪУи»СИіт┐ФжђЪжЕХУ┐ЄТЮЦ№╝їжЕХУ┐ЏТЮЉтГљсђѓУйдСИіСИІТЮЦтЄаСИфУГдт»ЪтЙёуЏ┤Ух░У┐ЏТѕЉт«ХжЎбтГљсђѓжў┐тЕєт┐ЎС╗јтидтјбТѕ┐Тћ╣Сйюуџёт░ЈтЇќжЊ║т░ЈУиЉтЄ║ТЮЦ№╝їТїАтюеС╗ќС╗гжЮбтЅЇ№╝їУ»┤№╝џСИЇУЃйУ┐Џтј╗№╝їТюЅт░▒УдЂућЪтеЃуџётГЋтдЄтЉбсђѓжў┐тЕєТїЄТїЄтцДжЌеСИіТЈњуЮђуџёТЪЈТаЉТъЮсђѓУГдт»ЪуФЎСйЈУёџТГЦ№╝їтЁХСИГСИђСИфт╣┤у║фУЙЃжЋ┐С║Џуџёт»╣жў┐тЕєУ»┤С║єС║ЏС╗ђС╣ѕсђѓжў┐тЕєуџёУёИтЈўтЙЌуЂ░уЎй№╝їуўФтЮљтюеС║єтю░СИісђѓтцДУѓџтГљТ»ЇС║▓С╗јуфЌтГљСИіуюІтѕ░С║єУ┐ЎС║Џ№╝їжАЙСИЇтЙЌУ║ФтГљСИЇуЂхСЙ┐№╝їУХ┐СИіжъІ№╝їТїфтЄ║тј╗уюІжў┐тЕєсђѓТ»ЇС║▓СИІтЈ░жўХТђДТђЦС║єС║Џ№╝їСИђСИІтГљу╗ітђњ№╝їС╗јС║ћт▒ѓтЈ░жўХСИіТ╗џС║єСИІтј╗сђѓтЄаСИфУГдт»ЪтљЊтЮЈС║є№╝їтЁеУиЉУ┐ЄТЮЦТЅХТ»ЇС║▓сђѓт╣┤жЋ┐С║ЏуџёУГдт»Ът»╣Т»ЇС║▓У»┤№╝џСйаУ┐Џтј╗№╝їСйаУдЂТюЅС║ІтЈ»т░▒Тў»СИцСИфС║║уџёС║ІС║єсђѓТ▓АС╗ђС╣ѕ№╝їТѕЉС╗гС║єУДБСИђС║ЏТЃЁтєхсђѓУГдт»ЪтЈѕУ»┤№╝џт░ЋС┐ЮтюеТѕЉС╗гжѓБжЄї№╝їтЦйуЮђтЉбсђѓТѕЉтюеТ»ЇС║▓УѓџтГљжЄїтљгтЙЌуюЪтѕЄ№╝їуЪЦжЂЊУГдт»ЪУ«▓уџёжѓБСИф“т░ЋС┐Ю”т░▒Тў»уѕИуѕИсђѓТѕЉт┐ФжђЪУйгтіеС║єСИђСИІ№╝їТііт«ЅТЁ░уџёТёЈТђЮС╝аУЙЙу╗ЎТ»ЇС║▓№╝їСИЇТЃ│ућетіЏУ┐ЄуїЏ№╝їСй┐Т»ЇС║▓уќ╝уЌЏтЙЌт╝ЊСИІС║єУЁ░сђѓУГдт»ЪТііТ»ЇС║▓ТљђТЅХтѕ░тЇДТѕ┐№╝їТЌатЦѕуќ╝уЌЏСИЇТГб№╝їтЈѕТљђТЅХтЄ║ТЮЦ№╝їТЅХтѕ░УГдУйдСИі№╝їТІЅтѕ░С╣АтЇФућЪжЎбсђѓ
У┐ЎтцЕТЎџСИіТѕЉтЄ║ућЪС║єсђѓУ║ФУЙ╣Тў»жў┐тЕєсђЂтцќжў┐тЕєсђЂТ»ЇС║▓№╝їуггС║їтцЕ№╝їУГдт»ЪжЎфтљї№╝їуѕИуѕИтѕ░уЌЁТѕ┐уюІТѕЉТЮЦС║єсђѓ
ТѕЉТѓћТЂеТъЂС║є№╝їуѕИуѕИТЮЦтѕ░уЌЁТѕ┐№╝їТѕЉТ▓АУЃйТИЁТЦџтю░уюІС╗ќСИђую╝сђѓТѕЉтцфТђДТђЦ№╝їтЄ║ућЪТЌЕ№╝їую╝уЮЏт«їтЁеуЮЂСИЇт╝ђ№╝їтЉеУ║ФтЈЉуЃГ№╝їТІ╝тЉйуЁйтіеж╝╗у┐╝тљИТ░ћ№╝їтЈ»УЃйТў»УдЂтЈЉуЃДС║єсђѓуЌЁТѕ┐жЄїтЁЅу║┐ТўЈТџЌ№╝їСИђтЈфуЎйуѓйуЂ»С╣ЪУбФТіЦу║ИжЂ«ТїАСйЈС║є№╝їТѕЉуџёую╝тЅЇТў»СИђуЅЄж╗ЉТџЌ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тє░тЄЅуџёТЅІтюеТѕЉУёИСИіТЉЕТї▓№╝їТ»ћС╗ќуџёТЅІТЏ┤тіатє░тЄЅуџёСИђСИфуАгжѓджѓдуџёжЊЂСИюУЦ┐С╣ЪУДдтѕ░С║єТѕЉуџёУёИ№╝їжѓБт║ћУ»ЦТў»ТЅІжЊљ№╝їТ▓АтЄ║ућЪтЅЇТѕЉтй▒тГљУѕгжџЈуѕИуѕИтј╗жЮњтєѕТаЉТъЌСИГуџёт░Јж╗Љт▒І№╝їтюежѓБжЄїУДЂтѕ░У┐ЄсђѓТ»ЇС║▓тцфУЎџт╝▒С║є№╝їтЄаС╣јТЌатБ░ТЂ»тю░У║║тюет║іСИі№╝їтцќжў┐тЕєСИђС╝џтё┐У┐Єтј╗ТІ┐ТЅІУ»ЋУ»ЋтЦ╣уџёж╝╗ТЂ»сђѓжў┐тЕєТійТ│БуЮђ№╝їжфѓС║єуѕИуѕИСИђтБ░№╝џСйаУ┐ЎСИфтГйжџю№╝ЂтЈѕУ»┤№╝џтЦйтЦйТііСйатЂџуџёС║Іу╗ЎтЁгт«ЅУ»┤ТИЁТЦџ№╝їС║ЅтЈќТЌЕС║ЏтЄ║ТЮЦсђѓ
СИђуЏ┤жЃйТў»У┐ЎТаи№╝їт«ХтцќтЈЉућЪуџёС║ІТЃЁжў┐тЕєтњїТ»ЇС║▓уюІСИЇтѕ░сђѓТѕЉ№╝їжЏфУі▒СИђУѕгУй╗№╝їУЃйжБјСИђУѕгУиІт▒▒ТХЅТ░┤№╝їтй▒УИфжџЙУДЁ№╝їуЕ┐УХітЄ║СИќтњїТюфтЄ║СИќуџёжѓБжЂЊжў┤жў│уЋїжЎљ№╝їТѕЉУЃйт░єТЅђТюЅС║ІТЃЁуюІтЙЌТИЁТЦџТўјуЎйсђѓтюеуѕИуѕИТІ┐С║єУ┤┤жЦ╝тГљуџёжѓБСИфТЌЕТЎе№╝їТѕЉт░ЙжџЈС╗ќтњїС╗ќуџёујЕС╝┤тё┐Ух░тЄ║ТЮЉтГљ№╝їУйгУ┐Єт▒▒тў┤№╝їтюежЮњтєѕТаЉТъЌтГљТи▒тцё№╝їУ┐ЏтЁЦСИђжЌ┤тЁЅу║┐ТўЈТџЌуџёт▒ІтГљсђѓС╗ќС╗гУ«▓С║єСИђС╝џтё┐У»Ю№╝їжЌетцќТюЅТЉЕТЅўУйдтБ░жЪ│№╝їТјЦуЮђ№╝їжЌеУбФТЋ▓тЊЇсђѓуѕИуѕИтњїС╗ќуџёујЕС╝┤тё┐СИцТЅІТіЊТ╗АтГљт╝╣№╝їжЋ┐уџёТюЅтцДС║║ТЅІТїЄтц┤жѓБС╣ѕжЋ┐№╝їуЪГуџётдѓТѕЉуџётцДТІЄТїЄжѓБУѕгуЪГ№╝ї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ТііСИђтЈфТЅІжЄїуџётГљт╝╣тАъУ┐ЏтЈдСИђтЈфТЅІ№╝їУх░У┐Єтј╗ТЅЊт╝ђжЌесђѓСИђжЂЊтѕ║ую╝уџётЁЅУіњт░ёУ┐Џт▒ІжЄї№╝їуЎйтЁЅСИГТЎЃтіеСИђСИфТѕ┤уІљуџ«тИйуџёжЮњт╣┤ућитГљУ║Фтй▒№╝їС╗ќуџёУЌЈУАБУцфСИІС║єСИцтЈфУбќтГљ№╝їУЄЃУѓ┐тю░у╗ЙтюеУЁ░жЎЁсђѓт╣┤Уй╗С║║уѓ╣С║єуѓ╣тц┤№╝їу«ЌТў»УиЪуѕИуѕИС╗ќС╗гТЅЊС║єТІЏтЉ╝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УхХт┐ЎТјеСИіжЌеТЅЄ№╝їт▒ІтГљжЄїуФІТЌХж╗ЉтЙЌуюІСИЇТИЁт»╣жЮбС║║уџёжЮбтГћсђѓСИЅС║║ТЉИж╗Љуѓ╣ТЋ░тГЌ№╝їтцДТдѓТў»тюеТЋ░тГљт╝╣сђѓуеђжЄїтЊЌтЋдтЊЇС║єСИђжўх№╝їт╣┤Уй╗С║║жЂЊ№╝џтЎХуюЪтѕЄ№╝ѕУ░бУ░б№╝Ѕ№╝ЂТјетЄ║жЌетј╗сђѓ
уѕИуѕИтњїС╗ќуџёујЕС╝┤тё┐ТЅІтюет┐ЎТ┤╗№╝їтѕитѕиуџётБ░жЪ│Уѓ»т«џТў»тюеТЋ░уЦетГљсђѓтБ░жЪ│тѕџтѕџТїЂу╗ГС║єСИцСИЅтѕєжњЪ№╝їжЌетєЇТгАУбФТјет╝ђсђѓУ┐ЎТгАтіЏт║дтЙѕтцД№╝їжЌеТЅЄСИђСИІтГљТЅЊт╝ђ№╝їуб░тѕ░тљјжЮбуџётбЎ№╝їуФІтѕ╗УбФт╝╣С║єтЏъТЮЦ№╝їтЄаСИфУГдт»ЪжЌ»С║єУ┐ЏТЮЦ№╝їСИЇућ▒тѕєУ»┤№╝їуѕИуѕИтњїС╗ќуџёујЕС╝┤тё┐У┐ътљїС╗ќС╗гТЅІжЄїТюфУбФТЇѓуЃГуџёуЦетГљжЃйУбФТћХУх░№╝їуѕИуѕИтњїС╗ќуџёујЕС╝┤тё┐УбФТѕ┤СИіжЌфС║«тє░тєиуџёТЅІжЊљ№╝їУбФтИдУх░С║єсђѓ
т░ЈтЇќжЊ║тЁ│С║єтЦйтЄатцЕ№╝їжў┐тЕєтєЇТЌат┐ЃТђЮТІЏтЉ╝жѓБт░Јт░ЈуџёућЪТёЈ№╝їуЮАтђњС║єсђѓтЦйтюетЄатцЕтљјТѕЉтЄ║ућЪС║є№╝їжў┐тЕєтњїТ»ЇС║▓т┐ЎубїУхиТЮЦ№╝їТџѓТЌХТиАт┐ўС║єуѕИуѕИуџёС║Ісђѓ
т«ъжЎЁСИі№╝ї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ТюЅТГБтйЊУЂїСИџ№╝їТў»у▓«уФЎуџёУЂїтиЦ№╝їтЇќжЮбтЇќТ▓╣№╝їтЇќТЮЦтЇќтј╗№╝їу╗ЊУ»єС║єСИЇт░ЉУАїУАїжЂЊжЂЊжЄїуџёС║║№╝їуфЂуёХСИђТ«хТЌХжЌ┤тќютЦйСИіС║єТЅЊуїј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т╝ёТЮЦСИђТЮєТъф№╝їТІ┐тѕ░ТѕЉт«ХТўЙТЉєсђѓжў┐тЕєСИЇт«бТ░ћтю░У«ЕС╗ќТііТъфТІ┐тѕ░тцќУЙ╣№╝їУІЦСИЇ№╝їСИЇтЄєУ┐ЏТѕЉт«ХтцДжЌе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УхћуЮђугЉУёИ№╝їС┐ЮУ»ЂСИЇтєЇТІ┐Тъфу╗ЎуѕИуѕИуюІсђѓжѓБС╗Цтљј№╝їуѕИуѕИС╗ќС┐Еуб░жЮбуџётю░уѓ╣Тћ╣тѕ░т«ХтцќС║єсђѓ
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ТЅЊуїј№╝їтј╗тЙѕУ┐юуџёт▒▒жЄї№╝їУиЉСИђтцЕ№╝їтЈѕжЦЦтЈѕТИ┤№╝їСЙ┐тѕ░уЅДТ░Љт║ётГљжЄїУ«етљЃтќЮсђѓуѕИуѕИУиЪС╗ќтј╗уџёжѓБСИђтцЕ№╝їС╗ќС┐ЕС╗ђС╣ѕС╣ЪТ▓АТЅЊуЮђ№╝їтЇЂтѕєТ▓«СИД№╝їуќ▓ТЃФСИЇтафтю░СИІт▒▒ТЮЦтѕ░т║ётГљжЄї№╝їуггСИђСИфжЂЄтѕ░уџёТў»жѓБСИфт╣┤Уй╗С║║сђѓт╣┤Уй╗С║║УДЂС╗ќС┐ЕУЃїуЮђТъф№╝їую╝уЮЏСИђС║«№╝їжю▓тЄ║угЉт«╣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У»┤№╝џућ▓УдЂТа╝№╝ѕТюЅУїХтљЌ№╝Ѕ№╝Ът╣┤Уй╗С║║У┐ъУ┐ъуѓ╣тц┤№╝џУдЂТа╝№╝ѕТюЅ№╝Ѕ№╝ЂУдЂТа╝№╝ѕТюЅ№╝Ѕ№╝ЂтИдС╗ќС╗гтѕ░УЄфти▒т«ХжЄїсђѓт╣┤Уй╗С║║т«Хт«бтјЁТГБСИГућЪСИђСИфТќ╣тйбтцДуЃцуѓЅ№╝їт║ДтюеСИіжЮбуџёжЊютБХуЏќтГљтЏЏтЉетєњуЮђУѓАУѓАуЎйТ▒й№╝їтБЂТЪюжЄїТЉєуЮђСИђТЉъТЉъжћЃС║«уџётЁФт«ЮуЊиубЌсђѓСИђСИфУђЂт╣┤С║║тЮљтюеуџ«Т▓ЎтЈЉСИітќЮУїХсђѓУђЂт╣┤С║║тњїУћ╝тю░уюІуюІуѕИуѕИтњїС╗ќуџёујЕС╝┤тё┐№╝їТЅІТїЄТ▓ЎтЈЉУ»┤№╝џтѕ░№╝їтѕ░сђѓуц║ТёЈС╗ќС╗гтЮљСИІТЮЦсђѓт╣┤Уй╗С║║т╝ђтДІТІЏтЉ╝уѕИуѕИС╗ќС╗гсђѓ
тЏ┤уЮђуЂФуѓЅтќЮУїХ№╝їтљЃу│їу▓Љ№╝їУ┐ўТюЅт╣▓уЅдуЅЏУѓЅ№╝їт╣┤Уй╗С║║ТїЄуЮђуѕИуѕИујЕС╝┤тё┐ТђђжЄїуџёТъф№╝їућеТЅІТїЄТ»ћућ╗С║єСИђСИІ№╝їжЌ«№╝џтГљт╝╣УдЂТа╝№╝ѕТюЅ№╝Ѕ№╝ЪС╗ќтЈѕУ»┤№╝џу╗ЎСйаС╗гжФўуЉъТ»Џ№╝ѕжњ▒№╝ЅсђѓуѕИуѕИуџёујЕС╝┤тё┐жЌ«№╝џтцџт░Љ№╝Ът╣┤Уй╗С║║С╝ИтЄ║тЄаСИфТЅІТїЄтц┤сђѓуѕИуѕИТюЅуѓ╣Т┐ђтіе№╝їуюІС║єујЕС╝┤тё┐СИђую╝№╝їујЕС╝┤тё┐ТЌЕти▓ТїЅТЇ║СИЇСйЈтЁ┤тЦІ№╝їую╝уЮЏжЄїтєњтЄ║уЂФУі▒№╝їтЈБТ░ћтЇ┤ТЋЁСйюСИЇС╗ЦСИ║ТёЈ№╝їТЉЄтц┤У»┤№╝џт░ЉС║є№╝ЂСИЇТѕљ№╝ЂСйауЪЦжЂЊтГљт╝╣СИЇтЦйТљъ№╝їт╝ёСИЇтЦйС╝џУбФУГдт»Ъжђ«Ух░тЉбсђѓт╣┤Уй╗С║║тЈѕС╝ИтЄ║СИђСИфТЅІТїЄтц┤№╝їујЕС╝┤тё┐жЂЊ№╝џтЦй№╝ЂС╗ќС╗гСИЅСИфТІЅС║єСИђСИІТЅІ№╝їтЊѕтЊѕтцДтБ░У»┤угЉ№╝їтќЮУїХтљЃУѓЅсђѓт╣┤Уй╗С║║У»┤№╝џС╗ЦтљјСйаС╗гУ┐Џт▒▒т░▒ТЮЦУ┐ЎжЄї№╝їТЮЦУ┐ЎжЄїтќЮУїХтљЃУѓЅ№╝їУ┐ЪС║є№╝їуЮАтюеУ┐ЎжЄїсђѓТѕЉС╗гуџёТЮ┐уѓЋтцДуЮђтЉбсђѓУ┐ЎТаи№╝їуѕИуѕИтњїС╗ќуџёујЕС╝┤тё┐СИјт╣┤Уй╗С║║т░▒ТѕљТюІтЈІС║єсђѓ
уѕИуѕИтє░тЄЅуџёТЅІу╝ЕтЏътј╗С║є№╝їтє░тЄЅуџёТЅІжЊљС╣Ъу╝ЕтЏътј╗С║є№╝їС╗ќТи▒Ти▒СйјСИІтц┤УйгУ┐ЄУ║Фтј╗сђѓС╗јС╗ќуџётљјУЃї№╝їТѕЉуюІУДЂС╗ќу║бу║буџёт┐ЃУёЈУи│тЙЌтЙѕСИЇУДётЙІ№╝їСИђС╝џтё┐ТЁб№╝їСИђС╝џтё┐т┐ФсђѓС╗ќтЏътц┤уъЦС║єТѕЉСИђую╝№╝їУх░тЄ║тј╗С║єсђѓТѕЉуЪЦжЂЊС╗ќуџёт┐ЃтЙѕжџЙУ┐Є№╝їжЃйСИЇУЃйТГБтИИУ┐љСйюС║є№╝їтє│т«џСИЇУиЪС╗ќтј╗№╝їуЋЎтюет«ХжЄї№╝їСИјжў┐тЕєтњїТ»ЇС║▓СйюС╝┤сђѓТІ┐т«џСИ╗ТёЈ№╝їТѕЉтЄєтцЄућюућютю░уЮАСИђУДЅсђѓУ┐иУ┐иу│іу│іСИГ№╝їУѓџтГљСИђУй╗ТЮЙ№╝їСИІУ║ФСИђтБ░Уй░тЊЇ№╝їТђјС╣ѕт░▒УЄфти▒т░єУЄфти▒ТЃіжєњС║є№╝їТѕЉСИЇуЪЦжЂЊсђѓ
жў┐тЕєуюЅт╝ђую╝угЉ№╝їжЂЊ№╝џт▒ЂТћЙтЙЌУ┐ЎТаитЊЇ№╝їжЋ┐тцДС║єТў»СИфТюЅтЄ║ТЂ»уџёућитГљТ▒Ѕ№╝Ђжў┐тЕєТјЦуЮђтЈ╣С║єСИђтЈБТ░ћсђѓТѕЉжЌГую╝С╣ўжў┐тЕєуџёжѓБтЈБТ░ћуЦъжђЪУ┐йУхХСИіуѕИуѕИсђѓжў┐тЕєуџёжѓБтЈБТ░ћУхитЁѕуЃГС╣јС╣јуџё№╝їтЁЁТ╗Ауќ╝уѕ▒тю░ТіџТЉИуѕИуѕИуџётц┤УёИтњїУѓЕУєђ№╝їтљјТЮЦтЈўтєиС║є№╝їтюеуѕИуѕИУЃїСИітЂюуЋЎС║єСИђС╝џтё┐№╝їТъюТќГуд╗т╝ђ№╝їТѕЉС╣ЪтЈфтЦйУ┐ћтЏъсђѓжў┐тЕєуџёую╝тЁЅТЁѕуЦЦтЙЌтЙѕ№╝їТі▒ТѕЉтюеТђђжЄї№╝їС╣Ёу╗Јт▓ЂТюѕтЈўтЙЌТЪћжЪДтЈѕу╗хУй»уџёУёИжбіУ┤┤СИіТѕЉуџёУёИ№╝їт»╣ТѕЉУ»┤№╝џТў»СИфТюЅтЄ║ТЂ»уџёућиС║║Тў»СИЇТў»№╝ЪТѕЉСИЇС╝џуѓ╣тц┤№╝їСИЇС╝џТЉЄтц┤№╝їт░▒тњДС║єтњДтў┤№╝їу«ЌТў»т║ћТЅ┐сђѓжў┐тЕєСИЇТё┐ТёЈТѕЉтЃЈуѕИуѕИсђѓ
тцќжў┐тЕєУ»┤№╝џтеЃтеЃтЃЈСйатцџСИђуѓ╣тё┐сђѓтцќжў┐тЕєТїЄуџёТў»Т»ЇС║▓№╝їУ»┤У»ЮуџёТЌХтђЎУ┐ЁжђЪУйгтц┤уюІС║єжў┐тЕєСИђую╝№╝їУ┐ЎТЌХтђЎтЦ╣ТЈљжЃйСИЇТё┐ТЈљуѕИуѕИсђѓтцќжў┐тЕєТјЦуЮђУ»┤№╝џж╝╗ТбЂТї║Тї║уџё№╝їт░єТЮЦтЂџС║ІУѓ»т«џТюЅСИ╗ТёЈсђѓжў┐тЕєУёИСИітЙѕт╣│жЮЎ№╝їУ»┤№╝џТў»тЃЈС╗ќжў┐тдѕтцџСИђС║ЏсђѓТ»ЇС║▓СИЇуюІтЦ╣С╗гСИцС║║№╝їтЪІтц┤УЄфжАЙУЄфтЙ«угЉ№╝їТЅІжЄїСИђт╝аСИђт╝атЈаТѕЉуџёт░┐уЅЄсђѓ
ТїЅуЁДжў┐тЕєтЦ╣С╗гуџёТё┐ТюЏтЂџСИфТюЅСИ╗УДЂТюЅтЄ║ТЂ»уџёућитГљТ▒Ѕ№╝їУ┐ўУдЂСЙЮуЁДТѕЉтЅЇСИќУдЂТ┤╗тЙЌт╣│ТиАу«ђтЇЋуџёт┐ЃТё┐№╝їТў»СИфжџЙжбў№╝їТѕЉуЪЦжЂЊуџёсђѓСИЇУ┐Є№╝їтѕџтѕџУйгСИќ№╝їТ╗АТђђТќ░ж▓юуџёТѕЉтЙѕТЃ│У»ЋУ»ЋсђѓТѕЉуюІтѕ░жў┐тЕєсђЂтцќжў┐тЕєсђЂТ»ЇС║▓тЦ╣С╗гжЃйтЙѕт╝ђт┐Ѓ№╝їтЈфжАЙжђЌТѕЉ№╝їт┐ўС║єт┐ДТёЂ№╝їТѕЉСИЇТЃ│У┤ЦтЦ╣С╗гуџётЁ┤УЄ┤сђѓ
тјЪтѕіС║јсђіжЮњТхиТ╣ќсђІ2018т╣┤1ТюЪ№╝ѕУ┤БС╗╗у╝ќУЙЉ№╝џУїЃу║бТбЁ№╝Ѕ

т«їујЏтц«жЄЉ№╝їтЦ│№╝їУЌЈТЌЈ№╝ї1962т╣┤ућЪ№╝їуј░СЙЏУЂїС║јућўУѓЃуюЂућўтЇЌУЌЈТЌЈУЄфТ▓╗тиъТќЄУЂћсђѓсђіТа╝ТАЉУі▒сђІСИ╗у╝ќ№╝їу│╗СИГтЏйт░ЉТЋ░Т░ЉТЌЈТќЄтГдтГдС╝џС╝џтЉўсђЂућўУѓЃСйютЇЈС╝џтЉўсђѓ1982т╣┤УхитЈЉУАеУ»ЌТГїсђЂТЋБТќЄСйютЊЂ№╝їтЁЦжђЅсђітЦ╣С╗гуџёТіњТЃЁУ»ЌсђІсђіСИГтЏйтйЊС╗БтЦ│У»ЌС║║У»ЌжђЅсђІсђіУЦ┐жЃеуџёТіњТЃЁсђІсђіУЌЈТЌЈтйЊС╗БУ»ЌС║║У»ЌжђЅсђІсђіућўУѓЃуџёУ»ЌсђІсђі21СИќу║фт╣┤т║дТЋБТќЄжђЅсђІуГЅСИЊжЏє№╝їУЉЌТюЅУ»ЌжЏєсђіТЌЦтй▒•ТўЪТўЪсђІсђіт«їујЏтц«жЄЉУ»ЌжђЅсђІсђЂТЋБТќЄжЏєсђіУДдТЉИу┤ФУЅ▓уџёУЇЅуЕЌсђІ№╝їтцџТгАУјитЙЌуюЂу║ДС╗ЦСИітЦќті▒сђ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