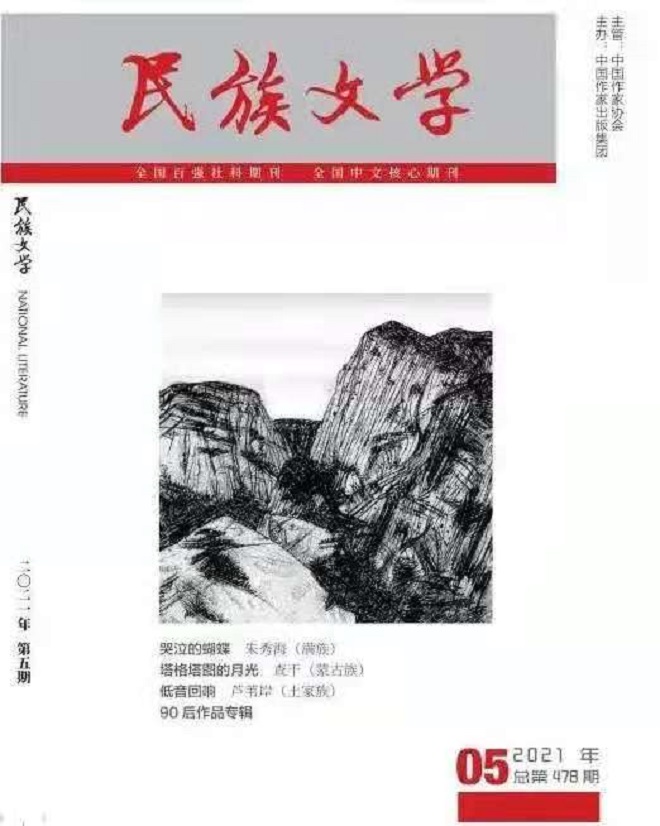
一
阳光温暖如水,抚慰着老木匠衰老的身子。
他斑白的头颅一点点往下坠,直到差点掉进自己怀里,才惊醒过来。“真是老了。”他抹了抹流到嘴角的口水,再次直起身子,感受太阳的恩赐。
老木匠一早上就没有挪过屁股,他从未如此感恩太阳的温暖。他用手搭起凉篷,感激地看了看天,太阳的一个回眸,让他的老眼直冒金星,双眼连眨了十几次,才总算看清眼前的东西,他不甘心,再次用手搭起凉篷,看看远处,这一看就有些泄气,春天的山川还是一身重重的褐色,远没有返青的迹象,他发出了一声浑浊的叹息。他把眼光收了回来,停在屋前的大树上,不知何时,它已蹿至二楼高,光秃秃的灰色枝条锋利地刺向天空,企图捅破天的秘密。这并不是树的意思,是他自己的意思。他的内心急切地渴望着一根比占卜师更灵验的魔杖,一个星期以前的一次提亲,让他越来越看不懂这社会。如果占卜师能预见到这件事不成,该有多好,他也不会自以为是地去提亲,他这张老脸……
老木匠顶着木匠的名号,却不摸刨子锯子有些年头了。前些年,他还时常拿出“老伙计”,修补家里的物件,可手与工具之间的默契感,再也找不到了,有一次还差点削了自己的手,这件事他当然羞于跟别人说。从那时起,他再也不摸那些家伙了,连钉钉子的事都不管了。缘分尽了。听到有人喊他木匠,他也不应答,装作听不见,直到喊他的本名,他才如梦初醒般应一声。
老木匠还是小木匠时,手艺就在协噶尔村一带冒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破旧损毁的寺庙迎来维修高潮,那是他的人生辉煌期,那么多寺庙在他手下新生,那么多徒弟在他手下成长,那些信徒见到他如见到高僧般崇敬,民间也有人为他编了好几段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一段是:“在维修某个古寺时,一根横梁必须换掉,但稍有闪失,就可能寺庙坍塌,作为施工队的灵魂,老木匠静等所有工作人员进到殿内后,用一把大铁锁锁住大门,威严地说,我们都在一起了,开始吧。”以至于在协噶尔村一带,“开始吧”这句话不再只是简单的开始的意思,更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意思。有人就这个传说,专门向老木匠求证过,但他不说话,这个传说就变得更神秘了。
老老木匠也以他为傲,可骄傲了没多久,发现村里人家有活儿要做,包着砖茶的哈达直接交到了老木匠手上,老老木匠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毕竟他是他的父亲,是他的师傅,更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钦莫啦(大师傅)。老老木匠和老木匠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爱面子,这之后,老老木匠对儿子忽冷忽热,老木匠对父亲时敬时撞,两人拧巴着过了半辈子。但老木匠的手艺再高,也没有高过老老木匠的寿命,待到老木匠干不动了,老老木匠才松了一口气,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也带走了“钦莫啦”这个称号。不管老木匠的手艺被传得多么神奇,也不管他脸上的皱纹如何沟壑纵深,在村民嘴里,他仍是乌琼啦(小师傅),这个名字像长在他的身上,揭也揭不掉,恐怕只能带到天葬台去。
老木匠衰老,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这是他自己的发现,他总以为衰老是个过程,今天一道褶子明天一道褶子,万没想到衰老就在刹那间,也许就在那女人带来不好消息的瞬间,他一个人喝了很多青稞酒,第二天发现自己浑身懒懒的,直想睡觉,他觉得那是喝了太多酒的缘故,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此后没有一天不是浑身懒懒的。
老木匠还是个小年轻时,拥有了协噶尔村第一辆自行车。后座上捆着他的木工工具包,车把上挂着一桶青稞酒,车铃敲得叮铃铃直响,看到村头晒着太阳的老头老太太,打一声招呼,“送太阳呐”,然后头也不回地出村去,任那些老头老太太在后头骂他。现在,他自己也成了“送太阳”一员,从东边迎接太阳,再将太阳送到西方的山后,他的心里也从未像现在一样,感觉到太阳的伟大。这个发现也让他格外能体谅老老木匠。他可能也不是慢慢变老的,也许是在村民绕过他找自己时,一下子变老的。这个老不是皱纹,不是白发,而是提不起劲的老。现在的他,特别后悔说了一些冲撞人的恶语,想起老老木匠像婴儿一般躺在床上,讨好地朝他微笑的情景,他的眼睛不觉酸涩起来。
轿车急刹的声音打破了他的遐想,他起身走到晒台边沿,只见邻居家在城里做导游的儿子从车上跳下来,从后备厢拿出几个大包。一股莫名的怒气突然而至,他立刻退回坐垫前。
“你还在屋顶吗?”偏偏这时传来妻子的声音,好在这声音也没有了以往的尖利,软绵绵的有气无力,轻得能被风吹走。
“乌琼啦,晒太阳呢?我就说看到人影一晃,原来是您在晒太阳呢。”
妻子有气无力的声音还是被邻居家儿子听到了。老木匠心里骂着妻子,没好气地说:“你回来了?”
“这不马上春耕节了吗?我送些布料过来,顿旦说,做藏装的人太多了。”
“这样啊,那你赶紧吧。”老木匠说完退回坐垫上,再次眯着眼睛感受太阳,平静的心海却掀起了波涛。这时,木质楼梯吱吱作响,他的妻子用围裙搂着酒壶上来了,专属他的银质酒碗边上,点着一块酥油,碗底放了一些糌粑,酒从壶嘴落到糌粑上,“嗞”的一声冒出很多气泡,待气泡退下,青稞酒还咝咝地欢腾了一会儿。
“头道酒呢,快喝吧。”
记忆中给他喝头道酒的只有阿妈。阿妈总是神秘地把他叫到黑黑的酿酒房,看着他把酒喝完,然后一手抓着他的小脑袋一手抹着他的嘴说,好喝吧。阿妈从不给老老木匠喝头道酒,她说那人呀,看人分不出善恶,品酒分不出好坏。自己的媳妇有没有给小木匠喝过头道酒,他是不知情的,他只知道小木匠从不跟村里的男人聚会喝酒,他只喜欢喝那种叫可乐的饮料。
“您别多想了,还是念念经吧,您不是常说这世间万事都是命中注定吗?”
妻子对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敬语,这使他稍感安慰,也让他略有不安。女人真是琢磨不透,年轻时出门做活儿挣钱,她总是怨这怨那,尖声利气的,现在老了没用了,挣不到一分钱,反倒又是敬语又是呵护,不知道是尊敬还是可怜。
二
小木匠是老木匠最小的儿子,顶着个木匠的名号,却没干出什么名堂,在村里,几乎没人叫他木匠,都是直呼其名——丹增。
丹增学成出师时,村里建房都喜欢安钢窗,家具也都进城购买,要是提议请人打制家具,他们就会说,太麻烦了,请个木工,好吃好喝伺候,还要赔笑,不合心又不能退货,到市场购买还能挑挑拣拣。有人说,请木匠来做更结实耐用。他们就说,要那么结实干吗,又不能活两辈子,好看就行了,这时代那么善变,谁知道儿孙当家时又流行啥样。协噶尔村有人说,从城里的自由市场拉来一车描金涂绿的家具,就能让房间开出花来。
丹增本就不喜欢这个行当,想着到城里卖力气也比这行当自在,当他对这行当表现出淡漠时,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致愕然,仿佛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成为一名木匠。老木匠唠叨训斥嘲讽的话语每天都向他射去,仿佛丹增这个小傻瓜竟然拒绝接受财富的金钥匙,连最疼他的阿妈,脸上也写满了失望,她日日夜夜盼来的男孩子,居然不明事理。他想投奔在城里包工程的姐夫们,两个姐姐同时跳出来反对,一个小工的诞生,将为木匠世家的光环蒙尘。尽管这些光环没有给她俩带去过任何实际利益,但仍是她们在婆家的骄傲与信心之源。家人的反对,在丹增看来都不占理,但还能接受,可村中的长者们也出来反对,他就纳闷了。他们说,谁都可以出去打工,但丹增不能,协噶尔村最有名的木匠家后继无人,那就是协噶尔村的损失,这个家族没落了协噶尔村也就没落了,但当他们的房子重新修建时,当他们的家里添置家具时,从来想不到协噶尔村还有个木匠世家。
丹增意识到自己是为顶着一个名号而存在时,这个被阿妈调教得满口敬语的孩子,没有像他的同学那样,愤怒地跳上一辆开往城市的货车一走了之,也没有大吵一架宣示自己的成长和叛逆,他顺从地接受了这个安排。从骨子里讲,他也是眷恋乡村的,恬静的晨曦,孤独的黄昏,翠绿的夏季和金色的秋天,每一样风景都令他不舍。尽管他学成之后,还从来没有一个令他骄傲的“作品”,他不能对着某个建筑或家具说,这是我做的。与其说他是木匠,还不如说是个修补匠,哪家的木门关不上,需要刨一下,哪家的家具开裂,需要嵌一个楔子,都是理所当然地找丹增,有的更夸张,连换个铁锹把子,也要请丹增。丹增从不拒绝,准确地说是羞于拒绝,从来都是提上工具包就走,顺手还抓一把糖果,父母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们,总是眼巴巴地看着他裤兜里的可乐。这种小活儿的工钱一般都是“谢谢”,大方一点的就是“非常感谢,帮了大忙。”当然每家都会端上茶满上酒,丹增却一口不喝,干完活儿坐在别人家的垫子上,聊聊天气,从裤子后兜掏出半瓶可乐,“吱”一声喝一口,多少像个城里青年,要说丹增在协噶尔收获了什么,那就是一堆好词:孝顺、听话、礼貌、规矩。
常年戴墨镜的顿旦,是丹增一起长大的玩伴,也一样成了手艺人。他学艺时,村里人没几个看好他。他有个双胞胎哥哥,他俩八岁那年,在初秋的麦田打闹,哥哥挥舞着麦穗追他,麦芒戳中了他的右眼。两兄弟担心挨父亲揍,瞒着父母躲到外面,等到实在瞒不住了为时已晚,顿旦的右眼彻底废了。之后,他戴着墨镜去学了裁缝,村里炸开了锅。不光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的他,去学了最费眼睛的裁缝,更重要的是,那时,村里时兴穿便服,小年轻更是人手一条牛仔裤,都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十年后没人会穿复杂的藏装。但世事就是那么难料,也不知是从哪天起,流行的朝向突然变了,城里流行开了各种面料轻薄、花色繁多,穿脱简便的藏装,连游客都喜欢买着穿,这一流行就流到了村里。顿旦想闲着都不行了,今天这家明天那家的,请来请去。他是个有心人,给年轻女人做衣服时还附送一些搭配技巧,渐渐地俘获了好多女人的心,约他上门做衣服至少要提前一周。后来,一直为刺伤弟弟的眼睛而心怀内疚的双胞胎哥哥,从城里批发各种布料,让他在家里做,这一招如美酒招酒客,附近村庄的裁缝都被吸引了过来,形成了制衣厂。顿旦还收了徒弟,成了师傅。每到春耕节、望果节前夕,顿旦家踩缝纫机的声音,伴着师傅们的劳动歌声,像万马奔腾,声势壮观。协噶尔村的人,眼瞧着顿旦的脸慢慢油润,肚子慢慢凸起,那个本用来遮掩的墨镜,换了一副更时尚的宽边镜。
丹增偶尔路过裁缝顿旦家门口,顿旦看见了或者听说了,都要请他进来坐坐。一起长大一起捣蛋的经历,让他们像亲兄弟。丹增说找不到人玩台球,顿旦再忙也要放下手中的活儿,两人骑着摩托车到县城玩一把。
顿旦和丹增一起玩,顿旦那有远见的阿妈从不说什么。她永远忘不了丹增拉着顿旦的小手,每天放学都将他送到家里的往事。她曾跟他说,顿旦还有一只眼睛,你不用每天都送他回家。丹增不理会,到哪里都牵着顿旦,从家里拿来的奶糖,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直接给他,而是剥开糖纸细心地送到他的嘴里。冬天村里的冬麦灌水,弄得通往学校的路上都是水和冰碴,丹增用鞋带把鞋子挂在脖子上,睬着刺骨的冰水背着顿旦上学。顿旦的阿妈在房顶上晾酒糟看见那一幕,一个人哭了很久很久,自那天后,她看丹增的目光也是看儿子的目光。
三
协噶尔村离县城近,春耕前的农闲时光,协噶尔村人基本都在县城泡掉了。
县城最有名的茶馆就是协噶尔村人开的,茶馆招牌上写着“幸福茶馆”,协噶尔村人却管它叫“梦想茶馆”。这个名字来源于茶馆主人——琼珠。琼珠年少时,长相俊秀,被选拔参加了某个运动会开幕式,在大家向往的拉萨集训了三个月,又在电视上露了面,后来又代表县藏戏队到罗布林卡演戏,扮演过美丽的拉萨姑娘。从此,拉萨成了她的梦想。
琼珠在协噶尔村年轻女孩中找不到一个知音,她和她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但凡村里有工作组来,不管是县上市上的还是自治区的,协噶尔村的年轻女孩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有时入户调查,还要害羞地藏起来。只有琼珠是主动去找工作组,只要听说有工作组来,不管是在开会,还是在调研,她都能找到,手里拿着她两次到拉萨参加文艺活动的演员证,寻求某种机会。她自荐时,背挺得直直的,眼神从不躲闪,说话一字一顿,不慌不忙。她的推荐词是请县文艺队的编剧起草的,感情真挚细腻,让人印象深刻,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工作组帮她寻到什么机会,但大家对她记忆深刻,据说,很多来过协噶尔村的工作组成员,想不起协噶尔村村主任的名字,却记得琼珠,常有人问她到底去了拉萨没有?
一次次的杳无音讯,没有让琼珠忘记梦想,她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放音乐,重温开幕式舞蹈,春夏秋冬不间断地播放,让协噶尔村八九十岁的老人都能哼唱这段旋律。她家的牛羊,也是听惯了琼珠的藏戏片段,偶尔有人路过哼唱一段,都要“哞哞”地配合一下。
梦想茶馆的红火,改变了村里对琼珠的些许看法。琼珠终于不做梦了,踏踏实实地做起了事。可是,客人较少的时候,她还是喜欢搬个凳子托着腮望着远方。
协噶尔村的年轻人自然就把春日光阴浪费在梦想茶馆,在别的茶馆浪费掉还觉得对不住协噶尔村,把挣来的钱花到别村的茶馆,有一种背叛的意味,从来不喜欢喝甜茶的丹增,也要在茶馆点一罐可乐,听一听别人聊天。梦想茶馆因此也成为协噶尔村的新闻传播中心,谁家添置了什么,谁家有什么矛盾,谁有某种打算,基本上都是从这里传播开来,当然,这些信息与事实相比稍有夸大,或者缩小。老木匠家了解协噶尔村的情况,基本就是靠丹增泡茶馆。
这些天,丹增不去茶馆了,也不到顿旦家看着他忙,更不到县城打台球了。他就在家里帮着阿妈做活儿,这一忙发现阿妈这一天到晚要做的事太多,琐琐碎碎,一件连着一件,一整天屁股都挨不上垫子。想着家里的两个男人,一个在房顶上叹气,一个在县城瞎逛,不觉有些愧疚。
丹增正想着,拴在门口的斯珠聒噪起来,然后重重的大门被推开了,门上挂着的铁铃铛跟着响起来,顿旦和他的双胞胎哥哥前后脚走了进来。顿旦一见丹增便是一拳,活着呢?怎么悄无声息的,酥油灯都准备好了呢。协噶尔村的年轻人喜欢学着老辈人的幽默,以显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但总是有那么几分不对味不自然。丹增也没有平时的从容,一脸不自在,甚至连脸颊都变得绯红。顿旦的双胞胎哥哥也是丹增的同学,在城里做导游久了,与丹增就没那么亲近。
老木匠沉浸在心事中,对楼下的动静毫无察觉,等倒尽酒壶里最后一滴酒,他朝楼下喊了一声,再拿点酒来。稍后,从木梯洞口上来了三个人,为首的顿旦单手握个塑料酒壶。“叔叔还是会享福,跑到楼上和太阳聊天。”顿旦还是那么幽默,老木匠堆到一起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了,但这不是高兴地舒展,而是惊异地舒展。他也想开个玩笑回敬一下顿旦,可怎么也想不出来,咧嘴弄出一个很难看的笑。
“叔,给您做了一件皮袄,今年城里很流行,过年都穿这款式。”顿旦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件皮袄披在老木匠身上。
老木匠一下子弹开身子,“不不,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顿旦捡起掉在地上的衣服,几乎是摁着老木匠再次披到他身上,老木匠还想推托,无奈顿旦的手劲太大,整个人动弹不得。他再次咧嘴弄出一个更难看的笑,老木匠真不明白他兄弟俩在搞什么鬼?
看着老木匠披上皮袄,兄弟俩一个劲地夸皮袄配老木匠最合适,丹增也在一旁附和着。老木匠却一改平日的谦恭,唱起反调了,“哈,这城里人,净穿些假皮假毛的,披在身上没有一点分量,还不如我那件旧羊皮袄。”
丹增一听这话,耳根都红了。顿旦却没表现出半点尴尬,争辩道:“衣服轻便点多好,干活儿都利索。”
“这么轻还能御寒?就图个好看嘛,就跟驴粪似的,外面光鲜里面草渣。”
丹增羞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顿旦却笑得不行,取下墨镜擦拭笑出来的泪。顿旦的双胞胎哥哥正经地说:“乌琼啦,您不知道啊,现在的人都喜欢轻便。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木匠行业不景气,也是因为我们做得太笨重,大家都喜欢轻型的,漂亮的,不追求传子传孙,我们要跟上这种变化,我们不是有句老话嘛,‘不合主人之意,再好的技艺也白瞎’。”
一听“乌琼啦”三字,老木匠就火了,再细听后面那些话,简直就是三岁孩童给老人唱古戏,火更大了。他时常跟嫁出去的女儿们讲,在婆家要懂得忍耐,即便肚子里着了火,也不要从鼻孔冒烟。轮到他自己却做不到了,他像个不讲道理的顽皮孩子,嘴硬道:“我就喜欢厚,喜欢厚重,这什么世道,都喜欢轻,呸,轻飘飘的让人讨厌。”
顿旦的双胞胎哥哥被老木匠唬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面色戚戚。顿旦还在笑,他再次用双手摁住老木匠的肩膀说道:“叔,这件您穿着,等来年我再给缝件真皮的,保证又厚又重,让您动弹不得。”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能这样对待客人呢,人家还是带着礼物来的。真是给老马治癣还被反踢一脚。”丹增给阿妈讲阿爸的无礼时,显得非常气愤。
“他们是心有愧疚,假装好人。要真长癣还轮不到他们来治,你爸吃的盐比他们吃的糌粑还多,发脾气是对的,要不然还以为我们一家都是绵羊呢,几十年的邻里,哪能让人这样难堪。”
丹增当然知道阿妈指什么。“人家又没说是哪家,你们怎么认定是他家呢?”
“你不也觉得是他家吗,现在人家送件假羊皮袍子你就变了?”
丹增的心里确实有些变化了,他觉得自己可能误会了顿旦,或者是顿旦父母所为,他不知情也是有可能的。
四
那天很奇怪,琼珠的阿妈走到丹增家的院子里,也没人察觉到,平日里喜欢逢人乱叫的斯珠也哑了。她一手提着一桶酒一手提着暖瓶,背上还背着个木筐,丹增正坐在院里修补缺了一条腿的凳子,一回头就看见了她。他以为自己天天挂念着她家的回复,就梦见了琼珠她妈。恰好这时阿妈从里屋走来,看见这一幕,赶紧满面笑容请琼珠她妈进来坐。丹增是事主,不好意思在场,便找了借口带着一颗慌乱又激动的心出门打台球去了。
估摸着客人已走,丹增哼着小曲进了家门,却见阿爸和阿妈面无表情对坐着,面前的长桌上端放着他亲自去城里买来的绿色缎子料藏装、浅绿色衬衣、围裙和砖茶,每一件都错不了,是城里藏装店的女店主亲自帮他搭配的。为了保密,他没有麻烦好朋友顿旦。丹增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明知故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呢,反悔了呗,我活这么长时间,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种事,整个协噶尔村可能也没有发生过第二件吧。”阿妈黑着脸说。
老木匠显然还不知道该如何评判这件事,满脸的不解,满眼的怨怒,全冲着小木匠发来:“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别人瞧不上眼也是情有可原的。”
丹增也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自己一直顺着父母的意愿,怎么就变成了不干正事呢,他第一次顶撞了父亲。“反悔就反悔呗,有什么大不了,她又不是什么天仙,何必哭丧着脸。”
“算了,不提这事了,好在没有定亲,算不上退婚,要不然被全协噶尔村的人看笑话呢。”父子俩一杠上,阿妈能做的就是打圆场。“也许是件好事,谁知道呢?这人世间的事,谁又能说得准。”
给小木匠提亲,老木匠也是操了不少心,他托徒弟们物色一个好人家的女儿,得来的回复却基本一致,村里的女孩都上城里打工去了,基本没人留守农村了。早几年,协噶尔村就见不到几个年轻女子的身影,老木匠以为那是协噶尔村离城市太近,往偏僻一些的地方找找,还是能找到吃苦耐劳的好女孩,没想到偏僻的农村也是这个情形,他们这才把这事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四处托人,两个嫁出去的姐姐也跟着张罗,却一无所获。有一天,小木匠的阿妈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说:“有了有了。”
老木匠没好气地问:“你说出来呗?”
“琼珠啊,这孩子长得俊,又一个村里的,知根知底。”
老木匠失望地“哎”了一声,“我还以为谁呢?就是那个老想着进城跳舞的女孩子吧,不像个过日子的……”
“什么叫不像过日子的,不会过日子的还能把茶馆弄得红红火火?”
小木匠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阿妈那惊奇发现的样子,是演给阿爸的,平常她没少拿梦想茶馆说事。
“你觉得行就行吧。”对老木匠而言,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但还是摆出一副让步的样子。
小木匠在提亲这件事上,并没有发表意见,但提亲要带的东西都是他置办的,从这点看,他是默认这个决定的。他和琼珠差不多大小,小时候也算玩伴,只是她去城里当过两回演员后就变了,待人冷淡,见人爱理不理,逢村里集体活动,也不扎堆,休息时一个人托着腮帮发呆,让好事者多了许多谈资。小木匠从来不说琼珠的闲言碎语,集体劳动或休息时,看她一人远坐,偶尔给她送去一罐可乐,当然,他会避开同伴。
“说是女儿现在还不想考虑。谁信呢?要放在过去,这年龄都有几个孩子了。”小木匠的阿妈藏不住心情,只要闲下来,就会唠叨一下。“肯定是有人提亲了,条件可能比我们还好。”
“您别说了,人家没那么势利眼,你不是说她妈那天也是内疚得脸都红了吗,不乐意就算了,强求不得。”丹增小声地说。
“提亲那天说得多好,什么能进你们家的门,是她的福分。老两口在村里的口碑那么好,丹增这孩子老实善良……”
丹增本来就有一种被人羞辱的感觉,听阿妈唠叨更难受,索性上楼去了。
老木匠经过一夜的苦思冥想后,也没有想出不让自己难受的办法,反而又被丹增他妈提起了一件更烦心的事。“老头啊,昨晚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的大女儿不是经常到县城卖牛奶吗,她说她每次要到梦想茶馆坐坐,每次都见琼珠穿着不同的新藏装,各种不同面料,又漂亮又合身,真是羡慕。”
老木匠一听就不高兴了,道:“说这些干吗,这些跟她家反悔有什么关系呀。”
“你想想呀,我们村里就顿旦会做衣服,并且做各种好看的藏装,小年轻小媳妇都到他家做,琼珠穿的会不会是他做的呢?”
“这又能说明啥呢,人家小姑娘也可以找顿旦做呀。”
“你真傻,大女儿每天都去县城卖牛奶,每次都见她穿不一样的衣服,能有钱买那么多?况且,顿旦他妈上次也对我说,正在为顿旦物色一个媳妇呢,也是到处托人没音信,很发愁。”
“琼珠那姑娘心多高,怎么会看上顿旦那……”老木匠把“瞎子”二字吞进了肚子。
“可是现在不一样啊,你没见顿旦把事情搞得有多大呢。”
老木匠感觉有点道理,突然一股无名火蹿上心头。“早知这样,你还怂恿我去提什么亲呀,你就是想丢我的老脸是吧。你算什么女人呀,这么清楚的事你都看不出来。”
丹增他阿妈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老木匠一大早嚷嚷起来,她就躲到厨房不理会,老木匠不罢休,一直唠叨不停。丹增心里一直沉沉的,不想往深里想,听到父母的争论,他的心也咯噔了一下,其实这件事好像早有端倪,只是他自己太不够敏感了。
在协噶尔村,正常人吵架互骂瞎子很正常,邻居间牵涉利益问题会骂瞎子,夫妻反目也会骂瞎子,唯独不会骂顿旦是瞎子。顿旦失去右眼时,他妈那撕心裂肺的哭声,犹如刻刀刻进了协噶尔村人的心,这一哭,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罪,如果早在意一下身边的孩子,或许会早一点发现问题,对顿旦,村里人仿佛有一种集体内疚感,从没有一个人喊他瞎子。但那天,琼珠破了这个规矩。那天,顿旦陪着他在县城打台球,琼珠从身边走过,他朝她微笑,她还一个凌厉的眼神。顿旦没有看见她,他在不断地变换着姿势,想以一种潇洒的身姿打进一粒球。琼珠就在他的身后喊了一声,“做妖呢?独眼。”这声音在丹增听来是如此刺耳,如此蛮横,他甚至想好了一段争吵的场面。然而,顿旦立即转身,扶了扶墨镜,罕见地以羞涩又忸怩的样子说,“那么大声吓死我了。”琼珠不理会往前走,顿旦一直看着她走远。
丹增想起这个场景,心里凉凉的,脸上烫烫的,那种感觉让他无法言说……
听阿妈说,琼珠的阿妈那天对她说,老木匠家提亲的事,她们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也请阿妈不要告诉别人,更希望不要记恨她们。
那么这件事,就能当它没有发生过吗?老木匠愿意这样做,他深信琼珠的阿妈在这点上是诚实的,这也是他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他觉得木匠世家的尊严没有动摇。
小木匠却做不到。
五
梦想茶馆的门槛不高,丹增迈过这一步,却思来想去考虑了很久。以前,丹增也是梦想茶馆的常客,他不喝甜茶,琼珠见他进来,就会“砰”地打开一罐可乐,嗞嗞地倒到一个大玻璃杯里。自从父亲到琼珠家提亲后,丹增不好意思面对琼珠,说来也有一个星期左右没再来过,即使路过他都不敢,生怕撞见琼珠那凌厉的眼神。
丹增正赶上梦想茶馆的高峰期,坐定几分钟也无人问津,这在以往是少见的,过了大约十分钟左右,琼珠的一个表妹走过来问他喝什么。丹增要了可乐,女孩也没有拿来玻璃杯,“砰”地打开后“哐”一声放到桌上扬长而去,丹增的心里一阵慌乱,觉得小姑娘也是知情的。
丹增心里正盘算着如何问得体面不尴尬时,突然进来了一大帮协噶尔村的人,丹增心虚,一阵惊慌,他们却没有任何异样,自然地坐到他身边,吵着闹着要打扑克牌。打了一上午的扑克牌,琼珠也没有出现,倒是顿旦的双胞胎哥哥来了一趟,丹增自然要打声招呼。
顿旦的双胞胎哥哥也是来找琼珠的,见琼珠不在,就把一包衣物交给丹增,让他转交一下,他没时间等了,说下午有个旅游团队要去接。丹增手一摸又隔着塑料袋一看,就知道是藏装,但还是问了一声这是什么?他说:“你就说是顿旦送的,她就明白了,这是顿旦做的最新面料的藏装。”
顿旦的双胞胎哥哥开着车,立刻就不见了,丹增抱着小小的塑料袋,却有抱着大铁砣的沉重感,他要的答案不必等到琼珠亲口告诉他,他的心酸酸的,眼眶也不争气地湿了,为这样的反应,又产生了内疚感。如果是顿旦,作为朋友,不该有这样的酸涩感呀。在协噶尔村,最好的朋友,应该是其中一人死后,生者应有能在死者坟前喝酒的勇气,怎可惧这点小事呢。丹增又坐了一会儿,他觉得答案已经有了,不必等待了,想着该把塑料袋交给琼珠的表妹,还是托付给同村的年轻人时,琼珠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跟在她后面,扛着一箱做甜茶用的奶粉。
丹增把塑料袋交给琼珠时,特意交代了一句:“最新面料的藏装,顿旦给你做的。”
“这个‘独眼’,一天让我换一套,我都不好意思。”
“那多好呀,女孩子不是喜欢新衣服吗,有人送多好。”丹增把“送”说得很重。
“我还不要他送呢,一天一套,茶客的闲话多得很呢,他还要我多站着少坐着,我一天都快累死了,还要我多站着,还要我多推荐给别人,我这里是茶馆又不是藏装店。这‘独眼’鬼点子最多,要不是看他是个‘独眼’,我才不替他做那么多呢。”琼珠看都没看一眼藏装,就把塑料袋扔到奶粉纸箱上。
“也许是顿旦哥哥的意思吧,刚才是顿旦哥哥送来的呢。”
“管他是谁的意思,我先休息一下再换上。”
“你看着办吧,我先走了。”丹增见琼珠对他毫无愧疚感,很失望很失落,转身就走,刚走了几步,就听见琼珠喊他:
“小木匠,你生气了?”
“我又没有背着斧子锯子,干吗叫我小木匠。”丹增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害怕琼珠再说出什么,赶紧往前走。
“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琼珠小跑着追上来了。
“我已经知道了。”丹增还不停步。
“小木匠,你还走啊,我要大声喊叫了。”
琼珠这么一说,丹增也不敢往前挪,背对着她说:“你说嘛。”
“你转过来,你慌张胆小、鬼鬼祟祟的样子,真是让人讨厌。”琼珠掐着腰脸色绯红,“你干吗要让老木匠来提亲,你自己不会说吗?”
“又不是我让他去提亲的。”丹增一急脱口而出。
“既然不是你的意思,你干吗听任他们安排。”琼珠的语气多了几分轻蔑,“我忘了你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你的‘开关’在你父母手里。”说完独辫一甩一甩地离去。
“我不是,我是……”丹增望着琼珠的背影,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想娶媳妇?”这句话就这样刻在丹增心上,很多年后都忘不了。但他不知道这句话是琼珠说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第5期(责任编辑:郭金达)

尼玛潘多,女,藏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媒体。作品曾刊于《长篇小说选刊》《民族文学》《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等报刊。出版有长篇小说《紫青稞》,被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藏文、维吾尔文,及英文出版。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第六届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