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丫,让我们来聊聊死吧!
阿丫转过头,用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诧异大眼珠盯着我。从她复杂而又惊恐的眼神里,我读到她想对我说什么,可终究还是没说出一个字。
阿丫僵硬的嘴唇在发颤。甚至在我说出那句话之后长达一分钟或者更长一点儿的时间里,我听见阿丫嘴里的牙齿在轻微地打颤,她仿佛想用身体里仅剩的那点儿力气嚼碎我刚刚说出的“死”字。
我知道阿丫接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一本正经地谈论死,平时是这样,现在更是。
我是故意在她面前提到死的。
胆小鬼。我接着说,我用冷背对着她。我不想看见阿丫楚楚可怜的样子,像只随时需要别人施舍关怀的流浪猫。
我不是。过了很久,阿丫从那僵硬、打颤的嘴里断断续续地挤出几个像铁一样冰凉的字。
我从陷着我和阿丫身体的软沙发里站起来,径自走向厨房。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阿丫就没有进过厨房,阿丫像变了一个人,她整个身体是空的,脑袋是空的,她就像活在人世间的一个皮囊,除了偶尔的叹息声有点重量之外,轻飘得能被窗户里刮进来的一阵小风吹得飞起来。当然,阿丫没有飞起来,或者说阿丫想飞起来却终究没有飞起来的能力。
因此,阿丫不知道我进厨房要去干什么。
我站在冰箱前犹豫了一会儿,那一会儿的时间我在想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否正确。也许正确吧,我宽慰自己。
我打开冰箱,看见它们原封不动地呆在那里。一只死的大闸蟹和一只活的大闸蟹,它们面对面看着对方快几天了。阿丫失去自我也快几天了。
买大闸蟹的那天晚上,阿丫莫名其妙地提到过死。那时的阿丫,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会那么惧怕这个“死”字,那时阿丫只是一个把“死”字说得很普通很随性的人。
我们买两只大闸蟹,她对店里全身湿漉漉的老板说。
两只?我问。
阿丫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她指着框里两只鲜活的大闸蟹,说:我们就要那两只。老板好嘞好嘞地答应着阿丫,一边拿着长长的夹子试探性地夹。
姑娘真会挑,这两只大闸蟹肥得流油。老板笑着,露出一口排列错乱的石灰牙。
两只大闸蟹在框里拼命地爬,最终没有逃过老板的手。老板熟练地帮我们捆绑着大闸蟹不断伸展的脚,不一会儿两只鲜活的大闸蟹在老板的手里变得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了。
还好我不是大闸蟹。这句话像是给自己说,又像是在说给阿丫听。
阿丫对我说的话没有任何反应。我说这话时,她在看其他地方。除了逛夜市的陌生人,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可看的。阿丫那晚怪怪的。
我没再问大闸蟹的事,多买一只或者少买几只大闸蟹对我也没什么影响。我内心是惧怕那种多脚物种的,只是阿丫爱吃大闸蟹。大闸蟹上市的季节,她每隔几天就邀约我陪她买大闸蟹,每次一买就是五六只。只是这次不同。
我和阿丫穿过夜市,我想去我们两个平日都爱去的藤蔓书店逛逛,一只脚踏上了台阶,又被阿丫拽了回来。
看,有新书上市。我指着书店门口的告示牌对阿丫说。
阿丫看了看摆放在书店门口的告示牌犹豫着,最后还是说:我们回家吧。
这不像阿丫。以前的阿丫每次到藤蔓书店门口,脚变得千斤重,无论再忙,她都会走进去问问老板有没有来新书?
我疑惑地看着阿丫,她的眼睛看着前面。她的眼神里有种不容更改的坚定。她在逃避我的眼睛。她知道我想说什么,她不想回答我。我心里有很多疑问,我还是决定听阿丫的。我收回跨上台阶的那一步,闷着头向前走。回家的路上,我和阿丫一句话没说。
到家中,阿丫恢复到平日的样子。她说今天的大闸蟹她来做。我当然高兴这样的提议,那样我就有更多时间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阿丫在厨房里忙,她哼着一首我没有听过的小调。阿丫快乐的时候都是这样。阿丫快乐,我也快乐。刚才路上的不开心,在她快乐的调子里慢慢消失。我到书房里打开电脑,改着学生网上传过来的试卷。
一群糊涂蛋儿。看着学生交过来的试卷,我骂到。虽然是骂,我并不生气,这和阿丫的快乐有关。我喜欢阿丫快乐的样子。
我想我听见了那声关门声,应该是。我没从书房里走出来,我必须尽快地处理完学生交过来的试卷,才有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来安排。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从学生的试卷中抽离出来,我伸展着酸痛的肩膀,脑袋里还回想着卷子上的那些试题。试卷是从学校题库里随机抽出来的,题量大,又超书本。
什么狗屁专家出的题,脑袋里有疙瘩吧。我骂着走出了书房。
客厅里静悄悄的,厨房的玻璃窗上雾气腾腾地沾着一层水蒸气。
阿丫,我叫到。没人回答。我又四处找了一遍,也没看见阿丫。阿丫去哪里了,我不知道。我走进厨房关掉液化气,揭开锅盖,看见一只蒸熟的大闸蟹静静地呆在里面。
还有一只呢?这个阿丫,简直心不在焉。不过,我也没把另外一只放进锅里蒸。我把蒸熟的那只夹在盘子里,准备先放进冰箱保鲜再说。当我打开冰箱,看见另外那只大闸蟹正眼鼓鼓地看着我,不对应该不是看着我,应该是眼鼓鼓地看着我盘中的这只大闸蟹。它的眼睛都快触碰到我手里这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很残忍,但这并不坏,我认为是这样。我把那只蒸熟的大闸蟹和那只活着的大闸蟹面对面地放在盘子里,它们互相看着对方。我想,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无论是人还是万物,都要有面对死亡的能力。
现在我要把盘子端到阿丫的面前。让她好好看看一只活的大闸蟹和一只死的大闸蟹在一个狭窄的幽闭空间里,另外一只是怎样活过来的。阿丫需要这样的力量。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迟疑了一下。我把头转向呆坐在软沙发里的阿丫,刚才那句“我不是”,是阿丫那天奇怪地消失又奇怪地回来之后给我说的第一句话。今天我为什么会在阿丫的面前突然提到死,是因为我看见阿丫身体里正在丢失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对阿丫来说很重要。阿丫却不想要它了。
阿丫,你看看这个。我走到阿丫面前对她说。
阿丫没急着转过头来看。这几天,阿丫变得迟缓,她身体里正在丢失的那些东西,让平时火急火燎的阿丫变得慢起来。阿丫的缓慢让我想到树懒。
在看过来之前,阿丫的眼眼珠子先动了一下,似乎眼珠比阿丫本人更好奇我想让她知道的东西,是眼珠拖着阿丫的整个身体慢慢转向我。
拿开,拿开。阿丫双手捂着耳朵,人缩成一团。
面对一只死在眼前的同类,它坚强地活到了现在。我对阿丫说。
阿丫颤抖着,把整个身体蜷缩得紧紧的。她需要有人抚慰她。不过想到那天阿丫回来什么解释都不做,直接冲进卫生间,服下我前段时间因为考博过度紧张买下的一大瓶安眠药,我就知道阿丫不想活了。我不想抚慰她,起码现在不想。
那天看见不想活自己的阿丫,我的脑袋里“轰隆隆”地响着。我不知所错,我一边臭骂阿丫,一边颤抖着打120。简单的三个数字,那晚在我的手指下总是拨不对。阿丫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手机,死活不让我打。她想死自己。我一团糟,无论我怎么骂阿丫,她都不把手机还给我。时间一分分过去,我知道那一分分过去的时间对眼前想死自己的阿丫意味着什么。为了拯救阿丫,我想起电视上看过的一则急救消息,肥皂兑水。那晚我把一杯肥皂水灌进了阿丫的喉咙里。她抗拒,我不管不顾,我们像两个疯子一样对抗着彼此。我问阿丫为什么,她怎么也不回答我问她的为什么?肥皂水在阿丫的胃里很快起了作用,阿丫一个劲儿地吐,把该吐的不该吐的都吐了出来。吐完后她不断地哭,那时她把大把的眼泪随意地挥霍,那晚哭过之后,阿丫眼里的泪水就再没有了。她透支了自己的眼泪。
阿丫,好好活着。我说。阿丫依然捂着耳朵,我不知道我的话是否钻进了她正捂着的耳朵里。我必须要说,我希望她好起来。比以前更好!
阿丫和我是初中同学。确切说是同年级不同班。虽然不同班,那时我就在一个年级七八百人的学生中认识阿丫,那种不说话的认识。我是怎么开始注意阿丫的呢?后来我和阿丫聊过。
阿丫,你那时为什么会养一条奇怪的狗?
它挺好的。
它整天在那里打转,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劳,傻乎乎的。
正是这样我才更爱它。
那条狗生活在一个环形空间里,挺可怕的。
阿丫只是笑。
我第一次注意到阿丫的时候,先注意到的是那条脏兮兮的白狗。每次放学,那条脏兮兮的白狗都会出现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棵大树下等她,一见到阿丫背着书包出校门,它就在远处开始转圈,只要阿丫不叫停,那条转圈的狗就不会停下来,而且越转越快。阿丫默默地走过去,带着狗消失在人群里。
我跟踪过你,阿丫。
因为那条狗?
也是,也不是。我更好奇你。
觉得我会操纵一条狗的思维吗?
不是,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每天都可以把一条脏兮兮的白狗带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独自享受一条狗在你面前几百圈几百圈地打转?你就不着急着回家吗?你就不怕家里人说你每次都那么晚回家吗?
不怕。
我还记得那次跟踪阿丫,我看见她看狗转圈发呆的样子,感觉有自己又没有自己。那一刻的阿丫是静止的,仿佛活在另外的一个世界。
那条狗呢?
消失了。
怎么消失的?
有一天我不让它给我转圈的时候,它就垂着头走了,再没来见过我。
为什么一定要让一条狗给你转圈?
你不觉得一条狗转出的圈很迷人吗?
不觉得。
那是你不懂。
可能是吧。狗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它不是我的狗。
后来,我确实没有见过那条在树下为阿丫转圈的狗。狗的消失,让放学后的阿丫显得更加孤单。我说过,我是因为一条狗才开始注意阿丫的,狗消失了,我也没兴趣再去注意阿丫。从那以后,阿丫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我是在一年前的一次校庆上遇见阿丫的。
阿丫,一见到她,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叫出了她的名字。激动让我忘记了我和阿丫根本算不上认识,或者说,我认识阿丫,阿丫不认识我。
阿丫形单影只地坐在角落里。听见我喊她,她一头雾水,随后腼腆地向我点了点头。那种毫无亲切、充满仪式感的点头。我知道自己的唐突,可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我不得不走过去向阿丫介绍自己。
唐颖,零三级三班的。我把手伸向阿丫,阿丫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
阿丫,你知道吗?那次你的手真凉,感觉快冻住我了。
那是我真实的体温,也是我心的温度。阿丫淡淡地说。
以上我和阿丫有关狗的对话都是那次聚会后的延伸。从那次聚会,我知道阿丫现在是一家企业新聘的办公室会计,我也知道那时的阿丫和我一样都是单身狗。
可能是单身狗的身份拉进了我和阿丫的距离。那天我们聊得挺投机的。在知道阿丫还在为找房子的事情焦头烂额时,我果断地说:住我那里吧?那是我的酒话,酒总让我意气风发。后来的事我一概不知了,也可以说在给阿丫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阿丫提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敲响了我的门。当时,我既吃惊又局促,阿丫羞涩地站在我门口,说:打扰你来了。那一刻,我一百次的在脑袋里回想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的脑袋闷闷的,所有的记忆都在我那闷闷的脑袋里更加稀泥糊涂。
我肯定给阿丫说过让她来这里,肯定还把详细地址给了她,要不她不会找到这里来。我把阿丫请进屋里,我的房子一团糟。昨晚的酒气还在屋子里没有散去。我一边道歉,一边慌乱地收拾着内衣袜子之内的东西。
阿丫木木地站在那里,我的慌张也让她不自在了。
不好意思,我太唐突了。来之前想给你打个电话,准备打时发现你昨晚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少一位数,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阿丫歉意地说。
没事没事,昨晚我喝得太多。我一边向阿丫道歉,脑袋里一遍一遍飞速地搜索着昨晚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想不起来,还是一团糟。我恨死自己了,心里一百次咒骂着自己:该死的唐颖,你看你这臭德行,喝点儿酒就不知天高地厚,这下可好,别人行李箱都拉过来了,看你怎么办。
昨晚我也喝了不少。阿丫说。
我失忆了,昨晚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我无奈地给站着的阿丫说。说这话时,阿丫还站在那里,而我由于这突来的情况,心里乱七八糟的,竟然忘记请阿丫坐。
是我送你到门口的。夜太深了,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家。不过还好,我问你家在哪里时,你还能回答我。阿丫说。
我一脸茫然,这时才隐约记起昨晚好像在楼道口有人送我,我依稀记得那人离开时的背影,单薄、轻盈,像禅的翅膀。
我停下手中正在收拾的东西,对站在那里的阿丫说:真是不好意思,丢脸了。
没什么丢脸不丢脸的,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阿丫说。说完她顿了顿,接着想起什么似的补充到:因为昨晚来过,我今天很快就找到了这里,哪怕喝了很多酒,我的记忆也没那么差。阿丫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阿丫的笑干净,仿佛没有被尘世污染过。
我喝点酒常常失忆,以前我被自己的这种症状困扰,我怕哪天我一失忆就再恢复不过来了。后来随着这种次数的增加,我也变得麻木和满不在乎了。我给阿丫说。
如果彻底的失忆也没什么不好的,世界在你面前都是新的。这不是很好吗?阿丫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阿丫,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需要我帮忙吗?阿丫把行李箱放在鞋柜旁,一副马上就要帮我收拾的架势。
不用,不用,你看我只顾着给你说话,都没让你坐。你随便坐,我马上就好了。我又开始忙手里的活。
阿丫拖着行李箱,坐在了我那张软软的沙发上。
你喜欢他?阿丫刚坐下,就问我。她手里拿着我放在茶几上的《人鼠之间》。
是的。我很少在外人前面说起过自己喜欢看书,挺羞耻的。
你看。说着,阿丫从自己的行李箱里拿出一本和我一模一样的书。两本封面相同的书一本挨着一本地摆放在桌子上,我和阿丫都笑了。
很奇怪对吧,阿丫?
在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这样的机率确实很少。阿丫后来说。
那天我们谈到了乔治,谈到了莱尼,谈到了书中的那片森林,最后谈到了死亡,那是作者斯坦贝克带领他的读者要去的地方。
这是一本很美妙的小说,连最后的死都那么美妙。在结束整本书的交谈时,阿丫若有所思地说。
那时,我还不太了解阿丫,只觉得当时从阿丫嘴里说出来的死,像一颗糖,甜蜜蜜的。
阿丫住了下来。两个完全不了解对方的女人住在一间屋子里,竟然很快就适应了。
阿丫给我提过一次房租的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为什么你要交房租?我很生气。
阿丫感激地看着我,后再没提过房租的事情。有时我希望和阿丫就这样住下去,直到白发苍苍都没问题。
外面阳光明媚,阿丫。我对蜷缩在软沙发里的阿丫说。我终于用手去抚摸了一下阿丫的后背。其实我早早就想这样做,可我希望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阿丫需要自己站起来,不要通过这种方式博得我对她的怜悯。
阿丫的后背冰凉。我记起第一次握阿丫手的冰凉,她说那是她心的温度。在相处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没有谈起过为什么阿丫说那是她心的温度这件事。平时阿丫温暖,阳光,像我遇见过最好的夏天。
不过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只是我们都刻意回避了那可能有什么的一面。
有好几次加班回家,我看见阿丫灯不开,一个人静默地坐在飘窗上望着窗外。阿丫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每次遇见这种情况,我喊阿丫的名字时,她看我的眼神总是湿漉漉中带着陌生。她要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重新认识我。
夜很美。
是呀,夜很美。
我们都不往下说了。这样的对话没有再往下说下去的必要。
走开,你走开,我求求你了。阿丫把自己裹得更紧了,她把头埋进蓬乱的头发里,惊恐的眼神穿过乱乱的头发盯着我手里端着的盘子。既然阿丫害怕,她可以不看我手里的盘子,但是阿丫一边叫我走开,一边却不放弃地盯着我手里的盘子看。阿丫被一种连她自己也矛盾的情绪控制着自己。
活着的那只大闸蟹眼睛还在动。它看着那只死了的大闸蟹,在探究,在思索,似乎它还没有好奇够同类的死。
妈的,它可能根本不懂死是什么?我突然想。我厌恶起自己用这样拙劣的手段去让阿丫面对死。
对不起,对不起。我心中有万般的愧疚不由而生。
我只是希望你好,我对阿丫说。阿丫还在惊恐地盯着那只把眼睛伸得长长的大闸蟹。阿丫那时的眼神有了锐气,她在憎恨盘子中的大闸蟹。死的或是活的那只。
我端着盘子走出了门,我把两只大闸蟹倒进了楼道里的垃圾桶。
无论怎样来到这里你们本身都会死,我对它们说。我转身准备走进门,想想又折了回去。我把那只装大闸蟹的盘子一起扔进了那个肮脏的蓝色垃圾桶。
阿丫看见我空手走进门,慢慢放松了自己。她的身体再次陷进软沙发里。她又一次变得松软,缓慢,像一滩摊在地面上的水。
那几天我焦头烂额。学校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我上班。我先说是感冒,后说是在输液,接到最后一个教务处主任的电话,主任语气坚硬地说:唐颖,你是位不负责的教师。说完这话,他“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的耳朵里“嗡嗡”地,主任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响在我的耳朵里,做为一位教师,这是对我职业道德最大的否定。
我气急败坏,想骂天的心都有了。后渐渐平静下来,也不怪主任,这件事是自己做得不厚道。我不能把阿丫一个人丢在家里,那样我会更加不安心。
阿丫好像从来没有朋友。她的日常就是上班下班,看书写作。她对生活的要求很少,少到基本没有要求。
阿丫,你不像女人。
干嘛要有女人男人这样的说法,太物理了。
能让这两种物种上升到化学层面,只有情感。
垃圾东西。
阿丫对情感不削一顾。我慢慢领悟到阿丫说过的那是她心的温度的含义了。
我不知道在阿丫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让她瘦弱的外表下有这么一股坚挺、执拗以及不容改变的东西。
阿丫不愿意告诉我的事情,我从来不问。她有她不说的理由,每个人内心都筑有一座迷宫。偶尔迷失自己,也迷失别人。
阿丫给我提过一次她工作上的事情。
那里圈养着一群无趣的人,各个一本正经得毫无意义。你知道吗?那地方挺魔幻的。那里会在某个时刻,某个瞬间在我眼里突然变化,那么真实地变化。我看着那里的人,他们有时变成猴子,有时变成老虎,有时变成鸟。他们说的话都是一群动物的语言。奇怪的是猴子发出鸟的叫声,老虎发出猫的叫声……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难看,有的往鼻孔里吃下去,有的从耳朵里吃下去,有的从指甲缝里喂进去。有时他们说话,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他们留后面的半句让我猜。我猜不准后面的半句,他们发出动物的叫声,那是他们自认为嘲笑我的声音。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切都被真空,他们却毫无察觉。他们每天在一个相同的环形空间里来回地走和飞,不知疲倦地、忙忙碌碌地。有些白天没走够和飞够的,就用晚上时间来走和飞。我看见那只猫头鹰,就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在环形空间里飞。有次,他飞着飞着就哭了起来。我说,你不想飞就不用飞呀。他说不围着这环形空间飞,他就想死。我说你这样不睡觉的飞,老板又不给你好处。他说他的命就是飞死在这环形空间里。我说我去告诉老板,把这环形空间改成别的样子,你就不用飞死了。他说,难道你知道谁是老板?我说现在是晚上,我找不到老板,明天我就知道了。他说你白天晚上都找不到老板。我说不可能。第二天,我去找老板,到处都是围着环形空间走和飞的动物。我确实不知道谁是老板。我看见那只晚上在飞的猫头鹰,现在还在飞。白天他一句话没给我说,或许在白天他根本记不起我这样一个全心全意想帮助他的人。我一脸沮丧,正在这时,一只兔子跑过来问我,你怎么还不工作?我说我在工作呀。他说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快去工作。我被他拽着往前走,我问他要带我去哪儿?他说你无知得让他想哭。接着他带我走上了环形空间的线路。我的任务就是和他们一样在环形空间里不停地走,不停地走。我说我要回去工作,他哈哈笑起来,他说这就是你的工作。我说我是这个公司新聘的会计。他说他们没有聘请过会计,他们不需要会计,只要我在这个环形空间里不停地飞和走,到一定时候,自然就会得到一份让自己饿不死的薪水。我不相信他,可我刚来没有一个熟人,只得选择信任他。我默默地跟着他们走,我走慢了总有声音后面催我,我心慌慌的,我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很多原有的东西在走中从我身上消失,我的思想在天上飞。我咒骂着这家破公司,咒骂着这些在环形空间里走和飞的每个动物。直到有几次,我听见有只老鼠气喘吁吁地在背后喊我,你这条丑陋的鱼,不能再游快点吗?我正准备和他争辩我不是鱼是人时,他理也不理我加快步伐从我身边一灰溜地跑到前面去了。后来又有其他的动物叫我长颈鹿、松鼠、蚯蚓、蝗虫、斑鸠,我才慢慢明白,我认为别人在我眼中变,其实我也在别人眼中变。谁都觉得自己是那个活得最清楚的人,其实谁他妈的都是糊涂蛋。我和他们争辩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对抗外界的力量变得虚弱,我已顺理成章的和他们同流合污了。总之到最后,我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围着环形空间不断地走和飞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那足以让我不饿肚子的薪水,我怜惜着它。
你还是阿丫。等阿丫把整件事说完,我哈哈笑起来。那次,我更确定阿丫的内心有一座迷宫,她把自己迷失在自己预设的空间里。
很早很早以前,我的大脑里模模糊糊出现过环形空间的样子,我迷恋那种没有出口又不能自拔的荒诞感。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荒诞,那就是我的世界。我就是一只每天在环形空间里不断行走并失去自我的小动物。阿丫沮丧地说。
我和阿丫经常交流最近读到的好书。遇到喜欢的作家,我们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到深夜。我和阿丫有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是我只读不写,而阿丫既读又写。
阿丫,分享是件美好的事情。
有一天,我会让你读,但至少不是现在。
现在读和以后读会有区别吗?
有些故事是适合以后读的。以后读会呈现故事的另一面。而现在读,你只能看见故事的本身。故事本身是无趣的。
我没有读过阿丫的小说。阿丫写小说,也不拿去发表。她写小说,似乎是只写给自己的小说,和这个世界都没有任何关系一样。也可能阿丫的小说就像她给我表达的一样,是需要未来读的。未来读阿丫的小说,我也许才能看见一个真实的阿丫。
现在的阿丫,是真实的阿丫吗?
我站在客厅中央,走过去看一眼阿丫,又走开了,然后又走过去,又走开了……在这不足一百平米的房间里,我已经来来回回地走了很多遍,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面对不想要自己的阿丫。
阿丫,你不应该这样折磨我。前面不是一切都很好吗?我们一起买大闸蟹,一起回家。你哼着快乐的小调,我忙着手里的事,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享受你做的美味大闸蟹了。所有的问题出在哪里?告诉我?你告诉我好吗?对阿丫说出这样的话,我的内心慌乱。阿丫在我面前像个黑洞,让我迷茫,让我不知所措。我想打破这个黑洞,走进阿丫真正的内心。
阿丫快从黑洞里走出来,快走出来。不要怕,不要怕,我就在你身旁,你不要怕。我一次次在内心呼唤着阿丫。这样的呼唤我没有说出口,我弄不懂自己,我相信阿丫能感知到我迫切、焦急的呼唤声。
阿丫目光呆滞,她的眼睛盯着头顶的天花板,仿佛要把天花板盯出个窟窿似的。
那晚,我听见你轻微的关门声了。我想那并不重要,你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以前,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你总在我们回到家之后又一个人单独出去。我没有问过你出去干什么,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处隐秘空间,这些我都明白。可那晚不同,你回来服下那些安眠药之后,我就知道那晚对你非同小可,你不想活了。阿丫死很简单,你现在想死,也可以。死从我们出生就被我们拖着在这世上走,我们随时都能触碰到死那张饕餮、随时期待我们死的模样。反而选择活才是最难的,怎么样的活,活得怎么样,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难题。
阿丫,自从你来到我家,看见你手里的那本《人鼠之间》之后,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心灵是相通的。我是一个不太容易接纳别人的人,但是我很快就接纳了你。有些人会用一辈子的时间让你去接纳她,但是一辈子你都可能没法接纳她。我们之间不是这样,我相信你的感受和我一样,要不你也不会陪我住到现在。
我没有告诉过你,在你没来之前,我的生活一塌糊涂。工作上不顺心,本来准备结婚的男友爱上了别人,父亲离世不久,母亲有了一个新的男人,那人肮脏,总想趁母亲不在的时候打我的主意,我感觉我再没有家了。那段时间一切的无意义都向我扑来,它们想压倒我,打垮我,干掉我。我快活不下去了,我想到了死。我差点就死掉了。命运弄人,我在医院里活了过来。昏迷的时间里,我像经历了我的另外一个人生,巧妙,充满暗的重。从那之后,我告诉自己,我不该死,该死的是那些想干掉我的虚无和无意义。他妈的,它们才该死。想通这一点,我变得倔强和刚毅。我常常对自己说:唐颖,你这辈子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没后悔过那次选择死,那次死拯救了我。阿丫,自从你吞下那瓶安眠药之后,你也算死过一次的人了,所以我想和你聊聊死。只有真正看透死的人,才能活得更像自己。
我见过一个死的人,就是我想死掉自己的那次。他半夜被救护车送进医院,他进来的时候,大口的呼吸着病房里的空气,他重重的呼吸声大得惊人,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呼吸声,仿佛想把病房里的空气都一下吸进自己的身体里。他是那么拼尽全力地想活,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可他最后死了。他那么努力吸进身体里的空气,被他用最后一点力气从嘴里全部吐了出来。
就在他送出去不久,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又推了进来。那晚是个奇怪的夜。她和那个刚推出去死掉的人完全不同,姑娘躺在那张冰凉的推车上,安静得出奇。她是突发车祸,医生们对姑娘的身份信息一无所知,虽然事态紧急,不过所有的治疗方案都停了下来。医生忙着去搜集姑娘的身份信息,一个昏迷着的姑娘就躺在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那么平静地躺着,甚至那么完美。在那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观察着她。我在想现在的她到底属于哪个世界?看着她那么美并且毫无疼痛地躺在那里,我觉得她是那样的幸福。
我还想给你讲件事情。我今天的话真多,但我想说,阿丫请允许我讲完好吗?阿丫无动于衷,我接着说。
前年我去过一个中药药材市场,那药材市场在中国数一数二。我一路闲逛,看见一间铺子半开着门,出于好奇,我走了进去。铺子里堆满了黄黄的药材,药材太多房间又有些潮湿,整个墙面上生长着黑色的霉点,那里充溢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我正准备退出去,老板从里面走了出来。为了不让老板觉得我是一个对药材一窍不通的人,我假装拿着一片对着外面的阳光看,阳光穿过轻薄的肤质,它在我手中散发着一种淡黄色的光。
买点儿?
什么功效?
无比大的功效。
无比大是多大?
老板犹疑了一会儿,说: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吧?
老板看穿了我,我有些尴尬。
既然看穿了也没什么。我安慰自己。
你说说看。
这样给你说吧,你从哪里来?
娘胎里来。
这就是娘胎。没有它,你来不到这个世界,你说它功效大不大?
我愣住了,再看看满屋子堆积如山的所谓药材,我想吐。我知道我可以马上吐出来。我扔掉手中的所谓药材,毫无顾忌地跑在药材市场的街道上,我和那些密集穿梭的人流擦肩而过,我感觉他们都是一个个胎盘。我突然很害怕人,也害怕自己。
阿丫,生活本身就很荒诞,我们却浅表地认为作为鲜活的人,作为暂时能感知到疼痛和苦难的人,我们就和世界很近。其实不是,很多东西都会用障眼法。阿丫,说不定你现在遇到的恐惧也是这个斑驳荒诞的世界馈赠给你的。你只要别逼近自己,把自己从深陷的黑洞中抽离自己一下,什么都会不一样。相信我,阿丫。
我从来没这么认真又这样义正言辞的和阿丫说过这么多沉重的话题。说完这些话,我说不出的难受,想到那位在医院大口呼吸空气的男人,想到那位不足我五米平躺在推车上昏迷不醒的姑娘,再想到那一铺子的胎盘,我的内心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我感到我的全身都不那么舒服了。我站在阿丫面前,我渴求地望着阿丫。我希望她能明白我为什么给她说这些。
阿丫瘫软的身体在软沙发里动了一下。我知道阿丫把我刚才的话听进了。
阿丫,你行的。我鼓励着阿丫,我想把阿丫从黑洞里拖出来。
我想喝水,阿丫说。
我心里无比开心,我挪动着僵硬的身体,哪怕刚才身体的不舒适感还在我体内产生着化学反应,可这和阿丫开口想喝水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找来阿丫的杯子,我给她兑了一杯上次我从唐山带回来的蜂蜜。阿丫喜欢这种蜂蜜,她说,这种蜂蜜水喝了感觉可以让她甜得想飞。
她太需要用水来填充自己虚弱的身体了。
我梦见过很多很多的胎盘。阿丫弱弱地说。
是吗?那太巧了。我说。
它们不是黄色,是光彩的艳丽色,它们更像蝴蝶。它们确实也能飞,不过它们飞得都不高,它们只在人的周围飞,一个人有多大,它们就绕着人飞多大的圈。偶尔飞到人的头发尖上,偶尔飞到人的耳边,还有的时候飞进人眼睛里,还有的时候顺着人的呼吸进入人的体内。梦里,人的肚子里全部装着胎盘。人不愿意消化它,人越长越大,越来越膨胀。最后炸裂,肚子里的胎盘全部喷出来,那个人最后也变成了一个新的胎盘,盘旋在下一个人的周围。梦里,一个人的死代表一个胎盘的重生。阿丫低头喝了一口蜂蜜水。
阿丫,你在梦里飞了吗?
我挤不进它们。它们嘲笑我,我试过好几次,我不愿被它们嘲笑。我需要它们,或者说是需要它们那种茫目的生和茫目的死。我想我是不是太重飞不起来,于是我把我的一只脚和一只手卸了下来,还是不能飞。我又把我的另一只脚和另一只手卸了下来,我只要那双有力的翅膀带我飞,还是不能飞。我不能再从我身体上拿走什么了。它们嘲笑我,它们的嘲笑声像利箭一样扎着我的心,但我不疼,我在梦里挣扎,结果被人吵醒了。
谁?
阿丫停顿了好久,我以为阿丫不想说是谁,阿丫却说了。
那个该死的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人。
阿丫。尽管我知道阿丫身体还很虚弱,我还是厉声地喊出了阿丫的名字。
你不应该这样说自己的妈妈。
为什么?
她是你妈妈。
阿丫顿了顿,似乎在重新审视“妈妈”这个词语。那次她站在我床前,奇怪地看着我。我问她,什么是胎盘?她说,如果你想认识胎盘,就得自己有个胎盘。我说,梦里我都变不成胎盘。她说,那是你自己没有拥有过一次自己的胎盘。后来,我拥有了一个胎盘,那是在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她把我送进了一个男人的被窝悻悻离去之后。
阿丫又喝了一口蜂蜜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之间有一段长长的静,这种静密不透风,让人窒息。
或许你那次手里拿着的胎盘就是在我身体里成长起来的。阿丫的话像把刀子,割破了静的同时,伤到了我。
阿丫闭嘴,我立刻制止住阿丫,我又想吐了。我冲进卫生间,狠狠地干呕着。我吐不出什么,阿丫这几天的差状态,让我吃不好饭。我干呕着,全身的血液都在膨胀。剧烈的干呕,我的胃部隐痛起来。我扶着墙,憋着自己。这种方法起初没什么效果,后慢慢把我的干呕缓解了。
阿丫从软沙发里坐了起来。阿丫身体里我认为丢失的一部分东西在慢慢回到阿丫的体内。
我见到它了。
它是谁?
那条打转的狗。
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
不可能。
确实见到它了。
时间,地点都不对。
是呀,都不对。
我前面说过,阿丫引起我注意是因为那条狗,然而那时我们还在读初中,离现在已经时隔十多年了。只因我说地点上不对,是因为我们读初中的那个小镇离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至少有三百多公里。一条狗能穿越三百公里的路程来找到曾经的主人?况且还是十多年之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见到它的时候,它离我远远的。它想靠近我,但显得迟疑。我看了一眼它,又把头转了回来。它曾经脏兮兮的绒毛变得更加脏兮兮,而且有些发黄。无意间看见它的那一眼,我没认出它。我继续走我的路,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我反复质问自己,自己是怎么了,为什么看见一条狗会让自己这样心慌意乱。我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答案的自己更加心慌自己。再看一眼,就只看一眼。我在心里鼓励自己。虽然鼓励自己,我还是迟迟不敢转过头去看它。我又一次问自己,阿丫你在想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一遍一遍地拷问自己,像把自己拿在火上烤一样。我全身燥热,心脏一次比一次跳得快,快到仿佛那已经不是我的心脏了,它快蹦出来了,就快出来了。就在我无法控制自己心脏乱跳的时候,我一下把身子转了过去。那么迅速,那么果断,那么连自己都吃惊自己地转了过去。我和它的眼神撞在了一起,那种碰撞有种从心里面升起来的疼痛感。是我撞到了它,它猛地往后退了一步,然后惊慌的在人群里为我转了一个圈。那是本能,就像以前它见着我,为我转圈一样。转完一圈,它再不转了。它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愣在那里。就是它,那双眼睛骗不了我,虽然那双眼睛和以前有区别,它浑浊,眼角通红,仿佛随时会从眼里流出血泪来,但是我依然能从它浑浊的眼神里看出当年的深邃。什么都可以骗人,那熟悉的眼神永远骗不了人。我第一次在大街上遇见它的时候,它也是这种眼神。我爱这种深邃又惊慌的眼神。
不可思议。然后呢?
我他妈的就变成了一个十足的疯子。我突然害怕。我不知道那一刹那钻进我心里的害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总之,第一时间我就想到逃离,像逃离自己制造的一个车祸现场一样。在我极速转身离开它的那一刹那,我恍惚又看见它在为我转圈,那种笨重的、老态龙钟地转圈,难看的样子让我全身起鸡皮子疙瘩。它的老让我感到羞耻。老太难看了,而它还在用那么老的身体在我面前不知羞耻地转着圈,像一个为我展示自己老的小丑。它不应该这么做。它应该藏起它的老,别出来丢人现眼。况且我相信它用它那难看的身体为我转出来的环形,也不怎么好看。我迷恋环形空间,我对环形空间有自己近乎洁癖的完美要求。那时,它是在破坏我对环形空间近乎苛刻地完美认知。它是故意来破坏我的认知的,它不怀好意,它很清楚我十多年前为什么让它滚蛋儿,就是因为它在我面前连续两天不能为我转出好看的环形了。我让它再别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它。但它又来了,还在我面前用它那臃肿的身体给我转圈,我恨它。我边骂它,边转身加快脚步逃跑了。
你不应该这样做。听完阿丫的讲述我伤心、难过。我回忆起那条狗。
后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觉得背后有双眼睛盯着我看,我不想回头。不想看见让我羞耻的一种老。
我不想再听下去,站起来,独自走到阳台上看外面世界的黑。这个夜比以往我所有看过的夜都要浓厚。我想到裹挟这个词。我们都是裹挟在滚滚黑暗里的人,被碾压,被抛弃,被丢失。
阿丫,有几次我看见你不开灯,静默地站在阳台上,你在想什么?
想死。
为什么?
我总是有种冲动,想划破夜的黑。无论用什么方式,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夜很美。你曾经给我说过。
是呀,夜的美在于它有黑暗陪着。不过夜里的公路很好看。
听阿丫这样说,我才注意下面的公路。
我从来没认真看过那条在我家楼下生长起来的公路,白天它们引不起我的注意,晚上那扇轻薄的白纱帘又把它掩盖了。此时,有几十辆车在公路上行驶,它们微弱的灯光照亮了镶嵌在黑夜里的公路。
它是环形的。
阿丫,你对环形的好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呆在老家的一口老井里开始的。
老井?
它陈旧,破败,让我彻底绝望和无法逃脱。
看来你从小就是个野孩子。
是她把我扔进去的。只因我看见了一件她不愿意让我看见的事。我把那件她在房间里干的破事喊得全村人都知道了,所以她把我扔进了那口没有水的老井。起初我试着想逃出去,我用尽全力在一口老井的墙沿上攀爬,手和脚都磨出了血泡,终将没有成功。我对着一口老井坚硬的墙壁呆了三天,恐惧又绝望。为了排解自己低落的情绪,我在井底画圈,一次次地画,画不好就擦掉,又重新画,又重新画,从小到大地画,一个垒着一个地画。我一遍一遍地画那个环形的圈,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阿丫这个圈就是你走出去的圈,阿丫这个圈就在你的脚下,阿丫你就快到圈的边缘了。从那时起,我就迷恋上了环形的一切事物。我对那种封闭环形的东西有着来自本能的认知和要求,是它救了我。而且到最后,我还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密闭的环形空间里重蹈覆辙却又自欺欺人的人。
阿丫是怎么出来的?阿丫在那三天的井底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不敢再问下去了。我发现我比阿丫胆怯、懦弱,连触碰曾经阿丫经历的勇气都没有。
那天我们买大闸蟹,它又隐藏在离我们不远的人群里。我感觉到了,就在我挑选大闸蟹的时候,我假装埋头看见了它。它披着一身老的皮毛,夹杂在人群中深情地注释着我。那天有你在,我想立刻逃离的恐惧感莫名地减低了,我们还逛了街,我在做大闸蟹的时候,还开心地哼起了我和它当年在一起时常哼起的小调。哼着哼着,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哼着哼着我的心就破碎了。我打开家门,冲进夜里,我感觉那时我想把我的一切苦难在一片夜里铺展开来,让夜帮我融化。这一生,我到底在经历什么?那口黑井在我心里越来越深邃,我在井底画的圈一次次出现在深黑色的夜里。这些年,我一直在逃离自己,逃离我那个亲情沦陷的城市,自从看见那条狗之后,我才明白我在做一件多么愚蠢荒唐的事,我什么也逃离不了,所有的东西只是暂时被我规避到我不想触碰的一个角落里,一旦被打开,它们就会潮涌般从我的内心喷发出来。我就像个傻子,傻傻地活在世界上。我想死。想死的想法很多年前就根植在我的心里,我却没有去死,我苟且地活到了现在。我可怜自己。当发现自己都在可怜自己的时候,我悲哀到马上就不想要自己。
阿丫,从过去中走出来,那只是过去,不属于现在。
唐颖,你是不是说过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你说过对吧?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阿丫突然摇晃着我,她那么迫切地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
是的,我说过。
那我也算有勇气死过一次的人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曾告诉自己一定要去死一次。我做到了。阿丫如释重负,她整个人看上去都轻松了不少。
对,你做到了。从阿丫轻松的样子看出来,死对于阿丫来说,像一个魔咒,这些年她被这个魔咒困扰着,阻碍着,没有勇气反抗,没有力量好好地活自己。如今她终于打破了死的魔咒,阿丫终于可以放松自己,好好地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了。
唐颖,我想我再也不怕环形空间了,我已从那口深井里爬了出来,外面阳光明媚。阿丫快乐地说着。
我喜欢阿丫快乐的样子,像我遇见最好的夏天。
后来,阿丫说她疲惫了。她今晚想好好地睡个饱觉,把这些天没有睡够的觉统统找回来。
晚安,唐颖。
阿丫,晚安。
那是我给阿丫道的最后一次晚安。
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阿丫已经收拾好她所有的行李,离开了我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住所。在她写作的书桌上留着一张粉色的便签条,上面写着:我要带着老狗的老回到让我逃离多年的城镇。
便签条旁边有一摞厚厚的打印纸,封面上用三号字体打印着四个醒目加粗的宋体字:环形空间。再往下翻一页,是阿丫的亲笔字:
献给我的朋友——唐颖。
原刊于《青年文学》2021年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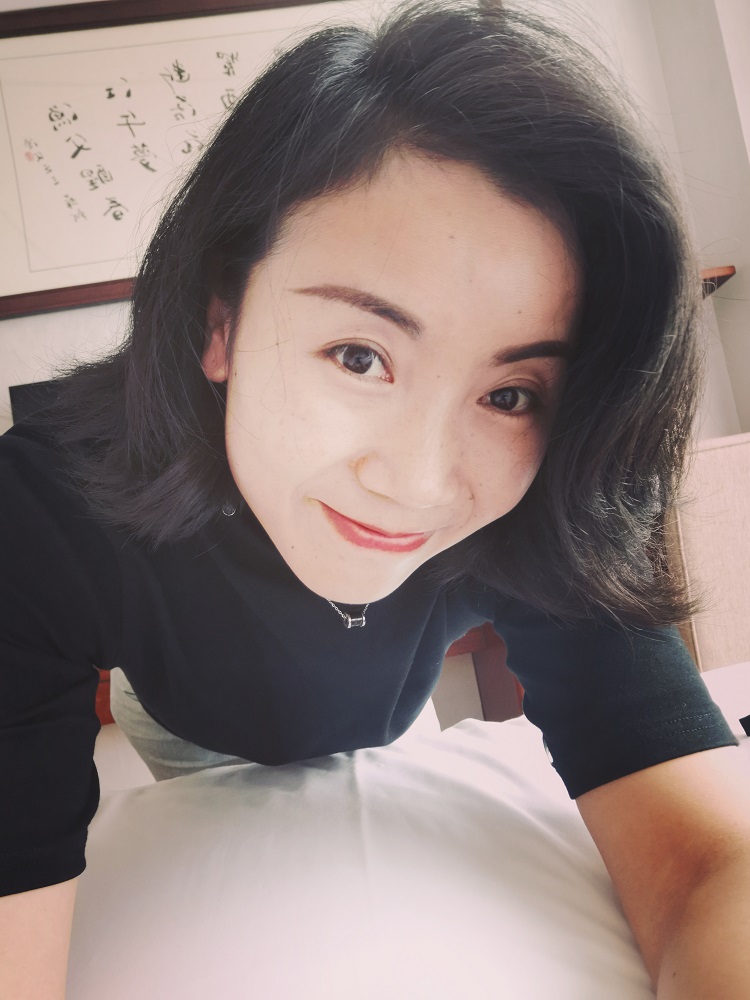
雍措,女,藏族,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小说、散文作品发表于《十月》《花城》《青年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期刊,收入多个选本。出版散文集《凹村》《风过凹村》。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第三届“三毛散文奖”等。






















